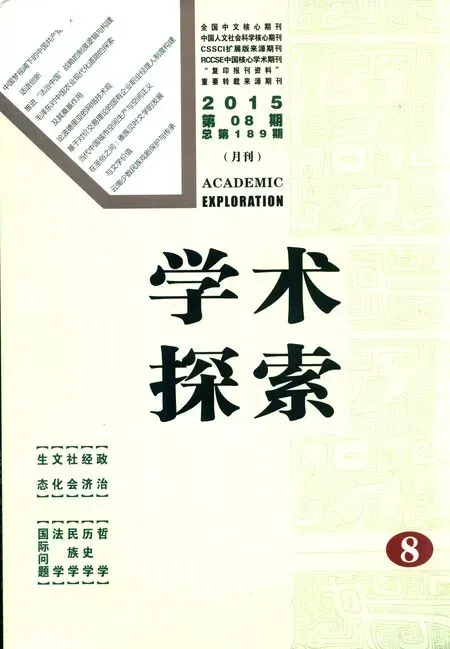在圣俗之间:傣族贝叶文学的发展与文学价值
黄方方,陈孟云
(1.云南财经大学 国际文化学院;2.云南财经大学 传媒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1)
在圣俗之间:傣族贝叶文学的发展与文学价值
黄方方1,陈孟云2
(1.云南财经大学 国际文化学院;2.云南财经大学 传媒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1)
傣族贝叶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宗教的“神圣”到市民的“世俗”,最初佛教的传播需要借助文学塑造感人形象感化教育人们,以《苏帕雪》和《佛教格言》为代表的佛教典籍借助佛教里的哲学思想提升和整合了傣族文化;随着傣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佛教经典文学不能解决人们社会经济发展及思想困惑时,预示着佛教经典文学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傣族市民文学出现,以《宛纳帕丽》《楠波冠》等为代表的市民文学出现,预示着世俗化文学时代的到来,但真正实现佛经文学走向世俗化的是佛本生经《召树屯》文本进入汉语文化圈所产生的文化流变,在民族文化融合中形成以孔雀文化符号为代表的傣族文学。
傣族贝叶文学;神圣与世俗;孔雀文化符号
中国傣族是一个文明而古老的民族。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划分,傣族群分别属于两大文化圈,分别是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文化圈和信仰原始宗教的文化圈,从宗教信仰、分布区域、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划分为:澜沧江流域的佛教文化圈和红河流域的原始宗教文化圈。前者主要指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孟连县、景谷县、德宏州在内的傣族支系,民俗节庆主要有佛教文化内涵的泼水节、开门节、关门节等,在佛教和印度文学的影响下创造了“贝叶经典籍”又称傣族贝叶文化;后者主要指云南红河流域的元江和金平县内的各“花腰傣”族群,“花腰傣”普遍信仰天神、祖先神灵及其他山川河谷神灵的原始宗教,节庆有春节、中秋节、中元节等,其文学几乎都是口头传承,保持发展和传承了傣族古老的口头文学。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不同文化圈里的傣族文学差异。澜沧江流域佛教文化圈的傣族创作的贝叶文学,文学样式多样,数量众多,史料记载有八万四千册,成为中国西南地区三大经籍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
一、“由俗入圣”与“圣俗一体”
傣族佛经文学世俗化现象表现在佛教的传播需要借助文学塑造感人形象感化教育人们,佛教与文学的融合产生佛经文学。傣族在最早介绍引进佛经故事时就完成了地域化,即作品里的佛祖人物艺术形象获得傣族文化的身份认同。印度佛经文学引进过程与傣族文化碰撞交融,从而形成新的文学样式,比如傣族佛经故事《佛祖巡游记》是以生活在傣族地域文化里的“佛祖”为主体建构而成的鸿篇巨制,通过佛祖巡游活动讲述傣族文化的渊源:他给山川河流、草木森林命名的典故甚至民众生活习俗的形成和他的故事息息相关。傣族地区流传的“佛祖”生平故事,既有佛经文学的神圣感同时又具有傣族文化身份认同感,两者交融并存。《佛祖巡游记》从传入到成为该地区佛教经典,在傣族民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为何这部作品会成为经典?主要原因是,佛教与傣族文化有机融合并借助文学的特殊功能来宣扬佛教教义,因而佛经文学首先是文学其次才是佛经文学。《佛祖巡游记》记述了佛祖的前世和今生,通过佛祖生命里历经的苦难和顿悟过程叙事讲述一代宗师在逆境中成长的故事,作品以丰富的内容、曲折的情节和丰满的人物形象及真挚的情感而触动读者心灵。早期宣扬佛教的佛经文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巧用命运多舛的人物形象编织感人的故事,在触动读者心灵的同时营造了宗教的神秘感和神圣感。德国宗教哲学家鲁道夫曾阐释“神圣感”为,“是一个宗教领域特有的解释范畴”。[1](P3)宗教神圣的内涵通过文学叙事对读者阅读产生教育功能的心灵效应,宗教神秘感在读者接受时心理油然而生“畏惧感”,甚至会在主人公超自然的神秘力量面前产生崇拜的心理现象,“神圣感”驱使崇拜者会在超自然的神秘力量面前顶礼膜拜,进而佛经文学的“神圣感”在流传过程中往往能起到震慑心灵的教育作用。这在法律制度尚未健全,社会秩序需要依靠宗教道德意识来约束的古代起到积极的作用。由于“神圣感”与崇拜者之间会产生心理距离,因而佛教文学又将故事浸泡在世俗生活中,让人物形象有血有肉具有生活的真实感。从佛经文学的特殊双重性看,早期作品中影响力较大的一部是《维先达腊》,这部作品使佛教核心思想“赕”在傣族地区的传播深入傣族民众人心,“赕”是西双版纳傣语的读音,它源自梵语,汉语翻译为“檀”,“檀那”是布施、奉献之意。南传佛教的基本教义在理论上仍然是以“四谛”“轮回”“十善”为核心。“四谛”是佛教最初成立时的总纲,以后一直是佛教核心思想,“四谛”是指:苦谛、积谛、灭谛、道谛。“苦谛”指的是生老病死的痛苦;“积谛”是解释痛苦的原因,是因为人的欲望造成苦恼和邪恶的因素;“灭谛”指的是消除痛苦的原因,断绝苦果的途径和方法;“道谛”指的是消除痛苦断绝苦果之后所必然要出现的或要达到的理想境界,既永生的“涅槃”。南传佛教信仰中最显著的一个行为就是“赕”。佛教认为由此岸到达彼岸的方法途径有六种,又叫“六度”,“六到彼岸”在汉语里翻译为六波罗蜜。“六度”之一就是布施,又叫“檀那”。南传佛教认为,布施可以破除个人的吝啬和贪心,从而免除出世的贫困。南传佛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并把它推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布施是针对佛的,因而称其为赕佛。傣族的佛教活动几乎是围绕着“赕佛”开展的。为强化民众的信仰热情,南传佛教宣扬了“做赕”的好处,以至于“做赕”成为西双版纳傣族佛教信仰的最重要和必不可少的义务。据说,在西双版纳建了佛寺有了“帕召”、有了佛爷就要开始赕佛。“赕佛”是如何成为傣族文化的核心内容,“行善,布施,修来世”的思想是如何深入人心的?这和《维先达腊》这部文学作品的流传有着一定的关系。这部作品在傣族佛经文学里具有代表性,它通过人物形象遭遇厄运和苦难的经历来阐释佛教行为“赕”的诸多好处。伊格尔顿认为悲剧在人类社会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作为人类社会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表征着社会变革和历史转型。佛教的传入仅仅是僧侣们的说教就能深入人心吗?如果没有生动的文学故事和人物遭遇厄运的悲剧因素的故事,是不能打动人心接受教义的。这部讲述维先达腊怎样成长为南传佛教忠实信徒的故事内容主要是为宣扬赕佛思想,感人至深的不是贯穿其中的宗教道德意识,而是作品中的人物悲剧命运。整个故事情节最扣人心弦的是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悲剧效果超越了宗教的枯燥说教,维先达腊的悲剧命运引发读者的阅读共鸣,人们在阅读过程中激发了内在情感,达到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悲剧往往能引起读者的恐惧与怜悯之情,悲剧能够借助于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来使人们的灵魂得到净化和陶冶。主人公维先达腊身上一件接着一件的苦难事件发生,所产生的悲剧效果比单纯说教更能深入人心。从傣族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发生的个人人生苦难,维先达腊由于赕的行为让他遭受了不应遭受的厄运。自然引起人们对于他的怜悯之心,但同时也加强了人们对于赕的行为认识,这是由这个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而引起的。人物形象厄运才是构成悲剧的重大因素,悲剧中的受难形式往往是一般观众获得强烈心灵震撼的来源。布拉德利认为厄运纳入到命运观念的轨道悲剧更具震撼力。在他看来,悲剧都是偶然的意外事故在起作用。作品中另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潘”是个集贪婪、狡诈于一身的市井小民形象。由于“潘”的阴谋致使维先达腊遭受磨难,先是失去国家带着家人流亡于森林,再接下来就是失去孩子和妻子,最后年老病多孤苦一人以致感动上天让他重返家园。叔本华认为悲剧世俗化是悲剧剧情常常与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它能引发人们对于人类普遍命运的理解。维先达腊的故事是围绕傣族民众自身承受的痛苦以及如何摆脱这种痛苦展开的,而这一点刚好吻合了佛教认为人生是痛苦的,人生最大的痛苦根源在于人的欲望,而人的欲望又是永远不可满足的渊薮,所以人生的本质是痛苦的,解决人们精神痛苦的一剂良药就是—赕,通过赕的行为来达到心理调节的作用。傣族悲剧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人生痛苦,使得人们认识到人类的欲望带来的精神痛苦,悲剧因素在文学作品里表现出的是生活里彼此斗争,相互摧残,因而维先达腊人生悲剧的结局不是悲剧冲突双方斗争的解决,而是斗争的双方在认识中对生命意志的否定。《维先达腊》跳出了以前固定不变的道德架构,变为苦难与精神危机之间更具活力的关系。通过人物形象的悲剧行动展现苦难正是为了超越苦难。维先达腊在历经了世间所有磨难后,才宣扬佛教道德要通过“赕”的行为才能让普通人去获得纯净心性,这是人类道德的终极源泉,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以《维先达腊》为代表的佛本生经故事成为傣族文学艺术的启蒙作品。
二、“雅俗共赏”到“由圣返俗”
傣族高僧在翻译佛教典籍时借助佛教里的哲学思想提升和整合傣族文化,通过语言文字表述形成了傣族文化经典,比如傣语版本的《苏帕雪》《佛教格言》等。《苏帕雪》里除了收集傣族格言、警句、俗语、箴言以外,还有形象生动的寓言故事。这些寓言故事有些和印度语言故事相似,有些完全是傣族本土的故事,通过动物故事、断案故事、机智人物故事等的精彩叙述,通过鲜明的人物艺术形象来揭示生活哲理,借文学宣扬宗教教义。在古代法律欠缺的时代,宗教道德起到教育和警戒的作用。例如“酒的罪孽”劝解过度饮酒的危害;“和丘比争吵的故事”告诫人们如何与僧侣相处;“挖银坑”故事告诉人们如何对待物质欲望和财富。这些形象生动的世俗故事直白甚至赤裸裸地讲述世人对于物质生活的利益追求和生活享受,启示人们生活中处处皆有生存智慧,因而特别关心交友之道,甚至通过动物之间的关系反映出傣族村社中的人际关系,指导个人在集体中如何避害趋利,如何生存的法宝,提倡不轻信和不冒失,尽量去结交对自己有利的朋友,甚至尽量避开或讨好有权有势者,提倡弱小群体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强敌等观点。从上述故事可以看到,这样的智慧和世故是从市井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因而具有较强的生活经验和直观感受,可以说字字珠玑,是饮食男女们永远值得铭记的生活智慧。在叙事技巧上则采用了民间故事里常用的手法,即大故事里套着小故事的连串插入式结构,把各种故事环环相套,既错综复杂又浑然一体,这种形式与印度和阿拉伯民间故事结构很类似。
随着傣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佛教经典文学不能解决人们眼前出现的思想困惑时,预示着佛教经典文学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傣族市民文学出现,以《宛纳帕丽》《楠波冠》为代表的市民文学出现,预示着世俗化文学时代的到来。文学作品里人物命运就会出现悲剧,悲剧可能是令人痛苦的,但是痛苦之后带给人们的是心灵震颤甚至还有恐惧感。产生悲剧的根源是什么?人物为何遭此厄运或不公平的命运?一部出色悲剧令人鼓舞的品质会引导人们去寻找原因,会去引发人们思考是人为的还是历史的?或者社会的还是宗教的原因?当圣人故事的文学魅力减退时人们会把注意力放到小人物身上,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小人物的生活不比圣人简单,他们身上依然有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他们身上有着同呼吸共命运的心灵感应。经典退潮,小人物登场,这时,市井文学形成。市井文学往往是在封建社会由昌盛时期走向没落的时期出现的,之所以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因为主人公的反封建意识和文学作品本身的基本主题就是反封建的。市井文学是封建社会后半期出现的。封建社会城市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兴市民阶层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于是前期的文学就被市民阶层意识的文学所取代,至此表达市民思想情感的市井文学产生了。所谓世俗化,从文学创作和表现形式来看,是相对于第一个文学发展的宗教信仰的性质而言,世俗化就是非宗教化和平民化,它主要的特征是关注当下现实生活,以生活中的市民为主人公,文学不再以创世神和英雄为主要人物,民众成为文化创造的主导力量,也成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的主体。傣族三大悲剧《宛纳帕丽》《楠波冠》《娥丙与桑洛》均是在封建社会后半期出现的作品,是悲剧艺术表现手法成熟,从叙事技巧看已经达到成熟的小说。傣族市井文学的出现预示着小说创作技巧的成熟,而且创作出了一些反映时代的优秀作品。傣族市井文学和汉族市井文学一样,基本主题是反封建的。但和西方不同,傣族市井文学反封建的矛头主要不指向宗教教权,而是指向封建等级、封建特权、封建伦理道德。和前面的文学相比较,市井文学没有过多地受到封建道德和宗教思想的束缚,作品里的人物通过勤劳经商等生产活动来改变社会地位,他们勇于追求情爱以冲破宗教禁欲主义,追求纯真爱情的婚姻以冲破封建等级门第观念,同时对于封建达官贵人辛辣嘲讽和毫不留情地给予揭露。这样的出发点,决定了市井文学的写实精神和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比较贴近寻常百姓生活,作品里的教训口吻减少,即便是体现教育意义也是通过悲剧的形式让读者去感悟,文学的娱乐功能成为主导。这个时期的文学,市井百姓甚至底层的贫苦人民成为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市井文学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文学,它的对于传统的叛逆,思想的革新与守旧都体现了由宗教造就经典的古代与近代之间的过渡时期所具有的复杂而矛盾的时代特点,为下一个时代文学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三、跨语际流变:佛经文学的文化重组
进入汉语文化圈,在跨语境跨文化交流中再次文化重组,傣族文学以新的姿态融入当代文化视域中。傣族文学出现世俗化的最为重要的案例是一部佛本生经的文学作品如何被汉语整合,进入到汉语文化圈。这个跨语境跨文化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一部普通的佛经文学作品,经过汉语整合后不仅成为傣族文学经典,而且还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这部作品就是《召树屯》。傣族文学里名叫《召树屯》,汉语翻译和整理后叫《孔雀公主》。
这个佛经故事在傣族地区广泛流传,时间长久,深受傣族民众喜爱。它最早源于佛教传入傣族地区时期的口传文学。随着傣族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傣族文字的出现,贝叶开始运用于刻写经文并成为重要的书籍形式。由于输入渠道多样化,因而民间流传异文较多,依照文学分类方法来看,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民间口传故事,又称为口头文本或口传文本,是主要存在于民间艺人和歌手脑子里的“大脑文本”,是存在于活形态的口头流传样式,名称多样,有的叫婻兑罕,有的叫诺娜等;二是篇名为《召树屯》的傣文版本,主要收集在我国云南傣族地区佛寺藏书贝叶经集子里;三是源于口传的民间歌手赞哈演唱的手抄本,又称活态史诗文本。就目前收集整理和发现的资料,把《召树屯》类型故事多种版本进行梳理,以时间为线索来看,有原始歌谣、神话传说、散文体韵文等体裁。其流传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歌谣→神话传说→散文体韵文。由于傣族贝叶经被称为“刻在树叶上的傣族文化”,因而在另一层意义上讲,《召树屯》传说故事又被称作傣族喜爱的贝叶爱情故事。它不仅是我国傣族文学所独有的宝贵文献,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作品之一。为何佛本生经会转变成傣族文学里的爱情经典之作?《召树屯》属于世俗经典佛经故事,它在傣族民间流传了上千年,最早源自佛教徒口头传播,后经历了滚雪球般的发展,到公元6~7世纪基本定型,以诵经、民间艺术赞哈说唱等形式,在傣族地区广泛流传至今。通过傣族历代民间流传,最终,民间的理想和最具代表性的英雄性格集中在召树屯一人身上,并使这一民族精神表达在流传过程中得到强化而逐渐定型下来,形成了一个具有极强凝聚力和包容性的箭垛式的人物形象。从召树屯艺术形象在民间的流传过程看,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本民族社会历史和民俗文化的一面镜子,是本民族人文思想的发展足迹,能以文学的真性情谱写本民族的心灵史。
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民歌运动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出现划时代的嬗变,著名少数民族理论家关纪新用“狂潮涌起”这个词来形容少数民族文学在新中国所受到的重视。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代文学领域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拥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同时也完成了历史性的超越。在这样的背景下,傣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保护和挖掘,《召树屯》就是在这股春风里被世人所认识的。回顾历史,对傣族民间文学资源的重视和保护工作,是以在傣族民间收集《孔雀姑娘》文本为开端的。以新中国少数民族文艺政策为指导思想,部分生活在傣族地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汉族文人出于对傣族文化情感上的认同,自发地深入傣族民间收集整理上述文本并翻译成汉语文本。这一行为,对于推动傣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于是,经过汉族和傣族文人共同整理的文本,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独具民族风格美的艺术样式,打开了傣族文学的界面,让傣族风格的文学作品丰富和充实了中国文学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傣族文学作品在翻译过程中(和所有译介文学一样)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作品由于跨越傣语到汉语语言翻译过程中流失了一些傣族文化元素,加上不同程度地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使作品名称和内容都发生了微妙而有趣的变化。所以,文本名称才会由《召树屯》演变成《孔雀公主》。但是,在傣族民间更为民众接受的是召树屯,而进入汉文化圈,接触到的却是孔雀公主。从傣族民间文学收集整理过程总结经验,似乎可以梳理出傣族文学进入汉语文学世界的意义和价值:
《召树屯(孔雀公主故事)》是以民间故事的形式为全国读者所认识的。由于该故事在傣族民间异文较多,因而收集到的文本也出现了不同的版本,主要有三种版本:第一个版本是作家谷青等人在西双版纳和思茅傣族地区收集、翻译和整理的文本,重新命名为《孔雀姑娘》;第二个版本是当代著名作家白桦根据傣族民间赞哈演唱本《召树屯》创作的现代抒情长诗《孔雀》;第三个版本是岩叠、陈贵培、刘绮、王松等人整理的叙事诗《召树屯》。版本多、形式多样化是这一时期处理少数民族文学时常遇到的共性,不仅傣族文学是这样,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也是这样的。源自同一母题的汉语版本傣族文学作品与读者见面后,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扩大了读者群体。例如,作家谷青等人整理的民间故事《孔雀姑娘》,在《思茅报》上发表后备受读者的喜爱,在读者的呼吁下又出版了单行本。王松等人整理的叙事长诗《召树屯》因遵循傣族叙事诗原汁原味的风格,虽然不像民间故事那么吸引读者,但是却保留了傣族古歌谣和叙事诗的特征,对于解读傣族古歌谣的叙事技巧和艺术特征,具有重要的文学研究价值。白桦根据自己所收集的民间故事内容进行再创作的叙事诗《孔雀》,在傣族叙事诗的基础上,大胆地运用了大量现代诗歌表现手法,甚至运用汉语思维方式和汉文化意识形态再构建文学框架,让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具有个性张力,增加了戏剧冲突,张扬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充满了现代意识和现代文化元素。因而这个版本的作品促使傣族文学脱离母语创作而走向汉语创作的现代性之路。
四、百年嬗变:新媒体孔雀文化符号
《孔雀公主》汉语文本出现后,这一题材的故事随即进入舞蹈艺术领域。《孔雀公主》因舞蹈艺术的魅力而迅速地被广大群众所接受,更主要的是舞蹈语汇传达了古老的傣族文化符号。在20世纪60年代,最早关注该故事并将其改编成舞剧的是我国著名傣族舞蹈艺术家刀美兰。以刀美兰的舞蹈天赋扮演孔雀公主这一角色并通过舞剧的艺术感染力,使观众感知到了这部作品的内容。刀美兰的非专业舞蹈背景,反而更好地把傣族民间原生态舞蹈肢体语汇和民间舞蹈的特色带到舞台艺术上,从而促进了民族舞蹈艺术化的进程。更重要的是,刀美兰在创作舞剧时向民间汲取了艺术营养,她到古寺观察壁画上的孔雀公主故事绘画,把傣族先民留在壁画上的文化符号记录下来,巧妙地用舞蹈肢体语言展现给观众。舞剧这种更加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推动了民间故事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全国人民逐渐认识了这部优秀的作品。到了20世纪70年代,舞剧再次受到关注,杨丽萍成为第二代孔雀公主的扮演者。云南省歌舞团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文工团在刀美兰创作的基础上再次改编创作了大型民族舞剧《召树屯与婻穆诺娜》,并在国庆30周年给祖国献礼演出中获奖。舞剧女主角婻穆诺娜由杨丽萍扮演的版本强化了故事情节,增强了戏剧冲突。但由于受到现代舞台艺术的影响,虽然视听效果增强,但傣族文化元素反而被弱化了。2000年后,作为舞蹈艺术家的杨丽萍先后创作了一系列以孔雀为主题的舞蹈作品,如《雀之灵》《两棵树》《孔雀》等,无一不是受到傣族文学和傣族文化滋养后的结果。进入影视媒体的《孔雀公主故事》,艺术语境由传统向当代转换。这部作品被电影艺术家发现,经过编剧改编并搬上了银幕,从而使傣族题材的故事在汉语文化圈进一步被广大观众接受。首先是20世纪60年代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改编的动画片《孔雀公主》,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80年代著名作家白桦将自己创作的长诗《孔雀》改编成电影剧本《孔雀公主》并搬上银幕,在全国人民心中塑造了美好的“孔雀公主”形象。
至此,《召树屯(孔雀公主故事)》在民间口传趋于萎缩,被舞剧、木偶剧、电影等艺术形式所替代。故事情节在改编后的艺术形式中创造了湖边邂逅、新婚离别、远征他乡、祭坛飞离、千里寻妻、夫妻团圆等情节模式。由于舞剧、电影的传播深入人心,给民间传说的生存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使孔雀公主故事情节固定化,原来在民间流传的多种多样的故事情节,逐步向舞剧、电影故事情节靠拢,变得单一化、模式化了,原生态的传说面貌逐渐变形;另一方面,使傣族民间传说失去了传播和传承的市场和渠道,在傣族民众的记忆中逐渐淡化。当下,随着对少数民族文学的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推进,贝叶经重新得到收集整理出版。一些学者、专家挖掘出了与文学故事有关的文献和失传已久的传说片段,使《召树屯(孔雀公主故事)》重新绽放出灿烂的光芒。新出版的《中国贝叶经全集》就收录了《召树屯》,而且兼顾到广泛的读者群,采用了傣文、汉字、英文对照文本,使得读者能够阅读到贝叶经中的经典故事。在全球化背景下,特别是随着当代通俗文化的兴起与蔓延,客观上影响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发展,傣族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一样面临着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剧烈的变化。一部古代的《召树屯(孔雀公主故事)》的流传演变和文化传播过程,其从原生态类型到再生态类型再到新生态类型的发展变化,反映出时代变迁使传统的口传原生态《召树屯》逐渐衰亡的过程;经过整理改编,转化为书面或其他艺术形式的民间文学形式(如赞哈)仍然在傣族民众生活中流传的事实,折射出民族民间文学在当下的挣扎;经过影视手段变形后的《召树屯》,重新走进千家万户,比以前传播更为广泛,使读者了解到傣族的独特文化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它有别于儒家文化传统中的人文精神和思维方式。探寻这一思维方式又与汉族的“寻根文学”有着相似的民族主义和多元文化思想背景。梳理《召树屯(孔雀公主故事)》百年嬗变,了解古代傣族文学里蕴含的鲜明的文学观念和极富于民族个性的文艺作品表达方式,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文学,对于中国民族民间文学的保护、传承,是一件对历史负责的有意义的事情。
[1]鲁道夫.奥托.论神圣[M].成穷,周邦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From Holy Religion to Public Secularity:Development and Value of the Pattra-leaf Literature of Dai people
HUANG Fang-fang1,CHEN Meng-yun2
(1.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s and Education;2.School of Media,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Kunming,650221,Yunnan,China)
The Pattra-leaf literature of Dai people has evolved from holy religion to public secularity.Buddhism first spread its ideas to educate Dai people with the help of shaping touching images in literature.Buddhist philosophy advocated in Su Paxue and Buddhist Mottoes,representative of the Buddhist classics immersed into Daipeople's culture to have them enlightened.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of the Dai,however,this literature could no longer help them with their ideological confusion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which also hints its educational role in history had completed and begun to withdraw.Under this background,secular literature with Van Na Pari and Nan Bo Guan as the representatives,appeared,and indicats the arrival of the stage of secularity in Dai's literature.But what really makes the Buddhist literature secularized is that“Zhaoshu Village”,a former Buddhist literature text became popularized in Han people's culture and made a great change in Chinese literature circle.This finally shapes the Dai's literature style with peacock as a cultural symbol.
the Pattra-leaf literature of Dai people;religion and secularity;peacock cultural symbol
I29
:A
:1006-723X(2015)08-0105-06
〔责任编辑:黎 玫〕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XZW030)
黄方方,女,云南财经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化、比较文学研究;
陈孟云,女,云南财经大学传媒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