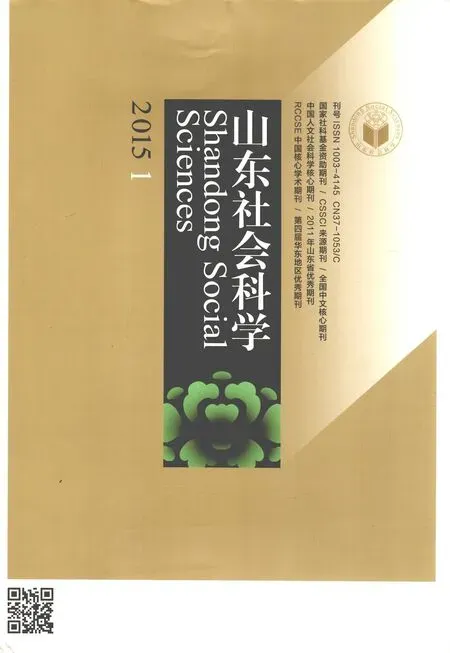关于包山楚简120~161号简的形制研究
裴乾坤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00042)
简牍的形制历来对简牍的编联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包山楚简中作为“一些案件的案情与审理情况的详细记录,以及呈送给左尹的情况汇报”[1]的第二类无篇题简,其形制问题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故本文将着重对此类简的形制问题展开研究。
此类简的形制中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契口的位置参差不齐,而参差不齐的契口位置将会带来编联上的不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是本文将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其二是此类简的长度有68~69厘米与64~66厘米两种,其长度差别高达3厘米左右,如果这些简被编辑成册,那么这样的长度差别将会是十分明显的,这种情况的成因,正是笔者将要在本文中着手研究的第二个问题。为便于讨论,笔者此类简文规格数据和摘要分列于下。其中68~69厘米的以下简称长简,64~66厘米的以下简称短简。
一、对于契口间距的研究
在简册编联的过程中,存在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即契口之间的长度差异,或称契口间距。若将契口间距较小的简与契口间距较大的简强行编联,则会导致编绳不能处于同一直线上,进而契口间距较大的简会在两道编绳产生压力下产生弯折。因此一般契口间距相近的简更有可能被编联在一起。因此本文将以契口间距作为是否能够编联在一起的依据之一。
在长简组中,简120~123与简126~128这两份记录的载体,虽然长度相近,其长度差在5毫米之内,但是两个契口间距有显著差异。简120~123的契口间距在32.8~33厘米间,而简126~128的契口间距在32~32.5厘米间,两者差异在5毫米以上,而简120~123三支简的契口间距差异则在2毫米以内。值得注意的是与简126~128内容类似的简12~13,其契口间距在31.9~32.5厘米间,与简126~128的情况十分类似。可见简120~123与简126~128不太可能编联在一起,反倒是简12~13与简126~128更有发生编联的可能。也就是说同为无篇题简的简120~123与简126~128,是各自编联成册的。
另外,有一些材料是记载在单独的一支简上,这些简上往往找不到契口。例如简155,单独记载了一个与安葬王士相关的案件,其内容并不与其它无篇题简相关联。很有可能一支简就是一份独立的记录。由于这种简不需要与其它简进行编联,因此在上面没有发现契口。除此之外,长简组的其他无契口简基本上都属于这种情况。而简128特别值得注意。简128与简126、127的内容密切相关,都记载着左尹等人命令羕陵邑宀大夫进行户籍核查的相关内容。但是简128是公元前317年夏之月癸卯之日由左尹发出的一条命令的记录。从这条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份命令中所具备的要素,如发令者(左尹及其助手)、执行者(羕陵大夫司败)、命令内容(查验户籍)、执行期限(夏之月己酉之日)以及不执行命令的后果(阩门又败)皆已齐备,故可视作一份完整的文书。这样记载在一支简上的一份完整文书,由于没有编联的必要,因此这支简上并没有契口的痕迹。
短简组中各简的形制也呈现类似的特点,简129~130的契口间距分别为30.7厘米和30.8厘米,而简145的契口间距为29.2厘米,也不太可能编成一册,而其他具有独立内容的单简都只有一个下契口,也不太可能编在一起。
但值得注意的是简131~139。虽然从内容上看都与这个案件相关,但契口间距仍然存在较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两种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材料的来源不同。学界一般将这批材料分为三个部分。陈伟先生认为材料的第一部分由简132~135组成,其内容是原告舒庆的诉状与左尹下达的重新调查此事的命令以及一份程序性记载;第二部分由简131、136和137三支简组成,其主要内容是汤公景军的调查报告;第三部分是由简138和139组成,主要内容是舒所提出的盟证参与人与左尹关于盟证的规范性批复。[2]李守奎先生虽将文书分为两组,第一组由简132~135和简131、136、137两份文书组成,第二组由简138、139组成,其对文书材料的基础分类仍与陈伟先生相同。[3]
这三个部分形成的时间很可能就不一样,如简132~135的形成时间当在简131、136和137之前,因为原告的诉状才能导致重新调查的开始;另外这三个部分也不一定由同一个机关制作,例如汤公景军的报告可能来自汤的地方官署,而其他两部分则有可能是左尹官署自己制备的文书。在这种情况下,材料的三部分之间出现一定差异是可能的。其次简册的制备过程会导致同一部分中也出现律了契口间距差异。例如第一部分四支简中,除简135外其他三支简的契口间距差都没有超过2毫米,但简135与其他三简的契口间距差却高达1.5厘米,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在简的制备过程中出现的误差。而简138与139之间存在的高达2.2厘米的契口间距差,笔者认为是在书写简139的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而使用了错误的规格所致。因为在简66和简68的规格与简139的规格相同。因而对于简131~139这份材料,应当视作几份独立文书构成的文书群。
综上所述,此类无篇题简的契口间距长短不一,但有规律可循,一份由若干简组成的文书,其契口间距大致相同,而不同的文书之间,契口间距会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反映了此类简在下葬之前,是以一份一份单独文书的形式存在着的,而并不如同睡虎地秦简《封轸式》那样被编联在一起,作为墓主个人使用的材料。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包山楚简很有可能是实际使用中的文书。
二、对于简的长度的研究
从内容上看,无论是长简还是短简,都记载了相似的内容。笔者暂且以是否明确记录争议为依据,将其分为案件记录和其他记录两种。例如简126~128的记载,由于其中并不存在争议点,因此将其归入其他记录类,而安葬王士案虽然简短,但由于其包含了鄢地方擅自任用左司马为丧客且征用了“五连之邑”,而作为告诉人的南陵公并不赞同此事这一争议点,因此这份记录应当被归入案件记录类。
现从案件记录出发。长简组包含了三个案件,分别记载于简120~123、简124~125与简155中。短简组包含了六个案件,分别记载于简129~130、简131~139、简141~144、简145、简151~152和简157中。
通过对短简组中六个案件记录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案件或为左尹官署直接介入,或为其他官署移交给左尹官署,或与左尹官署的业务直接相关。第一类案件如简131~139的杀人案,简141~144的出逃自伤案。简131~139中,记载了左尹与负责重新调查的汤公之间的文书往来。左尹官署并不仅仅是将案件交给汤公让其进行全权处理,简131、136和137组成的文书说明左尹仍需对汤公处理的过程进行掌握。在收到当事人舒提出的盟证要求和盟证人名单时,一方面向宛公发布为其进行盟证的命令,另一方面还以命令的形式发布了担任盟证人的限制条件。在这个案件中,左尹一直是一个十分积极主动的角色。而在简141~144的记载中,左尹及其助手则直接听取了争议双方的陈述。第二类案件如简129~130、简145和简156记载的三个案件。简129~130的案件是期思的地方官员直接将案件诉至左尹官署。简145和简156的案件分别是司马官署和陵尹移交给左尹进行审理的案件。简151~152记载的土地继承权纠纷属于第三类案件,此案中出现一个被称作左尹士的职官,很有可能与左尹官署有关,或为左尹官署中的某一职官。从这六个案件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案件材料都来自于中央各官署或地方官署,也就是说一般官署中日常使用的书写材料,当是这种64~66厘米的短简。
从包山楚简的其他司法类文书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规律。在包山司法文书中,其实长至68~69厘米的简非常少,大部分文书都采用短简书写。正如笔者在绪论中提到的,疋狱简、受简和无篇题简中的所简的长度都在64~65厘米左右,而68厘米以上的简总共只有32支,短简从数量上占包山楚司法文书简的83.6%左右,因此笔者认为这种长度在64~65厘米左右的简最有可能是以左尹官署为代表的楚国一般官署中日常使用的简。
那么,如何解释长简的存在呢?笔者认为还应当从长简中所记载的案件入手。在简120~123所记载的案件中,我们发现不了左尹官署存在的痕迹,这个案件从告诉到审理再到结案,左尹官署都没有介入。那么为什么这份案件会出现在左尹的身边呢?张伯元先生认为,“左尹之所以将此案收存在自己身边,是准备复查用的,不是单纯的档案收存。”笔者认为可从。但笔者进一步推测,这份材料很有可能是来自楚国专门收存文件的机关。
而简124~125所记载的案件则清楚的反映了左尹官署在获得这份文书后,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处理。在简125的背面有“为李”者的署名,并且还有文书正面所没有反映出来的内容,说明左尹官署在获得这份文书之后,对文书正文中所载事项进行了跟进。而这份文书的来源也应当是前述文件收存机关。
左尹如何从这一机关获得文书呢?笔者认为可能与楚王的命令有关。被冠以集箸言这一篇题的简15~17也是由长度在68~69厘米的长简书写而成。在这份文书的正面提到,五师宵倌司败的案件一开始是提交给楚王,而后来是楚王将案件移交给左尹处理的。也即“仆以告君王,君王仆于子左尹。”而后这个案件的处理并不为他所满意,因此他再一次提出告诉。而这次告诉的对象,在正文中仅仅写作“视日”,从前文可知,视日是一种通称,其指代的对象需要看具体语境。而从简16背的记载中,可知五师宵倌司败此次告诉的对象,仍是楚王。楚王在接收了这个案件之后,再次移交给左尹处理。如果存在上述笔者所推测的机关的话,那么来自五师宵倌司败的诉状应当是受这一机关所管理和收存的,进而接下来的案卷移交,也应该是由这个机关负责,而这个机关所使用的文书,可能恰恰正是这种68~69厘米的长简。
简153和154中关于疆界划分的记录,也体现了文书来源的不同而导致的文书形制的差异。这两支简都记载了“王所舍新大厩啻苴之田”的疆域,内容基本相同,只不过简154仅仅记载了疆域的四界,而简153还记载了这一疆域内六个邑的名字。从前面的表格中,可知简153的长度为65.1厘米,简154的长度为69.5厘米,分别属于短简组和长简组。笔者认为,简154当为专门的文书收存机关所收存的土地权利登记文件之一部分,而简153则是左尹官署在工作过程中,根据其具体需要而摘抄补充的文件。自西周时期开始,土地权属在进行变更时,都会进行土地边界的勘定,这一做法体现诸如散氏盘、五祀卫鼎等诸多青铜器中。根据《周礼·春官·大史》“凡邦国都鄙即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约剂乱,则辟法”,又《周礼·秋官》“凡民之约剂者,其贰在司盟”,说明周人会在官方设立管理民间财产权属的部门。而这一部门,很可能就是本文所称的文书收存机关。当楚王将啻苴之田划给新大厩时,权属流转的记录也被保留在这个部门中。当出现具体案件和纠纷时,左尹从这一机关调用了这份记录,并根据自己的工作需要进行了抄录。这便是简153与简154这两份内容大体相同的文书并存于左尹身边的原因。
综上所述,对第二类无篇题简中的形制问题的关注,对研究包山楚简的内容而言是有所裨益的。通过对契口间距的分析,笔者认为包山楚简在下葬之前,是以一份一份单独的文书的形式存在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批文书并不如睡虎地秦简那样是墓主自行编撰供自己使用的文书集,而是其工作中现实处理的文书。而通过对这类简的长度进行分组,笔者认为该类简的不同长度,源自于不同的文书来源。长度在64~66厘米的短简是左尹等司法、行政或军事机关日常使用的文书,而长度达68~69厘米的长简则是特殊的文书收存机关所保存的文书。这种文书根据王命传递到左尹手中,为左尹处理案件提供材料。
[1]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2]陈伟,包山楚司法简131~139号考析[J],江汉考古,1994(3):67-71.
[3]李守奎,包山司法简致命文书的特点与138-139号简文书内容的性质[J],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
[4]张伯元,包山楚简举隅[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