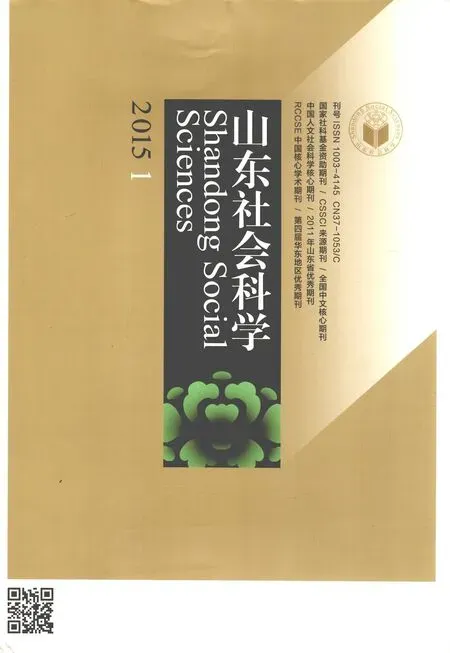“风险刑法”理论纷争的反思与出路
李宏杰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00063)
一、风险刑法的一场学术纷争
(一)风险刑法学术纷争的过程梳理
“风险刑法”理论对中国刑法学的渗透,广泛而深刻地发生在当下,并且大有学术纷争之势。虽然这一过程远未结束,但通过“为了前行的回首”,梳理这场纷争的起、承、转,应该可以作为一种有意义的铺垫。
劳东燕教授在2007年发表的“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一文开启了我国风险刑法的先河。①陈兴良:《风险刑法理论的法教义学批判》,《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刘国良教授编译的德国刑法学者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所撰《安全刑法:风险社会的刑法危险》一文撞开“风险社会”理论大门。一开始的声音多为肯定性与建构性的,即在承认风险社会背景的基础上,探讨传统刑法向风险刑法转变之路径。同时,或许是路径依赖的作用,抑或是对新事物的警觉,否定性(至少是质疑性)与解构性的思考也随之而来,并且产物颇丰。不过,这些反思与批评性意见多属笔谈性质,而且往往并不系统,直到2012年,南连伟在《法学研究》上发表论文《风险刑法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对“风险刑法”理论从“风险”概念着手进行了系统性的批评②参见南连伟:《风险刑法理论的批判与反思》,《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至此,我认为,对“风险刑法”理论的探讨迎来了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后,不少学者展开对该理论的系统批评。③如孙万怀教授认为风险刑法的实质是刑法威吓作用的重新泛滥,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厘清刑事政策与刑事法治的关系。参见孙万怀:《风险刑法的现实风险与控制》,《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年初《中外法学》的两篇重量级文章,分别是劳东燕教授《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刑法理论》与陈兴良教授《风险刑法理论的法教义学批判》。④陈兴良:《风险刑法理论的法教义学批判》,《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可以想象,虽然对于风险刑法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但是随着批评者的声势壮大,风险刑法理论的命运或将走向新的境地。
(二)风险刑法学术纷争的特点描述
通过对上述过程的考察,我认为“风险刑法”的学术战局有如下特点:首先,场面浩大。风险刑法理论着眼于刑法的结构性转变,其中涉及的问题无论从纵向上还是横向上看都相当丰富,既包括观念上刑法目的的流变,也包括技术上推定方法的运用;既包括总则中重要问题的探讨,也包括分则中具体罪名的解释。其次,对立鲜明。在上述诸多问题中,建构者与解构者、倡导者与批判者的观点产生了鲜明的对立。最后,波及甚广。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场学术争论招致了刑法学界广泛的关注和参与,中国刑法学由此展开一幅热闹非常的学术图景。或许可以说,风险刑法理论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理论。面对这样一个有野心、有争议、有吸引力的理论以及围绕其而产生的争论,为之寻求一条合理出路显得意义重大,而抓住问题的核心则是这一切的前提。
(三)风险刑法学术纷争的核心问题
从反对者的观点入手寻找争论的核心问题,不失为一条便捷的路径,其中,为了抓住根基性的核心问题,将注意力集中在宏观层面的批评应该是合理的选择。风险刑法理论遭受了诸多批评,例如张明楷教授认为“风险社会”并非社会的真实状态,而是“文化或治理的产物”,因此不能将其作为刑事立法的社会背景依据。①参见张明楷:《“风险社会”若干刑法理论问题反思》,《法商研究》2011年第5期。对于这个问题,至少“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者乌尔里希·贝克是持肯定答案的,“这恰恰是因为风险的积聚——生态、金融、军事、恐怖分子、生化和信息等方面的各种风险——在我们当今的世界里以一种压倒性的方式存在着。”②[德]乌尔里希·贝克等:《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除此之外,在宏观层面对风险刑法有以下几种常见的批判:第一,认为“风险刑法”误读了“风险社会”理论,曲解了其中的“风险”概念;第二,认为“风险刑法”泛化了刑事处罚,使人权和法治岌岌可危;第三,认为“风险刑法”违背了刑法基本原则。③参见魏东、何为:《风险刑法理论研究综述》,《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既然“风险刑法”与“风险社会”之间存在某种断裂,那么,将二者分而观之的二元视角,成为我接下来的分析工具。
二、风险刑法的二元视角分析
(一)“风险”刑法与“风险”社会间的断裂
“风险刑法”与“风险社会”以“风险”为联结,那么亦因“风险”而断裂。事实上,关于“风险刑法”对“风险社会”理论的误读,绝不是一个新鲜的观点,但却往往是有效的,这得归结于风险刑法理论建构时的一种模式:“首先引用几段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的论述,强调风险社会的来临,然后检讨传统刑法在应对风险时的乏力,进而提出风险刑法理论的主张。”④南连伟:《风险刑法理论的批判与反思》,《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这种模式是十分粗糙的,风险社会理论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它与刑法学之间存在着需要以细腻考察和严密论证架设桥梁的鸿沟,而多数的风险刑法理论却忽视了这一点。了解到这一谬误可能的原因,接下来就是以二元视角为工具,从“风险社会”与“风险刑法”分别出发进行考察。
什么是“风险社会”的“风险”?贝克认为:“风险概念是一个很现代的概念,是个指明自然终结与传统终结的概念……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副作用。”⑤[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那么,“风险刑法”的“风险”指的又是什么?有学者指出:“风险刑法论者几乎将当前社会的所有问题都归入了风险范畴:交通事故、矿难事故、医疗事故、飞机失事、毒品泛滥、信息安全事故,甚至包括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群体性事件、恶意欠薪、暴力犯罪等。”⑥南连伟:《风险刑法理论的批判与反思》,《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针对风险刑法理论很大程度上泛化风险的现象,陈兴良教授作出了十分深刻的批评:“风险刑法理论在对风险社会的风险概念理解上的外延溢出,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风险概念的特定性,并使风险社会的理论失去其解释力。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风险刑法理论,就可能丧失其现实基础。”⑦陈兴良:《风险刑法理论的法教义学批判》,《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可以说,风险刑法理论与风险社会问题在“风险”问题上发生了断裂,这导致原本建立在风险社会理论基础之上的风险刑法理论的内涵变得“可疑”起来,似乎并不是“风险社会的刑法”理论,而是“关于一般意义上的风险的刑法”理论。这种断裂,使得进一步的二元视角分析成为必要。
(二)“风险刑法”与“风险社会的刑法”
“风险刑法”理论的含义分为狭义与广义。狭义的风险刑法理论即我国刑法理论一直以来讨论的那种“风险刑法”,基于其泛化风险的特点,或许更准确的名称是“关于一般意义上的风险的刑法”理论;而广义的风险刑法在包括狭义风险刑法的同时,也包括了针对严格意义上的风险社会而建构的刑法,即“风险社会的刑法”。对于这种现象,我将其比喻为中国刑法学对风险社会理论的“协奏与变奏”。
将“风险社会的刑法”从“风险刑法”理论中拆分出来之后,再看狭义的风险刑法理论。陈兴良教授认为,虽然风险刑法理论做出了推动刑法理论发展的善意努力,但是由于存在理论根基不稳、论证大而化之的致命缺点,因而“只能获得一时之观点喧嚣,而难以取得长久之学术积淀”。①参见陈兴良:《风险刑法理论的法教义学批判》,《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对此,我认为或许言之过早。风险刑法理论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是究其本质,应该是可以通过理论的矫正而趋向完善和进步的,当然,对其的完善建议应该以其具有理论或实践价值为前提。
(三)“风险刑法”的二元价值探讨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风险刑法”指广义的风险刑法理论,因此这一部分的论述同样采分而观之的二元视角。关于“风险社会的刑法”——既然刑法无力应对风险社会,那么该论题的意义何在?我认为,该论题的使命恰恰在于警示我们刑法作用的局限性。关于狭义上的“风险刑法”——既然“风险刑法”理论原本的理论根基已被抽离,那么该论题是否还有继续存在乃至深化的价值?首先,风险刑法理论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其对应的现实背景,诸如食品安全、交通事故等领域存在的问题,也都是真实的,因而该理论是对这些问题的一种有益的探讨,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其次,其实很多风险刑法的论述除了借用风险社会理论作为背景之外,与该理论并没有太大关系,除去“风险社会”并没有完全斩断其命脉;最后,风险刑法理论也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对传统刑法的反思,承认并且鼓励这样的反思无疑有利于学术的深化。既然矫正的价值得到了承认,接下来便是矫正的努力。
三、风险刑法的三层次矫正路径
(一)把“风险刑法”从“风险社会”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风险社会理论并非当下风险刑法理论的命脉,脱离了“风险社会”,风险刑法中的诸多观点一样有生存的土壤,并且,脱离了“风险社会”,将减少由于误读而产生的误导,也消弭对于误读的批评,使风险刑法理论更具说服力。
(二)对“风险刑法”进行“化整为零”的改造
风险刑法理论各种问题之间并没有那么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在脱离了风险社会理论之后,其往往表现为对具体问题的具体看法,如对交通安全与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制、对危险犯与实害犯关系的探讨,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解答固然受现实社会背景的影响,但是完全无需以一个“风险刑法”的概念来统御全局。相反,在一个整体性的风险刑法理论之下,与其说各具体问题相互支持相互补充,不如说他们相互牵连相互拖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化零为整的拆分或许是更好的选择,将各问题归位到其原本的体系位置上,然后结合当下真实具体的社会背景展开讨论。
(三)将“风险刑法”置于“传统刑法”框架下
将风险刑法纳入到传统刑法框架下,一方面是因为风险刑法所讨论的问题绝大多数是传统社会的问题的量变而非质变,从而与传统刑法具有亲缘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对其进行了化整为零的拆分,使其失去了整体性对抗的姿态。而将其纳入到传统刑法的框架下,一方面可以使其中有益的探索内化为刑法理论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另一方面,面对其中一些冒进的做法,方才可以毫无障碍地用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的谦抑精神、刑法的保障法地位等原理进行批判与制约。
四、结语
因为风险刑法理论事实上并非建立在风险社会理论之上,所以我们把它从这种尴尬的断裂中解脱出来,并且化整为零地归位于传统罪责刑法之中。这是因为,第一,真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的刑法”并非也不可能是一个建构性的概念,面对现代化的危机与风险社会,过于依赖刑法的力量是危险的,这也是很多学者所强调的“刑法风险”的应有之义;②参见陈兴良:《“风险刑法”与刑法风险:双重视角的考察》,《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孙万怀:《风险刑法的现实风险与控制》,《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魏汉涛:《风险社会的刑法风险及其防范》,《北方法学》2012年第6期。第二,在我们看来,我们当下的风险刑法理论与其说是一个论题,不如说是一个“论题群”,交通事故、食品安全、持有犯、抽象危险犯、过失危险犯、因果关系理论与责任理论的流变等等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些也并没有脱离“传统”之可能范畴。我们将它们归位于传统刑法,还因为,站在应然层面,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永远应受推崇,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面对公权力对刑法的依赖倾向以及社会报复情绪对于公器惩罚的狂热呼唤,自由与法治的价值更应该不断强调。在这一点上,我们与那种站在实然层面描述刑法体系的预防性转变并且呼吁保障与制约的做法,③参见劳东燕:《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刑法理论》,《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可谓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