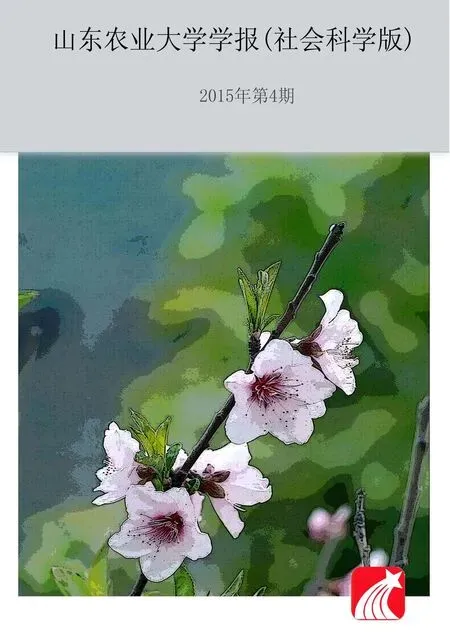六朝时期宁镇丘陵的农业发展
——兼论江南开发的历史进程
□王 勇
六朝时期宁镇丘陵的农业发展
——兼论江南开发的历史进程
□王 勇
六朝时期宁镇丘陵是北方移民最集中的地区,加之建康成为政治中心,其农业开发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通过政府组织的屯田开发、推广麦作、兴修水利等,这里的农业经济取得了长足进展,然而其开发程度仍然不如吴越平原。学者参考泰国湄南河流域开发过程,推导出的江南地区宁镇丘陵开发早于吴越平原的结论并不成立。
宁镇丘陵;六朝;农业开发;江南地区
六朝是江南农业开发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而在取得全面进步的同时,江南各地的发展事实上也存在程度差异与各自的区域特征。本文所要探讨的宁镇丘陵地区以宁镇山脉和茅山山脉构造为骨架,主要包括江苏省的南京、镇江两市,常州武进、金坛西北隅,安徽马鞍山市的一部分。这里是南方出现人类活动与农业经济较早的地区,也是吴文化的发源地。商周之际泰伯、仲雍南奔荆蛮,其早期都邑“宜”就在宁镇丘陵。吴国统治时期,宁镇丘陵农业有较大发展。《吴越春秋·吴泰伯传》载泰伯到南方后,“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人民皆耕田其中”。同书《勾践阴谋外传》载:春秋末年越国逢灾年向吴人借粟,“吴王乃与越粟万石”。粟是一种旱田作物,不适合在吴越平原的低田种植,当时吴国种粟只能在地势相对高亢的宁镇丘陵进行。吴王动辄借给越人“粟万石”,自然是宁镇丘陵农作已有相当规模的反映。但是吴国从诸樊时便将都城迁往苏州。苏州所在的吴越平原土地相当平坦,其泛滥平原上的水位一般很浅,特别适于发展水稻生产。吴国迁都的举动,事实上是从相对适于居住的地区向更适合于农业的地方发展。自从吴国农业发展的重心转向吴越平原,宁镇丘陵的农业开发便长期停滞不前。东汉时期宁镇丘陵主要归丹阳郡管辖,而当时丹阳郡治宛陵,其中心并不在宁镇丘陵。《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载楚王英被控谋反遭废黜,“徙丹阳泾县,赐汤沐邑五百户……英至丹阳,自杀”。同书《马援列传》载马援受不公正待遇,其子马防及孙马遵“皆坐徙封丹阳,防为翟乡侯,租岁限三百万,不得臣吏民。防后以江南下湿,上书乞归本郡,和帝听之”。丹阳既然是当时罪臣贬逐安置的场所,可想而知,其经济是很落后的。这种情况至六朝时期终于发生改变。
一、孙吴、西晋时期宁镇丘陵农业的发展
三国时期孙吴割据江东。孙氏起自富春,地属吴郡,紧邻会稽,这里是当时江南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孙策领兵回江东时,最初也是以吴郡为治所。建安十三年(208年)为便于与黄祖作战,孙权迁治所于京口(今镇江)。建安十六年,孙权又由京口溯江而上,迁治所于秣陵,并改秣陵为建业。《三国志·吴志·张紘传》注引《献帝春秋》载孙权曰:“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居之。”从此以后,建业成为孙吴的政治中心,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六朝结束。孙权将治所从吴越平原迁到宁镇丘陵,主要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庱亭,马为虎所伤”。庱亭在今常州与丹阳之间,《晋书·郗鉴传》载“会舒、潭战不利,鉴与后将军郭默还丹徒,立大业、曲阿、庱亭三垒以距贼”。孙权从建业回吴郡时在这里猎虎,说明宁镇丘陵即便是交通线附近地区也仍然人户绝少,土地未垦,是莽莽榛榛,野兽出没的地方。然而,建康成为稳定的政治中心,也给宁镇丘陵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孙吴为立足江东,与曹魏、蜀汉抗衡,曾大兴屯田,保障粮食供应,增加财政收入。宁镇丘陵由于其邻近都城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孙吴屯田的主要区域。毗陵是东吴最大的屯田区,《宋书·州郡志》记载:“吴时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校尉。”毗陵典农校尉辖今镇江、丹徒、丹阳、常州、武进、金坛、无锡、江阴等地,大都在宁镇丘陵的范围。这里起初是吴郡的农业落后地区,未开垦土地很多,拥有大规模屯田的条件。《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注引《吴书》:“赤乌中(238—249年)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陈表、顾承各自率领的部队及家属各达数万人,说明孙吴正式设毗陵典农校尉之前,在毗陵屯田的总人数就已经很多。在设置毗陵典农校尉后,这里成为固定的民屯点。据《宋书·州郡志》,丹徒郡之溧阳县,“吴省为屯田”;湖熟县,“吴省为典农都尉”;南徐州南琅琊郡江乘县,“本属丹阳,吴省为典农校尉”;淮南郡于湖县,“本吴督农校尉治”,也都是屯田集中的地方。孙吴屯田点在长江两岸沿线数量很多,当时长江中下游数千里皆需设防,处处置兵,屯兵之处一般都令军士屯田。但也因为如此,孙吴军屯相对分散,规模往往不大。而集中的民屯则大都在建业附近的宁镇丘陵上,毗陵典农校尉、溧阳屯田都尉、湖熟典农都尉、江乘典农校尉的屯田不只是为了供应军粮,也有巩固国本、支援四方的作用。
孙权对屯田非常重视,《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黄武五年(226年)陆逊“表令诸将增广农亩”,孙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由于此前南方开发程度低,孙吴屯田面临的主要是土地开拓任务,而集中领导、统一管理的屯田组织形式,特别有利于大规模的水土建设和土地开发,对于宁镇丘陵农业的发展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著名的赤山塘,据传就建于赤乌年间。赤山塘位于今江苏句容县西南30里,利用环山抱洼的有利地形,修筑长堤,引茅山山脉的山水汇注成湖,下通秦淮河,立斗门以灌溉农田。湖熟位于赤山塘下游,距离赤山塘只有八九里,孙吴曾设湖熟典农都尉屯田。赤山塘的修建可能就是出于发展屯田的需要。丹阳湖地区洼地平坦、土地肥沃,又有湖泽侵润之利,孙吴也曾在这里设屯田,围垦湖滩。《三国志·吴书·濮阳兴传》载:永安三年(260年)“都尉严密建丹阳湖田,作浦里塘”,丞相濮阳兴力主“会诸兵民就作”,结果“功佣之费不可胜数,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同书《陆凯传》载,建衡元年(269年)奚熙又“建起浦里田,欲复严密故迹”,丞相陆凯力谏止之。严密、奚熙修建的浦里塘位于古丹阳湖东北缘,在今溧水县南。《读史方舆纪要》卷20“江宁府溧水县”载,“蒲塘港在县南二十里……一名蒲里塘。三国吴永安三年丹阳都尉严密议建丹阳湖田,作浦里塘,久之不成,即此”。由于丹阳湖区洪枯水位相差很大,要围垦湖塘并非易事,孙吴时在这里筑塘围田成效微弱,但此事本身就反映了孙吴屯田对水利的重视。孙吴时期宁镇丘陵地区屯田规模相当大,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如果没有水利设施的配合难以取得较好成效,只是史载有缺,已经难知其详。
建康成为京畿重地后,权贵云集,人口增加,对于宁镇地区的开发也是积极因素。建康城周围的娄湖即为孙权谋臣张昭创建。《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润州上元县条”载:娄湖为“吴张昭所创,溉田数千顷,周回七里。昭封娄侯,故谓之娄湖”。为了加强与三吴地区的联系,保障建康城的粮食供应与长江两岸军队的给养,孙吴政权还加强了宁镇丘陵上的运河建设。当时太湖流域的行船都由京口入长江,再溯流而上去建业,为了缩短抵达建业的水路行船,孙吴开辟了破冈渎。《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载:赤乌八年(245年)“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巿,作邸阁”。破冈渎主要在今句容县境内,处在茅山山脉与宁镇山脉之间的丘陵间,凿冈为渎,由冈顶向两侧各建7座堰埭,共14座,用以平水和节制用水。孙吴末年又对江南运河晋陵至京口段进行了改造。《太平御览》卷170引《吴志》:”岑昏凿丹徒至云阳,而杜野、小辛间,皆斩绝陵袭,功力艰辛(原注:杜野属丹徒,小辛属曲阿)。”岑昏是孙皓时人,《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其“好兴功利,众所患苦”,所兴功利当包括改造此段运河在内。破冈渎与江南河以通航为主,但对于沿线的开发不无裨益。
西晋末年陈敏据有江东时,在丹阳县北修建练湖,既是为了补充水源,保障江南河的畅通,也有很大的灌溉效益。《太平御览》卷66引顾野王《舆地志》:“练塘,陈敏所立,遏高陵水,以溪为后湖。”《元和郡县图志》卷25“润州丹阳县”载:“练湖在县北一百二十步,周回四十里。晋时陈敏为乱,据有江东,务修耕绩,令弟谐遏马林溪以溉云阳,亦谓之练塘,溉田数百顷。”《读史方舆纪要》卷25引《南徐记》:“湖周百二十里,纳丹徒长山、高骊诸山之水,凡七十一流,汇而为湖。”练湖利用有利地形,对丹阳西北长山、高骊山的来水进行拦蓄调节,建成周长40里,蓄水面积两万余亩的大湖。练湖的建成,使丹阳、金坛、延陵一带雨季免受山洪侵袭,并灌溉农田数百顷,为当地农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东晋、南朝时期宁镇丘陵农业的发展
东晋南朝南方经济的发展与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移有很大关系,而宁镇丘陵是当时南迁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由于永嘉之乱后的移民最初是在胡骑逼迫下南迁的,很多只想找个接近北土的地方停留,以便有朝一日能重返故园,所以他们集中居住的地方,一般限于长江南缘。据谭其骧先生估计,晋永嘉丧乱后至刘宋末年,“南渡人户中以侨在江苏者为最多,约二十六万”,其中“江苏省中南徐州有侨口二十二万余,几占全省侨口十之九。南徐州共有口四十二万余,是侨口且超出本籍人口二万余”。[1]刘宋时期南徐州治京口(今江苏镇江),其辖境大致与孙吴时期的毗陵典农校尉相当。西晋罢屯田,设郡县,改毗陵典农校尉为毗陵郡,东晋改称晋陵郡。《晋书·郗鉴传》记载,郗鉴曾对在晋陵的流民“处兴田宅,渐得少安”,组织他们进行农业生产。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人口的多少往往会决定地区农业生产规模的大小与劳动集约程度的高低。宁镇丘陵因为移民大量到来而人口倍增,自然会给当地农业发展带来新的面貌。而且对于侨民,东晋南朝政府最初设侨州郡县管辖,可以获得免交租调、免服徭役的优待,亦有利于减轻其负担,促使其安心务农。
大量移民南来增加了南方的粮食负担,同时也是适应北方移民的生产生活习惯,东晋南朝政府曾大力推广麦作,宁镇丘陵是重点推广区域。《晋书·食货志》记晋元帝太兴元年(318年)诏:“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继新故之交,于以周济,所益甚大。昔汉遣轻车使者氾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勿令后晚。”《宋书·文帝纪》载元嘉二十一年(444年)七月诏:“比年谷稼伤损,淫亢成灾,亦由播殖之宜,尚有未尽。南徐、兖、豫及扬州浙江西属郡,自今悉督种麦,以助阙乏。速运彭城、下邳郡见种,委刺史贷给。徐、豫土多稻田,而民间专务陆作。可符二镇,履行旧陂,相率修立,并课垦辟,使及来年。凡诸州郡,皆令尽勤地利,劝导播殖,蚕桑麻纶,各尽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南朝·宋疆域图”,南兖州治广陵,南豫州治姑熟,主要辖今江苏、安徽江淮之间以及长江以南的铜陵、宣城、池州等地。南徐州治京口、扬州治建康,辖境在长江南缘。由于分割出了东扬州,扬州只统丹阳、吴郡、吴兴、义兴四郡,其中在最西边的是丹阳。[2](P25-26)可见,刘宋元嘉诏书中责成推广麦作的区域主要就在江淮之间以及长江南缘的宁镇丘陵、皖南丘陵。
麦作的推广改变了南方单一种植水稻的作物结构,能够起到稻麦互补的作用。中国农业自古就有“杂种五谷,以备灾害”的传统。在饥旱发生时,南方麦作的效果尤其明显。《晋书·食货志》载元帝推广麦作,“其后频年麦虽有旱蝗,而为益犹多”。《陈书·吴明彻传》载吴明彻年少时在家务农,“时天下亢旱,苗稼焦枯”,唯独他“秋而大获”,侯景之乱时,“明彻有粟麦三千余斛,而邻里饥餧”。吴明彻的农田独独能获得丰收,可能与他种植的是粟麦,而邻里大都种植水稻有关。而且,麦作的推广特别有利于宁镇丘陵的开发。农谚有云“麦要燥,田要高”,“高田种麦,低田种稻”。相对于吴越平原,宁镇丘陵地势高亢、比较容易受到干旱威胁。《元和郡县图志》卷25说:“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秽恶。”《太平广记》卷293引《搜神记》说京城“甚多草秽”。这些评价当然是从进行稻作的条件与稻作的发展程度做出的,但反过来也正好说明了宁镇丘陵会相对比较适合耐旱的麦作。东晋南朝建康城的市场上四季都有麦类出售。《宋书·孝义传》载何子平任扬州从事史,“月俸得白米,辄货市粟麦”。而且市场上麦类的交易规模还不小。《南史·陈纪·武帝》载陈霸先与北齐作战时曾经从建康市场调麦供应军粮,“食尽,调市人馈军,皆是麦屑为饭,以荷叶裹而分给”。这里的麦大多应产自附近的宁镇丘陵。
当然,对于南方的农业生产而言,水稻始终是最主要的作物。随着东晋南朝一系列水利工程的修建,宁镇地区发展稻作的条件也在逐渐改善。宁镇丘陵地势起伏较大,溪河源短流急,一经暴雨,山洪暴发,易成洪灾,洪水退后又出现旱情;高亢平原则因水源缺乏,干旱时间较多。因此农田水利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修筑陂塘堰坝,拦洪蓄水,以供灌溉之用。孙吴时期宁镇丘陵见于记载的陂塘工程只有赤山塘,东晋南朝,这里陂塘的修建明显更加普遍。新丰塘是东晋太兴四年(321年)修建的蓄水灌溉工程。《晋书·张闿传》载张闿任晋陵内史,“时所部四县并以旱失田,闿乃立曲阿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每岁丰稔。”新丰塘在今丹阳县东北30里新丰镇附近,“计用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二十功”,由于用功过多,张闿一度“以擅兴造免官”,但后来公卿认为他“兴陂溉田,可谓益国”,又被起用为负责国家财政的大司农。据《世说新语·规箴》注,时人名新丰塘为富民塘,葛洪作有《富民塘颂》。新丰塘能够被冠以“富民”,足见其灌溉效益之显著。南朝时期还对孙吴时期修建的赤山塘进行了数次修治,其中见于记载的有两次,一次在南齐明帝时,《梁书·良吏传》载明帝使沈瑀“筑赤山塘,所费减材官所量数十万”;另一次在陈朝时期,见于《江南通志·河渠志》。修治后的赤山塘周长120里,有两斗门控制蓄池,以后历代迭加修治,灌田号称万顷。其它见于记载的陂塘工程还有:萧齐单旻在金坛县东北主持修建的单塘,梁吴游在金坛、丹阳之间主持修建的吴塘,梁谢德威、谢法崇在金坛修建的南北谢塘,梁谢贺之在金坛修建的莞塘,以及建康城周围的迎檐湖、苏峻湖、葛塘湖等。没有见于记载的陂塘则更多。《宋书·孝义传》载刘宋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大旱,徐耕说晋陵郡“承陂之家,处处而是,并皆保熟,所失盖微。陈积之谷,皆有巨万”;《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载南齐建元三年(481年)萧子良任丹阳尹时提出,丹阳郡“旧遏古塘,非唯一所”,可略见当时宁镇丘陵水利陂塘的规模。此外,《宋书·文帝纪》载刘宋元嘉二十三年“浚淮,起湖熟废田千余顷”。这里的“淮”指秦淮河,湖熟在今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湖熟镇,孙吴时曾设湖熟典农都尉,也是通过兴修水利来拓垦荒地。
三、江南地区开发的历史进程
《王桢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一“梯田”条提到农田开垦的顺序时说,“盖田尽而地,地尽而山”。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开发是从平原开始的,然后才会是丘陵、山地。吴越平原的开发先于宁镇丘陵,一直是过去江南农业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然而,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研究宋代江南经济史时,参考泰国湄南河流域开发过程的研究后,将江南从地形上分为三个部分,并且认为江南的开发遵循以下顺序:河谷扇形平地—三角洲上部—三角洲下部。南宋至明初江南农业的开发高潮,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在三角洲下部强湿地带排水造田实现的。,长江下游中枢部分的生产力,在宋代大半还处于潜在状态。[3](P146-217,638)斯波义信的研究引发了国内学者对江南开发历史进程的重新思考。李伯重认为江南地区从地形上可以分为宁镇丘陵、浙西山地和江南平原,斯波义信的研究实际指出了江南地区“最先开发的是宁镇丘陵和浙西山地中的河谷平原,其次是江南平原上的高田地带,最后才是江南平原上的低田地带”,而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江南平原—宁镇丘陵—浙西山地”的开发顺序。他说“斯波氏提出的新模式,消除了过去流行的错误模式所造成的对江南地区开发方式的误解”。[4]
斯波义信与李伯重先生的研究,证明了“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江南平原低洼地带的进一步开发”,但这是否意味着“是江南农业生产重心从西部高田地带向东部低田地带的转移”,主要还应着眼于宁镇丘陵、吴越平原此前各自开发的程度如何。为了论证其观点,斯波义信提到了六朝时期的情况,认为当时“江南中心区域的情况,如果同后世相比,由于广大的泛滥原仅在中部地区移民开垦而能进一步扩大开垦,仍是人口较少的荒芜地域,此时这里绝非全区域的经济中心区。而全区域的行政中心地区,则是在南京边上的旧都,当时确实长期支配着江南的整个区域。但实质上,该区域内是以分散在各地的互不相连的高阜地上的资源为支柱的。因此,政府对低地的关心,主要表现在对交通组织的整备,以及沿海地区盐碱地的开发方面”。[3](P194)由于研究重点是宋代经济,斯波义信对这一观点没有具体论证。然而,就我们对六朝江南经济空间差异的评估,宁镇地区当时虽然取得了很大发展,其开发程度却远不如东边的低地平原地区。
何德章指出,“六朝时代,南方真正可以算得上经济区的只有会稽、吴郡、吴兴所在的‘三吴’地区”。[5]三吴在六朝是公认的富庶之地,国家的主要产粮区。《晋书·诸葛恢传》载诸葛恢为会稽太守,晋元帝对他说“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晋书·文苑传》载伏滔说“彼寿阳者,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南齐书·王敬则传》载萧子良说“三吴内地,国之关辅,百度所资”。关于三吴农业之发达也有很多直接记载。《三国志·吴志·钟离牧传》载会稽山阴人钟离牧少时“种稻二十余亩”,“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亩产达到三斛之多。《宋书·沈昙庆传》传论说“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相反,宁镇丘陵上的丹阳、晋陵等地则没有得到这么高的评价。孙吴时期能够在宁镇丘陵设置毗陵典农校尉等屯田区,本身就说明当时宁镇丘陵还是比较贫瘠的地方。尽管孙吴以来宁镇丘陵农业发展很快,但南朝时这里仍然有很多荒地。《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载萧子良任丹阳尹时提出,丹阳“民贫业废,地利久芜。近启遣五官殷沵、典签刘僧瑗到诸县循履,得丹阳、溧阳、永世等四县解,并村耆辞列,堪垦之田,合计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顷”。萧子良提议“修治塘遏”,加强开发,但“会迁官,事寝”,并未实施。南朝末年任昉的《述异录》说毗陵多虎。《太平御览》卷170引《舆地志》说“丹徒界内土坚紧如蜡。谚曰:‘生东吴,死丹徒。’言吴多产出,可以摄生自奉养,丹徒地可以葬”。甚至到南宋汪元量《增订湖山类稿》卷2的《京口野望》,也仍然有“南徐白昼虎成阵”的诗句。
如前所述,六朝时期宁镇丘陵因为建康成为政治中心,又是北方移民最集中的地区,在农业开发上拥有很多吴越平原所不具备的优势,而且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开发成就。然而其开发程度仍然不如吴越,主要还是地理因素的原因。斯波义信认为下游三角洲地区“特别适于发展水稻生产”,之所以开发较晚,是因为这里的“围垦排水造田工程,要经过周密的计划,运用水利工程学与组织营运等广泛知识及大量的资本投入才能得以实现”。[3](P179)这对于泰国湄南河流域开发是比较晚近的事,但由此推断江南的情况,却不一定正确。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技术无疑远远比泰国先进,早在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就已经修建水利,将发展重心逐渐转向江南平原的低地地区。而尤其不能忽视的是东汉以来江南豪族势力的发展。葛洪《抱朴子·吴失》称孙吴末年江南大族“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这些孙吴大族的代表主要就是吴郡的朱、张、陆、顾,会稽的虞、孔、魏、贺以及阳羡周氏、吴兴沈氏等。东晋建国后,孙吴大族的势力完全得到保留,又有很多北方大族定居三吴,这些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大族修建水利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宋书·谢灵运传》载“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坚执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宁岯崲湖为田,顗又固执”,《南齐书·王敬则传》载“会土边带湖海,民丁无士庶皆保塘役,敬则以功力有余,悉评敛为钱,送台库以为便宜”。谢灵运两次向会稽太守孟顗请求决湖为田均遭拒绝,王敬则认为会稽民间用于疏浚陂湖的塘役“功力有余”,说明湄南河下游三角洲地区开发起初所遇到的困难在六朝时期的江南地区并不存在。梁大同六年(540年)改晋海虞县为常熟,光绪《常昭合志稿》说明其改名原因,“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涝亦不为患,以故岁常熟,而县以名焉”。可见南朝末期江南低地平原塘浦圩田已经初具规模。总之,江南地区的开发进程比较复杂,而从六朝时期的情况看,对于江南地区开发顺序,“江南平原—宁镇丘陵—浙西山地”的传统观点应该是更为合理的认识。
[1]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C].长水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3] 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4] 李伯重.有无“13、14世纪的转折”——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的变化[C].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5] 何德章.六朝南方开发的几个问题[C].魏晋南北朝史丛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015-03-09
国家社科基金“汉晋南朝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5BZS040)阶段成果。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410082
王 勇(1975- ),男,湖南武冈人,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秦汉史、农业史。
K235;F329
A
1008-8091(2015)04-0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