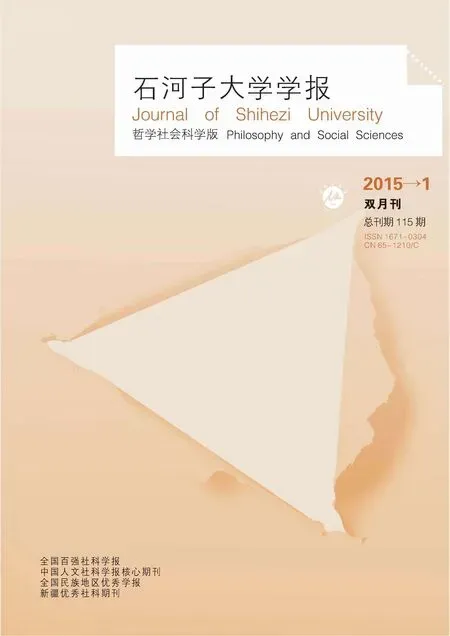清代新疆文化变迁的人文环境述略
杨发鹏,黄婷婷
(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清代新疆文化变迁的人文环境述略
杨发鹏,黄婷婷
(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随着清朝政府重新统一新疆以及对新疆的经营和开发,清代新疆文化发生了重要变迁。除自然环境的影响之外,清代新疆文化的变迁与当地的人文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其中新疆的疆域、政区、军事、人口、民族、经济、城市、交通等因素对新疆文化发展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代新疆;文化变迁;人文环境
URI:http://www.cnki.net/kcms/detail/65.1210.C.20150120.1341.010.html
随着清朝中央政府统一新疆以及对新疆大力开发和经营,新疆的文化随之发生了重要变迁。清代新疆文化的变迁既有自然地理因素方面的影响,更受到当时新疆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邹逸麟认为:“人文地理环境是指人类为求生存和发展而在地球表面上进行的各种活动的分布和组合,如疆域、政区、军事、人口、民族、经济、城市、交通、文化等等。”[1]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和新疆历史发展轨迹的独特性,清代新疆在人文地理环境方面与内地明显不同,本文拟从疆域、政区、军事、人口、民族、经济、城市、交通等方面分别对影响清代新疆文化变迁的人文地理环境加以论述,并简要阐明它们对清代新疆文化变迁的影响。
一、疆域
新疆古称西域,疆域非常辽阔。广义的西域是指今甘肃玉门关、阳关以西,即今新疆以及更西、更远的地方。狭义的西域,仅指今新疆天山南北,即玉门关、阳关以西,巴尔喀什湖和葱岭以东,准噶尔沙漠以南,青藏高原以北的地区。通常意义上新疆的疆域是指狭义的西域而言。清朝底定新疆,其疆域也是在巴尔喀什湖和葱岭以东。若以清代前期的疆域算起,新疆的疆域面积不下200万平方千米。清朝后期,随着国家实力的衰落与西方列强的侵略,清朝最终丢失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50多万平方千米的领土,因此新疆的疆域有所缩减。即便如此,新疆仍然是当时中国疆域最大的行政区。
辽阔的疆域为新疆多个民族的活动、多种经济的发展、多种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是新疆多元文化形成的地域基础。
二、政区
政区即行政区划,政区以国家或次级地方在特定的区域内建立一定形式、具有层次唯一性的政权机关为标志。清代统一新疆以后,在其疆域内实行军府制,于1762年设置总管伊犁等处将军,统管西域军政事务。伊犁、塔城、喀什噶尔各设参赞大臣,统辖当地军政;乌鲁木齐设都统,辖北疆各地及吐鲁番;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辖喀什、英吉沙、叶尔羌、和阗、乌什、阿克苏、库车、焉耆八城的办事大臣和领队大臣。伊犁将军及各地大臣皆不理民政,民政事务均由各民族头目自理,但他们的任免、承袭悉由各地大臣办理,有的还要奏报朝廷。伊犁将军府统治下的区域是清代全国最大的政区。
1884年,清政府正式在新疆建省,并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新疆建省,是清朝政府对历朝各代治理新疆的一次重大改革。自此,由巡抚统管全疆各项军政事务,新疆军政中心由伊犁移至迪化(今乌鲁木齐)。至1909年,新疆省下辖4道,道以下共隶有6府、10厅、3州、21县或分县,新疆行政建置与内地逐渐一致。
行政区划对于区域文化的整合具有重要作用。从西汉在西域建立西域都护到清朝前期设立伊犁将军府,再到清朝末年设立新疆行省,中央对新疆地区的管理呈现日趋加强和与内地逐渐统一的态势,这种态势从政治上给予新疆地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认同以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军事
西域历来为征战之地,自汉代以降征讨频仍,史不绝书,无须赘述。明末清初,西蒙古准噶尔势力崛起,奄有西域。清朝底定中原伊始,内乱未平,无暇西顾。准噶尔首领噶尔丹恃险远阻,兵戎屡见。康熙帝两次御驾亲征,打败准噶尔的进犯,噶尔丹兵败身死。噶尔丹死后,准噶尔的扩张一时受挫,但继任的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积蓄力量,势力复壮,并不时犯扰清朝疆界。雍正皇帝对准噶尔之野心早有防范,也不时对其用兵,但尚无大的征讨,因此雍正时准噶尔尚未归顺清朝。乾隆皇帝即位初,与准噶尔也保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噶尔丹策零死,准噶尔内部发生争夺权力的争斗,乾隆皇帝决心乘机收复西域。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清朝两路大军进讨准噶尔,准噶尔人纷纷归降,其头领达瓦齐也被擒获。但其后不久,阿睦尔撒纳又起兵背叛。清朝不得已再次对天山北路用兵,历时两年,至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将准噶尔彻底荡平。清军进驻伊犁之初,将被准噶尔贵族长期囚禁的南疆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大、小和卓木释放,欲使二人替清朝管理南北疆维吾尔人事务。但二人旋即叛变,窜往南疆,煽动各城叛乱。清朝从伊犁调动军队前往南疆平叛,也历时两年,至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秋,大、小和卓木被杀,天山南路完全平定。至此,清政府统一天山南北的大业终于完成。
自从乾隆年间清朝统一天山南北之后,在以后的五六十年当中,清朝在新疆的统治一直比较稳定。但从嘉庆末年起,由于清朝官吏的肆意盘剥和境外侵略势力的觊觎,新疆地区的变乱又起。主要的有张格尔之乱和七和卓之乱。张格尔是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孙,从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到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在浩罕封建统治者与英国殖民者怂恿支持下,三次潜入南疆发动叛乱。清政府命伊犁将军长龄调集清军3万余人,相继收复喀什噶尔等城。道光八年初,张格尔被清军擒获,解至北京处死,叛乱平定。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白山派和卓后裔卡塔条勒等七和卓为首在浩罕伯克胡达雅尔的支持下,带兵攻占了喀什噶尔回城,一度包围喀什噶尔汉城和英吉沙尔。清廷调兵南下后,三个月即收复喀什噶尔回城,七和卓逃回浩罕。
咸丰以来,中原多故,陕甘回民相继为乱。受此影响,新疆境内的回、维吾尔等族也纷纷发动反抗清朝的叛乱,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底,喀什噶尔的起事者向浩罕汗国求援,导致阿古柏入侵新疆。至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末,新疆大部分地方失陷。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俄国借机侵占伊犁。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清廷命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次年,清军西征,收复乌鲁木齐一带。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清军消灭阿古柏政权,收复了除伊犁外的新疆全境,持续十余年的新疆动乱最终结束。
清朝政府历次平叛的军事斗争在政治上的意义自不待言,这些军事行动对清代新疆的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清朝统一天山南北战争的胜利,中原文化再一次强劲地进入西域,并以各种形式渗透到新疆的各个角落。清代后期和卓余孽的历次叛乱、阿古柏入侵新疆所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不仅使新疆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也使新疆统一以来百余年的文化积淀几乎毁于一旦。但随着左宗棠收复新疆战争的不断胜利,新疆文化重建的活动又拉开了大幕,此后新疆文化更加快速地发展起来,并与内地文化的交往和联系更加密切。
四、人口
文化的本质是自然的人化,一个地区的区域文化是由所在地区的人口来决定的,并随着该地区人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迁。新疆虽然地域辽阔,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历史上的人口规模一直非常有限,而且增长相对缓慢。及至清代,由于清政府着力于新疆的经营和开发,新疆地区的人口增长较快。
根据吴轶群的研究,清朝统一新疆之初(公元1761年),全疆人口约为27万人;清朝统一新疆20年后,全疆人口增加到44.5万人;道光初年新疆人口增加到93.5万人;同治回乱之前,仅南疆维吾尔族人口就多达110万,加上汉族及其他各族人口,全疆人口不下140万[2]。同治年间,由于新疆回乱以及阿古柏入侵,新疆战火连绵,人口损耗较大,新疆人口数量有所下降。左宗棠收复新疆以及1884年新疆建省后,人口增长速度非常快,根据宣统元年(公元1909)的调查,新疆总人口超过了200万[3]。清代新疆人口快速增长的史实一方面表明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为新疆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疆人口的分布在地区之间往往是不平衡的,大部分时期,南疆人口一般要多于北疆,清代也是如此。如清代末年新疆的200多万人口中,南疆人口多达180万,而北疆人口尚不足30万,南疆比北疆有着绝对的人口优势。人口分布的这种不平衡性,导致地区之间文化影响力的差别,一般而言,清代南疆地区的文化影响力要超过北疆地区。
文化往往是伴随人口迁徙而传播的,人口的迁徙一般会打破或改变一个地区的文化现状。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人口迁徙比较活跃的地区,清代随着中央政府统一天山南北和对新疆的开发,内地移民开始或有组织或自发地涌入新疆,拉开了向新疆移民的序幕。新疆建省后,内地向新疆的移民活动更是达到高潮。随着内地移民的大量涌入,他们将自身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节日民俗等带入新疆,因而使中原文化源源不断地渗透到新疆的各个角落,并有力地影响和改变着新疆地区的文化色彩。北疆地区是内地移民迁入的主要地区,所以中原汉文化的色彩在北疆移民集中的地区格外浓烈。
五、民族
新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迁徙、融合的地区,因此其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多元民族文化的色彩。
清朝是新疆近代民族分布格局基本定型的时期。清朝统一新疆之前,天山北部活动的主要是准噶尔蒙古人。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叛乱的过程中,大批准噶尔人死亡逃散,损失殆尽。其后不久,游牧于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蒙古数万人历尽艰辛、回归祖国,被安置在伊犁地区。此时南疆地区依然主要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
清朝统一天山南北以后,为了推进新疆经济的开发,保卫西北边疆安全,在先前已有的民族迁徙分布格局基础上,陆续从东北各省抽调满、锡伯、索伦、察哈尔蒙古、汉等各族官兵数万人携带家眷进疆。之后,又组织、鼓励大批内地汉、回等族群众到新疆屯垦。此后部分民族从西部迁入新疆境内,新疆又增添了一些新的民族成分。至此,由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满、锡伯、达斡尔、塔吉克、塔塔尔、乌孜别克、俄罗斯等主要民族组成的近代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基本形成。
民族与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民族的分布格局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文化的分布格局,而民族分布格局的变动又会引起文化分布格局的变迁。清代新疆众多的民族构成,使得新疆区域文化一开始就呈现绚丽的多元色彩,而境内民族的迁徙活动,又使得新疆文化处于不断地变迁当中。
六、经济
清朝统一新疆以后,为了巩固西北边防和开发西部疆土,清政府决定在新疆实行移民屯垦,屯垦开发的重心在北疆地区。从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起,清政府大力倡导和组织各种形式的移民屯垦活动。经过广大移民的辛勤垦拓,天山北路的经济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农耕土地大片出现,村墟联络,人烟兴旺。嘉庆末年,北疆作为一个新兴的农业区域已经得到巩固。
同一时期,南疆地区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移民开发,但在南疆维吾尔民众的辛勤努力和有关措施的推动下,南疆的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道光年间,清政府同意在南疆实行垦荒屯田,由此南疆各地掀起全面兴垦的热潮。道光年间的兴垦活动,取得了明显效果。至道光末咸丰初,南疆的人口比乾隆中期增长了一倍,而官私新垦地亩也比乾隆中期成倍增长。
同治新疆回乱、阿古柏入侵新疆、沙俄侵占伊犁等一系列事件,使新疆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为了尽快医治战争创伤,发展新疆经济,巩固西北边防,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尤其是在全疆范围内掀起大规模修治水利的热潮。经过新疆军民的不懈努力,水利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经过多种形式的招徕聚集,新疆的人口逐渐回升,经济逐步恢复。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新疆垦成熟地1 000余万亩,额征斗粮30余万石[4]。耕地面积和额征赋粮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畜牧业是清代新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准噶尔部强盛时,作为其经济支柱的畜牧业曾一度繁荣,其游牧地从天山北麓向西向北扩展,直抵额尔齐斯河流域。尤其是策妄阿拉布坦与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畜牧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清廷统一新疆后,在北疆地区大力推行屯垦、进行农业开发的同时,也注意利用天山南北的优良草场设立官营牧厂,发展畜牧业。清代新疆的官营畜牧业在乾嘉年间得到很大发展,官营牧厂在天山南北的分布进一步扩展,开办规模不断扩大。咸道年间,新疆官营畜牧业逐渐萎缩,同光年间遭遇兵燹后,损毁殆尽,以后再也没有恢复起来。
此外,清代新疆的商业、采矿业也有一定发展。新疆统一后,天山南北官方及民间商业都很活跃。采矿业主要是为了配合国防、财政、农垦、民生的各种需要,着重发展以铜、铁为主干,包括金、银、铅、锡、煤、硝磺、玉石多项的采矿冶铸业,使新疆的矿业生产向前推进了一步。
经济对于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清代新疆各民族饮食与衣着之差别主要由其经济类型决定,从事游牧经济的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等民族,吃牛羊肉,喝奶茶、奶酒,穿着主要是皮毛类的衣服;而从事农业的维吾尔、汉、回等民族,以米面、蔬菜为主,穿着主要是布帛类衣服。清代新疆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物质与文化的交流。
七、城市
清朝统一新疆之前,北疆地区为准噶尔人的游牧之地,准噶尔人逐水草而居,迁徙不定,鲜有城郭。而南疆地区为维吾尔族聚居之地,“素习农功,城村络绎,视准部数千里土旷人稀,形势迥别。”①〔清〕傅恒等:《西域图志》卷32。新疆统一之后,随着军队的进驻和大量移民的到来,北疆地区的土地得到了大规模开发,而城市也迅速兴建并发展起来。
乌鲁木齐和伊犁是这一时期北疆兴建起来的最重要的两座城市。
乌鲁木齐城始建于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筑于乌鲁木齐红山之南,名为迪化。乌鲁木齐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历经改建、扩建,甚至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61年)离旧城八里处另筑新城,是为满城,名巩宁,而以迪化为汉城。乌鲁木齐城市的人口不断增长,至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迪化州属民商人户3 326户,男妇大小近3万余口②〔清〕永保:《乌鲁木齐事宜·户口》。。其商业也日益繁荣,据椿园氏记载,当时乌鲁木齐“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衢宽敞,人民辐辏,茶寮、酒肆、优伶歌童、工艺技巧之人无一不备,繁华富庶甲于关外。”①〔清〕椿园氏:《西域闻见录》卷1。在乌鲁木齐周边地区,也先后兴起一批中小城镇,如昌吉、阜康、呼图壁、奇台、古城、济木萨、绥来等。这些城镇最初是出关移民的落户地和兵屯屯区,以后筑堡修城,派驻文员,设立州县,渐具城市规模。此外,巴里坤地区的巴尔库勒城,自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始建以来,从军营发展为天山北路东段一大重镇。
伊犁城也始建于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起初仅在塔尔奇河边筑一小堡,供屯兵居住,后陆续建绥定、宁远、惠远、惠宁四城,与塔尔奇并为五城。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再增建广仁、瞻德、拱宸、熙春四城分驻绿营官兵,形成“伊犁九城”的格局。九城之中,惠远规模最大,为伊犁将军驻治之所。“伊犁九城”是清代前期新疆的军政中心,同时与哈萨克、布鲁特等民族的边贸活动也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洪亮吉诗云:“谁跨明驼半天回,传呼布鲁特人来。牛羊十万鞭驱至,三日城西路不开。”②〔清〕洪亮吉:《洪江北诗文集》卷4《伊犁纪事诗》。
南疆地区是传统的绿洲农业区,在大大小小的绿洲之上,很早就有众多大小不等的城市分布。据魏源《圣武记》记载,在清朝进兵之前,这里已有“大小回城数十,回庄小堡千计。”[5]较著者有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阗四大城,乌什、英吉沙尔、库车、辟展四中城及沙雅尔、赛里木、拜、库尔勒、玉古尔、牌租阿巴特、塔什巴里克、哈喇哈什、克勒底雅、玉陇哈什等23小城③〔清〕傅恒等:《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13。。清军进驻南疆后,在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八城设官驻军,镇抚其地。随着城池的修筑,人口的聚集,商业的繁盛,形成了以“回疆八城”统御各区的格局,而发展最快的首推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三城[4]。这些城市人烟聚集,商业繁荣,是南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同治新疆回乱、阿古柏入侵新疆、沙俄侵占伊犁等一系列事件,使新疆的许多城市遭到严重破坏,有些甚至夷为平地、荡然无存。新疆建省后,随着行政体制的改革,清政府又开始了举步维艰的城市重建过程。经过晚清二三十年的努力,新疆许多城市又逐步恢复发展起来,并开始呈现繁荣的景象,有些则被彻底废弃,成为荆棘瓦砾之地。
城市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方面的功能,清代新疆的城市,尤其是北疆地区的城市,在初建时其政治、军事意图明显,后来随着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城市的文化功能逐渐突出。风情各异的各种文化现象,在新疆的各个主要城市,如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城市里都能得到集中展现,清代新疆城市的兴衰见证了新疆文化的发展历程。
八、交通
清代新疆交通道路体系的建设是随着清朝与准噶尔的战争的进行不断发展起来的,其形式为以连接各主要驻防地为目的的台站体系。台站从形式上来看包括台、塘、站三种。台指军台,塘指营塘或军塘,站指驿站。军台主要用于军事目的,受军府驻扎大臣节制。军台的一些基本情况,根据潘志平先生的研究:“一般每两座军台设一委笔帖式、每台外委一员、兵丁4至10余名、供差回子10至15户。每台备马10余匹、牛2至10余只不等,铁瓦车二三辆、鸟枪5杆、腰刀5把及火药、火绳等装备。军台间距初百里左右,后陆续添设腰站,大体以70里为一站。”[6]营塘的作用与军台相同,是军台的辅助设施,规模较小,受绿营节制。台站与营塘的设置,各地并不一致,有些路段二者皆有,有些路段只具其中之一,例如:“伊犁至塔尔巴哈台及精河有军台无营塘,精河至乌鲁木齐有军台有营塘,乌鲁木齐至吐鲁番有军台有营塘,乌鲁木齐经巴里坤至哈密无军台有营塘,吐鲁番至哈密有军台无营塘,喀什噶尔至吐鲁番有军台无营塘,哈密至嘉峪关有军台有营塘。”④〔清〕松筠修,汪廷楷原辑,祁韵士编纂《西陲总统事略》卷3。驿站隶属地方州县管辖,比起军台和营塘,驿站的用途更为广泛。台、塘、站共同构成台站体系,主要承担文书传递、物资转运以及过往人员接待等功能。
清代新疆台站体系包括入疆台站和疆内台站两大部分。入疆台站又分为北、西两路。北路是指由京师出发向西北出张家口,经过内蒙古由外蒙古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翻越阿尔泰山进入新疆[7]。西路台站从京师出发,经直隶、山西、陕西、甘肃诸省,至甘肃嘉峪关后又分别向西进入新疆的巴里坤或哈密[8][9]。在这两条行军路线上,军台、营塘大量分布。
康熙年间,清军进兵新疆,应大学士富宁安奏请,在哈密、巴里坤设军台,是为新疆境内台站建设之始。乾隆年间随着平定准噶尔战争的展开,天山北路不断添设军台,辅以营塘,道路交通建设快速发展起来。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清军进军天山南路,军台进一步延展到南疆各城。底定新疆之后,结合新疆开发的需要,清廷对原有军台营塘的布局加以调整,并设置驿站,形成覆盖全疆的交通道路体系。
伊犁是清代前期新疆的军政中心,乌鲁木齐是新疆建省后的省会城市,哈密则是入疆的门户,所以清代新疆的交通干道大多以这三座城市中的一座作为起点或终点。从伊犁出发经乌鲁木齐至哈密的台站道路更是把这三座城市连接起来:“它西起伊犁惠远城,中经精河、库尔喀喇乌苏、绥来、呼图壁、昌吉至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分东南、东北两路至哈密。东南线经由吐鲁番,东北路经由巴里坤,在哈密底台会合,再通过哈密——星星峡——嘉峪关段与通往北京的皇华驿道相接。”[4]这条线路不仅是北疆地区最重要的交通干道,而且是整个新疆地区最重要的交通干道。此外,北疆地区还有从塔尔巴哈台至伊犁或乌鲁木齐,从古城连接科布多的台站道路。
南疆的主干道以哈密为起点,循天山南麓西行至吐鲁番,在吐鲁番有一路越天山至乌鲁木齐,另一路继续沿天山南麓西行,依次至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在阿克苏与向伊犁和向乌什的军台分道,折向西南到叶尔羌,在叶尔羌同向和阗的军台分道,再向西北经英吉沙尔到喀什噶尔[10]。
除了连接东西的交通干道外,也有两条翻越天山,沟通北疆和南疆的台站道路。一是从乌鲁木齐翻越天山至吐鲁番,再从吐鲁番向西至南疆各主要城市,此路比较平坦,但距离遥远。一是从伊犁到阿克苏之间的道路,这条道路要翻越俗称冰岭的穆素尔达坂,雪急风大、路陡冰滑,道路极为艰险,但这条道路距离较近,对于沟通南北相当便捷。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新疆的叛乱,使得新疆台站体系遭到极大破坏。战争平息之后,新疆的台站才得以重建和逐步恢复。新疆建省以后,新疆的台站一律改为驿站,归属地方州县管辖。
交通对于经济文化的交流意义重大,正是由于清朝政府在新疆建立起来的较为发达和完善的台站交通体系,才使得新疆与内地、新疆各地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经济文化的交流也更加频繁。
[1]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5.
[2]吴轶群.清代新疆人口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01:18-25.
[3][清]王树枬.新疆图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成崇德.清代西部开发[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128-157.
[5][清]魏源.《圣武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1:166.
[6]潘志平.清代新疆的交通邮传[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2):34.
[7]金峰.清代外蒙古北路驿站[J].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3):77-102.
[8]金峰.清代新疆西路台站(一)[J].新疆大学学报1980,(1):60-73.
[9]金峰.清代新疆西路台站(二)[J].新疆大学学报1980,(2):102.
[10]刘文鹏.论清代台站体系的兴衰[J].西域研究,2001,(4):31.
(责任编辑:赵旭国)
Brief Account of Human Environment of Xinjiang Cultural Changes in the Qing Dynasty
YANG Fa-peng,HUANG Ting-ti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Shihezi University,Shihezi 832003,Xinjiang,China)
With the reunite of Xinjiang by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its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Xinjiang,the Xinjiang culutre in the Qing dynasty witnessed tremendous changes.In addition to the impact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the changes of the Xinjiang cultur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ocal humanist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mong which the territory of Xinjiang,the government district,military, population,ethnic,economic,urban,traffic and other factor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volution of Xinjiang culture.
Xinjiang in the Qing dynasty;cultural change;humanist environment
K249
A
1671-0304(2015)01-0119-06
2014-09-10
时间]2015-01-20 13:41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清代新疆文化地理变迁研究”(13YJA770040)
杨发鹏(1972-),男,甘肃临洮人。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西北历史地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