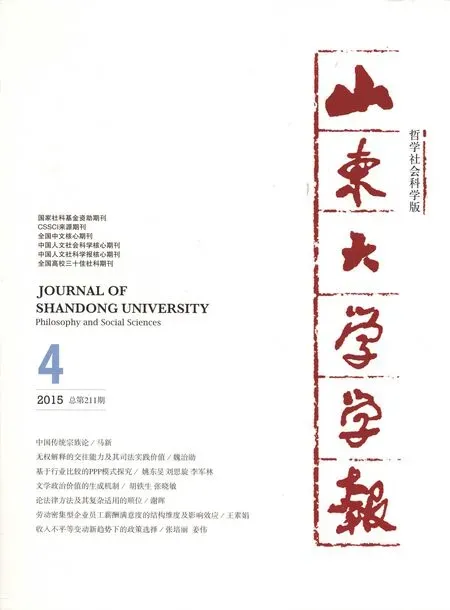中国传统宗族论
马 新
中国传统宗族论
马 新
研究中国传统宗族,必须从宗族与宗法血缘关系的内在结构与外在影响出发,对传统宗族进行客观的历史分期,尔后才能明确其范畴及其特征。中国传统宗族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宗族萌生到春秋时期;后期自战国秦汉直至现代。在这一大前提下,后期宗族又可划分为各具特色的三个阶段:自战国到唐前期的中古宗族,自唐后期到明清时期的近古宗族,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现代宗族。前期宗族是具有共同的生产、共同的财产、共同的组织与首领、共同的武装、共同的教育与信仰、共同的祖先等等的宗法血缘共同体;后期宗族则是具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组织与首领以及在生产、财产、教育等方面有一定共通关系的宗法血缘共同体。宗族与宗法血缘关系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标志性内容,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传统宗族;家族;宗法血缘关系
中国文明的发生走的是一条与经典道路不同的路线。它的发生既不是在商品经济与私有制的形成中,也不是在以地域关系编制民众以取代血缘氏族组织时,而是在商品经济尚未出现、私有制尚未正式形成之时。在中国文明的形成中,宗法血缘关系非但未被冲破,相反,还处在不断的强化之中。①详见马新:《中国远古社会史论》第五、六章,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夏商周的政治组织体系,实际上就是宗法血缘体系的复制与放大;战国以降,虽然在郡县制的实施中实现了以地域关系编制其国民,但在广大的乡村社会,宗法血缘关系并未消失,在多数时代的多数地区,依然是最为重要的乡村居民组织关系。村落实质上是地缘外壳与血缘内核的组合体,宗族与宗法关系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依然把“族权”看作束缚乡村人民的四大绳索之一。因而,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宗族与宗法血缘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中国传统宗族范畴的界定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是最为突出的社会存在之一。对于宗族与宗法血缘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意义,学界也给予了充分重视,但由于现有理论体系和中国传统社会实际状况的种种差异,导致在基本范畴上歧义甚多。要言之,大略可归为六说:
其一是血统说。该说强调血统体系在宗教组合中的意义。如陈其南先生提出:
宗族之称不过是证明以父系祭祀关系,即所谓“宗”所界定出来的群体这个宗族群体可以是缺乏实际社会功能的人群范畴(category),也可以是带着各种不同功能作用,彼此互动的社会团体(group)。②陈其南:《家族与社会——台湾和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217页。
这一范畴的界定是依据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而作出的。与之相类似的观点还有一些,如徐烺光先生认为:“所谓宗族,是一种沿男系或女系血统直接从家庭延长了的组织。”①[美]徐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薛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63页。程德祺先生也认为:“介于氏族和家庭公社之间的经济单位,无疑就是宗族公社。”②程德祺:《原始习俗与宗教信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74页。
其二是服制说。该说以丧制礼仪所确定的血族亲疏关系界定宗族、家族与家庭。如杜正胜先生即认为:
凡同居或共财的称为“家庭”,五服之内的成员称为“家族”,五服以外的共祖族人称为“宗族”。同居共财的范围最大到大功。③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67页。
其三是血缘组织说,即宗族不仅是血统的界定,而且是在这一前提下有组织、有制度的血缘集团。如王玉波先生认为:
宗族不仅是比家族更大的血缘集团,而且,在宗族内部还存在亲属贵贱的等级关系和相应的行为准则,即宗法。④王玉波:《中国家庭的起源与演变》,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52页。
常建华先生则进一步提出:
宗族已成为一种制度,即它是宗族活动有组织的系统,以祖先崇拜把族人结合在一起,强调共同体意识和互助精神,并有相应的规范。这一制度表现在祭祀先祖和睦族人的庙制,包含继承、分支、管理的大小宗制,五服亲属制度,最基本的组织是家庭。⑤常建华:《中华文化通志·宗族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页。
其四是社会组织说,即宗族是在宗法纽带下组成的社会群体。费孝通先生即认为:“所谓族是由许多家所组成,是一个社群的社群。”⑥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39页。钱穆先生则从“族”字的本义入手,分析古人观念中的族究竟为何物。此说本《说文》段注。《说文·方人部》:“族,矢锋也。束之族族也。从方人从矢。”段玉裁注:“旌旗所在而矢咸在焉,众之意也。”⑦[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12页。亦即众之所聚为族。由此钱穆先生认为,“族”字是一面旗与一支箭,同族即在同一旗帜下的作战者⑧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台北:正中书局,1951年,第94页。。何启民先生也持此说。他提出:
家族不仅是一个出自同一祖先的血缘团体,也是祭祀同一祖先的宗教团体;在古代,更是隶属同一旗帜的战斗团体。⑨何启民:《鼎食之家——世家大族》,刘岱总主编、杜正胜主编:《中国文化新论·社会篇》(吾土与吾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第41页。
其五是复合组织说。此说认为,宗族既是一种血缘组织,又是一种地缘社会组织,其实质是以豪强族长为核心的共同体。如贺昌群先生认为,宗族是古代以血缘关系、地域关系构成的(氏族公社的残余)集团,其存在有下列一些条件:
(一)宗族的家长豪强表面上以土地为共同体,实际是家长豪强垄断一个宗族所以聚族而居的物质基础;(二)虽不限于部落的形成,聚居一处,但必须有紧密团结的呼应关系……(三)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祭祀,作为对宗族成员的精神感召。……(四)要具有经济的调剂措施,以掩盖宗族内部的贫富对立和阶级矛盾。⑩贺昌群:《关于宗族、宗部的商榷——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
其六是财产关系说。此说以是否同居共财作为区别家庭与家族的标准。如徐扬杰先生认为:
一般说来,家庭和家族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这类社会组织中,家庭是个体,是基础,家族则是群体,是家庭的上一级的组织形式。正如前面说到的族字的意义,就是将许多个体家庭束在一起的意思。家庭和家族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同居、共财、合爨,家庭是同居、共财、合爨的单位,而家族则一般地表现为别籍、异财、各爨的许多个体家庭的集合群体。①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页。
岳庆平先生也持此说。他提出:
家庭范围较小,是一同居共炊共财单位;而家族范围较大,不是同居共炊共财单位。②岳庆平:《家国结构与中国人》,香港:中华书局,1989年,第5页。
除上述六说外,还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很多自成体系的论断,也颇具启发意义。如程维荣先生以较为综合的方式定义宗族,说:
宗族,由原始社会后期父系家长制的氏族与部落转化而来,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它是以拥有同一祖先的血亲关系为核心、以配偶和姻亲关系为补充,所有成员均处在一定的长幼尊
卑地位的一种人群集合体。③程维荣:《中国近代宗族制度》,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序言”,第3页。他还从狭义与广义两个方面进行宗族的划分,指出:
狭义的宗族,由同一曾祖或高祖的若干家族所构成。广义的宗族,包括家庭、家族、宗族、族系四层概念,即由一对夫妻及其子女二代,有时还有其祖父母共三代所构成的共同生活的家庭;由若干独立生活的兄弟家庭所构成的宗族;由同一曾祖或高祖的若干家族所构成的宗族(即狭义的概念);由同一始祖、居住在一个或相邻乡村的若干有远亲关系的宗族所构成的族系。④程维荣:《中国近代宗族制度》“序言”,第3页。
这一划分方法比较精细。但也正因为此,在现实社会中,这种区界清楚的家庭、家族、宗族与族系体系并不存在。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宗族问题一直得不到学术界所公认的界定呢?我们认为原因有三:
第一,当代学者对中国古代宗族问题的研究所使用的理论方法多是西方舶来或是源自西方的,无论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还是民俗学、行为组织学等等,都是如此。而在宗法血缘关系问题上,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二者没有共同的语境,以另一环境下生成的理论范畴去剖析中国古代之宗族社会,自然歧义迭生。如英语中的familly、法语中的famille、德语中的familie,大致相当于中文的家庭或宗族,这三个单词都源自拉丁语familia,从语源和其本义看,与中文的家庭或家族并不那么贴切。法国学者安德烈·比尔基埃曾对“famille”的词源与演化进行讨论。他提出:
这种一词多义的情形显然证明这个词所指的这一组织在历史上几经变换。familia是个拉丁词:它出现在罗马,从famulus(拉丁文,意为“仆人”)派生出来,但是它与我们平常对这个词的理解并不符合。“Familia大概指的是生活在同一屋顶下的全体奴隶和仆人……后来又指maison,一方面是主人,另一方面是在主人统治之下的妻子、儿女及仆人……后来词义扩展,familia又指agnati和cognati,成了gens这个词的同义词,至少在日常用语中是如此。”Maison是指生活在同一屋顶下的所有的人;gens是指同一祖先的所有后代组成的共同体;agnati是指父系亲属,cognati指母系亲属,后来词义扩展,指血亲的整体。这些不同的亲族单位,我们如今将其统统集合在“famille”这同一个名词之下。⑤[法]安德烈·比尔基埃等主编:《家庭史》第1卷《遥远的世界 古老的世界》上册,袁树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314页。
由这段讨论我们可以看到,“famille”是家庭和其他亲缘组合的泛称,无法与中文的家庭与宗族相对应,即便是曾经存在的代指父系亲属的agnati和代指母系亲属的cognati,也无法直接对应为宗族或家族。
第二,在中国古代的有关范畴中,宗族与宗法血缘关系是一个既清晰又模糊的概念。这必然给后世的研究者造成莫大的困惑与混乱。言其清晰,是指在宗法层次关系上的明确,既有“上凑高祖,下至玄孙”①[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八《宗族》,《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98页。的纵向层次,又有自缌麻至大功的五服之制。言其模糊,是指作为宗法血缘共同体的家族或宗族一直没有明确的内涵和清楚的外延。在中国古代人的观念中,宗与族是一个集合体,对这一集合体的常用表达是“宗”、“族”、“宗族”、“亲族”、“族党”、“九族”等等,而每一个概念都没有明确的定义,又几乎都可通用。如对“宗族”的经典解释,简明版当属《尔雅》所言:“父之党为宗族”②[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卷四《释亲》,《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93页。,繁缛版当属《白虎通》所言:
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礼》曰:“宗人将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
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③[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八《宗族》,《新编诸子集成》本,第393394、397398页。
事实上,《尔雅》与《白虎通》都未能讲清宗族的内涵与外延,宗族仍是一个说不清的模糊概念。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的宗族本身就是一个外延模糊的集合体。
第三,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族与宗法血缘体系自上古至现代,绵延数千年,其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各个阶段又各具特色,有时还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难以给中国传统宗族下一个一言以蔽之的定义。我们必须从宗族与宗法血缘关系的内在结构与外在影响出发,对传统宗族进行客观的历史分期,尔后才能明确其范畴。
二、中国传统宗族的分期
宗族与宗法血缘关系的内在结构主要是指个体家庭与家族的关系,其外在影响主要是指宗族组织与国家政权组织的关系。基于这两个要素,中国传统宗族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宗族萌生到春秋时期;后期自战国秦汉直至现代。
(一)前期宗族
前期宗族又可称之为“上古宗族”,主要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国与族的一体性;二是家与族的一体性。
所谓国与族的一体性,是指国家政权组织自上而下都与宗族及宗法血缘组织相一致,各级政治组织其实就是各类宗法血缘组织。对此,我们可以以殷商为例说明之。
殷商王朝是以氏族为一级统治单位,氏族既有其土地,又有其甲兵;同时又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宗法血缘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内实现着分层与管理,进行着从祭祀到生产到社会分配的所有活动。
从晚商卜辞资料可以看到,每一个氏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活动空间或者可以说是领地范围。在各宗族自己的领地内,宗族首领们有其武装,有其经济与政治权力,宗族实际上是领有一方土地的军事、政治、经济共同体。在商朝的宗族系统中,可以分为王族、多子族与多生(姓)族三个大类。王族当然是商王所在之大宗,多子族则是各王子之族。至于多生族,当如张政烺先生所言:“多生即多姓,即许多族的族长,在周代铜器铭文里,百姓亦写作百生。”④张政烺:《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历史教学》1951年第3期。王族居于王畿,多子族亦多环王畿而居,也有一些较为疏远的同姓宗族被派驻到西部地区,作为商王朝之屏障,抵御外族侵扰。异姓宗族或作为姻族交叉于内地,或作为臣藩分布四处。
对于氏族的性质,学界多有岐义。我们认为,可以从血缘与地缘两个角度探讨这一问题。
从宗法血缘关系上看,氏族中既有王族,又有子姓氏族,还有多生氏族。从地缘关系与社会关系看,氏族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受封一方土地或建方国者。如《史记·殷本纪》载“太史公曰”:“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①《史记》卷三《殷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9页。其中一些既有其封地又有其封爵者,则可二者连署。如子儿又称“儿伯”,子宋又称“宋伯”,子奠又称“侯奠”,等等。另一类则是以职为姓者。这种以职为姓者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职业为姓者。如晁福林先生所言:“除了这些‘以国为姓’者外,还有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其中大部分以职业为姓。”②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15页。以职业为姓的氏族主要集中于商都附近,直接为王族从事各种专业生产。另一种则是以官职为姓者。如子姓氏族之长担任中央王朝之多尹,便可称“子尹”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小屯南地甲骨》341,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任职于王室之氏族长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氏族就在王室附近,为商王之近支;另外就是居于远处有其领地与方国者也可在王室任职,如远居东北的孤竹氏族,其族长曾任商王室亚职,其姓便可称“亚微”。
氏族之下,也是宗族血缘组织与地方基层组织的合一,其分层较为复杂,以二级制和三级制较为普遍。从商代聚落考古资料看,城邑外的各种聚落多分为二级:一级聚落属于中心性聚落,可称为“宗邑”;二级聚落属于普通聚落,可称为“村邑”。
无论是村邑还是宗邑,其基本组织状态都是宗法血缘关系的组合。具体而言,都是聚族而居,一个村邑或一个宗邑是由一个或若干个家族组成。如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即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宗邑,它有1所大房子和3个以上单元的住宅。大房子共2间,50平方米左右,建在宗邑北头,应当就是宗邑的公房,而公房的存在又是宗族组织存在的重要体现。与之相邻的第二单元院落,由至少4间单室和1个套室组成,当系有直接血缘关系的5个个体家庭分别居住,可视之为一个父系大家庭或一个家族所居,该院落中有殉人坑和牛、羊、豕三牺牲坑各1个,应当是宗族长所在之家族。第三单元院落应当居住着6 7个有直系血缘关系的个体家庭。其中,F6各室为统一建造,F1系家族成员增加后新建,这本身也说明了血缘家族的客观存在。其余情况不详的2 3处院落当与之类似。④参见王震中:《藁城台西邑落居址所反映的家族手工业形态的考察》,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4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62174页;李捷民等:《河北蒿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6期。由此看来,台西邑落遗址中居住着3 5个家族,由唯一的一所大房子和各家族居院落规划性又可知,这些家族同处于一个宗族之中。
山东平阴朱家桥商代遗址则是较为典型的村邑,共发掘21座房屋,均为单室建筑,但又明显地分为2个组合。发掘报告称:
由于发掘面积较小,不足以了解该村落的全貌,但是,大概的分布还可以看得出。房基密集的地方是村落的中心区,另一个聚居区在离中心区40米的东边。至于中心区的南边、北边也有居住的遗迹,然而却很稀疏。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平阴县朱家桥殷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2期。
看来,该邑落有2个住宅组合,相距40米左右。与之相对应的是,邑落外的墓地也分别集中在西部和西南部两处。这些可以说明该邑落居民由2个小型家族组成。
从台西和朱家桥两处遗址的情况我们可以认为,殷商时代的宗邑与村邑,都是由一个或若干家族组成的,也就是“庶人、工、商,各有分亲”,是体现在各个社会阶层中的。那么,大大小小的邑落中,各家族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认为,殷代邑落分布的群聚性可以为我们提供答案。如对山东泗水流域商代聚落布局的调查表明:
聚落成群分布,间距一般2 4公里,非常密集。每个聚落大都贯穿整个中商时期,说明聚落及所反映的社会组织和结构是稳定的。①燕生东、王琦:《泗水流域的商代——史学与考古学的多重建构》,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4集,第143页。也有学者对晋南商代聚落遗址分析道:
晋南商代聚落遗址的分布,显示了每一个盆地都有一个中心聚落。这些中心聚落遗址如东下冯商城、垣曲商城等,均为若干小型村落环绕,形成二级聚落等级。②陈朝云:《商代聚落模式及其所体现的政治经济景观》,庆祝李民先生七十寿辰论文集编委会编:《中国古代文明探索——庆祝李民先生70寿辰论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8页。
由上述聚落群的状况我们认为,村邑与宗邑的关系,也就是家族长所在之家族邑落与其他分支家族的关系。如是,一个邑落组合就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家族组合。在这种家族组合中,村邑家族只是生产单位,而不是独立的经济、政治、军事单位,这些村邑最大的特点是普遍的贫困化,没有财富集中于一室一户的权力人物,也没有祭祀、军事等功能;宗邑及其所统领的村邑家族则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经济、军事与祭祀单位。③以上对于殷商村落形态的论述,参见马新:《殷商村邑形态初探》,《东岳论丛》2010年第1期。
所谓家与族的一体性,主要是指个体家庭尚不具备完整性,仍被包含在家族之中,两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以西周时代为例,这一时期,家族是最为基本的社会组织,个体的小型家庭即核心与直系家庭只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每一农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家室居所、相对独立的家庭生活;家族则是基本的生产单元与社会活动单元,从生产的组织到具体劳作直至基层社会组织的构建,都以家族为基本单元。
从社会生产与经济活动的组织看,无论是公田、私田,还是国中庶民的土地都是以家族为单位的集体耕作。《诗经·周颂·载芟》:“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彊侯以。”《毛传》:“主,家长也;伯,长子也;亚,仲叔也;旅,子弟也。”④[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十九《周颂·小毖》,《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01页。因此,参加“千耦其耘”的“主”、“伯”、“亚”、“旅”均应为同族之人。
从祭祀与其他社会活动看,主要也是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的。祭祀的家族性是由其祭祖特性决定的,西周乡村居民的最大特征是“死徙无出乡”⑤[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十《滕文公上》,《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58页。,同祖子孙聚居为族,因而祭祖就是族祭。郑玄所谓“出必共洫间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欢”⑥[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十九《周颂·良耜》,《十三经注疏》本,第602页。就是指此。《诗经·周颂·载芟》:“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又《良耜》:“杀时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续,续古之人。”朱熹注:“续,谓续先祖以奉祭祀。”⑦[宋]朱熹注,杨端志、周晓瑜校理:《诗集传》,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7、188页。当是。
如前所述,此期聚落之居民基本为同一宗族,因而各种社会活动自然也就是宗族性活动。如各种节庆、祭祀、婚丧嫁娶活动等等,都应如此。每到年末岁终,一族之人会聚于族中公堂,共享丰年。如《诗经·豳风·七月》所咏:“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⑧以上有关西周宗族形态的论述,参见马新:《乡遂之制与西周春秋之乡村形态》,《文史哲》2010年第3期。
(二)后期宗族
战国时代井田制的废止与授田制的推行,将土地所有权由宗法血缘组织的层级占有转化为国家君主所有。授田制下,以一夫一妻为主体的小型家庭成为基本的生产单位、生活单位以及社会活动单位。其原因前人已多有论述,诸如生产力的发展使一家一户的独立生产成为可能,集体耕作制对生产者积极性的压抑以及宗法血缘关系的解体与授田制的互动,等等。多数统治者都意识到了向小家庭授田、推进个体劳动的必要性。正如《吕氏春秋·审分》云:“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①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十七《审分》,《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31页。故纷纷“均地分力,使民知时”②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一《乘马》,《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1页。。个体小农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的小农不仅 “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③《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25页。,“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百亩之田,匹夫耕之”④[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二七《尽心上》,《新编诸子集成》本,第911页。,而且要“及上赋敛”,参与“社闾尝新春秋之祠”,公摊族内“不幸疾病死丧之费”⑤《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第1125页。,等等。这表明小家庭既是基本的生产单位、社会活动单位,又是基本的赋役承担单位。与之相应,既然宗族已不是基本的社会单位,个体小农则转而被编制在以地缘关系为基点的乡里组织之中,成为君主直接管理下的编户齐民。这样,上古宗族所体现的族与国的一体性及家与族的一体性都被打破,中国传统宗族进入到后期宗族时代。
后期宗族的主要特征是家与族的两合性。一方面,在“编户齐民”之制下,家不仅是婚姻与生活单元,还是相对独立的生产单元与社会单位,所有家庭都是直隶于天子的“编户齐民”。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家与族是分离着的两个内容。另一方面,“族”又通过宗法血缘关系将“家”罗织在其中,而这种宗法血缘关系数千年来一直是清晰明确的,从五服之制到族长、族规与族谱,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与组织。从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家”在“族”中。当然,从整体上讲,家相对于族的独立是根本特性。
此后两千年宗族的演进都是在这一根本特性下进行的。在此基础上,家与族的两合性一直得到充分体现。根据家与族的两合性关系的演进状况,后期宗族又可划分为各具特色的三个阶段,即:自战国到唐前期的中古宗族;自唐后期到明清时期的近古宗族;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现代宗族。
1.中古宗族
中古宗族的突出特色是内在组织与功能的弱化以及身份性特权的附加。所谓内在组织与功能的弱化是相对于前期宗族而言的,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古宗族是“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也就是以九族为限,超出九族,即不再视为同一宗族。这在两汉史料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证。如《汉书》云:“郇越、相,同族昆弟也,并举州郡孝廉茂材,数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余万,以分施九族州里,志节尤高。”⑥《汉书》卷七二《鲍宣传》,第3095页。朱邑 “身为列卿,居处俭节,禄赐以共九族乡党,家亡余财”⑦《汉书》卷八九《朱邑传》,第3636页。。进入东汉后,此类材料比比皆是。如刘般“收恤九族,行义尤著”⑧《后汉书》卷三九《刘般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06页。;宋弘将“所得租奉分赡九族”⑨《后汉书》卷二六《宋弘传》,第903904页。;《四民月令》也多处规定要“存问九族”⑩[东汉]崔寔撰,缪启愉辑释,万国鼎审订:《四民月令辑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37、94、98页。;等等。
其次,中古宗族只是社会活动单位,并非像西周春秋时代那样具有地缘与血缘组织合一的功能,其社会活动主要是族人会议、节庆婚丧的组织、祭祖等。以祭祖为例,各宗族之族长并不独占祭祖之权,一宗之中的所有成员均可祭其祖先。如《四民月令》所记正月元旦的祭祖仪式:
正月之旦,是谓正日。躬率妻孥,洁祀祖祢。前期三日,家长及执事,皆致斋焉。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家室尊卑,无小无大,以次列坐先祖之前,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⑪[东汉]崔寔撰,缪启愉辑释,万国鼎审订:《四民月令辑释·正月》,第1页。
复次,中古宗族只是一种经济互助单位,与西周春秋家族之作为经济生产单位大不相同。两汉时期这种同宗族内的经济互助,首先表现在富室宦门对贫弱宗人的救恤。这类记载十分常见,如东汉韦彪“清俭好施,禄赐分与宗族,家无余财”①《后汉书》卷二六《韦彪传》,第920页。;宣秉“所得禄奉,辄以收养亲族。其孤弱者,分与田地,自无担石之储”②《后汉书》卷二七《宣秉传》,第928页。等。但,这只是一个方面。除了这种单向式的救恤、施舍外,中古时期的宗族中还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经济行为,残留着原始家族财产公有的痕迹。如刘秀起兵后,“分财物不均,众恚恨,欲反攻诸刘。光武敛宗人所得物,悉以与之,众乃悦”③《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上》,第3页。。从这一事例中,我们似乎能捕捉到宗族财产中的微弱的一线公有遗存。当然,这种财产共有的痕迹已十分微弱,在宗族内部,各家庭都是独立的经济单位,宗族本身已丧失了其作为经济共同体的功能。④详见马新:《论两汉乡村社会中的宗族》,《文史哲》2000年第4期。
所谓中古宗族身份性特权的附加,主要是相对于近古宗族而言。
两汉之交,随着中古宗族的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拥有大片土地、在地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强宗豪族不断涌现。至东汉时代,豪族不断地经学化和武装化,他们开始垄断地方政治,控制地方社会,由此演化为魏晋南北朝至唐初的世族门阀政治。在这一大背景下,宗族首领往往拥有多少不等的身份性特权。士族之特权自不待言,“上品无寒门,低品无士族”是其政治特权的真实写照,其经济特权则体现为占田式及荫客荫亲属之制。自西晋以来的荫客荫亲属制,使士族及其宗亲往往有制度上的连带特权。《晋书·食货志》所记西晋之荫亲属制,规定自第一品荫及九族到第九品荫及三世,这是最为重要的连带特权,再加上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都拥有的荫亲属特权,其范围已相当大了,宗族中或家族中只要一人仕官或者前有人仕官,或前为士人,都可获得自三世到九族不等的连带特权。
一些世族之外的强宗大族虽然不能拥有士族那样的身份性特权,但他们往往通过出任地方掾吏或主政乡里获得多少不等的经济与政治特权。如北魏初期之宗主督护就十分典型,史称:“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⑤《魏书》卷一一○《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55页。,“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⑥《魏书》卷五三《李冲传》,第1180页。,而“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⑦《魏书》卷一一○《食货志》,第2855页。。可见,宗主督护基本为豪强充斥,且享有充分的权益。
至三长制确立后也是如此。“今之三长,皆是豪门多丁为之。”⑧《魏书》卷八二《常景传》,第1804页。此“豪门”当然是指强宗,但“多丁”则或可是庶民宗族。依三长制,一党百户,有党长一人,还有闾长、邻长,合计“有帅二十五人”,而且从党长到邻长都可享有不等的免疫与阴户特权。除党长外,闾长与邻长应当多是由庶民宗族之族长而为之。
2.近古宗族
近古宗族始于唐后期,但促成中古宗族向近古宗族转变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则发生得更早一些。在隋与唐初,社会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变化是中央集权政体的强化,包括府兵制的规范、科举制的全面实施、《氏族志》的重修等。当然,这些变化不是一夜之间的突变,许多变化在南北朝时代已经开始。
众所周知,中古时期的强宗大姓往往又是一个军事集团,无论是世家大族,还是乡里豪强,其影响力直接植根于所拥有的武装力量。而北周府兵制的实行,则开启了将乡豪武装中央化的进程。至隋唐时代,更是统一全国的军士征调与管理,宗族私家式武装已无生存空间,这对于中古宗族的消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炀帝时代,又开通了科举取士制度,使才学成为入仕的基本途径。唐王朝时代,更是全面实行科举制,使科举取士成为官员补充的最为重要的途径。这些变革的直接结果是剥夺了世家大族的入仕特权,也剥夺了旧有宗族集团的政治权力,既不可以以世族任于中央、州郡,又不能以宗族之力量被辟用于郡县,宗族的政治凝聚力大为消解。其结果是形成了较为典型的文官集团,而旧式的乡里豪族则失去了发展的政治基础。
唐修《氏族志》,对于世族与旧式宗族的冲击也较为突出。尤其是高宗时代将《氏族志》,改名为《姓氏录》,完全不考虑以往士族的地位,而是一律以官品高下,将五品以上官员全数列入,即使是士卒,也以“军功入五品者,皆升谱限”①《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42页。。这实际上完全否决了士族的身份与特权,在制度上宣告了士族的终结。②以上关于中古宗族向近古宗族的转变,参见马新、齐涛:《试论唐代宗族的转型》,《文史哲》2014年第2期。
总之,中古宗族身份性特权的消解与外在功能的弱化,大大降低了宗族的社会影响力,唐代宗族在中国古代宗族发展史上明显处于低落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宗法血缘组织开始转向宗族内部的体系与组织经营,近古宗族的特征开始出现。
安史之乱后,两税法取代均田制与租庸调法,其核心则是赋税体系开启了由税人向税地的历史性转折。在这一转折过程中,原先繁重的面向所有人的管理被忽视。乡政削弱,由各里里正轮流充担乡正之职,宋代更是出现了乡村管理人员的职役化与乡级行政机构的虚拟化。③详见马新:《试论宋代的乡村建制》,《文史哲》2012年第5期。为了应对乡政的削弱,防止乡村社会可能出现的混乱与失控,宋明时代均在乡村推行保甲法或里甲法,但在乡政损弱的情况下,保甲与里甲的效能发挥必须寻求新的依托,与乡里体系长期并存的宗法血缘体系是唯一的、也是最适宜的选择。而面对乡政的遗失与乡村部民的分散化与相对自由化,宗族体系的扩大与功能的延伸也成为历史的必然,两者的结合点是乡约的宗法化,其实质是宗族体系的社会组织化。随宗族体系的社会组织化俱来的,是宗族事务的制度化,具体体现是族谱、族规的规范与普及;与之相应,随着宗族事务的制度化以及宗族体系的社会组织化,乡村宗族的实体化也就不可避免,宗祠、族田、族学奠定了实体性宗族的基点。
近古时期乡村宗族体系的社会组织化有两个基本表现:
一是宗族组织的社会组织化。宗族在多数情况下只是宗法血缘关系共同体,是民间组织的范畴,与国家政权体系无涉。但在宋明时代,一些地方出现了宗族组织与官方乡里组织交叉甚至合一的现象。比如,明代江南有的地方,“其一族有千家以上者,则立保长三四人”④[明]吴应箕:《楼山堂集》卷十二《江南弭盗贼议》,《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8页。,宗族与保甲实现了结合。在推行地方乡约的过程中,更是如此。如明代江苏井阳姜氏宗族之例即很典型。由姜宝所撰《议行乡约以转移风俗》一文可以看到,姜宝在其宗族内也是乡约与保甲并行。他提出:
乡约之行于民间,风俗甚有益,其与保甲法相兼行者,则善俗而弭盗,于民间尤更有益者也。第在长民者实意行,又能选择约正副、保甲长得其人,斯善矣。⑤[明]姜宝:《姜凤阿文集》卷二十《议行乡约以转移风俗》,明万历年间刊本。
其具体做法是:“改乡约为宗约,以宗约行,又以保甲法相兼行”;“不令他姓人得参与有所妨”。⑥[明]姜宝:《姜凤阿文集》卷二十《议行乡约以转移风俗》,明万历年间刊本。在此,乡村宗族实现了与乡里组织体系的完全贯通。
二是宗族功能的社会组织化。所谓宗族功能的社会组织化,是指本为民间血缘组合的宗族具有较多的社会组织的功能,这一点在宋明时代较为突出。在相当广泛的地区,宗族已成为基本的社会组织,宗族功能中包括了众多的乡里组织的功能,已成为官方体系的延伸。具体而言是宗族对官方的认可与协助、官方对宗族的认可与授权。
许多的宗约族规都将对王朝国法的恪守作为重要旨归。比如,明代朱元璋的“圣谕元言”、清代康熙的“上谕十六条”等就常被直接使用。还有的宗约族规直接引入朝廷律法。清乾隆时代,浙江绍兴阮氏曾“就国法所严人情易犯者,订为二十条,编入家规”①[民国]《越州阮氏宗谱》卷十九《家训》,转引自常建华:《中华文化通志·宗族志》,第461页。。写在宗约族规中的这些“规劝”,较之官府的公文告示,其作用不知胜过多少,起到了公文告示所难以起到的作用。
官方对宗族的认可主要表现为对族规与族长的认可。一般情况下,官方对各宗族族规是默认的,认可族规在一定范围内的民事与刑事的司法裁量作用。也有许多宗族为了增强宗约族规的权威性,要求官府核批,经官府核批的宗约族规更是朝廷法律的直接延伸。官府核准认可宗约族规起于北宋,至明代万历时形成高潮,清代宗族向政府申请批准者也不少见②参见常建华:《中华文化通志·宗族志》,第468469页。。需要指出的是,地方官府对于这些族规并非简单的核准,而是赋予其法律地位,要求族众必须遵循;否则,官府要加以惩处。如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安徽歙县在核准朱氏宗族族规的告示中规定:
为此示仰朱姓通族人等知悉,务宜遵守家规,取有违约不遵者,许约正族长人等指名呈来,以凭究处,以不孝罪论,决不轻恕,特谕。③《朱氏祠志》,转引自张海鹏等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年,第33页。对此,英国著名学者莱芒·道逊曾总结道:
官府承认族长有权在族内执掌刑罚,宗族组织实际上成了最低一级的司法机构。族长的处罚权限包括罚款、笞杖、褫夺族规赋予的应享权力,逐出族门和名字不得载入族谱。④[英]莱芒·道逊:《中华帝国的文明》,金星男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88页。
事实上,在清朝的许多地区,除族长外,还另有族正之职,便是“官给牌照”的宗族首领。雍正四年(1726)曾规定:
如有堡子、村庄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遍查者,拣选族中人品刚方、素为阖族敬惮之人,立为族正。如有匪类,报官究治,徇情隐匿者与保甲一体治罪。⑤《清文献通考》卷二三《职役三》,《万有文库》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
此后,福建、广东、江西等地曾大力推广族正制。从各地实施情况看,族正最初以族内治安为主,但事权渐广,在许多情况下能居族长之上。族正的产生是先由族内推举,再由官府认可。这是官府对宗族权力认可的典型内容。
3.现代宗族
现代宗族是宗族制度的瓦解期。自1911年至1949年,宗族制度处在不断的冲击中,这种冲击主要来源于制度变动与社会变动。自清末至民国,当政者为应对社会危机,重构社会制度,进行了种种制度变革,而在一次又一次的制度变革中,宗族制度一直是无法回避的变革点。1911年8月,清王朝覆亡前夕颁布的《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国的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民律,该律将宗祧继承归入亲属编,而亲属编的核心是家庭,这实际上将以宗族为中心的宗祧继承功能转变为调整同宗家庭关系、维系基本家庭关系为主要功能。1930年,民国政府所颁行的《中华民国民法》则正式废除了宗祧继承制度。至此,宗族制度在法律上已告终结。⑥参见程维荣:《中国近代宗族制度》,第236、270页。在制度变动的同时,随着近代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流动以及城市化的进程,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着宗族的裂变与宗法血缘关系的淡薄。不过,就总体情况而言,宗族势力及其影响力仍然十分强大,尤其是在乡村社会,宗族与宗法血缘关系的影响力亦不亚于近世社会。
从上述原因出发,我们认为,如果给宗族作出一个统一的定义,只能是宏观的定性描述,即:宗族是以父系血亲关系为纽带的宗法血缘共同体。若要进一步明确描述,则应以这一共同体共同点的多少区分前期宗族与后期宗族。如前所述,前期宗族是具有共同的生产、共同的财产、共同的组织与首领、共同的武装、共同的教育与信仰、共同的祖先等等的宗法血缘共同体;后期宗族则是具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组织与首领,以及在生产、财产、教育等方面有一定共通关系的宗法血缘共同体。
三、中国传统宗族的特性
中国传统宗族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阶段都表现出鲜明的特色,这些都可以归之为中国传统宗族的特性。但仅止于此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应当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时段与大空间入手,深入考察中国传统宗族的总体特性,以更加全面地把握其历史本来与历史价值。
讨论中国传统宗族时,最为突出的感觉就是其绵延不绝的发展历史。自文明初生,宗族与宗法血缘关系便与之共生,此后无论朝代如何更迭陵替、社会如何治乱兴衰,宗族一直是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民间组织,有起伏变动,但从未中断。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仍将族权列为当时中国农民身上的四大绳索之首。其中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宗族的原发性。其一,中国传统宗族是与中国古代文明同时萌生的,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生发展中,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宗族的发展与宗法血缘体系的完备,是早期国家形成的基础。①详见马新:《原始家族与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生》,《文史哲》2004年第2期。其二,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一直存在着宗族发生与发展的社会条件,使其能够不断滋生,不断延续。以经济环境为例,中国传统经济一直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农业经济所造就的安土重迁为宗族聚居提供了有力保障,而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流行的家产的诸子均分制,则为宗族生成注入着源源动力。
诸子既然可以平等地从长辈处分得家产,往往会就地生活与繁衍,“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②[唐]白居易:《朱陈村》,《全唐诗》卷四三三,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4790页。,数代之后,便会形成一个自然聚居的宗族。如天复九年敦煌农民董加盈兄弟三人分家时,其家有一块集中的土地索底渠地15.5亩,兄长加盈分得6.5亩,两个弟弟怀子、怀盈各分得4.5亩;另外一些散地的分配是:景家园边地4亩分给加盈,渠地中心长地5亩分给怀子,渠地东头方地兼下头地5亩分给怀盈。房屋是一处正宅和两处相邻的宅子,正宅分给了加盈,正宅南边各有“舍壹口并院落地壹条”,分别给了两个弟弟。③参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05407页。土地与房屋分配中的一些不平均则通过其他财物的分配加以均平。这样分家之后,三兄弟自然是相邻生活,待三兄弟的下一代又要分家时,以每家有二个子嗣计,便会扩展出六个同宗家庭,这样,两代便可形成一个自然聚居的宗族。④参见马新、齐涛:《试论唐代宗族的转型》,《文史哲》2014年第2期。
讨论中国传统宗族时,其外延的伸展性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一般情况而言,任何一种成熟的社会组织都有清晰的外延。中国传统宗族本也如此,其外延便是以九族为限,九族之外,便非族人。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这一外延又较为模糊,往往可以随意伸展。如北朝李显甫,“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⑤《北史》卷三三《李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02页。;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也记此时之“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⑥[唐]杜佑撰,王文锦点校:《通典》卷三《食货三·乡党》,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2页。;至明清时代,此类现象仍然常见。如清初安徽新安一带,“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常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⑦[清]赵吉士辑撰,周晓光、刘道胜点校:《寄园寄所寄》卷十一《泛叶寄·故老杂纪》,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872页。。
李显甫之“诸李数千家”、《关东风俗传》之“一宗近将万室”以及新安之“千丁之族”,充分表明这一宗族已远远超出九族的范围。为适应这种弹性的伸展,中国传统宗法血缘关系中又出现了房分与联谱制度,有效地补充了原有宗族制度。
讨论中国传统宗族时,我们还发现它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具有很强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可以充当社会的调和剂,辅助王朝政权对基层社会的管理。中国传统社会缺少真正的宗教信仰,也没有欧洲历史上庞大的教会组织,宗族也就成为官方政权与普通民众最为重要的纽带。所以,历代王朝都十分注意将宗族组织与宗法血缘关系纳入治国实践中。比如,两汉王朝所强调的三纲六纪:
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①[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八《三纲六纪》,《新编诸子集成》本,第373374页。
在上述三纲六纪的九个方面中,父子、夫妇、诸父、兄弟、族人、诸舅等六个方面属于宗族与宗法血缘关系的内容。可见,汉王朝对宗族作用之重视。又如,宋代朱熹再三强调:“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收世族,立宗子法。”②[宋]朱熹、吕祖谦纂,张京华辑校:《近思录集释》卷九《治法》,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750页。
在多数情况下,宗族也的确不负统治者期望,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地方安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许多宗族往往直接以王朝代言人自居。如清咸丰时代,湖南彭氏“于大清律例中择其有关伦常或无知易犯者谨录之,以俾警觉,以著炯戒”③[清]《彭氏三修族谱》卷一《三修凡例》,转引自常建华:《中华文化通志·宗族志》,第461页。。明清许多宗约族规中都有“急公务”或“完国课”之类的条款。江苏常州张氏家规“完国课”一条规定道:
朝廷之取钱粮也,非以入私橐也,文武之俸出于是,士卒之养出于是,驱除寇兵之用出于是,取之百姓者还为百姓用之,故百姓得以从容安乐,以成其耕耨,以享其安饱也。此何必劳官府之催征,衙役之追促哉。世有拖欠以希宥赦,侵欺以饱私腹者,必不容于天地鬼神,凡我宗族夏熟秋成及期完纳,毋累官私焉,是亦忠之一端而实保家之道也。④[民国]《毗陵城南张氏宗谱》卷二《家规》,转引自常建华:《中华文化通志·宗族志》,第452页。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宗族势力过于强大对王朝政权的冲击与破坏,这种事例也是与传统宗族的发展相始终的。以汉代为例,强宗豪族有公开扰乱地方秩序者。如《汉书·酷吏·严延年传》所言:“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宾客放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张弓拔刃,然后敢行,其乱如此。”也有通过入仕操控地方者。汉代在本籍人士中可以被辟除为掾吏的很少有平民百姓,而是那些在地方上有一定势力或影响的人物。这样,强宗大姓中人便大量地充斥郡县衙署中,成为长吏左右的掾属人员。如东汉第五伦迁蜀郡太守时,“掾史家赀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达”⑤《后汉书》卷四一《第五伦传》,第1398页。。“家赀千万”,道出掾吏的出身背景。翻检一下《汉书》就可发现,出身于强宗大姓的掾吏的确占有较大比重。如尹翁归,河东平阳人,徙杜陵,先后为狱小吏、市吏,后被田延年辟为郡卒史⑥《汉书》卷七六《尹翁归传》,第32063207页。。韩延寿,燕人,徙杜陵,“少为郡文学”⑦《汉书》卷七六《韩延寿传》,第3210页。。郑崇,本为高密大族,祖父时“以訾徙平陵。父宾明法令,为御史,事贡公,名公直。崇少为郡文学史,至丞相大车属”⑧《汉书》卷七七《郑崇传》,第3254页。。到东汉时代,强宗大姓子弟出任掾吏似乎已成惯例。还有起兵争霸者,如在东汉末年的动荡中,“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⑨《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典论》,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9页。。
我们还要看到,在地方社会,不同的宗族拥有不同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宗族间的冲突与争斗是影响社会安定的重大因素,从早期的血族复仇到明清时代的宗族械斗不绝于史,社会与王朝政权都深受其害。
总之,宗族与宗法血缘关系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标志性内容。研究中国文明的发生、文明道路的形成,离不开对宗族与宗法血缘体系的研究;研究中国王朝的变迁、中国传统社会的演进,同样如此。而宗族与宗法血缘关系对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的影响,又绝非简单的二分法所能涵括,必须深入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真正把握其内核,核理其对中国传统社会各方面的浸淫,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中国传统宗族。
A Theor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Clan
MA Xin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Institute,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P.R.China)
To study the traditional clan culture in China,we must start from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external influence of clan and consanguine clan system and divide it into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objectively;only after that can we make clear its categorization and features.Chinese traditional cla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The first stage lasts from the birth of clan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the second stage last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Qin/Han until now.Clan in the first stage refers to the consanguine clan community in which people have the same production,the same property,the same organization and leader,the same army,the same education and belief,the same ancestors,and so on;Clan in the second stage refers to the consanguine clan community in which people have the same ancestors,the same organization and leader,and some common relationships in production,property,education,and so on.Clan and consanguine clan system are the key elements to for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Moreover,they are the symbol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and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society.
China;traditional clan;clan;consanguine clan relationship
[责任编辑:以 沫]
2015-02-16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村落文化研究”(12AZS003)、山东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中国乡村社会通史”(12AWTJ10)。
马新,山东大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