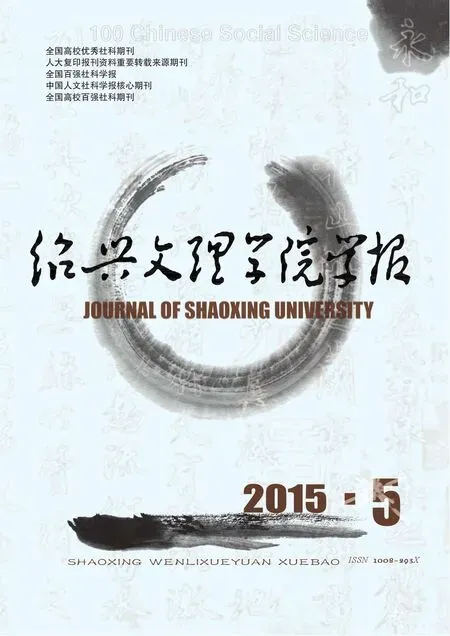绍兴社戏的宗教特性及其当代传承
蒋婷婷
(绍兴文理学院 元培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
绍兴社戏的宗教特性及其当代传承
蒋婷婷
(绍兴文理学院 元培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
社戏是指具有酬神祭鬼性质的戏剧表演活动,它不仅是一种表演艺术,也是一种宗教活动,它通过艺术与宗教的结合,达到人神沟通的目的。绍兴社戏是越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它如同一面通透的镜子,展示着绍兴地区的民俗风情,折射出旧时人们的文化观念与宗教意识。
绍兴社戏;宗教性质;当代传承
社戏作为一种与古老的宗教祭祀密切相关的戏曲表演活动,在绍兴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民众基础。宋代陆游曾写“太平处处是优场,社日儿童喜欲狂。且看参军唤苍鹘,京都新禁舞斋郎”[1],用以形容社戏的演出盛况以及人们对于社戏的喜爱与追捧。社戏不同于传统的戏剧表演活动,它在艺术表演的基础之上结合了宗教的意味,是人们藉以沟通鬼神、表达宗教意愿的重要工具。然而,在城市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媒介技术不断地发展,社戏的宗教意蕴正在逐渐消逝,社戏的功能自然也在这个环境中不断地变化。本文将以绍兴社戏为考察对象,从剧情内容与结构仪式两方面重点阐述社戏的宗教特性,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探析社戏的当代传承。
一、历史源头
社戏的产生与我国古老的祭祀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的历史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时代祭天地、祭日月山川等祭祀仪式。随着历史变迁,这种祭祀仪式逐步完善,到了商周时期,开始出现一些正式的祭祀活动如“社祭”“腊祭”等,同时,开始出现由统治者划分的特定的祭祀区域,这种特定的祭祀区域就是“社”。这种划分有利于商周时期祭祀活动的管理与规范,也为社戏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在祭祀活动进行中,为了使虚幻的宗教内容更加具体形象化,在宗教仪式中经常要穿插到表演。祭祀与表演的结合,一方面使人们更加容易理解虚幻的祭祀内容,另一方面也使人在艺术感官上得到满足。
与商周时期较为严肃庄重的祭祀表演不同,唐宋以后,开始出现更为热闹、欢乐、世俗的祭祀表演,如社火百戏。这些“社火”表演,虽然还不是真正的社戏形式,但是社火百戏中的杂技、歌舞、造型却为后来的社戏奠定了基础。
宋元时期,戏曲逐渐盛行,戏曲的形式融合了音乐、舞蹈、杂技等元素,这种独特而丰富的艺术形式很快被祭祀活动所吸收,成为祭祀活动中最主要的表演形式。社戏“祭祀—戏曲”相融合的雏形开始正式形成了。
纵观社戏的历史起源与发展脉络,不难发现,社戏具备三个重要的元素,场所——社、祭祀仪式及戏曲表演,它是在特定的场所“社”中进行的具有祭祀特性的戏曲表演活动。[2]它的产生及发展始终围绕着祭祀活动,它的原始目的——答神明、祛鬼魅,使社戏成为了一种宗教艺术。
二、宗教特性
社戏不同于纯粹体现审美观念的艺术表演,更重要的是,它是建立人与鬼神沟通的桥梁,所以社戏是给鬼神的献礼。这种特殊的目的决定了社戏表演应该符合鬼神的审美与口味,因此,人们在社戏的演出活动中加入了迎神送鬼的仪式,塑造了栩栩如生的鬼神故事,以讨得鬼神的欢心,达到与鬼神沟通的目的。在这种目的的指导下,社戏演出过程中的方方面面,如剧情内容、结构仪式、表演方式等无不折射出宗教的气息,它利用各种宗教性的表现方式,来行使它的宗教目的。
(一)剧情内容
社戏的剧情内容围绕着鬼神故事,充斥着大量的鬼神形象。鬼神故事、鬼神形象大大增强了社戏的宣教效果,它利用鬼神故事向人们传达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的宗教观念,从而行使它的宗教使命。
绍兴地区的鬼神戏以目连戏为代表,绍兴方言中有“看夜目连看夜鬼”之说,目连戏被频繁地移植到当地社戏的表演活动中,成为绍兴民间社戏演出中的代表性剧目。目连戏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剧目之一,历史久远,堪称“中国戏曲活化石”。它多在农历七月十五即中元节上演,中元节民间亦称鬼节,绍兴地区多称之为“七月半”。根据佛教传说,中元节当日,地府放出鬼魂,民间要举行各类祭祀鬼魂的活动。在绍兴地区,上演目连戏便是七月十五祭鬼活动中的重头戏。目连戏的演出仿佛鬼魅群像的缩影,显示出祭鬼祀鬼的宗教目的。
目连戏最早起源于佛教典籍《佛说盂兰盆会》,在宋元之后,又受到道教等其它教派的影响,在而后的发展中,它又由最初的宗教故事慢慢演变成为目连戏这种戏曲形式。从目连戏的产生与演变,我们可以看到宗教的艺术化过程,所以说,目连戏取材于宗教,发展于宗教,当然,它便具有了宗教的特性。
1.鬼神故事
绍兴目连戏讲述的是目连之父傅相一生行善积德,乐善好施,在死后得以升天受封。然而其妻刘氏误以为是玉帝夺其夫之性命,遂背弃佛门,不敬神明,甚至破戒杀牲,大肆烹嚼。刘氏死后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受尽折磨。目连眼见母亲刘氏身处地府受尽苦难,便祈求佛祖帮助。佛祖为目连孝心所动,便点化其于农历七月十五设盂兰盆会,供养十方僧众。目连依照佛祖点化,最后借助僧众之力超度亡母,使其母刘氏转世投胎,免受阴曹地府刑罚之苦。
从内容看,目连戏具有劝人向善、劝子行孝的寓意。社戏正是借助了这些生动有趣的鬼神故事,让人们深刻领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宗教理念。人们看到目连之父傅相积善修德、广济孤贫,终于升天受封,便会懂得在世行善必有福报的道理。看到目连之母刘氏因吝啬贪婪、杀生纵欲而被打入阴曹地府受尽刑罚之苦,便会领悟到在世作恶就会不得善终的真谛。
2.鬼魅形象
除了具有宗教特性的主题内容,绍兴地区的目连戏还展现了许多“可怖而可爱”的鬼魅形象,如男吊、女吊、无常。
《男吊》讲述了一名赌徒,因输光家产而投缳自尽。在戏中,他化身鬼魂为“讨替代”而来。何谓“讨替代”?按照绍兴地区传说,凡是“五殇”而死之人,化身鬼魂后必须找到替身才能投胎转世,这便是“讨替代”的由来。鲁迅先生曾在《女吊》一文中回忆道:“而且中国的鬼还有一种坏脾气,就是‘讨替代’,这才完全是利己主义;倘不然,是可以十分坦然的和他们相处的。”[3]男吊的上场一般伴随着毛骨悚然的气氛,观众凝神屏气,等待男吊上场。男吊表演奇特,用一条白布裹缚全身七七四十九处,又在布中表演钻、挂、跳等高难度动作。
女吊的表演在男吊之后,比起男吊,女吊的形象更令人不寒而栗。煞白的脸孔上一对乌黑的眼珠显露出一份杀气,再配以浓密的双眉,猩红的嘴唇,俨然一副厉鬼的相貌。女吊的动作极具特色,伴随着麻雀步,时而又配以摇头甩发的动作,给人一种阴森恐怖之感。
与男吊、女吊阴森可怖的形象不同,无常在舞台上的形象却以滑稽著称,给人一种可笑而不可怖的印象。无常在舞台的动作往往透露出些许诙谐,比如连打数十个喷嚏,撅起屁股放响屁,走路时用八字步一摇一摆,手上一把扇子连连拍击,动作夸张让人忍俊不禁。无常身着一袭白衣,高高的帽子写着四个大字:一见有喜。既是勾人魂魄的差事,又何来“一见有喜”?在绍兴,丧事被称作“白喜”,这“一见有喜”便如同这“白喜”一般,反映出当地人们对于死亡的一种豁达态度。[4]
“宗教虽然有一套抽象的概念体系(神学理论),但其对象又是确定的概念所不易把握的,同时它需要用直观可感的形象把其对象或其对象的象征物呈现在群众跟前,用幻想和情感去拨动群众的心弦。”[5]绍兴地区的鬼魅形象如男吊、女吊、无常正是这样一种“直观可感的形象”。这些鬼魅形象向我们展示了夸张的造型、生动的动作、独特的语言,这些活灵活现的表演代替了宗教教义当中虚无的神鬼理论,使人感同身受,让人看到一个真实的神鬼世界。
宗教原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往往是晦涩难懂的,它需要用直观鲜活的曲艺形式展现,才能深入人心。吕大吉在《宗教学通论》中提出:“当艺术作品为表达某些宗教观念服务的时候,它的这种作用会比神学著作更加有力和广泛得多。”[5]社戏正是将这些深奥的宗教原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戏曲表演,使之潜移默化进入民众的心里,进而达到宣教的目的。
(二)结构仪式
社戏另一个显著的宗教特征表现在其演出的过程中伴随的神圣而严肃的宗教仪式。这些仪式或列于首尾,或穿插其中,使社戏的演出内容融化在祭祀的结构框架中。社戏的演出不仅仅是纯粹的艺术表演,它是对宗教仪式的一个生动而直接的补充与表现,使虚幻的宗教内容更具表现力与感染力。可以说,宗教的仪式与艺术的表演相辅相成,融会贯通地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行使人-神-鬼交流互通的宗教使命。
宗教的仪式或是为了驱鬼逐祟、祓除不祥,或是为了祭奠亡魂、安抚鬼灵,亦或是出于请神送神的目的。
绍兴地区目连戏开始时所表演的“起殇”,便是带有驱鬼逐祟、祓除不祥目的的宗教仪式。所谓“起殇”,就是在演出开始前,利用一套宗教的仪式召集各路鬼魂,并邀请他们进入戏场看戏。通常气氛十分严肃紧张,一则可以管教鬼魂规矩看戏,二则人们认为这种严肃的仪式可能帮助祓除不祥,并得到庇护。蔡丰明先生在《江南民间社戏》一书中对绍兴地区特有的“起殇”作过细致具体的描述:“届时后场吹起目连嗐头,敲起锣鼓,台上走出王灵官、鬼王和一群小鬼。王灵官对着鬼王发号施令一番,鬼王便手执令牌,带着一群小鬼跳下戏台,向村外的乱坟堆跑去。小鬼们上身赤膊,下身穿着一条红色短裤,手中拿着汤叉(叉上有铜片,晃动时会啷啷作响),跟着鬼王跑进乱坟堆后,环坟绕圈三周,并用汤叉在坟头上乱戳一阵,然后回到戏台上。此时台上已准备好大公鸡一只,鬼王取过,摘下鸡冠,将鸡血洒于四根台柱,然后拧下鸡头扔向远处。”[2]到此之后,召鬼看戏的仪式才算结束。
“起殇”是一种开台的仪式,出现在演出之前,它的目的在于“召鬼”。演出结束之后,另有一个扫台的仪式,它的目的在于“驱鬼”。扫台的仪式同样由鬼王来担任主角,因为鬼王的统领具有权威性,在鬼王的召集下,小鬼们便会安分地随其离去。扫台的仪式上,扮演鬼王的演员身着红色短裤,手拿追魂牌,单腿立地,摇头晃脑蹦跳一番之后,驱鬼便大功告成了。
开台与扫台的仪式分别位于社戏的首尾,它们行使了迎神送鬼、祓除不祥的使命,同时也使社戏的曲艺演出包容在祭祀的一套系统以内,从而明确了社戏的宗教特性。
三、当代传承
(一)现状
在城市化、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乡土中国”的传统文化生态环境正在慢慢消逝,社戏最原始的社会功能——宗教祭祀,也在逐渐淡化。社戏从原来出于祭祀目的的宗教演义,演变成年节时期的应景活动,如做寿、办丧事、发财戏,甚至成为了旅游景区的观光节目。它所传递出的精神意愿远不同于古时人们内心朴素的宗教诉求,现如今,人们请戏多出于祈求平安富贵、唱戏还愿等。
再者,伴随现代科技的发展,古时根深蒂固的鬼神信仰渐渐地被摈弃,社戏所传达的“因果轮回、生死无常”的宗教理念渐渐被认为是愚昧无知的,古时人们敬神尚鬼的文化心态已经转变成更为科学、更为理性的科学主义。这种文化意识、生命意识的转变,不可避免地使社戏失去了它赖以生存发展的内在诱因与群众基础,社戏的生存空间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
(二)传承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社戏的传承与延续首先需要保护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设立文化保护生态基地,鼓励目前尚有自发组织社戏演出的村社继续走自发演出的道路,使民间社戏演出常态化。同时,减少行政干预、政策宣传,倡导民间自发保护与传承,使社戏最大程度地保有其“原真性”。
其次,社戏的传承离不开公众的参与。社戏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表达其精神寄托与文化品格的艺术形式,它凝结了一个族群的文化旨趣与宗教意识。所以,社戏的传承需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相联系,只有在大众的共同参与下,社戏才能真正保留其宗教特性与文化功能。
再者,在媒介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代社会,人们的审美情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观众的断层现象已是社戏传承之路上的根本障碍。社戏在保留其艺术精髓的基础上,也应适当地从当代审美价值体系出发,寻求更为多元化的艺术表现形式,最大化满足不同知识架构的观众的审美需要。[6]
当历史的车轮转向一个新的时代,社戏这种建立在原始宗教仪式基础上的演艺,该以怎样的形态生存下去呢?“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实际上,社戏一直在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作出适时的调整,改变自己的存在形态。只要人生还有苦难和痛苦,还有生离死别、婚丧嫁娶,只要宇宙还有四季的轮回、无常的命运,草庵和庙堂仍将吸引一些虔诚的目光,大红大绿的艳俗的布景也将依然放射出令人迷醉的光辉。”[7]因此,在当代社会文化环境中,社戏虽无法回到古时繁荣的光景,但也不会悄然退出历史的舞台,它会以“文化遗存”的形式继续存在于现代社会,会按照历史的轨迹,找到属于它的合适的生存状态。
[1]陆游.剑南诗稿:卷27[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63.
[2]蔡丰明.江南民间社戏[M].上海:百家出版社,1995:10.
[3]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14.
[4]叶志良,金琳.绍兴社戏中鬼戏的艺术人类学研究[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8(1):26.
[5]吕大吉.宗教学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6]周凯,田瑞敏.从“昆曲传承计划”看“非遗”戏曲的保护与传承[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8):25.
[7]张德明.绍兴社戏的当代传承及其文化功能[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2(4):112.
The Religious Characteristics of Shaoxing Village Drama and Its Contemporary Inheritance
Jiang Tingting
(Yuanpei College,Shaoxing University,Shaoxing,Zhejiang 312000)
Village drama,a form of theoretical performance,is a thanksgiving offering to gods and ghosts.It is a form of performing arts and a type of religious activities.It is a combination of art and religion contributing to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gods and mortals.Shaoxing village drama epitomizes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Yue region,reflecting like a transparent mirror the customs and practices of Shaoxing and its ancient folks'cultural values and religious awareness.
Shaoxing village drama;religious nature;contemporary inheritance
G127
A
1008-293X(2015)05-0021-04
10.16169/j.issn.1008-293x.s.2015.05.05
(责任编辑 张玲玲)
2015-04-13
蒋婷婷(1985-),女,浙江绍兴人,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讲师,硕士。
——弋阳腔艺术保护中心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