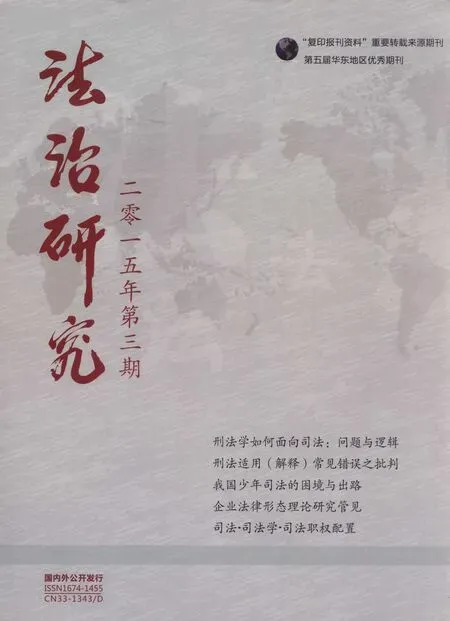唐代格式渊源考略*
吴海航
一、律令的渊源及与格式的关系
唐代格式的渊源与律令关系密切,在唐初曾经有过一段格律混一编订的时期,唐式在唐格之后陆续出现并持续颁行,格式相继颁行以后便开始形成了唐代的律令格式体系。因此,唐代格式的产生与律令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探讨唐代格式的渊源时,也要对律令的渊源进行回溯,以使格式渊源得以完整地呈现。
唐律作为国家最重要的刑事法律规范,以律典为外在的形式构成。在唐朝以前各代,国家律典的形式已基本完善,成为各代王朝开国之必备宪典。向前追溯至秦汉,首先以“秦律”系列为代表构成了国家的法典体系。秦墓竹简出土的《秦律杂抄》和《法律答问》主要承袭李悝《法经》的内容与精神,此外又发展出秦朝的《田律》、《工律》、《厩苑律》、《仓律》和《军爵律》等律典形式,使秦朝具备了完整的律典规模;①参见戴世君:《云梦秦律新解(六则)》,载《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又如汉律以《九章律》而成体系,辅之以《越宫律》、《傍章律》和《朝律》等律典,②参见王伟:《论汉律》,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但是孟彦弘通过研究则认为,“汉律”九章之说实为虚指,泛称汉律篇章之多。参见孟彦弘:《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形成对秦制的部分传承。至魏晋南北朝,国家律典主要有曹魏《新律》,晋《泰始律》③参见祝总斌:《略论晋律的“宽简”和“周备”》,载《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北齐的《北齐律》。至隋唐两代,隋有《开皇律》和《大业律》,唐代先后出现了《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和《开元律》④参见杨廷福:《唐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以下。等律典,历代律典形式的传承从未间断,且向着更为精致、规范的方向发展。中国古代律典的形式与内容已达致高度严谨和精湛的程度,无疑已走在当时世界之前列,且在唐代律典修订之际,制定者还同时撰有立法解释,因此有“律疏”之称的内容附着于律条之下,律疏与律文总为一体,不仅同具法律效力,也丰富了律典的形式构成。
古代律典的更替传承状况表明,律始终处在自身不断完善与精细化的过程之中。然而,律的调整范围和功能发挥依然有很大限度。尽管古代律典体现为综合性法典的特征,而实际上其刑事法律功能才是最根本的,其所展现的功能是与国家在各个管理领域内打击犯罪的任务相一致的。律的调整范围尽管也很宽泛,但还是不能替代国家在各项事物管理中的允许或限制等具体规则,因此,令、格、式的出现才能真正弥补这一立法上的不足。
令和律本来的关系较为接近,是针对相关事项确定的互补性规则,正如陈寅恪先生在解释唐代律令关系时指出的:“律令性质本极近似,不过一偏于消极方面,一偏于积极方面而已。”⑤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1页。说明了律令功能的接近而调整方式的差异性。律禁于已然,而令则禁于未然。实际上作为国家最高统治机构发布的“命”或“令”,在各代法律体系中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上古时期,国王发布的“诰”即为令。《尚书·汤诰》篇记述商汤伐夏桀的轶事,王曰:“嗟!尔万方有众,明听予一人诰。”⑥[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参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又记述了周伐殷商的轶事,“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⑦同注⑥,第341页。上古时期的诰文,即有令的功能与含义,有最高法律效力。《尔雅》的解释:“命、令、禧、畛、祈、请、谒、讯、诰,告也。”⑧[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参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可见“诰”与“命、令”具有同一顺位的含义。秦朝时已有“法令”和“律令”的区别,但实际都是指国家颁布的律和令。始皇帝称朕,树立个人威权,“……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⑨[汉]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6页。。进入汉代,“高祖初入关,与众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至汉文帝、景帝改革肉刑之际,为了形成新的刑制标准,因而有“具为令”的说法,⑩[汉]班固:《汉书》卷23《刑法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96页。这显然是以令的形式将改革肉刑的举措下达到全国。汉代的“令”由皇帝制定,再由朝廷发布。汉代以令的形式编成单行法者甚多,毋需完全列举,如汉代之《田令》、《戍卒令》、《水令》、《公令》、《功令》、《养老令》、《马复令》、《禄秩令》、《宫卫令》等。⑪参见[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66~868页。国学家陈梦家先生认为,汉代律、令、诏三者既有区别,又有混同之处,故引杜周语:“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⑫参见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8页。突出了律的相沿性和令的随机性。
至魏晋隋朝时期,律令的形式继续向下传承,曹魏有“《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⑬[唐]房玄龄等:《晋书·刑法志》卷30,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23~924页。可见此时对令的编订已趋于成熟。西晋朝廷编订多种单行令文并付诸实施,《唐六典》载:“晋命贾充等撰《令》四十篇:一《户》,二《学》,三《贡士》,四《官品》,五《吏员》,六《俸廪》,七《服制》,八《祠》,九《户调》,十《佃》,十一《复除》,十二《关市》,十三《捕亡》,十四《狱官》,十五《鞭杖》,十六《医药疾病》,十七《丧葬》,十八《杂上》,十九《杂中》,二十《杂下》,二十一《门下散骑中书》,二十二《尚书》,二十三《三台秘书》,二十四《王公侯》,二十五《军吏员》,二十六《选吏》,二十七《选将》,二十八《选杂士》,二十九《宫卫》,三十《赎》,三十一《军战》。三十二《军水战》,三十三至三十八皆《军法》,三十九、四十皆《杂法》。”⑭[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六,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4页。晋令当中有将令直称为法的形式,如上述《军法》和《杂法》,表明法可以归类于令的系统;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均有律令编订,根据文献的记载,北朝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年)有《狱官令》颁行,规定“诸察狱,先备五听之理,尽求情之意,……”⑮[北齐]魏收:《魏书·刑罚志》卷111,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78页。《隋书·经籍志》亦载,北齐曾撰有《北齐令》五十卷,⑯[唐]魏征:《隋书·经籍志》卷33,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72页。其后经过隋朝《开皇令》、《大业令》的编订,过渡到唐代令类系统的编纂问世。
唐令是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敕令类法文件。唐朝前期,皇帝发布的令大多经过整理、编纂和删订,已形成系统的法文件,使得唐令初具体系。“皇朝之令,武德中裴寂等与律同时撰,至贞观初,又令房玄龄等刊定,麟德中源直心,仪凤中刘仁轨,垂拱初裴居道,神龙初苏瓌,太极初岑羲,开元初姚元崇,四年宋璟并刊定。”⑰同注⑭,第185页。然而《唐六典》记载唐令的编纂是在开元四年(716年),此记载大概是仅强调开元朝编纂令的活动而已。《旧唐书·刑法志》载,开元七年(719年),吏部侍郎兼侍中宋璟等人曾奏上《开元后格》,“……删定律令格式,至七年三月奏上,律令式仍旧名,格曰《开元后格》”⑱[后晋]刘昫:《旧唐书·刑法志》卷50,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50页。。而《旧唐书·经籍志》在罗列《开元后格》之后,又书“《令》三十卷”,⑲[后晋]刘昫:《旧唐书·经籍志上》卷46,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11页。此即为《开元令》,其奏准时间一定是在开元七年之后。据《新唐书》记述,《开元令》在二十五年(737年)时与律、格、式开始混编在一起,称之为“《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⑳[宋]欧阳修等:《新唐书·艺文志二》卷58,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96页。其后,受这种混编模式的影响,唐令基本不再单独编定成册,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格式与律令的渊源关系。
《新唐书·刑法志》有言:“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㉑[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刑法志》卷56,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07页。唐令的地位及效力均高于唐律,它甚至是唐律内容形成的依据。如唐律的“疏议”部分是与唐律一体的法律解释及适用的重要标准,其在形成时即引用“令”文近百条,直接指引着律文的适用范围。如《唐律·户婚律》第182条:“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疏]议曰:同宗共姓,皆不得为婚,违者,各徒二年。……问曰:同姓为婚,各徒二年。未知同姓为妾,合得何罪?答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取决蓍龟,本防同姓。同姓之人,即尝同祖,为妻为妾,乱法不殊。《户令》云:‘娶妾仍立婚契。’即验妻、妾,具名为婚。依准礼、令,得罪无别。”㉒[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十四《户婚律》,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2页。可见唐律的这段法律解释标准来自唐礼和唐令。唐礼作为唐代法律体系的精神依据自然无可争议,而唐令作为解释标准则表明此令内容是先于唐律产生的。虽然唐律与唐令的编纂时间大致是同期进行的,但唐令作为唐律“疏议”部分的立法依据显然是有依据的。
格式与律令的渊源关系,用律令为格式之宗来表述并不为过。虽然格、式均可单行,但其与律令的辅助相行和细则、细化关系依然是其制定的主要缘由。格式与律令的渊源关系在律文中常有出现,如《唐律·断狱律》第488条有载:“诸赦前断罪不当者,若处轻为重,宜改从轻;处重为轻,即依轻法。”这是唐律条款正文规则的内容,这一规则的用意是从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角度考虑的,法官断案遇赦令时,若判决已加重则应改为轻,若判决已减轻则从轻。这一规则的依据在疏议中有进一步的解释:“故令云:‘犯罪未断决,逢格改者,格重,听依犯时;格轻,听从轻法。’即总全无罪,亦名轻法。”㉓[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三十《断狱律》,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66页。这里既提到了唐令,也援引了唐格,体现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格具有优先参考适用的导向作用,唐格改动前后对量刑可以产生直接影响,即与如今我国刑法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几乎相同,表明律的渊源既受到令的内容影响,也会受到格的规则影响。
唐律与唐式也具有渊源关系,并受到唐式规则的决定性影响。《唐律·职制律》第127条:“诸增乘驿马者,一匹徒一年,一匹加一等。主司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勿论。”此规定为唐律正式条文,其内容为限制官吏随意增乘驿马。按唐《公式令》规则,职事官乘驿马皆有本数,“数外剩取,是曰‘增乘’”。疏议还解释了“‘应乘驿驴而乘驿马者’,又准《驾部式》:‘六品以下前官、散官、卫官、省司差使急速者,给马。使回及余使,并给驴。’即是应乘驴之人,而乘马,各减增乘马罪一等”。这是一条有关成立“增乘马罪”的判断规则,唐律从唐令规则出发,又引出唐式规则的解释。唐式的规定是按品官类型、公务急切程度,确定应骑乘驿马或驿驴,若官吏违背规则增乘驿马,则触犯了唐律设定的“增乘马罪”。此处我们看到了唐律罪名的设置和审判的依据,均指向了唐令以及唐式既有的规则。
二、格、式渊源的考察
(一)唐格渊源的考察
作为特别法的唐代“格”,其原始渊源并不具有特别法的地位,而是以相当于国家的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的面貌出现的,以秦朝的“程”为例,其规定的内容即有“格”的早期特征。根据出土秦简资料,当时已有称为《工人程》的法律形式,规定手工业劳动者应完成的工作任务,这大致相当于“格”在早期的法规特征。《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资料现已被广泛利用,其中《工人程》篇有:“隶臣、下吏、城旦与工从事者冬作,为矢程,赋之三日而当夏二日。”㉔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此规则的译文是:“隶臣、下吏、城旦和工匠在一起生产的,在冬季劳动时,得放宽其标准,三天收取相当夏季两天的产品。”此内容是要求官奴和犯罪之人在不同季节(冬夏)期间,应当交付有差异的手工产品数量,其差异性就是可以依据弹性规则执行。这显然属于国家要求手工业者缴纳手工产品的一般行政立法规范。
汉代的“科”出现之后,其地位大致相当于后代的“格”,见于《后汉书》记载,“臣窃见元年以来,盗贼连发,攻亭劫掠,多所伤杀。夫穿窬不禁,则致强盗;强盗不断,则为攻盗;攻盗成群,必生大奸。故亡逃之科,宪令所急,至于通行饮食,罪致大辟。……”㉕[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郭陈列传》卷46,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58~1559页。文中的“亡逃之科”,即指这一法律形式的存在,其功能显然是为“宪令所急”之需,规定了汉朝中央政府为督促地方缉捕强盗罪犯的要务,如果有为逃犯周济饮食者,可刑至大辟。此类汉“科”,仍有其他记载,“覆车之轨,其迹不远。盖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糺增旧科,以防来事。自今强盗为上官若它郡县所糺觉,一发,部吏皆正法,尉贬秩一等,令长三月奉赎罪;二发,尉免官,令长贬秩一等;三发以上,令长免官。便可撰立科条,处为诏文,切敕刺史,严加糺罚”㉖同注㉕,第1559页。。这段文字同样来自《后汉书·郭陈列传》陈忠的奏疏,奏文中请求皇上批准对原来已有的科条进行增加,规定对今后发生的强盗犯罪现象,如果被上级官员或其他郡县的官员纠察出来,则对有直接管辖权的官吏分别予以处罚。奏疏提出应将此项规则立为科条,以示严厉之意。可见“科”在汉代是作为特别法施行的,如果按今天的部门法属性判断之,当时之“科”有属于特别刑法者,也有属于特别行政法者。又如,古礼制当中有“大臣得行三年丧,服阕还职”的制度,至东汉光武帝时期已鲜有遵守,礼义渐趋败坏。东汉陈忠又以此为由上疏奏曰:
臣闻之《孝经》,始于爱亲,终于哀戚。……周室陵迟,礼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诗》自伤曰:“瓶之罄矣,惟罍之耻,”言己不得终竟子道者,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萧何创制,大臣有宁告之科,合于致忧之义。建武之初,新承大乱,凡诸国政,多趣简易,大臣既不得告宁,而群司营禄念私,鲜循三年之丧,以报顾复之恩者。礼义之方,实为雕损。大汉之兴,虽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㉗同注㉕,第 1560~1561页。
陈忠上疏强调的是汉高祖时即创制的“大臣有宁告之科”,此科条至东汉光武帝时期渐不施行,因而他提出上述奏疏,期望恢复“先王之制”。“宁告之科”是汉初以来国家制定的官宦臣僚应享有的丧假制度,应属于行政法制规范。据史料所载,汉科不像汉令那样经过系统编订,因此,其仅具有补充律令不足的临时性与灵活性特征。㉘参见于振波:《秦汉法律与社会》,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魏晋以后,以“格”为名称的法律形式开始出现,渐有取代原有“科”的趋势。《唐六典》称“后魏以‘格’代‘科’,於麟趾殿删定,故名为《麟趾格》。北齐因魏立格,撰《权格》,与《律》、《令》并行”㉙同注⑭,第185页。。表明“科”这一法律形式自东魏、北齐以后开始以“格”代称,并趋于形成独立的格典。但这一时期大概仍处在“科”与“格”混用的状态。隋文帝在整治法律规范时颁行了《开皇律》,并下诏曰:“帝王作法,沿革不同,取适于时,故有损益。……宜班诸海内,为时轨范,杂格严科,并宜除削。”㉚[唐]魏征:《隋书·刑法志》卷25,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11~712页。这里所谓“杂格严科,并宜除削”的说法,表明隋朝初期对前代的“科”与“格”曾经进行过删减,但这恰恰说明“科”与“格”已经是同一类型或类型相近的法律形式。
经隋至唐,格已经转变为以帝王制敕为主,再由政府编纂颁行的具有确定形式的系统法典。如前所述,格是唐代法律体系中重要的立法成果之一,朝廷经常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其进行发布、编定和增删,㉛参见赵贞:《唐尚书六部二十四格初探》。《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三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6页。逐渐形成了动态且稳定的发展趋势。高祖武德时期最早制定的“五十三条格”,就是唐朝初期的一次系统立法活动。据《旧唐书》载,“于时诸事始定,边方尚梗,救时之弊,有所未暇,惟正五十三条格,入于新律,余无所改。至武德七年五月奏上,乃下诏……于是颁行天下”㉜同注⑱,第2134~2135页。。而唐初的“五十三条格”实际上最初也是与律混编的,《新唐书》所载:“武德二年,颁新格五十三条,唯吏受赇、犯盗、诈冒府库物,赦不原。……凡律五百,丽以五十三条。”㉝[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刑法志》卷56,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08页。显然,表述的是武德“新格五十三条”与五百条律文是附着在一起的。新格规定,对官吏受贿、盗领官物、欺诈冒领府库物资的犯罪予以赦免,但不得原其罪,这正是历代王朝在法律草创时期“务在宽简”㉞同注⑱,第2134页。原则的适用情况。但在法的渊源关系上,唐律在早期反而对唐格存在着依附关系,高祖时期的“五十三条格”与《武德律》附着在一起“颁行天下”,就体现了唐格对唐律渊源的一种基础作用。㉟刘俊文先生就认为武德“新格”在某种程度上是《武德律》的基础,诚如所言,自武德元年(《新唐书》为武德二年)始,五十三条格就已成为唐初的暂行法规。参见刘俊文:《唐代法制研究》,文津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其后,唐格的单独编订和修改才逐渐成为立法方向,《贞观格》就是沿着这一路径形成的,《旧唐书》记述:“又删武德、贞观已来敕格三千余件,定留七百条,以为格十八卷,留本司施行。斟酌今古,除烦去弊,甚为宽简,便于人者。以尚书省诸曹为之目,初为七卷。”㊱同注⑱,第2138页。此便是《贞观格》的由来及其最终定型。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开始了唐格的分类,“永徽二年闰九月十四日,上新删定律令格式,……遂分格为两部:曹司常务者为留司格,天下所共者为散颁格。散颁格下州县,留司格本司行用”㊲[宋]王溥:《唐会要》卷39,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701~702页。。于是,唐代开始通行散颁格和留司格,其调整范围有所差异。永徽之后,经武则天时期《垂拱格》、中宗时期《神龙格》、睿宗时期《太极格》和玄宗时期的《开元格》等,唐格基本上沿着散颁格和留司格两种类型发展,但是不排除又有“恢复贞观格旧制”的可能——散颁格与留司格合二为一的立法状况,㊳参见刘俊文:《唐代法制研究》,文津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页。这种情况与唐代文献对《贞观格》的记述亦相暗合。
(二)唐式渊源的考察
关于唐式渊源的上溯,有学者曾将其渊源追溯到秦朝的《封诊式》。㊴参见霍存福:《唐式辑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有25节简文,其范围主要如下所示:“治狱、讯狱、有鞫、封守、覆、盗自告、□捕、□□、盗马、争牛、群盗、夺首、□□□、告臣、黥妾、迁子、告子、疠、贼死、经死、穴盗、出子、毒言、奸、亡自出”等,各节事项涉及国家有关司法、行政管理的诸内容,㊵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164页。主要针对刑事民事案件的诉讼、逮捕、审讯、判决等程序性内容进行规定。如“治狱、讯狱”两节是对司法审讯过程的判断标准;“争牛”一节是法官(令史)对甲乙两造争执一头丢失的母牛的所有权判断过程;“亡自出”一节是关于逃亡徭役后投案自首的士伍甲的处置。出土的《封诊式》是秦朝法律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从其主要功能看,《封诊式》与后代唐式的功能确有一定的联系,且“式”这一古老的名称的使用也为后代“式”开启了一个源头。
进入汉代,迄今所知法律体系中未能延续秦《封诊式》一项,但有一种称为“品”的法律形式出现了,这是与后代唐式较为接近的立法类型。汉“品”与汉“科”同属一个层级,都具有行政细则的属性。“品”在宋代官修的传世韵书《广韵》中被称为“式”:“品,官品;又类也;众庶也;式也,法也。二口则生讼,三口乃能品量。……”㊶参见余迺永校注:《新校互注宋本广韵》(增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330页。显然,《广韵》所释出的品的含义是具有“式”与“法”的特征的,其“二口则生讼,三口乃能品量”的解释所揭示的道理是:两个人之间可以发生争讼,此时需要第三方力量的介入,通过以第三方参与的比较、衡量、调处、裁决等方式解决纠纷。这是对“品”属于式、法一类性质的一个很好的注解。汉代作为法律形式之一的品,常与科连称,表明品与科的关系密切。例如,《后汉书·舆服志》载:“诸车之文:乘舆,倚龙伏虎,……皇太子、诸侯王就,倚虎伏鹿,……公、列侯,倚鹿伏熊,……卿,朱两轓,五斿降龙,二千石以下各从科品。”㊷[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舆服志上》卷29,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652页。这是规定王室、贵族官僚的乘舆所应享受的标准,属于行政细则化的立法内容。科品虽然有时连署相称,但调整内容分别各有侧重。《后汉书》云:“丙子,诏曰:‘旧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务崇节约。遭永初之际,人离荒戹,朝廷躬自菲薄,去绝奢饰,食不兼味,衣无二采。比年虽获丰穰,尚乏储积,而小人无虑,不图久长,嫁娶送终,纷华靡丽,至有走卒奴婢被绮谷,著珠玑。京师尚若斯,何以示四远?设张法禁,恳恻分明,而有司惰任,讫不奉行。秋节既立,鸷鸟将用,且复重申,以观后效。’”㊸[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安帝纪》卷5,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8~229页。表达了国家要求朝廷官府、黎民百姓限制奢侈的风尚,有司应履行职责,督促官民厉行节俭。如此内容是规定在科、品之中的。在居延汉简出土资料中,发现有完整的塞上《烽火品约》内容,规定了当匈奴人进犯边塞时须燔举烽火,通报信息,这与唐《职方式》的“烽燧”规定无疑具有渊源关系。详见如下:
匈奴人昼入殄北塞,举二烽,□烦烽一,燔一积薪;夜入,燔一积薪,举堠上离合苣火,毋绝至明。甲渠、三十井塞上和如品。
……
匈奴人入塞,候、尉吏亟以檄言匈奴人入,烽火传都尉府,毋绝如品。
……
匈奴人入塞,天大风,风及降雨不具烽火者,亟传檄告,人走马驰,以急疾为故。
右塞上《烽火品约》。㊹参见中国简牍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简牍集成》 [标注本]第12册,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卷《居延新简》四,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7页。
《居延新简》中还有关于《复作品》的规定,是涉及到相对较轻微的刑事犯罪的补充性处罚规则:
甘露三年(前51年)三月甲申朔,癸巳,甲渠鄣候汉彊敢言之,府下诏书曰:徒,髡、钳釱左、……尉史常富。……右止城旦舂以下及《复作品》。书到,言所……㊺参见中国简牍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简牍集成》 [标注本]第11册,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卷《居延新简》三,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复作品》规定的内容是针对汉律对肉刑、劳役刑处罚标准的补充,属于对汉律的细则性立法规定,其功能应与唐式功能最为接近。
至魏晋时期,西魏《大统式》的出现,似乎为唐式的历史渊源找到了最直接的根据。《大统式》以西魏文帝年号命名,史载《大统式》有五卷说或三卷说,其作为法的形式最早出现在西魏,是西魏大统年间的系列立法活动的结果,“魏帝以太祖前后所上二十四条及十二条新制,方为中兴永式,乃命尚书苏绰更损益之,总为五卷,班於天下。”㊻[唐]令狐德棻等:《周书·文帝下》卷2,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28页。其后,《隋书·刑法志》及《唐六典》均记载为五卷,而“新旧两唐书”则记载为三卷。《隋书》自身还存在不统一之处,刑法志记载为五卷,而经籍志则记载为三卷。㊼同注㉚,第707页;同注⑯,第972页。
关于西魏王朝初期的“式”的规范,《唐六典》有追溯:“大统元年(535年),令有司斟酌今古通变可以益时者,为二十四条之制;七年,又下有十二条之制;十年,命尚书苏绰总三十六条,更损益为五卷,谓之《大统式》。”㊽同注⑭。此三十六条中的十二条制,颁行时曾专门对朝廷百官下令,重申其地位和效力。“冬十一月,太祖奏行十二条制,恐百官不勉于职事,又下令申明之。”㊾同注㊻,第27页。总括起来,三十六条制具有重要地位,它最初虽然以“式”的法律形式出现,但其原初效力应相当于令,称为“条”或“条制”,本身就体现为诏令形式的转换,是西魏初期的主要立法成果,因此,《大统式》的地位应比唐式的地位更加突出,是因为其刚刚脱胎于西魏朝廷的诏制。显然,西魏《大统式》的出现,为隋朝式的出台提供了一个蓝本,但史载隋朝仅有《大业式》,并不见“开皇式”,霍存福先生在《唐式辑佚》中追溯称“似开皇也有式,炀帝时沿袭之”,㊿参见霍存福:《唐式辑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此说应为合乎情理之推论。
进入唐代,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公布法律时就已经包括了唐式,“《武德律》十二卷,又《式》十四卷,《令》三十一卷,尚书左仆射裴寂、右仆射肖瑀、……太常博士徐上机等奉诏撰定。以五十三条附新律,余无增改。武德七年上”[51]同注⑳,第1494页。。说明唐式从诞生时起就是独具形式的。《贞观式》的制定时间应当与《贞观格》大致相当,《贞观格》是在贞观十一年(637年)时删定而成的,这一时间段正是唐太宗时期的立法体系完备期,因此,《贞观式》应当是在这期间形成的。根据《唐六典》记载:“凡式三十有三篇,亦以尚书省列曹及秘书、太常、司农、光禄、太仆、太府、少府及监门、宿卫、计帐为其篇目,凡三十三篇,为二十卷。”[52]同注⑭。唐式经过《贞观式》之后,又出现《永徽式》系列,《麟德式》和《仪凤式》等,永徽二年(651年)第一次公布系统性立法成果。《唐会要·定格令》载:“永徽二年闰九月十四日,上新删定律令格式,太尉长孙无忌,开府仪同三司李勣,……太府丞王文端等同修,勒成律十二卷,令三十卷,式四十卷,诏颁于天下。”[53]同注㊲,第702页。其后,武则天时期颁行《垂拱式》二十卷,中宗时期颁行《神龙式》二十卷,玄宗时期颁行《开元式》二十卷。《旧唐书》载:“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户部尚书李林甫又受诏改修格令。林甫迁中书令,乃与侍中牛仙客、御史中丞王敬从,……酸枣尉直刑部俞元杞等,共加删辑旧格式律令及敕,总七千二十六条。……总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54]同注⑱,第2150页。至唐朝中后期,有关“式”的立法规模又开始恢复到唐初贞观时期的状态,“至大中五年(851年)四月,刑部侍郎刘瑑等,奉敕修《大中刑法统类》六十卷,起贞观二年(628年)六月二十八日,至大中五年四月十三日,凡二百二十四年杂敕,都计六百四十六门,二千一百六十五条。至七年(853年)五月,左卫率府仓曹参军张戣,编集律令格式,条件相类者。一千二百五十条,分为一百二十一门,号曰《刑法统类》,上之”[55]同注㊲,第705页。。将律令格式统编在一起,唐代的立法格局进入了稳定期,其后关于式的立法发展,终至唐末也没有出现大的变化。
三、结语
格式作为唐代法律体系内部特有的法律形式,起到了对律令的重要补充作用。虽然唐代格式渊源分别有自,但各自的功能和效力仍有所不同。本文的主体部分仅对唐代格式的渊源构成进行了初步考察,形成了对唐代格式在历史上所呈现出的形态、源流和变化过程的探讨。《唐六典》曾对律令格式体系的制度功能有过高度概括,“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56]同注⑭,第185页。这种概括性的解释虽然对探讨格式的功能给出了较为明确的指示,但依然还有存疑之处值得解析。《新唐书·刑法志》有云:“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57]同注㉑,第1407页。此内容的表达虽与《唐六典》之义互为表里,但是道出了律令格式作为国家之宪典,外有分工,内有协作,令、格、式的功能范围,是规定政府机构的不同职掌和分工的规则,各机构分别负责管理本司职责范围内的事务,并须遵守一定的法律程序,实际上是关于国家行政、社会事务管理和运行的基本制度,对于违反令、格、式的犯罪行为则归于律来裁断。这正是唐代官府依法管理各项事务的主要制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