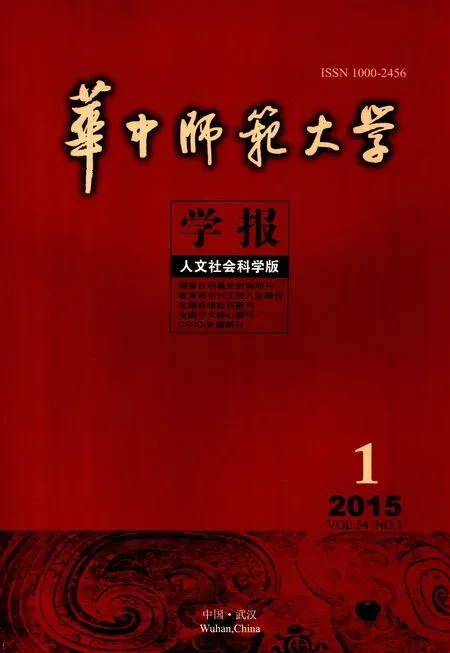“呐喊”何须“彷徨”?
——论鲁迅小说对于思想启蒙的困惑与质疑
宋剑华
(暨南大学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632)
“呐喊”何须“彷徨”?
——论鲁迅小说对于思想启蒙的困惑与质疑
宋剑华
(暨南大学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632)
《呐喊》与《彷徨》的创作主题,并不是学界原先所阐释的那样,被理解为攻击儒学“礼教”,而是通过一系列形象化的故事叙事,深刻地揭示文化个体与文化共同体之间关系的错综复杂性。鲁迅从“孤独者”与“狼子村”的思想对峙中,发现了构成乡土中国文化“长明灯”的历史原因:“庸众”与“庸俗”作为乡土中国的强大势力,一直都在以其强大的社会存在,与作为精英意识的儒学礼教形成对抗。因此在鲁迅个人看来,“庸俗”与“礼教”是截然对立的两个概念,反“传统”的重点也应首先放在反“庸俗”方面,这才是《呐喊》与《彷徨》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真实表达。
《呐喊》; 《彷徨》; “孤独者”; “狼子村”; “长明灯”; “礼教”; “庸俗”
《呐喊》《彷徨》作为鲁迅最具影响的代表作,其思想内涵与审美价值早已被学界做了反复论证,从“‘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檄文”,①到“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②人们无一例外都将鲁迅与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并尽其所能地去发掘《呐喊》《彷徨》的“微言大义”,进而以研究者的主观意志遮蔽了被研究对象的自我叙事,这无疑是鲁迅研究领域一直都难以摆脱的逻辑怪圈。
鲁迅对于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究竟是持一种什么样的主观态度?学界长期以来,都是以《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的一句话为依据,即“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③去推断鲁迅小说创作与思想启蒙运动之间的必然联系。其实人们并没有注意到鲁迅在这段文字的表述里,特意为启蒙主义和为人生加上了一个引号,显然是意味着他对“启蒙主义”认识的不确定性因素。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对于《新青年》杂志并无任何好感,据周作人回忆说,1918年4月,“鲁迅拿几本《新青年》给我看,说这是许寿裳告诉的,近来有这么一种杂志,颇多谬论,大可一驳,所以买了来的。”④查鲁迅日记,此间他确实有两次买《新青年》杂志送人的记载,由此可见周作人所说还是比较真实可信的。即使是到了1920年5月,鲁迅仍对“新文学家所鼓吹之新式”思想,表现出了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个人看法,比如他在致宋崇义的信中就写道:“仆以为一无根底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⑤鲁迅此话大有深意,他明显是认为《新青年》在崇尚“空谈”,故他才会鼓励那些青年学子,去“熬苦求学”做些“根底学问”。笔者始终认为,若要真正了解一个真实鲁迅的“五四”姿态,《呐喊》序言应是他本人最真实也最直接的心灵告白,其他外在的解读都只能是作为一种参考。在《呐喊》 序言中,鲁迅一再强调他是因为“听将令”,才去“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里,鲁迅同样也讲过与此相类似的话)⑥钱理群在解读这一现象时,曾说鲁迅当时虽然处于“希望”与“绝望”的矛盾冲突之中,但他最终是以“希望”战胜了“绝望”,并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新青年》阵营。⑦对于这种很有普遍意义的学界论点,笔者表示极大地怀疑,如果鲁迅真是以“希望”战胜了“绝望”,那么他要“呐喊”为什么又会“彷徨”了呢?可见鲁迅自谓的“呐喊”,与诠释者所臆想的“呐喊”,在词义理解上并不完全相同。笔者之所以强调《呐喊》序言的重要意义,是因为一方面它的写作时间靠近“五四”,更贴近于鲁迅“五四”时期的思想状态;另一方面它是出自鲁迅本人之手,笔者相信“言由心生”这句老话,它更能够展示鲁迅自己的精神世界。《呐喊》序言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千多字,但“寂寞”与“悲哀”竟出现了15次,这足以说明鲁迅当时的情绪是何等的消沉与低落!笔者特别看重鲁迅在《呐喊》序言中的一句话:“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识了。”不再“慷慨激昂”,暗示着鲁迅已告别了用感性去认知世界的思想幼稚,而转变为用理性去认知世界的思想成熟;为了“聊以慰藉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他以自己内心的“寂寞”与“悲哀”,去回应《新青年》阵营的“狂热”与“躁动”——这种“冷”与“热”的巨大反差。无疑是我们研究《呐喊》《彷徨》的重要前提。
重新阅读《呐喊》《彷徨》,笔者发现鲁迅对于《新青年》的思想启蒙,并不是给予了充分肯定而是充满着怀疑,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因为鲁迅在其作品文本中,强烈地表达了他对思想启蒙的忧患意识——“谁”是启蒙主体?启蒙主体与“狼子村”有何渊源关系?启蒙主体真能够吹灭中国传统文化这盏“长明灯”吗?启蒙主体为什么最后都变成了“孤独者”?《呐喊》《彷徨》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最终都归结到了一个关键的聚焦点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笔者个人认为,鲁迅思想与人格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其在“五四”狂热的启蒙浪潮中,始终都保持着一种高度清醒的理性意识;他不是在批判中去否定传统,而是在批判中去认识传统,批判传统使他感到“寂寞”(疏离感),认识传统又使他感到“悲哀”(沉重感)——应该说“寂寞”与“悲哀”,不仅是《呐喊》《彷徨》所要呈现的创作主题,同时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焦虑的时代通病。
一、“孤独者”:自我消解的精英意识
启蒙精英是《呐喊》《彷徨》中最受人们关注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是鲁迅本人表达他对思想启蒙真实态度的直接呈现。笔者用“孤独者”这一概念为其统一命名,目的就是为了揭示他们悲剧命运背后的意义所指。
无论是“狂人”、夏瑜还是涓生、魏连殳,他们究竟属不属于启蒙精英之列?虽然近来已有学者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但却因其忽视了“启蒙”一词的词义性,而很难使其论点从逻辑上得以成立。⑧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式的思想启蒙,并非像康德所讲的那样:是一种“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去“启蒙自己”的自我解放运动,而不是一种先知先觉者对后知后觉者的思想“教化”运动,后者即被康德所批判的那些自以为是社会公众的“保护者”所设下的“圈套”。⑨——对于他者居高临下的绝对“言说”,这是“五四”启蒙运动的典型特征。夏瑜等一系列“狂人”在《呐喊》《彷徨》中,毫无疑问都是些具有独立思想的“言说”者,故将其视为是变革社会的启蒙精英,绝没有曲解鲁迅塑造他们的原初本义。问题在于为什么鲁迅会将这些启蒙精英,都归为一群“孤独”离群的失败者呢?他们从“反叛”到“皈依”的人生轨迹,到底蕴含着鲁迅本人的何种纠结?笔者认为,让“言说者”失去启蒙“言说”的实际效应,并令其从“寂寞”当中去咀嚼“悲哀”,恰恰是反映着鲁迅对“五四”启蒙的困惑与质疑。
“谁”是启蒙主体?这似乎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当然是指“狂人”等叛逆者形象。然而进一步追问,他们依据什么去启蒙“言说”时,恐怕学界立刻就会变得缄口不言了。作为新文学参与思想启蒙的开山之作,人们对于《狂人日记》的深度阐释无可非议,但我们必须首先认清“狂人”是在何种前提之下,突然“觉醒”并发现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吃人”本质。笔者曾在一篇文章里,特别谈到过那个“月亮”,与“狂人”觉醒之间的辩证关系,⑩至今笔者仍坚持本人观点的正确性: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格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这段看似有些混乱的语言描述,其实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准确破解《狂人日记》的关键因素——“月光”意象。“月光”是一种暗喻,它是指启蒙主体“我”之觉醒的外部条件,“三十多年”是时间的泛指性,而“赵家的狗”则是无意识的生命体。“很好的月光”赋予了“我”以重新去认知历史的精神资源,使“我”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人们一般都认为“月光”是西方人文精神的隐喻性表达,但他们却忽略了“月亮”本身却并不是光源(启蒙的资源),它只有在折射太阳之“光”时才会发亮(能量的转借),这与“五四”时期通过日本去输入西方思想属于同构关系。“狂人”正是在这种混混沌沌的状态之下,开始了他艰难的启蒙之旅(“凡事总须研究”)——他发现了中国历史“仁义道德”的虚伪假象(“陈年流水簿”上写满了“吃人”二字),以及造成这种“吃人”文化的人文环境(“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由于“月亮”本身就是一种“黑夜”现象,故“狂人”根据“月光”去判断“黑暗”,其本身就是鲁迅有意安设的一个陷阱——“狂人”以“传统”去反“传统”,无论他怎样挣扎都毫无意义。小说《伤逝》里的主人公涓生,是对“狂人”形象的展开说明,他将“狂人”反传统动机的不确定性,演绎得更加清晰也更加直观。涓生与“狂人”一样,也是启蒙“言说”的绝对主体,阅读《伤逝》我们发现,通篇都是他一个人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自我“言说”(即破屋里“充满了我的语声”),而子君除了“聆听”的权力,几乎是无话可说。那么涓生对于子君的思想启蒙,他到底都说了些什么?翻遍作品文本,无非就是这样一套话语体系:“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这使笔者感到十分地震撼,原来“五四”思想启蒙话语,无非就是些从西方文学当中提炼出来的叛逆思想与爱情故事。其中“娜拉”式的离家出走,又被启蒙者理解为是最西方化的反抗方式。实际上,离家出走是私奔现象的现代演绎,它的根脉是在传统而非源自于西方,写过《中国小说史略》的鲁迅,对此恐怕要比任何人都清楚。因此《伤逝》故事的悲剧性结局,不是鲁迅对封建守旧势力迫害青年人的无声抗议,而是鲁迅对涓生启蒙“言说”自身荒谬性的一种否定。还有《在酒楼上》那个曾热衷于“改革中国”的吕维甫,以及《孤独者》里那个曾主张“家庭应该破坏”的魏连殳,他们一个飞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点”,另一个则公开承认“我已经真的失败”了,启蒙言说者之所以最后都变得失魂落魄,究其根因就在于他们都没有反传统的明确目的性。启蒙言说者既然没有明确的启蒙目的性,那么他们与阿Q无师自通的“革命”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微风早已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

二、“狼子村”:乡土中国的隐喻叙事
解读启蒙者的命运悲剧,我们必须去重视“狼子村”的文化意象。“狼子村”虽然始见于《狂人日记》,但却贯穿于《呐喊》《彷徨》的始终,它作为乡土中国的隐喻叙事,形象地表达了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理性认知。

毫无疑问,《狂人日记》以“狂人”与“狼子村”的文化对立,开创了一种属于鲁迅自己言说启蒙的创作模式。在这一思路清晰的创作模式里,他将启蒙者从文化母体中游离出来,去分析个体同母体之间的共生关系,进而极为理性地阐释了一个重要命题——每一个文化细胞都会必然性地去负载其文化母体的遗传因素,它不能也不可能脱离母体而向异质文化发生变体;这就有如生命细胞一旦脱离了它的生命有机体一样,其结局也只能是因缺乏母体的养分而趋于死亡。曾经学过医学的鲁迅本人,对于这点科学知识当然是十分了解的;故他通过“狂人”反叛“狼子村”的盲目行为,隐喻性地谴责了“五四”启蒙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在外界“月光”的作用之下,“狂人”从混沌中突然“觉醒”,他发现养育自己的文化母体,竟有着几千年的“吃人”历史,因此他便不顾一切地游走于“狼子村”,开始了悲壮而苍凉的启蒙呐喊。可是自从“狂人”说出了“狼子村”的“吃人”真相后,他立刻就变成了全体“狼子村”村民的共同敌人(有学者曾据此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和易卜生的《国民公敌》,两者的叙事结构十分相似,都是说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其实这两部作品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思想关联性:《国民公敌》讲述的是一个“真理”与“谎言”之间的生活悖论,而《狂人日记》则是在讲述“细胞”与“母体”之间的隶属关系)。热衷于启蒙的“狂人”出师不利,他不仅要面对赵贵翁和大哥那“铁青”的“脸”,还要去面对村里“孩子”们那“铁青”的“脸”,以及妇女和老人那充满着仇视与冷漠的“眼色”:“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狂人”在宣传废除“吃人”恶习的过程当中,真正感到“害怕”的还不是“狼子村”村民对他的“看”法,而是他在进行不要“吃人”的启蒙言说时,对于自身启蒙资格的自我否定:“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所以“狂人”不再“张狂”,而是迅速醒悟且去“候补”,并以回归历史“原点”的认同方式,结束了他那颇为荒唐的启蒙闹剧。仔细阅读《狂人日记》,我们可以发现鲁迅本人的明确态度:假定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吃人”文化,而“我”也是这种“吃人”文化中的一员,那么“我”同样应是被谴责的“野蛮人”,故“我”有什么资格去教训他者不去“吃人”?鲁迅让“狂人”最终醒悟并去“候补”,这绝不是什么讽刺与调侃,而是在通过“狂人”的思想转变,向《新青年》阵营发出了一种善意的忠告。

鲁迅之所以会提出一个“狼子村”的文化概念,这与他对乡土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不无关系。“狼子村”说穿了无非就是乡土中国的一个缩影,或者说就是一种乡土中国的生活状态,那么发生于其中的一切现象,都必然会与“乡土”概念有关。“乡土”社会即小农经济社会,这种文化最大的表现特征,就是自给自足的封闭性与稳定性,一切非稳定性因素都是它所排斥的对象。学界对于阿Q身份属性的争论由来已久,有人说阿Q是“落后农民”的代表,也有人说阿Q是“国民劣根性”的象征,其实这些说法都只是一种诠释者的主观猜测。尽管在阿Q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国民劣根性”因素,但这都不是鲁迅本人想要表达的思想核心。在《阿Q正传》里,鲁迅已非常明确地把阿Q视为是“未庄”中的不稳定因素,他无名无姓无家无业是个无业游民,连作者本人也意识到他“不能说是未庄人”。既然阿Q是个独立于“未庄”文化的游离细胞,那么他与“狂人”等受到母体文化的强烈排斥,也并无什么令人惊诧的本质性差别。“优胜记略”讲的是阿Q在受到排斥后的生存法则,为了能够苟延残喘地生活下去,他必然要以“精神胜利法”去尽量安抚自己的失衡心理;“恋爱的悲剧”讲的是阿Q很想娶妻生子融入“未庄”的生活秩序,却没有料到把吴妈吓得一通哭号,不仅使他遭受了秀才的一顿痛打,而且还变卖了棉被“到赵府上去赔罪”;“生计问题”讲的是阿Q落难以后,“未庄”人都对他心中生厌,为了生存他只好去尼姑庵偷萝卜,结果又与老尼姑发生了冲突;“从中兴到末路”讲的是阿Q“发财”,阿Q变卖偷来的衣物着实地阔绰了一番,可未曾想很快便被人们识破了真相,于是乎他们对阿Q更是“敬而远之”了;“革命”讲的是阿Q无师自通的“造反”,他从“未庄”人恐惧的眼神中感到了快意,然而赵秀才却比他先行了一步,搞得阿Q在尼姑庵碰了一鼻子灰;“不准革命”讲的是阿Q去找假洋鬼子参加“革命”,被假洋鬼子拿着“哭丧棒”赶了出来,阿Q愤愤不平发誓要去县里告密,想看假洋鬼子一伙被“满门抄斩”的笑话;“大团圆”自然是讲阿Q成了替死鬼,以自己之死去换取“未庄”的平静,阿Q之死“未庄是无异议的”,他“被枪毙便是他坏的证据”。

三、“长明灯”:庸俗文化的艺术符号
若要理解《狼子村》文化的超稳定性结构,我们还需理解“长明灯”这一艺术符号的真实用意。“长明灯”原本是小说《长明灯》中的一个意象,它代表着民间祈福愿望的情感表达。笔者在这里借用“长明灯”去作为民俗文化的象征符号,目的就是为了要去揭示《呐喊》《彷徨》“反封建”的思想内涵。

我们先来看看那些被学界理解为是“礼教”维护者的乡绅阶层。在《呐喊》《彷徨》当中,鲁迅塑造了众多乡绅形象,像“赵贵翁”、“丁举人”、“赵七爷”、“赵太爷”、“鲁四老爷”、“七大人”等,都曾被学界视为是信奉“礼教”之人;而持这种见解的全部理由,则是他们以封建“礼教”去统治乡土中国,满口讲的都是“仁义道德”,而骨子里却暗藏着“吃人”的杀机。我们首先应弄清一个基本概念:何谓“乡绅”?“乡绅”其实就是乡村中有些文化知识的普通农民,他们虽然肚子里有点墨水且经济条件比较好,但是由于“乡土”特性(自私)对于“绅士”气质(开明)的绝对制约,所以他们根本就不具有负载正统“儒学”的精神素养。《离婚》中那个气度不凡的“七大人”,竟然一点儒学“礼教”的常识都不懂,就连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爱姑都明白,中国古人“休妻”还要讲求一个“礼数”,可是“七大人”却连“七出”的条例也全然不知:“我一添就是十块,那简直已经是‘天外道理’了。要不然,公婆说‘走!’就得走。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鲁迅让“七大人”说出这番“天外道理”,并不是要去表现他对儒学“礼教”的刻意坚守,而是在强烈暗示他对儒学“礼教”的人为曲解,恐怕没有人会以此而相信,“七大人”就是儒学“礼教”的忠实门徒。《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甚至还不如那位“七大人”,如果说“七大人”还有点装腔作势,可“赵太爷”却完全是斯文扫地——他明知阿Q卖的东西值得怀疑,却偏要去购买占点小便宜。常言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赵太爷”这种农民式的贪婪心理,显然是既违背了“君子”之德,又背叛了“礼教”严禁的礼仪规范。《高老夫子》里的高尔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偷看女学生被轰下了讲台之后,他便以世风日下为借口,坚决主张停办新式女学。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鲁迅透过高尔础那泼皮无赖似的丑陋灵魂,深刻地揭示了儒学“礼教”的被歪曲过程,高尔础之类根本就不是在维护“礼教”,而是打着“礼教”的幌子去败坏“礼教”。还有《祝福》里的“鲁四老爷”,仅从作者对其书房的描写来看,无外乎是要告诉读者一个事实:爱好面子的“鲁四老爷”,对儒家学说一窍也不通。别看他在书桌上摆着“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除了这些补习文化用的工具书和儒学入门的通俗读物,在他书房里再也找不到任何与“礼教”有关的儒学经典。“鲁四老爷”的那个“书房”,应该说是对中国乡绅文化程度的一种诠释——大多数乡绅的知识水准仅此而已,那么他们对于“礼教”文化又能了解多少呢?



(关于本文的一点说明:这篇文章是笔者近来所写的鲁迅研究系列文章之一,关于鲁迅对于“庸俗”与“礼教”的不同看法,以及鲁迅小说与杂文两种文体在反“传统”方面的不同表述,笔者已经有过专文去加以详细地描述,所以就没有在此全面地展开。有关这一方面的观点阐述,可参见拙文《反“庸俗”而非反“礼教”:小说〈祝福〉的再解读》,载《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1期;以及《“热风”与“冷气”:从杂文看鲁迅早期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载《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4期。)
注释
①李希凡:《“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檄文》,《江汉论坛》1979年第2期。
②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

④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中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067页。


⑦钱理群:《“为人生”的文学——关于〈呐喊〉与〈彷徨〉的写作(一)》,《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⑧比如王晓初在《鲁迅与五四新文化精神》一文中,就认为夏瑜不是一个启蒙者而只是一个造反者,直接把夏瑜排除在启蒙精英之列,便明显是因其对“启蒙”概念的误读所导致的结论误判。该文刊于《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9期。

⑩宋剑华:《“狂人”的觉醒与鲁迅的“绝望”——〈狂人日记〉的反讽叙事与文本释义》,《学术月刊》2010年第10期。


















责任编辑 王雪松
No Need to “Hesitate” While “Screaming” ——On the Puzzlement and Doubt about Enlightenment in Lu Xun’s Novels
Song Jianhu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The themes of Lu Xun’s novelsScreamingandHesitationare not to attack “Confucianism” as was interpreted by previous literary researchers,but to reveal the complex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individual and cultural community through a series of vivid stories. Lu Xun has found the historical reasons for “altar lamps” of the Chinese local cultures from the mental confrontations between “solitaries” and “wolf village”:“vulgarity” and “mediocre mass”,as strong forces in Chinese countryside,have been defying the so-called elite “Confucianism”. In Lu Xun’s eyes,since “vulgarity” and “Confucianism” are two confronting concepts, anti-tradition should focus on anti-vulgarity,which is what “reforming national characters” really means inScreamingandHesitation.
Screaming;Hesitation; solitaries; wolf village; Confucianism; vulgarity
2014-11-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娜拉’现象的中国言说”(13FZW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