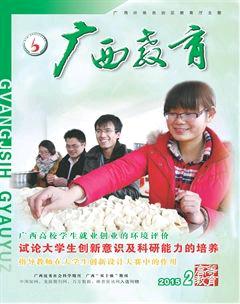君子与器:孔子道之观察
【摘 要】孔子并不排斥器,孔子看轻的是仅以己身供人用,则我身仅如一器,无道可言,己与道不是合为一体,而是己与道隔绝分离。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君子不器,而仍贵其能为一大器,己与道之合为一体,其义在此。孔子之道,进则以政治为业,退则以学术为业,道须臾不离己身,孔子用道行道之志坚,然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不得已删订诗书以讲道传道。
【关键词】君子 器 孔子 道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5)02C-0123-03
孔子言器,子曰:“君子不器。”孔子言道,子曰:“士志于道”。孔子言君子儒,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论语》讲“仁”109次,“君子”107次。 “君子”有着深刻而丰富的道的内涵,作为仅次于“仁”的价值追求,是孔子思想体系里的又一核心概念,它与“器”、“道”关系如何?
一、君子与器
《论语·为政》中“子曰:‘君子不器”提出了君子与器的关系,其含义为君子不像器皿一般,只有一定的用途。
“器,皿也……皿,饭食之用器也……有所盛曰器……”器本意為器皿。器皿,有用为其第一性,强调的是物对人而言的有用性,可以满足人的某种或某方面的需要,是以人言器,器是工具,人是目的。但君子,是以人言人,人是人的最高目的,亦即终极目的,不是手段,人的意义和价值不可与器同言。君子不器,这里孔子并没有否定器,而更为强调君子内在的品质,即道,通过自身的修养、克己、重礼来体道,修道,行道。
君子不器,而贵其能为一大器。孔门力主培养通人,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无所不通,尤要通于道,如此方能更好地求道明道,识得道之大体。儒者深以一事之不知为耻,应博学以成名,注重其弟子学识才能的多元性,若只强调某一特殊有用之目的,不免落入“器”之窠臼。君子表层显性为器,内里隐性为道,表象为器,内核是道。君子以道作为其身份理想与责任伦理。君子重道求道。
“器”在《论语》中一共六见,兹列于下: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论语·公冶长》)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
管仲之器小哉。(《论语·八佾》)
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君子易事而难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论语·子路》)
从上面所引材料中可以看出,“器”的含义可分为四类:器皿;工具;器量,器度;动词,把他看成器物。
器皿,只具有某种特定之用途,其价值是单向度的,而君子的价值是多向度的。这里孔子把君子与器类比,在一定条件下,事不成无以知君子,君子成事与器皿的价值是相符的,成事亦体现君子的有用性。孔子以子贡为器,认为子贡为瑚琏之器。瑚琏藏在宗庙,是贵器。所以孔子并没有排斥器。
器,强调有用性,是物理的、自然式的属性。道,强调无用性,即无功利之用,是社会式属性。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者中,形而下者的政事,接近于器;形而上者的德行、言语、文学,接近于道。因为政事仅行于国内,德行、言语和文学已超乎国而达于天下。所以孔子说,士志于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尽力于求的是道,而非衣食、钱财。樊迟向孔子请学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孔子说我不如老圃。孔子给樊迟下了一句断语“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这里无涉乎孔子鄙视生产劳动之说。孔子只是向其弟子表明孔门子弟任重而道远,要求形而上之道,求己与道之合为一体。孔子也不避谈劳动,太宰向子贡询问夫子何其多能时,子贡隐晦地回答说,天纵使其多能也。孔子听到后,道出了其多能的真相,“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孔子希望其弟子孜孜以求的是道而非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希望其弟子既有美德又能居于有影响力之地位,如此其道乃得常行于天地之间。
禄的获取要有合宜性,即“度于礼”。例如:“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
冉有仅为季孙氏用,成为其聚敛之器,不仅悖礼,也背离了孔门的君子理想,加剧了邦无道,是君子之耻,所以孔子说冉有非吾徒,可攻之,是器之犹下者。
君子不是像“器”一样仅是一个分的概念而是作为一个合的概念而存在。所谓“分”是指己与道相互背离相互脱离;所谓“合”是指己与道合为一体,即体道也行道。“‘君子不器这个根本的理念,意指人的自身就是目的,而不只是作为某一特殊有用之目的的手段。”在通才的教育下,儒家的“君子”所赞同的是人与道合为一体的身份理想与责任伦理,是以合宜之道求天下之有道。
二、君子与道
《论语》首章即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第一章第一篇便说君子之悦,君子之悦,悦在何?一悦,学而时习之。孔子曰:“君子求诸己。”此要求学者反求自身,自作考验。悦与不悦,必待学者自知之,非师所能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只是自身经验,令人亦亲验之,不强人以必信,此为学者留地步,亦是礼。二悦,有朋自远方来。此要学者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志同道合者自远方来,切磋琢磨,砥砺以进,自是赏心乐事。三悦,远离怨恨。此要学者“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自身经验不强人知,亦不急于别人之不知,怨恨自然不会来,此为别人留地步,亦是礼。
君子之悦,悦在求道明道,悦在自得其道。悦之体为道,悦之用在学,在朋,在己。而学之内容即道,“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困于陈、蔡之间,犹能弦琴于室,恬然推琴,子路、子贡以此为君子之耻,孔子却说:“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愧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故君子谋道忧道,士志于道,以弘道为己任,正因为学道得道,己与道合为一体,其遇虽穷,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因为道,所以甘之如饴。
孔子历聘诸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积极求仕,以实现其道,终而莫能用,西狩获麟后,孔子慨叹吾道穷矣。孔子之道乃人文世界人伦日用之道,即尚书之五教,五常,应然也: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孔子的求仕与求道是一体的。若仅以己身供人用,仕而不能行其道,我身仅如一器,孔子耻为。
道即秩序,平衡,而人伦日用之间则表现为“礼”。《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孔子对齐景公以君臣并言,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各安其道,大道得行而通,大同之理想亦可期而至。又《论语·八佾》:“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之相对以忠、礼并举,并非专责人臣。如此天下才能够达到“礼之用,和为贵”的效果,先王之道也尽在其中。但是也要避免为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事君尽礼,人以为谄”——的境况。
孔子不言天道,而专重之人伦日用之道亦由天道相感而来。“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此亦天道。道在阴阳之相对。三年之耕有一年之蓄,虽有水旱灾害而民无害。故贵于有人道以应天道。孔子不言天道而言天命。死生有命是天道,慎终追远则属人道。葬祭之礼由是而生。礼属人道,亦由天来。孔子虽由天道感应人道,会通合一,而终必以人道为主。
“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贞者,正也,指天地之正道以及万物之新生的前进的运动,即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与《尚书·大禹谟》中提出的“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一脉相承。此外,《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为政之道亦即正,君臣各守其德,各正己份。所以圣人参天地而措诸民,为政以德,泛爱众而亲仁,强调“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未知生,焉知死”。尽管孔子不言天道专论人道,但是礼作为人道的载体,沟通人道与天道的媒介,退可承载人道,进可效法天道,也为后儒形而上的推演留下了契机。
孔子之大同理想,可以从孔子与其弟子相处间,从弟子记载中可以窥见。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从孔子与其弟子的记录可以看出,孔子是从“治于道”——更高大统——的层面来讲述自己的志向,但是也不脱人文世界的本质。“秩序”是先秦时期元典文化中的核心关键词,先秦各家思想中都包含此一观念。孔子没有具体名言“道”的内涵,但是却从“道”的表现和外延很好地说明了“道”。孔子要求弟子在求道过程中自得其道并积极行道。孔子早期传道,登其门者为先进,其时皆有志于用世。孔子晚年传道,登其门者为后进,值孔子衰老,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即便道不行,孔子也没有“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转而致力于文章典籍,用道行道之志缓而讲道传道之心切,述而兼作者《易》《春秋》,孟子推孔子作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矣。庄子称《春秋》为先王之志。孔子卒后,孔门弟子普遍蒙受各方重视,大者为师傅卿相,如子夏为魏文侯师,小者友教士大夫,或者隐而不见,如子路居卫等,然而无一人获得政治上之大用。尽管如此,孔门七十多弟子散游诸侯,使得孔子之道乃得常传于天地之间。
君子不器,从理论层面而言谓讲道,从实践层面而言谓用道。不论是讲道还是用道,其边界是“度于礼”。孔子以子贡为器,子之器瑚琏也。瑚琏藏在宗庙,为贵器,不能随便使用。冉有,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冉有仅为季孙氏用,则犹下于子贡之器。由此可见,孔子并不否定器。孔子于政、教两大统之外,更追求更高大统——道。只是言道,更过于空疏迂阔,退而求其次,始则修其身,继则齐其家,专重人伦日用方面,从道的操作层面讲求。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天下有道强调的是人文世界的秩序,道即是目的也是手段。孔子之道包含着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孔子认为君子是有大德之人,大德即以众人之事为己事,君子之德风,其使命是纯风化俗,使天下有道,故而对以政治为业的君子而言,“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子贡向孔子问政,足食,足兵,民信,三者不得已先去其一,孔子说去兵;再去其一,孔子说去食。对于君子或者为政者而言,真正困扰的不是足食与足兵,而是信义。信义行,才能无道就有道;天下为公,大道方可行。而这也正是圣贤理论与现实政治实践存在相当严重差距的关键所在。因鲁国不见用,孔子不得已而周流,“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自卫返鲁,大不得已而删订诗书,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致力于文章典籍,求道讲道明道传道。所以朱熹私下坦诚招出:“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下转第151页)(上接第124页)
【参考文献】
[1]許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86
[2]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下册[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558
[3]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31
[4]应劭,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315
[5]唐明邦.周易评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5:225
[6]马克斯·韦伯.入世修行:马克斯·韦伯脱魔世界理性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3
[7]四部丛刊集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十六)·卷三十六·答陈同甫[M].
【作者简介】尹建强(1980- ),男,山西平遥人,硕士,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讲师,研究方向:专门史。
(责编卢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