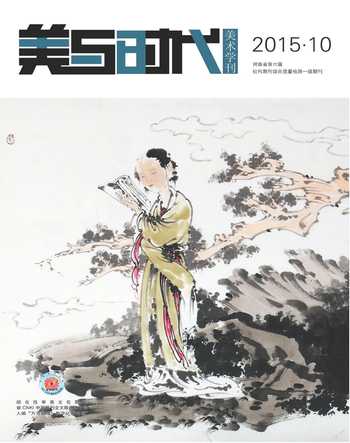生活中的艺术
摘 要:艺术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作为人类对世界的感知,艺术表现的是人类自身生活的真实体验。人体艺术、图画艺术以及死亡图像的艺术,这些生活中的艺术深深影响并震撼着人们,直到今天,纵然大众还是认为所谓艺术就是美术馆中陈列的作品,但是却全然不知所谓的艺术已经在自己的身边围绕,息息相关于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与物。
关键词:艺术;生活;意象;图画
艺术塑造并界定人类。人类先祖创造出使世界合理化的意象,制造了协助我们为自己定位的视觉遗产。这种意象主导人类生活,教导我们如何思考,如何去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每天都处处可见的这些意象、图画、象征物和艺术对人类具有如此之深的影响力。艺术作为人类对世界的感知,表现的是人类对自身生活的真实体验。让我们从下面几个方面走进艺术的世界,探索人类艺术的起源。
一、艺术中的人体
人体意象全面主宰我们的生活,人体图像充斥在我们的大街、杂志之及电视荧屏上。人的形体深深吸引着世上伟大艺术家的心灵,使他们创造出令人屏息的人体形象。然而不论以何种形式,在何处出现,世上最受喜爱最具影响力的人体意象都具有某种共同特点——都不像真正的人体。
在20世纪初期,三位奥地利考古学家领队在维伦多夫附近展开考古工作并发现了如今典藏在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中拥有两万五千年历史的人体雕像——维伦多夫的维纳斯,作为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有四英寸高,以石灰岩雕刻而成,玲珑小巧,显然这座裸体女雕像并不像真人。它夸张地表现了人体的某些部位,如胸部、腹部和大腿,同时完全忽略了其他部位,如手臂和面容。使这些远古艺术家创造出这种意象的原因,有些研究人员认为是人类大脑内的潜在意象。就像近60年前对海鸥的研究一样,认为来自于脑部受到刺激的夸大本能,对三条红条纹的木棒比对单红条纹的要更感兴趣。而海鸥的夸大本能并不能在古埃及的艺术创作中得到证实。在公元前五千年以前,埃及已成为全面定居的文明。作为世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埃及人是第一个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中采用人体意象的定居民族。这里的艺术家并没有夸大身体部位,而是选择以最清晰的角度去呈现每个身体部位。在卡尔纳克大神庙最古老的部分发现这种“埃及风格”一直延续并传承了几千年。埃及风格千古不变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意象创作是受到坚持一贯性和秩序的驱动,这正是后人关于埃及文明的文化价值观。一旦在他们的人体绘画中看到这种强迫观念后,就会开始在他们生活中的所作所为里见到它。就如在吉萨的三座金字塔建筑所表现的一样,它们是由法老王顺级而下的阶级制度之庄严的体现,它们的设计极为严密精确,象征在沙漠上所建造的严谨秩序。同时也可以在他们的雕像上看到对永恒及秩序的坚持,就像他们的建筑雕像规模之巨大宏伟,令人赞叹。埃及人之所以创作这样的人体意象,不是因为其脑部受到兴奋感刺激,而是起因于他们的文化。这或许可以说明意象主宰我们的现代世界是因为它们都反映或代表着人类文化的某个特定层面。我们人类不喜欢现实,我们共有的生物本能偏好夸大的意象。希腊人在达到完美复制人体的写实巅峰后并未一直持续下去,他们的文化驱使他们追求真实,但最终却本能地抛弃了这种艺术。这说明驱使我们意识的动力不只是文化,还有一种性喜夸大的原始本能。这种本能深植在我们的脑中,只是有些文化抑制了它们。于是人类便开始合乎法则地扭曲夸大脑部对于身体的审美反应。随着现代社会趋向多元化的发展,我们夸大的事物更有所发展。现今那种本能依然存在着,如夸张的漫画艺术,它将我们引到人体的最终极状态。服装和行销意象也是一样,推出一些我们认为总要夸大的特质吸引我们的目光。在科技时代,我们加深了这种渴望。在我们自身对于人体美的崇拜心态下,我们甚至会对自己那么做,会花费巨资去夸大我们认为迷人的部位。
世界在改变,未来我们可能会和埃及人一样压抑这种夸大的欲念。但目前,我们将承载远古先祖在三万年前所开创的一切。
二、图画艺术的诞生
我们每天都反复做同一件事好几百遍,那是人类极为赖以生存的能力,我们却视为理所当然。我们看到一些线条,就能联想到其意义。我们能够分辨不同形状,还可以清楚地了解色彩的安排可以代表什么。辨识意象的能力是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部分。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能力,无法理解意象的意义,意象便不会问世。我们会失去非常仰赖的事物,生活将变得无以为继,我们的世界将会无可辨识。但在远古时代的某个时间点,世界就是如此,没有意象存在。人类在某个特定时间开始创造图画,了解它们代表的意义。那些经典古董绘画中的骏马意象图画大约是在公元前一百年用来装饰罗马庭院的,说明当时的艺术家已经掌握了绘制二维图像的能力。这幅图画占据着庭院的顶部,由数十头野牛的图画组成,画中的野牛姿态各异,站着的睡着的跑着的都有。在这一发现公布于众后,考古学家们迅速对它们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他们很难相信这些是由史前的野蛮人创作的。但数十年后,一个个类似的发现接连出现在法国以及西班牙,这些发现都证实了那些图画作品的真实性。越来越多的史前图画得以重见天日,无疑表明了史前艺术家有着能与现代艺术家相媲美的自信与绘画功力。毕加索曾经说过:“当我们第一眼看到这些图画时,我们会意识到我们什么也没有学到。 ”
考古学家们认为数千年前的史前人类创作出图画是为了对周围世界做出反应。但是随着越来越多史前图画的发现,他们认识到这个解释很明显是错误的。因为如今的艺术家创作的素材源自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史前人类创作的主题却几乎是同一类事物。史前艺术家钟爱的创作主题是动物,但并不是所有的动物,只是一些特殊的比如牛、马以及驯鹿。一位20世纪最初关心洞穴艺术的法国专家Henri Breuil认为,这些洞穴艺术表现的是狩猎,史前艺术家们之所以创作关于动物的图画是因为他们相信这对于提高狩猎成功率有所帮助。但随着近代考古学家对洞穴附近被猎杀动物的骨骼进行检查后发现,这些被猎杀的动物并不是史前人类画的动物,他们吃的动物与画的动物似乎没有联系,所以“狩猎理论”站不住脚。我们不敢想象如果不懂反应,周围世界某些事物的绘画是怎样一种情形。我们将面对的只不过是一堆杂乱的线条符号,它们没有任何意义。人类并不是有天突发奇想去画画,而是我们先熟悉了大脑产生的图像,然后才把它们画在了墙上。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看到”的景象永久地保留下来。经过研究最终得出:数千年前从来没有见过图画的人是通过幻象创造出二维图画的。史前艺术家们的作品反映的不是自然界,而是大脑产生的幻象。这个理论解释了我们是如何从一个无画世界步入有了洞穴图画的世界的。
如今我们的世界已经被图像所主宰,它们正是由数千年前的人类从那些能征服世界的线条、图形以及色彩中得到的启发逐渐演变而来的。
三、死亡图像的艺术
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数以千计的图片在以不同的方式对我们施加影响。但是其中有一种图像特别有感染力,它们使我们在惊吓的同时也令我们感到舒服,这就是关于死亡的图像。
我们为亡者建墓立碑,并把他们的遗照挂于厅堂,像大多数人一样,我们把家族先人的图像都收集了起来并乐意处于亡者图像的包围之中。因为我们是如此地深爱着他们,我们希望保留着对他们的回忆。但事实上这个举动的起因不仅仅只是这些。
在19世纪50年代,一队考古学家在中东地区的约旦山谷发现了一些颅骨,这些颅骨被艺术性地装饰过,并最终推测出在9000年前,这些经过装饰的颅骨就被保留在人们的家里。这是个不可思议的发现,因为这很可能意味着这些颅骨就是最早关于亡者的图像,它们被制作出来就是为了被活着的人所观瞻。同样,考古学家们还发现,数千年前在现在是乌克兰的地方,古代的艺术家也有这样的举动。在如今的东南亚地区的土著居民对他们死去的先人也有同样的行为。考古学家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生物本能,一种人类的心理倾向。我们人类是唯一一种意识到生物体死亡的不可避免性的生物。我们拥有无穷力量的大脑可以想象出一个我们死亡后的世界的样子。只有人类明确地意识到他们会死亡的这个事实,为了消除这些意识带来的恐惧,心理学家认为它是可以通过艺术来达成。艺术所做的就是给我们以控制自然的力量。所以,通过创作出我们先人的图像,我们或许会认为死亡并不是那么可怕。
还有另一种关于死亡图像的存在,它们却起着相反的作用。他们会引起我们对死亡的更多更可怕的恐惧感。这些关于死亡的图像不是为了让人们安心,它们令人苦恼,令人害怕。在调查了人类创造这些图像的原因后,结果显示:这些令人恐惧的艺术品是对真实事件的艺术记录。数千年来,拉美地区被一系列古文明所统治,包括印加文明、奥尔梅克文明以及玛雅文明,它们无一例外地创作出了令人惊恐的死亡之图。太阳神庙是阿芝台克人最神圣的地方,在神庙的壁画上的太阳神手中有两样东西,手中是人类的心脏,嘴上则叼着一把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祭坛。通过这种死亡艺术手段的应用,他们牢牢控制了人们的心智。而且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图像令人们感到害怕,心理学家们还相信这些图像对阿芝台克人民有着更深远的影响,令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与社会价值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各种情况下,关于死亡的图像被用来把人们与某个原因联结起来。所以,由于我们的祖先在9000年前的寿命很短,死亡的阴影时刻都笼罩在当地居民的头上,令他们心神不安,为了对自己生存状态进行再确认,当地居民对死者进行了艺术性装饰。
我们周围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死亡图像,一种令我们心安,另一种令我们心惊。两者对人类的思想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就像十字架,它就是能够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影响人类思想的一幅图象。它是一幅可怕的图像,代表着痛苦、失去与折磨,同时它又是一幅能带来安慰与希望的图像。这种结合使得十字架成为了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象征。
这些生活中的艺术深深影响并震撼着人们,直到今天,纵然大众还是认为所谓艺术就是美术馆中陈列的作品,但是却全然不知所谓的艺术已经在自己的身边围绕,息息相关于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与物。
作者简介:
沈志,安徽师范大学研究生。
指导老师:鹿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