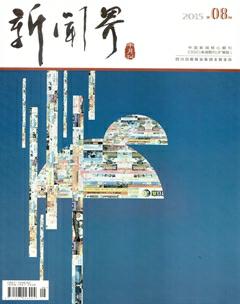旧历年
李天斌
敬母
西方有“母难日”的说法,说孩子出生的时刻,即是母亲的受难日。其实在我的乡村,也有这样的认为。我小时便经常听说:“儿奔生,娘奔死”,说的便是母亲分娩的时刻,这个时刻,既是孩子的生日,也是母亲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时候。
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在我的乡村,对母亲的尊崇,往往要胜过父亲。父亲们往往也甘愿把自己摆到其次,如果有小孩跟母亲不睦,甚至稍稍顶撞母亲,父亲们就会大声呵斥孩子,说你咋就这样忤逆?又说你母亲为了生你,已经去阎王殿里走了一圈呢。孩子们便都会知道自己错了,并且立刻就变得懂事起来,房前房后地忙着帮助母亲做这做那,来自小小心灵的悔意,把对母亲的敬意,一下子就从冬雪转到春风里。
我小时每每读到水漫金山的传说,或者是状元寻母的故事,便常常觉得人世之上,唯有对母亲的敬意最是赤子之情,最是能牵人情怀的念想。每当看到母亲在生活里奔波忙碌的身影,还忍不住会涌起一种隐约的功名思想,甚至幻想着自己也能金榜题名、仕宦有期,再或者英雄系马、壮士磨剑,总之在出人头地后回报母亲。
对母亲们的敬意,尤其是在母亲们去世之后表现得较为突出。
我小时便知道,每当有母亲们去世时,必定要为其诵念《血盆经》。关于这《血盆经》,古书里说的是,因为母亲生育总是沾染血污,会触污神佛,死后下地狱,必将在血盆池中受苦,唯有在生前为其诵《血盆经》,才能除此一劫。明人汤显祖在《南柯记·念女》这样记述:“到问契玄禅师,他说凡生产过多,定有触污地神天圣之处,可请一部《血盆经》去,叫他母子们长斋三年,总行忏悔,自然灾消福长,减病延年。”在我的乡村,母亲们生前是不需诵《血盆经》的,只有去世之时才诵念,诵念时必得要特意设置一问经堂,孝男孝女跪满一堂,并举家吃素,以示清洁的敬意。不过,关于《血盆经》,我倒觉得佛家真有些不是,甚至是曲解了的。母亲们生育时虽然沾染血污,但那又怎能说是不洁呢?在那血污里,既是生命的诞生之光,又是母亲们的牺牲之光,均充满了生命的圣洁与肃穆,又怎会触污神佛呢?神佛之心,或许也有失从容致远?
除了诵念《血盆经》外,在母亲们的葬礼上,凡亲生女儿,必要喊上一曲《清凉水》。关于“喊”,其实也就是唱的意思。但我无疑更喜欢“喊”字,总觉得一个“喊”字,更能让人看见那情感的真挚动人,也更能映照某个时刻的清凉无依。
喊《清凉水》时,必得在三更天。旧时乡村,没有手表计时,把一个夜晚分成“五更天”,“一更二更”尚属于浅夜,“四更”属于过渡,“五更”已近黎明,人世都处在喧闹之时。唯有“三更”正是夜深时候,正如花开正繁,酒醉正浓,而万物寂寂,人潮退去,世象隐退,一缕悲切之音便可以从遥远的天际慢慢清晰。这个时候,女儿们就要打来一盆清清亮亮的水,端端正正地放在灵前,然后虔诚地跪下去,一边呜呜地哭,一边轻轻地喊。至今我仍然能记得如下几句:
天上一声金鸡叫
地上儿女想娘恩
我娘要喝人间清凉水
我娘不喝阴间迷魂汤
清凉水,水凉清
我娘魂魄何时归
唱腔婉转凄切,哀怨如重重落霜。再加上每唱完一句,那喊的人便要舀出一瓢清水,洒向灵前的夜空,同时磕一个响头,那一份忧伤,就像一颗在此时醒着的心,人世清凉,诸多缱绻,均在此时荡漾漫漶。一直多年,我总不能走出这样的场景。也一直多年,我乡村的女儿们,在母亲们还未去世时,便一定要预先学会唱《清凉水》,好准备着在将来的某个三更天里,替自己的母亲轻轻地吟唱,去了结人世最后的情缘。若干年来,这已经成了村庄女儿人生必修的课题,——而整整一个乡村,乃至所有的旧时年月,也因为这样的坚持显得温婉柔情了许多。
端午
我的乡村不知道屈原,却很看重端午。端午这天,家家户户都要扯来菖蒲,但其实我们都不叫它菖蒲,我们并不知道它还有这样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多年后才知道的。那时候我们都叫它艾草,据说端午这天将其悬挂在门头上,就能驱邪避祟。又因端午正是蛇出没的季节,所以还在房前屋后泼洒雄黄酒,有个别人家,还吃雄黄酒,的确跟屈原的端午已经相去甚远。
不过,端午这天,家家户户却是要包粽子的,这似乎又跟屈原扯上了关系。但真要问及包粽子的意义,却又没人能说得清。由屈原留存在端午里的家国情怀,流淌到我的乡村之后,早已无迹可觅,就像一条断流的河水,最多是,只剩下了几块隐隐约约的石头,提醒一条河流曾经的存在。
从后山摘来青竹叶,再拿出隔年的糯米,便可包粽子了。旧时乡村,糯米极贵,有多余的,早都卖了换作儿女的学费或是用在亲戚之间的来往上,但为了过端午,几乎家家户户在上年秋收时就要有意留下几斤糯米,实在无法留下的,想办法也要弄它三两斤。因为如果不包,等别人家小孩拿出煮熟的粽子满村溜达时,自家孩子就一定会觉得委屈,甚至觉得低人一等。端午包粽子,显然已经超越了风俗的范畴,更有那做人的脸面在其中。
我母亲包粽子的手极为灵巧。村里很多新媳妇,端午这天都要来跟母亲学习。新媳妇们总是笑眯眯地围坐在母亲身边,一边听母亲仔细地讲解,一边目不斜视地看着母亲把一捧捧糯米放在一张张青竹叶中然后上下翻卷,其用心完全不亚于对女红的专注。还有我姐姐和妹妹她们,因为近水楼台的缘故,未及出阁,便已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包粽子。
包粽子自然是女人的事。男人们在端午这天,想的却是雨水以及农事。
早在端午之前,农事就已经很深了。稻秧已经可以移栽,天气却一日比一日还要晴朗,河流里剩下的水已经细若游丝,新田根本打不出来,望着一天比一天高的稻秧,男人们的心也一天比一天焦急。好在时间终于到了端午,很久以来的焦急似乎就石头落地一般。因为每年端午,似乎都一定是要下大雨涨大水的,俗称“端午水”。“端午水”年年如期而至的同时,也把农历节气的神秘,紧紧地留给了人们。
一般是早晨,果然一直晴朗的天空突然就出现了几片碎碎的云朵,再下去,那云朵便连成了片,再下去,整个天空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顷刻之间大雨滂沱。就连一直专注于包粽子的母亲和小媳妇们,也都忍不住站到屋檐下,抬起惊诧的目光,惊诧地看着这神秘而至的大雨,而当她们重新回到粽子上来的时候,就觉得在一场突然而至的大雨和一个粽子之间,似乎也有某种神秘的关联和对应。
“端午水”之后,整个田野里便响起了欢快的吆喝着牛打田的声音,无论是男人女人、大人孩子,便都纷纷走进了田里,把一根根稻秧,插进了刚刚打好的新田。一缕新的喜悦和希望,便在端午时节开始真正地荡漾起来。也因此,端午这天,还被亲切地称为“开秧门”的节日,到这里,我乡村的端午,跟屈原就已经彻彻底底地没了任何关系。
花灯
大观园里,每逢喜事,必定要唱戏,还要作诗。即使到后来人去园荒,那戏台仍然要搭起来。只是,在这里听到的已经不是人世的繁华和热闹,唱吟中满是繁华褪尽的落寞,是人世某种精神最后的挣扎和坚守。旧时乡村的花灯戏,虽然也年年都要唱,丰年唱,荒年也唱,却远没有这样的精神自觉,最多是寻觅一缕日子里的寄托,虽然跟精神有关,却不一定跟精神紧密相联。
不过,真要追根溯源,旧时乡村的花灯戏,却也是有来历的。据说这花灯戏原本生长在江南之地,只是后来随朱元璋“调北征南”的队伍来到黔地,并从此在黔地山野里留存了下来。我原先怀疑此说是村人对帝王和历史的攀附,直到后来我能读书识字,并亲眼看到我的家谱上追溯到的祖籍也在江苏南京时,才相信了关于花灯戏的传说,甚至还为我的乡村感到了几分莫明其妙的骄傲和自豪。
不过,传说毕竟是传说。真实的情形是,当花灯戏流传到我能亲眼目睹时,早已像一个流落民间的没落贵族。虽然那一唱一吟之间,仍然是帝王将相和忠孝仁勇那般的庙堂文化,一眼一眉也还是来自庙堂的端庄和肃穆,但更多的却是飘渺——只需看一眼那简陋的舞台,只需看一眼台下的泥土,生活与梦想的距离,就好比这花灯之夜跟那轮月亮的距离,凄清遥远。是的,旧时乡村的花灯,人虽然多,甚至是四邻八寨的乡亲们都要来,但所有一切却都是简陋的,舞台是简陋的,一盏盏的红灯笼是简陋的,演员的服饰也是简陋的,只有人们表现出来的热情堪称隆重。有时即使天上落着细雨,人们仍然要坚持着在那露天的舞台下坐着,而那露天舞台上的节目也一定要照样唱下去,那露天的红灯笼也一定要照样高高挂着,真好比那戏里的地老天荒,不论今夕何夕的浪漫与坚贞。
花灯戏里的节目,仅有《汉高祖斩蛇记》《三英战吕布》《杨家将》《岳家将》《穆桂英挂帅》等关于帝王将相的几出,抑或轻松些关于才子佳人的《唐伯虎点秋香》之类,却从来就没有过跟乡村的日子和岁月有关的节目。这实在是可以称得上奇异——村人并没有那些在花灯戏里的所谓高远的精神寄托,也不能从花灯戏里找到紧贴自己日常的种种,但对花灯戏却有着澎湃的观赏热情,这一矛盾,常常会引发我后来的思考。但我敢肯定的是,我小时每看一次那些节目,就都会有一次震撼,总觉得人世原来可以有另一种颜色,总觉得自己可以离开这山野里的大地、河流、庄稼,就像戏文里的那些人,完全可以铿锵一吓的。虽然我的命运证实了这只是一种妄想,但在后来的人生里,至少在精神上,我却是处处都能寻觅到那种铿锵之气的,这不能不承认,一台台的花灯戏,有意无意之间,必也是有它意想不到的作用,好比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我十五岁离开村子读师范后,不知怎的,花灯戏也随之落幕,并从此不再上演,再到如今,已然是彻底地湮没了。每次想起,都会有一种怀念之后的怅惘,总觉得跟花灯一起湮没的,并不仅仅是一段曾经的日子与岁月,——但还有什么呢?其实,说句实话,至今我也还没有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