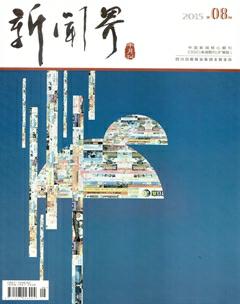酿酸了的葡萄酒
金者言
胡适先生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然则,历史向来是为现实服务的,这样一来,一段段往事经过采择、润色,款款朝今人走来,历史那蓬头垢面的狰狞面孔也变得鲜活起来,其中功效,足以引发今人的历史感与现实感。就国史而言,当今中外史学界有多种历史观,若以华裔中人论,则以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唐德刚的“口述历史”等等为其中荦荦大者,是脱离旧窠的治史方法。得失姑且不论,但仍然是以为今人提供借鉴蓝本为出发点的。这二者虽然在方法上颇具独特性,但顾此失彼处又令人不敢过分恭维。这便是毫无丘壑的实用主义历史观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
古称:信史难得,到了游戏化的今天,若再想要求得披沙拣金考据出来的史实,简直是不可能,如果不能够服务于现实生活,也是没有用的,有时甚至会让“受惠”者感到索然无味。胡适的那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甚至已经成了笑谈。这是历史进化造成的,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
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真学问是二三素心人于枯索的荒野、山村里求得的。标榜是一回事,事实又是一码事了。现在哪里去找这种人?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在治史时本来是一对冤家,将它们捏合在一起的时候,又不失为一种方法与工具,可是到了如今,连这个“法宝”也丢掉了。真是要令严谨的学者顿发“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惋叹。
抛开历史小说不谈,文学介入历史,大概不能算是中国人的创造,时下最流行的文体是“非虚构”,这是个舶来的叫法,乳名唤做什么“报告文学”或者“纪实文学”,作者写得兴起时“山呼海啸”,读者则“如痴如醉”,这路东西基本上是会被历史学家归之于“小说家言”的。所以,文学作者千万不要得陇望蜀,痴心想兼差再当当历史学家。为了不落旧套,高明一点的作者,如果能够把握好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以及所处时代的历史特征,文字再晓畅一些,百炼钢化作绕指柔,早已僵硬得裂开无数道口子的历史,肯定能够为其所用。但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个被“演绎”了的文学作品,仅仅可供闲暇一读而已,并不具备什么参考价值。当然,并不能就此来讥笑作家,因为更多的时候是历史学家们“失足”在先。
话又说回来,不妨将视野放得更宽一点,带些许“大历史观”扫描—下这个混沌世界的既往与现实,“唯物”地说: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历史,而且确实是“鲜活”的,它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在当今这个缤纷的舞台上隐现出没。更为要命的是,这么多位“小姑娘”在历史演进的长河里,被她们难以计数的“后爹”、“后娘”们梳洗打扮,赋予外在形式之后,又大多被安装了_一个思想内核,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自觉或不自觉地要为现实服务或是服务于某种目的。于是便有了孔仲尼诲人不倦的德操,太平天国天兵天将们亲和的笑容,义和拳大师兄高瞻远瞩、理念通达的高大形象等等,真是奇妙极了。真正如钱钟书所说的几个“素心”人在寂寞中皓首穷经的故事,恐怕只能够在教科书里头才读得到。
上世纪末,父亲的旧日同学,从台湾来的张慕飞老先生赠我一册自传《永不放弃》。张将军曾经率台军精华装甲旅屯驻金门,又因历史渊源与蒋纬国将军过从甚密,更妙的是他还当过蒋氏的死对头李宗仁先生的侍卫官。将军是我的父执辈,虽然他在西班牙陆军大学精研武学的时候,还读出个“比较文学”硕士的头衔,但是,在他的这本自传中竟没有一点文学味,质朴中透着纯真,给我启发不少。后来回想起来,将军曾于不经意间透露,纽约的唐德刚教授是其老友,黄仁宇先生更是多有过从。我在胡打乱撞中竟遇见个中高手了。
也是有缘,先后在慕飞老伯沪上闵行区古龙城寓所有幸见到黄仁宇先生与唐德刚教授,还有《塔里的女人》的作者卜乃夫(无名氏),几位前辈达人的旷世高论,真是令小子如闻天籁,受益匪浅。1945年7月,胡宗南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权倾一时,麾下的三位年轻上尉也大大有名,这三位便是蒋纬国、熊向晖、张慕飞。有一次去上海办事,顺道往访张将军,竟然见到了智勇兼备的熊向晖。真是难以想像这位垂暮老人当年的风采——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命令左手送给毛泽东,右手下达国军的攻击部队。述旧事如同讲天书,人和事的两面性阐释得淋漓尽致,所以要说“生活比文学更精彩”。当时便有了打张飞机票到台北去张望一眼蒋纬国将军,凑他个同花顺的念头。写出来呀,写出来呀,你为什么不写?朋友们劝我。我写这些干什么?我又不是写起居注的!好玩呀!对,但凡写文章总是要有个什么目的。尽管我们不时要扯个骗人骗自己的旗子,动辄说这个那个不是文学,口气沉长,南郭的庄严好似三炷香后面的菩萨。其实有看头,有内涵,就是一篇好文章。写小说或者捉写其它什么,总是要说事的,如果文章里头没有事,这种文章看它干什么?这个理由不知道站不站得住脚?甭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漫溢的野火烧过,再经过历史慌乱脚步的踏踩,多少有意味以至惨痛的历史灰飞烟灭,付诸流水,“残花败柳”般的历史素材实在是没有剩下多少。要想以古论今或是说说故事,难免要经过一番精心打扮之后才能够让那“小姑娘”登台亮相,这恐怕也是要将历史与文学结合的一个缘故吧。抚胸说,这真是历史的悲哀。不过,在现实社会当中总归会有人从各种目的出发,以各种各样的角度,千方百计地来剖析历史,好在被冒犯的“历史”,早已经成了被装订成册的“羔羊”,任凭后生小子们条分缕析。有人光顾,未始不是历史这位“小姑娘”的幸运了。否则,历史还有什么价值呢?
北京有座贤良祠,坐落在地安门西大街,是古时祭祀旧日贤达的场所,意思就好比法兰西的先贤祠。古往今来,大概在全世界都有类似的场所。对于“贤达”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标准,所以历史人物们也就走进了各自的庙堂之门。古人说——文以载道,文不能载道时,也可以撩拨开被藤蔓遮掩的历史,谈古论今。可以说,都是个人读书、生活的随笔而已,贻笑大方的地方自不在少,其实并无些许玄奥之处。笔者在读史之余,也曾记录了一些历史人物的斑驳行状,摆放在笔墨祭台上晾晒、评说一番,以祭奠他们给这个世界留下的痕迹。我想,如果历史人物们地下有知,他们大概是愿意的,也不会讥笑后生小子们的唐突。
既往的人和事还能够被后世记起,提及,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