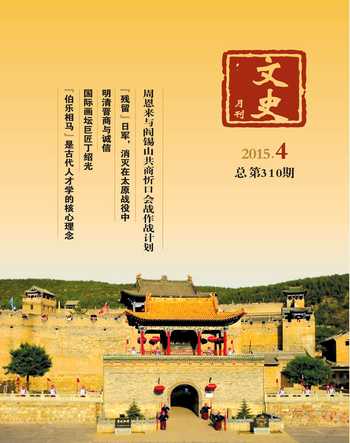“伯乐相马”是古代人才学的核心理念
孟肇咏
“伯乐相马”的故事流传了千百年,早已脍炙人口。它就发生在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张店镇虞坂古运盐道青石槽上。运城古称河东,境内有著名的河东盐池。盐池的开发很早,传说5000年前黄帝与蚩尤曾为争夺这块宝地,在此大战。晋商的兴起也是由运盐开始的。远在3000年前的春秋时代,为了打通由运城过黄河到达豫、陕的通道,人们历经千难万险,从太行山支脉中条山上开凿一条青石运盐山路。因“虞坂盘盘上青石”,又因形状如槽,故亦名青石槽,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诗文,而且有不少饮马池、相马处、响铃弯、十八盘等伯乐相马的历史遗迹。
“伯乐相马”的故事在我国古代人才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核心理念,是可以派生出许多人才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理念。我国有五千年的文化。一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也就是一部漫长的人才学史。“得人心者得天下”,同理,“得人才者也得天下”,这是贯穿时间长河的两条主线。所以人才学始终是与历史的前进同步,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在我国的经、史、子、集,以及儒、道、佛家的典籍中,都有着古代人才学理论和实践的丰富资料。
简单回溯一下历史,应该说从远古传说时代就已经有了人才学实践的雏形了。如黄帝与蚩尤大战,黄帝访求风后并封为相,终获大胜;帝尧于畎亩之中访得舜以后授以国政;帝舜启用“八恺”“八元”,又重用禹、皋陶、契、后稷、伯益等,均为“识才”“用才”的佳话。至于后来有了文字,史书有据的:汤用伊尹;五丁封傅说为相,文王用姜尚……这些脍炙人口的史实都蕴含人才学鲜活的“识才”“用才”的思想意识。但那时人们对于人才学的认识还是不自觉的、零碎的甚至是朦胧的,往往把“识才”、“用才”视为“天意”或国君的特殊才能。到了春秋战国的封建割据时代,各诸侯国竞争激烈,为了自身的发展,对有“识”、有“才”的“士”,有着特殊的需要;而“士”也确实为赏识重用他们的国君忠诚地服务,产生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意识。这就发生了古代人才学的滥觞。于是人们经过漫长的“识才”“用才”实践,孕育出了承前启后的“伯乐相马”的故事。
从典籍上考察,伯乐是实有其人的。伯乐原名孙阳,与春秋时秦穆公处在同时代。他出身草莽,因为是相马的专家,又是管马、驭马的好手,人们就把天上管天马的星宿“伯乐”的名字赠给他。秦穆公是古秦国一位中兴之主,他想富国强兵,需要大批的良马耕战,于是重用了伯乐,后来又封他为“伯乐将军”。应该说,“伯乐相马”这个故事的时代背景就发生在秦穆公时代。穆公在位时间是前659-621年,“伯乐相马”这件事发生已距今2600多年了。可是这个事件在秦穆公时未曾有典藉的记载,最早见于典籍的是在《战国策·楚策》上。说的是一位叫汗明的“士”晋见尊贤重士的楚国的春申君,想用这个故事作比喻来游说,以求见用。那么照此算来,春申君是战国前238年以前的人,这就说明这个故事在当时已经在民间流传了三四百年,并早已脍炙人口。
据《战国策·楚策》记载,开始春申君并没有被汗明打动而重用他,于是汗明就用“伯乐相马”的故事来进一步游说春申君:
汗明曰:“君亦闻骥乎?夫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蹄伸膝折,尾湛腑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阪迁延,负辕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纻衣而幂之。骥于是俛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者,何也?彼见伯乐之知己也。”
汗明的意思是,我是一匹拉着盐车的千里马,我正处在报国无门、无人识才的惨境,正等待春申君您这位识才的知己把我这匹千里马“相”出来,并把我提拔起来,让我为您做一番驰骋千里的大事。
这个不足百字的小故事,有着深刻的内涵。如果我们把它单纯看成是一方“伯乐(人)”和另一方“马”相互关系的事件,那么就可以找到贯穿于这个事件的两条线:
一是伯乐(人):重马——爱马——寻马——识马——惜马——用马;
二是马:蓄才——炼才——示才——展才。
如果把“伯乐”比作“重才”“识才”“用才”的人,把千里马比作人才,那么它在“人才学”上所占有的核心观念就不言自明了。
人才学是研究“识才”“用才”的一门科学,是研究用人一方与被用人一方各种关系的学问。在用人一方的活动是围绕“重才——爱才——求才——识才——惜才——用才”这条主线展开的;而在被用人一方的活动则是围绕“蓄才——炼才——示才——展才”这第二条主线展开的。“伯乐相马”的故事由一件真实的事件经过多人、多时的提炼加工,成为一个寓言故事,并且非常集中、凝炼、生动地体现了人才学的核心理念,这正是这个故事的难能可贵之处。
由“伯乐相马”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在古代,人们对于人才学的认识已经由不自觉的、零碎的甚至是朦胧的而变为比较自觉、完整而清晰的了。如果再进一步分析人才学中“用人”的链条可以看出,“重才”是本因,不“重才”根本谈不到“爱才”,也就不可能去“求才”。但在“求才”的过程中,“识才”才是关键。如果良莠不分、真假莫辨,那么可能求到的是“劣马”“驽马”,“重才”也会成为一场空。而如果“识才”失败,那么“惜才”“用才”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人才学中用人方面的关键是“识才”,而“伯乐相马”的关键是一个“相”字。为什么古人不说“伯乐爱马”“伯乐求马”,而说“相”马呢?这个“相”字就总结了以前的并派生出后来的人才学中的各种相(识)人法。诸如古代的“六戚观人法”“文王观人法”“孔子观人法”以及曹魏时刘劭所著第一部中国古代人才学《人物志》提出的“八观”“九征”“七谬”等具体的识人法。同时又相继产生了国家考察选拔人才的各种考试制度,如养士、九品中正制、察举制以及科举制等。一个“相”字就有如此丰富的内涵,这正是我们赞叹“伯乐相马”作为古代人才学的核心理念的原因。
同理,在“被用人”这条链条中也揭示了人才被“相”中的普遍规律:人才在被埋没时,如果不去坚持“蓄才”“炼才”,那么人才就不能战胜困难,就不可能在极端恶劣的环境生存下来,无法保持千里马的良好素质以待被“相”出,也就不能在机会来临时“示才”。在“示才”的过程中,如果不能与相马者互动,充分“展才”,有时也会与“识才”者失之交臂。作者认为,这是“伯乐相马”故事对我国人才学的一大贡献。
“伯乐相马”故事对古代人才学的第二个贡献就是如何去“相”,如何去“识才”。古代人们就认为,“得人”“用人”的前题是“识人”“知人”“观人”“察人”,怎样去“识”“知”“观”“察”,伯乐给我们以重大启示。这在汉代刘安著的《淮南子》中有记载:“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贵乎马者。”伯乐的相马理论,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以致后来出现了“牝牡骊黄”的成语。伯乐告诉我们,相马也好,相人也好,相的不是毛色性别等外在因素,而是要相其“精”“内”以及该“所见”的和该“所视”的;而要忘其“粗”“外”以及那些不该“相”的没有意义的因素。看人才要看本质,看主流,不要斤斤计较人才外在的非本质的东西,不要以貌取人,以门第取人,以富贵取人,不要求全责备,这是伯乐留给古代人才学第二个重要的遗产。
历史上,这些或因身份、或因地位埋没在人群中的“千里马”一一被举用,哪一个不是与伯乐提出的“识才”的理论相符合的呢?再拿伯乐的国君秦穆公来说,他本身就是一位“伯乐”,他能把孙阳(伯乐)从草莽中举用,本身就是“伯乐相马”的盛举。而在伯乐的暮年,他又让伯乐推荐接班人,于是伯乐又慧眼“相”人,举荐了方九堙(九方皋)这匹“千里马”,而后,方九堙又成了第二个“伯乐”。
“伯乐相马”的故事在秦穆公时已经流传,穆公受到伯乐相马的启发,由马及人,不拘一格地在各地广求人才,“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李斯《谏逐客书》)当然,在历史上,得到“伯乐相马”故事的启发,而在“识才”“用才”上取得成功的帝王将相以及爱才用才的人还有很多……
一则“伯乐相马”的故事,影响了后代无数君王和求才的人“识才”“用才”的实践,也促进了中国古代人才学的发展与成熟。在当今,它仍孳乳着现当代人才学理论的成长。所以说“伯乐相马”是中国古代人才学的核心理念是有充分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