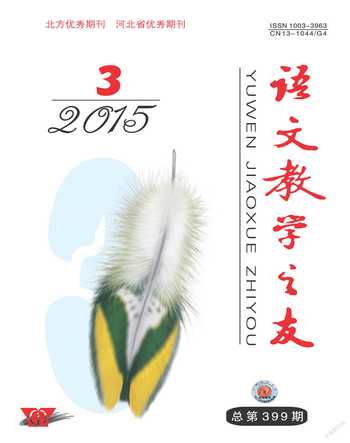关于“真语文”反思的再反思
贡如云
课程改革这14年,语文界围绕“真语文”的讨论此起彼伏,人们对语文的本体归属多了一分专业的自觉,对语文教学的泛人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对课堂教学的盲动形成了强力的反拨,对语文教学的合理形态做了广泛地探索。但是我们也发现,许多讨论陷入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怪圈,纠偏的同时,正将语文教学引入茧式化的误区,分科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正在抬头,改革正面临倒退的危险。这具体表现在七类“误读”上:
一、教学内容层面的误读
语文教学是个开放性的存在,教学内容的选择很容易跑偏。课改之前,许多语文课被上成了语法课、政治课、思想课,世纪末人文性大讨论之后,新课改拉开帷幕,实验教材陆续面世,文学教育峰回路转,语文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人文主义大转向,这对语文学科的发展来讲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但始料未及的是,稍后的人文取向的课标解读,实验教材人文组元的思想冲击,加上文本解读理论的推波助澜,不自觉地将语文引向了泛人文化的道路上。具体到教学实践层面,人们的话语重心渐渐偏向了内容、思想与情感这些“道”或“人文性”上,比如在教杨绛的《老王》一课时,许多教师过度纠缠于底层的光芒、悲悯的情怀、形象的感悟、情感的体验这类人文教育上,以致淡化了文本语言形式层面的教学内容。这之后,人们察觉到,此类过度的人文化解读,同样会把语文引向非语文的歧途。义务教育语文课标(修订版)正式面世后,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强调了“语言文字的理解与运用”,这一纠偏之举犹如一场及时雨。然而,我们在追求真语文教学之路上,倘使为摆脱伪语文的嫌疑,将语用(含文本语用与读者语用)的本质视为最高标准,彻底撇清与人文性的关系,那真语文又会被弄成狭隘的唯语文,最终也必将沦为伪语文,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担忧的。
二、教学特点层面的误读
语文教学特点很多,这里重点谈一下科学性的误读。在真语文的讨论过程中,我们偶尔会听到类似的批评:“语文课被上成了科学课”,“语文承受了难以承受之重”。语文课虽然不是科学课,但不是说语文课就没有科学性,比如思维的逻辑性、教学的规律性、内容的有序性,这些都是科学性的体现。语文素养虽然不包括科学素养,但科学素养与语文素养唇齿相依,而真语文这一概念本身就将语文跟真理、规律、科学拴在了一起。联系美国的做法来看,他们自小学就开始注重实验报告、调查报告等学术论文的写作训练,而SAT考试对学术性评论文的写作也极为重视;再看日本,受了西方实用主义的影响,科研论文的写作也是一大特色,他们的语文教材通常会提供科学研究报告作为范文,并鼓励学生进行类似的实用文写作训练。反观我国,由于历史传统、文化积习、民族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我们的语文教学长期疏于科学精神的培养,像科研报告这类学术论文的写作,多数孩子闻所未闻,而科技说明文,作为教材选文,其独特的文类价值尚未充分显现,作为评价材料,也仅成了检测学生思维能力的考试凭借。
三、教学方法层面的误读
语文教学方法很多,这里重点谈一下活动教学法的误读。目前,教学论界关于活动教学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是语文界对语文活动教学的历史发展、功能、地位、知识论基础、学习论基础、目标、内容、资源、实施与评价还缺乏深入的研究,搞活动往往会被扣上非语文的帽子。事实上,语文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它更适合在实际的言语活动中学习。明末清初教育家颜元师法胡瑗,反对“主静”之教育,强调“实学”“实行”,梁启超评价:“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1]联系欧美发达国家的母语教学来看,他们普遍注重活动情境的创设,让学生在活动、实践中提高语言运用能力,增强沟通交往能力。因为,“与成年人和同龄人交流是社会化的自然途径”,我们在提高学生读写能力方面,“应该利用孩子们语言习得的自然方式”。[2] 语文活动教学不是追求课堂表象的繁荣,它更为关注的是,学习主体本身的思维与情感应高度融入课堂。所以谈真语文的时候,需对活动的性质进行分类,对于那种贴标签式的伪活动、伪讨论,必须坚决抵制,对于符合语文学习规律的活动与讨论,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和运用。
四、教学手段层面的误读
真语文讨论的过程中,多媒体的名声每况愈下,公开课到底用不用多媒体?许多教师心里没谱。事实上,看一堂课是不是真语文课,关键不在其有没有用多媒体,仅仅是教学手段,如果合理使用,既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提高了教学效益,大可不必谈“媒”而色变。如果认为黑板语文才是真语文,白板语文乃是非语文,那语文岂不是成了墨守成规、固步自封的代名词了?联系美国语文教学来看,近年来,他们非常注重运用多媒体提高语文教学绩效,而这与我国多媒体所经历的先热后冷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的阅读,不仅指印刷媒介的阅读,它还包括观察与视听;所谓表达,也不仅指写作表达、口语表达,它还包括视觉表达,即借助视觉技术和手段来增强叙述、表达和沟通效果。而我国香港地区《中国语文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中,关于“学习材料”部分则明确规定:“教师要因应学生的学习需要,选取合适的多媒体及网络材料,设计适当的学习活动,以提高学习的效能。”
五、教学理念层面的误读
教学理念是人们对教学活动内在规律认识的集中体现,也是人们从事教学活动的态度和信念,明确表达自己的教学理念对教学活动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像本真语文、简单语文都代表了某种朴素的语文教学理念,类似的其他理念还有很多,诸如诗意语文、生命语文、快乐语文等,它们对语文教改的促进作用自不待言。但是,真语文并不等于教学理念,它是基于教学理念而又超越教学理念的,它既蕴涵着“何为语文”的本体论追问,又蕴涵着“语文何为”的方法论之思。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为了与课改初期的泛人文课与各类花式课划清界限,为了纠偏,将真语文降格为本真语文、简单语文等教学理念,那无疑是矫枉过正,将内蕴丰富的语文窄化与矮化。
六、教学风格层面的误读
讨论中,部分同志还误将本色、平实、简约等教学风格当成真语文。语文教学是丰富多彩的,风格多样的,就单一性教学风格来讲,它就包括理智型、情感型、庄雅型、谐趣型、严谨型等等;就综合性教学风格而言,它又有情理交融型、演导兼顾型、寓庄于谐型、雅俗共赏型等等。本色也好,简约也罢,它们都是单一性教学风格谱系中的一种。即如本色,它并不排斥其他风格,也不反对创新,更不放弃更高更好的追求,倘使我们对其进行过度诠释,将其功能无限放大,并与真语文等同起来,排斥异己,势必会影响到教学风格的多样化,进而扼杀语文教学的创造性。
七、课程结构层面的误读
首先,课程的分类有很多种标准,若按横向结构特征划分,可分为分科课程和综合课程。作为分科课程的产物,语文课程的独特性在于,它有其独当其任的目标,也有其他课程无法替代的职能。但是,课程的综合化、统整化是课程改革的必要组成部分,语文课程当然不可能“独守深闺莫倚栏,一缕相思寄吊兰”。因此,既独立又融合才是语文课程的应然状态,它体现的是一种自立而又开放的教育文化,而不仅仅是分化而又综合的学科形态。其次,学生是整体的人,其人格发展的整全性特点告诉我们,完全分治的课程既不利于学生人格健全的发展,也不利于学生认知图式的社会性建构。再者,课程是分立的,而生活却是综合的,情境也是具体的,世界更是关联的,忽视这种综合性、具体性与关联性,囿于语文一科去谈真语文,那显然是不完整和不科学的。联系香港地区21世纪的《中学中国语文课程指引》来看,他们已打破了分科的界限,中国语文科的课程内容可以与其他学习领域灵活配合,作跨学习领域的整合。再看欧洲,英国语文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中,他们特别强调“充分的综合实践活动”,而奥地利的语文课程理念中,也特别强调“语文能力的培养和跨学科学习。在语流和语境中学习语言”。所以,我们的语文课程,不应仅将综合性学习视为一种学习领域,它更是一种学习理念,这一理念应适度地渗透至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等领域中去。由于课程视野的狭窄,目前的许多讨论尽管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因为它们已经不自觉地陷入了分科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方法论误区。
总之,真语文不是单一的、静止的范畴。从课程本质上讲,语文性、语文味应该是个最低标准,即主色调必须是语文的,这个底线必须守住;而从教学特点上讲,真语文当然可以超越这个标准,适当吸收非语文的元素,还语文以合理的丰富性。真语文既要坚守语文性这一目标定位,也要兼顾语文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多维性、具体性与复杂性。许多教学理念与教学风格都是对真语文的独家阐释,真语文与教学理念及教学风格不宜等同视之。从课程结构上讲,语文课程既是单科性的存在,也是统整性的存在。东方的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因为语言在得道的同时,又会失道。西方的海德格尔则讲,语言既具有澄明性,又具有遮蔽性。道理相仿,我们过分澄明语文性、语文味的时候,或许会遮蔽语文性、语文味。
注释: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
[2] 布鲁斯·乔伊斯, 玛莎·威尔, 艾米莉·卡尔霍恩著《教学模式》第97页。兰英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南京晓庄学院教师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