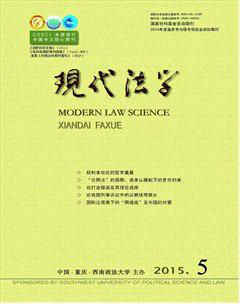论中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法律建构
摘要: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展开,投资领域的国家安全审查问题日益凸显,既面临着对外投资的法律挑战,又面临着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健全完善问题。从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在制度萌芽、建构和磨合的不同发展阶段,分别呈现出意识本能、理念混沌、结构缺失、目标无意识与标准错位等特点。以法学的视角省视与反思当前制度发展的路径,应在明晰目标定位的基础上确立“一体两翼”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在制度供给不足与过溢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夯实维护包括“居民、领土、主权、政府”在内的主体安全;两翼则一要聚焦于狭义国家经济安全的规制,二要聚焦于国防安全的规制。
关键词: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国防安全;国家经济安全
中图分类号:
DF415
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5.05.08
`
引言`
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概念自二战末期被提出以来,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解[1]64-65。综观之,国家安全是一种足以保持国家的统一和主权、领土完整,保障国民的生命、身体和财产不受侵犯,并基于合理的条件维护一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防止外来力量打击一国的制度和统治,并且控制其边界的能力或状态。基于自身国情、体制环境和所持理念,各国对外商投资采取的规制方式各不相同,然作为涉外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商投资都构成了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维度,形成了相适应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中国,一方面,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鸦片战争以来,是恢复并开展经济建设的急迫需求;另一方面,自鸦片战争以来,引入外资和技术裹挟着历史的风尘,各界就外商投资可能产生的主权和安全影响仍存隐忧,两相交织,扩展并限定着制度的安排。最终,在实用主义改革哲学、摸索型改革方针的牵引下,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形成了独特的机制,也遗存了相因相生的诸种问题。步入21世纪,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急剧变迁,各主要发达国开始强化国家安全审查的实施力度,既是出于应对全球恐怖主义蔓延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需要,又显露出阻拒新兴国家全球经济扩张的工具化诉求。特别是改革步入深水区、新阶段以来,自贸区“负面清单”的确立,国家安全审查的边界更面临重新划定的问题。回应错综复杂的形势,对外商投资国家安全机制的系统省视与反思,从而建构起理念清晰、内涵明确、结构谨严的制度体系已然刻不容缓。
`一、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之演进
`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外商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主要涉及企业设立审批、行业准入审批和外资并购审查等方面,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
(一)以企业设立审批为起点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1979-1994年
为了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1986年的《外资企业法》、1979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1988年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分别规定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举办外资企业或个人与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合营企业和合作经营企业,上述三部法律及其实施条例构成了中国“三资企业法”的主体内容。根据“三资企业法”的相关规定,申请设立外资、合营和合作企业,应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机关审查批准。
“三资企业法”明确提出了国家主权/安全的考量。第一,1983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规定了申请设立合营企业不予批准的情况,包括“有损中国主权”和“不符合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要求”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1983年)第5条。在2001年7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二次修订的最新版中,修订为第4条。。第二,1990年《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规定了4类禁止设立外资企业和5类限制设立外资企业的行业,并列明了申请设立外资企业不予批准的情形,包括“有损中国主权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和“危及中国国家安全”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1990年)第5条,2001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二次修订。。第三,1995年《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规定了申请设立合作企业不予批准的情形:“损害国家主权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危害国家安全”和“有违反……国家产业政策的其他情形”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1995年)第9条。。
在此阶段,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主要从外资企业的设立环节进行主体筛选,避免对国家安全的损害,国家安全首次在外商投资的法律文件中提出,构成了中国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发展的起点。
(二)以行业准入审批为主体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1995-2002年
为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使之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适应,中国陆续于1995年颁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以下简称《外商投资暂行规定》)、2002年颁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以下简称《外商投资规定》)。在目的的指引下,《外商投资暂行规定》
参见:《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1995 年)第5条(鼓励类)、第6条(限制类)、第7条(禁止类)。和《外商投资规定》
参见:《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2002年)第5条(鼓励类)、第6条(限制类)、第7条(禁止类)。将外商投资的项目分为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和允许类4种,并于1995年制定(后于2002年、2004年、2007年和2011年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下简称《外商投资目录》),就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的外商投资项目以分类具体目录的方式予以列明。根据现行审批权限,外商投资项目按照项目性质分别由发展计划部门和经贸部门审批、备案;外商投资企业的合同、章程由外经贸部门审批、备案。
在以行业准入审批为主体的制度安排下,准入范围的限定与国家安全审查发生关联。第一,限制类项目暗含了国家安全的内容。其中,先后规定了与国防安全相关的“稀有、贵重矿产资源勘探、开采”和“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勘探、开采”;结合加入WTO的要求,涉及产业安全的规定则从“需要国家统筹规划的产业”修改为“国家逐步开放的产业”。第二,禁止类项目中明确提出了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国防安全的规定。《外商投资规定》中的禁止类项目包括“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与军事安全相关的条款,也从《外商投资暂行规定》的混合型规定(“占用大量耕地,不利于保护、开发土地资源,或者危害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转换为单列规定(“危害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愈发突出了以军事设施为主体的军事—国防安全的保护作为独立目标的重要性。
在此阶段,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主要从外资进入相关产业的限制或禁止进行准入把控,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由产业安全理念所主导并得到细化和初步分类,其主体部分开始逐步发展、型构。
(三)以外资并购审查为重心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2003-2010年
为“促进和规范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就业、维护公平竞争和国家经济安全”,中国于2003年颁布《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以下简称《外资并购暂行规定》),2006年颁布、2009年修订《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以下简称《外资并购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应依法经审批机关批准,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或设立登记。伴随着外商投资方式的转变,外资并购审查成了该时期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重心。
维护公平竞争和国家经济安全成为外资并购审查所追求的主要目标。第一,《外资并购规定》明确了《外商投资目录》与并购审查的范围之间的关系:依照《外商投资目录》不允许外国投资者独资经营的产业,并购不得导致外国投资者持有企业的全部股权;需由中方控股或相对控股的产业,该产业的企业被并购后,仍应由中方在企业中占控股或相对控股地位;禁止外国投资者经营的产业,外国投资者不得并购从事该产业的企业此外,《国务院关于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规定:“大型重点骨干装备制造企业控股权向外资转让时应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选择一批对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建设有重要影响……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作为重点,加大政策支持和引导力度,实现关键领域的重大突破。”在《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和《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也申明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原则。。第二,集中审查的考量因素中提出“国家经济安全”。《外资并购暂行规定》规定“经请求的认定”中“可以要求外国投资者作出报告”的情形为:“外国投资者并购涉及市场份额巨大,或者存在其他严重影响市场竞争或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等重要因素的。”
参见:《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2003年)第19条。 《外资并购规定》则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进行了进一步阐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并取得实际控制权,涉及重点行业、存在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因素……当事人应就此向商务部进行申报。当事人未予申报,但其并购行为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商务部可以会同相关部门要求当事人……消除并购行为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
参见:《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2009年)第12条。
在此阶段,“国家安全”在《外资并购规定》中悄然化身为“国家经济安全”,直至2007年颁布的《反垄断法》中又回归“国家安全”的表述,在理念上应当经历了一个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不仅如此,在制度方面,依据《外商投资目录》投资是进入《外资并购规定》所设置审查程序的前置条件,国家安全的考量从单纯强调产业(供应)安全发展到同时兼顾市场(配置)安全,国家安全审查制度通过吸纳外资并购审查逐步发展和充实。
总体而言,对外开放的历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小平南巡,再到中国加入WTO至今,基本可以构成三个时间节点。基本与此相对应,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也在这三个时期演进迭代,其内涵和层次不断丰富和完善。
`二、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的理念混沌与标准错位
`
纵观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发展的三个阶段:在以企业设立审批为起点的制度萌芽时期,政策体现出国家安全的意识本能;在以行业准入核准为主体的制度建构时期,政策暴露出边界模糊、结构缺失与理念混沌;在以外资并购审查为重心的制度磨合时期,凸显出政策目标无意识、适用失焦与标准错位。盘点这些理念与制度遗产,是建构成熟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前提。
(一)制度萌芽中的意识本能
“三资企业法”在外商投资的企业设立阶段就对维护国家安全提出了要求,将国家主权/安全的考量纳入审批的范围,外商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开始萌芽。一旦萌芽,制度就按照自身的逻辑开始迅速生长:从最初合营企业设立的规定中立足于防止损害“中国主权”对可能产生的外商投资风险设置屏障;到为外资企业设立中分类规定禁止和限制进入的行业,在此基础上实施审查并对损害“中国主权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和“危及中国国家安全”的设立申请不予批准;进而在合作企业设立中明确规定了“违反国家产业政策”的设立申请都不予批准。
从法律文本的演进来看,改革开放初期合营企业设立规制所关注的是“国家主权”,到后来在外资企业和合作企业设立规制中才逐步提出“国家安全”。作为近代概念的“国家主权”源于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实际上安全威胁、安全战略、安全概念以及人们的安全观念在冷战结束以后经历了深刻的变革[2]。在此,“国家主权”更多地是一种政治上的宣示,其中更多隐含着闭关锁国所遗留下来的隐痛和新中国突破层层封锁过程中对主权捍卫的坚守,而在外国投资审查中的现代术语则应当是二战以来一直沿用的“国家安全”。法律文本中的此种变迁无疑是一种进步,然而,无论是从规制的切入点来看,还是从理念的演进来看,这一时期“中国主权”、“社会公共利益”和“中国国家安全”在“三资企业法”中只是一种国家意识的本能,其意识层次在政策上仅仅体现为主体合法的审批,谈不上概念的精确,遑论严谨的政策法律体系。在这一时期,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发展尚处于雏形。
(二)制度建构中的理念混沌
在《外商投资规定》的国家安全审查强化时期,相关制度深化了维护国家安全的要求,引入了行业的准入规制,细化了国家安全准入的行业划分及其限制/禁止,但与相邻概念之间的范围模糊。由于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规制尚未引入,在制度扩展的同时也存在结构缺失。更重要的是,制度的细化并未伴生认识的提升,国家安全审查在理念上处于混沌状态。
第一,由于国家安全与产业安全的混同,与公共利益之间边际模糊,与国防安全之间关系不明,该时期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处于混沌状态。一是国家安全与产业安全理念混同。一般认为,国家安全与产业安全存在一定交叉,但不应等同。产业安全主要指基于国内资本对本国产业的控制能力,产业具有在国际比较意义上的发展力和竞争力[3]。在《外商投资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规定》确立的限制类项目中,不论是“国家统筹规划”还是“国家逐步开放”的产业的提法,所暗含的都是保护幼稚工业和通过产业政策来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的理念。进一步地,国家安全作为内含于产业政策的一种考量体现在《外商投资目录》的限制和禁止进入行业的内容之中,而相关规定对于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的范围和边界尚未明确界定,二者一直存在不同程度的混同。二是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之间边际模糊。《外商投资目录》禁止类项目中“属于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牵涉到对二者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自乌尔比安提出以“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为基础构建“公法”和“私法”理论以来,唯物主义的爱尔维修、功利主义的边沁、新功利主义的耶林乃至社会法学派的庞德都作出了阐述[4]。然而,“公共利益”的提出及其概念体系的完善,多涉及公民财产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撞,落脚点则在于公民自由和国家权力的调和。可以认为,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交集,但是侧重点不同,前者重在防御外部力量的侵扰,后者重在调适权力与权利的平衡。
三是国家安全与国防安全之间关系不明。国防安全属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外商投资目录》禁止类项目中“危害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的规定,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是什么?国防安全是否仅仅及于“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第二,该时期的并购审查制度缺失。跨国直接投资一般分为直接投资开设企业的“绿地投资”和并购已有东道国企业的“棕地投资”两种方式改革开放之初,外国对华投资多采取“绿地投资”,即直接在华投资创建合资或独资企业。进入20世纪后,在华跨国并购急剧扩张,逐渐成为跨国巨头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外商投资目录》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将投资范围与比例进行了分类,通过鼓励、限制或禁止的方式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绿地投资”这一形式进行了较为细密的规定。以2011年修订的《外商投资目录》为例,限制外商投资的产业分为13类共79项,禁止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分为12类共36项。然而,在该时期,作为跨国并购这一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形式,则未能在法律政策中予以规定,不能不说是一种结构性的缺失。很明显,理念的混沌使得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只能停留在行业准入审批上,其内部尚需明确概念的界分,更无暇顾及外资并购审查制度的构建了。
(三)制度磨合中的标准错位
行业准入与并购规制共同作用下的外商投资相关制度,将维护国家安全的范围从单纯的行业准入拓展到包含对并购的审查,以期弥补前述制度结构缺失,在制度建构方面有了实质性的推进。然而,此时的国家安全审查受到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双重影响,自身的价值理念尚未完全成熟:由于国家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在理念上的叠加,以及并购审查虽已补足制度结构缺失,而实质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仍然缺位,该时期的国家安全审查表现出政策适用的“失焦”,而判断标准上的错位则是其主因。
第一,由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叠加及其标准的错位,致使国家安全审查政策实施“失焦”。国家经济安全在概念上历来存在争议,实质内容主要包括“国家的经济主权不受侵犯”和“导致经济危机的经济风险处于可控制的状态”两大因素[5]。此种界定已然让人难以捉摸。更要紧的是,在该时期,名义上的“国家经济安全”审查的主要考量,实践中则被常规的外资并购审查所遮蔽,而外资并购审查实际上又相当程度地竞争政策化了。
一方面,立法目标的多重指向与传统国家安全的基本目的相异。《外资并购规定》强调“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不得造成过度集中、排除或限制竞争,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即使将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视作叠加,《外资并购规定》立法目的项下的诸多诉求也无法与国家(经济)安全的目的相匹配。
另一方面,外资并购审查判断标准上的竞争政策化,对应于传统国家安全的考虑,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标准错位。《外资并购规定》明确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在满足一定市场份额或销售额的情况下应主动向执法机构报告;同时规定,“涉及市场份额巨大,或者存在其他严重影响市场竞争等重要因素的”,可由主管机构“要求外国投资者作出报告”。主管机构审查时主要考虑的因素则为:可能造成过度集中,妨害正当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易言之,在所谓的《外资并购规定》框架下的并购审查,起始于对外商投资中并购模式下国家(经济)安全的担忧,虽然审查也包含着国家安全的因素,然而其判断标准更多地错位聚焦于一系列妨害“竞争”和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竞争政策考量,与传统国家安全所应有的价值指向和判断标准相违,从而造成了政策适用的“失焦”。
第二,在经营者集中审查引入并提出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审查概念之后,正式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仍然缺位。外资并购审查制度仍然延伸发挥国家(经济)安全审查的功能,致使在正式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出台之前,审查的判断标准错位依然延续。经营者集中审查的主要目标为防止外资进入导致市场过度集中的外资并购审查,缺乏真正经清晰界定的国家(经济)安全,却一度成为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重心。进入内外资并购同一标准的经营者集中审查阶段之后(即《反垄断法》颁布之后),“经营者集中审查”和“国家安全审查”开始被有意识地加以区分。主要表现为:一方面,2007年《反垄断法》确定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立法目的;另一方面,根据《反垄断法》第31条的规定,“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除依照本法规定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外,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直至此时,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审查才通过立法目的的区分和专门规定在法律文件中被正式提出,预示着竞争政策下的经营者集中和国家安全政策下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进入了分类规制的轨道。
然而,之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家安全审查的基本制度却并未正式以法律规定的形式予以确立,只有外资并购审查一直在代行国家(经济)安全审查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难发现,经营者集中审查与外资并购审查呈现出另一种交错的格局,即外资并购审查在小幅修改后,在正式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缺位的情况下,有别于经营者集中审查的国家安全审查替代机制,而这种替代机制仍然是以“国家经济安全”的名义实施的。
综上,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演进迭代中,每一阶段都在遗留问题的解决上有所推进,但新阶段往往又凸显出新问题,在发展过程中既呈现出有意识的制度建构,又因认识局限造成理念混沌,进而引致标准错位。当前,解决在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共同作用下遗存的国家安全理念混沌和标准错位问题,是建构新时期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关键。
`三、建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一体两翼”
`
以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以下简称《外资并购安全审查通知》)为标志,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主体结构已经基本搭建成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通知》明确规定,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以下简称“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有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至此,外资政策、产业政策、竞争政策与国家安全政策多维互动的新时期开启了序幕。
在这一新时期的起点,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结构性缺陷已经得以基本弥补,而历史遗留的理念混沌和标准错位问题却仍悬而未决。有鉴于此,我们应当正视路径依赖的影响,首先必须明确国家安全与相邻概念的理念界分,确立新时期国家安全审查的内涵与定位;在此基础上,廓清新时期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体系架构,并厘定国家安全审查的判断标准,从这两个层面把握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明确国家安全与相邻概念的理念界分与确立新时期的定位
《外资并购安全审查通知》中关于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相关制度安排对“国家安全”予以重新确立,与《反垄断法》和《外商投资规定》中的规定相呼应,奠定了新时期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基础。然而,由于前期遗存下来的种种问题,要求我们首先要对国家安全的理念定位与相邻概念的界分予以厘清。
第一,“国家安全”与“国防安全”。有学者以领土安全或国防安全观念来理解、解释国家安全,把国防安全与国家安全直接等同起来。在此,需要明确“国防”完整的表述是“国家安全防御体系”现代国防是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颠覆、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进行的军事活动,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动。(参见: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学术[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7:7;秦子夫,等.一种国防安全性综合评估模型[J].信息工程大学学报, 2004(9):22-24.),而国防安全是国防系统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国防作为一种复杂的体系,能够保护国家的完整性、稳定性及其有效发挥职能和保持发展;能够可靠地保护自己和捍卫自己的利益,使其免受任何内部或外部破坏作用的损害[6]。笔者赞同如下观点:国防安全是确立国家安全的先决条件,构成国家安全的要害部分,但“国防安全”作为一种能力,仅仅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国家安全的全部[1]65。除此之外,应明确国防安全不仅及于军事设施,还应实现传统安全基础要素的全面覆盖,并顾及非传统安全
国防安全既包括领土防卫安全,又包括国家发展利益安全;既包括传统安全,又包括非传统安全;既包括执行战争行动取得安全,又包括执行非战争行动取得安全。(参见:李江磊.国防安全风险评估模型构建[J].国防科技,2010(2):41-46.)。
第二,“国家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有学者主张一种“综合安全观”,认为军事威胁已经不是和平时期关系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的主要因素,当今的国家安全主要是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科技安全等这种“综合安全观”在概念上存在两个倾向:第一个倾向是隐晦地用政府安全来取代国家安全;第二个倾向是把安全的概念泛化,使之成为生存、发展无所不包的东西。(参见:宋伟.国家安全:范畴与内涵——一种现实主义的视角[J].东南亚纵横,2009(3):86-88.)。也有学者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界定、阐述国家安全,认为广义上是指国家既要保障经济实力在国际上的相对优势,又要尽量稳定国际局势,抗御外部风险以保障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在狭义上是指当一国经济利益受到某些事件的威胁和影响时,国家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经济竞争力的能力[7]。笔者认为,用所谓的“综合安全观”替代完整的“国家安全”,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风险并存的今天,必然是不可取的;在广义上理解国家经济安全将会极大地增加政策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合理的方案应该是在恰当界定的前提下,将狭义的国家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目标体系,使其构成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三,作为政治术语和法律术语的“国家安全”。有学者从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和国家安全工作的角度来解释国家安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同步交流的困难。就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而言,将国家安全的概念收敛至法律术语的范围,无疑有利于澄清并确立其内涵和边界,从而推动制度的建构和实施。对此,有学者指出,当国家安全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术语或者法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时,通常是指国家作为政治权力的主体或者国际公法主体的安全,包括
居民、领土、主权和政府,加上国家生存和发展所必然存在的“国家利益”[1]66。还有学者以“国家安全”概念的法学定义进一步扩展吸纳国家尊严的内涵[8]。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背景下,作为法律术语的“国家安全”的边界仍需确定。
概言之,笔者认为,在理念界分的基础上,要准确定位国家安全审查制度,首先要将国家安全还原为一个法律术语。作为法律术语的“国家安全”应当在“居民、领土、主权、政府”四要素的基础上予以构建,重点应落脚于体系化的国防安全和狭义的国家经济安全,从而构成“国家安全”的一体两翼(图1)。在此基础上,前述“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等内涵,因其本身所存在的泛化倾向,不应独立构成国家安全的主体要素,而应当被吸纳为国家安全之两翼的国防安全和狭义的国家经济安全,以保障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明确理念界分的基础上,应当在“国家安全”理念下通过刚柔相济的适用标准来统合现有的“三资企业法”、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和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政策法律体系。
图1:国家安全的一体两翼
(二)“一体两翼”架构下新时期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适用标准
当前,根据“三资企业法”、《外商投资规定》、《反垄断法》和《外资并购安全审查通知》的规定,从投资行业准入、企业设立、外资并购审查,到反垄断审查,再到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全流程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体系架构已基本成型。从程序上看,由于外商投资的方式不同,新设企业投资的部分经由“三资企业法”规制,并购投资部分则进入外资并购审查的范围。一方面,进入“三资企业法”规制流程的“绿地投资”,将指引到《外商投资目录》,从限制类和禁止类行业的分类对危害国家安全的可能情形进行设限和排查,从而控制入口。另一方面,进入外资并购审查规制流程的“棕地投资”,将同时指引到《外商投资目录》和《外资并购安全审查通知》,前者主要关注外资并购的禁止和限制产业,构成第一道门槛;后者则将即使满足投资产业范围和要求但涉及国家安全的并购,经由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国家安全审查,构成兜底保护。此时,竞争政策退居后台,通过对内外资的一体化适用,基于经营者集中审查、垄断协议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来解决竞争性市场中的排除、限制竞争问题。《反垄断法》所发挥的功能,将依法被限定于对纯竞争议题的考察,通过竞争促进繁荣,也间接构成对国家安全在“狭义的国家经济安全”一翼的有力支撑。
基于此种架构,对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适用标准中的关键点进行控制,则是“一体两翼”架构下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
1.绿地投资
针对“绿地投资”一侧,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应聚焦于外资行业准入审批的制度完善,应当将国家安全中狭义的国家经济安全确立为适用标准的关键点。
第一,应当避免外商投资产业政策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范围划定过宽。就此,国家在《外商投资规定》中划定了十余类行业予以限制或禁止。笔者认为,在此种范围的划定中,既要维护国家安全,又应当避免将国家安全泛化,覆盖国家经济发展中应由常规行业监管和市场竞争所解决的问题;应当逐步淡化保护幼稚工业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容,根据国家经济安全的经济安全(宏观)、产业安全(中观)和技术安全(微观)三个维度的划分,将其范围收敛至产业安全和技术安全的范畴[9]。
第二,应当克服外商投资产业政策中国家安全的规制不足。外商投资的准入在产业政策下实施已有经年,《外商投资目录》的编制与实施不仅仅与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密切相关,也长期被“市场换技术”的思维所支配。在该思维下,其所引发的过于交出了市场而未换得技术的问题已经广受诟病。笔者认为,未换得技术已属棋差一着,如果将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产业拱手让人则更是后患无穷。这在当前鼓励类行业大面积铺开的情况下,已经成为一个潜藏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外商投资目录》的修订过程中,强化基于“国家安全”标准的筛选机制,通过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引入,对鼓励类目录的编制予以重新评估。
2棕地投资
针对“棕地投资”一侧,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应聚焦于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制度完善,应当将国家安全中的国防安全确立为适用标准的关键点。
第一,应当克服外资并购安全审查中国防安全的规制不足。涉及到国防安全,相关政策所指向的措施都是直接禁止。《外资并购安全审查通知》将禁止的范围划定为:“境内军工及军工配套企业,重点、敏感军事设施周边企业,以及关系国防安全的其他单位。”进一步地,其规定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考虑因素包括:并购交易对国防安全,包括对国防需要的国内产品生产能力、国内服务提供能力和有关设备设施的影响;并购交易对涉及国家安全关键技术研发能力的影响。就此,基于“居民、领土、主权、政府”主体安全四要素的考虑,外资并购安全审查中的国防安全还应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范围需要扩展。由于要涵括“陆地、海洋、天空、太空、电磁等领域”的广谱范围,聚焦外资并购关键设施的国家安全审查,应当确立一个辐射军民两用、包纳生产/服务的保护机制,除了能源、资源、港口、机场等物理设施,还要吸收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服务产业、电信、化工/危险材料行业等公共安全的内容“9·11”之后,美国将“重要基础设施”的收购纳入CFIUS审查范围,包括农业及食品、水、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服务产业、国防、电信、能源、交通运输、银行及金融、化工/危险材料行业、邮政及航运、信息技术等。2009 年《加拿大投资法》修正案通过后,增加了国家安全审查的内容,“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的双层结构开始形成。(参见:江山.加拿大“投资—国家安全”审查中的关键资源——基于《加拿大投资法》的分析[J].国际经济合作,2013 (1):77-81.)。二是内容需要体系化。在当前以科技实力为引领的军事和国防建设大背景下,应当对涉及国防安全的“关键技术”关键技术(又称临界技术)的范围小于重点技术,大于核心技术。一般认为,关键技术应用领域广泛,对实现战略任务或计划目标具有决定性作用,可以促进或带动多项技术或整个技术群体的进步与发展, 并在近期内可以实用化或部分实用化。(参见:江山.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中的关键技术——基于美国 CFIUS 审查的分析[J].国际经济合作,2012(6):40-43.)予以界定,并结合已有相关规定将关键技术设计的门类适当扩充和细化,将《外资并购安全审查通知》中的原则性规定与中国出口管制法律法规相匹配、相关联、相指引,在关键技术领域、核领域、生物领域、化学领域、导弹领域、军品领域实现出口管制和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无缝链接,防止相关技术以进出口管制之外的方式实现不当转移。三是基于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核扩散、武器扩散的考虑,强化非传统安全的防卫意识和机制建设引发国防安全风险既可以是敌国战争行动导致的侵略,也可以是低强度军事冲突,还可以是针对本国的恐怖袭击、暴乱、分裂行为、情报侦察、海盗、敌方对海外资产的侵占等非军事冲突。(参见:李江磊.国防安全风险评估模型构建[J].国防科技,2010(2):41-46.),不仅要对大数据架构下的数据库等网络安全的基础设施和技术给予高度关注,还应当将收购方企业的来源和企业性质纳入审查范围。
第二,应当避免外资并购安全审查中国家安全的范围划定过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通知》所划定的范围为“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农产品、重要能源和资源、重要基础设施、重要运输服务、关键技术、重大装备制造等企业”,审查的考虑因素则包括并购交易对国家经济稳定运行的影响、对社会基本生活秩序的影响。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中明确规定了对“国防安全”和包括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资源安全和技术安全等在内的“经济安全”的范围,反映了中国在政治经济崛起进程中所面临的多方面安全压力和忧患,具有其合理性。然而,在全面理解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目标和体系的前提下,应当使涉及狭义的国家经济安全的内容在外资行业准入审批环节的产业政策来解决,或者通过竞争政策的经营者集中审查等环节予以调整;在外资并购安全审查中,这种国家安全泛化倾向的表述应当通过相关的法律术语予以收敛,聚焦国防安全、辐射公共安全。如果试图把军事安全以外的任何内涵加入到国家安全的概念中,就必须证明它与国家生存利益存在直接的关系[10]。有鉴于此,“经济稳定运行”和“社会基本生活秩序”这两个因素都是高度抽象的情境,容易导致
国家安全泛化,陷入广义的“国家经济安全”之窠臼,应酌情作出修订。
由上可知,在“一体两翼”的法律体系建构中,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将被视为一个全流程的有机整体来对待,基于这种整体的政策视角和制度安排,充分把握两个侧翼的制度重心,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同时有效抑制制度供给的过溢,以有利于迈向更为均衡的政策实施:一方面,可以在将有限资源聚焦于核心关切的同时,避免由于护卫国家安全过于操切而过度介入市场,或以国家安全之名行特殊利益保护之实,在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中注入太多的非法律考虑因素,增强外商投资的规范性和可预期性;另一方面,可以在吸收产业安全和技术安全关键领域专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升国家安全标准在《外商投资目录》修订中的权重,从准入的源头实施调控,有效实现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灵活性和回应性。
`结语
`
史家有言,一个世纪的头10年往往是上个世纪的延续。穿越漫长的20世纪,21世纪的头一个10年酝酿着危机和希望。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国家安全这一议题呈现新特点、新趋势,国家层面也提出“总体安全观”的理念,强调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11]。毋庸置疑,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是“总体安全观”下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形势不断复杂深化的今天,如何保有理性的头脑,有意识、有条理、有侧重地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中驾驭维护国家安全和保持投资开放二者间的平衡,需要目的清晰、范围明确和程序透明的制度体系构建,更需要政策制定者超出部门利益、短线思维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深远战略视野。ML
参考文献:
[1]吴庆荣.法律上国家安全概念探析[J].中国法学,2006(4).
[2]刘胜湘.国家安全观的终结——新安全观质疑[J].欧洲研究,2004(1):1-15.
[3]许芳,刘殿国.产业安全的生态预警机制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8-21.
[4]胡鸿高.论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J].中国法学,2008(4):56-67.
[5]高昊,张一弓.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经济发展比较探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0(2):8-12.
[6]秦子夫, 尤春亭, 戴锋. 一种国防安全性综合评估模型[J].信息工程大学学报,2004(9):22-24.
[7]赵惟.国家经济安全与产业安全研究综述[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5(3):25-27.
[8]梁忠前.“国家安全”概念法理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1995(4):77-82.
[9]曾繁华,曹诗雄.国家经济安全的维度、实质及对策研究[J].财贸经济,2007(11):118-122.
[10]宋伟.国家安全:范畴与内涵——一种现实主义的视角[J].东南亚纵横,2009(3):86-88.
[11]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EB/OL].(2014-04-15)[2014-05-30] 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4/15/c_1110253910.htm.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NSR) in investment area becomes an urgent issue, facing NSR legal challenge of investment abroad, as well as the perfection of NSR legal institution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From germinal, construction, to grindingi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Mechanism for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instinctive response, ideological chaos, structure shortcoming, objectively unconsciousness and standard dislocation. Based on a legal reflection on current approach of NSR Mechanism for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we propose a “one trunk with two wings” system for 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 for future development. Based on a clarified objective, the new framework aims to achieve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insufficient and overflow of institutional provision, under which we should consolidate the policy trunk consisting of “resident, territory, sovereign and government”, focusing on the regulation of two wings, namely,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and defense security.
Key Words: foreign investment; national security; defense security;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本文责任编辑:邵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