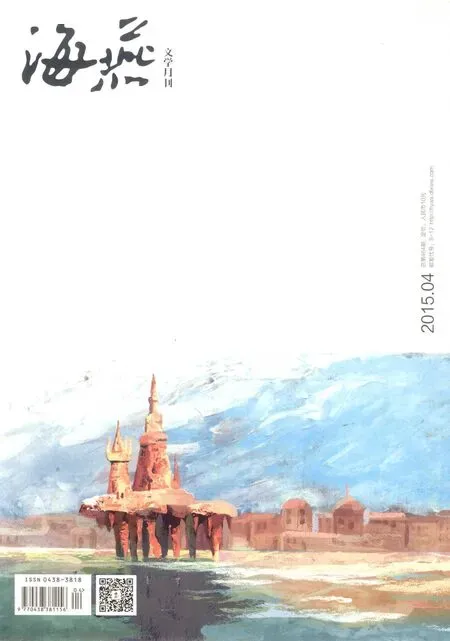从心灵出发再皈依心灵
——李少君与熊焱诗歌解读
□李犁
从心灵出发再皈依心灵
——李少君与熊焱诗歌解读
□李犁
李少君的诗歌有一种制纯的作用,读着读着,内心的杂草还有血液里的杂质就被清除,人真的成了在天空上休息的白云,或者是白云下面随风呈形的青草,不但干净而宁静,还有完全放下后的自然和自由。这让我想起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倡的“自然英旨”,这是强调诗歌要自然而然,也就是说诗歌要有人的自然情感和自然本性。而人只有在大自然面前,或者说只有身心全部地融入了大自然,才能彻底地打开和真正地恢复自然属性。所以在李少君看来自然就是神,就是诗。正如少君在《敬亭山记》中写的:“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抵不上/一阵春风,它催发花香,/催促鸟啼,它使万物开怀,/让爱情发光”。这就是自然之力,自然之神圣。所以面对大自然,诗人无需雕琢和粉饰,只要真实地表现了大自然,就是“英旨”之诗。从现实角度来讲,当下的生活是窒息的,是对人性的篡改和变异,而只有到了大自然中人才能通畅并复原。譬如这首《西湖边》:“为什么走了很久都没有风/一走到湖边就有了风?/杨柳依依,红男绿女/都坐在树下的长椅上/白堤在湖心波影里荡漾//我和她的争吵/也一下子被风吹散了”。这里大自然不仅能镇定安神,舒通心脉,还有化解情感之瘀,和谐家庭之功效。这说明大自然是一切生命之源,走进大自然就是回家,就是社会人向自然人还原,更是向自己还原,还原本真的自己。
作为诗歌理论家的李少君能把自然作为书写主题,绝非是随即随想,而是他漫长思考中形成的诗之思,是他哲学思想的外化和形象化。这思之内核,让他的诗歌柔软中有了硬度,抒情里藏有刀锋。而且每一首的最后两句都成为一种跃升,是对前面叙述的归纳和总结,我们可以看作诗眼和思想的剑尖,是意境更是觉悟,是诗美更是境界。譬如我最喜欢的这首《致——》:“世事如有意/江山如有情/谁也不如我这样一往情深//一切终将远去,包括美,包括爱/最后都会消失无踪,但我的手/仍在不停地挥动……”读这首诗,眼前一直晃动着一只手,而且挥之不去。这最后一句就是整个诗歌的峰巅,是诗歌的心脏和发光点。它凝结着诗人对美和爱以及一切事物的态度。这是一种精神,人类因有了这样的热爱和锲而不舍的精神而超越了生命的短暂和有限。此诗也因有了这样的思想而成为既有深情又有深度的大诗,从而有了高度并进入了一种永恒。这是诗的魅力。更是思的爆破力。
其实我们追求诗歌,就是让我们从缭乱的尘俗中超拔出来,向童年归依,向大自然归依,回到人性的源头,回到自然的源头。这也是少君内心的理想和人文关怀,它自觉与自在地自动呈现,说明无功利的追求让情感更加真实和自由,让诗歌更清澈与澄明,甚而多了一层圣洁的光芒。这光明是黎明的自然色,更是人内心中天然的色彩。所以大自然就是诗人的宗教,是诗人的理想所在。而诗人需要做的就是努力擦净心灵的镜子,让它清晰地映射出自然的真意,以及深藏在灵魂中的“小径与藤蔓”、“寂静与肃穆”,从而让自己摆脱沉重的肉身,进入到自由绝对永恒的诗意之中。这就是自然之诗,永恒之诗。
与李少君诗歌的美、抒情和境界相比,熊焱更强调诗歌的现实性和批判精神,这对80后出生的诗人来说非常珍贵,即使在整个诗坛像熊焱这样直接表达自己对不和谐现实的愤怒,让诗歌像烈火一样呼啸着推进的作品也非常的稀少。正是因为情感的鼓胀甚至溢出,熊焱的诗歌突出了性情,而忽略了文字和修辞。这让我想到古人说的“直寻”,就是直接抒写诗人的“即目”“所见”。这样开门见山的诗歌都是因为情感的激烈燃烧,省却或者来不及修饰和妆容,而直抒胸臆。明代的袁宏道曾说好诗应当“情真而语直”即是此意。譬如熊焱的《在人间》开头即情感奔泻如洪:“这珠光的宝气、衣衫的褴褛/这来往的人群密密如雨滴/无论高低贵贱,他们肚皮后的心 /大多都埋下了地雷,装上了利刃”。诗歌直接揭开现实的皮肤,让我们看到了残酷的真相,更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灼痛。而且诗歌的流速很快,这是诗人胸中之气在奔涌。读者随着他贲张的情感起伏颠簸,而忘记了语言和文字。这样的诗歌打动我们的是它的“真”,还有真的后面诗人的关怀和赤子之心。诗人有了这种正义感和同情心,诗歌就有了火焰和热量,变得侠肝义胆起来。
前不久我针对诗歌现状写了一篇《缺火的诗坛》,其中就说现在的诗坛缺少烈火,呼吁诗人要有良知,要用刀剑将现实刨开,让我们清醒和警醒。这烈火就是激情就是责任,更是诗歌的肝胆。所谓侠肝义胆,我更喜欢“义”的部分,义代表着挺身而出,奉献和牺牲。这种精神浇灌在诗歌里,就是钙和钢,这就是对软绵绵油腻腻的诗坛一种补充和修正。所以我珍惜熊焱诗歌中的道义和担当,我视这些为恢复和回归了诗歌的伦理。而下面几句的自省和反省又让诗歌升温:“人世浮华,我苟活了多少光阴/死亡是我最后的刑具/我来到人间,就是为了学会向生命鞠躬致歉”。品格中有了谦逊和感恩就是风雪中有了炭火。诗歌不仅需要一针见血的直接和尖锐,还需要像棉衣披身一样的温暖和关怀。熊焱的“向生命鞠躬致歉”,就是一种胸襟和大爱,我把这样的诗歌和品格称之为“炉火”。炉火就是传递温暖的诗歌。因为诗歌不仅要有痛,还要有爱甚至美。譬如熊焱在《流水的一天》中记录的经历,都是炉火在燃烧:“我在街口邂逅了两个乞丐/一个躺着,一个跪着/仿佛受伤的小兽正等待善良的拯救/虽然我知道,我们的善心/曾一次次地遭遇践踏。虽然我也知道/我的年收入,还不如一些乞丐的两根指头/但我还是丢下了二十元,……”读这样的诗歌,会浑身发热,内心亮堂。这就是正能量,这在冷酷又冷漠泛滥的诗坛显得弥足珍贵。每个写诗之人应全当珍惜,并对美好和万物永葆敬爱敬畏之心。所以炉火的诗歌是境界,也是情怀。是情怀的潜动力让炉火自然地发热,并催生着诗歌自动地绽开。
所以,我视熊焱为有情怀的诗人,他也有理由也配做这样的诗人。在他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他常常越过自己去关怀别人的苦难和不幸,把泪水和同情献给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小人物和卑微者,这就是常说的悲悯情怀,是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和外化,更是诗歌中的黄金和宝石。
本期两位都是有情怀的诗人,只是与体恤现实的熊焱相比,李少君更多关注的是自然与生命的关联,属形而上。但他们诗歌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从心灵出发再皈依心灵。
责任编辑 李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