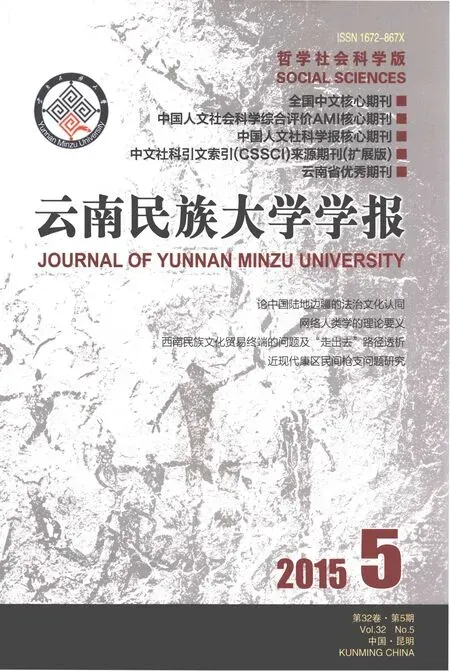“包容”与“局限”——论雍正帝民族观念的双重性
张 姗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100081)
论及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念,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华夷有别”“华夷之辨”。既不同于以往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也不同于此前的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由满族建立的清王朝为了消除汉族的排满思想,确立满族统治的合法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其统治版图内的一统管理,逐渐形成并在理论上提出了“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民族观。这个理论的明确提出者就是本文的研究对象雍正帝,而最能体现其民族观念的则为他于雍正七年 (1729年)所颁行的《大义觉迷录》。目前,海内外的历史学界已有不少从《大义觉迷录》入手研究雍正帝民族观念的研究成果,①中国学界的代表性论文有:《论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及其民族思想》(何晓芳,《满族研究》1986年02期)、《一次关于政权问题的大辩论—— 〈雍正大义觉迷录〉书后》(钱伯城,《书屋》1998年04期)、《也谈满族汉化》(郭成康,《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试论雍正帝的民族思想—— 〈大义觉迷录〉新解读》(吴洪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4年06期)、《从〈大义觉迷录〉看雍正的民族思想》(周玲,《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01期)、《帝王眼中的华夷之分与君臣之伦——从〈大义觉迷录〉看雍正的政治思想》(栾洋、姜胜南,《燕山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01期)、《析清代“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以〈大义觉迷录〉为视角》(库晓慧,《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02期)、《华夷之别思想的辩驳与消弭——以清雍正年间思想整合运动为中心》(林开强,《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03期)、《论清雍正帝的民族“大一统”观——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的考察》(衣长春,《河北学刊》2012年01期)等。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有:「雍正帝と大義覺迷錄」(小野川秀美、『東洋史研究』十六巻四号、一九五八年)、「忠義は民族を超越する」(宫崎市定、『雍正帝—中国の独裁君主』、中央公論社、一九九六年)、「清帝国の統合における反華夷思想と文化政策」(平野聡『清帝国とチベット問題—多民族統合の成立と瓦解』第二章、名古屋大学出版会、二〇〇四年)等。纵观这些研究特别是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对于雍正帝的民族思想基本上都是极为肯定。笔者虽然同样认可雍正帝较前朝统治者的进步,但通过对《大义觉迷录》以及当时实录、奏折朱批等资料的查阅发现:雍正帝貌似“平等”“包容”的民族观念其实是具有一定前提性与局限性的。因此,通过对上述文献档案等史料的利用,本文将着重阐述雍正帝民族观念所具有的双重性,并从用人标准与改土归流两方面着重分析这种双重性在其民族对策上的体现。
一、《大义觉迷录》的产生
雍正六年 (1728年),受吕留良“华夷之别”民族思想影响的曾静让弟子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策动其起兵反清。曾静在致岳钟琪的书中,叙述了当时广泛散播的有关雍正帝夺位、谋父、逼母、弑兄、屠弟、镇压功臣等“流言”,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并在此理论基础上反对清朝的统治。岳钟琪把此事以及曾静所写之书上报给雍正帝,曾静等人被押解至京由雍正帝亲自审问。雍正帝不仅就曾静著述中以“华夷之辨”为代表的反清观点与其进行辩论,还带头在朝野及全国发动了一场有关“华夷之辩”“君臣之义”等总称为“大义”的思想讨论,最终曾静认罪并作《归仁说》。为正天下人之心并宣扬自己的思想,雍正帝将这些辩论的内容连同上谕、《归仁说》等刊印成书,命名为《大义觉迷录》。《大义觉迷录》刊印之后,雍正帝下令“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官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①(清)世宗:《大义觉迷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5页。尽管在雍正帝去世不久,刚即位的乾隆帝就将此书定为禁书并将已经出版的书本全部销毁,而被雍正帝特赦不死的曾静、张熙也被处以凌迟,但是由于此前雍正帝要求全国上下乃至穷乡僻壤都要学习此书,因此书中宣扬的民族思想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而此书也成为后来学者研究雍正帝民族观念的第一手资料。
二、雍正帝民族观念的“包容”与“局限”
(一)“华夷一家”
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首先以“满清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是否符合正统之道?岂可再以华夷中外而分论?”为题,利用儒家经典反驳了此前的“华夷之别”,从“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的角度阐述了清朝政权的正统性及“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
1.以“德”论正统。
“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②(清)世宗:《大义觉迷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页。雍正帝先提出“德”是“为天下君”的条件,不能以其民族或者地域来论。“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③(清)世宗:《大义觉迷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4~5页。同时,他引用《书》中经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及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为自己论证。清朝建立是否符合“德”呢?“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④(清)世宗:《大义觉迷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6~7页。因此,雍正帝试图通过对比明朝末年的民不聊生与清朝建立后的太平盛世,进而说明清朝建立是有“德”的,是符合正统的。至于华夷之说,他则认为是“不务修德行仁”的产物—— “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⑤(清)世宗:《大义觉迷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5页。
2.阐述“夷”的含义及出现原因。
对于“夷”这一称呼,雍正帝并没有忌讳,他认为这只能代表地域,并不能说明其他。“且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孟子云: ‘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本其所生而言,犹今人之籍贯耳。”⑥(清)世宗:《大义觉迷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85页。“然则‘夷’之字样,不过方域之名,自古圣贤不以为讳也……夫满汉名色,犹直隶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甚至他还亲自批评当时有人避讳用“夷”等字眼: “朕览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声。如以夷为彜,以虏为卤之类,殊不可解。揣其意,盖为本朝忌讳,避之以明其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义,不敬之甚者也。”⑦《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96页。对于曾静以衣冠来论华夷的观点,他反驳到穿衣只是因时因地不同而已,与品德、政治能力没有任何关系,“盖衣冠之制度,自古随地异宜,随时异制,不能强而同之,亦各就其服习便安者用之耳。其于人之贤否,政治之得失,毫无关涉也。”⑧(清)世宗:《大义觉迷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11页。针对吕留良等人把夷狄比作禽兽,承认自己是外夷的雍正帝更是直接驳斥,认为若依其论调,中国之人是禽兽不如,“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据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①(清)世宗:《大义觉迷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8~9页。
虽然雍正帝声明“夷”只应该代表籍贯,并承认满族是外夷,但他也清楚华夏族对“夷”充满歧视,只是他把这种歧视的出现归结为以往朝代的“无能一统”,“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既然在以往历史上,华夷的疆域界限是随着朝代统治范围的变化而变化的,那么在开疆扩土,实现天下一统的清朝,自然已经不存在华夷之别、中外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②(清)世宗:《大义觉迷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9~10页。“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③(清)世宗:《大义觉迷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3页。
由上可见,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既承认满族是夷,但又认为“夷”只代表地域,批判历来“华夷之辩”对于“夷”的文化歧视。比起民族与地域,他强调“德”才是衡量君主统治的唯一标准,同时指出“华夷之说”是六朝乱世“不务修德行仁”的产物,而“华夷之别”也是前朝历代不能实现“大一统”之结果。因此,依雍正帝之言,在实现了“大一统”的清朝已经无需再分华夷,满清政权救百姓于水火是有德之为,曾静等人利用“华夷之辨”图谋叛乱才是失德背义之举。虽然《大义觉迷录》是雍正帝为了打击汉人反满思想,稳固清朝及自己的政权而作,但是从中体现出来的“摒弃华夷之辨,合中外为一家”的民族观念较前朝相比,是具有进步性与包容性的。特别是在《大义觉迷录》颁行之前,雍正帝就曾主张不必强求各方相同,应该尊重各自风俗习惯,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依旧可取。“盖天下之人,有不必强同者。五方风气不齐,习尚因之有异,如满洲长于骑射,汉人长于文章,西北之人果决有余,东南之人颖慧较胜,非惟不必强同,实可以相济为理者也。至若言语嗜好,服食起居,从俗从宜,各得其适。”④《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七十四雍正六年十月癸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01页。
(二)“华夷一家”的前提及局限
以往的研究虽然也总提及“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但多把“天下一统”当作“华夷一家”的原因,殊不知前者还是后者的前提。若没进入清朝的“一统”范围,雍正帝是不会将其视为“一家之人”,这一点在雍正帝宠臣鄂尔泰治理西南少数民族特别是开辟贵州苗疆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查阅当时两人的奏折朱批往来,不难发现:如少数民族服从清廷统治,则为“良民”,给予安抚;若有所反抗,则为“逆贼”,势必剿除。同时,即便在“一统”范围之内,雍正帝“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并非是提倡各民族完全平等。通读《大义觉迷录》可以得知:一方面雍正帝强调清朝已经实现大一统,不分华夷;但是另一方面他在说明满蒙已通文明、懂礼乐时又不自觉地又贬低了其他少数民族。比如他在驳斥曾静的“夷狄异类,詈如禽兽”时说:“若僻处深山旷野之夷狄番苗,不识纲维,不知礼法,蠢然漠然,或可加之以禽兽无异之名。至于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而喀等,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不兴,命案罕见,无奸伪盗诈之习,有熙宁静之风,此安得以禽兽目之乎?”⑤(清)世宗:《大义觉迷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81页。即雍正帝既反对给单纯代表籍贯的“夷”贴文化标签,但同时又把文化标签贴给那些深山旷野的“夷狄番苗”。暂且不提这些少数民族,即便对于汉族,若浏览当时的其他史料,也可以发现提倡“天下一家”的雍正帝也会时常流露出自己的民族优越感。“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节之行,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①《清世宗圣训》雍正二年七月甲子,赵之恒主编:《大清十朝圣训》,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892页。因此,雍正帝“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是带有前提性与局限性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我矛盾性。
三、“包容”与“局限”于民族对策之体现
论一个人的民族观念,不仅要从其言论入手,更应该从其实际行动进行考察。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所提倡宣扬的“天下一统、华夷一家”观念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其在执政过程中遇到民族相关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态度与采取的策略。鉴于本文主题与篇幅限制,本文无意对雍正时期的民族对策一概而论,仅挑选雍正帝用人标准与改土归流两个方面,分析雍正帝具有双重性的民族观念在其民族对策上的体现。
(一)雍正帝用人标准:政治取向重于民族出身
雍正帝颁行《大义觉迷录》之前,曾特意把曾静的言论发给远在西南的宠臣鄂尔泰。这一细节,在雍正七年 (1729年)四月十五日的鄂尔泰奏折②雍正七年四月十五日鄂尔泰奏折——钦奏圣谕事,《朱批鄂太保奏折》第3册,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274~280页,本段引用均出自此折,故不再重复做注,特此说明。中有所记载,“此因逆犯曾静之谕,朕欲遍示天下,录来与卿看”。颇让笔者出乎意料的是:鄂尔泰在表示一番愤慨之后,首先将矛头对准了满族臣僚特别是曾经与雍正帝争储的允禩和允禟,“即满洲臣僚内,无知无耻,无殊异类者,固不乏人……乃逆贼曾静捏造浮词,恣意狂悖,暗布匪党,耸动大臣,其所以能如此得如此者,臣以为其事有渐,其来有因。如诽谤圣躬诸事,若非由内而外,由满而汉,谁能以影响全无之言,据为可信。此阿其那、塞思黑③“阿其那、塞思黑”为满语发音,具体含义学界有所争论,可详见王钟翰《三释阿其那与塞思黑》(《历史档案》1998年04期)一文。在此处,鄂尔泰所指的就是曾与雍正帝争储的康熙帝第八子允禩和第九子允禟二人。等之本意,为逆贼曾静之本说也。如诋毁天朝等语言,则江湖恶类,山野诳愚,不识天日者皆能造伪说,而不至若此之甚,此怀疑二蓄怨望诸汉人等之隐意,为逆贼曾静之借口也。”继而,鄂尔泰表达了对满族人恨铁不成钢之意:“今国家一统垂八十余年,圣圣相承,教养备至,而汉人之心思终不能一。视满洲之人物,犹未能争光,每一念及,臣窃有余恨!”在此处,雍正帝也朱批:“叹息流涕耳”。由此可见:虽然作为满族,雍正帝与鄂尔泰都希望能有更多的本族人才,但比起民族出身,政治取向更为重要。即便满族臣僚甚至是雍正帝的亲兄弟,若有“不忠”之心,也与“异类”无别。
在实录中还可以看到雍正帝对于某些官员在意民族之事做了特别说明,以表明自己用人不拘民族出身,“用人惟当辨其可否,不当论其为满为汉也……盖汉人中、固有不可用之人,而可用者亦多。如三藩变乱之际,汉人中能奋勇效力,以及捐躯殉节者,正不乏人。岂可谓汉人不当用乎?满洲中,固有可用之人,而不可用者亦多。如贪赃坏法,罔上营私之辈,岂可因其为满洲而用之乎?且满洲人数本少,今只将中外紧要之缺补用,已足办理……朕临御以来,以四海为一家,万物为一体,于用人之际,必期有裨于国计民生,故凡秉公持正,实心办事者。”④《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七十四雍正六年十月癸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00~1101页。从雍正朝总督的民族成分统计来看:“39位总督中,满人10人,汉军旗人13人,汉人16人”⑤王丹丹,《雍正朝总督群体研究》,2009年黑龙江大学硕士毕业论文,第21页。,民族出身在雍正帝的选人条件中并非十分重要。
(二)“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与改土归流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虽在明代就已经展开,但是大规模地开展还是在清代特别是雍正时期。究其原因除了以往研究中经常被提及的“政局安定、经济繁荣、国力渐盛”等因素外,雍正帝“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所起到的作用也逐渐被学者重视,甚至被当作是首要因素。⑥李世愉在《清政府对云南的管理与控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4期)、《清代的国家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史学集刊》2000年第4期)中都强调“大一统”观念在雍正帝以及整个清朝边疆治理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黄秀蓉在《“夷夏变迁”与明清“改土归流”》(《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03期)中更是把雍正帝的民族观念看作是开展改土归流的首位因素。虽然对于某些具体结论,笔者认为还有待商榷,但从民族观念切入确实为当前的改土归流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虽然,民族观念在改土归流原因中所占的分量,目前还未有定论,但是其确实推动与指导着改土归流的进行。比如:尚未进行改土归流时,雍正帝就特意嘱托巡抚在少数民族地区要善待奉公的土司,不要生事,“云、贵、川、广、猺獞杂处,其奉公输赋之土司,皆当与内地人民一体休养。俾得遂生乐业,乃不虚朕怀保柔远之心。嗣后毋得生事扰累,致令峒氓失所”①《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三雍正元年正月辛巳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0页。。决定解决土司问题时,雍正帝也谕令西南各省督抚提镇,表达出要让土民受其恩泽之意:“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马牛,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莫非朕之赤子,天下共享乐利,而土民独使向隅,朕心深为不忍……嗣后督抚提镇宜严饬所属土官,爱恤土民,毋得滥行科派。如申饬之后,不改前非,一有事犯,土司参革,从重究拟”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论旨汇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任命宠臣鄂尔泰进行改土归流之后,雍正帝在鄂尔泰的奏折上也经常批示务必谨慎行事,以招抚为先,即便动武也不要伤及无辜等诸如此类之言语。以上均体现出雍正帝民族观念中的“包容”,而其“局限”的一面既体现在实施改土归流之后雍正帝在朱批中所表现出的对西南少数民族,特别是不服从管理的少数民族的鄙夷之情,“蠢”“恶”“丑”等字眼屡见不鲜,更体现在对少数民族土司及民众所采取的数次血腥进剿。顺从则为民,可被招抚;不从则为丑恶,须被剿杀。由此可见,所谓的“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果真是只有先实现“天下一统”,西南少数民族均臣服于清廷统治之后,才可谈及“华夷一家”。
四、结语
如果结合雍正帝自身所处的位置与当时的政局形势考虑,雍正帝在民族观念上所表现出的双重性并不难理解。一方面,作为满族入关一统天下之后的第三代君主,雍正帝不可能没有满族出身的民族优越感,也不可能完全放下对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提防与戒备,甚至担心满族的民族特色会被汉化殆尽。另一方面,已经成为全国统一政权皇帝的雍正帝又深知若要稳固自己的统治,必须联合与依靠其他民族的力量。因此,无论是他看待民族问题的观念,还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对策,无不体现着“包容”与“局限”的双重性。为了避免厚此薄彼、偏颇其一,今后对雍正帝民族观念及对策的研究,应该在广泛利用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对其进行更为全面客观的还原与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