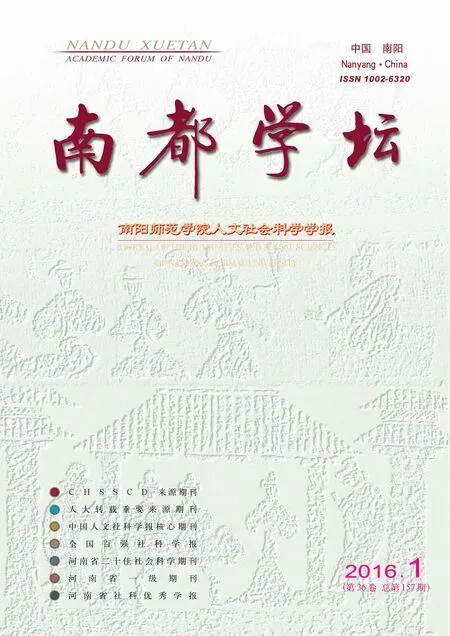王莽篡政过程中的西汉宗室王侯
张 斌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王莽篡政过程中的西汉宗室王侯
张斌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宗室王侯作为西汉统治阶层的重要成员,曾对维护汉政权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外戚势力的崛起,双方在政坛上展开角逐,他们的关系成为影响西汉中后期政局变化的重要因素。王莽在夺权过程中对刘姓王侯采取了兴灭继绝、经济收买、翦除政敌、军事镇压等手段进行笼络和控制,宗室与王莽的关系也由合作终至依附,但最后仍不免覆灭。分封的王侯与中央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深刻矛盾是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西汉; 宗室王侯; 外戚; 王莽
在西汉王朝建立的过程中,高祖刘邦对同宗有功者封以爵位,这对汉政权的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记·三王世家》言:“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为诸侯王,奉承天子,为万世法则,不可易。”[1]2109西汉分封宗室是吸取了周、秦两代的治国经验和教训,使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设想这样既可以保障最高统治者的皇权至上,防止列国纷争的局面再现,又能够荫及亲属,并利用他们拱卫朝廷,避免“二世而亡”的悲剧重演。在汉初之时,宗室王侯的设置的确巩固了立足未稳的西汉政权,特别是在平定“吕氏之乱”时,他们所起的作用至为重要。正如《汉书·诸侯王表》所说:“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如,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2]394但是在两百年后王莽以外戚身份逐步夺取最高权力进而即位称帝的时候,这些作为汉室“屏藩”的刘姓王侯除了个别零星反抗外,基本上都默默无闻,甚至谄媚邀功,这与他们在“吕氏之乱”时的同仇敌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上述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利益因素。
一、西汉宗室王侯在汉朝地位处境的演变
刘邦在开国后大肆分封同姓子弟为王侯,并赋予很大的权力,宗室的政治实力因此大增。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他们的经济实力也得以加强。“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2]528;诸侯王更是“连城数十,地方千里”[1]2961。至吕后时,宗室王侯已是“地犬牙相制,所谓盘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2]106。有强大的实力作为后盾,西汉宗室才能一举粉碎“吕氏之乱”。然而随着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发展,宗室王侯实力的膨胀已经影响到皇权,朝廷与这些有离心倾向的势力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冲突,景帝时晁错制订的削藩政策便应运而生,并受到了宗室王侯的激烈反对,最终酿成了“七国之乱”。有鉴于此,武帝采取了相对缓和的“推恩令”:“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辄别属汉郡。”[2]2425将“诸侯王割王国一县或一乡之地分其子弟,汉廷封以王子侯的名义,但该侯国须别属汉郡所有”[3]16。这样做便达到了贾谊所说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2]2237的目的。史载:“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厄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1]803王侯的领地被削减也使他们的经济实力受到了沉重打击,到此时已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2]2002。
经济上受挫的同时,宗室王侯的政治地位也在下降,汉廷采取一系列法律措施对之进行打压。景帝之前,诸侯王可自置吏、设赋敛。七国之乱以后,朝廷“令诸王不得治民,令内史主治民”[4]3627,开始大规模改革王国官制。“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武帝改汉内史为京兆尹,中尉为执金吾,郎中令为光禄勋,故王国如故。损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仆曰仆,秩亦千石。”[2]741此外中央政府对宗室王侯设置了诸多科禁,主要包括:不得窃用天子仪制;置吏需依汉制,王国仅得自置四百石以下的官;无虎符不得擅自发兵;不得在国内私自煮盐冶铸;不得擅爵人、赦死罪;不得收纳亡人,藏匿亡命;当定期入朝,且留京不得逾二十日;不得与外戚家私自交往;不得与其他诸王私自会晤;不得私自出境;不得对朝廷大臣私行赏赐。另外,诸侯王私行不检等行为更要受到汉法的严厉制裁,或削地,或夺爵,甚至诛死;颁布了“左官律”“阿党法”“附益法”,降低王国官吏地位,限制人才依附诸侯王[5]725-734。列侯的受封和朝聘等在中央归大鸿胪管辖,在地方受郡守尉的监督,不得擅出国界、擅兴徭役,更不得与诸侯王私下沟通[5]760-762。
此外,匈奴在西汉中期之后由于天灾和内讧而导致势力大大削弱,不再成为严重外患,政治斗争的焦点转移到统治阶级内部。自昭帝死后,汉室皇位继承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甚至出现皇帝(刘贺)被废黜而由其他宗室王侯继承皇位的情况。因此新君即位,对同宗亲属必然进行更严厉的打击以减少威胁。刘氏宗族在皇权的排挤下大多已沦为远离统治核心的碌碌无为之辈,他们逐渐被排挤到政权机构的边缘。公卿之中除宗正一职外鲜有宗室王侯的身影,而极受西汉王朝重视的刺史一职,除阳城侯刘德曾担任过外,其他宗室皆不曾染指*上述观点可参见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西汉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张传玺先生认为,由于政治地位的下降,宗室王侯的经济地位也进一步下降[6]108。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再加上这些宗室王侯自身骄奢淫逸、腐化堕落,更加剧了他们权力地位的衰弱。
二、西汉宗室王侯与王氏外戚的早期关系
汉初外戚的势力自“吕氏之乱”后备受提防与限制,如将军薄昭杀使者,当时薄太后尚在,但文帝为防异议仍一再逼迫自己的舅舅自杀。“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2]123又文帝欲用皇后之弟窦广国为丞相,但终因多方面的顾虑而“念久之不可”[1]2683。然自景帝晚年开始,外戚势力逐渐崛起。他们先是称雄外朝,窦婴、田蚡等人先后为相;之后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又统领军队,立下赫赫战功;武帝去世后,霍光以大将军领尚书事,终于正式掌控中枢。至成帝即位时,外戚势力已趋鼎盛,成帝“以元舅侍中卫尉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2]302。后又“悉封舅谭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红阳侯,根曲阳侯,逢时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2]4018。王莽家族的这支外戚势力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宗室与王氏外戚的较量在成帝初期便已展开,大将军王凤为了巩固自身势力,率先对宗室发难。他借日蚀之故反对成帝将定陶王刘康留居京师,声称“定陶王虽亲,于礼当奉藩在国。今留侍京师,诡正非常,故天见戒。宜遣王之国”[2]4019,迫使成帝与定陶王洒泪诀别。东平王刘宇来朝,求诸子之作和《太史公书》,王凤认为这些书多述纵横权术、谋臣奇策与地形险要,“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2]3325,成帝依奏不许。成帝欲任命宗室刘歆为中常侍,有司认为应该通晓王凤,而成帝认为此等小事完全可自己做主,然“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2]4019。连皇帝的贴身近臣都不许由宗室担任,王凤排斥宗室如此。此后王音、王商、王根相继为大司马,权倾朝野。他们都十分注重收罗人才以扩充自己的势力,手下汇集了诸如谷永、杜邺等一批有才华的幕僚和官吏。然而面对王氏外戚咄咄逼人的气焰,宗室王侯采取的对策却是忍气吞声,只将希望寄托于最高统治者,他们认为王氏得势源于成帝的母亲王太后,而成帝无嗣,新皇帝只得由藩王入继,如此王太后便会被架空,王氏外戚也将无所作为,宗室的利益便可得以恢复。
但是新即位的哀帝并未给予宗室王侯以他们想要的优待,反而加大了打击力度。他为使宠臣加官晋爵,不惜给宗室罗织罪名。史载:“息夫躬、孙宠等因中常侍宋弘上书告东平王云祝诅,又与后舅伍宏谋弑上为逆,云等伏诛,躬、宠擢为吏二千石。是时,侍中董贤爱幸于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缘,傅嘉劝上因东平事以封贤。”[2]3492这些手段直接威胁到了宗室王侯的生存。至此宗室对汉帝已经失望至极,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将希望寄托在王莽身上。
三、王莽对西汉宗室王侯的态度和措施
王莽是外戚集团中与众不同之人,他十分清楚诸侯王和王子侯是刘姓宗室的代表,这股势力必须着力控制,才便于自己将来称帝。王莽看清了这些宗室王侯的现状与处境,认识到只要保障他们那部分既得利益,夺取政权时便不会受到这一阶层的强烈反抗,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兴灭继绝,重申权利
自西汉开国至王莽当权,经历了二百余年的时间,其间许多宗室由于嫡子绝嗣、政策变动、因罪夺国等原因丧失了王侯的地位,其权利受到了很大损害,这引起了王莽的重视,为此他采取了“兴灭继绝”的行动,以保障宗室王侯的整体利益,达到收买人心的目的。汉平帝元始元年(1年)春,王莽“立故东平王云太子开明为王,故桃乡顷侯子成都为中山王。封宣帝耳孙信等三十六人皆为列侯”[2]349。元始二年(2年)又“立代孝王玄孙之子如意为广宗王,江都易王孙盱台侯宫为广川王,广川惠王曾孙伦为广德王”[2]353。元始五年(5年)祭祀明堂之时,“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余人征助祭。礼毕,皆益户,赐爵及金帛,增秩补吏,各有差”[2]358。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集中对宗室王侯进行大规模封赏的行为鲜有先例。不仅如此,王莽“又令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亡子而有孙若子同产子者,皆得以为嗣。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请。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者,复其属,其为吏举廉佐史,补四百石”[2]349。这些举措不仅放宽了王侯嗣爵的条件,而且在法理上又为其增加了一层保障,所以起到了显著的笼络效果。“一时显得王莽对他们的关心超过了刘氏皇帝,因而相当一批汉宗室贵族把王莽当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表。”[7]263
(二)打击外戚,减少威胁
王莽在拉拢宗室王侯的同时,也打击了宗室利益的主要竞争对手——外戚。汉代外戚取代宗室和功臣成为中央政权最重要的力量有其历史必然性,钱穆先生曾经指出:“良以同姓宗室,宜于封建,不宜于内朝为辅政。功臣嗣侯,数世而衰,亦难继盛。白徒孤仕,威信均有不孚。故君主政体之演进,当宗室封建,功臣世袭,两途衰绝,乃折而入于外戚之代兴。”[8]304这一言论揭示了汉王朝的实际权力在各个集团间的转移情况。至王莽时,西汉外戚势力达到顶峰。他执掌朝政、大权独揽,在短短八年时间内从“安汉公”至“宰衡”,加九锡,再到“摄皇帝”,登基称帝已是近在咫尺。富有政治眼光的王莽认识到,“外戚政治权势的基础其实十分脆弱,一方面需依附于皇后或母后,一旦皇后失宠被黜或母后亡故,即失靠山;另一方面在于有可控制的幼弱之主”[9]167。当时太皇太后王政君已是古稀之年,小皇帝富于春秋,王氏外戚极有可能再次遭遇如同哀帝朝那般的打击。为了彻底巩固自己的势力而免除后患,王莽决意称帝,这就和外戚中其他当权者的利益和理念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其斗争无法避免。他在平帝刚刚即位之时,便以“赵氏前害皇子,傅氏骄僭,遂废孝成赵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令自杀”[2]4044。将赵氏、傅氏等前朝外戚的势力彻底清洗;又借“吕宽之狱”铲除了平帝的母族卫氏;王氏外戚本身也在打击之列,例如,王莽的叔父红阳侯王立和兄长平阿侯王仁在朝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对他的进一步掌权形成了阻力。王莽便先“令大臣以罪过奏遣立、仁就国……后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杀”,并赐王立谥为“荒侯”,赐王仁谥为“剌侯”[2]4030。王莽在夺权过程中“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2]4045,甚至连自己的亲生骨肉也不例外,“元始中,王莽为安汉公,专政,莽长子宇与妻兄吕宽谋以血涂莽第门,欲惧莽令归政。发觉,莽大怒,杀宇”[2]3707-3708。王莽“大义灭亲”般的打击外戚,主要是为自己夺取最高政权扫清障碍,但客观上为长期受外戚压制的宗室出了一口恶气,并减少了他们在利益分割上的竞争对手。
(三)谦恭交往,塑造形象
王莽在政治上虽有很大的欲望,但却极为懂得韬晦。史载其“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阳朔中,世父大将军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2]4039。他还崇尚节俭,“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2]4041。王莽的这些行为在骄奢淫逸、飞扬跋扈的外戚子弟中实属与众不同,与那些腐化堕落、尸位素餐的官僚相比他更被人们奉为楷模。因此王莽赢得了包括宗室在内朝野的一致赞扬,几乎将其推上了道德的神坛。
不仅如此,王莽还利用儒学与宗室中的重要人物进行交往,以拉近彼此的关系,使其为己所用。西汉是儒学蓬勃发展的时期。钱穆先生通过研究汉代王国对学术的贡献认为尊崇儒学“其动机似先发于王国,而犹不在中朝”[8]79。耳濡目染中,当时儒学盛行的“三统”“五德终始”理论亦深深影响了刘姓宗室,刘向、刘歆父子正是此一理论的集大成者。王莽好儒学,着力与这些人交往:“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2]1972王莽最终正是利用这些理论,顺理成章地接受了汉朝的禅让。
综上所述,王莽对宗室王侯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一味排挤,而是大加封赏和笼络,结果使这些看似最不可能帮助王莽的人成了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完全是利益的驱使。这些宗室王侯虽然与汉朝皇帝同根同源,但却不断遭受历任统治者的严厉打击,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王莽因势利导,很容易便掌控了他们。相比较与以前的“削藩”和“推恩”,王莽的“继绝”措施无疑是受到诸多宗室王侯的大力支持。
四、西汉宗室王侯对王莽夺权的反应与结局
然而当王莽称帝的形迹暴露时,这些宗室王侯对王莽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他们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用武力“清君侧”,他们认为王莽在一步一步地篡夺最高权力,一旦江山易主,这些宗室就会丧失贵族身份,也就没有可利用的价值,他们要为自身的前途命运放手一搏。这一派以少壮的王子侯为主,他们多食一县封邑,王莽的“继绝”等措施对他们来讲利益甚微。这些列侯分散于全国,受到的监督也不及诸侯王,其自由度较大,因此可以突然起事。例如,居摄元年(6年)四月,安众侯刘崇与相张绍谋:“安汉公莽专制朝政,必危刘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举,此宗室耻也。吾帅宗族为先,海内必和。”[2]4082于是他们率领百余人起兵攻打宛城。居摄二年(7年),严乡侯刘信、武平侯刘璜与翟义等人谋划,认为“新都侯摄天子位,号令天下,故择宗室幼稚者以为孺子,依托周公辅成王之义,且以观望,必代汉家,其渐可见。方今宗室衰弱,外无强蕃,天下倾首服从,莫能亢扞国难。吾幸得备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汉厚恩,义当为国讨贼,以安社稷。欲举兵西诛不当摄者,选宗室子孙辅而立之”[2]3426。遂于九月都试之日起兵,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以东平国为基地,传檄郡国,共行征讨。始建国元年(9年)四月,徐乡侯刘快在其国结党数千人举兵攻打即墨[2]4110。此外,还有陵乡侯刘曾、扶恩侯刘贵等人的起事。
对于这些反叛者,王莽采取的措施是坚决打击。刘姓列侯起兵的规模都不大,在王莽的镇压下很快都失败了。据出土简牍记载:“六月戊午府下制书曰:‘安众侯刘崇与相张绍等谋反,已伏辜。崇季父蒲及令翚解印绶肉袒自护,书丁卯日入到。’”[10]48面对规模最大的刘信、翟义起兵,王莽派遣十一将军给予强力镇压,其中特别安排了两名刘姓宗室:忠孝侯刘宏和红休侯刘歆。以宗室镇压同姓列侯是王莽的讨伐策略,目的就是为了瓦解敌方的军心。徐乡侯刘快攻打即墨时,其兄刘殷竟紧守城池,结果使刘快大败而逃。这些零零散散的起兵都以失败告终,根本原因是双方实力的巨大差距,起兵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王莽对反叛者的处理也是异常严酷,“捕斩断(刘)信二子谷乡侯章、德广侯鲔,(翟)义母练、兄宣、亲属二十四人皆磔暴于长安都市四通之衢”。“发(翟义)父方进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烧其棺柩,夷灭三族,诛及种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2]3436-3439对其他参与谋反的宗室也不予赦免,杀一儆百[10]58*《居延新简》E.P.T59∶42:翟义、刘宇、刘璜及亲属当坐者盗臧证臧。。
另一派刘姓宗室则完全倒向了王莽,不遗余力地为其歌功颂德。自武帝之后,社会动荡、民怨沸腾、谣言四起,各个阶层对西汉政权的不满与日俱增。顾颉刚先生认为,当时“信五德说和三统说的人,以为汉的气运已尽,该改朝换代”[11]58。西汉的很多宗室王侯在经学家的影响下对这些说法深信不疑,最终甚至连最高统治者汉哀帝都相信汉室气运已尽,因此他才在夏贺良等人的鼓吹下于建平二年(前5年)六月改元改制,进行所谓的“再受命”,祈求上苍最后一次垂怜,但这次“再受命”仅仅进行了两个月便草草收场,演变成了一场闹剧[2]340*《汉书·哀帝纪》载汉哀帝建平二年六月,“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诏曰:‘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建平二年八月,“诏曰:‘待诏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过听贺良等言,冀为海内获福,卒亡嘉应。皆违经背古,不合时宜。六月甲子制书,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贺良等反道惑众,下有司。’皆伏辜”。。这次“再受命”的失败使刘姓宗室彻底对西汉政权丧失了信心,认定王莽的改朝换代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他们为求在新朝占有一席之地,必须表现出卖力为王莽摇旗呐喊的姿态。正如在为王莽加九锡时的诏书所言,“唯公功德光于天下,是以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诸生、吏民翕然同辞,连守阙庭,故下其章。诸侯、宗室辞去之日,复见前重陈,虽晓喻罢遣,犹不肯去”[2]4071。其中刘姓宗室王侯的行动最为积极。例如,元始五年(5年),泉陵侯刘庆上书言:“周成王幼少,称孺子,周公居摄。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2]4078此为王莽“居摄”之举的首倡。居摄元年(6年)刘崇和张绍起兵失败后,刘崇的族父刘嘉令张竦上奏,为莽歌功颂德,并大骂刘崇是“臣子之仇,宗室之仇,国家之贼,天下之害”[2]4084,并要将其宫室变为污水池以儆效尤。居摄三年(8年),广饶侯刘京又率先上书奏符命:七月中,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暮数梦,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亭长晨起视亭中,诚有新井,入地且百尺[2]4093。支持王莽改朝换代的言行层出不穷。等到他正式即位的时候,更出现了“汉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玺韨,惟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2]396的情景。经过这番表演,许多王侯天真地认为在新朝他们真的可以继续过尸位素餐的奢靡生活。
然而无论西汉宗室是反抗还是献媚,新朝建立之后,他们对王莽就已丧失了政治上的利用价值,不仅贵族身份被剥夺,而且成为王莽猜忌的对象。始建国二年(10年),立国将军孙建上奏:“请汉氏诸庙在京师者皆罢。诸刘为诸侯者,以户多少就五等之差;其为吏者皆罢,待除于家。上当天心,称高皇帝神灵,塞狂狡之萌。”[2]4119王莽同意了孙建的建议,于是在《汉书·诸侯王表》中可以见到许多诸侯王“贬为公,明年废”的记载;而王子侯“皆降称子,食孤卿禄,后皆夺爵”[4]561。
西汉宗室王侯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自身实力和素质的极度衰弱。经过西汉中央政权两百年的打击和外戚势力的排挤,宗室王侯的政治、经济地位与汉初已不可同日而语,既无法在政坛上发挥重要作用,又不能组织强力的武装对汉政权进行有效的拱卫。而且宗室王侯只求自保的心态致使他们进取心日益衰落,追求享乐成风,荒淫残忍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些王侯最后连染指中央政权的企图都消退了,以致连政务都不愿处理,东平王刘宇以“见尚书晨夜极苦,使我为之,不能也”[2]3323为由不愿辅政,只想过养尊处优的生活,整个社会都对刘汉政权失去了信心,改朝换代的呼声甚嚣尘上。王莽正是利用了这一点,结合其灵活的政治手腕,最终用“禅让”的方式实现了新朝取代汉廷的和平过渡。因此有学者称:“王莽代汉之所以顺利地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刘氏皇朝的腐败无能造成了整个社会对改朝换代的向往。”[7]261-262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M].济南:齐鲁书社,1984.
[6]张传玺.秦汉问题研究(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7]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8]钱穆.秦汉史[M].北京:三联书店,2005.
[9]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0]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
[11]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刘太祥]
The Imperial Family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n the Process of Wang Mang’s Manipulation
ZHANG Bin
(School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As the important member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imperial family once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keeping political stability. With the rising power of the maternal relatives, the two competed in the political arena, and their relationship had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late Western Han. In the process of seizing power, Wang Mang had carried out some means to capture and control the imperial family, such as reviving the extinguished ones, capturing some with money, getting rid of the political opponent, and military repress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erial family and Wang Mang were changed from cooperation, to attachment and finally to extinguish. The deep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imperial family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e were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is result.
Key words:Han Dynasty; imperial family; maternal relative; Wang Mang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6)01-0015-05
作者简介:张斌(1986—),男,河北省唐山市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秦汉史。
收稿日期:2015-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