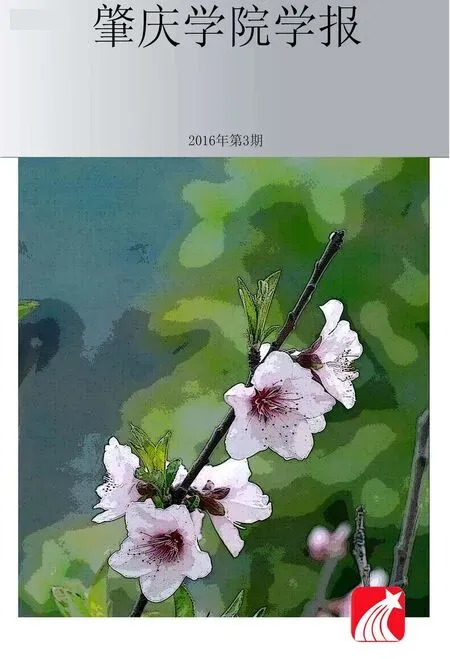端砚·革命·性爱·风物
——试析钟道宇《即墨侯》的文学地理叙述及内涵
赖翅萍
(肇庆学院 文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端砚·革命·性爱·风物
——试析钟道宇《即墨侯》的文学地理叙述及内涵
赖翅萍
(肇庆学院 文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钟道宇最新推出的端砚小说《即墨侯》,在叙事上具有清晰的文学地理写作意识。“端砚”不仅是小说的叙事核心,也是小说的叙事逻辑。作家通过叙写砚村郭家制砚人的人生起伏与命运变化,展示端砚刚柔相济的深厚文化与制砚人的伟大人格,并用端砚的文化精神与制砚人的人格力量,统领起与之有关的革命叙事、性爱叙事与风物叙事。“一方砚台,一座城市,一种文化”,这既是钟道宇通过《即墨侯》写作寻找到的文学矿脉,也是《即墨侯》的文学地理内涵。
《即墨侯》;文学地理叙述;端砚;革命;性爱;风物
新世纪岭南文学研究
新世纪岭南文学,是指21世纪以来的广东文学,主要指在广东工作、生活的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包括不在广东工作生活的广东籍作家的文学作品。新世纪岭南文学作家,既有刘斯奋、郭小东等老一辈作家,也有魏微、熊育群、王十月等知名作家;既有郑小琼、盛可以等后起之秀,也有当年明月、丛林狼等网络作家。而就西江文学或肇庆文学而言,钟道宇、徐金丽、聂怡颖等人的创作都可圈可点。本刊拟将“新世纪岭南文学研究”作为专栏,邀请省内外的专家、学者撰稿,不仅研究作家作品,也研究文学现象,分名家专辑、城市方阵、专门题材、网络文学等板块。此期先以本土作家钟道宇的端砚题材长篇小说新作《即墨侯》的研讨为契机,抛砖引玉,力求为岭南文学研究做些有益的探索。
主持人:黎保荣
“寻找文学的矿脉,应该从地理空间上入手”[1]16。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理空间以其丰富性与特殊性,不仅滋养着特定地理空间内人们的肉身与灵魂,还构建着文学特有的地理空间,塑造着文学的独特气质。从这一意义上说,真正的文学叙述是一种文学地理的叙述。诚如杨义所言,文学地理“实际上借用地理空间的形式,展开文学丰富层面的时间进程”[1]81。文学地理中的“地理”既包括作品描写的地理,也包括作家的出生地以及文学活动地的地理、作品传播的地理等。而文学地理叙述本质上是文学与地理的相互解释与交互叙述,一方面“地理”尤其是地理中影响全局的关键性地域文化会对文学叙述起到价值内化作用;另一方面文学叙述主体也会对客体的地理空间进行审美观照,并使客体的地理空间经过积淀、升华逐步衍变为文学的地理审美空间。在《即墨侯》里,钟道宇曾说过,“他之所以重新拿起笔来写小说,是因为陪一个外地有点名气的作家朋友到砚村去看端砚的时候那个作家劝他写写端砚的时候开始的。那位作家朋友对他说,你可以不写其他的小说,但是你不可以不写端砚。他问:为什么?作家朋友说:就因为你是肇庆端州人……写端砚,你有底气,你有地域的优势与资源,地气充沛”[2]143。这段自述不但表明钟道宇对文学地理价值的深刻认同,也表明他已经习得了文学地理叙述的根本要义。“端溪古砚天下奇,紫花夜半吐虹霓。”在钟道宇看来,历史悠久的端砚文化是对肇庆地域文化乃至整个岭南地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性文化,因此,多年来,他一直深耕端砚文化,喜蓄砚善国画,并致力于端砚系列文化小说的创作,相继推出《砚痴》《千金美猴王》《紫云》《即墨侯》等端砚题材作品,体现出作为“端砚产地”作家自觉的文学地理写作意识。如果说端砚是肇庆的一张名片,那么,端砚叙述则成为钟道宇的作家身份证明。《即墨侯》是钟道宇在2015年8月推出的端砚小说,笔者试着阐释其中所蕴含的文学地理审美内涵。
一、文化之厚与血火之重两相辉映
端砚的文化之厚与革命的血火之重穿插叙述,两相辉映,是《即墨侯》在端砚叙事上的一大特色。
作为四大名砚之首的端砚,自唐朝初年就在肇庆的古端州开始生产,并在漫长的制作、鉴赏与收藏中,形成了悠久深厚的端砚文化传统。端砚文化是一种刚柔相济的人格文化,诚如《即墨侯》里的作家夫人所言:“端砚材质温润,砚石精光内敛,其品格与中国传统文人的道德与人格理想不谋而合,你以砚喻德,并以君子比德的审美观念烛照端砚叙事,从而使端砚成为高贵、典雅、坚贞等美德的隐喻,成为坚强、刚正、清白等人格的象征。”[2]147不仅如此,肇庆还有源远流长的革命文化传统。1915年12月,肇庆成为讨袁护国战争大本营;1916年5月,肇庆成为两广护国军司令部与中华民国军务院所在地;1921年10月至1923年7月,孙中山为筹划北伐事宜三赴肇庆;1924年5月,周其鉴在广宁县新楼村成立中共广宁县农村党支部,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农民运动的典型;1926年5月,肇庆成为北伐战争发源地;抗战期间,肇庆成为西江抗日前线和保卫大西南后方的屏障;解放战争时期,肇庆成为粤桂湘边革命根据地中心,等等,这些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为风光秀丽的肇庆孕育出刚性的革命文化传统。
如何使刚柔相济的端砚文化与刚性的革命文化发生审美关联,这是钟道宇构思《即墨侯》端砚叙事的出发点。在晚清、民国与新中国等革命历史背景下,钟道宇叙述了砚村制砚世家郭端正一家几代人的人生裂变与命运起伏:郭家少爷郭天赐不惜忤逆父命,远赴京城,追随同盟会革命志士黎仲实;郭家徒弟郭树生因私生子身份,遭受郭夫人的冷眼,忍辱负重拜师学艺;郭家小姐郭家玉在圣德女子学校读书,与革命党人陈子忠相识相爱……。小说伊始,钟道宇就构架了《即墨侯》双线穿插叙述的叙事结构,即将端砚叙事与革命叙事交错编织,立体展示肇庆从晚清以降到改革开放的社会历史风貌。
钟道宇用副线简笔叙写郭家兄妹俩的革命故事。郭天赐追随黎仲实到京城谋炸摄政王载沣,事败后,为了革命浪迹天涯,先后转战广州、香港、上海,直到解放,成为肇庆新生人民政权的杰出领导者;郭家玉怀揣革命热情,投身于肇庆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即便是遭受了丧夫巨痛,也从不退却。她用教师的身份,掩护被国民党逮捕、暗杀的共产党人,加入广东人民抗日队伍,抗击日本侵略者。解放后,她也和哥哥一样成为肇庆新生人民政权的优秀干部。
对郭端正和郭树生等人在砚村的制砚人生,钟道宇则用主线予以具体描写。因受邀制作国父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砚,即墨侯郭端正和他的徒弟郭树生的制砚人生便与革命的血火联系起来。自晚清至解放前夕,肇庆地处军事要塞,为兵家必争之地,肇庆驻军今天还是孙中山、陈炯明的军队,明天就变成了桂系军队;原本的李耀汉省长,一眨眼就被广东督军莫荣新罢免,等等,诸如此类的腥风血雨,使制砚人的命运陷入了无常。高超的制砚技艺,不但使郭家有缘为军政要人制作天下名砚,如制作国父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砚”,省长李耀汉的“百鸟归巢砚”等,郭树生甚至因为“天下为公砚”而得到国父孙中山的召见。但也因高超的制砚技巧,使郭家接连蒙难,先是郭端正因为“百鸟归巢砚”,被砍掉了一只手,后是郭树生因日本人逼交祖传砚谱而跳塔自尽。然而,不管世事与命运如何变幻,不变的是制砚人对“端方正直”人格的坚守。“砚是文人心中的图腾”[2]58,郭家人的坚守,不仅表现在他们作为一名手艺人对技艺的卓绝追求上;也表现在他们对仁爱人伦的践行上,“侯爷郭端正去世后,郭树生独力支撑侯府,每天默默地做砚,勤恳地料理生意,每天还一如既往地伺候师娘,从没有半点怠慢,更不要说有一丝一毫的怨恨了。日久见人心啊!这让儿子不在身边的郭夫人心里感动之余,也十分的内疚……”[2]97;更表现在他们对民族大义、对革命的深刻理解上。面对日本桥本太郎对祖传砚谱虎视眈眈,郭树生选择跳塔自尽,用生命来捍卫砚谱,护卫端砚文化的浩然正气。
细究上述叙事,不难发现,文学与地理的交互作用在《即墨侯》里呈现出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共存的特征,比如同盟会成员黎仲实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但他到京城谋炸摄政王载沣则为作家所虚构;历史上孙中山也确实三到肇庆,并在鼎湖庆云寺上写下“众生平等,一切有情”条幅,肇庆砚人也确实制作过“天下为公砚”,但作家却根据这些历史事实虚构了砚人郭端正和郭树生为孙中山制作“天下为公砚”这一情节。日本的桥本关雪自1914年起,曾30多次来到中国,并在昭和三年(1928)买下沈石友藏砚。这一历史事实也被作家改造为桥本太郎觊觎郭家祖传砚谱,逼死郭树生这一情节。
而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相统一,将端砚叙事与革命叙事相关联的内在逻辑,恰恰是肇庆地域文化精髓的端砚文化精神。钟道宇指出,端砚叙事,是革命叙事的必然性链条。“端方正直”的端砚精神如天地苍茫一根骨,她使动荡的革命与岁月有了脊梁,有了灵魂,并使社会历史发展具有了连续性。正如勒庞所言,“只有当一个民族的精神拥有某种程度的刚性时,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民族才有可能稳定地建立”[3]。
二、性爱的忠贞柔美与端砚的端方温润相得益彰
“没有刚性,先辈的精神就无法继承;而没有柔性,则先辈的精神就不能适应由于文明的进步所带来的环境的变化”[3]15。勒庞在阐述刚性对建立民族共同体重要性的同时,也指出柔性对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基于勒庞的文化逻辑,钟道宇在挖掘并叙述制砚与革命的刚性品质的同时,也常常将端砚叙事和性爱叙事相结合,并用柔性的性爱故事去濡染制砚人生,点染端砚文化,从而使端砚文化携带上岭南山水文化与海洋文化所特有的阴柔气质。
“墨锭与砚台,其实就是古人对生殖崇拜的产物”[2]7。钟道宇对端砚的审美首先落在生命本能上。他对墨锭和砚台的生殖联想,得益于岭南传统生命文化的滋养。崇尚强旺的生命力,向往生命酣畅无阻的状态,是岭南文化的一种重要特质,如岭南自古就有对阳元石的生殖崇拜,广东丹霞山的阳元石因状似男性生殖器,而被尊称为“祖石”,被天下人膜拜。在《即墨侯》里,钟道宇以郭家的公狗与母狗阿花在香蕉林里的野合开头,抒写公狗母狗热血沸腾的本能追求、欣喜若狂的生命愉悦与生机盎然的生命活力,从而给整部小说奠定了讲述生命伦理的叙事基调。接着,作家在本能与伦理的冲突中,讲述砚村人的生命本能是如何僭越封建伦理的。从封建伦理的角度来看,即墨侯郭端正和青花巷女子秋香的青楼欢爱并不“端正”,罗彩云与刘副官也不过是一对奸夫淫妇,但钟道宇却细腻地叙写他们因性爱而臻达的生命自由状态。青楼女子秋香的温柔乡,恰恰是郭端正生命歇息与飞扬的所在地;罗彩云与刘副官的偷情,使长期独守空房、性爱缺失、生命淤塞不畅的她,重获新生,得到了生命如在云端的巅峰体验。这些,表明了作家对生命本能怀抱一颗敬畏之心,怀揣一份悲悯之情,体现了他对生命伦理叙事的坚守。
“那砚和那纸,皆宛如自己心中那超凡脱俗的玲珑女子”[2]71。钟道宇习惯在端砚与女人、砚痴与情痴之间作类比修辞,目的是使性爱叙事和端砚叙事相互映衬。在《即墨侯》里,随处可见文人对砚的痴迷,恋人对情的坚贞。前者如“文人耕砚于田,于是砚也就成了他们的精神家园。得意时,他们在砚池中神采飞扬,甚至手舞足蹈,放浪形骸。失意时,他们在砚中舔血疗伤,寻找寄托,聊以慰藉”[2]59。后者如郭端正与秋香的艳情,郭树生对家玉的痴情,郭树生对翠莲的恩情,家玉对陈子忠的同道之情等。性爱的热烈忠贞与端砚的端方正直交相辉映,性爱的细腻柔美与端砚的温润光滑相得益彰,这不但给端砚叙事增添了妩媚和动人的色彩,也使端砚叙事与生命叙事贯通,与市场趣味对接,为端砚叙事赢得了时尚感与可读性。
三、“端方正直,坚白同石”,端砚叙事与风物叙事同源同质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学是人学,这两个经典命题使风物民情与文学互为融通。作家常常通过风物叙事,表达主题,表现人物的行为、心理,塑造人物的性格。在《即墨侯》里,钟道宇较为全面地描写了肇庆的风光物产、古迹轶闻、日常礼仪、节日庆典、人伦举止、长幼规范等。丰富繁多的风物叙事,使《即墨侯》看起来就像是一部肇庆的“地方志”。但基于主题表达和人物塑造所需,钟道宇重点叙写了肇庆的名胜风景以及与端砚有关的风物。前者如对披云楼“披云鹤唳”胜景以及鼎湖山风景的描写;后者如羚羊峡的老坑、皇坑,端砚歌谣传说,端砚拜师习俗等。
如“披云鹤唳”,作家如是写道:披云楼前瞰西江,后枕北岭,崇楼杰阁,形如插天。每近黄昏,群鹤归巢,相互嬉闹,鸣叫不绝,把古老的端城点缀得异常空灵。端州古城因“披云鹤唳”胜景而生动了好几个世纪。这样的风物叙事,赋予了古老的端城与端砚以灵性。又如鼎湖山,作家以游客的欣喜,细数鼎湖山的美景:“鼎湖山山高林密,层岚叠峰。山上有天溪、云溪两大景区。天溪景区有庆云寺、荣睿大师纪念碑、飞水潭、宝鼎园、半山亭、补山亭、眼绿亭、苍翠桥、香界桥等景点;而云溪景区则有白云寺、跃龙庵、老龙潭、跃龙潭、三味潭、水帘洞天、白鹅潭、含珠涧、胡龙潭等景点,形态各异,各具特色,各有典故。白云寺,又称‘龙兴寺’‘鼎湖古寺’,坐落于鼎湖山云溪景区深山内,始建于唐高宗仪凤三年(公元678年),为六祖惠能高足智祥亲手兴建。古寺建好后,盛极一时。但因建于深山,交通很不方便,自明代后,日渐衰落,所有佛事活动,皆被交通方便的庆云寺所取代。白云寺下,还有一老龙潭。此潭四壁峭立,幽深莫测,传说当年有一青龙潜入此潭,老龙蠢动,使潭水翻滚,潭中便隆隆作响,其声如雷,并有奇光闪耀,后为开山祖师降服。”[2]106鼎湖山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留存,说明了肇庆有着灿烂的历史文化,无愧于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
而作家对端砚风物的描写,旨在全面立体地展示端砚文化的人格特质与成因。如叙写山高岭峭,道路崎岖,经常会出现云阴雾黑的羚羊峡里的老坑与皇坑,表现砚工采石的艰辛;叙写砚石歌谣:“食着采石个(这)碗饭,云盖山头也要行”“竹仔做床茅做瓦,手搓藤仔做门环”[2]41,表现采石工生活的艰辛与坚韧;叙写砚村的守护神——羚羊峡三块大白石的由来,以及村民逢初一、十五的祭拜活动,说明神佑制砚人,表现制砚的神圣以及制砚人对砚的敬重;叙写大唐贞观年间京城会试呵气成墨的故事,为天下闻名的端砚追溯其“闻名”的由来;叙写砚村婚嫁歌谣:“阿妹无心嫁街面,要嫁黄岗嫁砚村,羡哥会打青花砚,爱妹能绣并蒂莲。接到新娘回家转,拜天拜地拜祖先。”[2]49表现了砚村青年男女的可爱与痴情;叙写砚神顾二娘的“相石”本领,旨在说明砚人的高超技艺源于长期的制砚实践;叙写四月初八砚村“伍丁先师千秋宝诞”诞日的拜师习俗,意在表明师徒关系的重要性,重要到需要有隆重的风俗礼仪来确认和保护,如此等等。在诸多有关端砚风物的描写中,叙写阅江楼皇帝亲笔书写的“端云——岳牧之任”的御碑,是小说端砚风物叙事的点睛之笔:“‘端方’则是皇帝希望总督大人能像我们端州出的端砚一样,端方正直,坚白同石,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2]76,“端方正直,坚白同石”,正因为同源同质性,《即墨侯》的端砚叙事与风物叙事获得了叙事上的和谐与美感。
综观上述,不难发现《即墨侯》在叙事上的特点:“端砚”不仅是小说的叙事核心,也是小说的叙事逻辑。作家通过叙写制砚人的人生起伏与命运变化,展示刚柔相济的端砚人格文化,并用端砚的文化精神与人格力量,统领起与之有关的革命叙事、性爱叙事与风物叙事。概言之,“一方砚台,一座城市,一种文化”[2]143,这既是钟道宇通过《即墨侯》的写作寻找到的文学矿脉,也是《即墨侯》的文学地理内涵。
[1]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16.
[2]钟道宇.即墨侯[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
[3]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15.
Duan Inkstone·Revolution·Sex·Scenery:Abrief analysis of the narration and connotation of Zhong Daoyu's Ji Mo Hou
LAI Chipi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Zhaoqing University,Zhaoqing,Guangdong 526061,China)
Ji Mo Hou,a new piece of work written by Zhong Daoyu,developed a clear sense of literature and geography in its narration.Duan Inkstone was not only the core,but also the narrative logic in this novel.The novel presented a story of ups and downs in Guo's family,who relied on making inkstone for a living.Through the story,the strength and softness,the profound culture and the spirit of inkstone were shown to the readers. Moreover,the power of inkstone guided series of narrations of revolution,sex,and scenery.“An inkstone,a city,and a culture”,this statement was a great fortune founded through Zhong's work,and it also contained a deep connotative meaning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and geography.
Ji Mo Hou;literature geography narrative;Duan inkstone;revolution;sex;scenery
I207.425
A
1009-8445(2016)03-0001-04
(责任编辑:卢妙清)
2015-10-12
赖翅萍(1964-),女,广西陆川人,肇庆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