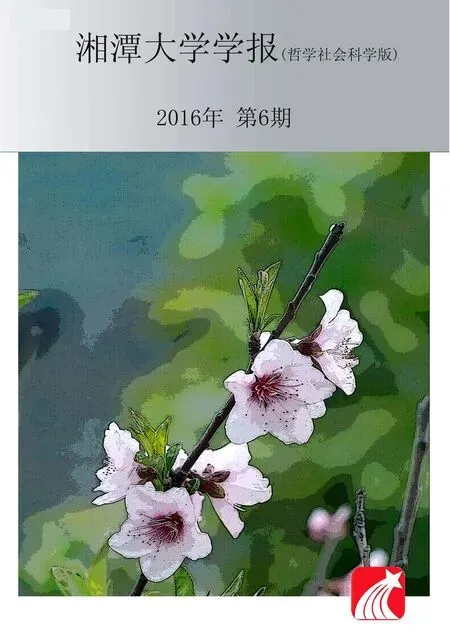略论海德格尔的历史思想*
邓 辉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略论海德格尔的历史思想*
邓 辉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海德格尔作为一个哲学家看似没有直接论述历史的专著,但其思想却是以“此在”的历史性为核心, 突出表现的是人的历史性意识,由此建构了关于历史性思想的系统理论。他通过对西方传统哲学即形而上学的批判和扬弃,开显了“此在”的历史性意识,获得了对历史之本性即时间性与生命性的真切认知,由此宣布哲学即形而上学的终结而提出澄明历史性之思的任务。海德格尔对“此在”历史性的理论解读正是对历史之为历史的根本性诠释,其历史观念亦就此而得以呈现。
海德格尔;历史性;此在;历史思想
海德格尔的思想奠基于西方传统的文化和哲学,但其哲学的核心却是“此在”的历史性意识。他在传统科学实证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时间本性的诠释与对历史性的解读,确立了真实本真的人的历史性特征,凭此力图弥缝西方传统哲学因为主客两分所造成的心与物、灵与肉、理性与非理性的鸿沟,发展了统合天人合一与主客分立思维的新思想,从而形成了时间性与生存性相统一的历史性思想体系。尽管他对历史本身并无直接文字表述和阐释,但在其理论系统中却包含了极其强烈而浓郁的历史观念。
一、存在之思对形而上学的解构
首先,海德格尔对西方传统哲学思想的历史性之缺席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明确了自然与历史的根本区别,指出人的本真性是统一自然与历史的存在。
著名学者叶秀山曾指出:正如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所指出的,长期以来欧洲人忽视了对自己的认识,见物不见人,最终导致了西方文明沦陷为一种僵化的体系,从而把人降为大机器中的组成部分;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唤起人对自身的自觉,把自己与僵死的物质世界区别开来。因此,海德格尔的哲学的主要基础就是建立在“历史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的严格区分上。[1]187-188而海德格尔的哲学正是“为了阐发人的特殊地位,强调从人即他所谓的此在(Dasein)来理解存在(Sein)的意义,要把存在与此在的时间性、历史性结合起来强调人之存在性意义”。[1]189海德格尔认为,西方传统的存在论“把存在理解为物之性或最本质的属性,这只是一种经验性、对象性思维的产物。也正基于此,西方人忘掉了存在真正的意义,忽略了人本真历史性意识”。[1]189他进一步批判性地指出,西方此种传统思维就是形而上学即哲学的思想方式,他说:“哲学即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和上帝。形而上学以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把握诸存在者之为存在者。”[2]58
恩斯特·布雷萨奇(Ernst·Breisach )认为,“自然哲学的胜利及其哲学所提倡的实证主义使形而上学体系在它们追寻非形而上学的真理中崩溃了。”[3]280海德格尔显然就是使形而上学体系奔溃的得力干将之一。他认为,哲学本意为爱智慧,最初来自于古希腊思想家赫拉克利特的残篇。[1]193-194就赫拉克利特而言,爱是指事物间的相互和谐与适应,智慧则指是者(存在者)都在是(存在)中,都属于是(存在),是(存在)把是者(存在者)集合为一。即是说,“一”统一着一切,所有是者(存在者)都在是(存在)中统一为一(即万物一体)。故爱智慧是人对此种万物一体的意识。然而,爱智慧逐渐变为对世界知识的追求,将爱智慧变成为一种对科学知识的追求的学问即哲学了。这种思维方式把世界作为客观对象加以观察,把握其中外在的因果必然联系以求得确切的知识。这种立场的根本性转变从苏格拉底开始,经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将哲学彻底沦为探究“第一性原则”的学问。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获得了与哲学等同的意义。海德格尔否认形而上学为人类根本的思维方式,以为这不过是物理学所派生的,是关于“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s)的一门学问,即探究诸在者之为在者的学问。虽然“形而上学”意义下的存在者是万物之本,是最高的最本质的具体共相,但不过是对象性思维的产物。它所要求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和对立,以世界为客体,以自己为主体,静观抽象地把握世界。这种态度实际上以僵化抽象了的理性即抹平时间性与历史性的理性去把握世界的外在规定性,而将世界的真实时间本性和因人(“此在”)而具有的历史性完全抹杀了。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了整个西方哲学史,虽然其地位经常受到挑战,但根基并未动摇过,直至近代康德,此问题才得到认真的对待。
康德把自由意志、道德律令等形而上学问题彻底排除于经验科学之外,从而严格地为科学知识划界。但康德的批判哲学是以二元论的形而上学方法来否定形而上学的。他首先承认了物理学(经验科学知识)和原物理学之间有原则性区别,进而通过物自体本身不可知即本源性问题之不可知来保证科学知识的可靠性和纯正性。而将形而上学本应思考的本源性问题通过别的方式来保留。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哲学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都是建立在先天逻辑性的基础上的,尤其是实践理性只是一个空洞的形式,毫无实际内容,一旦具体要求,便与柏拉图的理念无异了。实质上,康德的二元论不过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结果,而且这种分裂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混乱。黑格尔抓住了这一要害,批判并改造了这一抽象、孤立、空洞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然而,海德格尔认为,黑格尔看似卓有成效的庞大思辩哲学体系,不过是柏拉图以来的强大理念论的再造,仍以上帝作为自己哲学的顶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不过是此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极致体现。自黑格尔之后,所谓的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胡塞尔的现象学虽然提出“面向事情本身”,但这个事情却是意识本身。胡塞尔批评康德知识论夹杂了不纯的经验因素,其所追求的结果却是将康德哲学中最后一点经验因素毫不留情地排除出科学的大门而有所谓的纯科学知识的“严格的科学”。此种以意向性结构为核心建构的知识体系,依旧是理念式的主体性的,其先验还原最终导向的完全内心体验还是那个上帝。尽管胡塞尔的现象学不再是把人分裂成感性、理性等碎片式的活的思考者,但这种拥有所谓内在独立的人仍旧是抽象的孤立的僵死的,他所建构的所谓“严格科学”只是纯心理的结构,还是没有摆脱柏拉图理念论的致命诱惑。正是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2]58也正是基于此,他进一步得出结论:“哲学转变为关于人的经验科学,转变为关于一切能够成为人所能经验到的技术对象的东西的经验科学;人正是通过他的这种技术以多种多样的制作和塑造方式来加工世界,因此而把自身确立在世界中。所有这一切的实现在任何地方都是以科学对具体存在者领域的开拓为根据和尺度的。”[2]60
海德格尔认为,这种转变是“科学在由哲学开启出来的视界的发展。科学之发展同时即科学从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和科学的独立性的建立”。[2]60因此,海德格尔要求把哲学的目光转向前苏格拉底,转向哲学最初爱智慧的本源意义上去。他认为,在那里能够找到一种本源性的存在,真正的“一”和“全”。形而上学就应该是研究诸存在者之存在的本源性问题的,而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创立理念论之后,哲学就变成了后来的形而上学即哲学了。海氏总结到,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后,整个的西方哲学史就是将存在问题变成了存在者而完全忽略了存在本身,即忽略了历史性本身那个真实的时间性和生命性。因此,将整个关于本源性的存在问题变成为自然问题所追求的外在因果性联系的科学研究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声称在探求本源的道路上,哲学即形而上学已经终结了,开始了“思”的时期。“思”的任务就应该是“放弃以往的思想,而去规定思的事情”,[2]76即作为本源性的存在本身。
真正的本源性问题既包括自然也包括历史,是自然与历史的统一。历史是什么?历史与自然的意义相对,是“生存着的此在所特有的发生在时间中的演历:在格外强调的意义上被当作历史的则是:在共处中‘过去了的’而却又‘流传下来的’和继续起作用的演历”。[4]429海德格尔明确区分了自然与历史,他指出,“存在者只由于它属于世界才是历史的。但世界之所以具有历史事务的存在方式,是因为它构成了此在的一种存在论规定性。首要的具有历史性的是此在。而世内照面的东西则是次级具有历史性的;这不仅包括最广泛意义下的上手用具,而且包括作为‘历史土壤’的自然的周围世界。非此在式的存在者由于属于世界而具有历史性;我们称这类存在者为世界历史事物。”[4]431换言之,作为“此在”的人才真正具有历史性,才有其历史,“历史属于此在的存在,而此在的存在奠基于时间性”;[4]430自然如果能具有历史性的话,那也是因为“此在”。因此,在海氏看来,历史性是因为作为“此在”的真实的人才可能得以出现的;自然的意义不过是隐藏着的潜在历史性。因为自然与历史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本源性基础即存在本身,而作为“此在”的人是自然与历史的统一。海德格尔围绕“此在”的历史性展开其历史性哲学之阐释,即对本源性存在即“此在”历史性的追问之思。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尔虽然从西方自身传统出发,批判了西方传统的非历史性,但他却是从本源性的存在本身之发现开启的,进而认识到了历史性之意义所在。
二、“此在”历史性意识之开显
就海德格尔来说,对本真的生存历史性意识之思所获得的哲学本源意义之解蔽,是对真实的时间性、历史性的澄明,是对偏狭化的去时间性与历史性的理性的否定,是对理性本源的回归,因而是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的超越。
“海德格尔说,西方人在形而上学思想方式的笼罩下,一味追求科学之发展,沉溺于物质的世界,以求利用科学满足各种欲望,在沉重的文化的沉积下,醉生梦死,忘掉了存在,忘掉了作为Dasein的人的意义”,[1]201-202即本真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实际上,西方传统哲学追求的存在只是存在者,将存在者混同于存在,故追求的各个具体事物永恒不变性的那个抽象的共性,其最大的秘密就是时间的空间化,将时间理解为空间的位移,从而以空间代替了时间本性,即便是在黑格尔否定将时间等同于空间位移的空间的概念时间观里,其最终的时间概念本身依旧是“本身不变的变易本身”。*关于西方传统时间观及黑格尔的时间观,参见柯小刚《海德格尔与黑格尔时间思想比较研究》第二部分第一、二章的有关内容,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海德格尔洞悉了这一秘密,传统的时间观乃是对时间性的敉平,从而对本真源始的时间性做了极其深刻的历史性生存论分析。
海德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决定了西方传统思想中对时间的看法。与一般世俗将时间当作一种运动变化不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时间本身不是运动,因为运动是个别事物在个别地点的变化,而时间与一切事物同在;靠所用时间多少来测量运动有快慢之分,时间则无法再求助于另一个时间来测定自己的快慢。但亚里士多德又认为时间不能脱离变化而存在。我们只是在感到了变化的时候才感到时间的存在,说确切些就是,只有当我们已经感觉到了运动中的前和后以及这两个界限中间的一个间隔即现在时,我们才说有时间过去了。”[5]140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时间不是运动,而是使运动成为可以计数的东西”,“时间是关于前和后的运动的数,并且是连续的(因为运动是连续的)。”[6]125,127海德格尔认为,这种时间观表明,时间是通过计算物体运动数量获得的即日常因各种“钟表”获得的时间观念,它通过被数着的时间依据前、后视域确定了现在,而很容易成为现成的可安排的现在。这样一来,时间就被抽象缩化成以现在为核心的一个先后组成的序列。过去被看作“已不现在”,将来则变成为“还未现在”。海氏认为,亚氏这种时间观应对后世二千多年的现在化和庸俗化的时间观负责,他称之为“庸俗时间观”。黑格尔的时间观似乎具有着“历史性”,但海德格尔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黑格尔依旧是追随亚里士多德将时间作为自然哲学的问题来处理。他将空间和时间置于整个自然哲学最低级的“力学”阶段的开始处,认为是完全抽象和相互外在的东西,[7]39尽管通过辩证发展的具体论述获得了一定历史性,即从最抽象和外在于自身存在的空间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而达到时间,但从本质上,时间只是空间的真理所在。按照张祥龙的理解,海德格尔曾经对黑格尔的“时间是那种存在的时候不存在、不存在的时候存在的存在,是被直观的变易”[7]47这句话作了这样的解释:“时间的存在就是现在,一个现在或者已经不是现在或者还未是现在,因而也可理解为不存在。”因此,可以说黑格尔的时间观还“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仍然是“沿着庸俗时间的方向进行的”,“只是变得更抽象和现成化了。”[5]144海德格尔批评黑格尔的时间观是敉平了的时间观,其具有的时间性和历史性虽然是必然的,但只是抽象了的纯粹概念,是不真实的非本源性的。正是在对传统时间观批判的基础上,海氏从对本源性真实性时间的体察中,阐发自己独特的时间观,创发了对时间性、历史性本真的诠释。
海德格尔认为,“人必然要在存在中,即在时间中理解自己,剥夺人的时间性,也就是在消灭人。时间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只有在存在中,而不是在意识和外在的时间规定性中,人才能真正把握自己。”[8]179人作为“此在”是历史性的,而其历史性是植根于“此在”之存在的时间性的。“从一开始,时间就是海德格尔哲学关注的焦点和主要问题”,[8]184可以这么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就是一种时间诠释学。海德格尔指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就没有公正对待生命的时间性和历史性,而只是从作为时间的一个向度“现在”来考虑时间,时间被物化为一永恒的现在。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正是因此而得以可能的。康德的先天形式的时间实际上就是作为现在的时间。这种时间描述外在物质世界还勉强可行,一旦理解人就会使我们被迫转而以生命时间来理解自己。近代的生命哲学就是如此。生命哲学家虽然把生命体验为时间即绵延,然而绵延却要依靠记忆存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时间被形象地解释为“流”,这道流来自过去,流向未来,依旧是以现在为核心建构其时间观的。海德格尔认为,这些时间观都没有抓住时间的真正本源性即时间性,他认为,时间既是自然的即时间度量限定具有合法性,又是历史的即时间的生命性和意识性,它是从未来流向我们,存在于我们的决断中,时间是统一的。必须将时间与存在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才能揭示真正的时间性和历史性。
时间与存在的根本关系是通过存在来体现的。在存在中,存在者通过“此在”得到揭示,“此在”这个存在的揭示者是使人之为人之所在。人生在世(Being-in-the-world)。世界是我们如何遭遇事物方式的全体。“此在”处于世界之中,通过与世界打交道展示自己。“此在”对世界具有着领会,在这领会中生存和筹划。处世和领会共同构成一种表达或话语,从而使我们自己的存在成为可能。西方传统哲学要么通过感性使人陷入暂时事物世界后以理智把自己理解为永久的存在,要么把人提升到一个超感性的世界,把人的真实性、特殊性、个别性和有限性排除,却无视人的死亡或有限性。在海德格尔之前,从奥古斯丁到康德、胡塞尔大多是从意识出发讨论时间,只有海氏从存在即从人的存在的基本结构来确定时间的本源和意义。“此在”通过处世、领会及其因此而获得的话语来领会自己,即“此在”先行于自身而存在,又从这先行而存在回到自己。这个先行而存在就是“此在”时间性中的将来,死亡就是作为先在绝对可能性的最好证明,这个先在不是先验意义上的,是“此在”面前可能性的敞开。“此在”作为可能性存在,由于其趋死性必然是我的可能性。因此,先在就意味着来到自己的存在,即要到一定时候才成为现实之现在,而要来到自身就必须已经存在于世即曾经存在。换言之,“此在”必须被抛入于世,沉沦于世,才能通过领会最内在最本己的可能性从而回到自己的曾在。在日常生活即沉沦中,只有通过和周围世界打交道,才能让那些东西与我们相遇,从而表现出来,这就是现在。由是,海氏从其“此在”的生存结构中得出了先在或将来、已在和现在或当前三个时间性概念。这三个概念不是传统时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个向度的表面划分所导致的一种纯粹无始无终的现在序列,而是以“此在”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为条件,作为“此在”整体的存在样式。这是一种源始的时间概念,它决不是量的积累和相加,而是敞开自己不断放出自己,即“从将来回到自身来,决心就有所当前化地把自身带入处境。曾在源自将来,其情况是:曾在的(更好的说法是:曾在着的)将来从自身放出当前。我们把如此这般作为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而统一起来的现象称作时间性,”[4]372“时间性是源始的、自在自为的‘出离自身’本身。因而我们把上述将来、曾在、当前等现象称作时间性的绽出。时间性并非先是一种存在者,而后才从自身中走出来;时间性的本质即是在诸种绽出的统一中到时。”[4]375正因为先行于自身奠基于将来,“此在”才能够为其可能性存在而存在,根据于将来而筹划自身,所以海氏认定,此种自身筹划就是他所谓生存论的根本特性,故生存论的首要意义就是将来。*此上两段主要参阅张汝伦,《德国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191页。
海德格尔的时间观由此构成,它表明时间的达到是“此在”机缘境域“活生生地构成着、塑造着人生世界”,[5]136它以将来为重心,不断向当前,曾在敞开自身,从根本上相互牵挂组成一个不可分隔的流体而统一起来;这种构成无任何现成性可被超越,反而是使一切领会可能的缘在境域成为根源,因而与一切流俗时间、庸俗时间和被敉平的时间完全区别开来,形成一个从将来向当前和曾在敞开的“三维逸出”一体相互缘构着的时间本源性。这种“时间性必然体现为历史性,以时间为本性的缘在从根本上就是历史性的生存着”。[5]138这样本源性时间就与西方哲学论域里的存在问题直接相通,而这种存在却不是任何抽象的存在,既不是超出时间之外的实体之类的存在,又不是在任何时间之内的个别存在,毋宁说它就是统一时间性与存在本身的真实存在。因此,历史的分析就在“此在”的历史性分析,它“想要显示的是:这一存在者并非因为‘处在历史中’而是‘时间性的’;相反,只因为它在其存在的根据处是时间性的,所以它才历史性地生存着并能够历史性生存”。[4]426-427是故,“只有这样一种存在者,它就其存在来说本质上是将来的,因而能够自由地面对死而让自己以撞碎在死上的方式反抛回其实际的此之上,亦即作为将来的存在者就同样源始地是曾在的,只有这样一种存在者能够把继承下来的可能性承传给自己本身之际承担起本己的被抛境况并当下即是就为‘它的时代’存在。只有那同时既是有终的又是本真的时间性才使命运这样的东西成为可能,亦即使本真的历史性成为可能。”[4]435-436
事实上,海德格尔力图向我们述说的只是关于真实本真性的时间性本身以及它与生命性、历史性的必然联系,或者说,是时间性、生命性、历史性的统一。“此在”作为人之为人的存在是这一本真性存在的中介,是它使其有实现的可能,从而于自然中生发出历史的可能。人之为人的人就成为了自然与历史的关键环节,正是它将自然与历史统一起来。“历史的本质重心既不在过去之事中,也不在今天以及今天与过去之事的连系中,而是在生存的本真演历中,而这种本真的演历则源自此在的将来。……此在作为有时间性的此在就是有历史性的,所以它才能以重演的方式在其历史性中把自己承担过来。”[4]436-437也就是说,人之为人只要把握住真实的时间性,也就有其历史性,从而能以生存的方式演历本真,实现历史。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有其本真的历史性,才能使自然潜在的历史性被“此在”历史性意识开显,因为“此在的历史性本质上就是世界的历史性,而世界根据绽出的视野的时间性而属于时间性的到时。只要此在实际生存着,世内被揭示的东西也就已经照面了。上手事物与现成事物向来已随着历史性的在世界中存在的生存被吸收入世界的历史。……自然之有历史恰恰不是当我们说起‘自然史’时意思,它倒相反是作为村园、居住区和垦殖区,作为战场和祭场而有历史。这种世内存在者其本身就是有历史的,它的历史并非意味着某种‘外在的东西’,仿佛它只不过伴随着‘心灵’的‘内在’历史似的。我们把这种存在者称为世界历史事物。一方面它就世界与此在的本质上的生存上的统一而意味着世界的演历。但就世内存在者向来已随实际生存上的世界得到揭示而言,‘世界历史’同时就意指上手事物与现成事物在世内的‘演历’”。[4]439自然与历史本身统一,因“此在”的生存历史性活动而获得,在“此在”的历史性意识地不断开显和澄明中,历史得以不断从将来回到自身,自然潜在的历史性也就因“此在”的历史性得以解蔽而彰显。正是在“此在”不断彰显的历史性中,自然与历史获得统一,生存的历史性意识获得澄明。由此,存在、本源时间性、历史性、世界因“此在”获得了完满的统一和实现。
通过对海德格尔生存历史性意识的分析,我们明显体会到有着一种类似于东方式的“思”,正是凭着这“思”,海氏宣布西方传统哲学即形而上学的终结,提出“思”的任务。
三、思的任务即历史性之澄明
海德格尔所建构的是力图能够包容西方以往哲学思想,并克服其回避本真时间性、生命性与历史性之理论缺陷,而重新建构的全新思想体系,这一体系正是以其历史性特征而著名的。正如众多海德格尔研究者所指出的,海德格尔哲学明显受到了以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论为代表的道论思想的影响,但其思想体系并非因天人合一论而放弃传统,而是要化传统为己有,走上了一条从西方传统主客二分超越到天人合一的思维道路。这十分明显地体现于从其早期的基础本体论(存在论)到后期思想变化提出“本有”(Ereignis)论(大道论*国内著名的海德格尔专家和翻译家孙周兴就主张将Ereignis翻译成“大道”,见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五章“大道(Ereignis)之说”。)的思想转变中。
如果说海德格尔早年以存在为核心致力于基础本体论,依旧没有摆脱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气味,力图用一种不同意义的形而上学取代哲学即形而上学的话;那么其后期则一再提醒“存在”只是一个“暂时的词语”,几乎不再提及“存在论”也忌讳以“哲学”标识自己的思想,[9]278甚至直接论述“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相反Ereignis成为其后期思想的关键词语。根据孙周兴的考察,海氏将此词同希腊逻格斯(LOGOS)和中国的道(TAO)相提并论,认为这三者是处于同一层面的,具有相类似的含义。Ereignis就是成就世界诸因素而让诸因素成其本身,进入光亮之中而居有自身的;而不是传统西方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体、本原,不是至高无上的主宰,不是逻辑范畴可以规定的“思的事情”。[9]283而且学者们也十分详尽地记载了海德格尔对东方思想的关注和重视。尤其是他本人曾多次提及与中国台湾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老子《道德经》而未成就之事。在海氏著述言谈中,亦多次提及老庄。有学者认为,从“存在”走向“大道”正是海氏思想“转向”的根本内容,走向“大道”的道路就是他超越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转向非形而上学思想的道路。[9]293
海德格尔认为,“哲学之发展为独立的诸科学乃是哲学的合法完成,哲学在现时代正在走向终结。”[2]60这里海氏认为的哲学是针对于西方特有的哲学即形而上学而言的。他指出:“哲学在其历史进程中试图在某些地方(甚至在那里也只是不充分地)表述出来的东西,也即关于存在者之不同区域(自然、历史、法、艺术等)的存在论,现在被诸科学当作自己的任务接管过去了”;而“哲学之终结显示为一个科学技术世界以及相应于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的可控制的设置的胜利。哲学之终结就意味着植根于西方-欧洲思维的世界文明之开端”。[2]61那么,“在哲学从开端到终结的历史上,想必还有一项任务隐而不显地留给了思想,这一任务既不是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能够达到的,更不是起源于哲学的诸科学可以通达的。”[2]62这个任务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尝试,海德格尔论述道:“这种尝试甚至必得去思那种赋哲学以一个可能历史的东西的历史性。”[2]62这种可能性被海氏寄予极高的期望,他认为,“我们所思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眼下刚刚发端的世界文明终有一天会克服那种作为人类之世界栖留的唯一尺度的技术-科学-工业之特性。……同样不确定的乃是,世界文明是否将遭到突然的毁灭,或者它是否将长期地稳定下来,却又不是滞留于某种持久不变,一种持存,而毋宁说是把自身建立在常新的绵延不断的变化中。”[2]63显然,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这一思的任务用我们的话来说乃是建构历史性哲学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对西方传统的抛弃,它使“理性因无蔽的澄明而具有了历史性,理性在历史性的解释中被历史化。理性因而超越了因绝对固定不变的永恒本体所具有的客体化的知识能力,指向了无蔽的澄明。它摆脱了因追寻绝对固定的永恒真理而不可避免的偏狭”;[10]45-46而是建立在西方传统基础上的新文明,海氏称之为“世界文明”。“我们所思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眼下刚刚发端的世界文明终有一天会克服那种作为人类之世界栖留的唯一尺度的技术-科学-工业之特性。”[2]63这一文明需要“求助于一个由哲学提供出来的路标”。[2]63然而这个求助不是依靠传统西方哲学,它只是一个路标,是要在,“在传统哲学已经把事情带到了绝对知识和终极明证性的地方追问,如何隐藏着不再可能是传统西方哲学之事情的有待思的东西”,这个东西“植根于某个敞开之境,某个自由之境”,“我们把这一允诺某种可能的让显现和显示的敞开性命名为澄明。”[2]67因为“澄明乃是一切在场者和不在场者的敞开之境。思想必然要对这里称为澄明的那个事情投以特别的关注”,“澄明即自由的敞开之境”所揭示的“纯粹的空间和绽出的时间以及一切在时空中的在场者和不在场者才具有了聚集一切和庇护一切的位置”,[2]68“我们必得把被称为圆满丰沛的无蔽思为澄明,这种澄明才首先允诺存在和思想以及它们互为互与的在场”。[2]71海德格尔的意思很明确,不能离开西方既有的传统去空谈思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必须要满足两个基本的条件:一切在场者和不在场者。前者述说的是传统哲学所“带到的绝对知识和终极明证性的”而为现代诸科学已经所接手的东西,后者指向的是传统哲学“始终未曾思的东西”。他说:“我们指出在哲学中未曾思的东西,并不构成对哲学的一种批判,如若现在需要一种批判,那么这种批判的目标毋宁说是追问在哲学终结之际思的一种可能的任务的尝试”。[2]72因此,他特别指出,要用古希腊所运用而为后来所不常用的“无蔽”一词来翻译真理。
海德格尔认为,西方传统哲学把真理理解为“自然的”意义上的“在存在者那里显示出来的知识与存在者的符合一致关系”。[2]72澄明意义上的无蔽不能与被解释为关于存在的知识的确定性的真理等同起来。相反,“被思为澄明的无蔽,倒是使这种真理有其可能性。因为真理本身就如同存在和思想,唯有在澄明的因素中才能成其所是。真理的明证性和任何程度上的确定性,真理的任何一种证实方式,都已经随着这种真理而在起支配作用的澄明的领域中运作了。被思为在场性之澄明的无蔽,还不是真理。”[2]72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正是仅仅从在场性方面来究问在场者的。因此,追问无蔽本身并不是追问真理,否则那就意味着黑格尔与胡塞尔一样的绝对知识的确定性,而没有去追问此澄明被命名为无蔽本身未被思及,那些“追问真理即陈述的正确性如何只有在在场性之澄明的因素中才被允诺而出现”的不在场者未被思及。[2]73无蔽作为真理必须把无蔽思为自身遮蔽之澄明,只有遮蔽才是作为无蔽的心脏而属于无蔽。显然,海德格尔对真理一词的无蔽义提出在于唤起人们对哲学本源意义的觉醒,并同时提醒人们不要因为追求那个不在场者而遗忘放弃在场者的意义。虽然必须要确定的是,我们追问的是那个“应以何种方式去经验那种不需要证明就能为思想所获得的东西”,但它却为一点所决定,即“那种要求我们先于其它一切而允许其进入的东西的特性”,“即被思为澄明的那种圆满丰沛的无蔽本身。”[2]75-76不能包容含纳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在场性所澄明的东西决不会是自身遮蔽之澄明的无蔽,而这种在场性所澄明的正是得到后者之允诺才有其可能的。海德格尔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要化传统为己有,被思为澄明的无蔽必须要能有允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之真理的可能性。而海德格尔的结论“思的任务就应该是:放弃以往的思想,而去规定思的事情”,[2]76并不是说要完全抛弃西方传统思想,说的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不能思及其为能思的东西,而这才是允诺西方传统思想之可能的真正的无蔽。西方传统思想不能思考“思”的任务,所以面向思的事情要将它暂时放弃遗忘。这正是海德格尔思想最深邃的地方——化传统为己有才可能去面向思的任务,即要以主客二分超越而为天人合一。
恰如卡尔·佩吉所指出的,海德格尔苦心营建的所谓“有限历史性形而上学”标志着符合西方文化理性化要求的历史性形而上学(metaphysic of historicity)的初步尝试,尽管他认为是失败的。[10]129但毋庸置疑的是海德格尔思想的特征正在于历史性,突出表现的是人的历史性意识,由此建构了关于历史性思想的系统理论。海德格尔思想表面看似缺乏直叙历史的环节,其实他对“此在”的历史性解释却是基于历史之本性即时间性与生命性的真切体认获得的,他对“此在”历史性的解读正是对历史之为历史的根本性诠释,故他的历史观念亦就此而得以呈现。
[1]叶秀山.思·史·诗[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Ernst Breisach.Historiography[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econd Edition (1994).
[4][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二版)[M].王庆节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5]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M].北京:三联书店,1996.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德]黑格尔.自然哲学[M].薛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张汝伦.德国哲学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9]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M].上海:上海三联,1994.
[10]Carl Page.Philosophical Historicism and the Betrayal of First Philosophy[M].Pewnsy 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
责任编辑:立 早
On the Thinking of History of Heidegger
DENG Hui
(DepartmentofPhilosophy,Shanghai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s a philosopher, Heidegger seems to have no special books on history.However, he has constructed the system theory of historicity which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consciousness of people’s historicity with the core of historicity of Dasein.He criticized and sublated wester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which is metaphysics, opened a significant Dasein’s consciousness,and got real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history, which is time and life.Therefore,he announced the end of metaphysics and philosophy and put forward the task of thinking that enlightens the historicity.Heidegg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y of Dasein’s historicity is a fundament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Heidegger; historicity; Dasein; thinking of history
2016-10-02
邓辉(1972—),男,湖南衡阳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上海市高校高峰高原计划高原(1)建设计划哲学规划项目成果。
B516
A
1001-5981(2016)06-01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