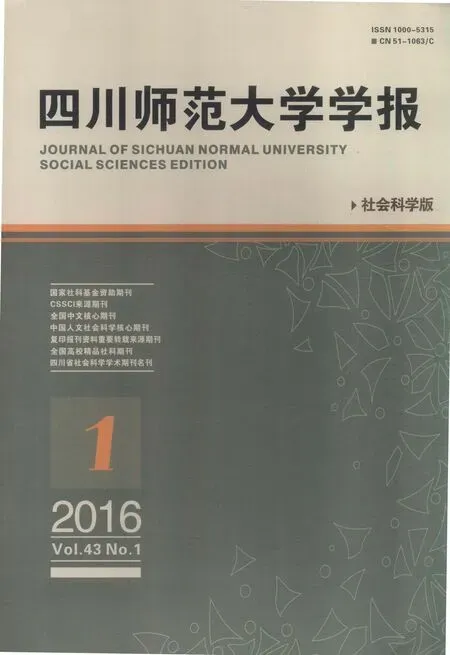网络犯罪的刑罚边界——以刑法不得已原则为视角
童春荣,赵 宇
(1.重庆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044;2.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网络犯罪的刑罚边界——以刑法不得已原则为视角
童春荣1,赵宇2
(1.重庆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044;2.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刑法不得已原则执基民众立场,载荷常识、常理、常情,依托人权保障,从刑法当为的内容追根溯源网络犯罪的刑罚边界,洞彻网络犯罪乃主观罪过支配的内在乾坤,揭示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同宗同源的实质意蕴,统一网络犯罪在秩序与人权、主观与客观、虚拟与现实、实害与风险之间的共识。刑法不得已原则以公众意愿考量他法是否能够有效调整以及不予刑法调整,相应的法律制度是否会崩溃,探寻区分赋值、刑事和解在网络犯罪之罪与非罪和缓连接中的不得已运用。在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的科予上,不得已原则又以公众情感直观测量刑量,并在相应的罪名之间以刑制罪,确保网络犯罪刑罚边界之适正性。
关键词:网络犯罪;刑罚边界;不得已原则;主观罪过;以刑制罪

赵宇(1985—),男,河北保定人,中央司法警官学院讲师。
随着三网时代的到来①,网络已经真切地侵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购物、数据共享、生活互助,网络已然成为现实世界的主导。网络应用塑造了全新的社会生活形态,其对衣食住行的影响与真实社会几无差别[1]。但是,伴随网络世界欣欣向荣之发展势态,网络有害行为也接踵而至。虚拟财产的盗窃,网络平台的诋毁,数据资源的破坏频频爆出,肆意危害着网络安全,使人们在尽享网络便利的同时,也时刻担忧网络风险。无疑,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信息的日新月异,以及大数据时代的迅猛来临,网络安全早已成为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在风险重生的数据时代,网络有害行为被视为洪水猛兽,并欲除之而后快,这也是缘何有关网络犯罪的立法建言、扩张解释、司法适用罄竹难书的原因。事实上,科技进步在促使新生事物不断涌现的同时,也驱使法律不断变更自己的保护边界[2]。刑法作为“后盾之法”和“保障之法”,自然当仁不让地向网络视域延伸和拓展。
毋庸置疑,网络有害行为存在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予以规制,但对于如何规制、何法规制、刑民界限何处,学界并无定论且争议不断。网络是一种虚拟世界,对虚拟世界的虚拟财产危害行为如何能够按照传统犯罪论处;网络犯罪以网络安全为目的,唯危害结果论,没有主观罪过的行为缘何能够进入刑法视域;网络犯罪以抑制网络不良行为为趣旨,强调罪刑法定,阙如刑法规定的网络行为何以适用刑法;网络犯罪以运用网络为前提,兼有网络犯罪和传统犯罪的特征,异质罪名作何取舍。
此种诘难和疑虑在网络犯罪之争中比比皆是,却鲜有一致解答。笔者认为,学界之所以在网络犯罪之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的抉择上举步维艰,进退维谷,皆因将传统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严格遵崇之法等同于文本之法、规定之法②,致使刑法在面对网络有害行为之新生事物时无所适从,陷入无限扩张和极力限缩的两级③。有鉴于此,网络犯罪的刑罚边界应当从不得已原则追根溯源刑法当为的内容,以此探幽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关系,洞彻网络犯罪乃主观罪过支配的内在乾坤,揭示不得已原则对传统刑法三大基本原则的统领地位。同时,网络犯罪应当依托常识、常理、常情知悉公众意愿,并在此基础上以刑制罪,以期通过刑法不得已原则在实践层面的严格操守,明晰网络犯罪的刑罚边界。
一根蟠节错:网络犯罪刑罚边界之现状
网络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涉猎,大数据的全力加盟,使网络犯罪呈现变异升级、千姿百态之相,给刑法规制带来全新的挑战。“当世界开始迈向大数据时代时,社会也将经历类似的地壳运动”[3]。网络犯罪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网络犯罪是指利用电脑作为犯罪工具或犯罪目的之所有犯罪,凡与网路设备相关之犯罪均属之;狭义者认为仅包含行为人为具备电脑专业知识与技术,故意违反破坏财产法益之财产犯罪[4]210。实践中,网络犯罪多被定义在广义范围内,故本文也采广义说。
网络犯罪具有复杂性、新奇性的特质,刑法规制较为混乱,定罪量刑毫无章法可循,同一行为之刑罚处遇偏差较大,难以保证实质公平。同时,网络犯罪之刑罚界限亦模糊不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之抉择困难重重,定案依据聚焦于网络犯罪的风险等级、危害后果,对网络安全关注甚多,而对人主观罪过较少涉及,致使网络犯罪成为有别于传统犯罪的新生事物。
(一)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混乱
1.一律不予入罪
网络是虚拟世界的载体,虚拟的人、虚拟的物、虚拟的空间。而犯罪的对象是现实社会具体的人和物,故刑法不涉及虚拟之物,网络犯罪自然无从论及。不过,随着网络犯罪刑法法条的专门化,纯粹的网络有害行为一律不入罪的做法已经销声匿迹,但对于专门法条之外的网络有害行为仍然有无罪化的倾向。这种做法主要基于以下观点:网络行为是对虚拟世界、虚拟对象的虚拟财产攻击,存在价值虚无的问题,难以确定的损害后果。如同BBS平台的谩骂不能与公共空间的侮辱相提并论,窃取游戏币不能与盗窃财物等量齐观,转发微博与强拿硬要之寻衅滋事不可同日而语,毕竟网络世界的虚拟毁损和现实世界的真切损害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而我国刑法法条一般存在数额大小和损害程度的限制,某种危害行为只有达致一定的数额标准和损害程度后才能定罪入刑,因此网络有害行为很难匡入刑法范畴。同时,基于网络有害行为的非暴力性,有人主张应当纳入民法或者行政法调整,而无须借助刑法的强力惩戒。加之,网络犯罪较传统犯罪而言存在侦查和适用罪名的困难,一些司法机关通常会出于畏难情绪,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庇护下不予犯罪认定④。此种做法固守刑法文本,抑制司法能动性,无法从理论的窠臼中超脱出来,难以实现刑法的实时跟进,而日益遭受唾弃。
2.依网络犯罪专门条款规制
网络世界在繁荣昌盛的同时,也成为网络有害行为孳衍生息的温床。面对日益增长和千变万化的网络有害行为,不予刑法规制,似有纵容网络恶劣风气之嫌;加以刑法惩戒,又有罪名适用是否恰致之忧。此时,将《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百八十六条沦为“口袋罪”,似乎是一种不错的抉择。即将“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扩张解释为“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进而再将数据一词的外延由“数据库中的数据”扩展到“一切数据”[5]。这样,不管行为人是利用计算机数据作为手段,还是行为直指计算机数据,只要行为借助计算机完成,都可以纳入该两条计算机信息犯罪的条款。同时,这一做法与刑法设置侵入和毁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名相得益彰,既避免了传统犯罪与网络犯罪的细微甄别,又可以避免上级司法机关的错案追究,是一种司法机关乐于采用的做法。但是,这一做法执基于计算机信息数据的扩张解释之上,存在突破法条固有内涵的缺陷,不仅贬抑司法能动性,还陷网络犯罪于统一定罪量刑的境地,难以满足网络世界多样化发展的需求,在实践中亦备受质疑。
3.比照传统犯罪定罪量刑
网络犯罪的基本原型是传统犯罪,是传统犯罪在网络世界的展开。网络犯罪虽然以计算机网络为工具和空间,但是并未改变行为人追求危害社会结果发生的目的。因此,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来分析,网络犯罪和传统犯罪别无二致,只是网络犯罪借助计算机信息系统,在表现形式上不如传统犯罪直观,我们才将其与传统犯罪区分开来。从这一层面上说,网络盗窃和现实盗窃并无差别,网络平台的诋毁后果可以与公共秩序的侮辱相当,寻衅滋事也并非受限于现实世界的必然之物,而可以突破三维视角进入网络领域。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网络犯罪被视为传统犯罪僭越的结果。如秦火火案中,犯罪人秦志晖在网络微博账号中转发微博的行为被视为有危及公共场所秩序的危险⑤,行为人在夸大转发微博信息内容时也有制造混乱的故意,因此秦志晖之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同时,秦志晖转发微博信息的内容纯属子虚乌有和凭空杜撰,其行为已经对当事人造成现实的名誉损害,符合诽谤罪的犯罪构成。故该案在比对传统犯罪的基础上以诽谤罪和寻衅滋事罪定罪量刑[6]。网络犯罪按传统犯罪定罪量刑的做法,摈弃了刑法专门法条的规定,将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融于一炉,避免了网络犯罪专门立法的繁琐,规避了采用侵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后与传统犯罪刑罚之间的不均衡,有利于调动司法能动性,在适用过程中不乏支持者。但是,网络犯罪比照传统犯罪,将公共场所延展至网络世界,把虚拟财产等同现实财物,有扩张解释之嫌。此外,网络犯罪的非暴力性、技术性,较传统犯罪之于受害人的现实危害和心理威胁,还是有所差别的,如果一律按照传统犯罪定罪量刑,有刑罚过重之嫌,也许行为人仅仅一次偶然的网络好奇而遭致牢狱之灾。
(二)网络犯罪的刑罚边界不清
网络犯罪的刑罚边界既包括罪与非罪的边界、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亦包括重罪与轻罪的区分。网络犯罪之刑罚边界的明晰,有助于司法实践正确把握刑法在网络犯罪中的规制范围,防止其过或不及。然而,以往网络犯罪在各地司法实践中截然不同的刑罚处遇,不仅没有明晰网络犯罪的刑罚边界,反陷其于重重迷障之中,需要在深刻剖析的基础上洞悉网络犯罪的争议焦点。
1.罪与非罪的界限不清
何种行为当为网络犯罪,何种行为不当为网络犯罪,目前的司法实践并未给出明确的解答。对行为造成的网络安全风险,定罪有之,不定罪亦有之,是否当属网络犯罪,司法机关大都依靠感观评价。如果网络安全风险较高,危害结果较大,则应当援引网络犯罪的专门条款或者比照传统犯罪之相应条款定罪量刑。反之,如果没有网络安全风险,即便有现实的危害结果,也不当定罪,而应当在民法和行政法中消化。由此可见,网络犯罪的构成与否主要取决于风险的有无和大小,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则被搁置一边。但风险本就是一个有待论证的概念[7]。网络犯罪执基其上必然导致众说纷纭的境地,罪与非罪争执不下也就不足为奇。
2.此罪与彼罪的边界不清
即便司法实践对同一网络有害行为均能达成入罪共识,也在此罪与彼罪中举棋不定,游离彷徨。例如针对网络发送木马程序盗窃游戏币的行为,究竟应当以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论处,还是以盗窃罪定罪,并无定论。如果把植入木马程序看做是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破坏,则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的规定,按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论处⑥。如果把植入木马程序看做是盗窃游戏币的手段,则盗窃结果是刑法评价的对象,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的规定⑦。对此,也有人将此种网络犯罪视为牵连犯,并认为应当择一重处或者数罪并罚⑧。故即便达成入罪共识,网络犯罪之罪名界限亦是模糊不清的。
3.重罪与轻罪的界分不清
网络犯罪此罪与彼罪的游离彷徨必然遭致重罪与轻罪的界分模糊。以上述嵌入木马程序盗窃游戏币为例,获刑盗窃最高可处无期徒刑,获刑非法侵入计算机数据罪则最多七年有期徒刑,七年和无期相差甚远,同一行为缘何分处轻重两极、重罪与轻罪泾渭分明。同时,这种轻罪与重罪的模糊界分,会减少公众对刑法的预期,使人们在网络世界手足无措。此外,网络犯罪对犯罪形态的认定也会导致重罪与轻罪的界限模糊。一般而言,对于网络犯罪的既遂通常以虚拟财产的获取、公众平台的诋毁言论发布以及转发信息的次数和浏览数量的达致作为标准。如果虚拟财产已被行为人控制,公众平台的诋毁言论已遭发布,网络信息已有一定的访问量和点击率,则视为网络危害的后果已然发生,可以按照既遂标准论处。但是,对于没有使用的游戏币很难说和现实的财物具有等质性,其定罪数额应当按使用部分论处,如果没有使用则应当按未遂科刑。网络平台的诽谤,言论的发布并非犯罪既遂的唯一根据,而唯有诽谤危害结果在现实世界形成才是既遂成立的标志。同样,转发微博的行为也不当以次数和点击量判定既遂,而应当以微博信息的转发是否引起现实公共秩序的骚乱为界,如果没有只能定为未遂。按照《刑法》第二十三条,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从这个层面上说,现行网络犯罪之实践一律按既遂处理之做法,必然使重罪与轻罪的界分模糊,且趋于重刑化。
二游离彷徨:网络犯罪刑罚边界之聚讼焦点
网络犯罪之所以在刑罚边界上模棱两可,错漏百出,既与网络犯罪的新兴地位有关,亦与网络犯罪的变幻莫测有涉。其争议主要聚焦于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关系,人权和秩序的取舍,主观罪过亦或客观危害决定犯罪的成否,虚拟之物可否评价为犯罪对象亦或犯罪空间,刑法能否扩张等问题,应当在仔细甄别的基础上寻求积极对策。
(一)网络犯罪和传统犯罪的关系:同质之物与异质之物的分歧
关于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是同质之物还是异质之物,存在较大的分歧。坚持异质之物者认为,网络犯罪是利用网络数据,或者直指网络数据的犯罪,是联结于虚拟世界之网的社会关系,与传统犯罪载荷现实社会关系有着较大的区别,是异质之物,应当予以专门规制,以免刑法的疏漏导致网络犯罪的放任。网络的快速普及与深度社会化,无疑加速了网络虚拟社会关系的再造,迫切需要刑法予以专门性回应[2]113。同时,网络犯罪是对风险社会的应对,是基于网络安全风险考虑之下的刑法规制,与传统犯罪之实然之害有着本质差异,应当作为正统刑法的例外,以此脱缰正统刑法的管控,有的放矢地予以网络安全风险的监管[8]。
坚持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是同质之物者则认为,网络犯罪对网络数据的利用、控制以及以网络世界为空间视域,并不足以说明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是异质之物。网络犯罪借助网络世界实现犯罪目的,只是向人们展示了传统犯罪在网络空间的演化过程,其实质上并未改变网络犯罪隶属于传统犯罪的事实。网络犯罪之虚拟财产的盗窃、公众平台的诋毁、虚假信息的散播都可以在传统犯罪中找到原型。毋庸置疑,虚拟财产是现实财产在网络世界的移花接木,BBS是公共场合的网络再现,网络消息的散布则是造成公共秩序骚乱的始作俑者,因此网络犯罪在传统犯罪中均有原型,应当以传统犯罪论处,而不必专门立法。事实上,《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二百八十六条完全可以通过适用《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故意毁坏财物罪、第二百七十六条破坏生产经营罪,达致同样的惩罚效果。此外,网络犯罪也不是风险刑法的特有产物,风险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并非大数据的专利,以规制风险之名,突破刑法的边界,实乃无稽之谈。贝克认为:“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相应地,与短缺社会的分配相关的问题和冲突,同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风险的生产、界定和分配所引起的问题和冲突相重叠。”[9]15换言之,风险贯穿人类社会的始终,并非发达社会的必然产物。因此,网络犯罪之风险刑法的论断,看似“言之凿凿”,实则“毫无根基”。
(二)网络犯罪的规制目的:人权保障与秩序维护的较量
网络犯罪保障的是人权还是秩序,决定了网络犯罪的坚守底限。如果网络犯罪旨在保障人权,那么网络秩序就应当让位于人权保障,并始终恪守刑法保障人权之终极目标。反之,网络犯罪其意在于保障秩序,那么为了网络安全可以牺牲人权,以使网络世界能够井然有序。对于何种观点居于主流,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坚持网络犯罪保障秩序者认为,秩序是人们安身立命之本,任何人都不能在脱离秩序管控的情况下获得幸福和过有尊严的生活,因此保障秩序乃万物之首。而网络社会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一个生活空间,把网络社会的秩序作为社会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很有必要的,也是理所当然的[10]。为了网络的安全运行,刑法需要以保障秩序之名对个人人权实施限制,以此实现威慑和规劝的目的,防止网络危害行为孳衍生长,流弊从生。从这一层面上说,为了网络安全,刑法完全可以恣意对个人自由强加限制,如微博转发五百次的,可以诽谤罪入刑⑨。
坚持网络犯罪保障人权者则认为,人权是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任何人不得以保障秩序之名侵犯个人人权。秩序只限于凝结人权内容的范畴,脱离此视域就是强权者的恣意和滥权。网络犯罪并不存在对独立网络秩序的考量问题,而仅需测量其是否突破人权保障的限度。“网络只是人的一种工具,人是使用工具的主体,而不会成为工具的一部分,对于网络空间秩序的规制实际上仍以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为出发点”[11]。搜查手机需要专门的搜查令,就是对人权保障的最好例证[2]117。
(三)网络犯罪的定性:主观罪过与客观危害的抉择
网络犯罪是否应当将主观罪过一以贯之,还是彻底摒弃,实践中也争执不下。否定网络犯罪需要依据主观罪过者认为,网络犯罪是风险社会的产物,其意旨在风险防控、秩序维护,应当基于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危险,以防止严重危及网络安全或增高网络风险的行为在主观罪过的开脱下逃之夭夭。换言之,风险刑法的特质乃是主客观分离化[12],且客观危害是犯罪认定的核心。加之,网络犯罪的主观罪过纷繁复杂,一一厘清较为困难,而从客观危害着手则较为简单,且能够有效地管控网络风险,避免网络危害行为的恣意横行,对于威慑潜在犯罪者作用甚大,应当在网络犯罪中坚持适用。
坚持主观罪过者则认为,刑法处罚的是行为人,而不是行为,行为人只有在具备主观罪过的基础上才能定罪量刑。客观危害只是一种客观存在之物。如果客观危害中没有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不是行为人意志控制的进程,则客观危害不能归责于行为人。风险刑法之风险在任何社会均存在,如果以牺牲人权作为代价控制风险、维护秩序,必然使网络犯罪陷入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境地。事实上,行为不可能不包括行为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且两者是辩证统一的,脱离任何一方都将陷入无所归心的随意。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如盗窃、逃学、破门而入,等等——对行为的描述丝毫也不能反映侵害者在违法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特征。当似乎必须给这种类型的行为贴上标签时,也必须意识到,就任何一般意义而言,给侵犯行为命名根本不可能揭示出行为的任何决定性要素。”[13]112-113而唯有主观罪过才能揭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此而言,网络犯罪必须坚守主观罪过决定论。
(四)网络犯罪的伊始:法益保护提前与人权保障坚守的纷扰
没有客观危害结果时,刑法可否提前介入,一直是网络犯罪争议的焦点所在。持法益保护提前论者认为,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法益保护前置化已然成为刑法发展的基本趋势,网络犯罪也概莫能外。在风险社会,“危险刑法不再耐心等待社会危害结果的出现,而是着重在行为的非价值判断上,以制裁手段恫吓、震慑带有社会风险的行为”[14]15。法益保护提前,使有害网络秩序安全的行为得到及早规制,避免了风险的升级变异,是应对网络犯罪行之有效的刑法措施。况且,网络犯罪危害甚大,影响深远,只有将风险抑制在萌芽状态,才能更好地起到以儆效尤的目的。如果等到危害结果显现,刑法再行介入,往往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因此即便法益保护提前可能危及人权,也应当为了维护更大的利益,而牺牲之。
法益保护提前论的反对者则认为,刑法不当以“未然之害”惩罚行为人,否则刑法必然嬗变为专横之法。“刑法是处罚人的法律。处罚人,必须有某种理由,必须有某人作了足以受罚的坏事的事实”[15]1。然而,何种行为可能危及网络安全,并不具有确定性。如果法益保护提前,必然赋予公权决断风险的权力,此时公权力会从效率的角度而非人权的视角考量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同时,公权力也没有主动发展网络技术、保障网络安全的义务。如果刑法规制可以达到效果,又何必劳神费力地发展网络防控技术呢?此外,法益保护的界限何在、何时介入,也并未明示,导致法益保护提前成为惩治网络犯罪的万能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犯罪旨在风险管控,秩序保障的目的不能成为法益保护提前的借口,而唯有对主观罪过,人权保障才是网络犯罪的实质所归。
(五)网络犯罪的视域:虚拟之物与实然之物的徘徊
虚拟之物可否成为犯罪对象,是网络犯罪成否的关键所在,也是争论各方僵持不下之处。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如何处罚虚拟之物的犯罪。持虚拟之物可以进入刑法视域者认为,虚拟之物和现实之物都是行为人实际管控之物。行为人窃取或破坏虚拟之物就等同于破坏现实之物,只要虚拟之物存在交换价值,可以在网络流通,行为人窃取的就不是无用的数码,而是能够从中获益的财物,其与现实之物并无差异⑩。同样,在虚拟空间发表言论,虽然面对的是电脑,但是汇聚的却是不同电脑前的个人,其诽谤信息的发布与公共场所当众谩骂、诋毁别无二致,因此虚拟空间可以扩张为公共空间,虚拟财物可以扩张为现实财产。毋庸讳言,“虚拟犯罪在本质上或效果上相当于现实中存在的犯罪,尽管它并没有现实发生,或者不具备现实的形式或名称。……这种‘犯罪’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真实的心理上的、社会意义上的以及金钱方面的损害,并且,它们还可能严重违背了人们对行为的合理、明智的预期”[16]。但是,阙如刑法规定始终是网络犯罪对虚拟之物规制的软肋。对此,部分学者纷纷主张仿效韩国、日本、瑞士以及台湾地区,明确虚拟之物的价值并予以刑法规制[17]。
反对虚拟之物进入网络犯罪视域的最有力论据是,虚拟之物不是刑法明确规定的现实财物和公共空间,比照传统犯罪定罪入刑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存在类推之嫌。这一论点的致命缺陷在于,一旦刑法明确规定虚拟之物的刑法地位,罪刑法定就不再是遭致非难的污点,而是大加申彰的亮点。对此,反对者也许会批驳,无论刑法对虚拟之物如何规定,如果虚拟之物无法产生现实的财物价值、空间效应,则虚拟之物即便有刑法的明确定性,也无法改变其无价值的事实,实难定罪量刑。如同盗窃无价值和轻微价值之物一样,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构成盗窃罪[18]154。
综上,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关系在秩序与人权的选择、主观罪过的定性作用、法益保护提前的利弊以及虚拟之物的刑法地位上各执己见,伯仲难分,极大地阻碍了网络犯罪的规制进程,亟待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合理应对。
三柳暗花明:刑法不得已原则之于网络犯罪刑罚边界的指引
网络犯罪在人权与秩序、主观和客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口诛笔伐,旨在达成网络犯罪的刑罚边界共识,寻求网络犯罪的正当性处罚根据。然而,由于刑法法条的抽象性,纯粹从刑法文本探求网络犯罪的刑罚边界困难重重,借助基本原则又因罪刑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以及罪刑均衡之法依附刑法文本,而难言实质性突破。有鉴于此,破解纷繁复杂的网络犯罪争议焦点,厘清网络犯罪的模糊边界,必须在揭示刑罚本质和犯罪本质的基础上,明确刑法当为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推演不得已原则。
(一)刑法不得已原则的推演
刑法的基本原则作为刑法基础性、本源性的价值原则,应当明晰刑法为何物,缘何当处刑罚。传统刑法之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罪刑均衡原则对此问题均未指涉,这些基本原则过于强调对刑法文本的绝对遵崇,至于缘何纳入刑法考量则在所不问,导致网络犯罪在适用基本原则时无所适从,且陷入寻求专门立法以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误区。而刑法不得已原则从刑法的概念入手,剖析刑罚的本质和犯罪的本质,探求刑法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实质意蕴,洞彻刑法“紧急避险”的不得已抉择,能够破解以往网络犯罪刑罚边界的争议焦点,使传统刑法从容应对网络犯罪。
刑法是规定犯罪认定和刑罚适用的标准,既包括犯罪也包括刑罚,是在犯罪的基础上定罪量刑。刑法以惩罚犯罪为内容,是一种强制惩戒措施,同时刑法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9]60。因此,刑法的本质也应当从社会关系中考量。刑法的一端是掌握刑罚权的国家,另一端是任何一个因犯罪就会受到刑罚处罚的公民个人,即刑法的本质表现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刑法是国家动用全部的暴力工具对个人实施的惩戒,因此又是整体的国家和孤立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国家动用刑罚,其意旨在于通过公民个人基本人权的剥夺保障国家基本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必然反映为国家的法律制度与个人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20]29-31。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从形式上看是为了保护国家的法律秩序正常运行,而基本法律秩序是个人基本人权的凝结,反映着公众人权的预期,每个人都有权过自由而有秩序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刑罚权的实质根据是为了保护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人权。剥夺犯罪人的基本人权,是为了保障全体公民的人权;对犯罪人实施强力惩戒,也是为了制止对全体公民人权的已然之害,防止未然之害。惩罚与预防仅仅只是一种手段,保障人权才是终极目的。

我们毋要忘记的是,“刑罚并非万能的惩戒工具,而是不得已的社会统治手段”[22]44。刑罚应当在纷繁复杂的基本人权之间做出权衡,在侵害人权大于犯罪人基本人权的范围内实施刑罚惩戒。刑法不得已原则揭示了刑法不到不得已不能用,到了不得已必须用的实质内涵。其理论层面以现有的法律是否能够有效调整,以及不予刑法调整是否会崩溃作为刑法启动的充要条件,确保刑法适用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在实践层面,不得已原则以刑法处罚是否会对行为造成褒奖,以及刑法处罚是否会引起普遍同情,动态测量刑法的适正性。刑法不得已原则直指刑法的边界,涵摄具体的适用标准,对网络犯罪的刑罚界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刑法不得已原则之于网络犯罪聚讼焦点的合理应对
刑法不得已原则以保障人权为圭臬,坚守行为主观方面对犯罪认定的核心作用,强调全体公民人权和公民个人基本人权的合法性,并从两者的权衡中明确刑法的合理界限,揭示刑法的当为内容,破解了网络犯罪有别于传统犯罪的谎言。从刑法不得已原则的内涵及其理论和实践标准能够合理应对网络犯罪的聚讼焦点,清楚界分网络犯罪的刑罚边界。
1.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同宗同源
网络犯罪是犯罪的一种,其罪与非罪应当接受不得已原则的检视,而不能以网络犯罪隶属于风险刑法就恣意脱离不得已原则的管控。事实上,风险刑法只是学术界的一种称谓,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专有产物,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存在不同的社会风险,如果一律以风险刑法论之,历史上的风险刑法将不胜枚举。此外,风险刑法并非传统刑法的例外,其并不能改变自身的刑法本质属性,因此妄图将风险刑法从传统刑法中孤立出来自成体系,无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神话。从这个层面上说,网络犯罪无论从风险刑法之基,还是从刑法本质之源,都与传统犯罪属于同宗同源,均可运用传统犯罪加以解决,而无需专门立法。网络犯罪利用网络作为工具或者手段亦或场所,只是网络犯罪的表相。毋庸置疑,“网络虽然增加了人的认知范围和活动领域,但网络空间的利益多数仍是现实空间中利益的延伸,差别只在于表现形式不同。同样,相当多的网络犯罪虽然表现方式比较新颖,但是其法益内容与传统犯罪并没有差别”[2]120。因此在实践中,我们应当从表相探究实质,从现实世界与网络信息的关联,洞悉行为主体对特定人或物存在状态的控制过程[23],并在此基础上比对传统犯罪,搜寻网络犯罪在传统犯罪中的原型。同时,这种比对与搜寻并非不加约束的随意,而是不得已原则之下的考量。此种情况下,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罅隙和隔阂必然在不得已原则面前消失殆尽,根本不存在适用上的难题。
2.网络犯罪的应对旨在人权保障
不得已原则是全体公民人权和公民个人基本人权之间的紧急避险,强调刑法的目的意在保障人权,而非秩序维护。网络犯罪借助网络信息实现危害社会之目的,在本质上是对人权的侵害,只有在其行为现实地危及到全体公民人权之时,才能动用刑法剥夺犯罪人的基本人权。在此界限之前,行为人的行为由于并无侵害全体公民人权之虞,不当以刑法规制。如果仅仅是个人对个人的现实侵害,则只需民法调整足以应对;如果行为超越个人人权的侵害范畴,但又明显不及全体公民人权,此时刑法规制悖离公众情感,人们会感到普遍同情,予以民法调整,又会使行为人在不法行为中获利,则可考虑在行政法中进行规制。在网络犯罪的应对中,我们必须坚守以人权保障为本位的刑法立场[12]242-243,并一以贯之。强调人权保障,舍弃秩序,可能遭致秩序不保、人权安在的质疑。不可否认,人权与秩序有相通之处,保障人权的秩序是应当维护的,以秩序之名推行强权统治则是应当贬抑的。坚持网络犯罪的应对目的是保障人权,就是为了避免强权秩序对人权的肆意践踏,使刑法严格遵崇公众意志。事实上,僭越人权界限的网络秩序维护,除了限制公民自由,让人们三缄其口之外,并无任何积极作用,反倒会阻碍公众合理意愿的表达,使网络犯罪之规制在人权保障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3.主观罪过的内容及其实现程度决定网络犯罪的性质及其形态
网络犯罪惩罚的是行为人,而不是行为,应当基于主观罪过的考量。如果行为人没有主观罪过,仅有客观危害,则与意外事件无异,不当以网络犯罪定罪量刑。行为不等同于客观危害,而是主观罪过支配的客观结果,是主体控制或者应该控制的客观条件作用于一定的人和物的存在状态的过程。意志贯穿行为的始终,客观危害是主观意志的支配结果,为证明主观罪过服务,主观方面是客观危害得以生发的动力,是犯罪认定的核心。因此,脱离主观方面,从客观危害考量网络犯罪,必然陷入客观主义的漩涡,极易导致一些没有主观罪过的行为不当入刑。以往网络犯罪之刑罚边界在主观罪过和客观危害之间争论不休,就在于没有清楚界定行为概念,把主观罪过和客观危害看成是油水分离之物,毫无关系可言,导致客观危害成为网络犯罪的评价中心。“刑法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刑罚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24]42。对于没有主观罪过的客观危害,无论其后果如何严重,都不可能再次发生,实无惩戒和规制的必要。一言以蔽之,刑法之所以对某一网络行为实施惩戒,只能基于行为人对刑法所保护利益相对立的敌视、蔑视和漠视的态度,舍此别无其他。此外,对网络犯罪形态的判定也应当以主观罪过为据,从其实现程度考量。如果行为人对某一网络危害结果具有主观罪过,但由于意志之外的原因没有实现,则应当以未遂论处。事实上,主观罪过,而非客观危害,才是规避风险、抑制风险的源头治理,从而使刑法成为导引人们网络生活良善的行为规范。
4.法益保护提前有害人权保障
不得已原则强调刑法当用则用,不当用则不用,明确刑法适用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其用与不用的权力在民众。就网络犯罪而言,只有网络有害行为已经危及全体公民人权,且不予规制将造成相应的法律制度必然崩溃的情况下才能适用。而法益保护提前是指行为尚未发生现实危害,但是继续发展有危及全体公民人权、造成重大危害之虞,为避免危害结果发生以及重大风险的来临,刑法提前进行防卫。按照行为的发展进程,法益保护提前的行为并不必然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行为人也不一定有追求危害结果发生的主观罪过,刑法提前防卫仅仅是国家单方面的风险评判,是越俎代庖动用刑法规制的结果。肯定法益保护提前,相当于是舍弃民众决断网络犯罪刑罚边界的权力,将人权的处置大权交予国家。此时,网络犯罪的适正脱离了民众意愿的左右,而如脱缰野马一般任由国家一意独断何种行为可能危及全体公民人权,刑法何时应当提前介入。问题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25]105。刑法主权在君的法益保护提前,必然陷公民人权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因此,网络犯罪不应当有别传统犯罪,更不应当法益保护提前。网络犯罪的规制,只能基于主观罪过的内容及其实现程度。脱离这一点,任何看似无可辩驳的法益保护提前,都可能嬗演为人权保障的羁绊。
5.具有现实价值的虚拟之物当属网络犯罪的视域
刑法不得已原则阐扬刑法人权保障的终极目标,认为刑法是在全体公民人权和公民个人基本人权两种都需要保护的权利之间,不得已做出的牺牲公民个人人权保障全体公民人权的做法。虚拟之物能否进入网络犯罪的视域,其主要评价不是虚拟之物本身,而在于虚拟之物对全体公民人权是否会造成现实之害,且如果不予刑法调整,现有的法律制度是否会崩溃。盗窃虚拟财产,如果能够对受害人产生现实的价值,且不予规制,对行为将是一种褒奖,必然鼓励他人踊跃效仿,则盗窃虚拟之物从侵害被害人的个人人权嬗演为侵害全体公民的人权,此时虚拟之物能够产生现实的价值,应当进入网络犯罪的调整视域。同样,虚拟公共空间也应当在达致与现实空间同等效果时予以定罪量刑。虚拟之物与现实之物的对接,涉及的最大问题就是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存在扩张解释之嫌。笔者认为,刑法不得已原则是对刑法当为内容的揭示,对刑法边界的确凿定性,具有统领罪刑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刑均衡原则的作用。罪刑法定之法是遵循刑法不得已原则之法,旨在全体公民人权和公民个人基本人权之间的不得已权衡。就此而言,罪刑法定并非单纯的文本依附,而是受制于不得已原则,符合公众意愿,得到公众认同的应然之法。在不得已原则的指引之下,虚拟之物依据主观罪过定罪入刑,不仅不是对罪刑法定的悖离,反而是罪刑法定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力学笃行:刑法不得已原则之于网络犯罪刑罚边界的实践展开
刑法不得已原则以常识、常理、常情为据,基于民众视角剖析刑法当为的内容,其不到不得已不能用,到了不得已必须用,深刻揭示了刑罚权发动的根据,在网络犯罪之刑罚界分上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刑法不得已原则不仅是一种基本原则,对刑法有统领作用,能够在规则不甚明确时进行宏观指导,亦能在微观上以不得已原则之理论标准和实践标准进行准确定位,使不得已原则不再停留于宏大的空洞见解,而是有具体标准支撑的原则指导。刑法不得已原则在理论层面以其他法律是否能够有效调整,以及如果不予刑罚调整,相应的法律制度是否会崩溃,直指刑法的边界。在实践层面,刑法界限的恰致又通过民众的情感意愿进行测量,防止其偏离公众认同的轨道。刑法的处罚不当让人们感觉普遍同情,也不当让人们觉得是种褒奖,看似简单朴素,实则清晰通透,在应对网络犯罪之刑罚边界上大有可为。同时,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虽然同宗同源,但是在危害程度上仍然存在细微差别。网络犯罪的非暴力性、非直接性,与传统犯罪之暴力性和直接性形成鲜明对比,若比照传统犯罪科予同样的刑罚,可能招致民众普遍的同情。此时,运用不得已原则,在准确知悉民众意愿的刑罚量上选择相应的罪名进行以刑制罪,不失为坚持刑法不得已原则的一种较为行之有效的措施。事实上,普通大众很少单独注意罪名正确与否,他们往往直接根据危害性判断刑罚量,进而以量刑是否公正,来评价判决是否合理[26]。有鉴于此,我们应该改变网络犯罪中唯定罪论的传统做法,在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传统犯罪中游离穿梭,实现不得已原则之下的以刑定罪。
(一)罪过定性:网络犯罪之罪与非罪的不得已界分
网络犯罪之罪与非罪的界分,主要取决于行为人主观罪过的内容及其实现程度。首先,网络犯罪必须考量行为人主观罪过的内容,在行为人侵犯了其他法律不能保护的利益,且行为人对刑法所保护的利益有敌视、蔑视或漠视的人格态度时予以入罪。如果行为人欠缺主观罪过,客观危害是意外所致,与行为人毫无关联,则无论造成多大的危害后果,都因为缺乏主观罪过,而不能纳入网络犯罪的范畴。其次,网络犯罪需要考虑主观罪过的实现程度。网络犯罪的入罪,既有质的定性,亦有量的考量。行为人主观罪过的实现程度必须达到危害全体公民人权的量,且不用刑法规制,相应的法律制度将难以为继,才能动用刑法。如果他法还能展现生机与活力,则刑法没有介入的必要。最后,网络犯罪的定罪入刑,必须得到公众的认同,在契合民众意愿的基础上实施。刑法是公众意愿的代表,网络犯罪亦不例外。从主权在民的视角,网络犯罪的规制既不能过于严苛,以致人们对网络犯罪报以深深同情,同时不予刑法处罚,也不能是对行为的褒奖,否则人人必将竞相为之。一言以蔽之,网络犯罪若能恪守不得已原则,坚持主观罪过对网络犯罪认定的核心作用,必然能够在网络犯罪之罪与非罪的界分上了然如斯。同时,不得已原则的坚持也有利于共识的达成,避免网络犯罪同一行为分属刑民两界调整的乱象频发。刑法不得已原则在网络犯罪刑罚边界的严格操守,可通过刑法与他法虚拟之物的区分赋值,轻微网络犯罪案件的刑事和解,改变刑罚的同情趋向,消减行为的褒奖获利。
1.虚拟之物之于网络犯罪与他法界限的区分赋值
对于刑法调整会遭致普遍同情,但网络行为又确实对他人造成侵害的,一般应当纳入民法或行政法调整。不过,对于虚拟之物的认定应当比刑法更为严格,以此改变行为人的行为支付,防止行为人接受民法或者行政法规制获利。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不具有惩罚性,旨在恢复受损的社会关系,民法裁量中被侵害人都不应当从判决中获利。因此对虚拟财物的数额应当按实然价值进行计算,以实际使用的数额为准,如果被侵害人实际损失大于实然使用数额的,按照实际损失计算。倘若此种规制,仍然使行为人获利,长此以往,民法所保护的利益将陷入崩溃的境地,那么则可以介入行政法调整。行政法兼有限制人身自由和行政惩罚的功能,能够在利益衡平时进行微小调整,以此改变行为人的收益。具体而言,行政处罚可以在考量行为人在民法中支付收益的基础上,在虚拟财产的实然价值和应然价值之间确定数额。同时,被害人不能在行政处罚中获利,因此其赔偿数额依然是虚拟之物的实然价值或实际损失,超出部分的数额,应当纳入行政处罚,收归国库。倘若财物处罚仍然不能改变行为人的获利状态,行政法尚有最多剥夺公民20天人身自由的权限,可以酌情判决,以此进行利益平衡。虚拟空间的判断,同样依此类推。
在网络犯罪罪与非罪界分明确的情况下,网络犯罪虚拟之物的赋值应当严格于民法和行政法。网络犯罪惩罚的是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只能根据行为人追求的实然价值定罪科刑,而不能在实际损失大于实然价值之时根据虚拟之物的实际损失认定。网络犯罪的惩戒立基于虚拟之物的价值和影响之上,是定罪科刑的承载基础,理应依托行为人主观罪过的内容及其实现程度,否则脱离公众预期的惩罚,必然使人们心生同情。同时,网络犯罪的刑罚科予本身就是一种大于犯罪得益的惩罚,且其程度明显严格于行政处罚,因此无需通过提高虚拟之物的赋值继续加重行为人的刑罚处遇。此外,网络犯罪还应当考量传统犯罪与网络犯罪在犯罪形态上的差别,防止悖离刑法不得已原则,一律按照既遂认定,且虚拟之物的价值与影响认定应当与民法和行政法有所区分。如虚拟财产的盗窃和现实世界的盗窃的犯罪形态就不尽相同。现实世界的盗窃通常以实际窃取财物时作为犯罪的既遂,而虚拟财物的网络盗窃应当以实际使用时为既遂。虚拟之物虽然可以和现实之物产生同样的价值,但是却有一个转换过程,只能在转换成功之后定既遂。虚拟之物窃取成功后,未使用前仍然是一堆无用的数码。在此期间,被害人修改程序密码或者行为人自愿毁弃,虚拟财物都不能产生现实财物的价值,被害人亦不受损失,因此虚拟财产在未使用前,其管控权并不在行为人之手,应当以未遂论处。对于虚拟空间的问题,同样也以行为人在该虚拟空间的言论是否会造成现实公共秩序的混乱,或者对他人造成实质性的诽谤影响为基础。事实上,信息发布之初,在线浏览人数不一定达致一定数额,难以和公众场所相提并论。即便达到与公共场所相当的浏览人数,也未必人人都相信信息内容,倘若确信信息的人数不能达致与公共场所相当的人数,且造成公共秩序的现实混乱,则行为就处于未遂的犯罪阶段。反之,如果网络信息的发布达致与扰乱公共秩序相当的结果,则成立既遂。
由此可见,虚拟之物在刑法和他法之间数额和程度的区分赋值,可以确保刑法边界的不得已界分,是对人权保障的终极坚守。
2.刑事和解之于网络犯罪与他法界限的和缓应对

刑事和解中,加害人通过真诚忏悔、积极赔偿以获得受害人的原谅,司法机关据此不予起诉或者减轻处罚;受害人也可通过加害人的道歉抚平心理创伤,获得物质赔偿,恢复受损社会关系。刑事和解真实地反映了公众,特别是受害人对案件刑罚趋向的真实意愿,是不得已原则在刑法边界上的实践考量,对于非暴力性的网络犯罪有广而推之的必要性。然而我国对刑事和解的范围规定过窄,大部分网络犯罪都无法进入刑事和解程序,导致行政法一旦无法调整,就必然接受刑法的强制惩戒,且无任何回旋的余地。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可以刑事和解。利用网络转发微博的行为纳入的是寻衅滋事罪,根本无法适用刑事和解,故犯罪一旦定性,公众就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和主张。此外,《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破坏计算机信息罪,由于属于《刑法》第六章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亦无法纳入刑事和解的范畴。然则,网络犯罪属于非暴力犯罪,行为者大多出于好奇猎艳而为,较传统犯罪之血腥暴力更为轻微,民众也多出于同情而希望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因此将网络犯罪纳入刑事和解的范畴较为符合公众预期。同时,网络犯罪之刑事和解的设定,也有利于刑法与他法之间的和缓对接,防止刑法适用让民众感到普遍的同情。网络犯罪应当给予网络失足青年更多改过的机会,避免一律入刑之“一棒子打死”的做法。沉迷网络,在虚幻世界难以自拔的,通常都是青少年,他们对网络未知世界充满好奇,并大胆涉足,殊不知一不小心就触碰了刑法的底限,必然面对犯罪的标签和苦涩的监禁。从常识、常理、常情来看,给这些网络失足青年一个免予入刑的机会,是公众的意愿所在。“浪子回头金不换”,如果刑法的宽宥能够感化失足网络青年,给予其免刑的空间又未尝不可。刑法不是要制造更多的犯罪者,而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安宁。我国台湾地区为避免青少年网络犯罪的入罪增多,就将盗窃游戏币的盗窃行为改为了“告诉乃论”,即自诉案件[27]。笔者认为,在青少年网络犯罪问题上采取公诉转自诉的办法,是回拉青少年的不错尝试,应当予以积极推行。对于一些学者认为网络犯罪查证困难,应当从自诉转公诉的观点[28],实难认同。此外,对青少年犯罪免予起诉,刑事诉讼法做了大胆尝试,但是范围仍然较为狭窄,难以实现有效减少青少年入罪的效果,应当予以相应拓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这一规定将不起诉严格限制在十八岁以下,难以把在校大学生匡入其中。而现实中,网络犯罪往往频发于大学生身上,这一阶段的大学生脱离家庭的管束,在网络世界流连忘返、沉醉其中,并在不良诱惑之下实施网络犯罪。从这个层面上说,网络犯罪以大学生身份为界执行不起诉的决定,较为符合刑法不得已原则。对不起诉规定之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的限制,也可适当拓宽至三年有期徒刑,这样侵入计算机数据罪、寻衅滋事罪都可纳入其中,从而给青少年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二)以刑制罪:刑法不得已原则在网络犯罪中的罪刑均衡
网络犯罪之刑罚边界不仅包括罪与非罪的不得已,还涵摄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适用的不得已。网络犯罪是传统犯罪在网络世界的展开,应当不加歧视地适用传统犯罪的罪名。但是,平面机械的网络世界与活色生香的现实世界仍然存在细微的差别,一律按传统犯罪入刑,有太过严苛之感。而刑法不得已原则的实践核心,既不能让人们感到普遍同情,又不当使刑罚适用成为一种褒奖。由此可见,恰致的刑量而非罪性才是认定网络犯罪的关键所在。具体而言,网络犯罪应当以刑制罪,在严格测量公众对网络有害行为刑罚量的意愿基础上,选择适当的罪名入罪。
1.不得已原则之网络犯罪以刑制罪的必要性
以刑制罪是指考察罪刑关系时不能囿于传统的由罪生刑模式,而是从刑罚必要性与妥当性的角度考察构成要件的选择,并最终影响行为的司法定性[26]167。网络犯罪在不得已纳入刑法考量的情况下,应先确定刑量,再确定罪名,确保刑罚轻重相当。刑事责任是刑法的核心,犯罪构成的认定最终需回归到刑事责任。对罪犯、受害人、社会公众而言,最根本的问题是:到底对罪犯进行了什么程度的评价(刑罚量)、而非适用了什么犯罪构成(罪名)[29]。
网络犯罪是一种新兴的犯罪形式,具有针对性的罪名仅在《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二百八十六条专门体现,但是对于具体的情节仍然规定得不甚清楚。如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强调犯罪构成中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的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且后果严重。但是,网络犯罪都是以计算机网络为工具、为手段、为空间,必然涉及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破坏问题,因此均可纳入此条调整,无怪乎学界也把此条看做是网络犯罪的“口袋罪名”。同时,网络犯罪也属于传统犯罪,其通过网络世界对现实生活产生的危害影响与传统犯罪相当,同样可以纳入传统犯罪论处。这就在适用传统犯罪条款亦或专门网络犯罪条款之间产生了矛盾,且适用专门网络犯罪条款和传统犯罪条款,其刑罚量并不完全同一,有的甚至存在霄壤之别。如盗窃游戏币之行为,入罪盗窃,最多可获无期,入罪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最高刑七年,而入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最高刑只有五年。由此可见,定罪对量刑的影响何等深远。实际上,在随意的罪名标准前,追求精确定罪乃是作茧自缚[26]167。有鉴于此,在网络犯罪的罪名边界上,我们需要从量刑妥当性的基点出发,反过来考虑与我们裁量的相对妥当的与刑罚相适应的构成要件是哪个,从而反过头来考虑该定什么罪[30]。
2.不得已原则之网络犯罪以刑制罪的实践展开
网络犯罪以刑制罪的关键在于确定量刑,以此确保罪名适用的正当性。如何确定量刑,笔者认为,应当基于公众意愿,在常识、常理、常情之下考量。事实上,常识、常理、常情是公民意志的最基本反映,是公民普适价值观的积淀,能够真实反映大众情感的趋向[31]。首先,决定刑罚量的主体是民众,公权力机关不能以个人意愿或者以对刑法文本的立法原意解读进行刑罚量的认定。刑罚权必须牢牢管控于民众之手,否则网络犯罪的规制必然成为立法者的恣意、司法者的滥权。如果刑法来自于罪刑法定,公权力机关完全可以借助文本,以风险之名限制公民自由,管控社会生活。从这个层面上说,决定刑罚量的主体只能是民众,否则以刑制罪必然成为刑法恣意的工具。其次,司法机关立基于民众视角,以常识、常理、常情确定网络犯罪行为的刑罚量。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中确定网络犯罪的刑量,通常需要知晓普通民众对此种网络行为的预判刑期。而普通民众对刑法的认知是一种经验性和习惯性,是基于常识、常理、常情之下的一种为大众所接受和认可的是非观、善恶观、价值观判断。司法机关要准确测量公众对网络犯罪行为的刑罚量,只能站在公众的视角,按照常识、常理、常情进行判断。最后,司法机关基于常识、常理、常情所得刑罚量必须能够经受不得已原则的检验,保证网络犯罪的刑罚量与公众意愿的严格趋同。即判决此刑罚量不会让人们对网络犯罪者感到普遍同情:如此轻微,何须重刑。同时,又不能让民众觉得判决此种刑罚量是一种褒奖:何等严重,奈何轻刑。如前述南京嵌入木马程序窃取游戏币的案件,行为人纠集多人组成研发、销售一条龙链条,其窃取他人财物的主观罪过展露无疑。入刑非法侵入计算机罪明显牵强附会,且与传统盗窃之刑量相差甚远,民众有刑罚过轻之感,应当在与传统盗窃相当的刑罚量内制刑。相反,对于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为满足自己在游戏世界中虚拟英雄的角色而窃取游戏币疯狂消费的行为,则不宜以盗窃的刑量计算。此时,失足网络青年是在游戏开发者的诱惑下实施犯罪[27]94,被害者有严重过错,入刑盗窃让人们感觉普遍同情,可以在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刑量或者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刑量范围考量,若太过轻微也可做无罪处理,并转由行政处罚。由此可见,不得已原则对刑罚量的严格测量,能够有效确保网络犯罪之司法过程对公众意愿的严格遵崇。
以刑制罪在刑量既定的基础上,比照与刑量相当的罪名入罪。这种比对并非类推,而应当在相似罪名之间进行,如果罪名间根本无相似性,危害后果和行为方式无可比性,则不能更换罪名[26]171。如新招电器工程师,拷贝电器设备程序,更改设备密码后失联,导致电器设备退货。假若公众意愿之刑量是三年有期徒刑,那么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破坏生产经营罪都是适合的,且两罪都是相似罪名。该案中行为人毁坏电器设备信息系统,使其陷入瘫痪之中,符合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犯罪构成。同时,行为人修改电器设备信息系统密码的行为,使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电器设备不能正常运行,阻滞了生产经营,无疑也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犯罪构成。适用何种罪名,则需从最为接近网络犯罪真实本相处入手。修改电器设备密码是为了破坏生产经营服务,因此,破坏生产经营才是行为人主观罪过的内容,应当以破坏生产经营罪论处。同时,以刑制罪需要考虑民众对此等网络犯罪是否有宽恕的意愿,以此确定定罪时是否需要创设刑事和解的机会。上例中青少年沉迷网络,窃取游戏币之案件,公众多有轻饶或宽恕之愿望,脱逸盗窃重罪之刑后,应当在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之间选择适用。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刑法》第六章的内容,入罪不能进行刑事和解。而故意毁坏财物罪是《刑法》第五章的内容,能够纳入刑事和解的范畴。此时,若失足网络青年能够积极赔偿、真诚悔过,则达成和解后不予刑法调整也是众望所归。毋庸置疑,以刑制罪确保了网络犯罪之刑罚边界对公众意愿的实时跟进,是刑法不得已原则在网络犯罪中的具体运用。
五合于民心:刑法不得已原则之于网络犯罪刑罚边界的意义
网络技术的蓬勃发展,继而繁荣昌盛,在极大便利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成为滋生网络犯罪的温床,对传统刑法提出挑战。网络犯罪借助网络、计算机信息数据实施,承基于虚拟世界,作用于虚拟之物,与传统刑法之直观性、现实性形成鲜明对比,难以在刑法法条未见踪迹的情况下定罪科刑。借力刑法三大基本原则,又因罪刑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刑均衡依附刑法文本而难以突破法条的窠臼,无法在统御网络犯罪上有所作为,陷入网络犯罪恣意而为的定罪乱相之中,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毫无界限可言。
事实上,规则模糊、原则无力,使网络犯罪在传统与现代、人权与秩序、主观与客观之间游离徘徊,苦苦挣扎,却终难达成共识。而刑法不得已原则立基民众视角,依托常识、常理、常情,明晰刑法不到不得已不能用,到了不得已必须用之原则内涵,阐释刑法不得已原则牺牲犯罪人基本人权、保全全体公民人权之紧急避险的实质意蕴,揭示刑法乃公众意愿的代表,从而将三大基本原则严格遵崇之法纳入不得已原则范畴之下,使刑法基本原则不再停留于文本依附,而成为契合公众意愿的原则指导。我们毋忘记的是,“法律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意志的记录”[32]51。网络犯罪脱胎于传统犯罪,自然应当受制于公众意愿,严格遵循刑法不得已原则。同时,刑法不得已原则,从常识、常理、常情洞悉公众意愿,旨在高举人权保障的大旗,坚守主观罪过的底限,从而破解长期侵扰网络犯罪的聚讼焦点。
刑法不得已原则以公众意愿考量他法是否能够有效调整,以及不予刑法调整,相应的法律制度是否会崩溃,探寻区分赋值、刑事和解在网络犯罪罪与非罪和缓连接中的不得已运用。在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的科予上,不得已原则又以公众情感直观测量刑量,并在相应的罪名之间以刑制罪,确保网络犯罪刑罚边界之适正性。毋庸置疑,刑法不得已原则从刑法当为的内容探究刑法适用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具有合于人心、顺乎民意的内在乾坤,在网络犯罪之宏观指导和微观调整上卓具成效,予以大加申彰,必然裨益于网络犯罪之刑罚边界的界分。
(特别说明: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重庆大学法学院陈忠林教授、扬州大学法学院马荣春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感谢!当然,本文文责自负。)
注释:
①三网融合,通常是指以电话网为代表的电信网、以有线电视为代表的广播电视网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计算机通信网三大网络,通过技术改造,使其技术功能趋于一致、业务范围趋于相同,网络互联互通、资源共享,能为用户提供语音、数据、图像等综合性的多媒体业务。参见:于志刚《三网融合视野下刑事立法的调整方向》,载《法学论坛》2012年第4期。
②传统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为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均衡原则,原则之间呈并列关系。参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杨春洗、杨敦先等著《中国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0页。
③无限扩张论者认为,刑法意在对社会秩序的保障,因此只要有碍社会秩序的行为都应当予以规制,此观点发端于风险刑法,有无限扩张刑法视域之嫌。极力限缩的观点则认为,刑法需要严格遵循罪刑法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某些网络犯罪因为缺少相应的刑法条文,而不予刑法规制,刑法被机械地限缩于刑法文本之中,而无法展现其灵活性。参见:郑泽善《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90-91页。
④从司法实践看,目前公安机关已经普遍办理过侵犯虚拟财产的案件,但能够成功进入诉讼程序的只是极少数,在大部分情况下,当被害者以侵害虚拟财物为由申请立案时,一般会被告知:因无法律依据,虚拟财产被盗不能够成为刑事案件。参见:郑泽善《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93页。
⑤2013年9月5日“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寻衅滋事犯罪的认定问题,该解释认为网络空间中也存在公共场所,从而将原本适用于现实空间中的寻衅滋事罪同步移植到网络空间中,这几乎颠覆了很多人的传统认识,在刑法理论界引起了较大争论。参见:孙万怀、卢恒飞《刑法应当理性应对网络谣言——对网络谣言司法解释的实证评估》,载《法学》2013年第11期,第113页。
⑥例如南京嵌入木马盗窃网络游戏用户“游戏币”、“武器”等虚拟财产销售牟利案,被告周某、王某按照木马系列程序所针对的不同种类游戏,通过“总代理”及变卖游戏账号中的虚拟财产,非法获利160万元及1010.32万元。2009年6月,法院审理后,认定周某、王某等人均犯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罪,判处主犯周某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10万元。参见:宁剑《网络黑客“大小姐”背后的产业链揭秘》,载《法制与新闻》2009年9月23日版。
⑦例如金华凤凰游戏山庄账号被盗案,犯罪嫌疑人自称美女与受害人聊天,进而通过发照片发送带木马程序的压缩文件,从而控制对方的电脑,盗取对方的游戏帐号、密码,提取30多亿两“银子”,总计价值20多万元,金华警方提请金华市价格认证中心估价15万元,最终以盗窃罪入刑。参见:宁容《网络虚拟财产刑法保护研究》,南开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第48页。
⑧计算机网络系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牵连犯罪的情况,极有可能同时触犯盗窃罪(《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一款)、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三款)、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刑法》第二百八十九条)等。此时,处理的原则应是《刑法》有明文规定的,按照《刑法》规定实行数罪并罚和从一重罪处罚。参见:邹政《盗窃虚拟财产行为的刑法适用探讨——兼论虚拟财产价格的确定》,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5期,第74-75页。
⑨2013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向传统刑法的社会危害性理论提出了挑战。该解释第2条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
⑩使用盗窃的游戏货币可以在网络游戏世界获得愉悦,出售给他人则可获得一定的钱财,因此虚拟财物看似没有实际价值,实际上却可以通过交换或亲身体验获得利益。


参考文献:
[1]张智辉.网络犯罪:传统刑法面临的挑战[J].法学杂志,2014,(12).
[2]于志刚.网络“空间化”的时代演变与刑法对策[J].法学评论,2015,(2).
[3]耿冬旭.“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分析[J].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2014,(1).
[4]谢立功,徐国桢.犯罪学——当代各类犯罪分析[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
[5]于志刚.网络犯罪的代际演变与刑事立法理论之回应[J].青海社会科学,2014,(2).
[6]秦川.秦火火已熄火,反谣仍在路上[N].京华时报,2014-04-12.
[7]储槐植.理性与秩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8]姜涛.风险刑法的理论逻辑——兼及转型中国的路径选择[J].当代法学,2014,(1).
[9]〔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0]张智辉.试论网络犯罪的立法完善[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
[11]孙万怀,卢恒飞.刑法应当理性应对网络谣言——对网络谣言司法解释的实证评估[J].法学,2013,(11).
[12]刘长伟.论刑法立场在“风险社会”的坚守与超越[J].社会科学论坛,2014,(4).
[13]〔英〕马林诺夫斯基,塞林.犯罪:社会与文化[M].许章润,么志龙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4]林东茂.危险犯与经济刑法[M].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
[15]〔日〕西原春夫.刑法的根基与哲学[M].顾肖荣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6]LASTOWKA F G, HUNTER D. Virtual Crime[J]. Draft, July, 2004.
[17]赵秉志,阴建峰.侵犯虚拟财产的刑法规制研究[J].法律科学,2008,(4).
[18]〔日〕船山泰范.财物之意义[C]//西田典之.刑法的争论点.东京:有斐阁,2000.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陈忠林.刑法散得集(Ⅱ)[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
[21]马荣春.中国刑法的当下出路:“附势用术”[J].南昌大学学报,2013,(1).
[22]〔日〕平野龙一.刑法总论[M].东京:有斐阁,1972.
[23]陈忠林,徐文转.犯罪客观要件中“行为”的实质及认定[J].现代法学,2013,(5).
[24]〔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25]〔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26]高艳东.量刑与定罪互动论:为了量刑公正可变换罪名[J].现代法学,2009,(5).
[27]郑泽善.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5).
[28]赵远.“秦火火”网络造谣案的法理问题研析[J].法学,2014,(7).
[29]高艳东.从盗窃到侵占:许霆案的法律与规范分析[J].中外法学,2008,(3).
[30]梁根林.现代法治语境中的刑事政策[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4)
[31]童春荣.论刑民界限的公众认同[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32]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责任编辑:苏雪梅]
Cyber crime punishment border:
In the perspective of criminal law principle of necessity
TONG Chun-rong1, ZHAO Yu2
(1. Law Schoo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
2. The Central Institute for Correctional Police, Baoding, HeBei 071000, China)
Abstract:In the perspective of criminal law principle to the principle of people’s position as the position, with common sense, common sense, natural for content, emphasis on citizens’ human rights safeguard. So the criminal law principle of necessity from the criminal law should be some content trace on the border of network crime.The criminal law principle of necessity to reveal the subjective fault is the key to network crime into whether, the criminal law principle of necessity to reveal the network crime and traditional crime is the same. The criminal law principle of necessity of unified network crime of real consensus in order and human right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virtual and reality, harm and risk, the criminal law principle of necessity to the public will consider other laws can effectively adjust, and there is no criminal law adjustment, the corresponding legal system will be paralyzed, that seek assignment respectively,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in the network crime and crime is not a crime gentle connection to use. In the crime and he sin, and families to felony and misdemeanor, the criminal law principle of necessity use emotional direct measurement of punishment to the public, and to make in the corresponding charges between punishment against conviction, to ensure the legitimacy of cyber crime boundary.
Key words:cyber crime; the penalty boundary; the principle of necessity; subjective sin; charges changed for fair sentencing
作者简介:童春荣(1981—),女,四川峨眉人,重庆大学2013级刑法学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刑民界限新论——基于不得已原则视角”(CYB14025)。
收稿日期:2015-09-17
中图分类号:DF6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1-003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