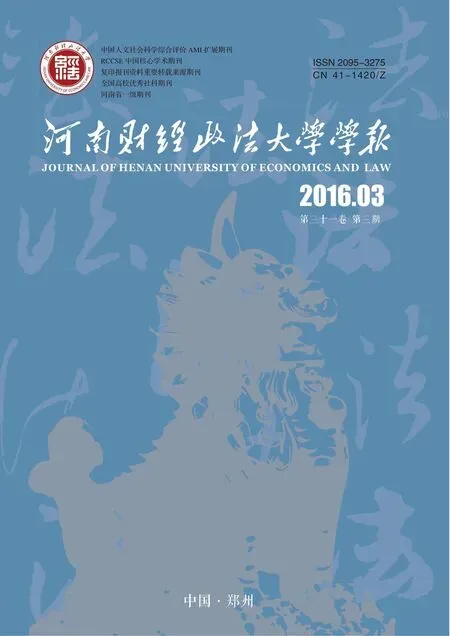论股东派生诉讼调解的公司法规制
王长华 张思宇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河南郑州 450046;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 )
论股东派生诉讼调解的公司法规制
王长华张思宇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河南郑州 450046;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 )
原告股东的派生诉权尽管也具有启动诉讼、维持诉讼进行的功能,但其毕竟派生于公司的诉权,因此原告股东在诉讼中的处分权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对于股东派生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有限责任公司和非公众股份有限公司应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众公司应由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股东派生诉讼的特殊性决定了派生诉讼调解的复杂性,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定难以满足制度供给的特殊需求,因此需要公司法对此做出特别规制。
股东派生诉讼;诉权;调解;公司法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原被告双方可以在诉讼中自行和解。然而,在股东派生诉讼中,原告是公司的股东,被告是侵犯公司利益之人,而真正的受害者——公司,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既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而是被列为第三人[]。简言之,股东派生诉讼的原告与被告所讼争的诉讼标的直接涉及的是公司的利益。由此,在股东派生诉讼中就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股东派生诉讼的原告和被告双方能自行和解吗?对此,我国《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出于诉讼经济和效率的考虑,股东派生诉讼中应当允许和解。但是,毕竟直接的利益受害者是公司而非原告股东,这就决定了股东派生诉讼的和解有其特殊之处,需要法律上予以特别规制。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的和解制度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和解制度不同,美国诉讼和解在法律效果上与我国的法院调解比较相似[]。然而,和解与调解这两个词语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有着类似的含义,并且在这些国家的司法中,和解与调解在交互使用[]。鉴于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是一项舶来品,学界在研究股东派生诉讼调解制度时有使用“和解”一词的,也有使用“调解”一词的。除非特别需要,本文在同一含义和同一问题指向上使用这两个术语。
关于股东派生诉讼中的调解(和解),目前我国司法实务界及理论界都认为应当给予一定的限制,但究竟应如何限制,目前尚无定论。司法实践中法院的裁判认为,调解协议不仅要经过诉讼各方一致同意,还必须经过提起股东派生诉讼的股东所在的公司和该公司未参与诉讼的其他股东同意后,人民法院才能最终确认该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二终字第123号民事调解书。。简言之,股东派生诉讼的调解须经公司及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法院系统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法院系统征求意见稿)》)第三十六条做了类似规定*《公司法司法解释四(法院系统征求意见稿)》第三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股东代表诉讼案件,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公司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调解协议。有限责任公司未召开股东会的,公司全体股东应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名、盖章或者向人民法院出具同意调解协议的书面意见。”。有学者认为,我国应尽快建立股东派生诉讼的司法审查制度,将司法审查权赋予法院,由其决定是否准许和解[]。但也有学者认为,法院不必作过多的审查,只要原告未从中渔利,协议基本公平,一般应予认可[]。还有学者认为,对于调解协议是否损害公司利益的问题,法院在审查中应交由公司来判断,即调解协议应当经过公司同意,法院才能确认[]。由此可见,对股东派生诉讼的调解进行一定的限制,这在我国已经达成了共识,但至于如何进行限制仍是人们争议的焦点。
任何法律制度的限制和规则设计,均导源于其内在的独特品性,股东派生诉讼调解制度也不例外。那么,股东派生诉讼内在的法律特性,是否足以支撑公司法就派生诉讼调解制度作出特别规制?若需要公司法对股东派生诉讼调解制度进行特别限制的话,该如何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本文拟对此展开论述,以期对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法律完善有所裨益。
二、原告股东诉权的特殊性
诉讼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自愿、平等地进行协商,以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也称为法院调解[]。关于诉讼调解的性质,通说是,审判权与处分权结合说。该说认为:诉讼调解是法院对民事案件行使审判权和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诉讼权利和民事权利行使处分权的结合[]。在诉讼调解过程中,尽管法院对调解的有序进行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当事人是否愿意调解以及调解协议的最终达成还是要以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为基础和前提的。正如有学者所言:“当事人同意接受法院的调解和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后达成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依据处分原则,对其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所作的处分。因此,法院调解的过程又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过程。”[]
既然诉讼调解的过程是当事人处分权行使的过程,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处分权行使的结果,那么,参与调解的当事人是否具有处分权,处分权是否完全就显得尤为关键。诚如有学者所言:“当事人对诉讼标的中的实体权利享有完全的实体处分权是当事人可以自由行使诉讼程序处分权的根本原因。”[]因此,若欲对股东派生诉讼调解作出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就必须首先搞清楚派生诉讼中的原告股东是否具有完全的处分权,其享有的诉权有何特殊之处。
(一)原告股东的诉权具有派生性
相较于一般民事诉讼,股东派生诉讼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原告股东诉权的派生性。在股东派生诉讼中,原告股东所享有的诉权是由公司的诉权派生而来的,并非其自身利益受损而直接享有的诉权。
就股东派生诉讼的法理基础而言,其核心问题是原告股东的诉权问题。因为民事诉讼作为对私权的公力救济,它是当事人的诉权与国家的审判权相互作用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而基于私权自治的原则,审判权的运作须基于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因此,欲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来寻求纷争解决或权利保障者,前提是须得享有诉权,否则将不能启动民事诉讼程序。显然,股东派生诉讼程序的启动,其前提也必须是原告股东享有诉权。正如前文所述[],在股东派生诉讼所讼争的纠纷中,公司是直接的受害者和诉权享有者,股东并不是直接的利害关系人,本来并不享有诉权,其诉权是法律在特定情形下由公司的诉权派生而来的。基于这种派生而来的诉权,股东获得了一种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限,据此,股东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启动民事诉讼程序。根据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诉权是起诉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诉权就没有诉讼。但有了诉权,也并不意味着民事诉讼程序的自动开启。诉权是一种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限,是实现实体权利的一种潜在的手段[]。诉权本身并不能引起诉讼的发生,只有当事人进行了诉讼上请求(起诉)才能引起诉讼的发生。
在股东派生诉讼所要解决的纠纷中,公司是利益的直接受害者,其实体权利遭到直接侵害,公司享有诉权,可以决定是否向法院提起诉讼。在民事诉讼中,诉权具有任意性,诉权的行使是由本人决定的,是否行使不是一种义务[]。在我国,公司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即取得独立法人资格,其行为活动不受他人的任意干涉。因此,公司作为诉权的享有者,原本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行使诉权,提起诉讼,但是,鉴于公司与股东之间特殊的股权关系,公司诉权的行使与否会极大地影响股东的利益。因此,出于利益平衡的考虑,法律将公司的诉权在特定情形下(公司怠于起诉时)赋予公司的股东。这样,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股东获得了一项由公司的诉权所派生(衍生)而来的诉权。据此,股东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作为原告)依法提起诉讼,启动民事诉讼程序,追究被告人的民事责任。原告股东诉权的这种派生性,是股东派生诉讼最为核心的特性,股东派生诉讼的相关制度设计都与此密切相关。
(二)原告股东的诉权仅具有程序内涵
相较于公司自己因利益受损而享有的直接诉权(也即一般民事诉讼中的诉权),原告股东在派生诉讼中所享有的诉权仅具有程序内涵而不具有实体内涵。根据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诉权不是抽象的权利,它包含着具体的程序内涵和具体的实体内涵。民事纠纷是有关民事权益的争议,与之相对应的是诉权的实体内涵;将民事纠纷引导到诉讼程序中则为诉权的程序功能”[]。诉权的实体内涵,是指原告提起诉讼欲获得的实体法上的具体法律效果或法律地位;程序内涵,是指在程序上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其目的在于启动诉讼程序。据此,人们习惯于将诉权分为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
纵观世界各地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立法或判例之所以赋予股东一项派生诉权,其主要目的在于让股东获得一种在特定情形下发动诉讼程序的资格。在股东派生诉讼中,原告股东与被告讼争的实体法律关系发生在公司与被告之间,而非原告股东与被告之间。换言之,公司是实体权利的享有者,被告直接侵犯的是公司的实体权利而非股东的实体权利。根据民事诉讼法的一般原理,公司享有直接的诉权,可依法直接对被告提起民事诉讼。然而,鉴于公司自己怠于诉讼,而这种怠诉行为又会间接侵犯股东的权利,在这种特殊情形下,各国法律普遍将公司的这种诉权赋予公司的股东。由此,股东获得了一项由公司的诉权所派生而来的诉权。
基于股东对这种派生诉权的行使(起诉),“不告不理”的诉讼程序随之启动,作为公权力的法院介入了当事人所诉争的民事私权纠纷(公司与被告人之间的纠纷),至此,基于诉权的“桥梁”作用,民事纠纷与诉讼程序得以有效连接。可见,在股东派生诉讼中,原告股东所享有的诉权乃程序意义上的诉权。至于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原告股东并不享有,而是仍由公司享有。对此最好的例证就是,各国普遍规定股东派生诉讼的胜诉判决利益归公司所有而非直接归原告股东所有,原告股东的诉讼请求只能是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向公司赔偿”。譬如《德国股份法》第148条第4款就明确规定,股东派生诉讼应以“向公司给付为目标”*参见《德国商事公司法》,胡晓静、杨代雄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43页。。综上,在股东派生诉讼中,原告股东的诉权仅具有启动诉讼程序、维持诉讼进行的程序内涵。
(三)股东派生诉讼调解的特殊性
综上所述,派生诉讼的原告股东对诉讼标的并不享有实体权利,其仅仅享有由公司诉权派生而来的诉权,并且这种派生诉权仅具有程序内涵而不具有实体内涵。原告股东派生诉权的这些特殊性,决定了股东派生诉讼调解的特殊性。概括地说,股东派生诉讼调解与一般民事诉讼调解主要存在以下不同之处:
其一,在一般民事诉讼调解中,双方当事人通常都是讼争法律纠纷的直接关系人,是实体权利义务的享有者,通常对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都享有完全的处分权。而在股东派生诉讼调解中,诚如上文所述,其中的一方当事人(原告股东)并非讼争纠纷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和实体权利义务的享有者,其享有的处分权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其二,在一般民事诉讼调解中,调解通常涉及的仅是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调解利益(犹如胜诉判决利益)通常也直接归属于原告。而在股东派生诉讼中,调解涉及的不仅仅是原被告之间的利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涉及原被告之外的第三方(公司)的利益。股东派生诉讼调解的调解利益,也并非直接归属于原告股东,而是归公司享有。
尽管股东与公司之间存在密切的股权关系,但二者在法律上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主体,二者的利益并非总具有一致性,实践中二者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形也数见不鲜。因此,如果允许股东派生诉讼的原被告像一般民事诉讼的原被告那样自行和解的话,极有可能发生原告股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而与被告串通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此外,股东派生诉讼调解的结果还与其他股东的利益密切相关,一旦允许原告股东未经其他股东同意而径行与被告自行和解,则其他股东的利益很难受到有效保护。简言之,股东派生诉讼的和解很有可能使公司利益或股东利益成为谋取某一方利益的牺牲品。鉴于此,世界各国在认可股东派生诉讼调解制度的同时,也对其设置了一定的限制。譬如《韩国商法典》第403条第6款规定,未经法院许可,股东派生诉讼的当事人不得进行和解*参见《韩国民商事法律汇编》,金万红、郑才荣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364页。。正如有学者所言:“从保护公司利益、提升诉讼效率的角度而言,应当准许诉讼当事人进行和解,但为了防止当事人之间的恶意串通,须就和解程序和和解效力加以规范、限制。”[]
综上所述,原告股东诉权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律有必要对派生诉讼调解作出特别的规制。在股东派生诉讼中,原告和被告不能像一般民事诉讼中的调解那样双方自行达成调解,而是还需受到其他主体的制约。鉴于股东派生诉讼调解的特殊性,《民事诉讼法》关于调解规则的一般规定难以满足股东派生诉讼调解制度供给的特殊需求,因此,作为股东派生诉讼特别法的《公司法》有必要对股东派生诉讼调解做出特别规制。
三、两种立法模式的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关于对股东派生诉讼调解的限制,世界上主要有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司法审查制,另一种是以意大利为代表的股东会决议制。
(一)股东派生诉讼调解的司法审查制
就股东诉讼调解制度而言,司法审查制特别强调法院对诉讼调解进程的控制,股东派生诉讼能否调解,关键在于法院是否同意。譬如《美国标准公司法》规定:“非经法院同意,派生程序不可以调解。”*参见《最新美国标准公司法》,沈四宝编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韩国商法典》也有类似规定*参见《韩国商法典》第403条第6款。。就股东派生诉讼的调解而言,美国法院改变了消极介入商事实践的司法传统,而是采取积极介入审查的立场。这是有现实背景的,因为在美国存在大量毫无意义的派生诉讼,原告的律师为了自己利益而促使调解,因此有必要对律师费等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同意派生诉讼的调解。这种模式对法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操守要求比较高,在判断股东派生诉讼的和解是否合理时,法院并没有任何单一的经验标准,而是要综合考虑诸如和解能否给公司带来净利益(包括金钱的和非金钱的利益)、原告在最好的情况下可能得到的补偿、继续进行诉讼的复杂性、费用及后续诉讼可能需要的时间、被告承受较(和解)重的判决的能力等因素[]。司法审查制的优点在于让法院把控诉讼调解的进程,防止公司利益受损。
但司法审查制模式也有诸多不足之处:其一,“强制性的审查程序势必会加重法院的工作负担,尤其是在决定和解当事人有无诈害公司权利之时,法院往往难以搜集证据材料、决定证据效力”[]。其二,法院对诉讼调解的审查同意或许可,有替代商业判断之嫌,毕竟股东和公司对商业经营和商业需求最为了解。既然如此,就应将派生诉讼调解的决定权交给公司和股东。其实,通过进一步分析美国股东派生诉讼的司法审查制度,我们不难发现:法院是否同意调解的关键仍在于对股东和公司利益的考量。譬如《美国标准公司法》第7.45条在规定调解需要法院同意的同时,该条还明确规定:“如果法院决定派生程序的停止或调解将实质性地影响公司股东或者某一类别股东的利益,则法院应指示向将受影响的股东发出通知。”*参见《最新美国标准公司法》,沈四宝编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显然,股东的利益成为美国法院是否同意派生诉讼调解的一个关键考虑因素。
如果说美国公司法关于股东意见在派生诉讼中的作用还不够直观的话,日本公司法的规定就非常直观明了。根据《日本公司法》第850条的规定,虽然法院在股东派生诉讼调解中也发挥重要作用,法院须对调解协议的内容向公司通知并催告其有权提出异议,但该条第3款明确规定,公司未在法定期间内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股东承认了”调解协议的内容*参见《最新日本公司法》,于敏、杨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58页。。如果在法定期间内提出了异议,那就不能进行和解,只能继续审判直至取得判决[]。可见,即使在司法审查制模式下,公司及股东的意见仍是股东派生诉讼调解中的关键考虑因素。
(二)股东派生诉讼调解的股东会决议制
相对于美、韩等国的股东派生诉讼调解司法审查制的复杂性,以意大利为代表的股东会决议制对派生诉讼调解的规制则显得非常简单明了。《意大利民法典》第2393条明确规定,股东派生诉讼的调解需要由股东会作出决议,并且股东会决议时持异议的股东的资本不得超过公司资本的1/5(在上市公司,则不得超过1/20)*参见《意大利民法典》,费安玲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5页。。相较于美国的司法审查制,意大利的这种股东会决议制立法模式具有更为明显的优点,值得我国参考借鉴:
其一,这种模式直接迎合了派生诉讼调解特殊性的要求。既然股东派生诉讼调解的特殊之处在于原告股东的处分权因涉及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而受限,那么解决问题的直接方法莫过于让公司和其他股东就诉讼调解事宜发表看法。因此,采取股东会这种会议体的方式,既实现了对公司意见的征询,某种程度上也实现了对其他股东意见的征询。
其二,这种模式不仅克服了司法审查干预商业判断、阻遏公司自治的弊端,而且充分尊重了公司和股东的商业决策判断。一项诉讼进行与否不仅涉及当事人的有形财产的得失,而且还影响到当事人的商誉、商业机会(比如上市融资)等无形财产的得失。在股东派生诉讼进行过程中,公司的一些商业态势和经营状况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派生诉讼已经没有必要继续进行,甚至诉讼继续进行还会对公司造成更大损害,因此和解也许就是各方利益平衡后的最佳选择。譬如一个正急于上市融资的公司,在辅导期内以及准备期内最忌讳诉讼行为,尤其是这种因“公司懈怠”而发生的股东派生诉讼行为。再譬如,出于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和挽留、笼络人才考虑,公司和股东与被告人(如公司高管、技术骨干)达成了和解。正如俗语所言,鞋子是否合脚,只有穿鞋者最为清楚。在这些情形下,股东派生诉讼是否还有必要继续进行,是否与被告进行和解,最为清楚、最为理性者莫过于公司和股东自己了。这也是公司自治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
尽管司法审查制中也可以通过通知与听证制度及异议权制度兼顾公司和其他股东的意志[],但是法院的主导地位难免会干扰商事决策的自治性。特别是在公司和股东均同意调解,而法院审查却认为调解不合适时,根据美国标准公司法和韩国商法典的规定,法院享有最终决定权。简言之,在司法审查模式中,法院的审查权比当事人的私法自治权处于更为优越的地位。然而,法院在事后对复杂多变的商事领域发生的纠纷所做的裁判,是否必然优越于公司、股东以及董事的商业判断是不无疑问的[]。正如有学者所言:“由于裁判者与商人之间在专业技能与思维定式方面的天然差异,裁判者无法在所有情况下做出贤明、公平的商业决策,即使法院出于良好的愿望也是如此。”[]法院的司法权介入商业事务的底线是不能威胁和伤害公司自治精神。倘若司法权的介入以牺牲公司自治精神为代价,那么宁可不要司法权的介入[]。
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的商事审判组织、法官的商事裁判思维和裁判技能尚未完全具备的条件下*鉴于商法的技术性、国际性、变动性以及商人的逐利性,相较于一般的民事案件,商事案件对法官的裁判思维和专业技能有更高的要求,对商事审判组织也有特殊的要求。(参见罗培新:《论商事裁判的代理成本分析进路》,载《法学》2015年第5期;曹志勋:《商事审判组织的专业化及其模式》,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法院司法权介入商业事务并在事后审视、评判商业决策的做法应当慎重为宜。因此,在股东派生诉讼调解过程中,法院的司法审查不应作为主导,拥有处分权的公司才应成为主导。诉讼调解不仅仅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结果,不能仅将法院的同意与否作为唯一的或最终的标准。在审判权与处分权发生冲突时,法院的调解活动受自愿原则的制约,不得将自己的选择强加于当事人,而必须接受当事人做出的决定。法院在调解中必须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说明处分权通常处于主导地位[]。既然当事人的处分权处于主导地位,我们就没有必要将问题复杂化,最为简单、可取的做法莫过于以股东会的方式征询处分权的享有者(公司)的意见。
四、我国股东派生诉讼调解规则的应然设计
(一)我国司法实践关于股东派生诉讼调解的现行做法
在我国,征询公司和股东的意见早已成为司法实践中处理股东派生诉讼调解纠纷的通行做法。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公布的典型案例中曾明确指出,股东派生诉讼的调解协议需要公司和未参与诉讼的其他股东同意后,法院才能最终确认该调解协议的效力*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第6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案例虽不属于指导性案例,但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一些地方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指导性意见亦采取了类似的做法*譬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年12月26日通过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条规定:“股东代表诉讼中,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并经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原告申请撤诉或者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撤诉或者出具调解书。”。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专家论证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专家征求意见稿)》)第五十四条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股东代表诉讼案件,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应经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或者经全体股东同意。”《公司法司法解释四(法院系统征求意见稿)》第三十六条也有类似规定。
《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专家征求意见稿)》第五十四条与《公司法司法解释四(法院系统征求意见稿)》第三十六条的不同之处是:第五十四条规定原被告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既可以由股东会决议通过,也可以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而依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既可以由股东会决议通过,也可以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而股份有限公司则只能由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而不能在不召开股东会的情形下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简言之,这两个条文之间的最大不同是,调解协议能否以非会议体的方式(即经全体股东书面同意)通过。
这两个条文的相同之处是,都重视公司在股东派生诉讼调解中的决定性作用,即都将股东会的决议作为能否将股东派生诉讼调解协议上升为调解书的标准。显然,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认识到以股东会的方式征询公司意思,尊重企业自治和私法自治精神的重要性。但是,《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专家征求意见稿)》第五十四条和《公司法司法解释四(法院系统征求意见稿)》第三十六条,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不加区分,进而一概地要求股东派生诉讼的调解须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做法,却是值得商榷的。
(二)我国股东派生诉讼调解规则的应然设计
笔者认为,鉴于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区别*我们在对比有限责任公司时不能以其与小型的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对比,而应抓住实质性区分要素将其与上市公司等公众型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对比。就我国现行《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而言,该法没有厘清这两种公司区分的本质要素,即封闭性与公开性。正如有学者所言,目前我国公司法律形态存在着结构性问题,有限责任公司虽属封闭公司,但没有涵盖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而股份有限公司却容纳了公开公司和封闭性的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因此,我国应整合封闭公司资源,重塑有限责任公司形态,涵盖所有封闭公司,即将发起设立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并入有限责任公司制度,使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成为囊括所有封闭公司制度资源的制度,使股份有限公司仅具有公开公司特点,不再涵盖发起设立的公司。通过这种改革,使封闭公司制度更灵活;使公开公司更加公开、透明。(参见王保树:《公司法律形态结构改革的走向》,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1期,第106-116页)有学者认为,我国公司法应当打破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分类,以上市与否作为公司类型化的标准,将公司分为上市公司和封闭公司。(参见张辉:《中国公司法制结构性改革之公司类型化思考》,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90-98页)正是由于有限责任公司等封闭性公司与上市公司等公众公司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学界才倾向于我国公司法进行公司类型化改革,以便设计出能够更加反映两者差异性的、更加有针对性的法律制度安排。,我国公司法应对股东派生诉讼的调解规则做相应的区分。具体来说,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派生诉讼的调解应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派生诉讼的调解应根据公司的开放性程度进行区分对待。
1.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派生诉讼调解规则设计。
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派生诉讼的调解应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而不宜由股东会表决通过。如上文所述,股东派生诉讼虽因原告股东行使派生诉权而启动,但毕竟原告股东仅享有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归公司所有,股东派生诉讼所讼争的实体权利归公司所有,公司享有实体权利的处分权,因此,本应由公司决定是否同意股东派生诉讼的调解事宜。但是,鉴于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冲突是有限责任公司等封闭性公司的主要代理成本问题[],因此股东派生诉讼的调解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比较合适。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人数较少,股权比较集中,股东会通常是大股东意志的体现,如果股东派生诉讼的调解协议交由股东会以决议的方式通过,则小股东利益可能会受到严重侵犯。在我国商事实践中,有限责任公司的管理者通常由股东担任,基于资本多数决原则,股东会和董事会通常由大股东控制。此外,鉴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通常比较少,因此作为一个整体的公司利益与股东利益的区分并不像公众公司那样明显,这样,“当封闭公司的利益受到侵害时,真正的冲突实际上是在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而不是侵害股东和受害公司之间”[]。
因此,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派生诉讼的调解协议应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而不宜交由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这样,实质上就是赋予小股东对调解协议的一票否决权。表面上看这样也许有些苛刻,可能会阻碍一部分调解协议的达成,但效率的追求不能以严重牺牲公平正义为代价。我们不能只顾前行而忘记出发时的目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主要目的正是对小股东进行保护。作为法律异态规则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是对资本多数决原则的适度突破,是法律赋予少数股东对抗多数股东暴政的一柄利剑[]。因此,赋予小股东对派生诉讼调解协议的一票否决权,不仅符合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立法目的,而且还可以防止发生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二次“暴政”。
其二,赋予小股东对派生诉讼调解协议的一票否决权,也符合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的特殊性。相较于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对外转让受到严格的限制(一般不得任意转让)、没有全国公开的交易市场、股权的流动性差,小股东退出渠道不通畅,小股东极易受到大股东的欺压。鉴于此,公司法中设置了诸多旨在保护小股东的法律制度,譬如我们此处探讨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赋予小股东对调解协议的一票否决权,并非是对大股东的不公,而恰恰是在重视有限责任公司的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地位差异的客观现实基础上所做的一种法律平衡,是股权形式平等基础上对股权实质平等的一种追求。
相反,如果派生诉讼的调解协议由股东会决议通过,则可能会发生对小股东利益的二次侵害。因为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会通常采用的是资本多数决原则,小股东的反对声音可能会被大股东的赞成声音所淹没。其实,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任何股东都有资格依法提起股东派生诉讼,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股东均可依法对资本多数决背景下的“公司怠诉”行为说不(即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股东派生诉讼)。既然如此,如果再将股东派生诉讼中的调解协议交由奉行资本多数决原则的股东会决定的话,那么,任一股东均可依法对“公司怠诉”行为说不的制度安排将被虚化。这样,也就背离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初衷。因此,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派生诉讼中的调解协议不宜交由股东会表决通过,而应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为宜。
2.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派生诉讼调解规则设计。
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派生诉讼的调解应根据公司的类型做进一步的区分对待。具体来说,根据公司的开放性程度,将股份有限公司划分为公众公司和非公众公司,公众公司包括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众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3年12月26日修订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非上市公众公司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其股票未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一)股票向特定对象发行或者转让导致股东累计超过200人;(二)股票公开转让。,公众公司之外的股份有限公司为非公众公司。对于公众公司,股东派生诉讼的调解应由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无需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对于非公众公司,股东派生诉讼的调解应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对于非公众公司,其在本质上与有限责任公司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两者都属于封闭公司,都具有非常明显的封闭性。譬如,两种公司的股东都有最高数额的限制,公司资本都不得对外公开募集,股份(股权)都不能进入证券市场公开上市交易。有鉴于此,有学者认为,我国应该科学地整合封闭性公司制度资源,将发起设立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并入有限责任公司制度,使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成为囊括所有封闭公司制度资源的制度。同时,兼顾它们的需要,进一步改革有限责任公司制度,使其成为现有有限责任公司、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都适用的制度规则[]。也就是说,非公众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因为我国现行《公司法》的不当设置才致使二者发生了割裂,今后的改革方向是将二者都纳入封闭性公司制度中,适用统一的规则体系。其实,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非公众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一样,其主要代理成本问题也是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冲突问题,上述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派生诉讼调解中存在的问题在非公众公司中同样存在。究其原因,乃在于其封闭性所致。故此,与有限责任公司相同,非公众公司的股东派生诉讼的调解协议也应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为宜。
对于公众公司,股东派生诉讼的调解应由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无需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规则设计对公众公司而言是低效率的,甚至是无效率的,不符合公众公司之股东人数众多的客观现实。因为,公众公司的股东人数众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股东数以万计,若想让所有股东对同一个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就上市公司而言,单不说人数众多的股东达成一致意见是困难的,即使就拟决议事项一一通知到每一位股东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市公司发行的许多股票是无记名股票,要想查找并切实通知到每一位股东犹如大海捞针,成本极为高昂,效率极其低下。。“尽管一致性规则可能是团体行为的最佳民主方式,但是很不现实,也不一定能满足帕累托最优。”[]此外,公众公司是典型的资合公司,股东之间基于公司股份而松散的联系在一起,股东之间缺乏人合性公司那样的信任基础。股东之间要么是互不相识,要么是血海深仇,但以购买或持有公司股份的方式通过上市公司这个平台而联系到一起。简言之,多元化的投资主体难以形成一致性的意见。
其二,公众公司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公司股份具有非常强的流动性,小股东有充分的退出通道。公众公司具有开放的股票交易市场,当小股东对股东派生诉讼的调解事宜不满时,可以在证券市场抛售股票进而退出公司。
其三,信息披露、控制权争夺、证券监管、证券服务机构的看门人机制等配套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减少和化解大股东借股东大会决定股东派生诉讼调解事宜侵犯小股东利益而产生的代理问题。鉴于公众公司的开放性及其对资本市场乃至金融市场的影响,公众公司不仅受公司法的调整,而且还受证券法的调整,而各国证券法无不强制要求公众公司必须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泡是最有效的警察。根据我国证券法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司的重大诉讼等事项需要依法进行披露,这样,向资本市场和监管部门公开披露股东大会关于股东派生诉讼调解协议的决议,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大股东操控股东会侵犯小股东利益的负外部性问题。此外,伴随着我国机构投资者的日渐发展壮大,其在小股东保护方面也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言:“一切代表多元受益人进行市场投资的机构集合了控制权,因而降低了投资者分散所带来的集体行动问题。”[]
五、结语
股东派生诉讼作为公司法的一项特殊制度,已在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予以规定,但是该法尚未对股东派生诉讼调解制度做出明确规范。正如上文所述,鉴于股东派生诉讼的特殊性,原告股东仅享有从公司诉权派生而来的诉权,股东派生诉讼的调解牵涉到原被告之外第三方(公司)的实体权利,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调解的一般规定难以满足股东派生诉讼调解的特殊需求。既然作为股东派生诉讼一般法的《民事诉讼法》难以满足股东派生诉讼调解制度供给的特殊需求,那么,作为股东派生诉讼特别法的《公司法》就有必要对股东派生诉讼调解制度做出特别规定。目前,正值我国《公司法》新一轮修改的关键时期,我们应抓住这次修法契机,对股东派生诉讼调解制度做出明确规定。对此,建议我国《公司法》今后修改时作如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股东派生诉讼案件,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有限责任公司和非公众股份有限公司应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众公司应由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1]甘培忠,刘兰芳.新类型公司诉讼疑难问题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72.
[2][15]李领臣,赵勇.论股东代表诉讼的和解[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0,(2).
[3]郭玉军,孙敏洁.美国诉讼和解与中国法院调解之比较研究,法学评论[J].2006,(6).
[4]魏亚琼.论股东代表诉讼中当事人处分权之限制——兼论对和解与撤诉司法审查程序的确立[J].法治研究,2009,(10).
[5]孟祥刚.公司股东代表诉讼的审理[J].法律适用,2007,(4).
[6]徐强胜.公司纠纷裁判依据新释新解[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266.
[7][8]江伟.民事诉讼法(第六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15,216-217.
[9][24]张卫平,李浩.新民事诉讼法原理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280.
[10]乔欣等.公司纠纷的司法救济[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96.
[11]江伟.论股东诉权[J].浙江社会科学,1999,(3).
[12][13]张卫平.民事诉讼法(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30.
[14]江伟.民事诉讼法(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5.
[16][18]刘凯湘.股东代表诉讼的司法适用与立法完善[J].中国法学,2008,(4).
[17][美]美国法律研究院.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下卷)[M].楼建波,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744-754.
[19][日]前田庸.公司法入门(第12版)[M].王作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39.
[20]施天涛.公司法论(第三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476-477.
[21]John M. Sjovall ,What Duty Do Company Directors Owe to Bank and Other Creditors? 121 Bank Law Journal 4(2004).
[22][23]刘俊海.现代公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61,860.
[25][26]李小宁.公司法视角下的股东代表诉讼[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01.
[27]胡滨,曹顺明.股东派生诉讼的合理性基础与制度设计[J].法学研究,2004,(4).
[28]王保树.公司法律形态结构改革的走向[J].中国法学,2012,(1).
[29]钱玉林.公司法实施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38.
[30]朱锦清.证券法学(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9.
[31][美]莱纳·克拉克曼,亨利·汉斯曼.公司法剖析:比较与功能的视角(第2版)[M].罗培新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64.
责任编辑:程政举
On the Regulations of the Company Law of Shareholder’s Derivative Action
Wang ChanghuaZhang Siyu
(HenanUniversityofEcomomicsandLaw,ZhengzhouHenan450046;East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Shanghai200042)
The shareholder’s derivative right or action can start and maintain civil procedures. However, it is born in the company’s right of action, so there must be some restrictions on the plaintiff ’s right of action. In term of the shareholder derivative action of a company with limited liability and a non-public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a mediation agreement requires unanimity of all of the shareholders, while in a public company limlited by shares, a mediation agreement can be agreed by the gener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shareholder derivative litigation determines the complexity of derivative litigation mediation, and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special needs of the system of the shareholder derivative ac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special provisions about the shareholder action in our company law.
shareholder derivative suit; right of action; mediation; company law
2015-09-20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股东派生诉讼立法研究——基于公司法与民事诉讼法协调的视角”(项目编号:09BFX082)的阶段性成果。在此特别鸣谢华东政法大学沈贵明教授的指导。
王长华(1979—),男,河南淅川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讲师,华东政法大学201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公司法;张思宇(1991—),女,河南淮阳人,华东政法大学2014级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
D925.114
A
2095-3275(2016)02-0124-10
——以既有裁判文书为对象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