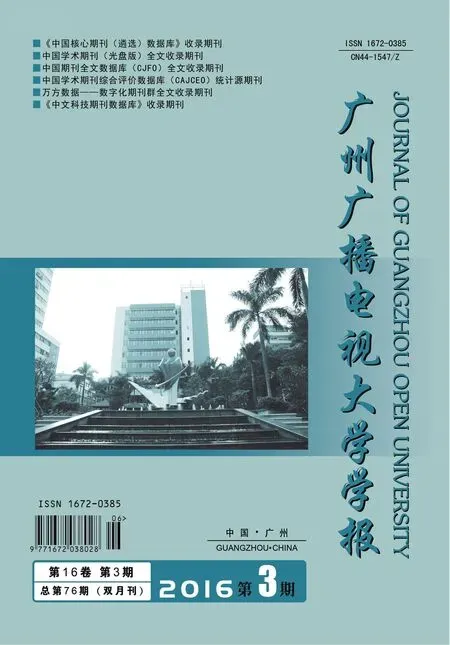《群山之巅》:人性与自然的双重变奏
魏 斌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群山之巅》:人性与自然的双重变奏
魏斌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群山之巅》的创作深受“天人合一”哲学理念的影响,在一场场小人物的命运交响曲中思考了人性与自然的内在统一,匠心独运地呈现了人性与自然关系中的人性自然化和自然人性化,对这两者关系的书写使小说《群山之巅》对人性跌宕的剖析更加深刻,小说中的故事演绎出了相互矛盾的人性与自然变奏模式,一是“出走”与“归来”的二律悖反,一是“现代化”与“生态意识”的辩证思考。
关键词:《群山之巅》;人性自然化;自然人性化;“出走”与“归来”
《群山之巅》是迟子建2015年推出的又一部扛鼎之作。故事发生在北中国龙山之翼的一个偏远小镇——龙盏镇。迟子建继续钟情于自然,在这片厚重的土地上上演着一场场小人物的命运交响曲,他们沉浮颠荡于滚滚红尘,在艰涩的命运里,时爱时恨;他们生在依山而建的龙盏镇,千百年来自然万物的灵气感染着它脚下的每一位子民,绵延偏僻的群山之巅孕育了他们善良、忠厚的美好秉性,也催生出自私、贪婪与险恶的一面,作者以令人动容的笔触,探入到人性深处,开始了人性与自然的双重变奏。
一、人性与自然的关系
迟子建追寻“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她认为那是人类的文明之境。“‘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理念,其基本含义是‘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1]可以说,在《群山之巅》里作者将其演绎到了极致,她笔下的自然万物与人性的推进演变交织成一首悲壮的奏鸣曲,无论是“人性自然化”还是“自然人性化”,人性这一本真纯、明澈的自然本能开始在自然之境中涤荡出一层又一层的命运涟漪。
(一)人性自然化
在这片北中国的乡土记忆中,作者站在群山之巅,在自己“无比钟情的大自然”的怀抱里,还原出一个个小人物命运的起伏与颠荡。在峰峦峻拔、林木蓊郁、溪流纵横的自然恩泽里,部分人物形象逐渐在这份滋养里呈现出秉性自然化的特征。小说中的辛七杂、安雪儿以及绣娘等无不体现出这一特征。首先是辛七杂,迟子建说:“辛七杂一出场,这部小说就活了,我笔下孕育的人物,自然而然地相继登场,”的确如此,当辛七杂“摸出凸透镜,照向太阳,让阳光赶集似的簌簌聚拢过来,形成燃点,之后摸出一条薄如纸片的桦树皮,伸向凸透镜,引燃它,再点燃烟斗”的时候,辛七杂的形象呼之欲出,带着某种紧紧攫取读者目光的神秘吸引力活跃于文本间。也恰恰是他这份心性自然化的人格特质,能够敏锐地感受到太阳火烧烟斗的奇异芬芳,能让月光来作为自己屠刀的最好擦布刀,从这份“自然化”里折射出来的正是辛七杂的执着乃至固执,善良而又愚昧,“他成年后找对象,对媒婆开出的唯一条件,就是这个女人不生养,他不想让不洁不义的血脉流传。”这个“导火索”让辛七杂显现了他的骨气,也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的王秀满结扎,领养辛欣来,辛欣来杀母并强奸龙盏镇的神话安雪儿等等一系列的事件接踵而至。其次是安雪儿,她能预卜人的死期,龙盏镇人因“对生命的敬畏、对死的恐惧、对神异之事的自然崇拜,以及心目中那来自原始社会对生存渴望的本能意识,夸大了安小仙所有的神奇,口口相传的最终结果是把安小仙塑成了龙盏镇的神话。”[2]成为了“仙女”与“精灵”。在“神话”被打入“魔鬼的行列”之前,安雪儿最为钟情的应该是大自然,她好似自然孕育出来的小精灵,从自然界获取食物:“到了下雪天气,她会伸出舌头接雨雪,说是天上的东西好吃;”在自然界寻找玩伴:废弃的石碑坊因为有风、月亮和星星,使她找到了家的归属感;她会通过天空预卜生死:乌云的形状让她预卜了老杨和架线工人的生死。她是北中国大兴安岭怀抱的一方净土,她以精灵般的纯洁与美好折射了龙盏镇人颠荡沉浮的人性变奏。另外一个具有人性自然化特征的人物是鄂伦春人绣娘,当她初次与安玉顺见面时,一张苹果脸,嘴唇像是一轮红日托起的乌云,脸颊还泛着自然的红晕,足蹬鹿皮靴,整个人就像落在大地的云彩。就是这样一位散发着原始野性魅力,浑身洋溢着自然活力的女子成为了安玉顺渴望已久的“好月亮”。她汲取了大自然的钟灵毓秀,练就了一手巧夺天工的刺绣手艺,“她拈着绣花针,在柔软光滑的丝绸上描龙绣凤。荷花鸳鸯、牡丹蝴蝶、喜鹊红梅、碧草蜻蜓、明月彩云、溪流红鱼,都是她热衷勾勒、也是深得新人喜欢的图景。”年近八十,她还骑马出行,最终风葬在白马的尸骨之上,真正融入到了自然的精魂里。
(二)自然人性化
作者赋予了自然界万物以灵性,使其具有了人的情感思维,群山之巅的山川草木与人类共同呼吸着光辉岁月,他们冷静地洞察人世间的悲喜离合,在四季的轮回中表达着属于他们的喜怒哀乐与心灵悲鸣。一类是动物的人性化,绣娘将白马视作亲人,在绣娘中风进卫生院后,“都不用安平打马,白马驮着他直奔卫生院而去;”辛开溜与部队走散绝望之际,红脑门的苏雀为他打开了一线生机;小青年临死前说:“叔,你要是能让我死的痛快、干净,不毁我容,我就化作一只鸟儿,给你唱一路的歌。”安平满足了小青年的最后愿望,然而在回去的路上,果真有只“黄雀儿一路追随,直到他进了城,打开车门,探出身来,它为他留下最后几声明丽的叫声,才飞回山林;”以及刑场上为红衣女孩松绑的狼,而“人们说为那女孩松绑的老狼,就是当年他们救过的狼。”一类是植物的人性化,小说第八章,辛七杂欲向金素袖表白,发现摩托车后轮的车圈里,夹着一支野百合,这火红的野百合,让辛七杂想起了苦命的王秀满,使他心惊肉跳,羞愧不已,我们暂且不说小说的处理技巧使得“野百合”具有通灵性,正是这种自然的人性化的通灵,使得人们在面对自然万物的时候,往往能够从中窥探自我的内心,达到灵魂、表现矛盾纠结人性的作用。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作者再现“人性自然化”和“自然人性化”过程中,对修辞技巧运用的信手拈来和匠心独运。所谓修辞技巧下的“人性自然化”是指作者在营造比喻等修辞手法时,将“人体”或者“与人密切关联的日常用具”作本体,“自然万物”作喻体,从而起到别样的修辞表达效果。而“自然人性化”恰好与之相反,不同之处在于多以拟人和比拟的修辞为主。首先,我们分析修辞技巧下的“人性自然化”在文中的具体体现,恰如自然界万物在审美上有优劣之分,为了映衬“本体”的身心特点,作者自如变换“喻体”,使得“好的”更具清新脱俗之气,“坏的”倍增厌恶之情。唐眉是“云朵”也是“枯枝上唱歌的鸟儿”,为了赎罪,她抑制内心的罪恶散发着仅有的生命活力;李素贞的“理容师”三个大字是“鲜艳夺目的绿叶”,她的善良与美丽让每一颗亡灵从她手里带走了片片春天;破身后的安雪儿有着“芍药蓓蕾”样的脚趾,是只“羽翼鲜艳的鸟儿,”诉说着“生活并不是上帝的诗篇,而是凡人的欢笑和泪水”的救赎之歌。此外,比拟修辞也有着精炼的使用,作者往往将具有对比效果的多个“喻体”组合使用,突出其间的讽刺意味和情感指向,得了钱的老魏似“鹅”,在窑子里将钱挥霍殆尽时又像一只得了“瘟疫的鸡,”极具形象感,也透露出一个小人物的悲哀与无奈;在王庆山眼里郝百香是“美玉”,烟婆就是“树墩”、“一截黑烟囱”甚至是“茅坑里的石头”,从而烟婆精于算计、贪财狡诈的性格特征便袒露无疑;陈美珍的鬓角是支“鹅毛笔”,而刘小红的秀发却似充满生命力的“椴树丛”,这正是陈美珍因未能以正经的方式得到唐汉成的爱而产生的自卑而又虚伪的真实内心写照。迟子建深爱着北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草木鸟兽、风月雨雪皆是她的恋人。情到深处,发乎笔端,任采一寸,便生发出别样的人景交融,嘴是“上弦月”,“颤抖的手”是“败军的旗帜”,“眉毛”是“没出齐苗的田垄”,补丁是衣裳的“花瓣”,“太阳”可以是白米,也可代表“一颗肾”,就连“满地的瓜子皮”,也可以成为营造氛围的“暴雨前聚集的蚂蚁”。总的来说,无论是自然生物与人互喻,还是自然生物与人类使用的日常工具的互喻,并没有将任何一方突兀地呈现,在群山之巅的龙盏镇,他们共同参与了这场“爱与痛的命运交响曲”。正如宗白华所说的,“大自然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推动无机界以进入有机界,从有机界以至于最高的生命理性、情绪、感觉。这个活力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也是一切‘美'的源泉。”[3]其次,“自然人性化”在修辞中充分体现。作者多数采用拟人的修辞方式,赋予自然万物以人的灵动,使其具有人的价值取向,再经由作者的慧心描述,太阳和月亮成了天上的表,牲畜成为地上的表;龙盏镇“植物的香气跟人的脾性一样”,也会“有浓有淡,有甜有涩”;“月亮”成了“烤鸡”,“星星”成了“虾球”,雷击树上端坐的猫头鹰也会“像是丧父的女人,发出哭一样的叫声;”油叽叽的水勺子像极了老妓女的脸……这种通过修辞将自然人性化的过程又往往会生发出多层内涵与深意,无论是对于人性的反补,亦或是作品整体主题的阐释均具有绝佳的效果。例如,作者写到辛七杂的屠刀时,有这样一段话:
“月亮好的夜晚,辛七杂起夜路过厅堂,总要多看它几眼。月光在刀上行走,似在燃烧。他曾将烟斗凑向它,企图点燃,可斩马刀上的月光,一副舞娘的姿态,无意做播种者,根本不理会他”。[4]
月光在行走,在燃烧,以一副舞娘的姿态,通篇分析,辛七杂与“太阳”和“月亮”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说“太阳取火”代表着辛七杂固执、硬朗的一面,那么“似舞娘般的月光”就将他内心中的柔情投射得万般动人了。如此一来,辛七杂既似“松山山顶的雪青色圆形巨石,在日光里熠熠闪光,”又似松间的月光,柔情似水。王秀满还在世时,院子里的晾衣绳“像一条彩虹,”王身亡后,在辛七杂的眼里却如“乌云压顶”;因为一朵王秀满生前喜爱的“野百合”,他会在愧疚中放弃他的求爱;尽管他一度怀恨父亲,但当老魏让他拔掉辛开溜头上的管子,让其走得轻松些的时候,他依然满含热泪地说:“不管咋的,他都是爹啊。只要他能喘气,就不能不让他活…”辛七杂的烟斗里装着一个太阳,心里却住着一个月亮,这种将自然秉性赋予人性的过程,反过来又较好地为人物形象的饱满度增添了几抹亮色,也是《群山之巅》给予我们的独特魅力的体现。
我们再看一段第九章中作者对于格罗江的一段精彩描写:
“这条江初始波澜不惊,江面狭窄,水浅,像个羞涩的少女;到了中段,它是一条硬铮铮的汉子了,江面开阔,波涛翻卷,水生滔滔,气势宏大。而格罗江下游,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江水幽深,风大的夜晚,山岭夹峙的江水,就像在唱一曲凄婉的爱情咏叹调。”[5]
初始是“少女”,中段是“汉子”,到了下游便成了“老人”,作者将这段描写放于第九章“格罗江英雄曲”,显然是与林大花和安大营未经绽放却已凋谢的爱情相照应的,若如从通篇来看,这段自然人性化的书写却将龙盏镇每一个人的命运交织其中,仿佛一副跃动的画,记录了龙盏镇人的悲喜苦乐:从生命之初的羞涩与单纯,到成年后的自信与浑厚,再到老年的饱经沧桑,有多少“水流”未曾走完就已干涸,又有多少想要“回头”,却不得不在赎罪的河道里混沌前行。
二、人性与自然的变奏模式
(一)“出走”与“归来”
迟子建在接受《北京青年报》的记者采访时曾说:“我在这部长篇小说里,着力描写了几个矛盾纠葛中的人物,他们挣扎在人性的泥淖中,双足在恶之河,可他们向往岸上人性纯美的花朵,于是他们挣扎。”[6]以唐眉和单尔冬来说,他们生在龙盏镇,因求学或是工作原因,暂时离开了龙盏镇,又因陷入罪恶的泥淖再次回到龙盏镇寻求涤荡忏悔之路。唐眉起初带着陈媛回到龙盏镇的时候,其中的缘由一直是一个未解的谜,如果说唐眉是因为善心的驱使,暂且可以解释,但当唐眉做了汪团长的情妇之后,又蒙上了一层难解的迷雾,直到暴风雪一章,唐眉向安平道出了她身上背负的“十字架”,真相终于浮出水面:面对败阵的爱情,骄傲好强的唐眉将有毒的化学试剂分三次下到陈媛的水杯,导致陈媛沦为智障,因良心发现愿一生一世守护陈媛,救赎自己所犯下的罪恶。那么唐眉为什么选择带着罪恶回到龙盏镇,且居住在高山环绕的小木屋?原因是她把崇山峻岭、静谧苍凉的群山之巅视作内心赎罪、涤荡灵魂的地方,唐眉离开龙盏镇去求学之前,“她的眼睛就像溪流上的云朵,湿润明媚,顾盼生辉”。可归来后,“那双丹凤眼宛如被霜打了的花儿,黯然无神”。她试图在群山的一草一木里赎罪,以清晨的山雾消散她的悔恨,借格罗江的流水冲刷她的罪恶,在林间鸟儿的鸣叫里寻求一丝的慰藉。她把安雪儿视作自然万物的主人,因而除了陈媛,她只对安雪儿好。然而救赎之路好景不长,辛七杂破了安雪儿的“真身”,唐眉瞬间跌进了绝望的深渊,她变得“脸色暗黄,眉头紧蹙”,并以自我堕落的方式做了汪团长的情妇,在一次次私会里,她的“呼喊像冲锋号一样嘹亮”。当罪恶的毒瘤愈发膨胀的时候,折磨自己成为了最好的“止痛药”,可“止痛药”终究是暂时的,为了获得长久的心灵安放,她选择了诱惑安平为她种下另一个“安雪儿”,却也以失败而告终。唐眉犯下了不可宽恕的罪恶,即使逃脱了现实的监狱,却终将在群山之巅这场罪恶与灵魂的监牢里囚禁终生。
与唐眉不同,单尔冬的人生轨迹总体上呈现出“出走”—“归来”—“出走”的模式。单尔冬在还未正式出场前,就因通过单四嫂的侧面描写便而永久地烙上了抛妻弃子的“陈世美”印记。他连发三篇小说,声名鹊起,便与单四嫂离婚,后被调至松山地区文联工作。他以牺牲道义与良知为代价,奔向了他的“出走”之路。随着安大营的不幸溺亡,为完成助阵安大营为英雄人物的报告任务,单尔冬回到了这个令他的良心战战兢兢的龙盏镇,不妨先看小说中的这样一段描述:
“白的磨盘在转,磨身漫溢着玉米金黄的汁液,好像磨盘流出的泪;蒙着黑面罩的黑驴也在转,它把院子的泥地踏出一圈深深的凹痕,远远以望,像只愤怒的眼,瞪着单尔冬。”[7]
单尔冬“攫取了她(单四嫂)的芳香,最终却抛弃了她”,当他再次回到家的时候,连“磨盘”和“泥眼”也可以将他“鞭笞”的“体无完肤”。这次“归来”,让单尔冬饱受良心谴责,而关于安大营英雄事迹的虚假报告也从侧面折射出他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无奈与悲凉,暂且搁置单尔冬抛妻弃子的行为不论,单说他对于写作的追求,起初的他怀揣着一颗热诚之心奔赴文学的圣坛,然而自我本身所背负的心理包袱以及逐渐失去价值导向重心的文坛现状,注定了单尔冬后来的落魄“归来”。再次回到龙盏镇,即使住在驴棚里,故土的气息也可以让他那在松山文联干涩的笔“有如神助,饱满滋润,一个个漂亮句子,像清澈的溪流汩汩流淌”。龙盏镇的自然风景一直是他写作的灵感,可面对伤残的春天,他的文思再次枯竭,再加上来自于家庭的烦躁与不景气,使他再次卑鄙地抛下单四嫂和儿子选择了“出走”。
唐眉与单尔冬皆是背负枷锁的矛盾纠结体,他们因私欲陷入了无休止的痛苦之中,本以为“归乡”可以暂且安放空虚流离的灵魂,却因本性的残损而陷入人性的泥沼之中。很显然,作者在处理“出走”与“归来”模式里的自然与人性的变奏时,处在一个矛盾纠结体里,对于诸如唐眉和单尔冬这批小人物的罪恶与救赎,作者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但是却因为道义与良知的谴责而将其转交于自然,试图利用自然的广博与幽深来获得释怀,然而自然与人性始终处于一个互相影响的模式中,企图借用任何一方来获取救赎已然成为一种奢望。
(二)“现代化”与“生态意识”:被“劫持”的“春天”
大自然这一温床是迟子建汲取写作养料的重要途径,因而在其作品中往往表现出对于自然的亲昵与厚爱,但因现代化进程对淳朴自然的侵蚀和浸染,多少又充斥着些许惆怅与无奈。如迟子建所说:“每到隆冬和盛夏时节,我依然会回到给我带来美好,也带来伤痛的故乡,那里还有我挚爱的亲人,还有我无比钟情的大自然!社会变革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新规,在故乡施行所引发的震荡,我都能深切感受到。”[8]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剧,龙盏镇终将不能避免这把“双刃剑”的侵扰,因而作者既有“伤痛”又有“美好”,只是二者如何权衡成为了作者震荡之余的深入拷问。
作者分别在“龙山之翼”与“花老爷洞”两章的开头对龙盏镇的自然环境做了细致的描述,所呈现出来的情感状态却截然相反:
“松山山脉平均海拔六百米,它像一条舞动着的彩练,春夏时节被暖风吹拂得绿意盈盈,秋季让霜染得五彩斑斓,冬天则被一场连着一场的雪,装扮得通体洁白。它绵亘数百里,一路向北……它这浪漫的转笔,给这一带的山峦,带来了不一样的气象,峰峦峻拔,林木茂盛,溪流纵横。”(第三章)[9]
龙盏镇的春天,被松毛虫给劫持了……连年的采伐致使森林树种趋向单一,这给松毛虫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温床……这时的森林仿佛出了丧事,一派萎靡,了无生气……林间小溪漂浮着死鱼,河岸边是野鸭的尸体,树丛中飘散着灰鼠和野兔腐烂的气味,连喜食腐肉的乌鸦也少见了。(第十五章)[10]
因人类操作不当以及技术手段的滥用,导致龙盏镇自然环境的极速恶化。当相继登场的人物,在龙盏镇上演着爱恨交织的命运之曲时,他们所依从的自然温床也饱尝“人生苦涩”的悲凉况味。而作者的生态忧患意识也显而易见,一种无意识下的“生态文学”书写介入,让自然与人性的变奏表现的更为复杂和深刻。当下部分生态文学易进入因偏重自然环境恶化的忧患书写和补救措施的呐喊的重复书写而忽略了文学深层价值的流弊中,所不同的是,《群山之巅》虽然流露出了生态危机意识,但是却将其与人性的颠荡交织变奏,在人性与自然的统一体里尝试抹平人性深层里的“褶皱”。龙盏镇镇长唐汉成较早意识到了这一点,青山县的自然环境可以让他血流顺畅,洗去一路风尘,“在他眼里,破坏资源的发展,就跟一个人为了抵御严冬,砍掉自己的腿当柴烧一样,会造成终身残废”。然而,唐汉成始终以消极的方式来应对“现代化滚轮”的碾入,甚至到了自我欺瞒的地步,在唐汉成看来,龙盏镇的气息之好,“仙草”安雪儿功不可没,在安雪儿遭到辛欣来的强奸之后,唐汉成试图说服单四嫂作伪证,意图蒙蔽安雪儿遭玷污的事实;为了隐瞒辛开溜发现无烟煤的事实,常常给他封口费;当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出现的时候,为了避免龙盏镇的开发,他在斗羊节意图利用斗羊挑伤工程师,使其望而却步,却使辛开溜误遭横祸。从龙盏镇的森林如出了“丧事”之时起,辛欣来被抓,辛开溜身亡,陈金谷取肾,唐眉的“秘密”等一系列事件相继发生。在人类的影响下自然环境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摧残,人性的浮沉颠荡也离不开自然变换的参与,无论是合理开发还是消极应对,最终在于人性沉浮的演绎与参与。
三、结语
后记《每个故事都有回忆》中,迟子建以一首小诗结束了这场群山之巅之旅,她说:“如果心灵生出彩虹,我愿它缚住魑魅魍魉;如果心灵能生出泉水,我愿它熄灭每一团邪恶之火,如果心灵能生出歌声,我愿它飞越千山万水。”由本文而知,作者追寻“天人合一”的文明之境,自然万物是真纯、澄澈的,人性最初也从这份明媚开始,只是当流入命运之流时,欲望与贪婪、罪恶与救赎等逐渐使这份明媚被魑魅魍魉所束缚。“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11]“自然”像一面镜子映射人性的复杂,而“人性”又在“自然”之境里明晓丑恶美善,小诗里的美好是人性自我良知的复萌,也是作者对真纯美好的向往,只是“生活并不是上帝的诗篇,而是凡人的欢笑与泪水。”[12]这场“人性与自然地变奏曲”只会一直上演,“出走”与“归来”的二律悖反、“现代化”与“生态意识”的矛盾纠葛也会单曲循环。
参考文献:
[1]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郭莉.蛮荒群山里的远古回响——论迟子建《群山之巅》中“安雪儿”形象的文化意蕴[J].小说论丛,2014:165-167.
[3]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220. [4][5][7][9][10]迟子建.群山之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6]王佳莹,迟子建.罪恶,一样抵达鸟语花香之地[N].北京青年报,2015.
[8][12]迟子建.每个故事都有回忆,群山之巅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11]雨果:克伦威尔序.武蠡甫,胡经之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精选(中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126.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385(2016)03-0092-05
收稿日期:2016-04-24
作者简介:魏斌,男,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