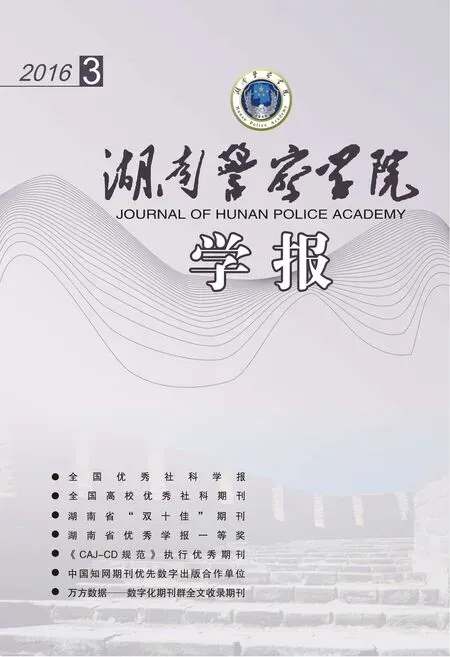当代中国人“偏好”上访的成因探析
——基于国家治理制度供给视角的观察
王 亮,彭中礼
(1.中共湖南省委直属机关党校,湖南 长沙 410003;2.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 长沙 410006)
当代中国人“偏好”上访的成因探析
——基于国家治理制度供给视角的观察
王亮1,彭中礼2
(1.中共湖南省委直属机关党校,湖南长沙410003;2.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长沙410006)
摘要:有人认为当代中国形成的“上访热”,是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结果。虽然上访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制度,但是在古代中国并不发达。而且,古代中国存在上访制度的原因是行政与司法混同,其上访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上诉。当代中国人“偏好”上访,最直接的原因是国家的治理制度供给存在缺陷:一是民众权益表达机制不畅,二是司法维权困难,三是政策的“逆向鼓励”使得上访暗合了制度要求。当代中国,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然要求应当认真对待上访,将上访问题法治化。
关键词:上访;法治;国家治理;制度供给
一、问题的提出
上访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热门的词汇之一。其“热”之理由在于:民众喜欢通过上访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且不去京城上访也算不得上访。更为重要的是,与上访这一词汇对应的是,官方形成了一个“截访”与“接访/截访”①如下有关上访的案例,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应当说是比较多的,后文也将会涉及到下列三个案例。案例1:马某是某地村民。自2009年以来,他多次前往北京上访。上访的理由是:他家的房子自2007年被政府拆迁以后,补偿款一直没有到位。而且,原来定的拆迁款价格每平米600元。但最近几年物价上涨较快,已经不能再重新建房。因此,他多次找当地政府要钱,但是政府都以各种理由给予打发。于是,马某踏上上访之路。案例2:唐某是某地居民。2007年,她未满14岁的女儿被查证自愿卖淫。后来,公安机关将唐某的女儿带出娱乐场所。相关涉案人员都被抓获,且依法判刑。但是唐某以其女儿尚为幼女,要求将所涉案犯全部判处死刑,有一段时间吃住在法院办公场所,并多次进京上访,最终法院在政法委的协调下屈服于唐某的要求,判处全部案犯死刑、死缓不等。所涉案犯家属对此判决极为不满,亦走上上访之路。案例3:王某是某村村民,1979年2月报名参军,后经过选拔获得参军资格。1979年3月中旬拟派往广西地区参加越战,但当坐火车到南宁时,越战结束。后来王某在南宁服役两年回家。2008年,王某听其占有说中央军委有政策,凡是1979年越战人员皆有相关待遇。于是,王某自2006年起至2011年数十次到市、省、北京上访。王某逢过年过节均扬言进京上访,基层政府只好花钱制止其上访。政府花费在王某身上的“截访”与“接访”费用已达25万余元,还不包括“消号”等费用。!在“上访”与“截访”之间,演绎了诸多关于共和国法治建设的故事。甚至有些人说,当代中国基层政府的“主要矛盾”是“上访户”和“截访人”之间的矛盾。这虽然是一个夸张的表述,但是这种夸张表述后面,所蕴含的不是有关回忆的美好,而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某种悲哀。毫无疑问,数量庞大的上访人群,地方政府花费巨大的“截访”与“接访”,都是不正常的现象,也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所应当出现的现象。特别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其能力现代化的主题任务之下,如果无法对上访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显然也就无法从制度上解决上访问题,国家治理的目标就很难实现。
在学术界,上访亦是研究热点之一。在各个学科,学者们对民众为什么喜欢上访给出了形形色色的理由,比如最早的“维权论”②该种观点认为上访是公民维护权利的一种方式,参见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应星:《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信访救济》,《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美国学者也对此有了相应关注,如Kevin O.Brien& Li Lianjiang,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1-24.。在诸种对上访行为进行解释的理论中,有一个比较受关注的解释理论就是基于文化方面的解释,笔者拟将该种观点称为“文化论”。“文化论”认为,民众之所以“偏爱”上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传统法文化在其中所起的潜移默化、甚至是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寻求权利救济的过程中,为什么不是选择常规的司法途径而是偏好直接去上级机关‘告状’?这确实是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法治现象’。认识这一现象,必须考虑我国传统法文化在其中所起的潜移默化、甚至是推波助澜的作用。以法文化的视角观之,上访是一种民本主义的治理传统;它游离于传统情理与现代法治之间。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诸多问题产生的根源,其实就在于我们的法文化本身。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法治建设,其核心就是一个法治文化建设问题。”[1]任何一个社会问题背后都可能涉及到文化问题。因此,用文化来解释社会问题当然在一定意义上是行得通的。但是,在笔者看来,就有关上访问题而言,用“文化论”来解释,却存在不合理之处。这也是本文创作的主要原因。本文希望学者们在解读社会热点问题的时候,最好不要动不动的就在文化上进行过度审视,否则就会造成文化自卑。
从上访的类型来看,有学者认为:“从上访诉求是否合理来看,至少存在三种类型的上访:有理上访、无理上访、合理性模糊的上访。一个守法的基层政府困于应对的,不是有理上访,而是无理上访和合理性模糊的上访。”[2]其实,从制度的供给角度看,不管是何种形式的上访,其之所以出现,都与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为前提。传统的文化或许可以引导人民孜孜不倦的维护自己的权利(实际上,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注重维护公民权利的),但是如果在制度上能够达到维护公民权利的目的,那么上访也将不复存在,至少不会像今天那么“火”!可见,有些社会问题或现象根本就不需要深入到那么远的历史当中寻找原因,只要仔细思考一下我们的制度供给,就有可能找到相应答案。本文的目的是在对上访的“文化论”解释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通过现实的制度供给来解释上访的成因并寻找上访问题的解决之道。
二、从传统中国的“京控”到上访
要对“文化论”解释的错误进行指正,就必须回到中国古代文化中去寻找历史上的上访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判断古代的上访和今天的上访存有什么样的关联。其实严格审查上访一词在今天的含义,我们发现,古代中国并没有上访这一词汇。在古代中国,最典型的、案例最多的就是“京控”,甚至在许多朝代还有“登闻鼓”制度(从“登闻鼓”制度来看,这是允许告御状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一个比较早的关于“京控”的故事:“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逮,诏狱逮徙系长安。太,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堤萦自伤泣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乃随其父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肤德薄而教不明软?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肤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3]“缇萦上书”的故事既说明了古代巾帼女子也如男,也说明汉孝文帝在这件事情上的德性仁厚。但是在这里最重要的关注点就是缇萦绕过了中间一些环节直接上书给皇帝,这个细节在今天可以说是“越级”进行“京控”或者说是“越级上访”。而缇萦的“京控行为”,早在尧舜之时就已出现,如当时的“进善族”、“诽谤木”以及“敢谏鼓”等直诉形式。后来,在西周使其又设立了“路鼓”和“肺石”。秦汉时,设有公车司马,专门负责接待直诉事务,同时还出现了“诣闭上书”、“邀车驾”等形式。从魏晋开始,正式设置了“登闻鼓”制度。唐代武则天时还设立了匦使院,使直诉制度渐趋制度化和正规化[4]。
在“缇萦上书”故事中,我们有理由认为,汉朝时期对于“越讼”或今天所谓的“越级上访”之行为尚未禁止(当然,也有人说古代中国就存有严格的“越讼”之规定,但是目前没有发现古代有相应的法律条文或者其他形式的禁令来佐证这种观点)。目前所能够见到的最早的关于诉讼必须逐级进行的规定是隋朝时期制定的法律。隋文帝曾诏令全国:“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①《隋书·刑法志》后来,《唐六典》对此做了比较严格的规定:“凡有冤滞不伸,欲诉理者,先由本司本贯;或路远而踬碍者,随近官司断决之。即不伏,当请给不理状,至尚书省左右丞为申详之。又不伏,复给不理状,经三司陈诉。又不伏者,上表。”②《唐六典·卷六·刑部》《元史·元世祖本纪》中记载:“如为人杀其父母兄弟夫妇,冤无所诉,听其来击。其或以细事唐突者,论如法。”也就是说,如果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京控”则是不允许的,但是有关死人的大事则可以。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越诉是合理的。宋代在沿袭唐代某些规则的基础上,打开越诉之禁,而且增立了越诉之法。特别是在宋徽宗时期,他为了标榜“革弊恤民之意”,相继颁发了允许人们越诉的诏令。比如,1113年,宋徽宗针对州县官乱打官司,大肆收取钱财,导致无辜之人被害的现实情况,要求凡“官司辄紊常宪,置杖不如法,决罚多过数,伤肌肤,害钦恤之政”。在宋朝,还有一种登闻鼓制度,也可以说明当时的越诉是允许的。登闻鼓机构设置的目的就是“通下情”,而通过登闻鼓进状的主要是普通百姓,有些致仕官员也可通过登闻鼓进状。登闻鼓制度开通了一条联系国家与社会的渠道。对于民间百姓和贬滴官员而言,他们不能通过正常的行政系统向最高决策者表达意愿,登闻鼓就成为了他们申诉冤情、上书议政等最重要的途径。因此,该制度确实解决了民间不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公民的一些权利[5]。到了清朝,对“越诉”进行京控的行为进行了严格规范,《大清律例》规定:“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若迎车驾及击登闻鼓申诉,而不实者,杖一百;事重者,从重论;得实者,免罪。”可见,实际上在古代中国,并非禁止正常的“京控”,主要禁止的是越级进行的“京控”。
如果进一步研究,我们会发现今天的到北京上访和古代的“京控”表面上看有相同之处,实质上是两回事。在笔者看来,其本质差异是:上访(包括到法院的上访)是一种基于行政制度的行为,而“京控”则是一种基于司法制度的行为。通过对上访与“京控”的比较,我们也就弄清楚了为什么说用“文化论”来解释当代中国人为什么喜欢上访是不恰当的。
要理解“京控”,就应当理解古代中国的司法制度。中国古代司法体制中,国家层面有专门掌管司法的官员,比如在周朝就有了“太宰”和“小宰”,专掌司法。但是在先秦那种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均不完善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分封制下,法律本身不发达,司法体制也难以有所成。秦汉时期,地方行政机关分为郡县两级,郡是当时的地方最高政权组织,直属中央,衙署称郡府,长官称太守。秦汉时期的太守位高权重,秩两千石,与丞相的秩相同。郡守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同时又是最高司法长官,负责处理全郡事务。举凡制民,颁发地方性法规、进贤、劝功、断狱、决讼、检奸、按讯诸囚、平其罪法、考课属官、劝农赈贫,所有政治、经济、司法,甚至风俗、民情都管。在太守掌管的事务中,最重要也最突出的还是司法事务[6]。在西汉时期,就有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等“三辅”专断刑狱。“三辅”的职权基本上与太守一样,体现出了古代高度的行政与司法合一的特征。而在秦汉时期,郡以下设县,其职责是管理人民、收取赋税、征发徭役、掌管司法审判等。县以下设乡,有乡官三人,其中有蔷夫听讼,主持民事案件的裁决,游徼负责缉拿盗贼,维持社会治安[6]25。这也是一种行政与司法高度合一的政治体制。可见,理解中国古代地方司法制度的关键就是行政与司法合一,行政长官也就是司法长官。古之朝廷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没有类似于“GDP”之类的概念,也没有强制要求促进经济发展,当然也没有今天的所谓行政权与司法权分开、制约和监督理论。有的只是基于行政权的司法行为,法官与行政长官合二为一。所以,当古代之朝廷强调按级诉讼的时候,实际上是强调穷尽地方行政长官的司法权救济,基本原理就跟当今法院的一审、二审制度大体相当。古代中国的有些朝代对“越诉”有严格限制,原因就在于希望民人能够利用现有的权利救济制度走完所有的救济程序,而不要耗费朝廷资源。所以有人说“越诉”体现了“古代统治者为了保护统治者的利益”的理解有些偏离制度主题。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司法讲究的是程序正义,违背程序的矛盾解决方式是不合理的。所以,古代中国适当限制“越诉”完全应当进行“同情似理解”。还需要注意的是,古人进京告御状并不完全等于是直接要求皇帝处理案件。前有所述,古代各朝代在中央有专司案件的官署,所以告御状也有可能是告状者在专门司法衙门前告状。当然,如果皇帝事必躬亲,那么到中央司法衙门告状的信可能被皇帝看到而获得“御批”(也有通过特殊关系将申冤材料直接递交给皇帝的,如“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杨乃武的家人通过帝师翁同龢将申冤材料直抵宫闱)。东汉时期的,宁阳县主簿为了给自己的领导伸冤,跋山涉水到京城告御状,给中央各大衙门包括司法衙门递交诉状几百次,无人问津,案子一拖就是六七年,后来该主簿直接给皇帝上书,将问题闹大才获解决。总之,在古代,虽然有些百信不得不寻求特权的帮助,但是在当时的那种体制下,行政权与司法权纠缠在一起,当事人或者其亲属们“京控”行为应当理解为一种司法行为。理由是:第一,“京控”是最后一道权利救济防线,无“京控”则再无权利救济途径。第二,“京控”的当事人们按照当时的法律到京城所进行的诉讼事宜,按照行政与司法合一的体制,此乃诉讼范围内之事。第三,“京控”行为本质上是通过最高司法权力影响下级司法权力的行为。
而当代中国的上访,却是起源于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信访制度。1951年6月7日,当时的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要求对于人民群众的意见要分别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处理。可见,在那时,信访是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此后,我国进入了一个信访井喷时期。其主要特点是以政治信息传递为主,揭发他人的政治问题成为此时信访的主要内容。“文革”结束以后,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又开始进入一个信访的高潮期,此时的信访主要是以追求拨乱反正为主,要求落实国家的相关政策。而我们今天所要分析的上访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上访,即民众基于维护自身权利或者利益的需要而向上一级政府诉求意愿的行为。可见,在我们今天来看,上访行为可能涉及到诉讼问题,但是绝对不是唯一问题。甚至从我国的诸多上访现象来看,很多民众的上访都是为了用行政权力压制司法权力,或者用上级行政权力压制下级行政权力,获得较好的利益追求效果。因此,当代中国的上访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追求较高或者最高行政权力帮助的行为(即使是到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访,本质上也是为了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来影响下级人民法院,这依然是一种追求行政权力运作的行为),其本质是要通过行政权力来影响下级行政权力或者司法权力的行为。
三、被制度逼迫或诱惑出来的上访
如上所述,如果说当代中国的上访与传统文化有必然关联的话,肯定是不公允的。毕竟,古代的“京控”制度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上访是两码事。虽然从文化的角度来解读上访看起来很正确,但是却没有抓住当代中国上访“火”的本质成因。一种直观的印象就能说明这点: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当代中国这么庞大规模的上访潮?有人会说,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因此问题堆积,矛盾尖锐。但是,不要忘记了,中国古代也同样经历过各种社会转型期,但是上访潮很少出现。可见,“文化论”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实际上,认真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的各种制度,我们可以从国家治理制度层面来解析为什么当代中国人热衷于上访,这样的解释或许或更令人信服一些。
首先,当代中国人“偏好”上访的重要原因是民众权益表达机制不畅。从理论上看,如果民众的权益诉求能够通过各种机制和制度获得合理解决,上访是不存在的。实际上,我国的法律制度设计理论中,比较合理的考虑到了民众的利益诉求。比如,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当中,就要求人民代表必须代表人民利益。在行政体系当中,为了方便民众表达利益诉求,设置了行政复议、行政问责、信访局等工作部门,还设置了党委纪委举报系统,在法院可以立案诉讼等等。从这些制度本身来看,似乎民众的利益能够获得充分的表达。可是,在实际运作当中,这些利益诉求机制并没有真正充分发挥作用。比如,就党委纪委的举报系统来说,当人民群众举报当地某个领导干部之时,特别是到了一定级别的干部之时,纪委无权决定是否启动核查程序,程序的启动权掌握在同级党委的一把手当中。再就行政复议来说,当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不满之时,只能就具体行政行为进行诉讼,对于抽象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对此望洋兴叹。因此,大量的行政行为都以抽象行政行为而被掩盖。最后,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看,虽然法律规定人民代表必须来自于群众,必须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但是,从该制度的现实运行来看,不管是那一层级的人大代表,都存在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选民们不认识人到代表,人大代表也难以倾听到选民的呼声,难以真正代表人民。虽然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但是实际上,地方主要领导人的任命,都由上级领导决定。因此,在现实生活当中,不仅上级领导干部的权力大于下级官员的权力,而且有些下级官员会以“坚决服从领导为荣”。上访的民众深谙这种权力的级别之道,所以只相信上级领导干部的权威。甚至,有时地方政府因与下级政府存在利益相关性,还会共同打压百姓的权益诉求。2011年底的“乌坎事件”就是明证。当乌坎村的村民向当地各级政府反应情况,要求解决问题时,镇、县、市三级地方政府对此置之不理。而在“乌坎事件”初期,汕尾市政府还偏信下级政府的汇报,歪曲乌坎村民的行为。直到广东省委干预此事,乌坎村民的要求才被认为是“合法的,可以理解的”①后来,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说:“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片面理解‘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认为平安就是不出事……这种逻辑下的维稳,不是权利维稳,而是权力维稳;不是动态维稳,而是静态维稳;不是和谐维稳,而是强制维稳。”朱明国:《莫让权利维稳变成权力维稳》,《人民日报》2012-07-18.。民众的权益诉求在现有的制度范围内得不到化解之时,自然只能选择上访之道。
其次,当代中国人偏好上访的根本原因是司法维权困难。在常态社会中,社会矛盾和纠纷的解决途径应当是司法。如果司法是有权威的,法官是有权威的,所有的社会矛盾能够被司法解决,那么这个社会就处于动态平衡之中。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司法体制不仅无权威,而且还经常存在司法腐败、制造冤假错案的话,那么通过司法解决纠纷的人数就会大大减少。从当代中国来看,法院作为利益诉求通道的作用没有能够在根本上发挥作用,无法成为社会矛盾化解的主阵地,其原因来自于两个方面:(1)外在的制度制约,即法院的司法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地方政府的干预。就当代中国来看,虽然从法律上确立了政府行政工作与司法工作分开的体制,但是本质上看党又主管一切工作,因此党也管理司法工作。这样,从横向体系来看,基层党委政府制度格局体系中,党委书记是整个管辖区域的“一把手”,掌握了财权、人权。而且,在党委机关当中,设置有政法委这一专门组织,原意是协调公、检、法的工作,但是到了后来政法委凌驾于公检法之上,不仅进行宏观指导,而且还进行具体个案干预(最近中央规定,政法委不再干涉具体个案,这是一个巨大进步)。从这种权力分配格局来看,如果某个地方的党委或者政法委的领导同志对于某些问题,如拆迁,有具体指示的话,法院就可能必须遵守领导的指示。这样,导致司法权力在行政权力面前失却了权威,从而出现存在民众不相信法院的现象。(2)内在的制度制约,即法院自身的一些制度限制了法院功能的发挥。第一,案件受理把关严。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要求,当事人到法院起诉,只要具备三个条件就可以,即有适格的原告、被告和事由,不属于法院排除管辖的事由,立案庭所进行的只应当是形式审查。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公民去法院起诉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是有许多案件法院不会受理,比如在很多地方凡是涉及到拆迁的事情,法院都不会受理;而且还有很多的行政诉讼案件,法院一般也不敢受理或者不愿意受理①比如2003年,广西高院就发文要求对下列13种案件不予以立案,该十三种案件为:“一、集资纠纷案件,包括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为生产、经营、建房而向职工集资引发的纠纷案件以及未经依法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乱集资活动而引发的纠纷案件。二、以“买卖”形式进行的非法“传销”活动而引起的纠纷案件。三、因政府行政管理方面的决定、体制变动而引起的房地产纠纷案件。四、因企业改制或者企业效益不好等原因出现的企业整体拖欠职工工资而引发的纠纷案件以及因劳动制度改革而出现的职工下岗纠纷案件。五、政府及其所属主管部门进行企业国有资产调整、计划划转过程中的纠纷案件;因企业改制过程中违反民主议定原则或者因企业改制而引起的职工安置纠纷案件等。六、村民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问题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生的纠纷案件,但是直接支付给个人,未经集体经济组织安排发生的纠纷案除外。七、政府部门对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争议作出处理决定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另一当事人以民事侵权诉讼的案件。八、地方政府根据农业产业化政策及规模经济的发展要求,大规模解除农业承包合同而发生的纠纷案件。九、在合作化时期入社而参加裁缝社、铁器社、理发店、马车队等小集体经济组织的职工要求分割该集体经济组织积累的财产而发生的纠纷案件。十、以“两会一部”为债务人的纠纷案件以及“两会一部”与农户间的纠纷案件。十一、当事人申请破产但提交的申请企业破产材料不齐备,职工安置不落实的案件;十二、因操纵投价、内幕交易等证券违法行为而引起的证券侵权纠纷案件,但是因虚假陈述已经有关机关行政处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的,受害人提起侵权的案件除外。十三、葬坟纠纷案件包括因争坟地争风水等引发的各种纠纷案件。”当然,还必须思考的是,省高院有权要求地方各级法院对某些案件不予立案吗?。二是司法程序设置不人性化。比如,《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要求一定要有书面起诉状,但是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人想去法院口头立案,法院是肯定不立案的。三是法院对“政治”过于敏感。许多本来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案件,却左思右想政治后果而不敢立案,很多本应在正规司法渠道中解决的案件,被推到了上访渠道中,结果因为不立案而影响了民众信任司法这一最大的政治后果。四是法院办案周期长,有些案件,在法院系统解决没有三五年时间甭指望有个好的结局。第二,案件审理受法外干涉因素太多。虽然我国宪法规定法院是独立审案,但是实际上我国法院的法官在审理案件之手所受到的外界影响是比较多的,而且法院内部的行政色彩太浓,导致案件审理的公正性常受质疑②百姓上访的基本逻辑是:我们相信中央的农村政策都是正确的,法律也是公正的,但问题出就出在那些基层干部身上,以为“天高皇帝远”,没人能够管得住他们,所以就为所欲为、贪赃枉法。从电视上看(老百姓也只能从电视等媒体上了解),上面的领导平易近人、容易沟通,算得上真正的人民公仆,哪像我们身边的这些干部,当了个芝麻大的官就以为了不起了。实际上,在这里,访民们的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希望自己的权益能够通过行政权力的强力介入获得保护,但是另一方面,行政权力介入司法,又何尝不是影响司法的公正裁决?。这样,内外两层制度限制,使得法院的功能大大弱化,有些民众也不得不走上访之路。
最后,当代中国人偏好上访还受到了来自于政策的“逆向鼓励”。严格说来,民众选择通过何种途径来化解纠纷都是他们的自由,是法律权利。然而,如果受到了某种制度的刺激,或者寻找到了制度的“漏洞”,那么民众必然趋向于选择对他有利的纠纷解决方式。最近10年来,为了将矛盾化解在基层,中央制定了几项出发点都很好的政策:一是对基层政府的工作成绩考核以GDP为主要指标(现以取消),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严格控制进京上访,对进京上访多的地方所在领导进行“一票否决”(现亦取消),特别是对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当进行“一票否决”;三是对全国的信访工作进行排名(也已取消)。这三项政策的本意是要促使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解决社会矛盾。然而,在国家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就逐渐的出现了制度异化,这些异化表现在:一是政府盲目追求GDP,特别是简单地通过大拆迁大开发的方式来追求GDP,导致了大量矛盾的发生,但是由于政府利益参与其中,矛盾化解在基层的说法很难实现,注释1中的案例1就是鲜明例证。而且,有调查表明,大量的上访民众就来源于“拆迁户”;二是地方的主要领导害怕“一票否决”,但是在追求政绩的过程当中又不注重充分关注民众权益。一旦有民众进京上访,地方政府为了“平安”,不得不花钱“消灾”。三是问责不分青红皂白,导致基层领导干部害怕出现围观人群过多的事件,最后只好屈服于一些无理上访或者无理取闹之事,花钱了事。在执行这些制度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尽快免责或者无责,再加上财政监管不严,用钱不受制约,衍生了“花钱买平安的心理”。而一些“访民”则利用了地方政府的这一心理,不断无理上访、重复上访和缠访(如案例2和案例3),获得了额外非法利润。当上访维护权益的速度高于诉讼维权的速度,或者上访维权获得的效益高于诉讼效益,或者纯粹上访也能够“不劳而获”之时。这样,就进一步刺激了其他民众的行为,上访不想“热”都不行了!当然,目前我国已经逐步取消了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察制度、全国信访工作排名制度和进京上访“一票否决”制度,基于制度的“逆向鼓励”而上访的人数会有所降低!
但是,整体上看,如果民众无法基于现有制度获得权利救济或者通过制度的权利救济成本过高,司法没有权威,行政权依然能够有效敢于司法裁判,那么上访就依然会存在!
四、根据法治认真对待上访“偏好”
从上述的分析来看,我们已经对当代中国人为什么上访的制度原因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然而,接下来我们还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是,对于当代中国人已经养成的这种“偏好”该如何处理?是继续放任,还是应当规范?目前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要取消信访制度,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要加强信访制度。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都告诉我们要认真对待上访——认真对待上访制度,就是认真对待上访这种“偏好”。“认真对待”——从根本上说,就应当将上访行为法治化,根据法治来治理上访行为,使之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第一,要根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认真看待上访的性质。虽然上文在批判“文化论”观点的时候就已经指出,上访本质上是一种通过行政权力解决纠纷的路径。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上访又何尝不是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在法治国家,公民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和自由,也有迁徙的自由,只要他的行为不违背宪法和法律,我们都不能对之有任何歧视和限制。实际上,偏好上访的民众愿意到北京去上访,所散发出来的信号是:一是相信中央政府的权威,二是相信纠纷解决终有完毕之地。我们不能因为任何外在于法律的缘由而禁止进京上访,更不能因为上访人数多而取消信访制度。纵观古代中国,严格限制或者禁止京控的法律都不存在,他们所限制或者禁止的是越级京控。也就是说,古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强调纠纷和问题解决必须一级级来,要求民众遵守基本的程序原则。这当然是合理的。实际上,上文指出,在宋朝,对于越级京控的行为并不严格规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很鼓励。可见,在古代那种法律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对民众的利益诉求机制都比较重视。我们今天的上访,实际上也是一种权益诉求制度,所以不应当将该种制度彻底废除。总之,我们应该谨记的是:上访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即使是到北京上访,只要不违背国家的基本法律,也应当允许。
第二,要根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坚持互惠正义原则是上访的理论基础。作为一种权利,上访是不应当被剥夺的。但是,任何权利都是有限度的,不管是基于何种原因行使权利,都得有克制。比如,在权利理论最为发达的西方国家,也强调权利必须互惠。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说:“社会是由一个无所不在的互惠性纽带绑结着的,在社会中,各种义务一般都能追溯到互惠原则。”他举合同规范程序之例证明在人们基于权利的行为之间,也存有合理的互惠性。可见,互惠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互惠正义使得社会生活成为可能,社会才能延续发展。伯尔曼说:“就相互的给和取的意义上说,互惠性本身在所有的文明中就是一切商业的实质所在……然而,自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以来,西方人所理解的权利互惠性原则,涉及的还不只是交换。在观念上,它还包含有在进行交易的双方之间那种负担或利益均等的因素,即公平交换的因素。这点依次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程序上的,另一方面是实体上的。在程序上,必须公平地参与交换,即不存在强迫、欺诈或其他滥用任何一方意愿或认识的行为。在实体上,即使是自愿和故意参与的交换,也不得使任何一方承受与他所获得的利益极不相称的代价;这样的交换也不能不正当地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或一般的社会利益。”[7]正因为有了互惠,才能真正实现权利,所以,“欧洲数以千计的新城市和城镇发展出它们自己的法律类型,这种法律也具有以下特征:客观性、普遍性、互惠性、分享裁判权、整体性和发展的特性。”[7]657也就是说,“无论是权利互惠性的程序方面还是实体方面,都蕴含在自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以来西方人所理解的‘权利’这个术语之中。”[7]425从社会存在的角度看,没有互惠,就没有权利。当代中国有部分人“偏好”上访,迷恋于对绝对正义的追求之中,实质上就是忽视了权利的互惠性。他们一遍又一遍的上访,不仅给基层政府的正常工作带来了困难,也影响到了其他正常上访的公民实现自身的权利。比如,案例2中的唐某,其女儿尽管属于未成年卖淫,但是组织卖淫者也罪不当死,但是她却长期以来在各级政府缠访、违法闹访,已经严重的违背了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也妨碍了司法公正。案例3中,很明显王某不属于可以享受政策待遇之人,其多次进京上访的行为也给基层政府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因此,我们要呼吁的是,上访必须是有理、有据、有节。
第三,要根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促进上访行为应当法治化。上访既然是权利,一方面我们要从法律层面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上访行为也必须规范化。从我国目前的制度供给来看,有几项制度必须给予严格注意。首先是要放松对上访的规制,特别是不能将上访与政府的政绩联系在一起。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之所以上访成为中国社会的乱象,特别是无理上访盛行,成因之一在于将上访与基层政府的工作联系在一起,搞信访排名,强求政府化解矛盾。实际上,有些矛盾本身是政府酿造的,基层政府怎么解决?而有些矛盾,本是无理取闹,怎么能解决?可见,不恰当的要求对非正常上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访既然是公民权利,那么就应当让公民自由的享受这种权利。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必须不能无视那些违法上访的人。从法治层面来讲,我们必须强调依法办事,即上访过程中有违法行为,都必须严格处理。行使自己的权利是一回事,违法行为又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因为有部分人违法上访而急急忙忙废除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有部分人违法上访而放任违法行为发生。这就是法治化管理的基本原则所在。所以,在对待那些闹访、侵权上访等违法行为,我们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进行处理。我们的法院不能因为当事人一方在法院门口威胁自杀、跳楼等而遭受威胁,也不能因为当事人到北京去上访而网开一面。正确的做法是,法院不能受到上访因素的影响,当然也不能屈服于自杀和跳楼等行为。上级政府也应当依法打击因为当事人违法自杀带来的闹事行为。不受跳楼威胁的影响,损害的只是无理取闹之人的利益;但是如果司法不公正,损害的却是整个国家的威信!
最后,要根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吸引民众通过司法解决矛盾和问题。上述已经指出,当代中国民众“偏好”上访的基本原因在于利益诉求机制不畅,其中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司法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机制得不到发挥。认真对待公民的上访权利,就应当认真对待司法,让司法在整个社会当中发挥真正的作用。具体规划是:首先是废除法院的不予立案制度。司法机关本来就是解决矛盾的机关,如果这个案件不立,那个案子也不立,司法机关还能发挥作用吗?涉及政府的案子不敢立,稍微复杂的案子不敢立,那么人们怎么会相信司法机关呢?在司法没有作用的体制中,上访会成为必然选择。正如上文所说,在法治建设中,如果法院从政治利益考虑而拒绝受理一些案件,那么最终法院失去的将是最大的政治利益——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享有公平的审判权利是法治的核心要求。”[8]如果民众之间或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基本诉讼要求无法在法院获得解决,要么他们或寻求上访,要么就会寻求其他一切方法,甚至是暴力方法。我们认为,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立案条件,法院应当立案;凡是法院不立案的,都应当以渎职来追究责任。其次是要进行改革司法体制。十八届三种全会已经将改革司法体制当作是我们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重心,主要内容是要去行政化、去地方化,树立法院权威和法官权威。主要内容是要将法院脱离地方管理体系,所有法院的财政要纳入中央财政范畴统一支配,任何人都不得干预;法官系统纳入独立的公务员管理系统,当然,也还需要根据司法改革的需要,建立其他相应的配套制度,比如改革法院现行的人事制度。这些年司法改革的最大问题在于,司法职业化努力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想象的廉洁、公正的司法,相反,一个维护自身利益胜于维护社会正义的法官群体正在形成。因此,我们要破除法官群体的利益,特别是官本位利益。从根本上说,如果法院权威和法官权威树立了起来,司法腐败行为大大减少,地方政府很难干预司法,行政权力不再是一切权力之源,“偏好”上访的人终究会站到诉讼的队伍中来。
五、结语
回到本文的开头,我们会发现,上访行为只是制度供给当中的某些碎片化问题导致的时代现象。这意味着,我们要解决上访问题,不能迷信于“文化论”的思维,而是要从现实的制度需求着眼。任何时代任何人的行为都应当是有规范的,不管是来自于伦理的、道德的,还是法律的。我们当然要思考传统的力量,但是更应该重视倾听现在的声音。而且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会有相应的问题,也需要有具体的解决办法,但是根本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法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说法治是人类所寻求到的治国理政之最好方法的根本原因所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题任务之下,只有从根本上变革国家治理制度,“上访”才会逐步回到法治的轨道!
参考文献:
[1]封丽霞.中国人为什么“偏好“上访——一个法文化视角的观察[J].理论与改革,2013,(04).
[2]陈柏峰.无理上访与基层法治[J].中外法学,2011,(02).
[3]司马迁.史记(卷十)[M].长沙:岳麓书社,2012.369-373.
[4]夏炎.古代的“越级上访”[J].人民论坛,2013,(03).
[5]黄纯艳.宋代的登闻鼓制度[J].中州学刊,2004,(06).
[6]张兆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M].长沙:岳麓书社,2004.23-24.
[7][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25.
[8][英]汤姆·宾汉姆.法治[M].毛国权,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128.
(责任编辑:天下溪)
Preferenceto Peti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Based on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WANGLiang,PENGZhong- li
()
Abstract:Some people think that the contemporary China are preference to petition,because it is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petition has existed in ancient China,but in the ancient China was not developed. Moreover,the reason for the existence of petition system in ancient Chinese is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confusion,the petition is equivalent to today's appeal. Contemporary Chinese are preference to petition,the most direct reason is the supply defect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First,the public interests expression mechanism is not smooth;Second,the judicial rights safeguard is difficult;third,the policy of the reverse encourage the petition to imply the system requirem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to promote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modernization must treat seriously petition and the petition problem must be legalization.
Key Words:Petition;the Rule of Law;National Governance;System Supply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 1140(2016)03- 0000- 00
收稿日期:2016- 02- 27
基金项目: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国家政策的民事司法运用研究”(15FFX017)
作者简介:王亮(1982-),女,湖南沅江人,中共湖南省委直属机关党校行管法学部讲师,主要从事诉讼法学研究;彭中礼(1981-),男,湖南隆回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法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