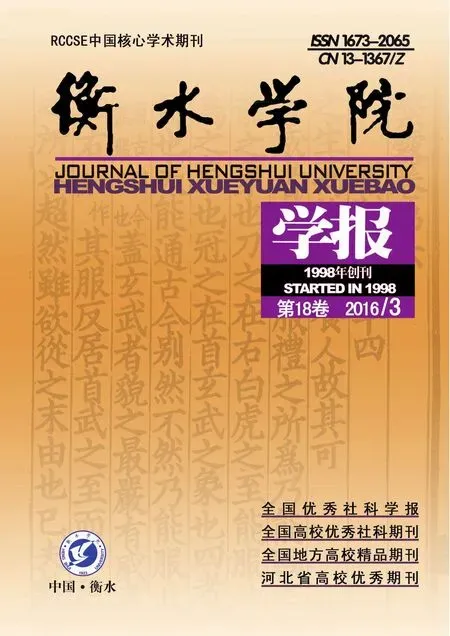孟子与董仲舒对仁、义理解之同异
陈 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社科部,北京 100089)
孟子与董仲舒对仁、义理解之同异
陈 昇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社科部,北京 100089)
摘 要:把仁理解为恻隐之心(董仲舒称爱人),是孟子与董仲舒之所同。孟子在讲恻隐之心(即爱人)与亲亲之间,孟子更看重亲亲,董仲舒则更看重爱人;孟子理解的仁(恻隐之心)是自然而然的情感,董仲舒理解的仁(爱人)带有很浓厚的理性成分。董仲舒理解的仁只是爱别人不能包含利己的因素,孟子理解的仁既是利人也允许利己。这是二人之所异。孟子与董仲舒都认为应当用义来调节君臣关系,但是对义的具体含义二人的理解大相径庭。二人都讲义利之辨,但对义、利的含义理解不同。二人都认为仁与义有密切的关联,但是对于关联的表现理解不同。
关键词:孟子;董仲舒;仁;义
《论语》中有“仁”“义”二字,但仁与义二字尚未连用。仁义二字在孟子与董仲舒那里既单独使用,也把仁义连用。但二人对仁、义的理解,有同有异。研究此问题也许有助于了解这一历史阶段价值观变化的走向。
《春秋繁露》篇幅庞大,仁义二字出现频繁,一时不能逐字考证,令人遗憾。
一、对仁的理解
1. 相同之处
把仁理解为“恻隐之心”是孟子与董仲舒之所同。
《论语》中没有用“恻隐之心”释仁的语句,用“恻隐之心”释仁是孟子的发明。孟子讲“恻隐之心,仁也”(《孟子》11.6),又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3.6)、“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等等。用“恻隐之心”释仁,实际上是在揭示仁者为什么会爱别人的原因。反过来说,没有同情心的人是不会爱别人的。在这个问题上,董仲舒与孟子的理解相一致。董仲舒认为司马子反“废君命,与敌情”[1]51之所以被《春秋》肯定,是“为其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远之而大,为仁者自然而美”[1]52。这些评价都是说司马子反有恻隐之心。可见董仲舒也是同意用恻隐之心释仁的。
2. 相异之处
其一,孟子既讲“恻隐之心,仁也”(《孟子》11.6),又讲“亲亲,仁也”(《孟子》12.3,13.15)。在这二者之间,孟子更看重亲亲,而董仲舒更强调爱人。这是二者之所异。
《论语》中记载了多位弟子问仁于孔子,孔子没有一次用“亲亲”作答。《论语》中唯一把亲与仁联系在一起的语句,是“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8.3) 。用“亲亲”释仁、揭示仁的功能,是孟子首倡的。所谓“亲亲,仁也”,是说爱自己的亲人是有仁德的表现;换成另一种说法,那就是爱自己的亲人是仁德的重要功能。“亲亲,仁也”的另一种说法是“仁之实,事亲是也”(《论语》7.27),即事亲是仁德所结的果实。《春秋繁露》中也出现几次“亲亲”用语,但都没有把仁与亲亲直接联系在一起。
其二,孟子把恻隐之心视为自然而然的情感,董仲舒所理解的爱人带有很浓厚的理性成分。这是二人又一个相异之处。
在孟子看来,“亲亲”与“恻隐之心”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13.15)。在讲恻隐之心时,他特意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3.6)所谓“乍见”就是突然看见,没有思想准备,事先没有思考的过程。这种恻隐之心是纯粹的情感因素,没有半点理性思考在其中,没有任何超出救人之外的目的。
而董仲舒所讲的“爱人”不纯粹是情感因素,其中的理性思考是十分明显的。请看他所举的例子:“仁者,爱人之名也。巂,《传》无大之之辞。自为追,则善其所恤远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则弗美。未至预备之,则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蚤而先之,则害无由起,而天下无害矣。然则观物之动,而先觉其萌,绝乱塞害于将然而未形之时,《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非尧舜之智,知礼之本,孰能当此?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远,而《春秋》美之。详其美恤远之意,则天地之间然后快其仁矣。非三王之德,选贤之精,孰能如此?是以知明先,以仁厚远。远而愈贤,近而愈不肖者,爱也。”[1]251-252这里所讲的“爱”,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一个军事集团的行为。这种行为也可能包含着爱人的因素,但它是以“先知”为前提的。这个“以知明先,以仁厚远”固然有“爱”在其中,但也有很多理性思考在其中。“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理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1]254。“推恩”这个术语是孟子首先使用的,它是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概括。推恩者推己及人也,其心理过程是情感和理性两种因素同时在起作用。由此可知董仲舒讲的“爱人”不是纯粹的自然而然的情感,其中有理性因素。
其三,董仲舒理解的仁只是爱别人,不能包含有利己的目的在内。孟子理解的行仁既是利人,也允许包括利己的因素在其中。这又是二人的一个重要区别。
在《仁义法》中董仲舒讲:“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1]250又说:“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此之谓也。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著于顺逆之处也。”[1]254在董仲舒看来,行仁应当完全是无私的,不应有利己的意图在内。在这个问题上,孟子的理解与董仲舒有所不同。
《孟子》一开篇就提出了君王应当行仁义的问题。“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1.1)过去我们大多把这段话解释为“孟子把道德和功利看成是对立的”[2]。冯友兰认为这段对话是“孟子特别注重动机的言论。儒家认为义与利是对立的,孟子特别强调这种对立”[3]。张岱年也说“孟子尚义反利,比孔子更甚”[4]。
现在,我们除去极左思想的影响去反复读《孟子》时,会觉得我们过去对孟子讲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解释大概是错误的。孟子并没有用仁义排斥、否定对利益的追求,而是讲仁义与利益是相通的。行仁行义对于主体来说也有利可得。朱熹在解释“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时就说:“此言仁义未尝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义而已之意也。”(《孟子集注》卷一)
孟子虽然讲“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但他对行仁行义可以给行为主体带来利益是坚信不疑的。此言有何根据?根据就是他对于仁的功能以及他对君王行不行仁义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的论述。
孟子在讲到仁的功能时认为仁是“人之安宅”。他说:“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7.10)在另一处他又说:“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13.33)
孟子所说的“仁,人之安宅也”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行仁德能庇护自己的生命与有利于自己的事业。他引孔子的话说:“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孟子》7.2)又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7.3)这些论述都表明,孟子认为行仁义对于行为主体自己是有莫大的益处的;而不行仁义,灾难迟早会降临到头上。
我曾经把“安宅”解释为人的精神家园,认为仁是安顿人的灵魂的地方,行仁则己心安。没有这个精神家园,人的灵魂就无家可归,不得安宁。这样解释是把仁作为一个名词对待的,是把人视为一个精神存在物看待的。这样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反复读《孟子》中的相关文字,觉得在《孟子》中“仁义”二字在很多地方不是当名词用,而是当动词用的。仁义当动词用时可解释为行仁行义。这个时候,仁义就不仅仅是人的精神家园了,它就变成了能切切实实庇护人的生命、成就人的事业的“安宅”与“正路”了。就是说,人行仁义不仅是为了爱护别人,它也能给自己带来切切实实的利益,甚至他说“以德行仁者王”(《孟子》3.3),又说“仁者无敌”(《孟子》1.5)。
这就是说行仁义对于利益攸关的双方都有利,在孔子那里称之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时下流行语把这种行为叫做“双赢”。因此,行仁义比只讲单方面对利益的追求要好得多。它在自己得利的时候兼顾了相关方的利益。如果只是追求自己一方面的利益,就会形成孟子说的“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孟子》1.1)的局面;行仁义能够在人我之间达到双赢,这就是所谓的“美美与共”。
二、对义的理解
1. 相同之处
董仲舒在《仁义法》中说:“义云者,非谓正人,谓正我。”又说:“义在正我,不在正人。”这是董仲舒对义的功能的一种理解。《孟子》中没有与“义在正我”相似的表述,但我认为孟子对义的功能的理解,有与董仲舒相通的地方。请看“羞恶之心,义也”这句话。
所谓“羞恶之心”,讲的是行为主体的一个心理过程的两个阶段。当行为主体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背了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时,首先是自己会感到羞愧、内疚,这是第一个阶段。如果过失比较严重,悔恨的情绪比较激烈,当这种激烈的情绪发展到主体感到自己面目可憎时,就会谴责自己,深刻反省自己的过错与采取相应的补救行动,以减轻自己的过失和平衡自己的心理。这是第二个阶段。只有内心的羞耻,没有由憎恶自己所导出的反省与行为上的改正,那还不能说“义在正我”,至少是正我的勇气不足。只有达到憎恶自己的过错,下决心痛改前非,才能算是“正我”。据此,我认为孟子虽然没有“义在正我”的表述,但是有“义在正我”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孟子与董仲舒对义的理解有相通、相同之处。
不过要是按照朱熹对于这句话的解释,就不能得出我所讲的结论。他说:“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也。”(《孟子集注》卷三)他认为“羞”与“恶”的主体是一个,而“羞”与“恶”的对象是两个。“羞”的是自己,“恶”的是别人。“恶”别人当然就不可能“正己”了。我以为朱熹对“羞恶”的解释只对了前一半,后一半是错误的。
2. 相异之处
其一,孟子提出五伦说,其中第二伦是“君臣有义”(《孟子》5.4)。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多次论述“君臣大义”。他们二人都认为君臣的关系要由“义”来调节。这是二人之所同。但是对于君臣之义的具体内容,二人的看法大相径庭。这是二人之所异。
孟子虽然主张“君臣有义”,但是他对这个“义”的具体所指,没有一个概括的说法。我们只能从他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中来概括:
第一条: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2.8)
第二条:“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孟子》7.1)
第三条: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8.3)
第四条: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孟子》8.3)
第五条: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10.9)
从以上五条论述看,孟子所讲的“君臣有义”包括以下几点意思:第一,君臣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不分高低。由此决定了处理君臣关系的原则是相互尊重,共同维护。第二,为臣的有责任、有义务对国君提出相关的建议与意见,为君的应当择善而从之。否则,臣有权废掉君,另立新君;或者是弃君而去。第三,对于残暴之君,为臣的有权处死他。
董仲舒所理解的君臣大义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他在《盟会要》中说:“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1]141这个意思在《正贯》中又重复了一遍,具体说法略有变化:“立义定尊卑之序,而后君臣之职明矣。”[1]143在《玉杯》中他说:“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1]32在《王道》一文中对尊卑之序讲得非常具体:“《春秋》立义,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诸山川不在封内不祭。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适天子之贵。君亲无将,将而诛。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废置君命。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夫人以适不以妾。天子不臣母后之党。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1]112-116而他对君臣关系最简要而又最深刻的表述,莫过于三纲五常中所讲的“君为臣纲”。
孟子与董仲舒都讲“君臣之义”,但义的具体内容相差甚远。
其二,他二人对于义利之辨中的义与利的理解也有不同之处。
董仲舒也谈到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但是仔细推敲,董仲舒使用的义与利的含义,与孔孟所讲的义与利的含义已经有了不小的差别。
不论是孔子讲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4.16)还是孟子讲的“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孟子》9.7),义都是指道德原则,利是私人利益。道德原则是什么?道德原则看来是抽象的条文,但一旦付诸实践,道德原则所承载的就是公共利益。到了宋、明时期,理学、心学都认为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的问题。就是说,在道德实践中,孔孟讲的先义后利,就是把公共利益摆在第一位,其次才是个人的私利。如此看来,孔孟讲的义与利实际上是如何处理公私两种利益的关系问题。而董仲舒在《身之养(莫)重于义》中所讲的义与利的关系,并不是公利与私利的关系问题,而是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
董仲舒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于)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1]263这个“义”中包括了道德原则,但不能归结为道德原则,它是与物质利益相对的、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的总称。其中包含道德原则,但不限于道德问题。他讲的利也不是私人利益,而是人不可或缺的物质利益。我这样理解董仲舒义与利的含义的根据,就是他是把“利”与“体”(即人的身体)联系在一起,把“义”与“心”联系在一起。所谓“利以养其体”,就是滋养肉体的是物质利益;所谓“义以养其心”,就是滋养心灵(人的精神世界、人的灵魂)的是精神食粮。难怪胡毋敬说:“此篇与孟子‘养其小体为小人,养其大体为大人’相发明。”[1]263苏舆在这句话下面写道:“宋程子言‘义理养心’,本此。孟子曰:‘义理之说(悦——陈注)我心,犹刍豢之说(悦)我口。’”[1]263苏舆对于董仲舒所用“义”字含义的理解我以为是符合董仲舒的本义的。孟子所讲的“小体”是耳、目、口、鼻、四肢等,“大体”是心——精神世界。耳目口鼻四肢靠物质食粮滋养,精神世界(心)靠精神食粮滋养。这与董仲舒讲的“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完全相同。
三、对仁义的理解
1. 相同之处
其一,孟子与董仲舒都既把仁、义二字单独使用,也把仁义二字连用。之所以要把仁义二字连用,表明他们认为仁与义这二者有某种关联性,分开使用时体现不出这种关联性。
从董仲舒在《基义》篇的论述来看,他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与其相对的另一物在伴随着它。他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右,必有左;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董仲舒虽然没有十分明确地说仁与义也是相偶合的关系,但是他在总结这段论述时说:“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1]350-351他所说的“仁义制度”我理解就是所谓的“仁义法”,即“仁大远,义大近”“仁主人,义主我”等。
这就表明他是把仁与义也视为一种“凡物必有合”的现象,即仁与义在性质、功能上有相反之处,但它们又相互关联在一起。这种关联表现在它们是同一个复杂事物的两个不同的环节;其功能只有在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的时候,这一复杂事物才能正常存在与发展。具体地说,只有以义正我、以仁爱人,才能处理好人我关系。
《孟子》中虽然没有相似的理论阐述,但是仁义连用达 27次,仁与义对举有 10多次。孟子认为仁与义有关联是可以肯定的。在肯定仁义相关的问题上,孟子与董仲舒同。
其二,董仲舒在《仁义法》中讲“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他反复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1]250-251他要求人们明于仁义之别,“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董仲舒讲的仁义之分是有价值的,因为《论语》中虽然讲了仁是爱人,但并没有讲义是正我。
董仲舒从功能上明确区分仁义的思想在孟子那里有相通之处可寻。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孟子》11.6)另一处讲“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3.6)“恻隐之心”即对他人的同情心,对他人的同情心也可以说是爱他人。“羞恶之心”即是对自己过错的悔恨、内疚之情。对自己过错的悔恨、内疚之情是主体的自我批判、自我纠正的行为。这就是董仲舒所讲的“以义正我”。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的提法中虽然隐含着董仲舒讲的仁义之分,但孟子的立意不是董仲舒讲的“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所以很少有人从人我之分的角度去理解“恻隐之心”与“羞恶之心”的关系。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孟子对中国后来的影响,远远不如董仲舒大。孟子的贡献在于对孔子仁义思想的发展。其一,他明确了“恻隐之心”与仁的关系;其二,明确了孔子在回答“樊迟问仁”(《论语·颜渊》)时所说的“爱人”的“人”是指他人。其三,“义”在《论语》中出现24次,没有一次是明确阐述义的含义。“羞恶之心,义也”的表述,是对“义”的一个义项的揭示。
其三,董仲舒在《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中有一句名言,即“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这个说法与《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说法有很大的区别。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评价董仲舒,不能采用《汉书》上的说法)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董仲舒与孟子的认识有一致的地方。
“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与孟子讲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可以说是一个意思,即都是讲“义”(与“利”相对的“道”也就是“义”)是本,利是末。“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就是说在自己的“道”尚不端正的时候,先要端正自己的“道”,而不能为了获得一点利益而忘记端正自己的道路。简单地说就是不能急功近利。只要自己的道路、方向是正确的,功利自然就能够获得。
《孟子》中虽然没有相似的语句,但这个思想在《孟子》中比比皆是。孟子说“以德行仁者王”(《孟子》3.3),又说“仁者无敌”(《孟子》1.5),“仁,人之安宅也”等论述中,都隐含着一种思维方法。即看问题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根本的、方向性的问题。所谓“仁者无敌”之类的说法,都是一种战略家的眼光,是从长远、从根本上讲的,而不是战术行为。把“仁者无敌”当作战术是错误的,必然会带来类似宋襄公那样愚蠢的行为。
2. 相异之处
虽然孟子与董仲舒都认为仁与义二者之间有相关联的地方,因此有时要把二者连用,但是他们对于仁与义的具体关联是什么,认识不太一致。
董仲舒在《基义》中说:“凡物必有合。”从行文看,他所讲的“合”是相对的意思,所指的是世界上只要有一种事物(或事物的一种属性)存在,就必然会有另一种在性质上与之相反的事物(或事物的一种属性)与之相对(二者除了性质相反之外,是否有相互依存的一面,不太清楚)。按照这一理论,与“仁”相对的则是“义”。他在《仁义法》中反复说:“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又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仁主人,义主我。”等等。就是说,董仲舒所理解的仁义的关联性,表现在二者在性质上有相对的地方。所以他说:“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著于顺逆之处也。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1]254
孟子所理解的仁义的关联性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其中第一种与董仲舒理解的关联性相同。
其一: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也。(《孟子》1.1)
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13.15)
这两段话中的“仁”与“义”所表征的是一种亲与疏的关系。仁为亲,义为疏。用董仲舒的模式讲即是亲与疏相对,有亲必有疏。
其二: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11.11)
这一段话中的“仁”与“义”表征的是内心世界(灵魂)中两种既不同而又不是截然对立、互不关照的因素。仁是人的内心世界中的情感,义是人的内心世界中的理性。不过对后者要做一番说明:义仅就羞恶之心而言,也是情感——羞愧与憎恶。但是,这个羞愧与憎恶之情是事物的外在现象,它是人的内心世界中的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的外在流露。其根本的环节、起主导作用的是理性判断,即主体根据公认的行为准则判定自己的行为失当。从根本上说,义是人的理性表现。所以仁与义有较明显的情理的关系。情与理交织在一起,相互制约,甚至经常发生冲突,然而二者又不能分离。情与理的关系协调,既合情又合理,是中国文化所追求的境界。《孟子》“尽心上”第35章所表现的就是折衷于情与理的问题。
其三:
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13.33)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7.10)
这两段话中的仁义的寓意与上一段相似,都说仁是人生的安宅,义是人生的道路。但从用语上看,孟子是用安宅和正路的比喻,强调了仁和义缺一不可的关系。仁是家园,义是道路;有家必有路,走对了路才能找到家。
孟子大量使用连用的与对举的仁义,是在向人们表明仁义是有关联性的,只有仁没有义或者是只有义没有仁都是不行的。亲疏要兼顾,情理不可只居其一,仁与义、内心世界与外在的行为不可分割。
孟子与董仲舒对仁义理解的同异,似乎反映了从先秦到两汉儒家价值观的继承与变化。
参考文献:
[1]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 朱伯崑.先秦伦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1984:68.
[3]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七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247.
[4]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387.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Mencius’ and Dong Zhongshu’s Understanding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CHEN She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China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tudies,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The similarity of Mencius’ and Dong Zhongshu’ understanding of benevolence is that they both considered it as sympathy. When it came to the love for everybody and the love only for one’s relatives, Mencius attached more importance to the former while Dong Zhongshu to the latter. Mencius thought that benevolence was one’s natural emotion while Dong Zhongshu considered that it was more rational. To Dong Zhongshu, benevolence was loving others without any thought of self, however, to Mencius, it benefited both others and self, and this is their difference. Both Mencius and Dong Zhongshu thought that righteousness should be used toregul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arch and his subjects, but their understandings of the specific meaning of righteousness were quite different. Both of them mentioned the differences of righteousness, but their understandings of their meaning were different. Both of them considered that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but the understandings of their relevance were different.
Key words:Mencius; Dong Zhongshu;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6)03-0012-07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6.03.003
收稿日期:2015-04-27
作者简介:陈 昇(1945-),男,山西闻喜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科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