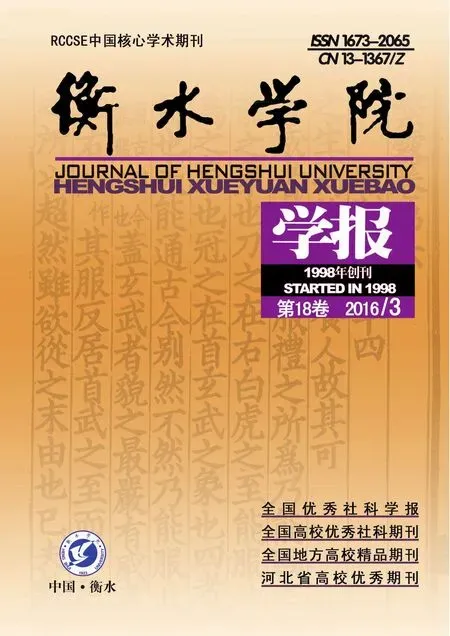紧扣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本核心
——钱耕森教授“大道和生学”的逻辑内涵
陈 驰 山(广东省文史馆 深圳教育基地,广东 广州 510000)
紧扣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本核心
——钱耕森教授“大道和生学”的逻辑内涵
陈 驰 山
(广东省文史馆 深圳教育基地,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大道和生学”是钱耕森教授从中国传统哲学中精思慎为而得出来的科学结论,文章从中国传统逻辑与中国知识论关系中给予了内涵阐述,证实了钱耕森所构建的“大道和生学”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基础上的,与中国社会现代发展中的思维关系是密切关联着的,对丰富与发展中华民族理论思维是一个历史性推进。
关键词:钱耕森;“大道和生学”;中国传统哲学;人本核心;逻辑内涵
一
2015年10月,在北京清华大学纪念我国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诞辰120周年大会上,与钱耕森先生交谈甚欢。会后,谈及他的“大道和生学”,更是让我兴奋与感叹!钱先生作为长辈身体力行地为中华走向世界高峰的理论思维倾心尽力,中国哲学思想是以中国思想特征为基础的,先生八旬以上高龄还在中国浩瀚的文史资料中精思谨为,提取中华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构建“大道和生学”数篇论文(载于多期《衡水学院学报》、《光明日报》2015年 3月2日(国学版)、台湾《孔孟月刊》401期),读先生的论文时给我以极大震撼,这是先生数十年心血的结晶,是长期对中国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研究与思考的成果。
二
一个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以她的理论思维高度作基本标准的。所以,给出认知世界的基本方法与社会实践的一致性,被世界公认为标准。思想家在历史文化中精为思考,又在现实实践磨炼中求索,才具有这种理论思维的高度。尤其在现今物欲横流的世界,更是要有耐得住的寂寞。一看到钱耕森先生的“大道和生”就会想起先秦思想家尹文子的“大道”专论中“大道容众,大德容下”的思想主旨,思想家史伯“和实生物”(《国语·郑语》)更是耕植中华文化的土壤,更使人们的思考进入一个恢宏的空间。一个学科体系的成立应具三大要素:一是具有深厚的哲学文化历史与文化价值(基于实用价值的);二是具有学科体系自己的概念基础;三是具有始终如一的逻辑关联所反映出来的性质体现。按照这种严格的学术标准,来审视钱先生的“大道和生学”学科体系,我们会惊见先生以深厚理论思维的大雅之笔及开拓风范。
三
钱耕森先生的“大道和生学”是成体系的哲学专论,是以“和实生物”的物质的存在为基础的,以“大道”作语义限定的,其“大道和生学”命题之中就具有了“大”“道”“和生”“学”几个重要的范畴词连缀。这几个范畴词,也是中国哲学史上内涵极为丰富的范畴词,钱先生把它们的价值发掘出来是功德无量的,所构成的学科体系关系中的个体关联所反映出来的性质,可以说是浓缩了中华几千年文化的精粹与精华。
世界一切事物的存在中,对理由与根据的真实存在的认定,是我们掌握真理的途径之一。纵观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史,对“大道、和生”名词的解释也是非常至精至到的,掌握它们不同的语义内涵对理解钱耕森先生的“大道和生学”是有极大帮助的,是对钱先生“大道和生学”学科体系掌握的入门基础之一。
首先,我们对“大道”这个概念的存在做一个理论解释。“大”的存在是中国哲学中对思维存在特征表现的一个精简概括与固定,它最早出现在《易经·坤卦》中,“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这个语句中的“大”是与“直、方”联系起来讲的,简单地讲就是“对直、方、大的存在不学习掌握,是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学问的,对办任何事情都是不利的”,这是作为知识对象范畴讲的;尹文子认为其重要性是:“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杂。然后术可秘,势可专。”(《尹文子·大道上》)
“道”在最早的文献中的出现也是在《易经》之中,是以“有孚在,道以明”(《易经·孚》)的关系承载出现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存在为依据,就为道的存在提供了根据与理由”,这是作为知识内容的范畴讲的;老子《道德经》开篇中的“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第章)也是作为知识内容的范畴讲的,是对“名”的最高概括。
为什么“大”与“道”的存在及关系这么重要?我们看一看思想家尹文子的论述就知道了它们存在的价值了。他对“大道”的存在有“无形、不称、无称”(《尹文子·大道上》)的语义限定而成为必然的“有名”“有必名”,都是对“大道”作为范畴的存在价值的功能给出的,“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大道;不称、众有必名”“大道;无称、有名”(《尹文子·大道上》)。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范畴的存在是与“类”的“实”关联的“有名”与现实世界的关联为必然的存在,在《尚书·洪范》中箕子就要求“畴”(种类)、与“祉”(事物存在的根据)紧密关联,“洪范九畴”(九条大法)的出现,正是在这些重要传统哲学要素表现过程中,呈现出了尹文子的“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这些事实存在都说明了“大道”是作为思维存在的抽象范畴的,与“直、方”形成了逻辑上关联而成为必然,也与中国众多思想家的思想论述像老子的“枉则直”、在“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老子》第 22章)的要求中就是用“道”作限定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 42章)是作认知规律阐述的,是形成“常道”的一个条件,“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为“式”,是一个喻例;“物”则为“常”;笔者这里是以金岳霖先生在他的名著《论道》中的“道、式、常”条件解释的,“道”是作为对范畴阐述的专名。像“和实生物”本质上就是事物存在的基本规律,是一个人们对事物认知时所抽象出来反映其性质存在的一个范畴,“和实生物”也就是“常道”而不是直指的“道生万物”。从中国逻辑方法论上来看:墨子的“大方、小方、多方”对事物可以从大的、小的、不同的角度去定法取类。像“人类社会”为存在的根据“大方”时,国家的存在就为“小方”,形成国家存在中的各种政权结构即为“多方”,就对“大道”形成了逻辑与知识论的关联,成为“大道和生学”的有机载体,因而构成“大道和生学”逻辑词项的关系承载。
四
钱耕森先生对“大道和生学”的本体论述是“和”,对先秦时期思想家史伯的“和实生物”以深度的揭示,在对史伯思想的论述中以理论条件、定义、影响、传承与现实适应五个方面给予了肯定,使我们直接与古代思想家对话,在《尚书·虞书·尧典》“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大意是:“羲和,恭谨地遵循上天的意旨行事,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来制定历法,以教导人民按时令节气从事生产活动”的“羲与和期望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周期,剩下的天数,每三年置一闰月,以推定春夏秋冬四时而成岁。由此规定百官的职务,这样许多事情便得以顺利进行了”)时的范畴限定“畴咨若时登庸”,从而达到“畴咨若予采”(大意是:限定“谁能顺应四时的变化获得功绩”,从而达到“谁能够根据我的意见来办理政务”)的应用目标的“和实生物”。从钱先生所构建的“大道和生学”体系的范畴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生是把“和实生物”作为哲学本体的,“和实”是物质的存在关系的关联,是理由也是根据,从中我们就得出“生物”的结果;“大道”是对“和生”的限定与判定,都为逻辑条件率关系的关联,形成逻辑与知识论关系存在结果的,形成了性质与关系的统一。
世界万事万物都是存在于矛盾之中的,在世界哲学史的发展中是这样,在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中也是这样,“大道和生学”把“和实”作为主体的认知理念,那么就有“不和、不实、和虚”等矛盾语词语义的关系对应,同样在“和实”的存在中也有生成条件的 “阴阳”等等矛盾关系的关联,这些都是知识论与逻辑学解决的“调和”问题。这些问题都为“大道和生学”的表现形式,从时空观念上讲使我们的思维来一个质的飞跃。鸠摩罗什大师在翻译印度哲学家龙树的《十二门论》,也是自然界存在的十二种范畴中,就有因缘门(范畴的关系构成)与生门(范畴生成的条件)对“生”这个范畴的论述,其“生生之所生,生于彼本生;本生之所生,还生于生生”(指“生生”的现象与“本生”的本体,是互生的)为关系反映性质的存在条件,当与范畴词“生”联系时,我们就会想到毛泽东主席所赞美的,先秦思想家郑国人列子在《愚公移山》中,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力、以无可穷尽的“生生不息”挖山精神的现代继承,就是先秦楚国思想家庄子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庄子·齐物论》)(指生与死、可与不可……都是相对的,所以圣人就不走这条路,而是顺其自然如实地反映客观现象的“天道”)的自然现象存在中的认知规律掌握,从而启迪我们的思维以“和生”相关联的适应时代实践的需要。
五
钱耕森先生所构造的“大道和生学”学科体系,我们可以归结为人本主义哲学体系范畴。一个成体系的哲学范畴也是具有严格的本体论、知识论、工具论(逻辑)标准的,它们的个体存在的关系是互相渗透关联的。这是我们理解钱先生学科体系的关键的地方,也是掌握钱先生“大道和生学”学科体系并成为我们认知世界的哲学方法论之一。
(责任编校:耿春红 英文校对:杨 敏)
Sticking to the People-oriented Co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Logical Connotation of Qian Geng-sen’s Tao's Harmony Giving Birth to the New Things Theory
CHEN Chishan
(Shenzhen Education Base,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e and History in Guanhdong Province, Guangdong, Guangzhou 510000, China)
Abstract:Through a thorough and careful thinking about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Qian Gengsen drew the conclusion of “Tao’s harmony giving birth to the new things theory” scientificall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illustrated the connotation of his theory in the aspec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traditional logic and Chinese knowledge and then proved that his theory was really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izing,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hinking relationship of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and which makes a historic advance in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heoretical thinking.
Key words:Qian Geng-sen; Tao’s harmony giving birth to the new things theory;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people-oriented core; logical connotation
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6)03-0044-03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6.03.009
收稿日期:2016-05-25
作者简介:陈驰山(1954-),男,湖南津市人,广东省文史馆深圳教育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