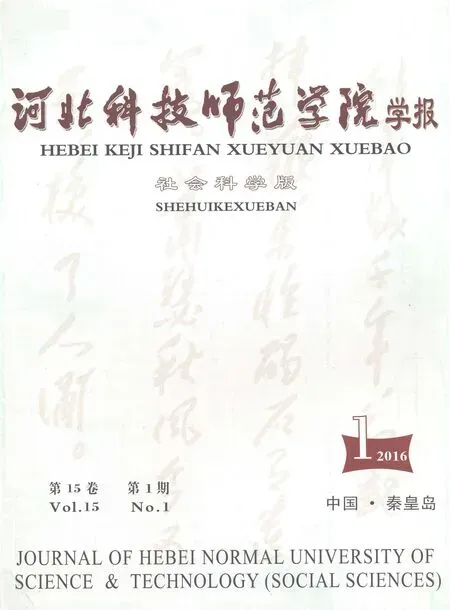论清代诗人“并称”佳话的传播途径与效应*
陈凯玲
(惠州学院 中文系,广东 惠州 516007)
论清代诗人“并称”佳话的传播途径与效应*
陈凯玲
(惠州学院 中文系,广东 惠州 516007)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流传着大量有关作家并称的佳话美谈,构成文学批评的一种特殊形式。清朝文坛上标榜诗人并称齐名的风气炽盛,传播并称佳话的途径和手段也是形式多样。以诗歌传播者,多以人物合咏、相互赠答的方式来表达和强化并称关系;以总集传播者,其书名通常冠以“×家”、“×子”等目,有助于并称名号的生成与定型;以诗话传播者,大多为零散、片言只语的点评,这也是清代诗人并称佳话的主要传播方式;以绘画传播者,表现为若干诗人联袂登图亮相,以真实的现场效果吸引更多人的关注。
清代;诗人;并称;传播途径;效应
“并称”是一种人物品评方式,即在不同的人之间做相提并论的评价。它起源于汉魏人物品评、清谈论事的风气*例如后汉的“前有管鲍,后有庆廉”,三国的“荀氏八龙,慈明无双”、“五氏五常,白眉最良”,西晋的“二王当国,羊公无德”、“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洛中雅雅有三嘏”,梁代的“二傅、沈刘,不如一丘”,北齐的“三崔三张,不如一康”等等。,最初作为人物月旦评的一种方式,以“歌谣”的形式流诸于口头。后来由于文学批评的需要,许多文学家并称也存在这种形式中,如“东海三何,子朗最多”[1]、“前有沈宋,后有钱郎”[2]、“前有四皇,后有三张”[3]、“文中三豪,浙中三毛”[4]等等。这一类歌谣式的评点虽只是三言两语,却能够迅速促成一段文坛佳话的流传。随着后世文人并称现象的不断繁衍,“并称”佳话的传播载体亦趋于多元,传播途径和手段经累代的选择与淘汰,至清代趋于集大成之势,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笔者拟就涉及清代诗人并称佳话者,选取诗歌、总集、诗话、绘画四种传播方式,通过典型案例,考察这些传播方式在当时文坛的使用与流行情况,力图揭示并称佳话流行背后的某些特征和规律,希望对整个古代文人并称的文化现象做一些积极的探索。
一、以诗歌形式传播
诗歌中有一类题目是专以若干人物为描写对象,可称之为“人物合咏”。由于这一诗歌形式本身具有相提并论的效果,故所咏对象一旦入题,便很容易构成某种并称的关系。换句话说,如果作家主观上有意要将某几个人进行并称的话,采取人物合咏的形式提出,将会是一种颇为有效的传播手段。
人物合咏最早见于咏史题材,多以历史人物为述叙对象,往往兼具史传、史论、咏怀等多重功能。南朝颜延之《五君咏》组诗,分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等五人,堪称为人物合咏诗的首创。唐代杜甫《饮中八仙歌》一首,则较早地将人物合咏应用于时人,打破了所咏对象为历史人物的传统范畴,为后世纷纷仿效。然而,这种写法在明代之前并不十分流行,只有到了明、清人手里才被熟练地运用。例如,明代何景明的《六子诗》,李梦阳的《九子诗》,李攀龙的《五子诗》,王世贞的《五子篇》《重纪五子篇》,吴国伦的《五子诗和于鳞、元美作》《八子诗》《十二子诗》,梁有誉、宗臣都分别作有《五子诗》,李开先的《九子诗》《六十子诗》,等等,大抵是作者“用以纪一时交游之谊”[5]。值得注意的是,从明代起,诗歌作为并称佳话的传播手段,有不少为同题创作,作者既咏他人,也为他人所咏,故所谓的“×子”往往也包括作者在内;于是,人物合咏也就带有了作者标榜齐名的意味。
在明人经验的基础上,清代诗人创作人物合咏的诗歌,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首先,人物合咏在日常赠答活动中频频出现,成为诗人间相互致意、推许的常用手段。比如,郭麐与彭兆荪初次相遇,有感而作《淮阴两生相逢行赠彭二甘亭》,彭兆荪作《相逢行答吴江郭频伽麐》应之,遂有“彭郭”并称之目。其次,人物合咏在题目上,更加鲜明突出人物的并称关系,常径直以并称群体的名号为题。即如张丹《“钱唐三子”歌》、石韫玉《“苏门六子”诗》、陈僖《“兹社七子”歌》、黄文旸《“阙里八诗友”歌》、张让三曾作《溪上诗人“三病夫一狂夫”歌》、万廷苪《“螺墩九子”诗》等题,与明人诗题中简单泛称“×子”相比,在并称提法的明确性上,无疑又进了一步。再次,某些人物合咏的模式往往被重复运用,构成“姊妹篇”系列。例如,陈文述先有《“两生”行赠沈生式如(秉钰)、蒋生黼庭(元甄)》,后又作《“后两生”行答朱酉生(绶)、沈闰生(传桂)见赠之作……》;此外,他还作有《“西湖两女士”诗赠汪逸珠、家妙云》《“后西湖两女士”诗为吴苹香、顾螺峰作》二诗。类似者还如丘炜萲《“诗中八贤”歌》及梁启超续作《“广诗中八贤”歌》,高旭《“诗中八贤”歌》《“后诗中八贤”歌》等等,也都是系列化的人物合咏,尤其是诗题已醒目标出文人并称名号,这对于并称群体的产生和定型,无疑是起到了积极作用。
并称的提法,除了以人物合咏的形式出现,还可以通过诗篇中的“警句”传达。例如,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与宋荤有齐名之目,其缘由之一,就是他们曾相互赠答推许的诗句。康熙四十年辛巳(1701年)时任刑部尚书的王士祯作《叹老口号寄宋牧仲开府》绝句一首赠江宁巡抚宋荦,诗有云:“尚书北阙霜侵鬓,开府江南雪满头。谁识朱颜两年少,王扬州与宋黄州。”[6]该诗巧妙地将两人名字嵌入句中,起承转合处皆对举成偶,如此警句播于艺林,便成为二人齐名并称之口实。
二、以总集形式传播
有关清人编纂并称诗人总集的情况,笔者已有专文探讨*参见拙文《清代诗人并称群体的繁盛及其启示——基于密集程度的抽样考察》,载《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49-54页。,兹就总集作为并称传播载体方面的表现,做一番专门讨论。
总集作为保存诗学文献的一种形式,记录和传播作家作品无疑是其第一功能,而就并称群体来说,总集还有其他的宣传效用。首先,以并称群体为选录对象的诗歌总集,其书名通常冠以“×家”、“×子”等目,这对于那些没有名号或名号不固定的并称群体来说,命名不确定的问题便迎刃而解。再有,一般总集都会有凡例、序跋之类的附件,编者可以通过它们介绍并称诗人的基本情况,从而取得读者对该并称群体的认同,加深读者对他们的印象。基于此种认识,就不难理解清人刊刻并称诗人总集的热情何以历久不衰了。如康熙间,顾有孝与赵沄辑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诗为《江左三大家诗钞》“谋付剞氏,传布通都大邑”,“使海内之称诗皆以三先生为准的”[7],即以总集标立名目;又如,上及关于“王宋”齐名之目,所以能够成为文学史上一个固定的名称,关键是有总集作为传播手段。早在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年),宋荦便以己作合王士祯诗编成《渔洋绵津合刻》(一名《二家诗钞》),其门客邵长蘅为该集作序称“今海内称诗家,并称新城、商丘两先生无异辞,盖如室华之有太、少,禅宗之有南、北矣”、“两先生,一代之宗工”云云[8],极尽称美赞誉之意。宋荦不仅多次将此部总集寄赠友人,而且还进呈御览,该集实为助其成名之具。
此外,在报刊传媒工具缺乏的古代,书本实际是当时最为有效的传播信息途径,而总集正是具有书面化的优势,可以为某些带有歧义的并称说法下一论断。比如,有关屈大均、梁佩兰和陈恭尹三家并称的提法,在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年)王隼编刊《岭南三大家诗选》之前,在诗界并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据今人王富鹏先生考察,在王隼之前人们并举岭南诗人者,大多不止3人,或不足3人;虽也有将屈、梁、陈并举而不及他人的情况,但也只是偶然提及,不算是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组合[9]。而自《岭南三大家诗选》一出,屈、梁、陈并称遂成为一种盖棺定论。有关总集这方面的作用,不妨再以反例证之。清中叶曾有日本人安积信提倡吴伟业、王士祯、袁枚并称之说,欲辑三家诗并行,但该书似乎未见刊行,而吴、王、袁并称的提法,亦终究没有获得广泛认同[10];又如,清末以来文献对清初“(长安)十子”成员的记载常有错乱之处,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十子诗略》一书后来流传不广所致。
三、以诗话形式传播
诗话作为一种叙述性文体,主要承担着诗歌批评的任务,特别到了明清时期,大量诗话著作主要内容是记录文坛掌故、诗人轶事,当中不乏诗人并称的话题,甚至出现单纯针对诗人并称者,如道光间尚镕所撰《三家诗话》。该书以袁枚、赵翼、蒋士铨“乾隆三大家”为批评对象,全篇分“三家总论”、“三家分论”、“三家余论”三部分,其规模虽偏小,然条分缕析、论列精当,堪称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三家”的诗学论著。由于作者距离“三家”生活时代较远,故其所作与通常出于阿好之私者不同,诚如姜曾序言称:“若存贵远贱近之见,或以为妄下雌黄,或以为互相标榜,则乔客[尚镕]与余皆所不计焉。”[11]该诗话对“三家”诗作之优劣短长,多为平心之论,大抵许袁之巧丽而非其纤佻,许蒋之雅洁而非其粗露,许赵之赡博而非其冗杂;又往往置“三家”于历代及本朝诗人之列,以较量高下特色,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三家”的诗史地位。
除了上述一部专门性的论著以外,绝大多数的清人诗话,是将诗人并称现象作为可资闲谈的话题,其评论往往是“蜻蜓点水式”的发挥。常见的叙述套路,或侧重从生平交游叙群体之遇合,或侧重从具体作品论个体之异同,或仅仅作为介绍作家基本情况的一个附件。然而,正是这些大量零散、片言只语的点评,成为了清代并称话题的主要传播方式。以乾隆间的知名学者兼诗人法式善所撰《梧门诗话》,对当时诗坛人物并称现象多有留意。该书有不下50则的评诗条目提及诗人并称,且尤多关涉当时具有并称美誉的学者兼诗人,如“毗陵七子”中的洪亮吉、黄景仁、孙星洐、杨伦,“吴中七子”中的曹仁虎、钱大昕、赵文哲,“江左十五子”中的缪沅,“吴门三蒋”中的蒋征蔚,“广东四才子”中的张锦芳。民国间杨钟羲撰辑的《雪桥诗话》及《续集》《三集》《余集》系列,当中提及清代诗人并称的地方多达257次,除去重复出现者,亦不下200余次。由此可见,清代诗话载录并称信息之丰富,及其传播并称诗话题之热门。若就某一并称作家而言,在多部诗话中也都可能频繁曝光。以“乾隆三大家”为例,据笔者目前粗略统计,其见诸后人诗话之中(《三家诗话》除外),至少在25种、45条以上。此种情况,尤多发生在那些争议性较大的并称诗人身上。至于那些名气较小、声望不高的诗人并称者,在无力刊刻总集的情况下,恐怕惟有赖于诗话作家的采录,方可能不至于湮没无闻。
再有一种是专门收集并称词条的资料汇编,亦属诗话笔记一类的范畴。光绪间宗廷辅所辑《诗家标目》凡四卷,就是一部专门辑录历代作家并称群体、社团、诗派等专称的书籍,今人蒋寅先生《清诗话考》下编亦著录之。该书卷一为地域类,专取历来地方诗人并称群体或社团,尤详于清代;卷二为家族类,专收家族诗人并称群体。这两卷集中收录了历代的作家并称群体,在古代诗话著作中殊为少见。
四、以绘画形式传播
中国古代人物画中有描摹群体形貌一类,相当于用现代照相技术拍摄的“大合照”,可称之为“人物群图”。据说五代南唐画家陆晃(一作滉)即擅长作此类图画,《宣和画谱》称其:“善人物,多画道释、星辰、神仙等,而又喜为数称,如三仙、四畅、五老、六逸、七贤之类是也。”[12]可见,人物在图画中亦能构成具有特定意义的并称组合。在清代之前,绘画史上就已经出现与文人并称相关的人物群图,如宋代画家李公麟有《饮中八仙图》,就是以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并称佳话为题材。在清代,人物群图更普遍用于记录文人日常生活,其功能或为游宴雅集、诗文酒会增添雅趣,或为标榜名人、崇拜偶像渲染造势,故此承载着大量有关文人并称的信息。兹以涉及清代诗人并称佳话的六幅绘画为例,略作考证,以见并称话题在当时之流行。
例之一,禹之鼎《五客话旧图》。该图所纪,为康熙二十一年壬戌(1682年)七月王士祯、徐乾学、陈廷敬、汪懋麟、王又旦于京师城南山庄雅集之事。汪懋麟有《五客话旧图序》载五人订交始末甚详,其序称“古人以道义文章相合者,其游处与共,后人慕其风,辄见于图画,若香山、洛社、西园诸图记,流传最广,虽市儿贩妇皆知之。至于齐名比肩,连类以称,如厨、顾、俊及七子、五君诸品目,大抵皆一时矜饰之词,而千载而下,亦遂以为不可易,或亦不仅以其名也”云云[13],道出了写此画图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五人将来齐名千古,预先制造某些凭据口实。事实果然如此,该图流传至清中叶,仍大受世人追捧,“叹羡不置”,即如翁方纲、曾燠等著名诗人皆有题诗。“五客”在当时可称是京师坛坫、翰林馆阁之内名望颇高的几位诗人,其中徐乾学、陈廷敬、汪懋麟皆入史馆,自是过从频密;同时,陈廷敬与王士祯、汪懋麟与王又旦,又分别在“海内八家”、“(长安)十子”中,皆为同游唱和之辈。
例之二,佚名《渔洋、绵津合像》。此图藏于苏州邓尉山圣恩寺还元阁内,为王士祯(渔洋其号)、宋荦(绵津其号)两公合像。汪学金《静厓诗后稿》卷四《登还元阁题渔洋、绵津两先生合像》一诗有云:“诗卷长留良有以,画图合并岂无因。”[14]该诗系于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另检宋、王二家诗文,见有题当地名胜之作,但均不曾提及合像一事。据此可推断,合像应是后人借重二家名气以提高景点知名度的一个手段。
例之三,程拱字*按:《续修四库全书》第1701册影印乾隆间刻本《随园诗话》卷四第六十九则,称“程拱字”,而今日通行之《随园诗话》或有将“字”误作“宇”。《拜袁、揖赵、哭蒋图》。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年)前后,江南诗坛流传有桐乡秀才程拱字手绘《拜袁》《揖赵》《哭蒋》三图,以推崇袁枚、赵翼、蒋士铨三家;袁枚当时听闻此事,便书告赵翼,并将绘图者误作松江秀才张凤举*赵翼:《瓯北集》卷三十二《子才书来,有松江秀才张凤举,少年美才,手绘〈拜袁〉、〈揖赵〉、〈哭蒋〉三图,盖子才及余并亡友心余也,自谓非三人之诗不读,可谓癖好矣。书此以复子才,并托转寄张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下册第749页。。有关袁、赵、蒋并称的提法,最早来自赵翼的一句戏言:“我本欲占人间第一流,而无如总作第三人。”[15]示其推服袁、蒋之诗;据此,袁枚便煞有介事地一再宣传三人并称之说,如其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年)所作《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之十九有句云:“云松自负第三人,除却随园服蒋君。”[16]所以,自乾隆末年诗界就盛传三家并称,至于绘图一说,当在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年)蒋士铨谢世后才开始流传。然而,这幅《拜袁、揖赵、哭蒋图》纯属子虚乌有,赵翼《瓯北诗钞》卷首题辞载程拱字一诗,题称:“拱字少时,喜读简斋、云松、心余三先生诗,曾欲绘三人真,张之座右,未果也。他日读《瓯北集》,见有古诗一首,题曰《得子才书……》,述拱字曾手绘《拜袁、揖赵、哭蒋图》,此不知何人所传。果若此,亦佳话也,行当作一图以实其事。”[17]事实上,有无《拜袁、揖赵、哭蒋图》一图,已不太重要;因为关于此图的种种谣传,以及当事人的系列言论,就足以达到宣传三家齐名的目的,绘画只不过是袁、赵等人以资标榜的“道具”而已。
例之四,胡骏声《梅社七贤图》。据江标《黄荛圃先生年谱》卷下“(道光)三年癸未[1823]六十一岁”条,按语引潘麐生《诗社册后跋》有云:“曩余见芑香胡君所摹《梅社七贤图》,为荛圃黄先生、琢堂石先生、苇间彭先生、春樊尤先生、莳塘张先生、族祖理斋公六人,诗具见册中。”[18]可知,该图所绘“梅社七贤”即江苏吴县黄丕烈(荛圃其号)、石韫玉(琢堂其号)、彭希郑(苇间其号)、尤兴诗(春樊其号)、张吉安(莳塘其号)、潘世璜(理斋其号)等人,作画者为同邑胡骏声(芑香其字)。
其结社缘始,据彭希郑题《问梅诗社图册》诗自注交待:“余移居城内甫十日,春樊、荛圃过访,往积善西院看梅,因以问梅名社。”[18]“问梅诗社”自道光初年迄中叶,共举行上百次的社集,涉及人员众多。所以该图所绘“七贤”,应只是其中某次雅集的主要参与者。
通过上述举例可以看出,清代诗人并称佳话以绘画为传播的物质载体,大都和时人的偶像情结、社集活动等有关。以《渔洋、绵津合像》、《拜袁、揖赵、哭蒋图》为代表的诗人并称图,都是出于当时人们的一种偶像崇拜心理;类似者还有以自己与古人并列合为一图,如清初诗人方文,其诗歌创作主要取法东晋陶渊明和唐代的杜甫、白居易,并且四个人刚巧都是“壬子”年出生,因此他曾托人特地画了一幅《四壬子图》。以《五客话旧图》、《梅社七贤图》为代表,则是文人间风雅生活的真实写照,参与雅集的诗人联袂登图亮相,再加上名流的题诗赋吟,遂使平凡的集会获得了不平凡的意义,制造了一种类似于“明星化”的效果。众所周知,清代结社雅集之风盛行,商业化的绘画创作亦颇为发达,人们日常生活中以图纪事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与社集有关的诗人并称佳话,往往容易成为绘画表现的对象。自从近代引入西方摄影技术以后,绘画渐为拍照所取代,如清末诗人王韬曾与友人在徐园“以西法影像合印一幅,名之曰《海天五友图》”[19],其弟子许鑅亦有“天涯五友图”合照*参见王中秀、茅子良、陈辉等编著的《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附录《清末画苑纪事补白》“一九○○年”条:“蔡小香、袁仲濂、张小楼、李叔同、许鑅假徐园小宴,余兴未阑,在园内悦来照相馆合影,各有诗词纪事。许鑅仿其师王韬在徐园摄有‘海天五友图’之例,名之曰‘天涯五友图’。”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410页。。这些缘于某次雅集而产生并称名目,通过合照的方式传播,无疑比口头或文字的转载更能使人加深印象。
五、余话
清代诗人并称佳话的传播之盛,确实是一种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研究价值,可为当下的清诗研究提供一个新角度。就整个文学史上作家并称现象而言,其所包含的多种认识价值,刘跃进先生曾经这样总结过:“有时候,它是某一时期文坛横断面的扫描;有时候,它是某种风格集中的呈现;有时候,它是某种文学流派的表现形态。”[20]严迪昌先生也指出:“诗歌史上屡见之‘七子’、‘五子’、‘十子’一类名称,不应轻忽为一般的文人风雅习气,其实这类现象正是朝野诗坛领袖们左右风气走向的表征,当是治史者梳通诸种脉络时的重要观照对象。”[21]就清代诗人并称而言,其所涉清诗研究层面是相当广阔的。即如从内部关联来看,几乎所有重要的诗人都有某种并称关系,乃至兼有好几种并称关系,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或折射诗人创作、交游的一个片断,或成为评价其文学地位的一个标准;从外部关联来看,并称群体与诗歌流派、诗人结社、诗坛风会、诗学批评等论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庶几可构成诗歌史上的许多重要论题。因此,并称现象在清诗的研究领域里,具有很大的学术涵盖面,很值得我们去关注、思考、清理和研究。
[1]姚思廉.梁书(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3:714.
[2]高仲武.中兴间气集[M]//唐人选唐诗新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463.
[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483.
[4]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M].北京:中华书局,1984:170.
[5]王世贞.艺苑卮言[M]//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1068.
[6]王士祯.蚕尾续诗集[M]//王士禛全集(第2册).济南:齐鲁书社,2007:1314.
[7]顾有孝.江左三大家诗钞[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3.
[8]邵长蘅.二家诗钞[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3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443.
[9]王富鹏.岭南三大家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9-27.
[10]方濬师.蕉轩随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5:450-451.
[11]尚镕.三家诗话[M]//清诗话续编(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919.[12]佚名.宣和画谱[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79.
[13]杨钟羲.雪桥诗话[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85.
[14]汪学金.静厓诗后稿[M]//续修四库全书(第147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95.
[15]袁枚.随园诗话[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368.
[16]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689.
[17]赵翼.瓯北诗钞[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24-25.
[18]江标.清黄荛圃先生丕烈年谱[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146.
[19]王韬.蘅华馆诗录[M]//续修四库全书(第155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78.
[20]刘跃进.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魏晋南北朝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167.
[21]严迪昌.清诗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456.
(责任编辑:刘 燕)
The Theory of Route of Transmission and Effect about the Much-told Stories of the “Juxtaposition” of Qing Poets’ Name
Chen Kail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Huizhou University, Huizhou Guangdong 516007, China)
There are many stories about juxtaposition of poets’ name spread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literature in China, constituting a special form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Qing Dynasty, it was very popular to combine the name of the poets who got along famously with each other in the literary circle, and there were various forms of different ways and methods to spread the story about the combined name of poets. Most poets who spread by the poems used to express and strengthen their relationship of combining their name together by writing the poem together or presenting each other with poems; the poets who broadcast their name by anthologies used to label the book they write by “...ism”, “...cius” etc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and maturity of their names’ combination; the most transmitter who used the notes on poets and poetry often commented by a few words, which was the main method of transmission about the combined name of poets; the transmitter who used paintings showed several poets’ paintings together in order to attract more people by the real spots effect .
the Qing Dynasty; the poet; juxtaposition of name; transmission; effect
10.3969/j.issn.1672-7991.2016.01.003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项目“清史·典志·文学志·诗词篇”(2001410220204001)。
2015-12-08;
2015-12-18
陈凯玲(1982-),女,广东省广州市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I207.22
A
1672-7991(2016)01-0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