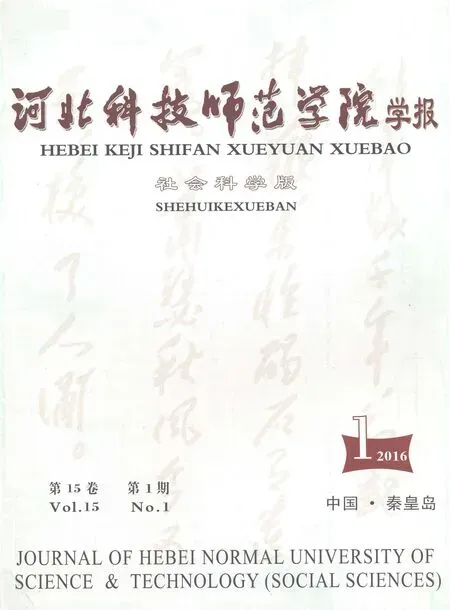曹叡的文学史定位再探析
许 总,汪 钰
(华侨大学 文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曹叡的文学史定位再探析
许 总,汪 钰
(华侨大学 文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曹叡作为“曹魏三祖”之一,其文学史定位学界一直莫衷一是。然而从建安文学的分期与其创作实践来看,应将其定位于建安文学后期的“黄初体”,属于沈德潜所谓的“魏响”这一理论范畴。同时,曹叡的政治文化举措与其创作都有“启后”迹象,正始文学一些主要作家在曹叡生前已有作品问世,应将其看作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的过渡人物。
曹叡;文学史定位;“黄初体”
魏明帝曹叡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文学研究者所忽略,隐没在其父祖以及叔父的巨大光环之中而难以显示出其独立的价值与地位。文学史家更多的是将其作为“三曹”的附庸一带而过。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有关曹叡的专论,譬如张亚新先生的《曹叡文学成就浅说》。
21世纪以来,对曹叡的研究渐渐增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曹叡研究》和《曹叡与建安文学论略》两篇硕士学位论文。另外,魏宏灿对曹叡的文艺政策以及其诗歌艺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他说:“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曹叡对曹魏文学的发展还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以往论者通常只及魏武、文帝,而不论明帝,有失公允。”[1]不过,细究与曹叡相关的论著不难发现,对曹叡的文学史定位一直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尤其是在《曹叡研究》和《曹叡与建安文学论略》两篇硕士学位论文中出现了似乎对立的两种观点。《曹叡与建安文学论略》认为:“综上所述,曹叡在历史上处于建安向正始过渡的时代,但文学上却是建安之音,并无正始痕迹,不能视其为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的过渡人物,而应将其列入建安诗人群。”[2]而与之相对的是,《曹叡研究》则认为:“概而言之,曹叡在历史上处于建安向正始过渡的时代。其诗歌同建安文学传统一脉相承,但对正始诗人及正始诗歌也存在着些许开启之迹象,可将其视为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的过渡人物。”[3]
如此大相径庭的阐述实在令人费解。不过细究起来,古人对此亦有不同论述。刘勰一方面说:“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4]77似乎将曹魏三祖视为一体;而《时序》篇,却将“三曹”与“七子”一并论述,而曹叡却在其后,与何晏、刘邵被一并提及,属于另一个时代。再看今人文学史著作中关于曹叡的只言片语,也是各说各话。譬如,李景华说:“曹氏父子,以及曹叡、曹髦皆能诗,都躬身示范,带动邺下文人的创作活动,史称‘三祖纷纶,咸工篇什’,‘三祖叶其高韵,七子分其丽则’,君臣父子,兄弟僚友,在文学这一点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走到一起来,蔚成建安文学之大观。”[5]65-66袁行霈明确指出:“建安是汉献帝年号,建安文学指‘曹氏三祖’(曹操、曹丕、曹叡)时代的文学创作,大致包括汉献帝和魏文帝、明帝时期的文学。”[6]然而,徐公持则认为:“曹叡在文学方面亦有建树,他是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间的过渡人物。”[7]
一、建安文学的断限与分期
要探求曹叡是建安文学的一部分还是从建安到正始的过渡人物,首先必须对建安文学的断限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位。建安文学如果简单地理解为建安时期的文学,曹叡显然不能算作建安文学作家。因为即便到魏文帝受禅,黄初改元,曹叡仅仅15岁,显然建安时代不是其创作的主要时代。
可是,建安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范畴,显然不能仅仅以曹魏代汉这一简单的政治事件作为其结束的标志。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往往需要论及“三曹”、“七子”,“三曹”中的曹丕、曹植均在建安年号结束之后仍然在世并从事文学活动。罗宗强在其《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一书中称:“建安诗坛,上起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下迄魏明帝太和六年(232年)。”[8]王巍也说:“文学史上所称的建安文学的时限要比建安年号所表示的时间更广一些,上可追溯到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下则推及魏明帝景初末年(公元240年),前后约50年。”[9]李景华则将下限定在曹植去世的232年,给建安文学到正始文学留下了一个长达8年的空窗期。不过上述各家观点虽不尽相同,然而无论按照上述任何一种断限方法,曹叡及其文学活动均应被纳入建安文学的范畴。
不过细究起来,“三曹”、“七子”中,曹丕、曹植年辈相对较小,诗歌风格与创作思想也与曹操有着明显的不同。以生卒年看,“七子”当中,孔融于建安中期的公元208年便被曹操假以“不孝”之名诛杀,当时曹叡尚在襁褓之中。其余诸人,除阮瑀卒于公元212年外,均于公元217年去世。建安二十二年时,曹叡不过11岁。而曹操于建安末去世,曹叡时年15岁。而曹操、曹丕、曹植、曹叡之卒年各相差六七年。
从着力较多的文学体裁来看据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可知:曹丕存赋 31 篇,乐府 22 首,诗 23 首;曹植存赋 47 篇,乐府 49 首,诗 38 首,另有骚体诗歌1首。与曹操相较,两人更多着力于赋的创作。
单就诗歌而言,曹操的作品四五言数量相差不大,很多名篇均为四言,曹丕、曹植五言的作品比重更大,曹丕的七言诗甚至在后世被看作其作品的代表。从语言风格而言:“曹操诗歌的语言,和他的散文一样,也很质朴简约,没有浮华的辞藻”[10],曹丕已经开始讲求“诗赋欲丽”了,而曹植诗赋辞藻之富丽华美更不待言。从情感表达方式而言,曹操与“七子”较为外化,多抒发对离乱社会现实的感慨,而曹丕、曹植较为内省,偏重于个体独特感受的开掘。从内容上看,曹操或关怀现实,或书写理想。曹操的《短歌行》写其对人才的渴求和自己的政治理想。曹丕的《短歌行》则写对长寿的期望。曹丕在其他诗作中还曾以彩虹与燕子为描写对象,而曹植甚至有一首闺情诗传世。
其实前人早已注意到这一问题。《文心雕龙·时序》中虽将“三曹七子”一并论述,但南宋严羽《沧浪诗话》的“以时而论”中就提出“建安体”和“黄初体”的概念,对传统意义上的建安文学加以切分。时至清代,沈德潜则提出:“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恒以下,纯乎魏响。”[11]今人有关著作中也往往将建安文学加以分期,或为前、后两期,或为前、中、后三期。可以这么说,在传统的广义的建安文学的大概念下,事实上活跃着时代略有先后、风格差异明显的两个作家群体。前者以曹操和“七子”为代表,后者以曹丕和曹植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吴质、“二丁”等人为代表。在当代,陈际斌针对上述问题在其论文中提出了“黄初文学”的概念,企图将其塑造为能够与建安文学和正始文学并峙的文学史范畴。他说:“黄初是曹丕称帝之年号,时间是公元220年到226年。但是本文所论的黄初文学所包括的时间比黄初年间要长,上限应推前三年,即公元217年,(建安二十二年),下限应向后延续13年,即公元239年(魏明帝景初三年),共23年时间。”[12]
不妨说,广义的建安文学实际上包含了“建安体”和“黄初体”两个不同的体派或者“汉音”与“魏响”两种迥异的风格,而狭义的建安文学或者说严羽所谓的“建安体”,作为与新提出的黄初文学相对应的概念,主要指曹操与“七子”的创作。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建安体”与“黄初体”、“汉音”与“魏响”、建安文学与黄初文学等等也并非完全对立,有着截然的分野。譬如曹丕、曹植在创作上,尤其是早期,当然地会受到其父及其周围的文人影响,也产生了一些语言相对质朴自然的作品。
对建安文学做了如此界定之后,曹叡与建安文学的关系也相对明晰起来。曹叡生活的时代较曹丕、曹植更晚,建安时代结束时仅有十余岁,其创作当属于“黄初体”、“魏响”无疑。然而,考虑到传统的建安文学的文学史概念已经绵延多年,加之曹叡文学在创作实践中亦刻意追摹祖父曹操,也有相当数量的四言体作品,将其纳入广义的建安文学范畴也似乎并无太多不合理之处。
二、曹叡的政治文化举措
对于曹叡的文学史定位,不能单纯地局限在其具体创作方面。曹叡作为一位握有实权的君主,其政治文化举措对当时的文艺走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首先,曹叡的以守为主、不战屈人的军事策略为北方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宁的社会环境,与建安乱世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区隔。曹叡一改祖父、父亲军事上的进攻性战略,对外尤其是对吴、蜀等主要对手采取守势。曹真、司马懿虽曾征伐蜀汉,但遇大雨便被曹叡及时召回。针对诸葛亮的屡次北伐,曹叡实行坚壁清野的防守措施,待其粮尽兵疲而已。除了对于半独立状态的辽东公孙氏进行过一次长距离征伐之外,曹叡主动进攻的举措似乎并不多见。如此的“守成”作风加之曹魏政权相较于吴、蜀明显的国力优势,使得曹魏政权统治的核心区域大体上维持了安定的局面。
其次,曹叡大量修筑宫室苑囿,广采美女,开启后世奢淫之风。曹操、曹丕主政时期,一再强调节俭。曹操曾严禁民间厚葬之风并亲自垂范,这一举措非但史有明载,而且亦得到曹操高陵考古结果的证实。而《三国志·明帝纪》记载:“帝愈增崇宫殿,饰观阁,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起景阳山于芳林之园,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铸作黄龙凤凰奇伟之兽,饰金墉、陵云台、陵霄阁。百役繁兴,作者万数,公卿以下至于学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13]531陈寿修书以曹魏为正统,而且有碍于“为传主讳”的传统,只得用“春秋笔法”,明写曹叡亲自参与劳动,为人表率,实则道出明帝修筑宫殿所耗人力物力之多。与增修宫室相对应的就是广采美女,充实后宫,这从魏明帝时期诸位大臣的劝谏就可见一斑。蒋济劝之:“欢娱之耽,害于精爽;神太用则竭,刑太劳则弊。愿大简贤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齿,且悉分出,务在清静。”[10]341《三国志·高柔传》:“后大兴殿舍,百姓劳役;广采众女,充盈后宫;后宫皇子连夭,继嗣未育。”[10]511甚至将魏明帝皇子夭折以至于没有亲生儿子承继大统的原因归结在后宫女子太多上。这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使之由节俭走向奢靡。王朗、王肃、高柔、陈群、华歆、蒋济、王基、钟毓、杨阜、高堂隆、毋丘俭、卢毓、卫臻、卫觊、徐宣、徐邈、栈潜、司马芝、王昶、董寻、张茂等一大批朝臣极力劝谏,曹叡表面优容,内心抵触。据《三国志·魏书·卢毓传》记载:“及侍中高堂隆数以宫室事切谏,帝不悦。”[10]389最重要的是宫殿的修筑并未因此受到太大影响,其在位后期的青龙三年,起昭阳、太极殿,总章观等建筑在洛阳新建。又因崇华殿毁于火,复建改名为九龙殿。
曹叡身为皇帝,奢淫享乐,用度不节,自然上行下效,遂养成一种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并对曹魏后期、西晋的世风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西晋奢侈腐化、斗富比阔的习气正肇始于魏明帝时期,刘师培在其著作中谓正始文学实肇基于明帝太和年间,实为真知灼见。
再次,魏明帝的很多举措都促进了当时的文学发展。主观上,魏明帝倡导文学,奖掖文士,很大程度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文心雕龙·时序》云:“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照耀。”[3]326客观上,大起宫室建造楼台,则促进了宫殿赋的创作与发展。
最后,不得不谈到曹叡对于身后事的处理问题。曹叡亲生皇子早夭,遂以“不知所出”的曹芳为后嗣(也有学者认为曹芳是任城王曹楷之子)。由于曹芳年幼,需要安排辅政大臣。曹叡一开始选择了德高望重的燕王曹宇为首辅大臣,并安排了曹肇、秦朗、夏侯献等与曹氏有密切联系的官员作为辅助,但临终之时,却换为以曹爽、司马懿为首的辅政集团。其中缘由,后世揣测甚多,《三国志》本传与《资治通鉴》所载各异,这里因篇幅原因,姑且不论。然而这些变动无疑是对曹魏宗亲势力的打压。无疑,这一举动为曹操“三马食槽”梦境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致使正始文学的代表人物竹林七贤中的多位,都不得不在曹魏与司马氏集团的夹缝中生存,何晏、嵇康甚至因此而遭难。一般以为正始文学是玄学与曹魏后期的恐怖政治影响下的产物,而玄学兴盛又与当时政坛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足见曹叡对辅政大臣的安排对正始文学影响之深。
三、曹叡本人与正始文学代表作家在曹叡时期的创作
曹叡本人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体式上,他的作品似乎更多地表现为对于父亲和祖父的承袭。曹叡的诗歌四言诗占了相当的比例。所用的乐府诗题也与其父祖类似。譬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燕歌行》等,其中,《燕歌行》也是以七言的形式出现。在具体语汇上,对其父亲和祖父的陈言也多有引用。曹叡的文学创作受到其父亲和祖父极大的影响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在诗歌的精神内质方面,曹叡的作品似乎与其叔父曹植晚年的作品有更多的相通之处。陈际斌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曹叡的怨妇诗歌,与曹植后期的作品颇有共同之处,都以抒发忧思怨愤为主。”[14]其实,曹植晚年的创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由建安到正始的过渡性倾向。“由于在政治斗争中的失利,再加上晚年生活的困窘,曹植产生了悲观厌世,向往佛道的想法。晚期所作的《远游篇》、《释愁文》便是这种心境的抒托,实际上已开正始之音的先河, 使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渐变成低回凄婉的人生哀叹。”[15]曹叡的诗歌应当与曹植晚年的诗歌一样,具有从建安到正始的过渡性倾向,《种瓜篇》便是其中典型,今录全诗如下:
“冉冉自逾垣。与君新为婚,瓜葛相结连。寄托不肖躯,有如倚太山。兔丝无根株,蔓延自登缘。萍藻托清流,常恐身不全。被蒙丘山惠,贱妾执拳拳。天日照知之,想君亦俱然。”[16]
诗中女子将委身的丈夫比作泰山,自己如浮萍一般,高度缺乏安全感,希望丈夫能够成为其依靠对象。女主人公的不安全感是全诗最明显的一种情感基调,这一点与正始文学作家在政治高压之下缺乏安全感是十分相似的。
文学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创作本身。虽然曹叡本人曾经向其叔父直言其并不善于赋体文学的创作,然而,因其修造宫殿甚多,每当宫殿落成之际,往往会命臣下作宫殿赋。作为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何晏、缪袭就分别作乐《景福殿赋》和《许昌宫赋》。正始文学的代表人物实际大都参加过曹叡组织的文学活动,因而可以认定,曹叡对由建安到正始的文学转折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同时,阮籍在曹叡去世时已经年届三十,在曹叡死后三年便以文名为后人称道,很难否认其在曹叡执政时期就已进行文学创作。
魏明帝与嵇康亦有交集,据北堂书钞引《嵇康集》:“嵇康曾著《游九山咏》,魏明帝异其文辞,问左右‘斯人安在,吾欲擢之’遂任嵇康为浔阳长。”[17]
结 语
由以上论述不难发现,首先,广义的建安文学可以理解为由“建安体”和“黄初体”两个不同的文学体派构成的文学史范畴,这两个体派分别代表了所谓的“汉音”与“魏响”。曹叡在诗歌创作上虽对曹操也有所借鉴,但仍应归为代表魏响的“黄初体”。
其次,曹叡的政治文化举措,使得文学创作的环境从建安时代的乱世逐渐趋向于较为稳定的局面,文人遂将注意力由外部世界更多地转向内心世界的开掘。曹叡大修宫室,广采美女,客观上促进了宫殿赋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社会风气从节俭到浮华的转向更是深远地影响到后世的文学,不仅是正始文学,就连太康文学的“繁缛”倾向也正源于此处。魏明帝重视文学活动,许多正始时代的代表作家在其执政期间早已开展文学活动。魏明帝有关继承人和辅政大臣的抉择直接影响了正始时代的政局走向,从而对正始时期代表作家的生存状态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最后,曹叡本人的创作虽较为明显地承袭父祖,但也与陈思王晚期的作品一样,具有从建安到正始的过渡倾向。很多正始文人在这一时期即参加了曹叡主持的文学活动。
因而,所谓“曹叡对正始诗歌并无启后之迹象,不能将其视为过渡人物”[1]26的说法实有偏颇。曹叡对正始诗歌的“启后”作用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作为建安文学到正始文学的过渡人物是毋庸置疑的。
[1]魏宏灿.曹睿对魏文学的贡献[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90-93.
[2]王薇. 曹叡与建安文学论略[D].长春:吉林大学文学院,2004:26.
[3]王雪晶.曹叡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2009:63.
[4]陆侃如.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1.
[5]李景华.建安文学述评[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6]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47.
[7]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60.
[8]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6:1.
[9]王巍.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1.
[10]李宝军.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7.
[11]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1978:103.
[12]陈际斌.黄初文学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4:1.
[13]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4]陈际斌.黄初宗亲文学[J].黑龙江史志,2009(13):21-23.
[15]袁济喜,洪祖斌. 论建安风骨向正始之音的转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2):76-81.
[16]逯立钦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8:417.
[17]伍联群.论嵇康的悲剧之美[J].许昌学院学报,2005(1):50-52.
(责任编辑:母华敏)
A Further Analysis on Literature History Position of Cao Rui
Xu Zong,Wang Yu
(College of Literature,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21,China)
As one of the masters of Wei clan in Jin Dynasty, Cao Rui’s position in literature had not been approved by scholars. Howeve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Jian’an literature stage and his creation practice, he should be in Huang Chu literature form in the late of Jian’an Literature, which belonged to the Wei Xiang theory mentioned by Shen Deqia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olicies of Cao Rui had impact on the poets of later generations. Some of the major poems of Zhengshi literature had come out before Cao Rui, therefore, he should be thought of as a transitional figure in the Jian’an literature and Zhengshi literature.
Cao Rui;literature history position; “Huang Chu Literature Form”
10.3969/j.issn.1672-7991.2016.01.009
2015-11-16;
2015-12-02
许 总(1954-),男,江苏省南京市人,教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I206.2
A
1672-7991(2016)01-004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