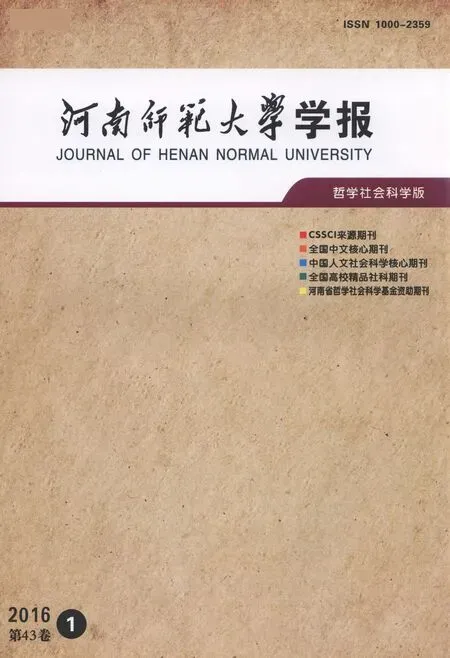略论“伦理能力”:意涵、问题与培育
卞 桂 平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略论“伦理能力”:意涵、问题与培育
卞 桂 平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伦理能力指主体在实践境域中认知、认同并践行伦理同一性之能力,是道德主体性的重要表征。伦理能力日渐退隐之中国表征是:政治领域官员与群众之于权力及权利的伦理认知缺失,经济领域市场主体物化,文化领域价值多元、多样及多变,公共领域社会公德沦丧。其成因在于传统人伦终结、现实境域不公、法治精神式微及公共舆论缺失。主体伦理能力养育必须基于家庭、社会、国家诸实体的伦理场域建设。
伦理;伦理能力;意涵;问题;培育
《现代快报》2014年10月30日曾以“扶不扶”为标题,报道一起发生在苏州阊胥路之跌倒事件。一名65岁大妈雨天骑自车不慎摔倒,造成腿骨骨折,在10分钟内路过的上百辆汽车及几十名行人中,竟无一人上前搀扶,乃至于她对围观者大喊“是我自己摔倒的,我不会讹你们”也无济于事。虽有点匪夷所思,但实际上,“苏州阊胥路事件”只不过是众所周知的2006年“南京彭宇案”之升级版。与其说此类事件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祛魅”,还不如说是“伦殇”之反映。因为黑格尔早已阐明:“德毋宁应该说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1]170因此,人们在进行道德批评的同时,伦理的分析绝不能缺场!从一定意义看,“苏州阊胥路事件”是一次典型意义之伦理事件,是社会伦理能力式微之重要表征。
一、“伦理能力”之内在意涵
基于词语构造审视,“伦理能力”一词带有典型偏正结构特征。其中,“伦理”已基于性质、内涵等层面对“能力”进行了内在设定。也即是说,“伦理能力”凸显的是“伦理”之能力,而非其他。因而,考察“伦理能力”意涵之前提,在于“伦理”。
(一)伦理:“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
在考察伦理时,黑格尔曾有一著名论断:“在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或者从实体性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渐提高。后一种观点是没有精神的,因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但是精神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1]173由此可见,“原子式”还是“实体性”,是区分是否“伦理”之最为根本性的条件。因为,“原子式”所标识的是“集合并列”而缺乏“精神”,而“实体性”则以“精神”为最典型标识,所凸显的是内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有机关联。这样而言,“伦理”的观点就是“实体性”的观点,也即是“精神”的观点。进而也就可以认为,既没有无“精神”的伦理,也不存在无“伦理”的精神,二者内在相通并互相诠释。
以“实体性”为显著标识的伦理,在中国文化中尤为典型。中国文化属典型的“伦理”型文化,而这种“伦理”文化之突出体现就在于孔子所凸显的“礼”。因为“礼”所呈现的是伦理实体性的文化设计。中国人的价值法则突出体现在要懂“礼”,否则就代表叛逆而难以被外部环境所接纳。孟子就强调“无礼义,则上下乱”(《孟子·尽心下》)。而无论是“礼貌”、“礼节”还是“礼尚往来”,都是希冀以守“礼”为中介而达到伦理的“实体性”建构,即“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进而生成一种伦理精神。因此,以“实体性”为标识的“礼”就是“精神”凝聚的文化设计,从属于“伦理”方式。老子为了化解轴心时代“原子式”危机,也积极倡导基于伦理实体的哲学主张。如“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道德经》二十八章)。“婴儿”之本义就在于原初之伦理实体,“复归于婴儿”就是要回到伦理的实体性。同样,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八章)。“水”就是伦理实体,“上善若水”则强调主体之“德”源于伦理之“道”,也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德是伦理的造诣”。可见,作为中国文化之两种典型,儒家之仁、道家之德都是基于伦理实体,二者在此意义上殊途同归并与黑格尔哲学相通。
对“伦理”内涵的进一步考察,还可以从“人伦”与“人际”的区分得以确证。“人伦”观点就是典型的“伦理”观点,诉诸伦理的“实体性”。如孟子所言:“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呈现的是“分”,即人一旦只依循自身喜好,最终必然是“分”,即因“普遍性”丧失而滑入“个别性”的“原子式”存在。而“圣人”则是过“普遍性”生活的人,因“个别性”张扬而表示忧患。“教以人伦”即要通过“教化”使“个别性”回归“普遍性”进而达到二者同一。可见,孟子强调“教以人伦”即是教导人们过伦理的“实体性”生活。相对来看,“人际”则有所不同。“际”之本意在于“交界或边际之地”,如“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因此,“人际”与“人伦”之“实体性”差别在于:“人际”表征“分”,是“原子式”的“集合并列”。可见,“人伦”与“人际”之分正是黑格尔两种伦理方式的表达。
因此,伦理的观点是基于“精神”的“实体性”观点。在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体系中,其所呈现的伦理形态就是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其中,家庭是原初样态,市民社会是过渡样态,国家则是基于前两者之综合,是成熟形态。经历三重演进的伦理实体从“实体”最终蝶变为“主体”,道德主体的伦理能力诞生由此具备生成之可能。
(二)能力:主体活动的个性心理特征
作为人之个性心理特征之一,“能力”是指直接影响人们有效地完成某种活动的个性心理特征,是完成一项目标或任务所体现出的素质。能力并非先天的,而是立足人的生理素质之基础,经过后天教育和培养,并在实践活动中形成与发展。正因为如此,能力才会因人而异。能力与知识及技能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彼此相互包含、渗透。相对来看,作为稳定性的心理特征,能力生成比知识、技能缓慢。人的活动顺利实施不是依赖某一种能力,而是多种能力之综合,只有各种能力高度匹合,富有创造性地完成各项活动才有可能[2]
可见,“能力”并不是一个用来形容某种机械存在的概念,而是专属于“人”的形容词,所表征的是行为主体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的程度,所表征的是人的主体性。“能力”强,则意味着主体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的程度与效果强;相反,则“能力”弱。当然,人的能力强弱影响因素很多,既有内在的、外在的,也有主观的、客观的。不过,能否科学认识并利用客观规律,是衡量人之能力强弱的最为核心要素。
(三)伦理能力:基于“伦理同一性”的“道德主体性”
在一定意义上,“伦理能力”所表征的不仅是“伦理”,更是“能力”。“伦理”之本性在于“实体性”,它表明的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而以“精神”作为其最显著标识,是一种客观存在样态。而“能力”则是主体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的程度与效果描述,属主体范畴。因此,当“伦理”与“能力”联袂,就意味着主体能否认知、认同并践行“实体性”或“伦理同一性”之能力。如主体与外在世界能够保持程度较高的“伦理同一性”则意味着其伦理能力很强;反之,则弱。因此,由“伦理”推进到“伦理能力”,则意味着“伦理”由客观推进到了主观,由“伦理实体”演进到了“道德主体”。而由“能力”推进到“伦理能力”,则意味着主观关照到了客观,主体联袂到了客体。因此,伦理能力所标识的既不是单一的“伦理”,也不是单一的“能力”,而是二者的生态联袂。最终所构建的则是“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的生态同一性。
综上分析,在概念层面“伦理能力”就可规定为:行为主体在实践活动中认知、认同并践行“伦理同一性”的能力。作为道德主体性的重要表征,伦理能力的生成及实现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环节构成,其中最基本的环节有伦理认知、伦理认同、伦理意志以及伦理行动等,其简化的形式就是认知—认同—意志—行动。在诸环节中,伦理认知是前提,伦理认同是关键,伦理意志是保证,伦理行动是落实。唯有这些环节的紧密相扣,主体的伦理能力也才有实现之可能。伦理能力不仅影响与制约着诸伦理实体的行动效能,也是能否形成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关键要素。
二、“伦”殇:“伦理能力”现形态
全球化时代,“孔家店”“被”倒了、“上帝死了”,整个世界因“丛林镜像”而光彩夺目!然而,一切“被允许”的背后也宣示着以“实体性”为标识的“伦”的传统之终结,世界由此步入“后伦理时代”[3]。但当人们沉浸于“人人都是上帝”的喜悦之时,并没有想到人类正步入“失家园”的尴尬境地!失去“伦”的守护,无论“丛林镜像”如何炫目,世界都因过度“原子化”而不免步入分崩离析之危机,人的“伦理能力”也由此步入涣散的境遇。
(一)政治领域
政治领域的伦理能力缺失突出表征为相互交织之两大政治主体:政府官员与普通群众。政府官员之关键问题在于:伦理认知与伦理行动相脱节,习惯于把“为人民服务”仅看作台面上的某种摆设与宣扬口号,而私下却利用公职身份大肆谋取私利,成为“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堕落为伦理的“伪善”。即“因为它表示它的内心生活与普遍物是不一致的;并且,由于它又宣称它的行动是与他自己的本心是一致的,是出自义务感和本诸良心的,所以是伪善”[4]190。而普通群众之问题则在于:因伦理认知缺失导致“权利”意识弱化,对权力既敬畏又希求,渴望得到权力保护,或攀高结贵,或请客送礼,在权力追逐中迷失了自我。诚如鲁迅对中国人的描述:“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5]这既是伦理的异化,更是以“伦理普遍性”为标识的主体伦理能力缺失的表征。
(二)经济领域
经济领域的伦理能力缺失突出体现为行为主体的“物化”。市场语境中的行为主体在价值取向上常以金钱作为衡量一切事物之标尺,传统的知识、智慧与美德反而成为不合潮流之代名词。有钱人因“家财万贯”而受人追捧,作为新时代“弄潮儿”而享受他人与社会的追捧,良心、爱情及声誉等传统美德相比于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而言显得不堪一击,成为“落伍”的代名词。面对强势的“占有性”非理性消费方式,现代人似乎丧失了还手之力,而心甘情愿地成为“物”的奴仆,伦理亲情在人的追名逐利中丧失殆尽。而各类型的利益集团则常以“整个的个体”面目进行各种牟利活动,其行为无论之于个体或社会而言更具有危害性,如毒奶粉事件、毒胶囊事件等等。市场之“物化”诚如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描绘:“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1]197正是基于极度的“单一性”物质追逐,现代人似乎已然忘却作为“伦理普遍物”之内在本质,伦理能力几乎丧失殆尽。
(三)文化领域
文化领域伦理能力耗散突出体现为价值生态的多元、多样与多变。中国社会文化生态存在三种交织的价值形态:马克思主义、西方价值以及中国传统价值。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表征的马克思主义立足实践论域已形成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以及中国表达的价值表征。同时,因官员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也引发不少反马克思主义声音。西方价值则主要是源于西方社会的诸价值形态,包括各种政治制度、民主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等。西方价值思潮通过学术引进以及日常渗透(如影视文化、节日文化及餐饮文化等)对当代中国社会诸群体(尤其青少年)构成极大影响,如黄头发泛滥、情人节兴起以及麦当劳、肯德基的快速普及等。中国传统价值则因其对中国人内在精神的嵌入,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潜移默化之影响。如果基于“群体”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社会价值形态镜像是:50后比较保守,尊重传统;60后积极主动,名利意识强;70后媒介意识强,家庭观念重;80后个体意识突出,经济意识强;90后人际交往重平等、看品行,寻求自我认同[6]。在社会奔向“地球村”之现时代,时空的减缩又加速了价值领域的嬗变性,在“原子化”境遇中,社会整体“伦理同一性”难免被消解,核心价值缺守之后果必然是社会伦理整合能力之式微。
(四)社会生活领域
社会生活领域的主体伦理能力涣散突出体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三大领域的相互交织。从人与自然关系看,现代人习惯把“自我”标榜为“主人”,而“自然”则被看作是“奴仆”,砍伐森林、开采矿山,到处烟囱林立、垃圾成山、水土流失,资源枯竭也导致人的生存条件迅速恶化。从人与人的关系看,“金钱”成为人们价值评价标准之首选,唯利是图的异化人际关系使“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化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7]。赤裸裸的金钱伦理催生社会关系的离散化与对立化,相互猜忌、彼此利用的人伦关系演变成人格的扭曲与社会关系之变异。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侵蚀社会利益、漠视社会秩序已构成当下常态,不少人习惯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行为准则,只要与自己“不存在”切身利害关系,一概不闻不问。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特性》中甚至这样说:“中国人有私无公或公私不分的脾气,其实还不止于此,他不但对于‘公家’的事物不负责任,而且这种事物,要是无人当心保管或保管而不得法,便会渐渐地不翼而飞,不胫而走。”[8]社会生活领域“伦理同一性”的日渐式微,导致个体、社会乃至国家伦理整合能力日渐祛魅。
三、“伦理能力”祛魅之当代病灶
道德主体能否积极创设、维持及践行伦理精神,关键在于主体之于伦理精神的价值认同。唯有对伦理精神持以坚定的价值信仰,主体之积极伦理感、伦理能力才具备生成之可能。因此,能否基于主体价值视域达成“伦理认同”就成为伦理能力生成并践行的基础与前提,也进而成为当代主体伦理能力祛魅成因分析之理论视角。
(一)传统“人伦”的终结
一部中国史堪称“伦”的历史。相信“伦”、依赖“伦”成为人们赖以生存之前提。诚如黑格尔所述:“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的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书经》内列举五种义务,都是庄严而且不变的根本关系(五常):一、君巨;二、父子;三,兄弟;四、夫妇;五、朋友。”[9]中国社会的“伦”之存在可见一斑。然而,在近代以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伦”的传统一再遭遇“腥风血雨”式的涤荡,使“伦”从一种“存在”,逐步演化为一种内在的主观信念或者主观理想。其中,尤以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批孔”为显著标识。伴随这些以“反传统以启蒙”之口号,作为中华文明之根本的“伦”风雨飘摇。在尼采“上帝死了”的高呼声中,一切皆被允许、人人都成了上帝。“伦”倒了,“实体”奔溃了,以“理性”为显著标识的后现代精神取代了传统“伦”之地位。随着“伦”的传统终结,“后伦理时代”宣布来临。不知不觉中,回归“伦”的传统,过“普遍性”生活已构成当代中国人的伦理难题。
(二)现实境域的不公
黑格尔早就申明,“国家权力是简单的实体,也同样是普遍的[或共同的]作品”,“个体发现在国家权力中他自己的根源和本质得到了表达、组织和证明”[4]52。因此,权力之本质在于伦理实体性,是人们过“普遍性”生活的重要前提。然而,在当代中国境遇中,权力正在或者已日益失去其作为伦理普遍性的“守护神”之意义及价值,反而成为个别人以公谋私的工具与手段,乃至于成为不少人公报私仇的不法工具,权力正日益丧失其所存在的伦理合法性。同时,作为国家“普遍物”之体现,财富的本质也在于伦理普遍性。因为“财富虽然是被动的或虚无的东西,但它也同样是普遍的精神本质,它既因一切人的行动和劳动而不断地形成,又因一切人的享受或消费而重新消失”。即“一个人享受时,他也是促使一切人都得到享受,一个人劳动时,他既是为他自己劳动也是为一切人劳动,而且一切人也都为他而劳动”[4]53。这表明,只有在普遍享有中,财富才能真正体现其存在价值。然而,当前的社会镜像却是,财富的增长与财富普遍性的提升呈反比关系,财富普遍性本质并没有因财富的不断积累而得到提升,相反,财富增长所导致的则是向少数人的集聚,财富伦理普遍性也因此荡然无存[10]。现实层面的腐败与不公凸显权力与财富的伦理异化,进而催生伦理信任危机,也就谈不上伦理能力之生成。
(三)法治精神的式微
“法”之本质在于最大限度维护社会公平及正义。因而,是否具有良法是社会得以正常运转之根本前提。鸟瞰当代中国社会法治生态,其存在之首要问题是:法律制定相对滞后,难以及时处理及应对相关问题,并由此导致相关问题得不到法律正当支持而走向反面。在2006年南京“彭宇案”中,正义一方终因“法”之解释能力式微最终落败。问题之关键在于,本案所带来的负面效果远远超越其本身存在意义,直接催生出一系列饱受道德批评的“冷漠行为”案例,其中又以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影响最为深远。如果以这一事件为“基型”,则本文开始所提及之“苏州阊胥路”事件则堪称此类事件的“升级版”。第二个问题在于:公职人员“知法犯法”。2013年8月,喧嚣一时的“上海高院四法官集体嫖娼”事件可谓近年来公职人员“知法犯法”之典型。该事件已使人们对“伦理同一性”之失望达到登峰造极。当作为“社会公器”之法律毫无约束力而变为“一纸空文”,则意味着“伦理存在”之终结,伦理实体性的价值认同以及伦理能力培育也不可避免地化为虚谈。
(四)公共舆论的缺失
社会伦理能力如何,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具有“伦理同一性”,不仅是该社会现状之呈现,更是对该社会今后能否发展及发展到何种程度之提前折射,而考量社会伦理能力的最为直接与形象的范畴就是公共舆论。“个人所享有的形式的主观自由在于,对普遍事务具有他特有的判断、意见和建议,并予以表达。这种自由,集合地表现为公共舆论。”[1]331因之,公共舆论在内在意义上也是伦理形态之一,其根本价值旨趣在于“伦理同一性”。正是基于这种“伦理普遍性”意义,公共舆论作为一种“伦理”形态在整个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中始终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即“无论那个时代,公共舆论总是一支巨大的力量”[1]332。然而,因所处文化境遇之差异,公共舆论的客观功效并没有在当代中国社会发生如黑格尔所言说的那种应有功能及意义。因为,除了儒家“刚健有为”,道家“无为而不为”的智慧也是中国人精神结构之一。这种“贵柔守雌”之智慧反映在社会公域就是“枪打出头鸟”、“各人自扫门前雪,别管他人瓦上霜”。作为一种文化基因,这些日常“智慧”一直潜藏于中国人的内在精神品性中,并进而影响人的一言一行。面对有悖于“伦理同一性”之极端行为,国人思维大多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正因如此,公共舆论就没有真正发挥出其在社会“伦理同一性”建构中的应有功能。
总之,主体伦理能力的培育根植于伦理价值同一性的生成。当社会伦理信仰遭遇解构,伦理认同则必定沦落为“镜中花、水中月”,主体伦理能力也无生成之可能。
四、伦理能力培育之场域建设
作为“伦理的造诣”,“伦理能力”匮乏并非只归结于纯粹主观,其根本在于“伦理存在”。这意味着,如果“伦理存在”持续弱化,则作为伦理“造诣”之“能力”也难以生成。因而,伦理能力的当代培育,不仅要诉诸如康德意义上的“道德之德”,更应诉求于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之德”。这样,夯实诸伦理实体场域建设,重塑当代伦理精神,就构成伦理能力培育的必由之路。
(一)家庭伦理场
家庭是基于血缘的“自然”伦理实体,是一切伦理实体发育的最基本范型。尤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伦理构造更在某种意义上宣示着家庭在整个伦理大厦中的自然、基础性地位。《礼记·大学》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由此,家庭伦理场域建设必然成为个体伦理能力培育之最基本条件。从当前情况看,当代中国社会家庭伦理功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考验。从农村家庭看,农村家庭壮年劳动力因外出务工基本常年在外,在留守的则大多是被媒体戏称的“6199部队”即儿童和老人。这样,传统“三代同堂”甚至“四代同堂”的“伦理存在”正在或已经发生改变,家庭成员间的“伦理温情”只能依赖“电话线”传递,新时代的“乡愁”正在使伦理的情感依赖因时空阻隔而悄然发生变化。其次,与农村不同的是,城市面临的问题则是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后催生的新问题。随着独生子女成家立业,父辈则往往独居,大量城市“空巢老人”应运而生,物质生活富足并不能代替这一群体在精神领域的贫乏,伦理温情的缺失使他们倍感孤独。因此,当前的家庭伦理场域建设必须立足新问题、新情况之基础,采取新的方式弥补伦理的缺失。虽然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硬性要求”子女必须定期关爱老人,然而,伦理之同一性,更多地应诉诸主体的慎独与自觉,以伦理关爱唤醒与弥补家庭应有的“自然”情感,培育家庭成员之伦理信仰。其中,尤其要重视家庭教育中的伦理示范功能,即成年人应做积极的“伦理”践行者,以实际行动塑造家庭伦理氛围,使未成年人在持续的耳濡目染中接受伦理之熏陶,培育伦理感,生成伦理信念,提升伦理能力。
(二)学校伦理场
康德曾言:“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一个人。”[11]从个体生命发育史考察,从家庭这个原初的“自然”伦理实体分离之后,个体一般并没有直接进入社会,而是存在于一个相对缓冲之地域:学校。从某种意义上看,个体进入学校学习知识文化,对人的后期发展具有积极的铺垫性功能。然而,从另一种视角审视,学校对个体伦理能力之养育则更具有直接性作用,它是承接家庭与社会的中间地域。当前,学校伦理场域建设,首要之举在于教育者要率先垂范,做“伦理”践行之范型,以“伦理行动”对受教育者进行潜移默化的引领。其次,“伦理同一性”理念尤其要贯彻到教育者的教学设计中,与受教育者平等互动,创设“伦理商谈”的教育情境,进而达到教学相长之目的。同时,在此过程的长期贯彻中,也要培育受教育者之伦理品性,进而生成伦理信仰。当然,学校作为特殊的伦理实体,在课外教育中,应尝试各种有效途径去关爱他人、关爱社会,立足日常生活教学达到对受教育者的伦理情感培育,进而提升伦理能力。
(三)社会伦理场
个体从自然伦理实体“家庭”走出便蜕化为社会一分子。虽然经历过学校等伦理实体之“教化”,但受教育者所获得的常常是与实践脱离之理论知识,现实艰难处境难免催生该群体孤立无助感。尤其伴随当代中国社会市场发展提速,“丛林镜像”凸显已构成当前社会发展的“常态”。人与人之间往往因一己之利而尔虞我诈、相互排斥。“原子化”的加剧使本来就已式微的伦理温情日渐耗散。个体如此,基于利益需求之上的各种利益团体更是如此。但与个体有所不同的是,这些利益团体则往往因利益需求而构成暂时相对稳定的伦理场域,在外部形态上,它们又总是以“整个的个体”出现,“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之悖论就必然不可避免。如何给予这些随风飘荡、孤立无助的“原子们”以伦理之温暖已成为摆在当前中国社会眼前的一项迫切课题。除了发挥单位、社区等伦理组织的功能之外,各种“关爱型”组织也应迅速建立。同时,尤其要规范诸如“红十字会”之类的关爱型组织运行的伦理合理性与合法性。只有不断增强诸组织之“伦理关怀”功能,社会才不至于因“伦理”缺失而迈向分崩离析,进而为人的伦理信仰及伦理能力培育夯实基础。
(四)国家伦理场
“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并完成一切它所知道的,而且只完成它所知道的”[1]253。可见,国家意味着“伦理精神”之成熟,即“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中国社会因“家国同构”使“国”尤其具有“家”的“自然”伦理温情。这样,国家伦理场域建设之关键就在于夯实“伦理同一性”之基础。首要之举就是着力恢复与重建权力与财富之公共性,真正实现二者的伦理合法性。因此,惩治官员腐败、重构分配正义就成为当前社会重中之重。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使伦理之实体本性得以复归,让权力与财富在伦理意义上真正合理且合法,进而促进社会之良性发展。其次,要增强执政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执政党只有真正诚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也才能真正做到黑格尔意义上的“单一物与普遍物”的合二为一,也才能真正实现党群关系的“鱼水之情”。也只有基于这样的“伦理同一性”,伦理信仰才得以获得深厚的群众基础,创设、维护、践行“伦理”的能力才可能得到加强。
总之,因诸伦理实体间不可分离的内在关联,使伦理能力培育并非某一个伦理实体之论域,而在于多种伦理实体共通之结果。只有在全社会实现“家庭—学校—社会—国家”诸伦理实体的生态关联,个体伦理能力的生成才真正可能。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张永谦.哲学知识全书[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736.
[3]樊浩.后伦理时代的来临[J].道德与文明,2013(10):5-16.
[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5]鲁迅.鲁迅著作全编:第2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29.
[6]陈晓辉.当代中国社会多元价值观评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2):177-180.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3-104.
[8]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M].匡雁鹏,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198.
[9]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56:165-166.
[10]樊浩.中国社会价值共识的意识形态期待[J].中国社会科学,2014(7):4-25.
[11]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M].贾泽林,侯鸿勋,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86.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1.022
2015-11-24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BZX110)
B82-02
A
1000-2359(2016)01-0109-06
卞桂平(1976-),男,安徽宿松人,哲学博士,东南大学伦理学博士后,南昌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哲学伦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