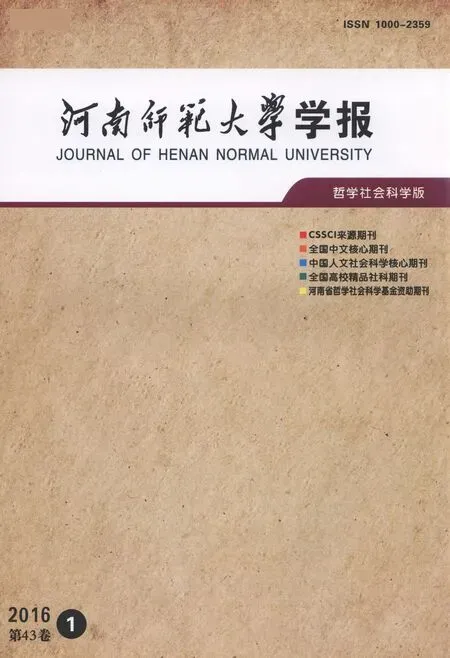对“革命历史”的“迎合”与“游离”
——以师陀《三个小人物》到《历史无情》的创作转变为例
张 东 旭
(河南科技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0)
对“革命历史”的“迎合”与“游离”
——以师陀《三个小人物》到《历史无情》的创作转变为例
张 东 旭
(河南科技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0)
师陀的长篇小说《历史无情》是由他的短篇小说《三个小人物》改编而成的。由之前的写“人物”写“风景”,到建国后的写“任务”写“运动”,《历史无情》在师陀的创作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彰显出一位“现代作家”进入“当代书写”的努力过程。小说中出色的小人物描写,日常化的叙事方式,浓厚的生活化气息,实在是京派叙事话语在20世纪50年代闪现的最后一抹霞光。
革命历史;迎合;游离
整理河南籍作家的长篇小说,映入眼帘的首先是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师陀的《历史无情》。以短篇小说为主,“以其朴实而又热烈的感情,浓郁的抒情笔调,流畅而富有诗意的语言,向读者介绍了一个又一个凄凉而又亲切的故事”[1]的师陀,在40年代曾写有三部长篇小说,两部未完(一部是《荒野》,载1943年7月1日《万象》月刊第3卷第1期至1945年6月1日第4卷第7期;一部是《雪原》,载1940年上海《学生月刊》第1卷第1期至第6期),1951年出版的《历史无情》,遂成为建国以来河南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此书的写作时间在1948年,从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来看,此书不仅丝毫没有50年代“英雄叙事”的影子,很多地方还坚持着师陀固有的清新沉郁的风格——“以真挚的感情和动人的描述来摇撼读者心灵的,使读者承受着感情的重压,诅咒那不合理的社会,黑暗的时代。”[1]现在看来,正是这种坚持和固有的风格,使得这部小说格外精彩。
作为一个性格鲜明的“现代作家”,在当代文坛的格局中要站稳脚跟,首当其冲的一个大问题是将“五四”所界定的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家的社会角色、文学的写作方式等等,接受新的历史语境(“现代版的农民革命战争”)的“重新编码”问题。这部小说是从短篇小说《三个小人物》改编而来的,从改编前后的人物设置以及命运安排的效果来看,长篇小说《历史无情》正是作者努力接受新的历史语境,对以往的叙述“重新编码”的结果。可是,作为一个有着鲜明创作个性的现代作家,无论他怎样努力,他的创作和当时的“规范”都有着明显的距离,文本中流露出的生动活泼的乡土气息和时而闪现的国民性批判意识,使小说主观上的“迎合”和客观上的“游离”构成了显著的张力。
一、“迎合”的姿态:从《三个小人物》到《历史无情》的改编
《三个小人物》是师陀在1945年至1946年所做的一部短篇小说,主要写一个旧式望族胡家的败落过程,其中偶尔闪现了门房老张的儿子参加革命暴动的身影。胡家高祖做过“布政使”,在任上捞到“论升论斗计算银子”的地步。胡太太娘家(马家)也是果园城首富,当时的民谣是:“马家的墙,左家的房,胡家的银子用斗量。”[2]562但是,时间却不饶人,这样一个家族,现在已经在走下坡路了:“马家的高墙早已夷为平地了,至于用斗量的胡家的银子,也早被‘布政爷’的游手好闲的子孙们用光。”[2]562胡凤梧的父亲仅给马夫人及子女们遗留下一小部分田地和那些又深又大的老布政第门宅。“这些一重一重的房屋是神秘的,大半经年空在那里,高大阴森,没有人敢进去,也没有人想进去。里面到处布着蛛网,顶棚下挂着长长的灰穗,地上厚厚的全是尘土和蝙蝠粪”[2]562。
胡家母子的命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胡太太现在依然活在过去的光辉岁月里:“她在婢仆的奉承与绫罗绸缎的包围中度了半生,只要肯动动嘴,一切都会送到面前,连走路都要丫环搀扶。她从来用不到求人,也从来不知道活着需要工作,提到别的绅士人家,她便轻蔑的说:“小家子气!我们马家是拿肉喂狗的。”[2]563胡太太的大儿子胡世梧是那些善于挥霍的布政子孙的后裔,他承袭下那些破落主子的全部德行,虚妄、骄傲、自大,无所不为。于是本来已经败落的家业在胡家儿子胡世梧的大肆铺张下迅速败落,他出外上学两年花费的银元,比人家一生的消耗还多,吃喝嫖赌样样在行。作者详细地陈述了这个败家子败家的过程。终于,在胡世梧掌握家政第四年,胡家宣布破产,他卖出去了剩余的田地和布政第,后来无以为生,只能替绑匪与肉票的家人做中间人,最后由于过于贪心,中间吃了过高的差价被绑匪打死。胡太太由于要吸食大烟,没有经济来源,便强迫女儿去卖淫,成为当地一大传闻。
小说叙述了门房老张的儿子小张离家闹革命的故事:“他领到一根从警察所缴来的枪,和众人一起上街‘工作’去了,去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走狗’,‘打倒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去了’!”[2]564在《三个小人物》中,小张们的革命也就限于把公共的墙壁刷成蓝色,写上标语,上街喊喊口号,“正规军一来,他们就被打跑了”。他们的命运是:“至于以后他们怎么样过日子,他们怎么样在世界上荡来荡去,饿的眼睛发绿发花,除了到处搜寻他们想把他们丢进牢狱,当然没有人管了。”[2]564
在《三个小人物》中,作者最着力的部分是对布政第家族生活方式的批判和反思。作者不动声色地展现着这大家族的一切,以悲悯的情怀叙述着一个昔日荣耀家族的破败过程,写出了旧社会旧家族的人们奢靡无度的生活方式和腐朽堕落的思想意识。小说对小张儿子的“革命生涯”不报生的希望,倒是对布政第的兴衰充满了人生无常的感叹。结尾处有这样的话:“人世间原来就是这样,在生活着的本人看去是庄严的,由旁边人看去却像讥诮。”[2]575小说两次提到当时世人对这胡家兴衰过程的评论,大有“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的情景构造,读完全篇,亦有一份“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遥深感慨。值得注意的是,这凄凉的挽歌调子,在《历史无情》中,得到了大大的改观。
(一)人物命运的改变
在1949年之前,师陀的“果园城系列”主要关注的是旧中国现实境况下人物的“不变”状态:“《果园城记》中,书中真正的主人是城镇本身。改革者、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官员来的来了,去的去了,可是城镇本身却我行我素,继续着它懒惰、懦弱和残酷的行径。”[3]如果是变,也是走向堕落,师陀很善于写人物的堕落,在堕落中抒发人生世事无常的感慨。但自《历史无情》开始,师陀在关注旧时代旧家族人性的丑陋的同时,开始展现历史前进的动力,展现人物的新变化。历史不再是圆式循环,而是曲折前进。《三个小人物》中老张和小张的命运有了光明的前途,有了可期待的改变,这是建国后师陀的历史态度最为显著的变化。
首先是纨绔子弟胡世梧的命运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三个小人物》中,他在家庭败落之后做绑匪和肉票家人的联络人,因为中饱私囊,贪了太多的钱被土匪打死,如此处理人物,除了说明人物从“小康”坠入“困顿”的可怜,还彰显了人性贪念之可悲。但是,在《历史无情》中,胡世梧的命运轨迹发生改变:不仅率先成为汉奸,还成了日伪统治下的县长,正式与贫苦农民、郑恩领导的游击队有了阶级分野;其次是小张由原来的革命流浪者形象,一下跃升为游击队警卫连连长,营长,一直到司令,其父老张也加入了游击队。最后,小张的恋爱情节也有较大的改观:《三个小人物》中,小张暗恋凤英,但凤英一直嫌弃他是鼻涕虫,无视他的存在。但在《历史无情》的结尾,却是凤英为等待小张煞费苦心,为伊消得人憔悴。
按上述人物的变化情况来看,长篇小说《历史无情》的情节设置显然基本符合了“革命历史小说”的观念:“历史的主体和推动者是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推动历史的动力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历史的发展会有曲折,有暂时的倒退,但历史的规律是从胜利走向胜利。”[4]小说标题之所以改为“历史无情”,意指历史的“前进”发展势不可挡。无情的“历史”就是:胡家必然破灭,日本人必然失败,游击队八路军力量必然胜利。同时生动地说明:只有革命才能使小人物彻底翻身。
作者一向非常重视小说的结尾设计,他说:“文章先有结尾不一定篇篇精彩,而先有结尾好比射箭有了‘的’,设计有了‘靶’,先有了结尾,考虑开头就方便多了。”[5]116《三个小人物》的故事结局是胡家败落,胡世梧因贪钱被土匪打死,而《历史无情》的结尾是胡世梧由于围剿游击队失败被日本人打死:“炮弹落在拐角上,掀起泥土,烟雾腾上去,遮住阳台,慢慢淹没了整座大楼。”[6]618作者后来在1981年写的回忆文章里说:“是八路军最后开的一炮。那一炮掀起的尘土遮掩了华洋旅馆的阳台,也就是海陆空俱乐部的阳台,暗示那个荒淫无耻的旧社会要灭亡”[5]116。作者如此精心策划的结尾和如此鲜明的预设的结局,岂不是作者对新政权认同的一种努力?
(二)关于革命者郑恩和小张的形象
在《历史无情》中,小说增加了郑恩这个游击队的组织者形象。他是小说中和日本人打仗的指挥者,是利用国民党保长做线人的筹划者,也是游击队员小张的革命启蒙者。相较于其他小人物的描绘,作为一个革命者,他的形象是比较模糊的。小说中他出现的机会很少,但却担任着很重要的话语功能:由于他的出现,一种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化论与爱憎分明的阶级优胜论已经代替了门房老张的历史循环论。同样,由于他的出现,小张和老张的人生道路彻底得到了改变。小张的历史命运本来是极有可能像老张那样循环的:“从他爷爷的爷爷开始,就在这做门房”。但他给小张讲的道理是:“一个人所以卑贱,不是因为他祖上没做过官,不是他穷也不是他坏,而是他自以为祖上没做过官,自以为穷,自以为吃的穿的不如人家,地位不如人家,那才是真的卑贱。”[6]451他的语言和行动最终“唤醒”了小张,小张正是在他的引导下一步步走向革命,最后得以翻身。
小张恋爱情节的转换,充分彰显了“革命”的意义。《三个小人物》中,小张对大小姐胡凤英充满了单相思最后被抛弃,小张一直到十六岁才明白了“世情”:“除非他有本事穿上西装,梳起分头,变成个大学生,根本别存娶她的心。”而《历史无情》的结尾,凤英反过来追求小张,小张的角色得到了反转。成功的秘诀在于他参加革命,并从警卫连长、营长……一直升到了司令。小说有两个对比性的画面很引人注意:一副画面是小张在革命前胡凤英的相思画面:“他自幼觉得她的声音是仙乐;她的眉目、鼻子、嘴唇、小手……什么都有引力”[6]448另一副画面是小张成为了司令后,胡凤英焦急等待小张前来看望她的心情:“她站起来拿着镜子照,看了这面再看那面,像画家鉴赏他刚完成的作品:色彩和不和谐?线条生不生动?小地方是不是忽略或添改……外面又是什么声音,是谁走进来了……她故意咳嗽,怕生客误会家里没人。”[6]614胡凤英为什么如此前倨后恭?怎么突然就对小张“回心转意”?这里就有个革命逻辑问题。其实,每个人都能看出来,她等待的不是那个流鼻涕的小张,而是一个传说中的八路军司令员。这里隐含着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革命,改变了小张在“爱情”中的位置,革命,打破了世俗的门第传承,改变了世界和个人生活的一切。胡凤英之所以能以热恋般的情感等待小张,正是小张革命的结果。虽然作者一再说,这个结果不是讲述“原来被高贵人看不起的‘底下人’,由于地位的变化,‘底下人’成了高贵人的幻想中的救星的,它的真实意义要宽广的多,是八路军最后开的一炮,暗示那个荒淫无耻的旧社会要灭亡。”[5]116可从实际情形来看,“底下人”小张和胡凤英位置上的反转关系的确清晰地表达了“旧社会”人物阶级关系的一去不复返,而这种“反转”无形中为新政权的合法性做着最充分的注解。
二、“游离”于“革命叙事”之外
早在长篇小说《结婚》中,因为师陀笔下的主人公胡去恶说了“这是个吃人的世界,你不吃人,人就吃你”的话,被尹雪曼评为:“充分表露出他(师陀)要向共党靠拢的心态”[5]262。并且被认为,“这部小说从一开始破题,就落入共党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八股’窠臼之中”[5]262。尹雪曼的理由也就是“作者不从人性出发用力地描写,去描绘,只知道一味的谩骂,一味的抨击,说这人不好,那人混蛋,这是为政治服务的一种文学作品”[5]262。可在我看来,《历史无情》这部长篇小说有趣的地方恰恰在于师陀写作目的的“政治倾向性”和实际写作中不自觉流露出的“批判国民性”所构成的矛盾张力之中。
从内容上来说,长篇小说《历史无情》主要反映了三方面的社会现实:一是“九·一八”之后,官宦人家“布政第”老主人遗孀胡太太一家人的命运变化;二是郑恩领导的游击队力量的逐渐发展、壮大;三是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汉奸魏仲达们的活动。如果放在50年代及后来的“英雄主义”叙述文本中,这应该是一个典型的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斗争故事,讲述我方游击队员在党的英明指导下和敌人开展曲折的斗争将是故事的重点,塑造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将是小说的中心。但今天看来,这个长篇的珍贵之处恰恰是师陀的“反英雄主义叙事”的风格以及大量的个人话语的涌现。在上述三方力量的各自叙述中,作者将叙述重心放在了做生意出身的魏仲达与胡家的争斗上。作品最出色的地方,恰恰不在于敌我之间的斗争,而是在于人物性格的展示,在于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的出色表现。
(一)写作重心的“游离”
虽然小说写的是抗日主题的“重大”事件,但作品的表现重心很大程度上放在了展现旧家族的畸形文化和几股丑恶势力之间的斗争上面。从篇幅的安排和所占比重来看,小说总共十章,其中,郑恩和小张的游击队抗日活动仅仅在第三章(郑恩组织溃兵、学生、无业游民拉起队伍)第五章(郑恩训练队伍,打第一仗)第九章出现。而且,正面战斗的场面描写也如漫画一般草草而成。游击队领袖郑恩的面目也非常模糊,除了三次讲话之外,没有其余的活动。小张的艺术形象最生动之处仍是在“布政第”之时的表现(也就是未参加游击队之前),最出色的部分是对胡小姐单相思的心理活动。看得出来,虽然作者在主观上有意融入革命叙事“主题”,但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和固有的写作习惯等因素仍使他不由自主地把笔墨大量地花在了“主题”之外。如展示“布政第”遗孀胡太太整天吸食大烟,动辄骂人的寄生虫一样的生活方式;描写八面玲珑,内心狠毒的魏仲达一步步蚕食胡家田产和宅第的过程。与游击队对胡家这个封建式的大家庭的打击相比,魏仲达对胡家的蚕食和陷害才是胡家——这个布政第世家最后落下帷幕的直接原因。作者详细地叙述了魏仲达怎样舌蜜腹剑,巧设机关地将胡家的土地和宅第据为己有的过程,通过对这样一个在各方势力的夹缝中虚与委蛇巧妙发迹的人的生动描绘,小说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阴谋和权诈横行的混乱世道。
(二)日常生活中的“战争故事”
与五六十年代出现的“革命历史故事”相比,作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的革命斗争故事明显不同,最显著的特点是将斗争放在了“日常生活”的叙述中:“九·一八”事变发生了,街头上有了日本人,侵略者来了,要打仗了。然而胡太太只想着吸大烟,她的生活逻辑是“横竖日本人也是人,总得叫人抽大烟。”[6]486冯嫂一有空就想偷胡家点东西;丫环秋香想着怎样在太太跟前跟冯嫂斗气;门房的儿子小张,加入了游击队,但满心想的都是自己喜爱的姑娘胡凤英;商会会长魏仲达在收取军队的“开拨会”从而中饱私囊;乡下的杨保长借机把“救国捐”存起来取利息;知识分子郑恩逃难到一个村庄,把溃兵、学生、地痞组织起来,成立抗日武装……所有事件都搅合在一起,泥沙俱下,扑面而来。
这是作者笔下的抗日过程:日本人来了,邻居中慢慢就有人做汉奸了。这些昨天还和你一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乡里乡亲,今天就成了“汉奸”被捉住了,是个什么样子呢?小说中有如此叙述:“汉奸们被游击队缴枪后放了,有人要他们下次带几挺机枪来,大家交个朋友,他们中有不在乎的,笑着说:‘不用急,朋友,后会有期’。”[6]556这里的农民还没意识到自己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什么“汉奸”不“汉奸”,不还是邻居?
有关游击队的描写也是如此:郑恩组织的游击队的组成成分是:“地主,富农,退伍兵,无赖光棍,失业长工,有做生意的,原来在各级地方机关吃公事饭的,也有上过几年中小学半瓶子醋的地主儿子。”[6]515他们的目的是:“为发展势力,为闲着无聊,为出风头,为发财,或纯粹为吃饭。”[6]515面对着这样一支队伍,组织者郑恩给他们讲演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他们的表现也就可想而知了。
打麦场上堆着绿豆秸和黄豆秸的圆垛。队伍刚解散不久,照例乱乱糟糟的,一片的吵闹声,笑声和邪许声。有人使劲朝同伴屁股打上一巴掌,被打的立刻去追,人们便逃着笑着:“喂!喂!我是打日本呀。”被打的也笑着骂:“操你妹子,咱们瞧谁是日本!”同伴们就喊着助威:“逮住他,别饶他”,“抄他的后路“打!打小舅子!”[6]517。
这就是师陀笔下的抗日游击队的面目。这些人物,不高大,不“英雄”,有些土气。一次乡间“集训”,我们既看不到备战的紧张,也看不到老百姓同仇敌忾的面孔,看到的却是茅盾笔下百姓在“香市”集会的情形。这里没有“概念”下的拔高,没有“理念”指导的痕迹。写的是老百姓的日常状态:日子虽然过的苦,但总有精神上的“胜利”。一有机会彼此就会互相取闹,博得精神上的愉悦。我们可以说师陀不会写战争,但这也是他的可贵之处,他没有脱离乡村的实际,故意美化这些刚刚被组织起来的乡亲,而是写出了一种他认识到的农民游击队伍:成员复杂,动机多元,队员胆小懦弱,无组织观念,无纪律性……他们带着乡间麦秸秆的味道,带着活泼生动的生活气息而来,不那么高大勇猛,不那么无私无畏,但显得更真实,更可爱。
(三)旧时代小人物性格的生动展示
《历史无情》中最出色的人物是“小人物”。像虚与委蛇,饱含心机,阴险狠毒的魏仲达;整天躺在烟炕上抽大烟、骂人、骄纵儿子的胡太太;自幼不学无术,欺凌弱小,嫁祸于人,毫无廉耻之心,亦没有自知之明的胡凤悟等人。作家对这些小人物是那样的熟悉,或粗笔勾勒,或细节呈现,或静态素描,或动态刻画,寥寥几笔,他们就栩栩如生,个性张扬。
小说人物的语言和行动都极具个性化。如小时候胡世梧的骄横跋扈,就是通过他跟姐姐胡凤英斗嘴的话表现出来的:“我是妈的儿子,将来没有了她,家是我的……你是个赔钱货,我要把你嫁给小张,给我当一辈子门房。”[6]446下人冯嫂劝他少吃梨,他鼓起眼睛说“大爷高兴,滚你的蛋。”[6]447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语与行动,一个纨绔子弟的蛮横嘴脸跃然纸上。出场不多的下人冯嫂和秋香也写得活灵活现。下层小人物冯嫂的特征是刻薄、势利、狡猾、贪婪,会说非常得体的漂亮话,会用自轻自贱的姿态讨主人欢心,表面上对主人逢迎巴结,一转身就偷主人的东西。当她偷东西时被秋香看见,怕被告发就寻找各种机会主动出击,怂恿胡太太将秋香卖出家门。这个小人物身上,有着怎样一颗扭曲的灵魂!
作者还擅长从人的相貌描写摄取人的灵魂,进入人的内心世界,从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刻画人物的性格,如对秋香的描写:“她的黑眼睛是冷的,阴险,她唯一的本事是烧烟,经过了长期训练,先不说火候,单那双小手活动的巧妙就够教人人迷。”[6]444秋香姑娘那冷漠的眼神,阴鸷的性格,就是在“布政第”氤氲的鸦片烟雾中形成的。那个时代,那个家族,给予一个少女的,是空洞的岁月,黯淡的青春和无知的未来。
门房老张是一个罕见的“厚道”人。作者用一句话就表现了他的“厚道”:“他的工钱,大概还是那位老祖宗在道光年间讲定的,至今也没有人要求增加过……他只要天天能喝几两酒,就什么都不关心了。”[6]447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在鲁迅、茅盾、老舍等人的笔下,有一系列这样的“厚道”的“老中国儿女”,他们是鲁迅笔下的闰土、华老栓、祥林嫂、茅盾笔下的老通宝……统治者长期的残酷压迫,自身境遇的凄凉悲惨,造就了这些人沉默的性格,麻木的灵魂。他们是中国“沉默的大多数”。闻一多的“这是一汪绝望的死水”,鲁迅的“人民在欺骗和压制之下,失了力量,哑了声音”,正是一个个“厚道”的老张们的真实写照。
一个出场不多的杨保长,作者也能用一两个画面将此人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历史无情》的第三章第一节中,胡太太去乡下逃难的路上,胡凤英、门房小张、乡下杨保长和胡太太关于日本人进中国的认识各抒己见。作者用简练而富有个性的对话,显现了各自不同的身份和性格特征。杨保长一句一个“太太明白”,“太太知道的顶清楚”,那种奴才对主子说话的谦恭劲儿十足,充分地说明着他过去的身份——“布政第”的佃户。他对胡太太毕恭毕敬,对凤英的见解不以为然,对小张就倚老卖老,嗤之以鼻。这种对不同人说不同的话的风格,很符合乡下保长八面玲珑、“见多识广”的圆滑性格。他有着一代遗老的盲目自信:他对现实的判断根据全部来自于古代的戏文,他能接触到的信息来源也无非如此。这一切,都非常符合他本人的身份特征。
三、一个转折点
其实,早期的师陀对社会上各种时髦的主义包括共产主义是没有信心的。在1936年,他曾写了讽刺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的短篇小说《马兰》。大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翻译者,从乡间带了村女马兰回城,小说通过马兰的视角展现了“五四”后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令人鄙视的行径。不管是李伯唐、乔式夫,还是“五四”后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通病就是太醉心于编织自己的梦想,而没有投入到社会实践中去。所以,他们的结果最后要么是幻灭,要么是跌落到更加痛苦的深渊中去。
也许为时代形式所感,作者也想吸取往日沉思感伤的乡村小故事的不足,想写一部抗战时期混乱背景下的“重大题材”,以表达自己的“姿态”。但是,对文学特性尊重的立场和自己的写作习性使他避免了过多的时代功利主义的干扰,只能以自己的方式为时代“呐喊”。所以,他的小说中,小人物的故事以及对小人物性格的生动刻画依然占据了文本的核心。
不论“转变”如何艰难,作家在实际生活中逐渐适应了新的时代要求,开始按照新的意识形态规范写作。1950年后,师陀在社会身份上已是“国家干部”,正式地纳入了国家体制,从1950年至1952年1月,他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1957年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专业作家,河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上海文联理事等职务。此期的师陀不断按照党的要求“深入生活”,发表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和散文等“应景之作”,如《石匠》《前进曲》《保加利亚行记》,短篇小说集《山川·历史·人物》,历史小说《西门豹的遭遇》,电影剧本《农村钟声》《洋场狼群》等,70年代以后,师陀还对《无望村的馆主》《结婚》《马兰》等作品的再版进行了修订,并发表了一批总结自己创作经验的文章。
对很多现代作家来说,面临新中国成立这个大的时代语境,他们的写作都要面临一个转型问题,考察这个转折点,可以发现作者很多微妙的心态,更容易发掘出作者所坚守的创作个性。正像丁玲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杜晚香》的创作过程中“《在医院中》恰好是一个戏剧转捩点”[7]那样,师陀的《历史无情》也无意中成了他创作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之后,师陀的写作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原来的写“人物”写“故事”写“风景”,变为了后来的写“任务”写“运动”,由展现中原乡村人物落后的精神状态变为了宣传党的政策,渲染对党的感恩之情。在这个转折过程中,《历史无情》中那扑面而来的生活化气息,小人物的种种表现形态,那种将激烈动荡的大时代与周密细致的日常生活相融合的表现手法,无疑是京派叙事话语在20世纪50年代闪现的最后一抹霞光。
[1]刘增杰.师陀小说漫评[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2(1).
[2]师陀.师陀全集:第1卷(下)[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95.
[4]孙先科.说话人及其话语[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58.
[5]刘增杰.师陀研究资料[C].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6]师陀.师陀全集:第2卷(下)[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7]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54.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1.032
2015-06-26
河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2015-JCZD-010)
I206.6
A
1000-2359(2016)01-0166-06
张东旭(1977—),男,河南兰考人,文学博士,河南科技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