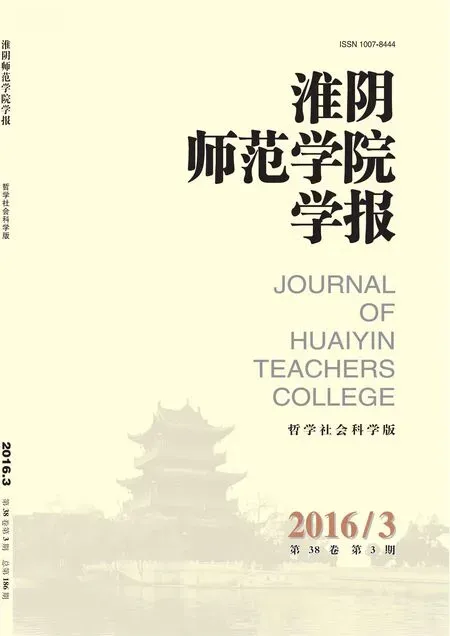互联网+时代的文化转向
——从编辑中心制到作者中心制
刘 影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 上海 200241)
互联网+时代的文化转向
——从编辑中心制到作者中心制
刘影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 上海 200241)
摘要:工业经济时代建立了以编辑中心制为核心的审核—过滤—发布的知识生产体制。它赋予主编和编辑们作为信息把关人的专有权力,确保了内容生产的高质量和专业性,但也剥夺了作者和读者自由表达的权利,使他们沦为被大众媒介规训的对象。当下互联网自Web2.0时代特别是社交媒体基于人的信息互联模式,在不断消解工业化媒体技术官僚体制的同时,重新建立了从UGC到PGC的知识权威体系。作为优质原创内容的提供者——作者,代替编者,成为文化新世界的魔杖执者。
关键词:互联网+;编辑;作者;知识生产体制;文化转向
互联网+、互联网思维等热词的流行,反映了人们对互联网认识的一种普遍趋势,即无法再把互联网简单视为带来威胁和挑战的新媒体、第四媒体,当它像水、电一样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带来的是全新的社会范式和文化转向。正如喻国明教授所说,这是“过去运作模式的逻辑中断,而不是简单的惯性延长”。但是这种范式转变和文化转向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雾里看花,众说纷纭。本文拟从知识权力论的视角,结合当下互联网热点文化现象,论述从工业化媒体时代编辑中心体制的精英掌权经过UGC的用户赋权再到互联网+时代的作者中心制的知识权力交接过程。
一、工业化媒体的危机:编辑中心制的崩塌
19世纪以来,随着机器大生产和商业资本的介入,报纸、广播、电视三大媒介代表的工业化媒体逐渐确立了一整套严密的产销机制:主编中心制、大批量复制、多数人的口味、广告二次售卖,并在20世纪早中期迎来它的黄金时代。互联网的侵入,首先是以技术的姿态带来渠道和介质传播的困惑,但是近十年逐渐从媒体品牌、精英人才、文本传播三方面全面侵蚀工业化媒体体制,其核心是编辑中心制的崩塌。
(一)媒体品牌。
“2043年春季的某一天,美国一位读者把最后一张报纸扔进了垃圾桶——从此,报纸消失了”[1],这种“狼来了”的预言在2008年后逐渐变成寒冷的现实。2008年11月美国第一份全国性大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停办印刷版,同年12月美国第二大报业集团论坛报业集团申请破产保护,2009年9月读者文摘公司申请破产清算重组,2012年底《新闻周刊》停发印刷版,2013年8月亚马逊收购《华盛顿邮报》……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同样延伸到受体制保护的中国新闻业,纸媒陆续关张、报业集团合并,全力转战新媒体并号召“野蛮生长”。除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上几家全球性“超级报纸”有限度、有松动地设立付费墙举措外,传播快速信息的“报纸已死”,基本已是业界共识。
(二)精英人才。
有一长串的名单说明,传统媒体的精英人物或昭告天下或悄无声息地离开他们一手缔造辉煌的阵地:前《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前《南风窗》《第一财经日报》主编秦朔,前《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苗炜,前央视《对话》节目制片人罗振宇,前央视主持人张泉灵……2014年,新浪门户网站总编辑陈彤辞职,背后还有一串离开的互联网1.0时代的老兵,他们无一例外选择去全新的领域创业。资深媒体人陈序说,转型时代的人“要用几年里学到的点滴来解构、否定之前一百多年中笃信的一切。美联社的修辞训练、华尔街日报的叙事方法、纽约时报的版式风格、新闻周刊的编辑流程都是羁绊而非助力”[2]。但媒体人仍然义无反顾地“转型”,本身也说明工业化媒体的生无可恋。
(三)文本传播。
如果说有倒掉和离场,也有屹立和坚守,新旧媒体仍然处在交错融合的状态。但是,互联网+创造的一种新的内容生产机制,完全把传统媒体摒隔在新世界的大门外。典型的例子可以举韩寒的《ONE·一个》,这个号称电子杂志的互联网产品(文艺阅读应用),在“复杂的世界里,一个就够了”的编辑方针下,每天只为你准备一张图画、一篇文字和一个问答,从app迅速扩张到纸质书刊、淘宝店、“很高兴遇见你”餐厅、“One Plus”线下体验店,网罗韩粉和文艺范儿的小年轻,建立起一整套“青春商品体系”。而传统纸媒杂志品牌《三联生活周刊》的数字化转型还停留在对纸质内容进行适合网络终端阅读的形式改造,采用内容免费加传统广告的运行模式。两者就是“互联网+”和“+互联网”的区别。
二、互联网+的文化转向:从机构到人
韦伯和福柯的理论最能清晰阐释工业化时代的组织结构和文化特征。一是“科层制”的金字塔结构,强调职能化的劳动分工、严格的等级层次、技术专长、公事公办以及制度,排斥非理性的情感、心血来潮、个人关系以及个性。二是“权力—知识”观,福柯把权力的概念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领域,强调权力并非单纯压制性的力量,而是生产性的,知识精英通过掌握知识,拥有妨碍民众表达的自上而下的“查禁权力”,权力的策略是话语。编辑中心制恰是工业化时代知识生产秩序和权力的象征。
互联网进入中国20年经历了门户网站、搜索引擎和自媒体、社交媒体主导的四个阶段。门户网站时代用户有了予用予取的自由,但“目录套目录”的树状架构仍然是工业化末期的秩序等级的产物;搜索引擎开始真正将这种工业化思维颠覆掉,信息呈网状态势存在,信息与信息之间,只有相关关系,并没有从属关系;但是直到Web2.0媒介兴起,自媒体才彻底颠覆工业化时代编辑中心制赖以生存的自上而下的钟式组织架构。
(一)关注“人”:自媒体的传播特征。
2004年丹·吉尔默(Dan Gillmor)提出著名的“自媒体”(We the Media)概念[3],或称草根媒体,其代表类型是博客、Facebook、Youtube、维基、Twitter等Web2.0机制媒介,跟Web1.0时代的门户网站、Email、BBS等相比,最大变化是用户生成内容,使得互联网由“可读”变“可写”,互联网信息权力中心发生从公共机构或组织向个人的转移。正是基于这一本质区别,美国媒介学者保罗·莱文森提出“媒介三分说”:前互联网时代的报纸、广播、电视是旧媒介,Web1.0媒介是新媒介,Web2.0媒介是新新媒介[4]。
社交媒体是所有自媒体关系的总和,其出现更强化了这一人本趋势。微博微信重点是“我”的关注和“朋友圈”,由此回到互联网早期的元精神,建立点对点之间真正自由、完全平等的直接交流,将互联网的“内容位于中心”模式彻底改变为“用户位于中心”模式,将权利交还给用户。而传统媒体机构谋求数字化生存,往往沿袭工业化时代机构主体的旧思维,根本上忽视了研究互联网技术媒介形态演进所带来的组织更新和文化转向。
(二)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作者的赋权。
Web2.0媒体的特征是去中心化和多点化,每个用户都可以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西方为此专门造了一个新词“Prosumer”(产消者,或称生产性受众),所谓“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全民麦克风时代,但是这种理想模式中的平权光环很快褪色。用户创造内容(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s)的缺点是杂乱、碎片化,缺乏专业性、系统性,有国外新媒体研究人士尖锐批评这是以傻子专政代替专家统治[5]。另外,微博的“关注”功能,使它呈现45度角的仰视姿态,有研究者认为类似社会交往中的攀附现象[6],即你只会关注你瞧得起的人,导致掌握更多现实资源的人再度成为社交媒体的意见领袖和圈子核心。所谓微博的二八定律,20%的人掌握了80%的流量,呈现“再中心化”趋势。
这些20%的优质内容生产者(此文我们为便于与“编辑”对称,仍采用工业化媒体时代的“作者”称谓),导致UGC文化向PGC(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文化回归。所以有人说,新媒体上活跃的仍然是精英。但此精英非彼精英,这是一场“知识精英的接力”。
三、“作者中心制”凸显互联网思维
工业经济时代建立了以编辑中心制为核心的审核—过滤—发布的知识生产体制。它赋予主编和编辑们作为信息把关人的专有权力,确保了内容生产的高质量和专业性,但也剥夺了作者和读者自由表达的权利,使他们沦为被大众媒介规训的对象。首先,作者无法在作品面世前与读者直接交流,使作品最优化,也无法使自己的读者数值最大化;其次,作者无法跨越报刊、图书、游戏、动漫、影视等门类产业的槛限,使内容传播和自身价值最大化。这两项权利均受制于工业化媒体组织的垂直架构和专业人士的“权力审查”。
自媒体恰恰可以克服工业化媒体知识生产的重大瑕疵。其一,自媒体是一个由个人驱动的文化环境,更多地彰显了个体的力量。个体之间可以以不同的自组织方式形成互动交流,比如作者和读者(用户)。其二,自媒体去中心化的依靠信息流动形成的交流模式,使知识生产跨媒体跨行业成为可能,比如网络IP热。优质内容创造的个体者——作者,兼具两者优势,成为互联网文化新世界权力的魔杖执者。
(一)作者的传播权:内容生产的个体私有化和范围经济。
内容为王还是渠道为王,曾是新媒体发展头十年争论的一个焦点话题。互联网注意力经济特征、渠道的专业性独立性,都导致渠道一度有凌驾内容之上的趋势。但是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已经如同水、电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渠道资源呈现饱和状态,此时优质内容反而成为真正的稀缺资源。特别是当今人们身陷碎片化的阅读无力自拔,对系统优质知识的渴求比古典阅读时代更强烈。但是互联网+的内容生产呈现作者个体控制和范围配置的特征。
著名自媒体人罗振宇认为,自媒体把原来媒体的两极价值枢纽——内容和渠道,变成了魅力人格体+运营平台[7]。《罗辑思维》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它是罗振宇主持的网络火爆的知识脱口秀节目,倡导“在知识中寻找见识”,借助优酷和微信平台发布,跟有道云笔记平台、多看阅读、长江文艺出版社、手机轻电台荔枝FM多方合作,打破传统印刷和视觉、线上线下媒介的专业阈限,吸纳各渠道用户,探索并成功打造了一个网络知识社群品牌。其成功策略包括罗氏个人品牌、内容跨媒介生产和粉丝经济。
网络IP(Intellectual Property)词汇的流行,也是这一特征的表象。IP本义是技术性的互联网协作地址,突然在不重视知识产权的国度变成优质内容资源得到热捧。主要是作为IP核心来源地之一的网络文学,通过影视剧改编,包括诸如游戏、漫画、周边衍生产品的销售,其综合品牌及衍生价值导致作品身价水涨船高,卖书不如直接卖IP。精品化的内容带动全产业链多渠道的营收模式,在前互联网+时代并不罕见,像《哈利波特》《黑客帝国》。但是网络IP大热的奥秘在于买IP首先买的是IP背后的粉丝,有媒体人士透露:一个优质IP首先要具备的因素是,粉丝量必须大,另一个则是,要符合主流受众的审美。社交媒体奠定了粉丝经济大行其道的社会基础。虽然有学者从文化批评视角认为“大IP就是大垃圾”,但是如果我们从IP热凸显了互联网+内容自由流动的特征观察,它无疑解放了作者的生产力,而且詹金斯认为真正跨媒体叙事最重要的是创意,而不是对延伸技巧的使用[8]。所以作者仍然起着关键作用。
新媒体环境下只要有运营平台,作者——魅力人格体的具象,就能把内容生产紧紧抓在自己手中。而且传播渠道和平台的多样化以及受众碎片化特征明显,使得商业模式中产品、接入点、渠道、消费语境和价值主张等要素有了新的配置可能,可以创新性地融合各种媒介形式,开发跨媒体产品,实现范围经济效应。
(二)作者的话语权:从组织传播到粉丝经济。
媒介机构是工业化时代新闻和知识生产的主要场所,其组织的特性与常规是影响新闻生产的重要因素,比如从“记者中心制”到“编辑中心制”,个人的效能依附取决于组织内部的科层结构、劳动分工和生产流程。社会化媒体则是一种去组织化的自组织,权力基本模式是行动者凭借话语吸引其他行动者的关注而累积的关注者(粉丝)的规模。作者话语权的来源,就是注意力经济的典型——粉丝经济。
粉丝现象本是大众媒体工业化的产物。从法兰克福学派以生产主义理论视野对粉丝是丧失自我意识的被动无助、无分辨能力的“文化瘾君子”的严厉批判,到霍尔、德赛都、费斯克等从消费理论视角转而积极肯定迷群体的文本再生产能力。互联网+的泛媒化,使粉丝由“过度使用媒介”的人群演变为普遍的跟随现象,人人有“粉”(follower),人人皆“粉”(follow)。
作者能够创造“粉丝经济”的优势在于:首先,粉丝起源于崇拜性,作者通过话语传播策略或专业内容生产,更易获得他人的认同、信服与顺从,基于精神和价值层面的互动和共鸣,使他们与粉丝的联系比专业机构更坚韧而富有人情味;其次,粉丝需要参与感,作者的内容生产天然具有开放度,比如关于封面书名甚至故事进度和结局征求意见,更能得到忠粉的积极响应和到位点评;再者,粉丝看重社交性,社交媒体导致他们拥有自己无限外延的小圈子,转发是认同,也是一种信任机制[9],同样等于是口碑营销。
“粉丝经济”的特殊之处在于价值观认同转化为经济利益的过程,而不是传统产品经济理性、技术、干巴巴的标准,它基于爱、喜好和共同语言。所以雷军小米手机被视为国内粉丝经济的开山鼻祖,“卖手机卖情怀”,这一概念迅速从商业实体领域弥散到精神文化领域。先有《小时代》系列粉丝电影横空出世,出版领域亦不乏其例。2014年众多畅销书排行榜首位的张嘉佳《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以其新浪微博“睡前故事”系列出名,引发几百万粉丝围观转发,6个月创下两百万册的图书销售佳绩。
胡泳在翻译克莱·舍基的名著《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时,把主书名定为《未来是湿的》,认为互联网的终极意义、社会化网络和社会性软件,会让世界变得更人性和有人情味[10]。个体化的作者显然比机构、微群在这个世界更长袖善舞。不过,他认为“粉丝经济不是社群经济”,社群强调个体活跃度和个人意愿与整体的协作,人与人的横向沟通最重要,“粉丝经济”本质是主流化策略,它们的向心力过强。这一观点也侧面印证了互联网+文化环境下粉丝经济实际是“作者中心制”模式。
四、结语
资深媒体人陈序写了本书《主编死了——没有主编才是新媒体》,他说:主编“死”了意味着各式各样的编辑中心体制被连根拔起。主编和这个职位所代表的媒体技术官僚体制在死去。
这让人想起罗兰巴特的著名命题:作者死了。但这不是一个讣告。他在文章末尾说:“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作者在作品交付后就不存在了,赋予读者各种阐释权。死亡宣告某种替代物的新生。
今天,主编死了,作者重生了。互联网+时代,作者在工业化媒体时代被剥夺被损害被贬抑的各种权利重新得到释放,无限蓬勃无限自由。
参考文献:
[1]菲利普·迈耶.正在消失的报纸——如何拯救信息时代的新闻业[M].张卫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
[2]陈序.主编死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3]丹·吉摩尔.草根媒体[M].陈建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保罗·莱文森.新新媒介[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5]安德鲁·基恩.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M].丁德良,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
[6]黄绍麟.微博最关键的运作原理:45度仰角,一种我们称之为高攀的社会行为[EB/OL].(2011-04-09)[2015-12-20].http://china.digitalwall.com.
[7]罗振宇.新媒体的本质就是社群[EB/OL].(2014-03-20)[2015-12-20].http://fj.qq.com/a/20140120/013287.htm.
[8]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旧媒体的冲突地带[M].杜永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57.
[9]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的简化机制[M].瞿铁鹏,李蓓,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0-40.
[10]克莱·舍基.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M].胡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孙义清
作者简介:刘影(1971-),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美国纽约大学传播学系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传播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6)03-0403-04
收稿日期:2016-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