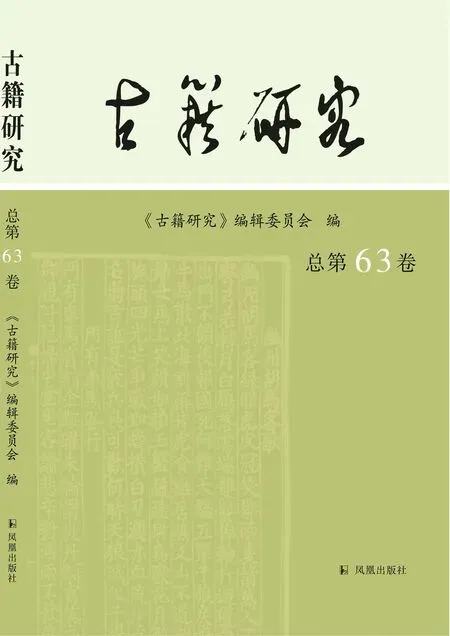《隋志》总集三例发覆*
智晓静 胡 旭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
《隋志》总集三例发覆*
智晓静 胡 旭
由于年深月久,加上兵燹水火,《隋志》著录的许多总集,早已亡佚,我们要了解其原貌与性质,困难极大。有的总集虽然保存了下来,但辗转传抄,鲁鱼亥豕,讹误颇多。《文章流别集》《文选》《善文》等就是如此,它们在《隋志》著录的诸多总集中,有一定典型性,本文对其进行探讨,力图揭示它们的某种真实面貌或基本性质,尽量深化长期以来围绕着它们的一些简单认识。
一 《文章流别集》的双重性质
《文章流别集》早已亡佚,但唐人尚能见到约三分之二*《隋志》著录《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下有注:“梁六十卷。”然《晋书·挚虞传》云:“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疑六十卷本为后人分卷,与《文选》初三十卷被后人分为六十卷相类。。故《隋志》论及《文章流别集》,当有相当的可信度。其中有云: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此段文字历来被学者关注并大量引用,但理解却有偏差。其内涵至少有三:第一,总集出现的背景。建安以后,文人之作——特别是辞赋——越来越多,文人的作品汇集也越来越广,但这些汇集是杂乱的,没有什么标准*关于“众家之集”一语,易生歧义。一是承“辞赋转繁”,指辞赋的汇聚;二是众多的别集。笔者认为,建安时期时虽然已有别集编撰,但依然在萌芽阶段,并没有明确的别集概念,故认为“众家之集”指以辞赋为代表的作品汇聚。。第二,挚虞的划时代作用。挚虞看到当时读者浏览文章的繁杂与辛苦,对这些作品进行了整理和分类,形成诗、赋等系列,并汇聚在一起,称为《文章流别集》。第三,《文章流别集》的影响。挚虞之后,文人多认可他的做法,效仿他的人很多,类似于《文章流别集》的文章类聚,次第出现,影响深远。
然而,看似明白的这一段记述,其实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挚虞究竟是怎么分类的?比较传统的看法,是挚虞以文体来分类,即诗归为一集,赋归为一集,其他文体依此类推,各为一集。各集之中,大约再以作家依次排列。这种看法,得到古今学者的普遍认可。
但也有不认同这一看法的,章学诚云:
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于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于晋代。*叶瑛认为,“实仿于晋代”之“仿”,当为“昉”之误,乃起源之意。说可从。参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卷三〈内篇三〉)》,北京:中华书局,第300页。
很多学者看到这一段文字时,认为章学诚所谈的是别集的起源,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章学诚所说的“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很显然地认为,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是以一部部别集为单元的,众多别集汇聚在一起,形成一部大型总集。
那么,章学诚的看法与多数人的看法究竟哪一个更有道理呢?不妨先对《文章流别集》这一题名的关键字作出解释。
关于汉魏六朝时期“文章”的概念,郭绍虞先生、杨明先生都进行过论述*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0页。又,杨明:《欣然斋笔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231页。,简言之,泛指一切文字作品。“流”该如何理解?它体现的应该是时间顺序,自古至今的作家及其作品依次排列,顺流而下。“别”又如何理解?它是区分的意思,不仅将一个个作家及他们的作品区分开来,而且在每一个作家的集子中,用文体将作品区分开来。“集”乃汇聚之意,文章汇聚而称之为“集”者,实自《文章流别集》始。
把《文章流别集》理解为一部部别集汇聚而成的总集,并不突兀。在《文章流别集》之前,这样的情形已经出现过。曹丕《与吴质书》云: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
曹丕所做的事,就是搜集徐幹、陈琳、应玚四人遗文,汇聚成册。怎么汇聚?应该是人各一集,然后再合成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先成别集,后再合成总集。虽然此时别集、总集的概念都没有出现,而编撰别集和总集的实际行为,已经实实在在地出现了。曹丕为建安诸子撰集的做法,对挚虞编撰《文章流别集》有所启示,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综上所述,《文章流别集》是实实在在的一部大型总集,但这部总集是由一部部别集组成的。别集实际上早已出现*胡旭:《先唐别集叙录(前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5页。,只是有其实而无其名而已,别集概念是随着《文章流别集》概念的出现而出现的。然而,此时的《文章流别集》虽然是实实在在的总集,但也是有其实而无其名,直到南朝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时,才出现了总集的概念。
二 《文选》编次体现的选本特征
《文选》是总集,更是选本。我们通常说《文选》编撰是出于梁建立后文化建设方面润色鸿业的需要,这是一个形而上的考量。其实,《文选》还有一个很现实的编撰目的,就是提供文学写作的范本。既然是范本,选文得有一定的标准。古今学者大多认为“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是《文选》的选文标准,固然不错。但是,作为一个选本,文体类型与作品典范是必须考虑的,因而典范性是《文选》选文的重要标准。
《文选》序最后谈到编次顺序:“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可是,实际编纂时,却并不遵守这个规定。一些学者进行了考察与统计*关于《文选》编次问题,骆鸿凯、王晓东、力之等学者都有统计和论述,不一一列出。,多认为是编撰失误。当然,编纂失误是可能的,但大面积的编纂失误,就很值得怀疑了。其中有些看起来编次不按时间先后的情况,恰恰是着眼于选本典范性的要求。兹举若干典型实例,予以说明。
赋之“音乐类”,一般学者都认为潘岳《笙赋》不当排在成公绥《啸赋》之前,因为成公绥(231-273)比潘岳(247-300)年长甚多。但是,潘岳是西晋文学家的代表,他的《笙赋》和同入选《文选》的王褒《洞箫赋》、马融《长笛赋》、嵇康《琴赋》,是音乐赋的正体,具有典范性。而成公绥的文学影响远逊潘岳,其《啸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音乐赋的一个变体,独具特色却非主流。《啸赋》次于《笙赋》,原因或许在此。
诗之“公宴类”,建安四位诗人的编次是曹植、王粲、刘桢、应玚。对此李善注曰:“赠答、杂诗,子建在仲宣之后,而此在前,疑误。”*(梁)萧统:《文选》,(唐)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83页。但仔细考察,好像是有意为之。考察《文选》所收公宴诗,曹植这一首写得最好,内容包括宴饮、冶游、言志,其中的“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乃千古神来之笔。将其看作《文选》所收公宴诗的最佳典范,并没有什么疑问,置其于此类之首,当出于这种考量。王粲的《公宴诗》在文学成就上与曹植之作,相距甚远,但形式上切题,所谓“述恩荣,叙酣宴”是也,入选的形式意义远远大过内容价值。刘桢的《公宴》不写宴会情形,而写宴后游览,景致清丽优美,所谓“怜风月,狎池苑”是也,其入选《文选》,也是出于“典范”的考虑。可以说,王粲、刘桢之作,各写了一个侧面,不及曹植之作的典正,他们和应玚之作皆位列曹植之后,从选本的需要来看,是符合实际的。
诗之“哀伤类”,嵇康的《忧愤诗》排在首位,曹植的《七哀诗》次之,王粲的《七哀诗》又次之。众所周知,嵇康的《忧愤诗》乃其身陷囹圄时所作,既有对自身遭遇的叹息,又有对世事黑暗的愤慨,思想深广,一唱三叹,十分感人,实为此类诗歌之冠,故能排在早于他的王粲与曹植之前。这是《文选》给“哀伤类”诗歌选择的模版,即个人的彻骨感受与深刻的社会意义。相对于嵇康的忧愤诗,曹植和王粲的《七哀诗》是对社会的哀伤。曹植的《七哀诗》之所以排在王粲的《七哀诗》之前,则与《文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有关。相较而言,曹植之作华美流丽,却又怨而不怒,王粲之作过于直露,有伤渊雅之致。李善注云:“赠答,子建在仲宣之后。而此在前,误也。”如果子建在仲宣之前为误,那么嵇康在子建仲宣之前,如何理解?李善显然没有看到《文选》选文强调典范性这一本质。
文之“弹事类”共选文三篇,任昉的《奏弹曹景宗》《奏弹刘整》在前,沈约的《奏弹王源》在后。沈约比任昉年长近二十岁,《奏弹王源》一文写于他在南齐任御史中丞时。任昉的两篇文章,写于他入梁后任御史中丞时。无论从年辈看,还是时间先后来看,《奏弹王源》似乎应该排在前面。《文选》将任昉之文排在前面,绝非编次失误。弹事类文章之特点,《文心雕龙》说得明确:“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宪清国。昔周之太仆,绳愆纠谬;秦有御史,职主文法;汉置中丞,总司按劾;故位在鸷击,砥砺其气,必使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者也。”从这个角度而言,任昉之文笔挟风雷,正气凛然,确实较沈约之文略高一筹,所谓“沈诗任笔”,此言非虚。显然,最能体现南朝弹事类文章特点的,是任昉的此类文章。还有两点,也有申述的必要。第一,弹劾对象曹景宗、刘整、王源三人中,曹景宗是梁开国元勋,对其弹劾最有代表性、典型性,编次在先当与此有关。第二,就事件而言,奏弹曹景宗是军国大事,奏弹刘整、王源则着眼于整齐风俗,孰轻孰重亦有分别。总体而言,这三篇文章分为两大类,第二类中又分成两小类,侧重点各不相同。
《文选》中只要选录谢惠连的作品,全部排在同类作品之首。他的《雪赋》在谢庄的《月赋》之前,这是没什么可说的,因为他年辈长于谢庄,作品也不亚于谢庄之作。而他的《泛湖归出楼中玩月》排在谢灵运以《登池上楼》为代表的八首游览诗、颜延之以《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的三首诗之前,还是令人惊讶的。但是,仔细阅读他们三人的游览诗,可以看出颜延之的是应制之作,不及二谢之自然。谢惠连和谢灵运对自然之景皆别具只眼,悠然心会,但谢惠连之作,境界更为阔大,抒情也更为深远,谢灵运的格局则要小一些,爱发一己幽情,相形之下,高下立分。尽管谢灵运在后代的名气更大,但齐梁时人们对谢惠连的评价也很高。《诗品》云:
小谢才思富捷,恨其兰玉夙凋,故长辔未骋。《秋怀》《捣衣》之作,虽复灵运锐思,亦何以加焉。又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谢氏家录》云:“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
在钟嵘看来,谢惠连死得太早,未能尽展其才,即便如此,《秋怀》《捣衣》这样的作品,谢灵运也无法超过。甚至谢灵运的绝世佳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之得来,也与谢惠连有关。虽然《诗品》置谢灵运上品,谢惠连中品,但从评语来看,贬灵运褒惠连之意甚明,于此不难看出谢惠连在齐梁时期的巨大影响。
《文选》的编次确实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究竟是源于当时的编纂,还是后来的传抄,甚为复杂。但是有些看起来有错误的编次,可能实际上却是撰者的匠心独运。正如众多研究者所看到的,《文选》基本上没有把作家朝代编错的情况,这是其严谨之处。同一朝代的作家在某类作品中的编次,不遵守“时代相次”的原则,某种程度上是从作品典范性的角度考虑而作出特殊安排,这正是《文选》作为选本的重要特征。
三 《善文》与《古今善言》的误判
《隋志》著录杜预撰《善文》五十卷,两《唐志》著录杜预撰《善文》四十九卷。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著录两部《善文》,一是杜预撰,另一华廙撰。前者题解云:
《齐书·晋安王子懋传》:“赐子懋杜预手所定《左传》及《古今善言》。”是此书一名《古今善言》也。《玉海》五十四云:“《史记》李斯传注,辩士隐姓名,遣秦将章邯书,在《善文》中。”《困学纪闻》卷十二同。廷式案,陶渊明《圣贤群辅录》、章怀太子《后汉书·皇后纪》注并引《善文》,当出此书。《御览》四百三十一引《古今善言》曰:“灵帝时欲用羊续为三司,而中官求赂,续出黄纸补袍以示使者。”*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二十五史补编(三)》,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3795页。
文廷式的观点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杜预的《善文》一名《古今善言》。第二,《史记》裴骃注、陶渊明《圣贤群辅录》《后汉书》章怀太子注所引《善文》,皆杜预之书。
《古今善言》究竟是什么样的一部书?撰者是谁?《宋书·范泰传》云:“泰博览篇籍,好为文章……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传于世。”《水经注》云:“范泰《古今善言》曰:日南张重,举计入洛,正旦大会,明帝问:‘日南郡北向视日邪?’重曰:‘今郡有云中、金城者,不必皆有其实。日亦俱出于东耳,至于风气暄暖,日影仰当,官民居止随情,面向东西南北,回背无定。人性凶悍,果于战斗,便山习水,不闲平地,古人云:五岭者,天地以隔内外,况绵途于海表,顾九岭而弥邈,非复行路之径阻,信幽荒之冥域者矣。’”*《水经注》卷三十六《温水》。参《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997-2998页。《隋志》《旧唐志》《新唐志》皆录范泰《古今善言》三十卷。《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古今善言》二十一卷,不云撰者。《崇文总目》著录《古今善言》二十卷,不云撰者。从上述文献不难看出,《古今善言》的著作权基本上没有争议*《崇文总目》著录诸书,皆不云撰者。,当属范泰。《古今善言》的著作权是明确的,那么其性质如何呢?《隋志》《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旧唐志》《新唐志》《崇文总目》皆明确地将其归入子部杂家,没有任何分歧。可见,将《古今善言》与总集部的《善文》等同,是一件荒谬的事。
那么,文廷式为什么要说《古今善言》就是杜预的《善文》呢?原因在于他对文献的误读。《南齐书·晋安王子懋传》之“赐子懋杜预手所定《左传》及《古今善言》”一句,确实容易产生歧义:一是《左传》和《古今善言》都是杜预手定的,二是《左传》是杜预手定的而《古今善言》不是。揆以实际,正确的应该是第二种解读,即“杜预手所定《左传》”和“《古今善言》”,后者与杜预无关。文廷式的误读,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影响,他们的研究也因此发生了某些误判*如范子烨先生依据文廷式的结论,推断范泰的《古今善言》很可能是在杜预的《古今善言》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参范子烨:《华廙善文考略》,《书品》,2010年第1期,第78页。。
《隋志》等文献著录杜预《善文》,归入总集,但华廙的《善文》却不见著录。《史记》裴骃注、陶渊明《圣贤群辅录》*《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类书类存目》力辩《圣贤群辅录》非陶渊明所作,而是北齐阳修之增入陶集。、《后汉书》章怀太子注所引《善文》,皆未明确指出撰者,因而要说这三处引文出自哪一部《善文》,尚无充分的理据。
华廙的《善文》虽然不见著录,但却可从传世文献中找到一些讯息。《晋书·华表传》附其子《华廙传》云:“栖迟家巷垂十载,教诲子孙,讲诵经典。集经书要事,名曰《善文》,行于世。”这一段记载,时间稍有点含混,“十载”不很精确。华廙栖迟家巷,原因有二:一是父丧葬讫,晋武帝要他回到都督河北诸军事任上,他拒绝,因而忤旨。二是鬲令袁毅贿赂公卿获罪,华廙与袁毅同为卢氏之婿,且有不法之事,受到牵连。《华表传》对华表之死记载明确,为咸宁元年(275)八月。袁毅事发生时间虽不载于《华表传》,却见于《何劭传》:“咸宁初,有司奏劭及兄遵等受故鬲令袁毅货。”二者互证,可知华廙咸宁元年末废官。又《华廙传》云:“太康初,乃得袭封。”因而华廙栖迟家巷亦即编撰《善文》的时间当在咸宁二年(276)到太康元年(280),前后约五年,而不是本传所说的十年*范子烨先生认为,华廙撰《善文》的时间在太康初年以前,颇有见地。参《华廙善文考略》,第74-78页。。顺带而及,华廙的生卒年也不太难考,本传云其惠帝初与韩寿不协,不登台司,年七十五卒。而《晋书·贾充传》云:“寿官至散骑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大致可知华廙的生年在建安二十一年(216),最迟也不超过其后一二年。
上述考证,可以得到两点启发。第一,华廙的《善文》是“集经书要事”,可能是部分抄录、撮要,形成一部书。同类情况有被《隋志》著录在总集部的隋代李文博的《政道集》。马总《意林》序云:“隋代博陵李文博,攓掇诸子,编成《理道集》十卷。”*李文博此书原名《治道集》,唐人避李治讳,故称《政道集》《理道集》等。这种归类是否正确,是另外一个问题,此处不赘。第二,华廙与杜预(262-284)基本上是同时人,很难找到华廙《善文》讹为杜预《善文》的理由。杜预的《善文》,《隋志》等著录确切,但相关传记则无一提及,除了知道这是一部五十卷的总集外,其他信息皆付阙如,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至于后代学者的评价,如骆鸿凯先生云:“最初选集列代之文以成一书者,当自晋杜预之《善文》始。”*骆氏此说,遭到一些学者的反驳,如力之先生的《总集之祖辩》(《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就认为,骆氏的观点是总集始于《善文》。窃以为,这是一种误读,骆氏只说“选集列代之文为一书”自《善文》始,并没有说《善文》是总集之祖。又,近人黄逢元在其《补晋书艺文志》中云“据杜预撰《善文》五十卷,则荟萃文章自杜预始。”骆氏之说,当源于此。都是就《隋志》、两《唐志》等文献的著录来说的,其实可能并不知道原书的真正面目。
《隋志》著录的总集,大多已经亡佚,要准确地了解其原貌,已经相当困难。更为重要的是,《隋志》著录的一部分总集,与其阐述的总集概念,并不完全吻合,与后人的总集概念也有一定的分歧,这越发给我们的理解带来了困难。如何在相关文献中寻找蛛丝马迹,深入考察,反复比勘,获得尽量客观、合理的认识,是先唐总集研究的重要任务。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13&ZD109)之子项目:先唐集部叙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