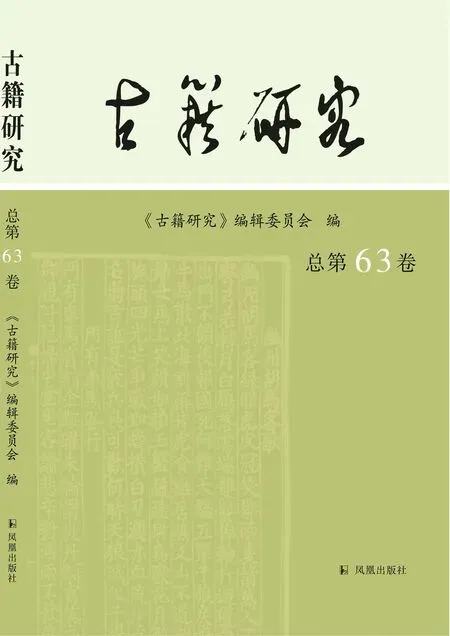空间、地域文化与文化观念
——论班固的地域移动与《汉书》正统史观的形成
杨 霞
(作者单位: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
空间、地域文化与文化观念
——论班固的地域移动与《汉书》正统史观的形成
杨 霞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同时也是一部“宗经矩圣”*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之《史传第十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0页。、充满正统思想的政治文本。“正统”本指血统纯正,而后发展为一历史政治概念,多指某一政权建立、存续的合法性。《汉书》以儒学为尊,以神化帝王之出生情境来附会“君权神授”论;以大量灾异记录来凸显“灾异谴告”说;强调等级制度,主张“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班固:《汉书》卷92《游侠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697页。;抨击王莽代汉之举,指出“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汉书》卷99下《王莽传》,第4194页。。——所极力呈现的正是“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严可均:《全后汉文》卷26《典引》,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56页。的政治信念,以证西汉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意在说明光武政权乃西汉王朝的继续与发展。这一政治立场鲜明的著作得到统治者的褒扬和推广。“《汉书》一出,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范晔:《后汉书》卷40上《班固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334页。。在其后历代,“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12《古今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39页。,——已然是史学正宗。
《汉书》由班彪、班固、班昭、马续相继成之:先是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即《史记后传》数十篇)”*《后汉书》卷40上《班彪传》,第1324页。,乃《汉书》编撰之发轫期;班彪去世后,班固续修其业,自二十余岁始,前后历时二十余年,在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此著;班固卒,班昭、马续分别撰写“八表”与《天文志》,正式完结此书。
作为《汉书》最重要、最主要的编写者,班固本人的正统意识是《汉书》正统史观的思想来源,而他本人浓厚的正统意识的形成,不仅与其学识、家学、时代有关,与其一生行迹也有大关联。本文尝试以班固的地域流动为考察对象,对其浓厚的正统史观的形成作一论述。
一、 地域流转:扶风故里与洛阳新都
(一) 班固一生行迹
班固生于光武帝建武八年(32),卒于和帝永元四年(92)。据《后汉书》记载以及有关学者的论述,可将班固一生行迹作大致归纳。其中,考虑班固入窦宪幕府发生在89年,而此前数年,也即章帝建初七年(82),班固已将《汉书》上呈朝廷,所以这里重点梳理章帝建初七年(82)之前班固的流动轨迹,大致若此:
1. 少居洛阳
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河西大将军窦融征还洛阳,“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807页。。后光武帝“雅闻彪才,因召入见,举司隶茂才”。由这两则材料可知作为窦融从事的班彪携家属一同至洛。《后汉书·班固传》记载“(固)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又《后汉书·崔骃传》记载“(骃)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可知班固一度受业于太学。
2. 丁忧安陵
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班彪卒。班固返回扶风安陵,为父丁忧。其间,“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后汉书》卷40上《班彪传》,第1333页。。
3. 陷京兆狱
在安陵期间,“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后汉书》卷40上《班固传》,第1334页。。时间约在汉明帝永平五年(62)或稍前一段时间。
4. 重返洛阳
汉明帝永平五年(62),班固弟班超“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关于班固何时除兰台令史,可参见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92页。。此后班固常居兰台,观书、修史、论难、编书。直至汉章帝章和元年(87),班固因丁母忧再返故里扶风安陵*关于班固丁母忧返回扶风的时间,可参考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之分析。。次年十月,“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与参议”*《后汉书》卷40下《班固传》,第1385页。。
综上可见,班固一生大部分时间居于京都洛阳,次为扶风安陵故里。因此,洛阳与扶风也就成为了我们研究班固思想的空间背景。
(二) 学术发达的扶风安陵
班氏本为楚国贵族,“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秦之灭楚,迁晋、代之间”(今山西、河北一带),“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今山西雁门一带)。西汉成帝之初,班氏“徒昌陵。昌陵后罢,大臣名家皆占数于长安”*《汉书》卷100上《叙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4197-4198页。。王莽之世,班彪一代徙居扶风安陵,安陵也就成为班固的故邑所在。
扶风所在的三辅地区,一直是西汉的学术、政治中心,众多名士出入此间。至东汉之初,该地域学术实力依旧不衰。据卢云《汉晋文化地理》推测其时三辅士人在京师者就有六百人左右*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页。。这一时期、这一地域还有一位重要文化人物,即“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被“学者宗之”*《后汉书》卷36《贾逵传》,第1240页。的经学大师贾逵。
而作为班固本籍的扶风安陵是三辅地区文化最为发达的郡县之一。三辅地区以长陵、安陵、阳陵、武陵、平陵五县最为发达,“五县游丽辩论之士,街谈巷议,弹射臧否,剖析毫厘,擘肌分理”*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2《京都赋》李善注“五陵”,中华书局,1987年,第52页。。安陵县学术之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班固所在的班氏家族更是为故邑文化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西汉成帝时期,班氏就有班伯、班斿、班稚以学行驰名于世。班伯少受《诗》于师丹,后师从其时著名经学家郑宽中、张禹学习《尚书》《论语》。班斿博学有俊才,以对策为议郎,曾与刘向共同校书,成帝赏其才华,赐书于他;其子班嗣是当时著名学者。班稚少为黄门郎中常侍,性格“方直自守”。班彪是班稚之子,其从小好古敏求,“幼与从兄嗣共游学”。正如班固所总结两汉之际的班氏“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杨子云以下莫不造门”*分别见《汉书》卷100上《叙传》第4203、4205、4205页。。而班固留居故里之时,州郡之中更有“宿儒盛名,冠德州里”的故司空桓梁、“好古乐道、玄默自守”的京兆祭酒晋冯、“廉清修絜、行能纯备”的扶风掾李育等名士*《后汉书》卷40上《班固传》,第1331-1332页。,且与班固相熟、相善。
(三) 名士聚集的京都洛阳
班固幼时因父职而得以居于洛阳,三十岁因祸得福返回洛阳。此后至章和元年(87)复归故里丁母忧止,班固都生活在洛阳。
就在此间的几十年里,洛阳学术在光武、明、章三帝王的倡导下获得极大发展。先有光武“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的文化感召,四方名士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次有汉明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的躬身示范,以致“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再有汉章帝召集诸儒集于白虎观,论定《五经》异同,数月乃罢。
在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下,儒学昌盛一时,众多名士宿儒由四方汇聚京城,连“朝门、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经》。匈奴亦遣子入学”。就班固自身经历而言,早在少时,他便与傅毅、崔骃、李育、王充等同在太学*分别依据《后汉书·崔骃传》“(骃)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后汉书·儒林列传》“(育)知名太学,深为同郡班固所重”、《后汉书·班固传》李贤注“班固年十三,王充见之,抚其背谓班彪曰:‘此儿必记汉事。’”;置身兰台后,先“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又与贾逵、杨终、孔僖等经学大家相交*可参见梁宗华《班固师友交游考》中对班固与贾逵、杨终、孔僖交游的考论,《齐鲁文化研究》第12辑。。
综上,班固无论身在故里还是京城,都浸润于浓厚的儒学之风。特别是居于洛阳之时,他与上层关系密切,更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正统儒学带来的全面冲击。
二、 心境变迁:从囹圄到朝堂
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班固因父丧丁忧故里,开始致力于父亲班彪未竟的修史事业。建武中元二年(57),光武帝崩,明帝即位,其弟东平王刘苍以至亲身份拜骠骑将军辅政,并“开东阁,延英雄”。班固借此良机作《奏记东平王苍》,向刘苍推荐桓梁、晋冯、李育、郭基、王雍、殷肃六位“有殊行绝才,德隆当世”的名士。从奏记主要内容来看,这是身在故邑的班固向朝廷推荐贤达,而仔细体会,可发现,这又是班固的一封自荐书。在奏记开篇,班固自言“幸得生于清明之世”,因而“私以蝼蚁,窃观国政”,在文末更殷切希望刘苍“咨嗟下问,令尘埃之中,永无荆山、汨罗之恨”,表达了自己不愿归于尘土,欲发奋有为的士子情怀。然而,刘苍阅后,对班固推荐的名士“纳之”,却没有将班固一并延揽*《后汉书》卷40上《班固传》,第1330-1333页。。
欲有为政治而自荐不成的班固转而继续汉史编写工作。汉明帝永平五年(62),班固被人告发私改国史而收系于京兆狱。有关班固下狱时的心情,我们无法从现存文献中觅得。但观其先前“窃观国政”以为朝廷士的远大理想到突然沦为阶下囚的残酷现实的巨大反差,我们大约也可以想象班固此时的惊恐之状。此后,经班超陈其意、州郡上其书、明帝奇其才,班固非但没有罹祸,相反被朝廷召至兰台,自此开启长达二十余载的洛阳仕宦生涯。
入洛后,班固相继得到明帝、章帝赏识。他不仅奉明帝诏令参与编撰《世祖本纪》《列传》《载记》,还得以继续修撰西汉历史;章帝雅爱文章,班固更加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后汉书》卷40下《班固传》,第1373页。。
细观班固安陵自荐、京兆下狱、洛阳得意的行迹,再仔细体会其时心境后,就不难理解班固在《汉书》中“光扬大汉”的用心与努力了。这种用心与努力不仅是大时代儒风熏染、家学传承、自身学识的驱动,也来自班固独有的经历。作为一个博贯载籍、入仕无门,且一度身陷囹圄、有性命之忧的普通士子,在其因才华获得帝王肯定而逃出生天,并由此进入仕途且一路恩宠有加后,他的才华也就要得到最大程度地展现了——于史家班固而言,这种才华在《汉书》中得以充分发挥。前文已提及,班固修史,本因其父“所续前史未详”而欲补充完善之,也就是延续《史记》体例,将其未竟的汉武帝太初年间后的历史补充完毕。而后经过入狱、赦免、征召等一系列事件之后,班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史迁所记,乃以汉氏继百王之末,非其义也。大汉当可独立一史”*《初学记》卷21《史传第二》,中华书局,1962年,第503页。,将汉刘地位从“百王之末”提升到“独立一史”,或许正是班固有感知遇之恩而作出的一份最有力量的拥汉宣言。正如他在《典引》(序)中的心迹自陈,“臣固被学最旧,受恩最深,诚思毕力竭情”以“启发愤懑,光扬大汉,轶声前代”*《全后汉文》卷26《典引》,第256页。。
三、 成书洛阳:官修与私撰
《汉书》浓厚正统史观的形成,与其成于洛阳这一地域也是分不开的。作为政治中心、学术中心的洛阳对《汉书》的成书意义重大。
东汉政权是作为西汉政权的延续而存在的。所谓“光武中兴”之“中兴”,正是越过王莽新朝对西汉刘氏所作出的呼应。东汉定都洛阳后,“更以河南郡为尹,以三辅陵庙所在,不改其号”*《后汉书》志27《百官四》,第3614页。。东汉历代皇帝也多有“巡幸长安”之举。光武帝先后六次“幸长安”,明帝、章帝、安帝、顺帝、桓帝也至长安谒高庙。这些都意在说明两汉政权的延续性。
就《汉书》成书的东汉初期而言,经过了王莽代汉这样一段插曲,东汉初期的政府更需要采用各种举措来论证、宣扬汉室的正统地位。西汉后期,社会上流传“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汉书》卷75《李寻传》,第3192页。的预言,王莽也正是依据于此得到士人群体支持,从而顺利代汉。有鉴于此,东汉政府一直都重视史书的编撰,重视书籍中的舆论导向。从与班固同时代的同郡士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后汉书》卷40上《班固传》,第1334页。事件就可知当时政府对不同言论的警惕与控制。故当有人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朝廷即收捕其人、尽取其书,足可见上层对士人思想动向的重视。
其后班固被释的最主要原因是班超向明帝澄清“固所著述意”。关于班固的著述之意,史书有载:“以彪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究,欲就其业。”——仅作完善而已。而班彪著述之意,是有感于前人所续《史记》“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更有“褒美伪新”之作(如扬雄、刘歆的撰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史通通释》卷12《古今正史》,第338页。。因此,班彪著述的根本意图在于矫正视听,更是忠于汉室之举。因此,与其说,“显宗奇之”,感叹的是班固的才华,不如说,是班固父子对汉室的忠诚打动了明帝。
即使班固被明帝奇之,并召至洛阳为兰台令史,也并不是立刻开始了续写《汉书》的进程。班固先是参与编撰《世祖本纪》,后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在这些完成之后,明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即《汉书》。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将班固续西汉史之前先撰东汉史这一过程视为东汉政府对他的再一次考察。《汉书》也就此完成了私撰到官修的性质的转变。官修史书打上了国家意志的烙印,正统性得以大大提升。
四、 见贤思齐:王充与班固
班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结识的士人对他的正统意识的形成也有影响。前文已经提及的与班固有交集的洛阳名士,如同在太学的崔骃、傅毅,共撰史书的陈宗、尹敏等。在诸多名士中,王充与班固的关系值得探究一番。
王充,会稽上虞人。少游太学,师事班彪。学成后“归乡里,屏居教授”*③ 《后汉书》卷49《王充传》,第1629页。,著有被后世誉为“奇书”的《论衡》一书。该书以“疾虚妄”为宗旨,大力宣扬天之无为、谴告之缪和祥瑞之虚,似与当时政府所极力宣扬的正统儒学思想格格不入,与班固所秉持的正统思想就更是“道不同”了。而事实上,班固、王充彼此相熟。并且,二人有诸多相通之处:
两人年龄相仿:班固生于32年,卒于92年;王充生于27年,卒于97年。二人有共同的时代背景,也有足够漫长的时间来维系这自少年时代就开始的同学情谊。
两人同在洛阳:班固幼时因父至洛,时间大约在36年;王充于44年游学洛阳,投于班彪门下。两人又分别于54年、59年离开洛阳*有关王充离洛时间,可参看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第384页。。两人同在洛阳的时间从44年至54年,有十年之久。这十年时间,也正是二人学业有成、思想日趋成熟的重要时期。
两人学术背景相同:班固“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受学于班彪;王充则直接师承班彪。
两人治学态度相似:班固“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不为章句”;王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③。
两人至少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会稽谢夷吾。明帝永平十八年(75),班固作《为第五伦荐谢夷吾疏》,代第五伦向朝廷推荐谢夷吾,赞其“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全后汉文》卷25《为第五伦荐谢夷吾疏》,第244页。;而谢夷吾不仅与王充同在一郡,两人更是好友。谢夷吾曾上书力荐王充,称“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全后汉文》卷29《上书荐王充》,第296页。。
此外,王充“为人清重,游必择友,不好苟交”*黄晖撰、刘盼遂集解:《论衡校释》卷30《自纪篇》,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90页。,却对班固赞赏有加,曾预言班固“必记汉事”*⑩ 《后汉书》卷40上《班固传》,第1330页。,日后也多次赞美班固“名香文美”*《论衡校释》卷13《别通》,第602页。,“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论衡校释》卷13《超奇》,第615页。,有大国气象。同时,班固“性宽和容众”⑩。因此,两人成为密友可能性极大。
那么,如何解释《论衡》《汉书》不同的思想呢?后世多因王充在《问孔》《刺孟》《异虚》《自然》《乱龙》等篇中质疑圣人、批判灾异谴告的言论而将其放置在与同一时期官方意识形态对立面。而事实上,细观《论衡》,可发现王充对刘氏政权多有溢美之辞。特别在《宣汉》篇中表示要“高汉于周,拟汉过周”,而作《恢国》目的竟是“论汉国在百代之上”,甚至于前文说“凤凰麟龙皆谓不足为世瑞”,而后文“扬厉汉家之功德则又备著其佳祥”*王洲明:《中华大典文学典·先秦两汉文学分典·汉文学部》,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87页。。可见,王充并非对东汉政权不满,更不是质疑其政权的合法性。相反,他认为“前汉已灭,光武中兴,复致太平”*《论衡校释》卷19《宣汉篇》,第818页。。由此可见,王充也是拥护刘氏政权的“正统”士人。这一点,也可从王充晚年被谢夷吾推荐于朝廷,而“肃宗特诏公车征”的礼遇可知:汉室未曾将王充视为异类,而王充也从来就不是汉室的反对者。
综上所言,作为班固密友的王充非但没有影响班固的判断,反之,两人在“颂扬汉德”的深层思想与具体文章层面都达成了根本性的一致。
五、 田野派与学院派:司马迁与班固
班固《汉书》是西汉一代历史,起自汉高祖元年(前206),终于王莽地皇四年(23)。司马迁《史记》是通史,其中西汉部分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两部史著从汉高祖到汉武帝时代重合。《汉书》对这一时段的撰写,大部分借鉴了《史记》,但同样由于正统史观的影响,即使是同一时间、同一人物、同一事件,仍然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与倾向。比如,对屈原的态度,对游侠的态度,包括高祖刘邦的出生的情景描述等。有关司马迁与班固著史的同异之处及其原因,学界已有很多成果论及。这里仅从二人的游历来看两部史著的成书及其中的差别。
首先,两人自身游历不同。
司马迁少时耕于河山之阳,及长,游学于长安,先后师从大儒伏生、孔安国、董仲舒。弱冠之年,司马迁开始漫游全国,先后“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63年,第3293页。。同时,在对自然山水的考察中,司马迁对富含文化气息的历史人文地理也给予了极大关注,比如,“秦汉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公胸中固有一天下之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及也”*顾炎武:《日知录》卷26《史记通鉴兵事》,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31页。。在游历中,司马迁又结识了不少士人,由此得以耳闻目见诸多史实,而非尽取自于书。
进入仕途后的司马迁依然游历不止。其间,除去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293页。之外,又多跟随汉武帝巡行郡县、东巡封禅、祭祀五帝,曾“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史记》卷1《五帝本纪》,第46页。。从元狩五年司马迁出仕为郎中起,到征和四年汉武帝最后一次封禅泰山止,司马迁更随武帝36年,巡游26次。
相对司马迁一生丰富的地域流动,班固的学习于太学,仕宦于兰台及幕府的经历就稍显单薄。特别是当其处于兰台期间,一方面,兰台所秘藏的皇帝诏令、臣僚章奏、国家重要律令、地图、郡县计簿与各种书籍为班固撰写西汉史实提供了最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但同时,也将班固禁锢于文献之中,以致对文本之外的各地域的山川风物、百姓民生等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接触较少。这种地域流动的差别会导致二人的视野有差、心态有别。司马迁更有历史纵深感,也更有全局眼光,特别是他还身处国力强盛、意气风发的汉武时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理想是这样大的时代背景下,个体士人通过广泛游历而开阔眼界、增益见闻的产物。
其次,两人对“游”的态度也有差别。
可以《史记·游侠列传》和《汉书·游侠传》作对比。在司马迁陛下,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史记》卷124《游侠列传》,第3181页。。更甚者,司马迁游历时还曾与燕赵豪俊交游,因此宋代苏辙评之以“其文疏荡,颇有奇气”*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卷22《上枢密韩太尉书》,中华书局,1990年,第381页。。相反,班固对游侠则持否定态度。班固所谓的游侠中包括“学经传”、“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的楼护,包括“略涉传记,赡于文辞,性善书”的陈尊。可见班固所谓的游侠有的具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与我们今天说到的东汉流动之士并无本质不同。班固认为游侠促成了“背公死党之义成,守职奉法之义废”的不良习气,同时,更是对等级制度的冲击,“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其上,而下无觊觎”。而类于游侠郭解等人,“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僭越之举,“罪已不容于诛矣”*分别见《汉书》卷92《游侠传》,第3706、3711、3697、3697、3699页。。
司马迁之宽容、班固之批判,两者态度的不同,还是要回到开始说的第一点,即与二者的自身游历有关。司马迁有丰富的游历经验,且是主动出行,结交名士、感受风俗,他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普通民众,也因此对很多正统史家所不能理解之事怀有深沉的“理解之同情”。而班固自十余岁游学洛阳,后又入兰台、校书籍、参加白虎观会议,倾听各位大儒讲解五经异同,奉命撰写《白虎通德论》,亲身参与儒学谶纬化的改造——接收到的都是正统的儒学思想。观两位行迹所至,可以说,司马迁走的是一条田野派的路线,而班固则是正统的学院派士人。
结 语
正统史观经由班固系统、具体地呈现于《汉书》这部史学名著之后,遂成为后世撰修史书的重要法则,《汉书》也被后世史学奉为“不祧之宗”*章学诚:《文史通义》卷1《内篇一·书教下》,上海书店,1988年,第14页。。而这一正统史观的形成又与作者所处时代有关,与作者在这一时代中的地域流转、心境变迁有关。就班固而言,其一生所至之地域,儒学大行其道,儒者环于四周,原本承袭其父志,后又得遇于明帝,因此,其正统史观之形成,既是国家意志之体现,却更是作者个体地域流转、情感浮沉、思想也随之渐趋成型的必然产物。
(作者单位: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