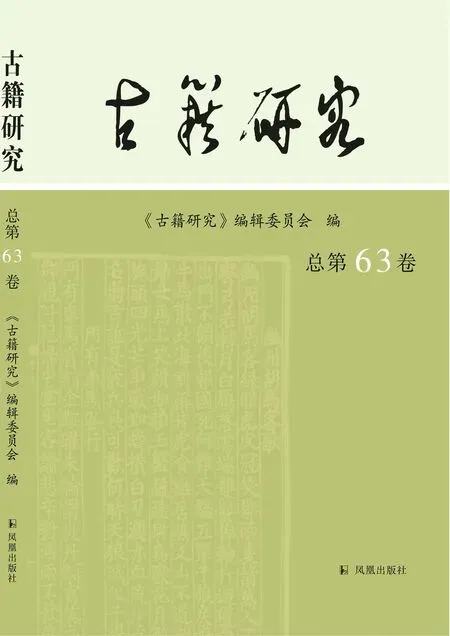杜诗辨疑三则
陈道贵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
杜诗辨疑三则
陈道贵
一、 《题忠州龙兴寺所居院壁》之“独园”
此诗乃杜甫寓居忠州龙兴寺时所作,其末二句云:“淹泊仍愁虎,深居赖独园。”对其“独园”一词,历来注杜者几无异辞,认为是援引佛教典实。赵次公谓:“独园,指言龙兴寺。给孤独长者有园,佛尝居之,故佛寺谓之给孤园,又谓之独园。”*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81页。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高崇兰《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仇兆鳌《杜诗详注》等,均以给孤独园注此“独园”。曹慕樊先生则认为,以佛教典实解“独园”不确,佛典中的“给孤独园”,可称“给孤园”“给园”“孤独园”,但不能省为“独园”。据此,曹先生自立新说,解“独园”为孤立无依之园*曹慕樊:《杜诗杂说全编》,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14页。。按,曹先生此说有未周之处,难以信从。佛教中所谓祇树给孤独园,又称祇园精舍,乃印度佛教早期著名寺院。中国历代文人在言及佛教寺院时,往往用以作为寺院代称。在具体援用时,常有简化之现象。而简化时,又非限于某种特定形式。其中既有如曹先生所指出的“给园”“给孤园”“孤独园”等,也有如杜甫此诗中所用的“独园”。“独园”用指寺院之例颇多,兹举若干,以解曹先生之疑。颜真卿等《月夜啜茶联句》诗:“醒酒宜华席,留僧想独园。”*(清)彭定球等:《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37页。孙狄《酬万八贺九云门寺归溪中作》诗:“独园余兴在,孤棹宿心违。”*(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1217页。以上二例,均以“独园”指佛家寺院。如果仍有疑问,那么下面两例则更有说服力。于邵《阿弥陀石像赞》:“独园对境,双树齐阴。”*《文苑英华》,第4125页。释良秀《奉敕造波罗蜜经疏进上表》:“至道同源,圣人一贯。大雄示相,演妙音于独园;宝位分身,霈湛恩于双阙。”*(清)董诰等:《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234页。这两处“独园”无疑是给孤独园之省称。
又,曹先生述及此诗时,将诗题写作《题忠州龙兴寺壁》,而杜诗传世诸本如《九家集注杜诗》《集千家注杜诗》《钱注杜诗》《杜诗详注》等均作《题忠州龙兴寺所居院壁》(《瀛奎律髓》录此诗题作《题忠州龙兴寺壁》)。也许曹先生没有注意到“所居院”三字,故而导致将“独园”视为与龙兴寺无关的所谓孤立无依之园。换言之,如果曹先生注意到题目中“龙兴寺所居之院”的“院”字,恐怕不会将诗人所赖之“院”理解为孤立无依之“园”了。也就是说,即使此“独园”是孤立无依之园,那也应该是依题作“独院”。
二、 《西阁夜》之“盗贼尔犹存”
此诗有“时危关百虑,盗贼尔犹存”句,一般解“盗贼尔犹存”为指盗贼而言。顾宸曰:“‘盗贼’,言崔旰之乱。”边连宝谓:“‘盗贼尔犹存’,诗恨极语,愤极语。”*两条皆转引自张忠刚:《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3880页。《杜诗阐》释为:“嗟尔盗贼,至今尚存耶!”*(清)卢元昌:《杜诗阐》,卷二十五,台北:大通书局,1974年。黄生则解为:“击柝之声何处?无衣之子可怜!百虑遂尔关心,盗贼尚满天地,故若呼而怪之。非怪盗贼也,怪其以盗贼遗君父者也。”*(清)黄生:《杜诗说》,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165页。此类解说均为有据合理。曹慕樊先生则主张应将这两句和前面的“击柝可怜子,无衣何处村”联系起来,解为:“不晓得哪里的村子里还有衣裳单薄的可怜人在打更呢!接着说,在危急的年代,人们为自己的打算多极了,不料在盗贼纵横的时候你(更夫)竟仍然还在啊!”*《杜诗杂说全编》,第252页。
曹先生之所以如此解说,可能是出于两个原因。其一,杜诗中有“盗贼敢忘忧”之类的句子。其中“敢忘忧”与“盗贼”的关系有些特别,不是说盗贼不敢忘忧,而是说因为有盗贼存在,所以(我,诗人)不敢忘忧。也许是受了这类诗句的引导,曹先生把“盗贼尔何存”理解为有盗贼,你(击柝子)却还在打更。实际上,“盗贼敢忘忧”与“盗贼尔何存”是不一样的。“盗贼敢忘忧”是说因为有盗贼存在,自己怎么能将忧患放在一边呢?如果以此为参照,如曹先生所言,那么“盗贼尔犹存”就应该解为:有盗贼存在,你竟然存在(或:你为什么存在)?更夫的存在,似乎不当与盗贼存在构成矛盾;相反,正因为天下未宁,乡村更夫执夜才更加重要。
“盗贼尔犹存”是一种“呼告句”式诗句,即黄生《杜诗说》所谓“盗贼尚满天地,故若呼而怪之”。徐仁甫先生所见与黄生略同,认为“盗贼尔犹存”应读为“盗贼,尔犹存!”是“呼告句”,并例举谢道韫《登山》“气象尔何物”、韩愈《奉和仆射裴相公感恩言志》“自然无不可,范蠡尔其谁”为证*徐仁甫:《杜诗注解商榷·杜诗注解商榷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83页。。徐先生的解说,使得历来公认的解读更具说服力。笔者在此再补一例。《六度集经》中的《镜面王经》,其中有“盲人摸象”的故事。当众盲人各依所摸部分判断大象为何物,争论不休之际,“镜面王大笑之曰:‘瞽乎!瞽乎!尔犹不见佛经者矣。’”*《六度集经》卷八,《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册,第51页。此例或更可见“呼告”之意。
其二,对“时危关百虑”句意的不同理解。“时危关百虑”,以诗意脉络而言,应该是诗人在前面诗句所描述的情景之下而引发的主观情思,即在这动荡不安的时局中,自己心系天下,百虑关心。而这正是由于“盗贼”所起,故结句以“呼告”语出之。曹先生另有所见,以为此“关百虑”者非诗人自己,而是“人们”,且此“虑”是“为自己打算”。这样的解读,似乎太为曲折,也过于主观,因为“虑”怎么就一定是“为自己打算”呢?再者,曹先生将“无衣何处村”与“击柝者谁子”并观,认为其应当解为“不晓得哪里的村子里还有衣裳单薄的可怜人在打更呢!”如此解会值得商榷。就诗意脉络而言,这两句应该说的是两件事,一为“击柝子”,一为“无衣村”,均为诗人“百虑”关心的表现。如果将其视为一事,像曹先生那样串讲,主观添加的成分太牵强;“无衣”变成“衣裳单薄”,似乎太勉强了。
又,将“尔”解作“击柝子”,曹先生似非第一人。黄生《杜诗说》引洪舫之言:“陋士竟以‘尔’目此子。”*《杜诗说》,第165页。可见在清初或之前,已经有人将此诗之“尔”视为“子”了,只是由于不可信而影响几绝。
三、 《别董颋》之“小长安”
《别董颋》诗“南适小长安”之“小长安”,注者多持邓州小长安聚说。如《九家集注杜诗》《集千家注杜诗》《杜工部草堂诗笺》《补注杜诗》《钱注杜诗》《杜诗详注》等。邓绍基先生则认为此诗之“小长安”指的是江陵*邓绍基:《读杜随笔》,《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4期,第25页。。《杜甫全集校注》据陶敏先生说,认为旧说全误,定“小长安”为指桂州*萧涤非等:《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5656页。。按,《别董颋》之“小长安”何指,确为值得探讨之问题。但笔者以为,解“小长安”为桂州,只可作一说,不宜视为定论。
先看“桂州说”之立论依据是否无懈可击。郭曾炘《读杜劄记》已指出《别董颋》诗“小长安”或指桂州,其立说是由“南适小长安”之“南”所示之地理方位问题引发,其提出“小长安”或指桂州的依据是李商隐《即日》诗自注与张叔卿《流桂州》“胡尘不到处,即是小长安”诗句(张氏此诗,钱谦益已经注意到了,《钱注杜诗》在《别董颋》一诗后录张诗“胡尘不到处,即诗小长安”句)。但是,郭曾炘却不愿贸然下断语,而是审慎地说:“此则桂林亦称小长安,正在荆湘之南,或董是赴桂州,但此外亦无确证耳。”*郭曾炘:《读杜劄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28页。一则谓“或”,一则谓“无确证”,只是存疑而已。陶敏先生立说之据未出郭氏所及,并没有提出新的证据。丘良任先生也依据《读杜劄记》,定“小长安”为桂州*丘良任:《杜诗考索》,《暨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3期,第108页。。笔者以为《读杜劄记》的存疑态度是可取的,因为其立说的两个依据都不是十分可靠的。李商隐《即日》诗自注“宋考功有‘小长安’之句”,并不见于宋之问传世之作,而且这“小长安”之句出现在什么样的语境也不清楚,恐怕不能因此而直接得出宋之问说过桂州有小长安之称这样的结论。至于《即日》诗“自注”的可信性,也有学者提出疑问。叶葱奇曾谓这个所谓自注“显然也是宋人的批注,决不是作者的手笔”*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467页。。张叔卿《流桂州》诗“胡尘不到处,即是小长安”,更可能是比喻的用法,即没有受到“胡尘”之扰的地方,就可以称为小长安。邓绍基先生即持此观点,认为“张叔卿诗中‘小长安’云云,当是自嘲自慰之词,在通常意义上,‘小长安’是喻平安乐土”*《读杜随笔》,第25页。。由此可见,支持“桂州说”的材料,既是孤证,又存歧义,怎么能说就是定论呢?
再者,如持“桂州说”,则《别董颋》诗存在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一是其诗云:“士子甘脂阙,不知道里寒。有求彼乐土,南适小长安。”由此四句可知,董颋去的是所谓“乐土”,而此“乐土”就是“小长安”,且往“小长安”所经过之地(“道里”)的气候寒冷。如果“小长安”指桂州,杜甫怎么会因为路途寒冷而替董颋担忧呢?桂州属五岭以南的“炎方”。唐时桂州冬天的气温在炎方相对属于比较低的。戎昱《桂州口号》云:“谁道桂林风景暖,到来重著皂貂裘。”不过李商隐却觉得桂州冬天并不十分寒冷,其《即日》诗云:“桂林闻旧说,曾不异炎方。山响匡床语,花飘度腊香。”杜甫《别董颋》诗作于大历三年冬由公安赴岳州途中*杜甫与董颋分手之地,历来有歧见。本文据张忠纲先生《杜甫年谱简编》,《杜甫全集校注》,第6570页。。由这里南适桂州,道里所经之地,其气候应该是趋于温暖的。由此,诗人再三为董颋衣裳单而生发的关切之情似有多余之嫌。二是诗末“汉阳颇宁静,岘首试考槃”难以理解。如解为南适桂州,杜甫怎么又在诗末写出这两句呢?“汉阳”、“岘首”和桂州以及他们分手之地均无关联,不免给人“游离”之感。
如果按传统说法,诗中的“小长安”为邓州附近的小长安,上述两个问题却可以得到较好的解释。“道里寒”指的是由他们分手之地北上所经之地的气候。“汉阳”“岘首”为北上所经之地,而“岘首在襄州,与邓州相近。公因董君之往邓,故思及之”*《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第1455-1456页。。
不过,解“小长安”为邓州小长安,确有一问题不能无视,即往邓州方向怎么能说是“南适”呢?这的确是持邓州小长安说者难以回避的问题。令人不解的是,诸家在解“小长安”为邓州小长安时,却多无视“南适”问题。只有浦起龙说“南适恐误,邓州在江陵西北也”*(清)浦起龙:《读杜心解》,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94页。。而持“小长安”指江陵的邓绍基先生则认为,此“南适”非指离别时董颋去往的方向,而是追述董颋因生活所迫由秦地“南适”*《读杜随笔》,第25、26页。。浦起龙疑“南适”可能是文字的错误,只能说是主观推测,难以服人。邓绍基先生的解释倒是有些道理(只是我们不同意“小长安”指江陵)。如果按邓绍基先生的思路,我们似乎可以说“南适小长安”乃董颋由秦地南下邓州小长安,后又到公安、岳州之间某地,在此与杜甫相遇。作此诗时,董北上而杜甫南下。因为董北上,故杜甫忧其“道里寒”;也因为董北上将经“汉阳”“岘首”,故诗末歌咏及之,聊发心向隐逸的情怀。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