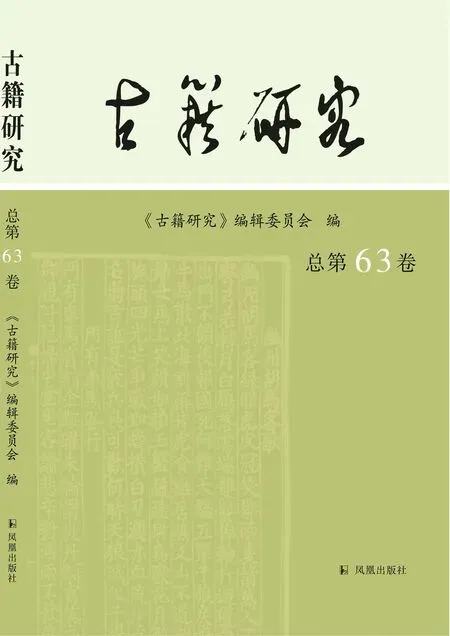广东省域清诗总集的开山之作
——屈大均《广东文选》成书背景论略*
陈凯玲
(作者单位:广东惠州学院中文系)
■文献学评论
广东省域清诗总集的开山之作
——屈大均《广东文选》成书背景论略*
陈凯玲
一提到清代的广东诗人,人们首先会想起“岭南三大家”,“三大家”中又以屈大均的创作成就最为突出。如果提到广东清诗总集的编者,屈大均依然无愧为“大家”。他一生著述宏富,不仅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和学术专著,还编纂了一系列情系桑梓的文献,尤其热心于广东地区历代诗文的整理和编刊。其中,刻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的《广东文选》,为目前存世的清代最早一部广东省域诗文总集*“广东省域清诗总集”范畴的界定,主要依据三个标准:一则该总集所收作者,必须籍属清代的广东省(大致以清代广东省辖境为准,包括广东道和海北道、海南道,即今天的广东、海南两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部分地区);二则该总集选诗范围,必须立足全省,而并非限于省级之下的府、县、乡镇等局部地区;三则只针对选集一类,凡以其他形式编纂之总集(如丛书、合刻等),均不在讨论范围之内。,荟萃了从两汉至清初二千多年内广东(包括个别寓贤)代表性作家二百余人的文学作品,其文献价值已得到学界充分肯定*骆伟:《论岭南文献》,《高校文献信息学刊》,1995年第4期,第6-11页;汪松涛:《屈大均与广东地方文献》,《岭南文史》,1997第4期,第4-8页。《广东文选》已有点校本问世,参陈广恩《点校说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上册,第1-7页。。
《广东文选》全书四十卷,虽然规模称不上宏大,却是屈大均毕生丰富著述经验的结晶。一方面,该书借鉴前人的成果和经验,在明人张邦翼所辑《岭南文献》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取舍,以更为鲜明的文学色彩,超越了前人的同类总集;另一方面,屈大均本人也是多种总集的编者,曾有《广东文集》《岭南诗选》等相关总集的编纂计划与活动,无疑为后来《广东文选》的顺利成书奠定了基础。本文即就《广东文选》的成书背景略作考察,对该书与几部相关著作的关系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以发掘其背后颇为曲折的编纂历程。
一、 《广东文选》与《岭南文献》
总集的编纂,是一定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广东地区从汉代赵佗建立南越国始,经历长期的开化与文明的过程,逐渐形成丰富的人文资源,诚如屈大均所言:“广东自汉至明千有余年,名卿巨公之辈出,醇儒逸士之蝉连,操觚染翰,多有存书。”*(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年,第318页。特别是在明代嘉靖以后,商业经济的迅猛发展更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兴旺和印刷技术的进步,粤人开始大量著书,不仅别集纷纭众多,总集的编纂也开始受到重视。据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九十八《艺文略·十》集部之四总集类著录,明人所编各种广东地方性总集即达三十余种之多;而其中最早的省域诗文总集,则为万历年间张邦翼所辑《岭南文献》*(清)阮元等:《(道光)广东通志》,《续修四库全书》第673册,第334页。。
张邦翼,湖北蕲州(今蕲春)人,万历年间曾官广东提学副使。其《岭南文献》自序称有感于广东人文蔚盛,“所为论撰,率真醇尔雅”,而遗著散佚,甚至“片语不遗,姓名俱逸”,因此以整理岭南历代文献为己任,“乘校士余闲,征书十郡”*(清)张邦翼:《岭南文献》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万历刻本,补编第21册,第2页。。自万历四十三年(1615)“乙卯之冬”,至四十四年(1616)“丙辰之春”,成书凡三十二卷。全书按体裁分类编次,计散文二十五卷,包括诏诰、敕批、奏对、笺疏等二十余种文体;诗歌七卷,包括四言至七言诗、词、歌谣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三集部总集类存目之三,称入选此书者“起唐张九龄,迄于明之万历,凡二百六十余人”*(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下册,第2704页。;但据原书卷首作者“姓氏”统计,实际收录共有三百一十九人。其中以明人为主,尤以嘉靖朝文人居多,占总人数近三分之一,而唐、宋、元三代合计只有十四人。《四库全书总目》说该书“于岭南诸集搜辑颇广,然明人著作,百分之中,几居其九焉,盖时弥近而所收弥滥,亦明季标榜之习气也”*《四库全书总目》,第2704页。,实则这也是广东地区文化日益发达的一个结果。
《岭南文献》虽然“文”与“献”并称,但实际更侧重于“献”亦即今天所说的文献。即如入选作家,据凡例第六款所说,便是“重流品,次文章”。虽然它也提到“禄位之崇卑,行踪之显逸,无论也”*《岭南文献》卷首《凡例题评》第六款,第5页。,但考其作者“姓氏”,其中入仕者凡二百六十八人,上起丞相、尚书,下至进士、举人,均按官品、科名由大到小、由高至低排序;而“青衿才士,遗逸布衣”,则“附收篇末”*《岭南文献》卷首《姓氏》附“论”,第15页。,总共不过四十七人,形同点缀而已。再如“文章”,也明显存在重思想而轻文采、重文献而轻文学的倾向,如其自序所说:
惟是以理为鹄,以品为权。谈学术,必其醇而粹者亟收之,不则漱芳润,猎菁华,其为金玉渊海,弗顾也;谭经济,必其典而确者亟收之,不则悬画饼,饰象龙,其为黼黻河汉,弗顾也。*《岭南文献》卷首,第3页。
具体则如“奏对、笺疏、札议”,“即文不简古,然忠肝赤胆,可照汗青,故博采之”*《岭南文献》卷首,第4页。。可见,张邦翼编纂《岭南文献》,的确更看重“学术”、“经济”之类的文献价值。
张邦翼之后,福建晋江杨瞿崃续纂《岭南文献轨范补遗》六卷,后世也称为《岭南文献续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三集部总集类存目之三,称该书“必其事与理关切者,纂而补之”,“中间又自分理类、事类等目”*《四库全书总目》,第2705页。,可见其于“文章”强调“事”“理”,注重文献,比《岭南文献》更进一步。并且,该书还只收散文,不选诗歌,这从对待文学的态度来看,显然比《岭南文献》还要不如。
《岭南文献》及《岭南文献续集》,作为广东地区较早的省域诗文总集,其开创之功自然不可磨灭。只是从文学的角度考察,它们的局限也是相当明显的。
屈大均《广东文选》,在资料方面多有取资于《岭南文献》及《岭南文献续集》,如其《凡例》第一款所说“合二书为一”*(清)屈大均:《广东文选》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36册,第128页。。以诗人为例,此集共收录一百三十八人,其中七十八人即已见于《岭南文献》,占全书诗人总数近百分之六十。这种情况又相对集中在唐、宋、元和明初,距离屈大均年代较远,很可能是因为“文献不足征”而造成了不谋而合。
但是,《广东文选》对《岭南文献》及《岭南文献续集》,事实上还是做了大量的增补工作。以时代范围而论,《岭南文献》《岭南文献续集》两书“皆起自唐开元年,至明万历年而止”;而《广东文选》所收作者,“起自汉文帝时,至明崇祯时而止”*《广东文选》卷首,第128页。,并实际延续到清顺治、康熙年间(关于《广东文选》所收作者时代下限的问题,笔者另有专文探讨,此处不赘)。可见,此集所收作者时代范围,上限和下限都有所延伸,而尤以明末清初为突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广东文选》在选择作品的标准上不为前人所囿,而以文学家的眼光“选文定篇”,特别注重作品的文学审美价值。其《凡例》第一款曾说:
吾粤旧有《岭南文献》一书,乃督学蕲阳张公凤[邦]翼所撰。又有《岭南文献续集》一书,乃督学晋江杨公瞿崃所撰。……今合二书为一,删者五之,增者五之;删其不文,增其文。……而是书主于“文”,不主于“献”也。*《广东文选》卷首,第128页。
所谓“主于‘文’,不主于‘献’”,正是《广东文选》最大的特色。这里的“文”,即指文学。其具体表现,则大致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增加诗词在各类文体中的比重。《广东文选》和《岭南文献》《岭南文献续集》三书,内部均按文体分类编次,但是,《岭南文献续集》“有文无诗”*《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三集部总集类存目之三,第1758页。;《岭南文献》总共三十二卷内,诗词之类只有七卷,占全书百分之二十二弱;而《广东文选》总共四十卷,其中诗词有十五卷,接近全书百分之三十八。尽管散文中也未必没有文学色彩相当浓厚的作品,但诗词之类,显然更具有文学的气息。二是强调作品本身的文学审美价值,以文存人,而不以人存文。如其《凡例》第三款明确说:“予所选止于文,盖以文而存其人,不以人而存其文。故其文未能尽善者,虽大贤,弗敢多录。”*《广东文选》卷首,第128页。这与前述《岭南文献》“重流品,次文章”,以人存文的做法,可谓截然相反。具体如明弘治年间儒学大师湛若水,《岭南文献》同时选其诗文,其中诗歌多至十八首;屈大均虽然也推尊他为“圣人之徒”,以之与陈献章、王守仁相提并论,“倡明洙泗之学,以开聋聩”*《广东新语》卷十“甘泉之学”条、“事师”条,第308、312页。,但《广东文选》却只选录他的散文,于诗歌则一首都不录。这显然是屈大均以一个诗人的眼光,认为湛若水的诗歌水平不够,所以如此对待。三是注重文学创作的独创性,推尊“真作者”。如其《凡例》第五款曾说:“为文当以唐、宋大家为归;若何、李、王、李之流,伪为秦汉,斯乃文章优孟,非真作者。”*《广东文选》卷首,第129页。这就是批评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模拟风气,主张文学创作要有作家自己的风格,抒写个人的真实感情。这样写出来的作品,自然更具有文学的审美价值。
因此,《广东文选》相对于《岭南文献》及《岭南文献续集》来说,最主要的也就是突出总集的文学性,而相应淡化它的文献色彩。这实际上就是远绍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文学独立意识,与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连成一气。作为广东地区的省域文学总集,《广东文选》的出现,真正将总集编纂引向了文学的角度。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文选》堪称广东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
二、 《广东文选》与《广东文集》
在《广东文选》问世之前,屈大均本人也曾编纂过一部《广东文集》。该书现今只有残本流传,但其《广东新语》卷十一《文语》第一则“广东文集”,还完整保存着该书的自序,其中提到:
嗟夫!广东虽一国乎,求文于人,人或不足于文;求人于文,文则有余于人矣。博取而约之,撰为一书,名之曰《广东文集》。使天下人得见岭海之盛于其文,文存而其人因以存,以与《广东通志》相表里,岂非一国人文之大观乎哉?*《广东新语》,第316-317页。
据今人汪宗衍先生考证,《广东文集》最初于康熙二十五年丙寅(1686)由广州知府刘茂溶出资刊刻,“然草创是书,当在早年”*汪宗衍:《屈大均年谱》,屈大均《屈大均全集》附录之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8册,第1962页。。从《广东新语》已经收录该序这一点来看,屈大均着手编纂《广东文集》,再迟应该不迟于《广东新语》完稿,亦即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顷*《屈大均年谱》,第1932页。。有关该集的编纂情况,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
1. 关于命名
屈大均对《广东文集》的命名,经过一番详密的推敲与论证,可谓别具匠心。其自序曾针对《岭南文献》一书,说:
先是时,吾粤有《岭南文献》一书,吾尝病其“文”不足,“献”亦因之。盖因“文”而求其“献”耳,非因“献”而求其“文”也。斯乃《[昭明]文选》之体乎,以言乎“文献”,则非矣。且“岭南”之称亦未当:考唐分天下为十道,其曰“岭南道”者,合广东西、漳浦及安南国境而言也。宋则分广东曰“广南东路”,广西曰“广南西路”矣。今而徒曰“岭南”,则未知其为东乎,为西乎?……是皆非今日四封之所至,与本朝命名之实,其亦何以为征?凡为书必明乎书法,生乎唐则书“岭南”,生乎宋则书“广南东路”,生乎昭代则必书曰“广东”,此著述之体也。以尊祖宗之制,以正一代之名,而合乎国史,其道端在乎是。*《广东新语》,第317页。
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从所编内容来说,屈大均有鉴于《岭南文献》“其‘文’不足”,所以有意把《广东文集》称作“文集”,借以突出“《[昭明]文选》之体”。二是从行政地名来说,屈大均认为用“岭南”不符合“本朝命名之实”,所以特地将它改作“广东”,借以遵循“著述之体”,以求“名副其实”,“名正言顺”。并且在《广东文集》之外,他的《广东新语》《广东丛书》也同样都以“广东”命名*《广东丛书》拟收《广东文集》“外诸家著书非文体者”,见《广东新语》卷一一,第319页。。而《广东文选》一书,既称“广东”,又称“文选”,这显然正是《广东文集》书名的一个翻版。
2. 关于时代范围
《广东文集》所涵盖的作者时代范围,也比《岭南文献》更广。其自序接下去曾说:
吾尝谓广东……文,其以汉之陈元为始乎。其《请立左氏》一疏,大有功圣经。次则杨孚,有《请均行三年通丧》一疏;即其《南裔异物志》,辞旨古奥,散见他书,搜辑之亦可以为广东文之权舆。今徒以曲江冠简端,抑疏矣。*《广东新语》卷一一,第318页。
这是说的上限。通过追溯广东文学创作的源头,屈大均把东汉陈元定为广东本土最早的文学家,打破了长期以来以唐代张九龄(曲江其号)为“文宗”的惯论,从而将广东的文学发展史推前了六百年之久。至于其下限,则屈大均在《广东文选·凡例》第二款中提到:“予所编纂《广东文集》,自汉至今。”*《广东文选》卷首,第128页。也就是一直到清朝康熙间。唯现存《广东文集》存目(详后),其中所收时代最晚的作家为顺治三年丙戌(1646)在江西抗清殉节的黎遂球。至于《广东文选》的时代范围(参前),则又与《广东文集》不尽相同。
3. 关于体例规模
《广东文集》规模宏大,远远超过《岭南文献》及其《续集》,其体例编排也较一般总集复杂。据其自序说:
以张天如所撰《汉魏百名家》为例,可乎。其例也,人各一集,集分诸体。体不必兼,即一体亦成一集。不成一集,则以其可附者附之。……书成,总计三百余卷。集皆有原序、新序或书后。集末则以本传、行状、墓志附焉,俾其人生平本末尽见,易以考求。统名曰《广东文集》,分名则曰某人集。*《广东新语》卷一一,第318-319页。
可见,全书是以个人专集的形式,分集编刊,各专集内部再按体裁分类编次。现今唯一为南京图书馆收藏的康熙刻本《广东文集》残卷,所存即《陈议郎集》《杨太守集》《刘御史集》《谭处士集》《杨文懿集》《林光禄集》《黎太仆集》七家专集,凡十六卷*骆伟:《广东文献综录》,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41页。。而据《广东文选》自序所述,“予先有《广东文集》之役”,计收“大家数十,名家百余,凡为二百余集”*《广东文选》卷首,第128页。,其原书确乎规模惊人。只是就其性质而言,《广东文集》显然属于典型的“丛书”,与《广东文选》以及《岭南文献》正、续集之类一般意义上的总集不同。
4. 关于选录标准
《广东文集》号称“一国人文之大观”,但在选录作家的作品时仍然不无选择,具体来说也就是排除与文学无关的“非文”之体,如其自序所说:
其集外诸家著书,非文体者,约有百余种。若丘文庄之《大学衍义补》,湛文简之《格物通》《周易测》《二礼经传测》《非老》《非杨》,黄宗大之《皇极经世传》,黄文裕之《乐典》,王光禄之《正学观水记》诸书,虽为体博大,为理精微,可以羽翼圣经贤传,概不编入。*《广东新语》卷一一,第319页。
这里所列举的“非文体者”,都是与经史相关的学术著作,严格来说并不属于文学的范畴。可见,《广东文集》虽然自称“宁宽毋严”,博取诸家作品,但事实上却还是以“文学”作为一个基本的选择标准。这与前述该书命名为“文集”,可谓正相一致;换一个角度说,这也正是“文集”之“文”在全书编纂中的具体体现。而《广东文选》,显然也是基于这样的标准。
《广东文集》由于规模太大,在屈大均生前没有能力全部刊刻。但它对屈大均编纂《广东文选》,却刚好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广东文选·凡例》第二款在叙及《广东文集》时曾说:“但是书浩繁,未能尽刻,姑于诸集中拔其十之二三,以见大概。不能连篇累牍,为先哲多所表章,予之所不得已也。”*《广东文选》卷首,第128页。这里一方面说明了《广东文集》的刊刻困难,另一方面也交代了“拔其十之二三”,精编成《广东文选》的过程。这对于《广东文选》的诞生来说,显然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屈大均案头的这部《广东文集》,它本身就是一个现成的资料库,足以使编纂《广东文选》省去许多工序,占尽厚积薄发之利,因而其成书自然更容易。
从《广东文集》精编为《广东文选》,还有助于提高《广东文选》的总体水平。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岭南诗纪序》曾经提到:
予兹不揣愚蒙,谬有《广东文集》之役,思为同乡先哲罔罗放失,纂辑成编,以一国之文献,为一家之私书;而裁择未精,中多冗滥,颇为识者所病。然予志在广收以为富有,备史臣之肆考,资学士之多闻,若武库之有利钝,太仓之有精粗,不遑计矣。*《屈大均全集》,第3册,第58页。
而《广东文选》一书,对《广东文集》所收作品有删有存,如其自序所说:“存者为先哲显其日月光华,删者为先哲藏其珠玉瑕类,是吾之所以为恭敬也云尔。”*《广东文选》卷首,第128页。因此,从客观上来说,《广东文选》收录的作品自然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
《广东文选》与《广东文集》两书,虽然有大有小,有粗有精,但各自都有它们存在的意义。正如《广东文选》自序所说:
譬之水焉,《文集》为牂牁大洋,而《文选》为一勺;譬之山焉,《文集》为罗、浮二岳,而《文选》为一卷。使观者从一勺以求牂牁大洋,从一卷以求罗、浮二岳,是一勺为牂牁大洋之所必须,一卷为罗、浮二岳之所不可少。《文选》为《文集》之车右轮,相辅而行,而不可废一者也。……书成,……以为《广东文集》之先声。*《广东文选》卷首,第128页。
《广东文集》与《广东文选》两者缺一不可,如同“大洋”与“一勺”水,“罗、浮二岳”与“一卷”石,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小中可以见大;又如“车”与“轮”的关系,后者可以辅佐前者。同时,这两个比喻还都说明了屈大均始终坚持《广东文集》的刊刻,其“未能尽刻”只不过是一时之困;而为了改变这个困局,他有意以《广东文选》作为《广东文集》的“先声”,不仅可以宣传推广后者,而且很有可能也是为了赚取、积累后者的刊刻资本,走“曲线救国”的道路。
屈大均本人重视《广东文集》的程度,无疑更甚于《广东文选》。但一方面由于《广东文集》最终“未能尽刻”,已刻者又散失严重,另一方面则《广东文选》这部晚出的“先声”凭着以少胜多的优势,使得其知名度实际上盖过了《广东文集》,这也许是屈大均始料所未及的。
三、 《广东文选》与《岭南诗选》及其他
屈大均在《广东文选》自序中,曾经说过:“广东者,吾之乡也。不能述吾之乡,不可以述天下。”可见,他始终以编纂“吾乡”总集为己任。而他生前亲手编刊的地方总集,除了《广东文选》以及《广东文集》刊布流传以外,还有数种最终未能成书,《岭南诗选》即为其一。
《岭南诗选》是屈大均早年拟编的一部广东省域通代诗歌总集。其《广东新语》卷十二“宝安诗录”条曾提到:
予撰《岭南诗选》前、后集,《前集》自唐开元至明万历,《后集》自万历至今;人各有传,仿《列朝诗集》之体;积二十年,亦未有成书,可叹也。*《广东新语》卷一二,第358页。
又其《翁山文钞》卷一《东莞诗集序》,同样提及这部《岭南诗选》,当时“尚未就”*屈大均:《翁山文钞》卷一,《屈大均全集》,第3册,第280页。。根据这两条线索,可以推知,此书体例仿照钱谦益的《列朝诗集》,以人系诗;又分前、后两集,以明万历朝为界。《前集》与清代绝无关系,《后集》则一直收到清初,总的时间跨度大致与《广东文选》的诗歌部分相同。其编纂时间,据本师朱则杰先生《清诗考证》书稿推断,大致在康熙三年甲辰(1664)以后。可惜这想法虽早,却“积二十年,亦未有成书”。究其原因,近人朱希祖先生在《屈大均(翁山)著述考》一文中认为,一方面在于“王隼已有《岭南诗纪》”,不必重复劳动;另一方面是书名“‘岭南’二字之不谛”*《屈大均全集》附录之三,第8册,第2163页。,即不符合前述应取“广东”之原则。不过,更大的可能,恐怕还是由于后来长期奔波逃亡各地,无暇顾及该书编纂,而后来却被王隼捷足先登了。
屈大均编纂总集的目光,还不仅仅局限于广东本省。他曾有《麦薇集》,拟专门收录清初全国遗民诗歌,今《翁山文钞》卷一尚载其自序*《翁山文钞》卷一,第280-281页。,而有关计划远在后来卓尔堪辑《明遗民诗》之前*朱则杰:《全国性清诗总集佚著五种序跋辑考》,《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332页。。又有《绿树篇》,以咏“绿树”为主题,属于题咏类诗歌总集,《翁山文外》卷九载有《书绿树篇后》。再有《三闾书院倡和集》,则系唱和类诗歌总集,其序亦见《翁山文钞》卷一。此外,屈大均还积极为他人所编有关诗歌总集做宣传,分别为前及王隼辑《岭南诗纪》、蔡均辑《东莞诗集》,以及陕西张云翮(曾任广东驿盐道)辑《岭南倡和集》等书撰序。特别是前两种总集的编纂者,他们和屈大均一样都是广东人,又都是“生当乱世,有志纂修”*《翁山文钞》卷一,第279页。,可谓志同而道合。而这种“志同而道合”,亦即通过纂修总集的方式曲折表达自身的遗民意识,正是明清易代之际十分突出的一种文化心态。
《岭南诗选》《麦薇集》《绿树篇》《三闾书院倡和集》等总集虽然没有成书,或者已经遗失,却可以见出屈大均编纂总集的热诚和志向,并且这种热诚和志向一直贯穿他的一生。更重要的是,它们作为总集编纂的经验积累,客观上有助于《广东文选》后出转精,成为一部集大成的著作。
综上所述,《广东文选》的成书背景,可以说是屈大均热心乡邦文化活动的一个缩影,折射出广东清初遗民文人思想中的浓郁乡邦情结。屈大均此书,不但完成了他要“为父母之邦尽心”的愿望*《广东文选》卷首自序,第128页。,而且也扩大了广东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同时,它作为广东省级清诗总集的开山之作,对后世广东地区总集的编纂活动,曾起到很大的引导作用。时至今天,当我们评价清代广东文化发展的推动者时,屈大均及其《广东文选》仍然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
(作者单位:广东惠州学院中文系)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资助项目“广东省域诗歌总集研究”(GD15YZW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