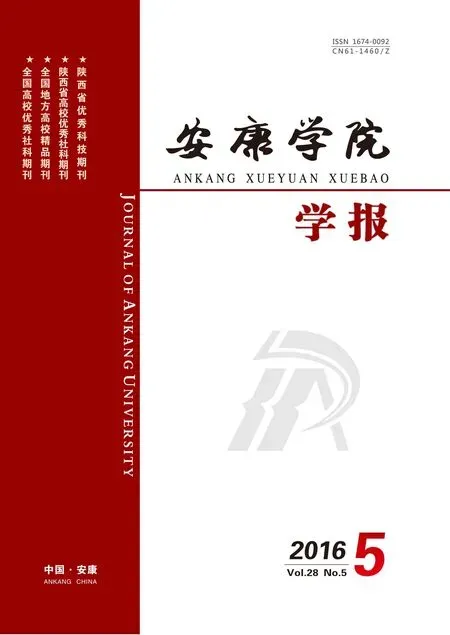后殖民生态视角下的《等待野蛮人》
张兰
(安康学院 外语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
后殖民生态视角下的《等待野蛮人》
张兰
(安康学院 外语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
作为一部政治寓言体作品,《等待野蛮人》一直以来被广大学者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进行剖析,而忽略了作品中丰富的生态书写。库切的生态书写和后殖民书写相映成辉。通过探究小说中所蕴含的后殖民生态关切,可以窥见库切反对一切殖民霸权、尊重所有生命、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后殖民生态伦理观。
J.M.库切;《等待野蛮人》;后殖民生态批评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全球化带来的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由全球环境危机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引起了一些极具危机意识的学者们的注意。后殖民社会的生态问题愈益引发关注,后殖民生态批评研究也应运而生。澳大利亚学者格拉姆·休根(Graham Huggan)和加拿大学者海伦·蒂芬(Helen Tiffin)的专著《后殖民生态批评:文学、动物和环境》(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Literature,Animals,Environment)是后殖民生态批评学说的开创性著作。他们试图从文学理论研究向促进社会正义、环境正义和生态正义的转化。南非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J.M.Coetzee)以后殖民文学创作著称于世,而丰富的生态书写氤氲于其后殖民创作之中。19世纪末,后殖民研究与生态批评的对话和融合为我们探讨库切别具匠心的生态书写提供了良机。
《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barians)是库切的一部寓言体作品,也是其第一部为自己赢得国际声誉的长篇小说,被称为是一部政治恐怖小说,它继承了约瑟夫·康拉德的文学手法,是一部典型的殖民小说。在小说中,库切展现了帝国的一个边境小镇,为了证实帝国的存在以及不断扩充自己的疆土,帝国通过散布谣言——野蛮人即将来临,派来了以乔尔上校为代表的帝国军队。他们打着传播文明的正义旗帜欺压、凌虐边疆土著人民,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运用后殖民生态批评理论去解读该小说,可以从双层视角管窥这部经典之作。本文通过分析《等待野蛮人》中殖民战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小镇等建设性工程为标志的生态帝国主义表征以及被视为他者的人和动物的描写,来解读库切小说中所蕴含的后殖民生态思想。
一
帝国征服和殖民主义对非洲地域环境和生态的影响,对于从小生长在南非的库切有着切肤之痛,因此揭示殖民扩张以及相应的经济和文化活动对南非生态系统的毁坏可谓其生态关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库切把《等待野蛮人》的故事背景设置在辽阔的异域边疆。在那里,殖民者未出现前,随处可见一片片绿洲,湖边水草丰美,“那是一片靠着湖边富饶美好的土地,甚至在冬天也不乏丰美的牧草”[1]76。土著居民应天顺时地生活在春种秋收和水鸟迁徙的周期中。然而,为了驻领和占有殖民地,推进殖民进程,100多年前,“我们把这地方从一片荒野开垦成耕地,建立了排灌系统,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劳作,建起了坚实的房屋,在城镇四周筑起了围墙”[1]76。殖民者涸泽而渔的行为极大地影响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以致湖边浅浅的地表水太咸而不能喝,“每年湖水把湖岸吞噬一点,把盐和明矾扫进了湖里”[1]88,湖里的水就会变得咸一点。为了抵御所谓的野蛮人的侵袭,建立一道防护线,帝国军队决定把河岸边的灌木丛统统烧掉,“火势蹿过芦苇丛,杨树像火炬一样燃烧起来。一群群鸟儿惊恐地飞去;剩下的,每样东西都被焚毁”[1]121。帝国军队为了他们所谓的军事行动,蹂躏、糟蹋着边疆土著居民的土地,“他们才不在乎一旦土地被如此修理,风就好剥蚀土壤,沙漠就会向前推进”[1]122。殖民帝国对殖民地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表明,生态掠夺是其殖民扩张的前提。这些破败的自然景象表明殖民战争彻底地影响了殖民地的自然生态环境。
小说中,通过行政长官对当地野生动物的描述也可窥见殖民扩张对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二十年前,羚羊和野兔多得不得了,看守庄稼的人只好带着猎狗夜里巡逻守护,防着这些动物来啃噬青苗”[1]57,然而“随着居民点的发达和扩张,特别是成群的狗儿们放出去狩猎后,羚羊就向东面和北面撤走了,很少再来光顾河边或是远岸地带了”[1]57。在谢泼德·克拉申(Shepard Krech)看来,“今天有限的动物和植物,以及因为干涸的河床而闻名的河流,是无数力量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几十年过度放牧的结果”[2]。这番话表明,殖民帝国过度地掠夺和使用殖民地的资源,从而使资源枯竭,导致当地自然生态系统恶化。帝国对待土地和自然的野蛮态度表明,他们对殖民地的自然生态毫无敬意可言,殖民地只是他们资源掠夺的对象。为了推进和巩固帝国的统治,他们可以肆意盘剥和掠夺殖民地资源,夺取和毁坏自然界的一切为其所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惜以毁坏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
库切在《等待野蛮人》中采用寓言方式,描述了为巩固帝国的殖民统治而打着文明旗号的帝国军队对一个边疆殖民地生态环境的肆意践踏,流露出“对人类崇尚工具理性的批判以及对人类未来之生存状况的担忧”[3]。在小说中,库切用隐喻的手法揭示了在殖民战争的阴影下,边疆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蹂躏的不可避免性。而通过描述在帝国殖民战争下日益恶化的边疆栖息地,库切旨在说明殖民扩张所构建的违反生态和谐的政治规约必然走向坍塌,成为历史的陈迹。这一点,可以通过小说中老行政长官之口得以证实:“帝国注定要存在于历史之中,并充当反历史的角色。帝国一门心思想的就是如何长治久安,苟延残喘。在明处,它到处布下它的爪牙,处心积虑追捕宿敌;暗地里,它编造出一些假想敌:城邦被入侵,民不聊生。尸骨遍野,赤地千里,并以此来巩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1]19。
二
贸易作为一种扩张性的人类经济活动是殖民者进行殖民扩张的直接动力。随着17世纪以来世界贸易的扩大,殖民者从18世纪起在南非内地掀起了大规模和持续的殖民扩张狂潮。他们打着文明的幌子,来到南非这块陌生的土地安营扎寨。当他们抵达目的地后,首先会建立一个边防要塞为其提供生活必需品,一般肉类通过与土著居民的物物交换获得,蔬菜、粮食则主要靠自己解决,因为南非土著居民并不种植诸如莴苣、西瓜、西葫芦、胡萝卜等殖民者所喜好的食物。为了使殖民者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他们无视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掠夺了原居民的土地建起了农场,进行了移民,“给殖民地带去了源自欧洲的植物、动物和疾病,致使当地由植物、动物和原住民构成的原生生态系统被毁坏和取代”[4]。殖民者对殖民地的殖民扩张,忽视了自然的韵律和节奏。
为了加快对南非殖民地扩张的步伐,帝国以传播文明为名,认为边疆殖民地是黑暗世界,原住民为“肮脏的”“丑陋的”“野蛮的”“像动物一样的”种族,需要帝国殖民者用所谓的西方先进的文化帮助其消除愚昧,促使其向文明社会发展。而以小镇等为文明标志的建设性工程以驯化自然为主要特征。小说中,行政长官说“这地方先为前哨基地,后为边防要塞,现在已经慢慢变成一个有三千之众农业人口的定居城镇了”[1]6。他们还建造了屠宰场和磨坊,沉溺于过度捕猎,“成百上千的鹿、猪和熊被杀死,漫山遍野都是动物尸体,多的没法收拾,只好让它们烂掉”[1]1,殖民者肆意践踏自然的馈赠。小镇及其配套设施的建立说明,帝国殖民扩张以抢夺原住民世界为前提,给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带来了毁灭性打击。看似稀松平常的小镇的建立实际上掩盖了殖民扩张背后的真正危机——生态破坏乃至不可逆转性的生态毁灭,克罗斯比将其称之为“生态帝国主义,即帝国在定居者殖民地的扩张过程中,种族与环境相互关联,共同推进帝国殖民进程,维护西方殖民统治”[5]。小镇的建立展现了定居殖民者对于原居民的生命、土地和自然的主宰,“随着定居者人口的增加以及越来越多的森林被砍伐而成为牧场,当地动物的栖息地面积和动物数量锐减”[6]。小镇等建设性工程设施是帝国殖民扩张导致自然界毁灭性后果的物质体现。
帝国殖民者通过战争、屠杀等血腥手段把原居民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建立起他们的定居点。随着居民点的发达和扩张,又发展成为商贸集散中心。在与当地游牧民们做交易时,他们缺斤短两、欺行霸市。帝国殖民者对原住民的掠夺与压迫以及相应的经济和文化活动对南非生态系统产生了深远影响,致使南非原居民传统思想受到践踏,破坏和摧毁了南非的社会环境公正和生态公正。
三
库切在《双重视角》里说:“我作为一个人,一个存在的人,感到很不安,这个世界上苦难,不仅仅是人类的苦难,让我思绪困乱无助。”[7]这表明库切在关注殖民历史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危机的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殖民霸权下被人类肆意蹂躏的动物生命的关切。正如在《动物的生命》里库切借助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之口所表达的那样,动物和人一样也有着丰富的情感,具有智力,能够体验痛苦,感知死亡气息。在《等待野蛮人》中,库切笔下的蛮族女孩和动物之间似乎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在女孩被老行政长官送回到自己部落的艰苦跋涉中,一场暴风雪使马群陷入惊恐之中。她通过体态语和心灵感应的方式对马匹进行安抚,“那女孩站在那里张开双臂像是在两匹马的脖子上飞翔。她好像在对那两匹马说:两眼睛瞪得老大干嘛,你们给我老实待着”[1]100。她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安抚了马群。由此可见,非人类动物是能够与人相互交流感情的群体。
同样在这次长途跋涉途中,一匹不堪重负的马即将死去,同行的伙伴打算将其杀死作为食物,老行政长官说:“我发誓动物绝对有灵性有感知。一看见刀子,它的眼睛就惊恐地转动起来”[1]92。传统的伦理思想认为动物是没有情感的生物,人类的权利和生命高于动物的权利和生命。库切在小说《等待野蛮人》中破除了这种偏见,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物种主义,打破了人与动物二元对立的模式。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的戏仿“我思动物故我在”[8],很好地诠释了人类应该重新审视与其他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追求各物种之间的相互平等。
为了重建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库切对动物尊严的呈现几乎都与主人公巨大的身份颠覆同时完成,成为动物问题与身份建构问题联接的平台。在《等待野蛮人》中,库切详细地描述了由于护送蛮族女孩回家,老行政长官遭受的像动物一样的遭遇。从长途跋涉中回来之后,老行政长官被定以“擅离岗位、通敌叛国”的罪名。首先是几天的单独监禁,“围着一日三餐被人喂食的时间打转,到时候狼吞虎咽就像一条狗”[1]119。屈辱的监禁生活让他慢慢地变成了一头野兽,逐渐了解了低级的自由的滋味,过着“饥来即食、困来即眠的动物般的日常生活”[1]129。后来,由于无法视若无睹被俘的野蛮人所遭受的酷刑而被毒打了一顿,疼痛使得他“像一条狗似的哀号着”[1]158,丧失了作为人的最后一丝威严,“就像一头疲倦的老熊,已经被太多的折磨驯服了”[1]168“活得像门背后一头奄奄待毙的野兽”[1]179。库切将动物意象与老行政长官的遭遇相关联,无疑凸显了殖民战争的残酷性,即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一切阻碍殖民扩张的人和物都要被压迫、被摧残。而作为自然界的动物,在殖民扩张中因为可以为殖民者提供各种给养,保障其战斗力,从而为暴力征服和殖民扩张做必要准备将必定遭受更多的苦难。威廉·普斯顿(William Preston)的评论“殖民主义最直接、最广泛的影响在于动植物群体”[9],揭示了西方殖民活动的生态内核。
殖民者将他者动物化的生态帝国主义心态不仅在老行政长官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对待野蛮人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乔尔上校带着大队人马押着一群野蛮人回到小镇,一个骑兵牵着一条绳索,“绳子上系着一个个被拴着脖子的人……一个个都用手捂着腮帮子……一根环形铁丝从个人手掌穿过,又穿透他们脸颊上打出的小孔。这样他们就像羔羊一样顺从”[2]151。“动物化原住民并将其暴力征服,是生态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和结果,对当地原有的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造成很大危害。”[10]库切的这种书写表明,殖民扩张活动与动物的灾难联系紧密。殖民主义不仅毁坏殖民地原居民社会,而且破坏原住民的自然生态环境并危害当地动物。正如格瑞塔·伽荷德(Greta Gaard)所言,“原住民与动物之间的联系,他们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共同遭受的压迫,以及人与动物共同的沦丧,令人叹息,使人痛苦”[11]。
四
作为一部寓言体小说,《等待野蛮人》既没有给出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也没有典型历史人物的出现,一切好像和现实脱离了关系,但库切作为一位典型的后殖民小说家的良苦用心跃然纸上。他不仅控诉了殖民战争给南非人民带来的切肤之痛,而且警醒人类要深思殖民战争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联,并指出在环境急剧恶化的时代,殖民战争对殖民地原居民压迫的问题已经转变为全球环境正义问题。可见,种族问题和生态问题是相互联系的,生态危机与后殖民政治危机密不可分。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指出,“追求真正的全球正义需要我们将与我们生活完全交织在一起的其他有感知的物种纳入考量范围”[12]。
在库切笔下,《等待野蛮人》呈现了南非的殖民历史、种族霸权、物种问题与自然生态等诸多议题。通过探究小说中所蕴含的揭示殖民战争对生态环境的毁坏、以小镇等建设性工程为标志的生态帝国主义行为及对被视为他者的人和动物的压迫,可以窥见库切反对一切殖民霸权,尊重所有生命,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从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后殖民生态伦理观。重新审视被殖民的历史,以及被殖民经历给殖民地国家和人民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和其在当代的表征,反思后殖民语境下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这是南非和其它曾经被殖民的国家面对新殖民主义和全球化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1]J.M.库切.等待野蛮人[M].文敏,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
[2]SHEPARD KRECH III.The Ecological Indian:Myth and History[M].New York:W.W.Norton&Compony,1999.
[3]钟再强.库切《生活和时代》的后殖民生态书写[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52-58.
[4]JOHN MILLER.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and Victorian Studies[J].Literature Compass,2012(7):476-488.
[5]ALFRED W CROSBY.Ecological Imperialism:The Bio 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900—1900[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6.
[6]GRAHAM HUGGAN,HELEN TIFFIN.Postcolonial Eco criticism:Literature,Animals,Environment[M].New York:Routledge,2009.
[7]J.M.COETZEE.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 views,ed[M].Cambridge:Havard.UP,1992.
[8]JACQES DERRIDA.Trans.David Wills.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J].Critical Inquiry, 2002,28(2):369-418.
[9]WILLIAM PRESTON.Serpentin theGarden:Enviromnental Change inColonial California[J].California History,1997,76(2/3):260-298.
[10]姜礼福,孟庆粉.英语文学批评中的动物研究和批评[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3):66-74.
[11]GRETA GAARD.Ecofeminism and Wilderness[J].Environ mental Ethics,1997,19(1):5-24.
[12]NUSSBAUM MARTHA C.The Moral Status of Animals[J]. 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2006,52(22):B6-8.
【责任编校朱云】
Analyzing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ZHANG Lan
(School ofForeign Studies,Ankang University,Ankang725000,Shaanxi,China)
Asa political fable,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has beenwidely studied by scholars from the perspectiveof post colonial theory,the rich ecological writing ignored in theworks.Ecological themesand postcolonial themsare intertwined in Coetzee’sworks.By exploringecological concerns thenovel contains,we can getaglimpseof Coetzee’spostcolonial ecological ethics:fightingagainstall kinds of hegemony,respecting forall formsof life,protecting theecological environment,soas to promote the harmony betweenman and nature.
J.M.Coetzee;Waiting forthe Babarians;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I478.074
A
1674-0092(2016)05-0080-04
10.16858/j.issn.1674-0092.2016.05.017
2016-02-25
陕西省教育厅2016年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后殖民生态批评视域下南非当代白人英语小说研究”(16JK1007);安康学院校级培育科研计划项目“后殖民生态批评及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小说研究”(2015AYPYR W 04)
张兰,女,陕西安康人,安康学院外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后殖民英语文学与理论研究。
——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阈中的马琳·诺比斯·菲利普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