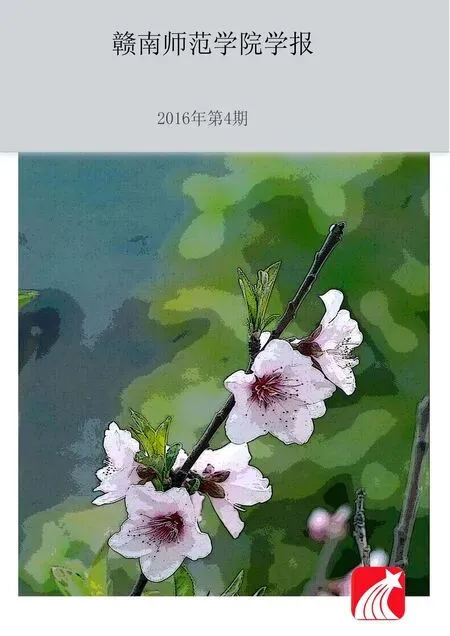价值共识视域下红色文化的教育探析*
周金堂,许金华
(江西省教育厅,南昌 330038)
·特稿·
价值共识视域下红色文化的教育探析*
周金堂,许金华
(江西省教育厅,南昌330038)
摘要:价值多元呼唤着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今社会价值共识的重要体现。红色文化包含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价值共识的基础。因此,我国必须大力推进红色文化教育,创新红色文化教育的目的、内容和路径,形成社会价值共识。
关键词: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红色文化;教育
社会价值多元化正在我国形成,由价值多元向价值共识的转化已必不可少,而价值共识的生成需要先进文化的凝聚与引导。红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价值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当下的共识价值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通过红色文化教育的加强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共识价值的生成,而从价值共识视域出发,可为红色文化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借鉴和启示。
一、价值共识源于价值多元
没有差异就没有共识,价值共识源于价值多元的社会生成。理论上,社会价值的多元化源于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传统西方世界,宗教神学遮蔽了人和人性的存在,文艺复兴开启了西方的启蒙,开启了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的转变,人与人性得到恢复。据此,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逐渐占据主导,传统时期统一的、超越的、目的论价值观被终结,价值与事实开始分化,价值客观性逐步陨落,使得价值失去了客观的保证和统一的标准,好与坏、善与恶、丑与美的判断与甄别,难以分别。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那些古老的神,魔力已逝,于是以非人格力量的形式,又从坟墓中站了起来,既对我们的生活施威,同时他们之间也再度陷入无休止斗争之中。”[1]人类进入了“诸神并立”时代。在逻辑层面,客观事实属于实际、实然层面,而价值属于应当、应然层面,从事实的实然层面推导不出价值的应然层面,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分属不同的场域,由此,我们发现价值与事实的二分为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现代社会价值的相对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当前,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当代中国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转化;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正在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正在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正在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化;正在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化。”[2]人们在时代的大潮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现代社会,同时,又留恋旧有的社会价值,社会新旧文化矛盾冲突、交织交融。另一方面,国际化大发展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多样化进程加速发展。而科技信息化的大发展,使信息传播更加快速、便捷,打通了多元价值进入大脑的最后障碍。人们的价值观念因此发生深刻嬗变,各种价值观念相互碰撞、冲突,从而促成价值多元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总之,只有一种声音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嘈杂”成为当下的一个显性表征。
然而,社会需要共识引领,多元社会更需要核心价值的存在。事实上,由于价值共识的缺失,政治领域、道德领域、文化领域、个人生活领域正逐步丧失公认的价值标准,中国已显现出哈贝马斯所说的“政治危机、文化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各种潜在的危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3]而由于个人只有在彼此间的交往中才能实现自身的实践和价值,个人所追求的特殊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的不相契合始终存在,共识价值的培育和价值共识化的形成已迫在眉睫。为此,党的十八大提出要积极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社会的共同价值(价值共识)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就是共识化价值的形成过程,它需要包括红色文化资源在内的优秀文化的推动与支撑。
二、红色文化是价值共识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4]这表明,社会价值不是存在于某种理论时空中的抽象概念,而是一定时空下的社会主体进行社会实践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进程中孕育形成的,源于各种先进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因子。与此相对应的是,红色文化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先进文化。红色文化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建构提供理论支持。
首先,红色文化蕴含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民主革命初期,党就把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和统一的新中国作为自己的斗争纲领。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红军实行“士兵委员会”制度,实施民主决策,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决策为日后党内民主提供了实践和理论基础。苏区时期,苏维埃政权实行工农民主制度,建立中央、省、县、乡、区五级苏维埃民主政权,赋予普通民众普遍的选举权。“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并赋予人民群众以批评、监督、检查、罢免政府官员的权力,对不称职的苏维埃代表和政府工作人员,“只要选民10人以上提议,经半数以上选民同意,即可撤销其代表资格,或通过代表会议予以开除”。[5]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战争的困难环境下,始终重视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以学校教育为例,苏区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制:“小学教育的目的,要对于一切儿童,不分性别与成分差别,皆施以免费的义务教育。”在政府的大力提倡下,苏区小学教育快速发展。“根据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在2 932乡中,有列宁小学3 002所,学生80 910人。”苏区许多地方,学龄儿童多数接受小学教育,兴国县学龄儿童入学与失学的比例为60%与40%,远高于同期国民政府统治区域。[6]
其次,红色文化内含“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基础。苏区革命根据地的社会建设进程,彰显着这些价值理念。井冈山时期,官长士兵平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一致。苏区民众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报》、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设有“铁锤”“突击队”“警钟”“工农通讯”“红板”“黑板”“反贪污浪费”等专栏,各地各部门设有“人民通讯员”,工农群众随时可以在上述专栏发表意见,批评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年11月)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5]不仅在法律条文上有平等的规定,战争环境下的苏区社会,时刻彰显着战时共产主义的平等:中央领导在作风建设上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中央政府主席到乡苏机关干部一律没有薪饷,每人每天只发一角钱菜金和大半斤粮食,领导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员一道向食堂交伙食费、吃“包包饭”,同甘共苦。苏区革命实践彰显着法治理念。苏区政府各级部门成立工农检查部(科),下设控告局,负责“授受工农劳苦群众对苏维埃机关或国家经济机关的控告及调查控告的事实。”在政府门口挂设“控告箱”,“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7]1933年12月15日,苏区中央政府发布了毛泽东主席和项英副主席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规定“凡苏维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最后,红色文化凝聚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道德准则。“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层面的价值标准。苏区普遍开展的革命竞赛很好诠释了“爱国、敬业”的模范品质。1932年3月23日,中央组织局发布通知第八号——《关于革命竞赛与模范队的问题》,号召全党“用组织模范队和革命竞赛的新方式”,深入转变工作方式,开展革命竞赛。其实,据笔者所见资料,早在1931年2月,永丰县在工作报告中就提出当前的中心工作是抓好“四县革命竞赛条约的执行”。[8]革命竞赛早在苏区建立之初就已实行。随后,这种工作方式遍及苏区各地,省与省、县与县、区与区、乡与乡、村与村、团体与团体、个人与个人等各种形式的革命竞赛纷纷上演,革命竞赛成为苏区日常工作的基本方式,苏区干部在争创“第一等”工作中,将敬业爱岗的可贵品质展现到极致。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传承了中华民族“诚信、友善”品德。1928年2月,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中,提出善待俘虏四原则:不打、不骂、不杀、不虐待;不搜俘虏腰包;伤病者给治疗;释放俘虏,愿留者欢迎参加工农革命军,愿走者一律发给路费,欢送回家。[9]
显然,红色文化与作为共识价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深度的价值契合。为此,我们在教育传播红色文化的同时,就是传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由此可见,红色文化教育实质是价值观的教育,更是社会主流的共识价值观的教育,这为红色文化的教育传播提供了新的启示。
三、共识价值观教育对红色文化教育的启示
价值共识化的进程就是共识价值观教育的过程,而价值观的教育与知识教育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价值观教育的目的不仅仅停留在所传授信息被个体所掌握,还要内化为个体的思想认知并指导个体实践。价值观教育的内容要充分体现“政治”和“文化”的统一,其教育路径与一般的知识教育也应有所区别。目前,红色文化教育效果不彰、影响不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忽视了其作为价值观教育的本质属性,红色文化教育需要在价值共识化的视阈下重新审视。
(一)要创新红色文化教育的目的
红色文化教育并不是智育、体育等单一传授知识技能的教育,而更多的是传播社会价值,实现社会价值共识化的价值观教育。虽然价值观教育和知识教育都具有传授知识的共同之处,但这种教育与知识技能教育相比较,目的有着明显的差异:“其不同之处在于,知识教育是一种纯粹的知识传授,它所传授的知识是可以技术化的;而价值观教育所传授的知识则是一种特殊的价值知识,是一种意会型的、不能技术化的目的性知识。”[10]因此,作为一种价值观教育的红色文化教育,其目的不仅仅传授红色知识,而是让知识背后的精神内化为教育客体的价值认识,推动客体形成社会所期望的价值认知,即接受、认同社会的共识价值,并以之指导自身的社会实践,最终实现教育客体价值认知和行为习惯的内在统一。涂又光曾经指出:“知道为智,体道为德”。“体道”和“知道”是两种不同的教育过程,红色文化教育的终极关怀无疑是“体道”。然而,现存的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各种红色文化教育的实施,大体仍遵循着“知道”的教育方式,表现为特定人员在一定的时空中,以传授的形式、灌输的方法,将抽象的、概念化的知识传授给客体,简单而言,就是将红色文化教育知识教育化了,将红色文化教育的复杂进程简单为一般知识的教育过程。总之,红色文化教育的目的不仅仅视为具体知识的传授,而更应视为社会共识价值的传播。
(二)要创新红色文化教育的内容
从“红色文化”的字面来看,似可得出结论:红色文化教育在内容上应包括两部分:一是红色教育(政治性内容);二是文化教育(文化性内容)。此外,作为价值教育的红色文化教育,其承担的使命也是要把教育客体由“生物人”向“文化人”的转化,而不仅仅是由“自然人”向“政治人”的转变。《易经》中提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文化人”的认知和传统,红色文化教育更应注重“文化”教育,做到政治内容和文化内容的统一。然而,红色文化的教育实践中,“文化性”内容严重缺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强调:“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11]其实,今天的红色文化教育也有大量空洞的教条,标语式的口号,存在过多的政治说教,从而使红色文化教育的生命力遭到侵蚀,红色文化教育的实效性大打折扣。因此,要通过不断提升红色文化教育的“文化品位”来创新红色文化教育的内容,更多的挖掘、整理红色文化中的价值内涵。诚然,文化的“红色”标记显示了红色文化的政治取向,红色文化必须服务于政治教化这一根本,红色文化教育的“文化性”不能以否定它的政治性为前提,而是力求 “文化”(文化育人)和“教化”的统一。这里还要提及的是,出于对红色文化教育过度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反思,有些红色文化资源的市场开发和娱乐利用呈过度化迹象,使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在物质化和娱乐化的追求中偏离了其应有的“教化和文化”的功能定位,红色文化教育的政治性和文化性都被抹掉了。
(三)要创新红色文化教育的路径
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的创新,决定了教育路径和教育形式的调整改变。传统的红色文化教育依赖大范围的宣传、集中的主题活动、灌输式的课堂教育、意识形态的维护批判和种种政治界限的划分等。这些教育方法的采用体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势灌输,彰显的是教育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影响了教育的实效性。据相关调查统计:有73.6%的人认为主流价值文化缺乏现实关怀;有54.3%人认为宣传得多,说教太多,缺乏实效。[12]红色文化等主流价值观教育在实施路径上的创新急需加强。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这对同属价值观教育的红色文化教育来说,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与生活化”的价值教育路径就是使教育与客体的实际相对接,做到“以人为本”,实施“人本教育”。一是要尊重个体的现实需要。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3]强调“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4]红色文化教育首先要关照个体的现实利益,关注人们日益丰富多样的各种正当需要,在关注民众日常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引导他们追求更高的人文素养,引导他们认同红色文化所蕴含的共识价值。二是尊重个体的主体地位。传统教育观对教育施教方赋予了更多的“主体性”,对教育受众的“主体性”则多有忽视,教育客体的主动性、积极性难以发挥,大大降低了教育客体对所传授知识的认知和认同。
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要加大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红色文化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崇高的价值取向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发展红色文化教育,尤其是在社会价值多元化的现实语境下,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意义尤为重要,而将红色文化教育与社会价值共识化的历史进程相结合,则应成为红色文化教育今后发展的目标与方向。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40-41.
[2]李培林.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3(3):125-134.
[3]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诚,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3-120.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4.
[5]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M].(第6册).江西: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109.
[6]赣南师范学院,江西教育科学研究所.江西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二)[M].(内部资料).1985.
[7]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N].红色中华(第32期),1932-09-06.
[8]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M].1931:7.
[9]常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与运用[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10):108-112.
[10]王玉萍,黄明理.价值共识及其当代意义[J].求实,2012,(5):37-40.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9.
[12]陈俊.主流价值文化社会认同面临的困境及其化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81.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责任编辑:侯伟浩
·苏区研究·
主持人语: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在苏区反“围剿”失败后作出的被动回应。长征作为一次战略大转移,中共中央在出发前是做了充分准备的。比如中央红军长征前,中央派出了红六军团前往江西、湖南、贵州等地探路,开始了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井冈山大学陈钢教授的《红六军团突围西征的历史定位》研究了红六军团西征所遭遇到的困难和从中体现出来的红军革命精神。红军长征由红一、二、四方面军组成。长期以来,学术界重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对其他红军长征研究不够。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董振平教授的《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刍议》研究了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和再出发的问题,提出了红四方面军有两次长征。过去常言说,战争让女性走开,但解放妇女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因此,妇女成为苏区革命的重要角色,红军长征也活跃着一批红军女战士。复旦大学谈思嘉博士和博士生导师高晓林教授的《“她们”的长征——论长征中的女红军》研究了女红军长征的目标、任务、挑战及意义。工农红军长征不仅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江西理工大学魏建克博士的《改革开放以来长征胜利周年纪念中的话语资源建构——以<人民日报>文本为中心的考察》以《人民日报》为中心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长征胜利周年纪念中的话语资源建构问题。本期四篇文章的内容不仅覆盖了长征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而且从全新的视角比较深入地研究了长征相关问题,不仅全景式反映了长征的历史场景,而且彰显了长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曾耀荣
*收稿日期:2016-06-10
DOI:10.13698/j.cnki.cn36-1037/c.2016.04.001
作者简介:周金堂(1956-),男,江西永新人,江西省教育厅巡视员,博士、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原副院长,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8332(2016)04-0001-04
On the Education of Red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Consensus
ZHOU Jintang, XU Jinhua
(JiangxiProvinceEducationCommission,Nanchang330038,China)
Abstract:The value pluralism calls for value consensus,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oday's social value consensus. Red culture contains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 value consensus. Therefore, our country must vigorously promote the red culture and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red culture and education of the purpose, content and path,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value consensus.
Key words:value consensus; socialist core values; red culture; education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6.1037.C.20160708.1519.0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