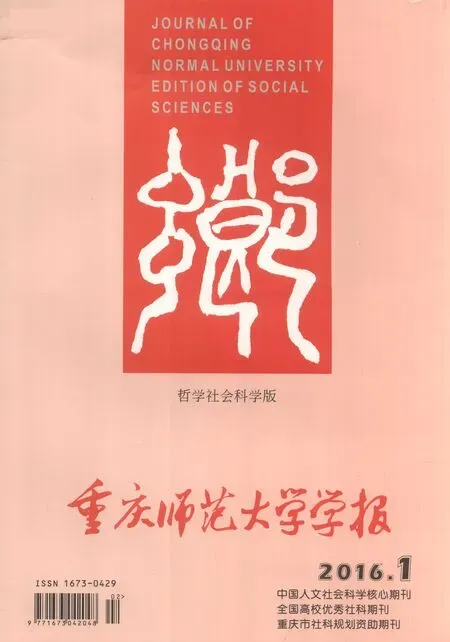“小说的问题应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
——论莫怀戚小说中的“身体叙事”之一
张 育 仁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047)
“小说的问题应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
——论莫怀戚小说中的“身体叙事”之一
张 育 仁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047)
莫怀戚的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身体叙事”,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为什么他之前的小说很少有“身体的在场”?他为什么突然对身体表现出了强烈的书写兴趣?他通过身体书写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小说中大量的身体叙事对莫怀戚而言又意味着什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那以后他是如此地醉心于身体书写,这会使他和他的小说都陷入到消费主义的窠臼而不能自拔吗?通过对诸如此类疑问的解析,将会使我们对这个风格特异的小说家能有一个较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莫怀戚;身体叙事;无身体写作;暴力美学;身体想像
在中国当代卓有成就和颇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中,莫怀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家。莫怀戚的特别主要在于:他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和平民作家的立场和视角,从事自由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并且使他的作品在社会各阶层中赢得广泛的赞誉和持久的精神回应。文学评论界在评价莫怀戚的“特别”时是这样说的:“生性洒脱,举止放松,擅长文化推理,精于人性透视,说话深刻得让人脸红,行文透彻得让人心惊,为中国文坛最独特的智慧作家之一。”[1]本文试图以“身体写作”的视角来审视和研究莫怀戚,从而论证其“擅长文化推理,精于人性透视”的诸多奥秘,揭示其叙事的“特别”和精妙。
一 、“无身体写作”中的“身体政治”悬疑
“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这是梅洛·庞蒂的名言,也是这些年来被中国文学界广泛引用的关于身体写作的一个著名论断。事实上,站在小说的立场,我们完全可以说:小说的问题,可以,而且也必须从身体的问题开始。莫怀戚先生在世的时候,我和他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表示完全赞同,他说:“我是一个小说家,小说的问题,不从身体问题开始,又从哪里开始呢?”对那些蔑视身体,甚至敌视身体、消灭身体的写作,他认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因此,对莫怀戚文学世界的研究,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或者说切入口,那就是身体写作。
文学可不可以理直气壮、堂堂正正地书写身体?很长一段时期在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中竟然成了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身体被意识形态视作不信任不放心的对象;特别是作为个体化的身体更是被主流政治所极力贬低、敌视和批判;惟有阶级的身体、革命的身体,亦即符号化的政治的身体才具有价值意义,才有被意识形态接纳的合法性地位。也就是说,个体化的身体不仅在文学中,而是首先在社会生活中是没有合法性地位的。如此一来,身体在文学中完全处于边缘化,即使偶尔在叙事中出现,也是偷偷摸摸、躲躲闪闪,甚至呈浮光掠影,一鳞半爪之窘态。与个体化身体密切相关的“性”更是成了被主流政治所放逐和囚禁的对象。因此,对小说界而言,所谓“思想解放”,如果不包括身体的解放,特别是个体化身体的解放,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解放。小说家莫怀戚身体书写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
必须说明的是,莫怀戚将自己的小说世界纳入“文学身体学”的范畴,并且醉心于身体写作,并不是出于追风赶潮,而是出于一个小说家的职守和生命的本能。1985年,小说家张贤亮推出了后来成为名篇的中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率先闯入了“身体写作”禁区的大门。二十多年后,莫怀戚谈到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时内心依旧激动不已。他说:“如果没有张贤亮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挺身而出,把日常生活中男男女女的肉身、性爱等等重新找回来,给身体以合法性地位,并且让身体成为文学叙事的主角,成为堂堂正正的书写对象和正面形象,我们这些既呆又傻的‘无身体’写作者可能直到今天都还不知道‘身体写作’是何物。所以,我们必须永远感谢张贤亮,永远记住张贤亮!”尽管张贤亮是打着“批判文革极左政治的旗号”,以携带“私货”的图谋而混入“身体写作”的禁区的,但是,这一举措非同小可,若用民国诗人殷夫的诗歌来形容——“这是一个叛乱的开始!”
从那以后,中国的作家,特别是中国的小说家共同加入了这场具有颠覆性意义的集体行动,那就是由公共写作的立场转移到了私人写作的立场,由“无身体”和反身体写作立场转移到了回归身体和尊重身体的写作立场。莫怀戚不赞成把这种回归说成是所谓的“革命性行动”。他说:“回归嘛,就是回到原初的立场,回到常识和本真。哪里是什么革命?真是革命,那身体就在文学当中没有主体地位了。”
“小说的问题从身体问题开始”,是莫怀戚在认真回顾和检视自己多年来的写作经历,特别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获得的重要觉悟和深刻启示。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前,莫怀戚的绝大多数中短篇小说几乎很少涉及“身体”,处于“无身体写作”的蒙昧状况。当然,也就谈不上进入真正意义的“文学身体学”的范畴,更谈不上从事真正意义上的身体写作。
莫怀戚早年的小说有相当的篇章是叙写青年男女的情感生活,而且重点是叙写青春浪漫的男女大学生的初恋和热恋。这与他中后期的小说热衷于叙写商品社会男女情欲相比反差相当的大。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他早期的小说中,身体书写对他而言还基本处于沉睡状态,至少是处于羞羞答答的暧昧状态。因为在那时他根本就没有“身体叙事”的概念。甚至在《月下的小船》《神枪手八岱》《南月一》和《金神》《公平的惩罚》这样的情感叙事中,也很少可以寻觅到男女身体书写的明显痕迹,以及试图触摸“身体”的动机。 比如,像《公平的惩罚》这个短篇就具有标本意义。这篇小说的叙事构架并不复杂,“主题”也比较鲜明而且“正面”:是一篇用文学的面目来“形象化”地宣讲政治文化逻辑的“主流故事”;简言之:在宣传“五讲四美”的政治道德语境中,他认为:无论国人还是老外,都应该将自己的身体纳入这一社会道德伦理的规训当中。否则,就应该受到“公平的惩罚”!
非常有意思的是:莫怀戚的小说中常常出现一种特殊的叙事对象,那就是改革开放后来到中国帮助或者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国女人。即官方修辞语汇中的“外国朋友”,或者叫做“国际友人”。他对这种角色一直保持着浓厚的书写兴趣。但奇怪的是,他对这些来华工作学习的“洋女人”历来没有正面的描述和评价。他很早就学会了用中国“文化人”的民族主义“审美眼光”来审视这些洋女人的身体,同时对她们的“思想道德”面貌进行“革命伦理”和“中国逻辑”价值尺度上的评判。莫怀戚一生当中写得最多的洋女人,是在重庆高校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女外教”。而且这些特殊的书写对象都比较年轻,浑身上下充满“现代化气息”。即中国的改革开放最渴望吸纳的那种文明气息。《公平的惩罚》里面的凯蒂小姐,是莫怀戚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个“女外教”形象。或许是当时由于作家的身体意识还处于蒙昧的状态,抑或是作家强烈的主流政治道德意识窒息了身体意识的萌发。因此,凯蒂小姐有幸逃脱了身体描述上的劫难——小说当中几乎没有一字叙写她的身体——因而她就完全避免了像后来出现的“洋鸡”安菲迪,或者日本女外教池上荷子以及“长的像洋女人”的团委书记等所遭受的具有“文化强权”意味的性暴力之蹂躏。从身体叙事的角度来看,凯蒂小姐无疑是悲剧的。她在小说中走了一遭却连身体的痕迹也没有留下,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无身体”的女人;但是,如果从“主流叙事” 的角度来看,凯蒂小姐无疑是幸运的。至少她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体缺乏“中国范”而遭受暴力美学的审视和鞭挞。
不过,小说中对那个“外语系女学生”简略粗疏的身体描写,还是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的莫怀戚“身体政治”的基本状况:其身体审美的基本评价逻辑是与当时官方的政治审美逻辑是一致的:“总之我一见到她,就要想起两个人的诗:一是鲁迅的‘美目盼兮’,另一是张衡的‘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特别是他对学校青年部那个女部长身体的正面描述,既不见“性”审美的痕迹,更难以窥见身体暴力肆虐的那种“任性”式的酣畅淋漓书写:“她虽然已不是青年,可是身段依然秀美,面容依然明净。她同你说话呀,口气又温暖又柔软,像刚刚弹好的棉絮。”这个女部长的身体倘若进入莫怀戚中后期的小说叙事当中,很可能是悲剧的,至于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暴力风险,根据莫怀戚后来的叙事脾性和审美逻辑,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但是,谢天谢地!由于那个时期,他整个的写作状态还处于“无身体写作”的蒙昧当中,而且具有不太浓厚的 “身体政治”意识,因此,他笔下的女性整体而言处于“无身体”的状态——关于身体的“暴力叙事”似乎离这些无辜的女性还很远。
以他那个时期的代表作《诗礼人家》《猜谜的人们》《都有一块绿茵》为例,就可以知道,身体在他的小说当中至少还处于暧昧的隐匿的状态,真正意义上的身体写作还没有开始。对于小说与身体的关系莫怀戚还没有搞清楚。比如,《诗礼人家》有一大段是关于昌迩的婚恋叙事。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昌迩的对象是他的中学同学。刚开始两人都在西双版纳支边,感情炽烈。但到第三个年头,姑娘便回城去了,于是慢慢地冷淡了他,昌迩愤然中断了关系,后来,他考上了大学,那姑娘又回来找他了。但是昌迩却不原谅她,于是,哥哥昌怡劝服了弟弟,说:“不原谅人的人没有幸福。”之后,昌迩慢慢试着和她接触,昌迩在上海读书四年,姑娘替昌家洗了四年的被单。昌迩是很爱她的,因此感激哥哥。照理说,这正是小说家展开“身体叙事”的大好时机。遗憾的是,直到昌迩要结婚了,我们也没有见到字里行间有任何与身体有关的迹象。
严格地讲,莫怀戚这一时期小说人物的身体是缺位的,至少是暧昧的和残缺不全的。因此,这就构成了与“身体政治”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悬疑”。显然,长期以来,那种压抑身体的权力机制已经在潜意识当中规训了他的叙事策略乃至叙事趣味。尽管私下里,或者说日常生活中,莫怀戚和那时绝大多数中国男人一样对革命伦理提倡的崇高的禁欲精神持怀疑态度,并热衷于谈论女人的身体,进而在内心中燃烧着渴望进行“身体革命”实践的熊熊烈火。可是,具体到小说叙事中,他还是相当的拘谨,一直小心翼翼地规避着身体。因为,身体写作在那时还是一个敏感的意识形态雷区。《都有一块绿茵》中有一处差点快写到女一号谢青鸥的身体了,谁知叙述者却十分扫兴地将笔触突然宕开,饶有兴致去谈那些与主流意识形态合拍的大道理了。因此,“无身体写作”是考察和评估莫怀戚早期写作精神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
二、有一个支配身体的宏大的“历史法则”
《猜谜的人们》原本是一个与身体有密切关联的婚恋故事,但遗憾的是,由于作者那时缺乏起码的主体自觉和身体意识,尽管小说的思想文化含量和社会信息含量相当大,却无可救药地陷入了遮蔽身体乃至逃避身体的意识形态写作窠臼。小说讲述的是父子两代人在婚姻上的遗憾。在当时这是一种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事关“权利缺失”的遗憾。作者揭示出,在这种婚恋悲剧的背后是那种反人权、反人性的“极左政治”在操控;种种荒诞和吊诡皆由这种权力霸权的规训和凌压而催生。小说中的父与子原本有自己的“真爱”,却根本无法支配自己的身体,最终因“长辈”的“指导”而跌入终身难以摆脱的悲情之中。小说中的“我”与立春,一个是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是邮局的送信人。具有深刻的反讽意味的是:“我”最了不起的能耐是,能将找不到主人的“死信”变成有主的“活信”。吊诡的是,这种能耐却不能帮助“我”找到真正的爱情与幸福。“作品立意的可贵在于:人的真正价值绝不决定于宿命论的出身和表面的学历、地位等,而在于自己的创造。”[2]说到作品的这种“立意”,这在当时的语境下无疑是可贵的。可是,这种可贵完全是“主流政治” 意义上的,是与“新时期”意识形态合拍的那种“立意”,而绝非文学意义上的,更不是小说逻辑和小说伦理意义上的。
其实,长期以来“主流政治”对普通民众婚恋,乃至对普通家庭和家族繁衍施加的干预和规训,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对民众身体,特别是对个人身体选择权和身体支配权的干预和规训。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还是从家庭的层面,个人的“身体主权”基本上处于被剥夺的状况。在“长辈指导”的背后,隐匿着的是那个无处不在的主角,那就是“权力政治”! 为什么这些在世俗生活中多少有些“办法”的普通民众,他们在日常中却始终无法为自己的身体找到真正的爱情与幸福?原因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作者没有这样的主体意识,所以就根本不可能在“身体主权”视角上进行深入的开掘,从而进一步将思考引入到“文学身体学”的纵深境域。
在《都有一块绿茵》中,我们还会发现:婚姻的荒诞往往是通过支配身体的那个宏大的“历史法则”在编演。因此尤为凸显出人生的无常、无奈和被“忽悠”的性质。较之《猜谜的人们》,《都有一块绿茵》似乎具有更加令人“费猜”的信息含量以及荒诞而深刻的反思意义。但是,这种所谓“荒诞而深刻的反思意义”,也是仅仅止步于对“主流政治”,尤其是对“极左政治”的揭露与批判层面,几乎没有触碰到身体的层面,即故事的核心人物谢青鸥的身体的选择权和支配权到底由谁做主?这样一个重要而且不可回避的问题。谢青鸥是否有权支配自己的身体?是否有将自己的身体交付给真正所爱的人的处决权?因为,整个小说叙事的核心问题是紧密围绕谢青鸥的身体而产生和发展的。也就是说,悲剧的核心问题聚焦在此:谢青鸥的身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那还是她自己的身体吗?
莫怀戚将谢青鸥人生的曲折起伏归结于“时势”和“命运”。那么,“时势”和“命运”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无形的手”在操纵着谢青鸥的身体呢?作者就此没有作出任何思考和回答。如前所述,莫怀戚早期的小说对女性的叙述和描写极为粗疏和简略,几乎看不到身体的具体情状,使人感到似乎有一种逃避女性身体描写的暧昧或者淡定。这种写作情状完全可以用他在后来的小说《透支时代》中的一个细节加以描述:“面目冷漠,内心激动。”对谢青鸥的所谓描写,作者仅仅强调了她“漂亮”“相当漂亮”,至于谢青鸥的身体,却语焉不详。也就是说,谢青鸥的身体在小说当中基本上消失了,最多处于朦胧漂浮的状态。在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大于或者高于文学意义的那个时期,小说对身体普遍呈现一种无知和漠然的情状。虽然张贤亮等少数“胆子大的作家”具有了“文学身体学”的自发性觉醒,但是,对当时绝大多数作家而言,即使是这种自发性觉醒,还是相当缺乏的。当然就更谈不上进入身体写作的主体自觉阶段了。这说明,“身体主权”的被剥夺,在当时已经普遍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学叙事不能理直气壮、大大方方地书写身体,实质上反映出“身体主权”在文学写作中已经被剥夺。更其悲剧的是,当时许多的作家并未意识到这种主权的被剥夺,是多么重要和悲剧的一件事。
现在,我们必须回到“谢青鸥的身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这个核心问题上。而要揭开这个谜底,又必须从文化与权力的逻辑关系上去寻找答案。按照西方现代身体政治学、身体社会学或者身体文化学的观点,人类社会一直处于“身体社会化”和“社会身体化”的境域当中。身体具有二重性,即自然的身体和社会的身体。但是,自然的身体在人类的历史文明行程中逐渐被塑造为了社会的身体。在这一塑造的过程中,身体与权力的关系尤为密切,权力成了规训和塑造身体的主宰;权力使自然的身体成为了文化的身体、政治的身体,乃至被操控、被使用、被观看的消费的身体等等。用福柯的话来说,“权力关系总是在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发出某些信号。”[3]72显然,谢青鸥的身体已经不是自然的身体,而是被权力,或者如小说叙事中所说的“阶级意识”所塑造的,亦即被控制、被干预、被打上标记的社会的身体。因此,这个身体不属于她,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同时也是她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的现实处境。
“出身资产阶级家庭”,这就是权力给谢青鸥的身体打上的文化标记;她的这具身体与“出身无产阶级家庭”的汪国华的身体的结合,自始自终笼罩在“无产阶级政治”威权的巨大阴影之下。对谢而言,在当时的权力语境下,她似乎是幸运的——她为自己的身体找到了幸运的“处置之所”。可是时过境迁,权力语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谢青鸥的“阶级出身”又重新被权力所解释所形塑。于是,她的身体不仅不再卑下,反倒成为一种“时代的优势”。相形之下,其配偶汪国华的身体却在丧失“阶级身份优越感”的同时,兼之文凭较低,与权力政治要求的“现代化”各项指标相去甚远,因而只能在学校当一名毫无“社会地位”可言的电影放映员。这种社会落差所爆发的“反制力”,终于在谢青鸥升任为文化馆舞蹈队长后,导致成了不可逆转的婚姻裂变。
从“客观上”来说,谢青鸥身体的俊美和汪国华身体的健美,作为自然的人、自然的身体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变化了的是权力语境,或者说是权力对身体形塑的需要及解释发生了变化。尽管小说用大量篇幅去叙述和描写汪国华面对政治语境的荒诞变化。比如,他如何白手起家组建起了教工足球队,又如何因训练有方而深受球员们的尊敬与爱戴等等。总之,汪国华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挽回身体在权力重新形塑和解释中的劣势,但是,其自然身体在强大的权力面前终究是无奈和弱小的。作者明显是为了抚慰汪国华和读者,在小说叙事的结尾,让他最终在与实力强大的对手的对抗中巧妙地赢得胜利,进而使其重新找回了所谓的自尊和自信等等,也就是将劣势转变为了某种“优势”。但是,无论对谢青鸥,还是对汪国华而言,其始终难以逃脱权力对身体的监控和形塑,这一点却是无可置疑的。
三、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双重规训下的身体
到了写作《透支时代》,莫怀戚无疑已经真正进入了自觉意义的“文学身体学”写作阶段。但是,对“新时期”以前身体与权力的逻辑关系,他依然保持着持续的关注状态。在这篇小说当中,叙事的主题稍微有了一些变化。可以看出他对身体作为生产工具的历史境遇,以及身体被“解放以后”又不由自主跌入消费主义的历史境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按照福柯的解释,“身体遭受惩罚的历史、身体被纳入生产计划和生产目的的历史,以及权力将身体作为驯服的生产工具的历史,即整个生产主义的历史”已经逐步让位于“身体处于消费主义的历史”。这一历史时期的显著特征是:权力格局已然发生了变化,“政治”似乎悄然隐匿,它换了一个消费主义的马甲。身体依然在它的操纵之下;身体的历史面貌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们面临的是“身体成了消费对象的历史;是身体受到赞美、欣赏和把玩的历史。身体从生产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不可自制地陷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4]38。现在我们来看,身体是如何在逃离了生产主义的控制之后,却被一种新的权力机制,即消费主义的温情脉脉所控制的——这样一幅世俗风情图画。
《透支时代》当中,男一号泰阳原本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妻子王静漂亮而且颇具才华。与谢青鸥相似,王静的自然身体形貌和社会身体优势相当突出。在告别革命伦理或曰人民伦理对女性自然身体的敌视或刻意遮蔽之后,王静的自然身体得到了消费主义的承认与欣赏。小说的身体叙事意图十分明确:作为知性妇女,王静的美非同一般:
王静很美。这样美丽的画家是不多的。她眉毛漆黑,面色红润,瞳仁如水晶,牙齿像玉石;加之她面若满月,耳垂敦厚,所以路边那些专业的和业余的术士和星相学家常常追着她走,坚持免费给她看相。他们众口一词地说她“貌好,相也好”。
即使这样的身体描写仍然潜隐着权力意志的“知识话语”和“真理话语”意涵,但毕竟进步到了不再敌视或遮蔽女性身体的“正常审美”时代。然而,吊诡的是,情人吴越的身体远不如妻子王静,可是从消费主义的多元化审美,特别是多口味需求着眼,吴越身体的优势居然为王静所不如——按照泰阳的说法:“这个我不应该爱上的女人……但是她迷人。”面对吴越的身体,泰阳感叹不已:“ 问题就在这里:迷人的不一定美丽,美丽的不一定迷人。”这样的感慨和觉悟,只有在消费主义时代才有可能大胆地生发出来;而在生产主义时代,女人身体的美丽,如果再加上迷人,就只能成为革命伦理敌视或者规训的意识形态靶子。“革命者”或者“革命群众”即使对女人身体的美丽、迷人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只能在私下里偷偷感慨,更多时候只能默默地埋藏在心里。否则就是思想情趣不健康。
耐人寻味的是:沉醉于消费主义中的泰阳,面对这两个女性的身体,其注释是:“我爱王静,但我需要吴越。”和泰阳一样,吴越也爱自己的丈夫。不过泰阳明显能感觉到:“我显然不如她的丈夫重要,我只是那个男人的补充。”就这样,双方的身体“行动”起来,在你的“需要”和我的“补充”中,他们开始积极地卖力地注释和创作自己。在生产主义与消费主义这两个“不同”的时代,始终处于权力文化“求真意志”支配和形塑中的男男女女,他们的身体表现有何区别呢?莫怀戚借泰阳父亲的口揭示道:
以前是男人要疯,只是女人不敢疯,所以疯不起来;现在是女人也敢疯了,还更疯,所以现在要疯起来了。要疯得血淋淋的,每个人都伤得很重才算事。
真可谓入木三分,准确而深刻,但有点恐怖。这所谓的“男人要疯”或者“女人也敢疯”等等,其实说的是世俗的肉体欲望像潘朵拉的盒子完全被打开了。而且,女人的肉体欲望因为禁锢得实在是太久,其爆发力就非同寻常,所以伤得也非常厉害。值得注意的是,泰阳父亲关于身体的这番高论,是站在革命伦理的立场而生发的。这个父亲是个“老革命”,但是在身体问题上他并不僵化保守,也不独断专行,对女性自然身体之美的“自发性”赏析功能自来就没有丧失。这个“老革命”虽然在其精神深处已经被革命伦理所完全占领,但是他的肉体却游离于革命伦理之外。或者说,他非常清楚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应该用革命伦理来批判“肉体享乐”,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可以堂堂正正地享用革命“分配”给他的具有肉体享乐性质的“胜利成果”。不过,与儿子泰阳不同,他一方面暗暗享受着权力话语带给他的“消费主义”好处。另一方面却始终保持着对消费主义的警惕——他常常以调侃的方式去玩味和批判消费主义时代男男女女的身体,以及灵魂。这是一个眼光很毒的杰出的“身体审视专家”。他时刻以权力文化的全能主义眼光来打量和洞悉各种各样的身体。比如,他说:“瞄一眼我就能看出这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种本领来自于“他管了几十年的人”;又比如,他对什么是“交际花”的洞察明显比儿子高明:“我儿莫以为交际花就是电影里那珠光宝气的样子。真正的交际花是不妖精的,还有些人格上的魅力,不一定很漂亮,但很能往男人心里钻。”因此,迷人的女人身体以及内在气息,在革命伦理,抑或人民伦理看来,是相当有害和相当危险的——这样的身体在任何时期都应该是权力监控和防范的对象。因为这种身体对“真理”和“秩序”来说太具有挑战性和杀伤力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当中,莫怀戚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从容和淡定,讲述了一个比谢青鸥的身体更加具有荒诞性和悲剧性的故事:泰阳对母亲当年处置“自己身体”的方式,以及父亲挟权力文化之威仪“合理合法”接管母亲身体的历史情形,一直有一种难言之隐。“当年我妈是被组织劝说嫁给我爹的。我妈不敢说那人太丑,只说年龄相差太大。组织说那个男人是为了革命事业耽误了个人问题。那时管婚姻叫个人问题。”诡异的是,泰阳披露说:“其实组织并没强迫我妈,是我妈自己想加入组织。”在本质上,这种处置“自己身体”的方式和对方“合理合法”接管女性身体的情形,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当中,是权力文化所导演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时尚和身体处置法则。
问题是,女性的这种处置“自己身体”的方式,竟然成了当年许多“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的女性的难言之隐和终身遗恨。请看小说叙事中对母亲内心隐秘的揭示——
擦肩而过,我本打算把头别过一边。伤感的矜持让我不相信这个城市有任何的浪漫。但在转过头之前,我还是不由自主地看了她的脸一眼。只一眼。
我妈嫁了我爸后就加入了组织,而且调了好工作。但是她闷闷不乐,问她为什么不快乐,她总是说没有不快乐。几年前她生了场病,以为自己要死。她居然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其实一个女人不喜欢男人又老又丑,是正当的想法。”
“其实一个女人不喜欢男人又老又丑,是正当的想法。”即使这个男人笼罩着“革命”的光环,被上了权力的铠甲,他还是个“又老又丑”的男人!几十年来,“我妈”就在这种矛盾中痛苦地挣扎而无法解脱。具有深刻悲剧意味的是:“我妈”这种几乎是出自女性本能的“觉悟”,是在“闷闷不乐”地隐忍几十年,人生已入老境之际,才如回光返照似的吐露出来的。权力文化形塑着每一个凡俗的身体,并且在实质上对其拥有至高无上的处置权,但通常它并不直接出面,而是以女性“自己”处置“自己身体”的方式,把它那种蔑视和规训身体的意图深深隐藏起来。与小说《都有一块绿茵》不同,莫怀戚在《透支时代》当中,通过自觉而积极的身体叙事揭示出了“合情合理”的世俗社会中身体支配的历史真相和权力法则:权力文化一直是通过规训或曰“改造思想”的路径,从而达到改造身体,使之成为一个个被驯服的身体,并且使之自觉交付自己的身体。归根究底,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在规训手段上尽管有很大的差异,但在本质上却是完全一样的。
四、沦陷于民族主义暴力美学中的女性身体
在告别了旧意识形态敌视身体和明目张胆地操控身体,使之改造成为“和革命目的性”的“政治的身体”、“劳动的身体”之后,世俗世界和文学世界对身体的热情急剧升温。“身体已然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自恋话题。身体文化以视觉愉悦与快感体验为主,注重感官刺激和快感体验,使性和暴力成为身体文化的重要主题。”[5]在90年代以后的小说叙事当中,莫怀戚在描述消费时代权力文化特征及本质时,对这种混杂着性和暴力的感官刺激和快感体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揭示。需要注意的是,女性身体沦陷于这种新型的权力文化及其所建构的暴力美学当中,对此,他不仅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和展示,而且还对高扬在这种暴力美学之上的极端民族主义正义感和合理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嘲讽和批判。对于一个在现代化艰难转型过程中曾经惨遭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凌虐的民族来说,这样的民族暴力复仇心态以及由此建立在性征服心理基点上的身体暴力美学观念,无疑是真实的、愉悦的和具有普遍意义的,同时也是危险的和可悲的。
具体到这一时期的身体写作实践中,以《陪都就事》和《六弦的大圣堂》为代表,最具有文化认知的标本意义。男权主义政治文化意图由于裹上了民族主义正义性、合理性的面纱,这样一来,其对女性身体及灵魂的凌虐似乎就不再是野蛮和罪孽了。这种心态及其理论与一些西马理论家,如詹明信等人的暴力美学理念不谋而合。在《陪都就事》这部以推理小说或侦破小说面目出现的身体叙事作品当中,由于莫怀戚深谙中国人,特别是重庆人的地域文化性格及世俗文化心态,因此,在诡异多端、扑朔迷离的叙事延展当中,将“银娘”号旅游船暴力复仇事件的策划者和实施者霍沧粟的心理发生、发展以及成长、壮大的过程,描述和刻画得淋漓尽致,一览无余。可以说,霍沧粟这个文学形象的塑造不仅是相当成功的,而且也是具有“开创性”的和不可多得的。在此之前,我们在别的小说家的笔下还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小说人物出现。
小说叙事的背景线索是:霍沧粟的母亲在民国三十七年,即1946年,被驻扎在陪都重庆的美国大兵所强奸。这个身体暴力事件与发生在北平的“沈崇事件”一样,迅速注入了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权力文化内涵。母亲的身体在那时已经不再是她自己的身体,她已经成为了政治的身体、民族的身体——成为了负载着复杂丰厚的社会文化内涵的意识形态化的身体。毫无疑问,这个意识形态化的身体是被美国大兵和自己的同胞合力想像并塑造的。因此,母亲的身体在当时既具有遭受凌辱的民族悲剧的文化特征,同时又具有控诉和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特征——总之,这个身体是正面的,具有“政治正确性”特征。不过,这个身体是不属于她自己的,而是成为了负载着民族主义政治内涵的一个身体符号。
因此,历史文化和民族心态的种种复杂和吊诡也正在于此。“解放以后”母亲曾经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玷污的身体,却陡然从正面形象变成了反面形象,成为了中国人的“耻辱的象征”。于是,身体暴力叙事的施虐方由美国大兵转为具有民族主义正义感的同胞。不仅母亲供职学校的男男女女每日饶有兴致地争相传播这个发生在“解放前”的“大丑闻”,“更有甚者,连在‘官茅厕’里挑粪的粪夫,也要来看‘美国大兵究竟搞了哪个婆娘’?!这个婆娘到底长得是啥样子?”“这个婆娘的身体何以能够引起美国大兵强烈的兴趣?”等等。尤为恐怖的是,这些知识民众和非知识民众的暴力施虐心态如出一辙——在这种通过性和暴力的偷窥和想像当中,民众获得了普遍的感官刺激和心理快感满足。由此可见,民众建立在革命伦理或人民伦理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暴力美学理念,其荒诞、丑陋以及无耻下流暴露无遗。且看这两种民众的隐私窥探和快感体验性评论:其一,“美国大兵如狼似虎,她哪里跑得脱?”其二,“母狗不摆尾,公狗不爬背。”理由是“想找个美国如意郎君托付终身,别人却只将你当鸡看。”尽管也有女权主义者在学校为之打抱不平,然而,终究劳而无功,根本无法抵挡革命伦理或人民伦理的汹涌世俗浪潮。莫怀戚饶有深意地感喟:
她实际上是被自己的同胞逼得走投无路。……我们这个民族,自己人待自己人怎么总是那么苛刻、那凶狠呢?
然而,依照詹明信等人的暴力美学理念,身体从来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身体自始自终深刻着理论暴力的烙印。他们认为,由此身体才获得了意义,即具有了作为前瞻性革命力量的理论质态。在革命进程当中,身体只有作为针对资本主义的颠覆性破坏力量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同样,性、暴力以及感官刺激、快感体验等等,只有将其理解为一种革命政治行为时,身体才因之赋予了唯物和辩证的历史高度。在小说叙事中,莫怀戚表达了对革命伦理或人民伦理意识形态的不适和质疑。在他看来,这种身体政治学和身体美学的确是值得批判和整肃的。
霍沧粟进厂时还不是共青团员,但仍然被团委召集学习。就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这位新徒工们需要仰起头来看的女书记。就只看了一眼,那种要“干掉她”的念头便从天而降。
不仅如此,霍沧粟寝室墙上还贴着一张美国女影星的剧照。姚云梅第一次看到这张图片时压根就想不到其中所蕴含着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政治玄机。小说写道:“已经初具政治素养的女团委书记永远也不知道,那个坦胸露乳的美国女人根本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思想’,而是她本人的一个‘参照物’—— 霍沧粟在干她时,眼睛盯着那美国女人,感觉上就成了‘干’那个洋人儿了。霍沧粟自己都说不出这‘美感’来自何处。”这难道不是诡异之极吗?!
五、个人化“身体想像”背后的全民身体施虐狂欢
詹明信等人的暴力美学理论在霍沧粟的身体暴力实践中得到了审美贯彻和执行;女团委书记的身体成为了他战胜“帝国主义”、为国家民族,也为母亲和他自己报仇雪恨的替代品和参照物。女团委书记本来是专门来做后进青年霍沧粟的思想转化工作的,却万万没有想到她的身体反倒被偷放入茶水里的药物麻翻——
当她突然反应过来,本能地开始反抗时,她感到无能为力:既喊不出声,又动弹不了。他双手抱住她的头,拇指压住她耳后什么地方,慢慢地,冷冷地将她放倒了。鲜血糊满了她的大腿根,染红了床单。这第一次会出这么多血,是她想不到的。这说明了他的粗鲁:岂止是“占有”,简直是屠杀。其时不知怎的下起了雨。仲秋已过,居然还有这样的骤雨,也是奇怪。腥湿的风吹开了窗户,扑进室内,墙上的洋女发出呻吟,同床上一个东方女书记的呻吟混为一谈。
这段关于身体暴力的实践性描述意义重大。尽管与全能主义政治盛行年代革命伦理的大规模实践中,全民参与的“身体想像”与身体施虐狂欢情景完全不同,霍沧粟的行为仅只具有非组织的个人暴力实践的非理性特点。但是,莫怀戚的这段具有悲喜甚至闹剧色彩的身体叙事,其独到性和深刻性却是毋容置疑的。如果说,霍沧粟在“干掉”女团委书记的“身体想像”当中承载了复杂丰厚的民族的、国家的、革命的乃至人民的群体性暴力文化内涵的话,那么,这样一种源远流长的关于女性身体的意识形态想像,却无疑反映了具有普遍意义和典型意义的主流政治文化心理特性,同时也反映了隐伏在底层民众俗世心理中的真实文化情状。与过去年代“身体内部的阶级斗争”的叙事方略不太相同,“身体内部的民族斗争”在今天已然成为了消费主义时代叙事的强大动因——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的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征用,作为工具或者作为商品。表面上看,仿佛是小说家在随心所欲地征用她们的身体,实际上,真正的征用者和施暴者,还是那个隐伏着却又无处不在的权力体系。
“干掉女团委书记”这一叙事逻辑具有十分芜杂诡异的政治反讽和解构意味。本来是一桩蓄谋已久、彻头彻尾的个人犯罪行为,但由于施暴者意识深处充满民族主义身体复仇的正义感。即,一种被意识形态暗中鼓励的“身体政治”行为,因此,这种身体暴力就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具有文化实质意义的潜在的群体行为。最深刻同时也最有意思的身体叙事及文化解析发生在施暴后的第二天。在此,我们必须将霍沧粟的身体暴力叙事与鲁迅笔下的阿Q联系起来审视,才有可能洞悉革命伦理的奥妙。霍沧粟的这种明显的个人犯罪行为是怎样变为“正义”行为的呢?在《和平时代》里,莫怀戚从文化心理视角作了微妙的剖析:
实话说,犯罪,或者干不道德的事,有两个档次。低档的也就是本能所驱,高档的则有观念做依托。一个留学生要干的事,都是“想好了的”;当我们说“想好了的”的时候,说的就是观念了。
有观念作为强大的依托,一切都顺理成章,毋庸置疑。就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霍沧粟不仅终结了他自己以及民族耻辱的历史,而且通过这种“暴力革命”方式,他,及他的族群从这种来自性和身体的暴力占有、征服当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刺激和快感体验。然而,就如同政治家和思想家常常忧虑的那样——真正的难题不在于暴力革命本身,而是“革命后的第二天”。 霍沧粟在“革命成功” 之后都做了些什么呢?这无疑是需要我们认真寻究的。“身体革命”之后的第二天,女团委书记充分体现出一个青年政治工作者的良好素质。她执著地想要搞明白,由霍沧粟发起的这场突如其来的“身体革命”的真正动因是什么?她原以为自己的政治地位决定自己是天然 “正确”的,殊不知盘踞在“政治正确”制高点上的不是她,而是发动“身体革命”的施暴者和后进青年霍沧粟!在霍沧粟“政治正确”逻辑的一番猛烈的击打之下——
她渐渐明白了,寝室里那张美国影星照片……那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如果一定要上纲,倒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她想明白了:他在心灵上干的是那个美国影星,只不过是借了她这个仿佛洋女人的中国女人的肉体……一时之间心绪复杂,无与伦比,她发出一声情不自禁的长叹。一个团委书记会如此这般地长叹,连她自己也没想到。
“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无疑蕴含着“共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政治文化内涵,以及解放人类的崇高使命感。于是,女团委书记自觉提高了思想认识:自己的身体能被这伟大的“革命”进程所征用,从而汇入这具有崇高审美意义的历史潮流。因此,“他的民族正义感让她十分感动:‘能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实在是不多。’她真诚地说,‘但你要能控制情绪,否则对身体不好’。”当他提出要和她结婚时,她不仅深深地表示理解,而且感动得一塌糊涂。可是,“她永远不知道,他真正动机是:这样就可以使他“一直将‘美国女人’干下去!”
显然,“身体革命”之后的第二天,“身体革命家”霍沧粟在与女团委书记的意识形态话语互动中达成了一致。重要的是,他在理直气壮阐释自己的“身体暴力革命”的理论体系时,同时也完成了他和她的“肉体意识形态共同体”的文化建构。更加重要的是,他的“革命意志”似乎没有松弛;他怀抱宏大的“肉体乌托邦”理想,决心“继续革命”:除了要实现“革命的近期目标”,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民族革命宿敌美国大兵老施鲁德的儿子戴维之外,更加弘毅的“革命的远景目标”是:要“干掉”各种各样的洋女人!
叙事中,霍沧粟的下一个首选目标是:“洋鸡”安菲迪。此时,霍沧粟已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已经成为他妻子的女团委书记,总是心情复杂地在赞美他:“每次放假回来,都比上次年轻。”她压根就不知道,她的老公在校园里瞄上了一个女外教——美国女郎安菲迪。在小说的身体叙事中,霍沧粟既充满性的想像和激动,同时又充满民族主义的审美批判精神——
她短发齐耳,灰蓝的眼珠一片单纯,皮肤白晰,汗毛茂密,女性的曲线比东方人夸张——由于手上吃力,身体略倾,就更夸张。她着长袖衫,着肥大的短裤,都说不准算什么颜色。总之那种随便不是中国人能扮演的。她滚圆的膝盖,在他看来,就像屁股。
“霍沧粟盯着她突然一阵发怔,全身失去知觉,周围的声音也消失了。在这一怔里,一个已经沉睡到近乎死亡的东西苏醒过来。”显然,发怔以及全身失去知觉,是因为这个美国女人的性感冲击力所致;那个“苏醒过来”的东西,就是民族主义的革命暴力意志。在民族主义“政治正确”的文化审美眼光里,任何一个洋女人,除了她们那种撩人的性吸引力能充分地激发民族主义者身体复仇的强烈欲望之外,无论从自然审美还是社会审美意义上,她们都不是正常的、科学的、良善的和正确的——“他嗅着她的气息,这气息很浓,而且不同于任何中国女人。这或者可称为食肉动物的膻腥之气”——这段心理描述充分说明:在“肉体暴力革命者” 霍沧粟眼里,洋女人,乃至所有的洋人在进化的阶段上,还处于“食肉动物”的阶段。霍沧粟将其定位于“洋鸡”,即可见他的种族主义政治文化立场和审美态度是如此的鲜明、如此的坚定不移。
[1] 莫怀戚长篇小说《经典关系》研讨会综述[J].当代文学研究,2002,(5).
[2] 李敬敏.读莫怀戚[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0,(4).
[3] 福柯.规训与惩罚[M].三联书店,2012.
[4] 汪民安.尼采与身体[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 金丹元.后现代消费语境下的当代身体文化[J].中州学刊,2006,(6).
[责任编辑:朱丕智]
“The Problem of the Novel should be Started from the Body Problem”—on “Body Narrative” of Mo Huai Qi’ Novels
Zhang Yuren
(College of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A large amount of body narrative appeared in the Mo HuaiQi novels, started in the 90s. Why his previous novels there are very few “bodily presence”? Why did he suddenly show strong interest in writing to the body? What does he want to achieve a purpose through the body writing? What means to him of a lot of body narrative in the novel?The next question is: After that he was so wrapped up in the body writing, which would make him and his novels into a consumerism trap and cannot extricate him?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such question, this will enable us to have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for this specific style of novelist.
Mo Huaiqi; body narrative; no body writing; violence aesthetics; body imagination
2015-12-08
张育仁(1954—),男,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I206.7
A
1673—0429(2016)01—005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