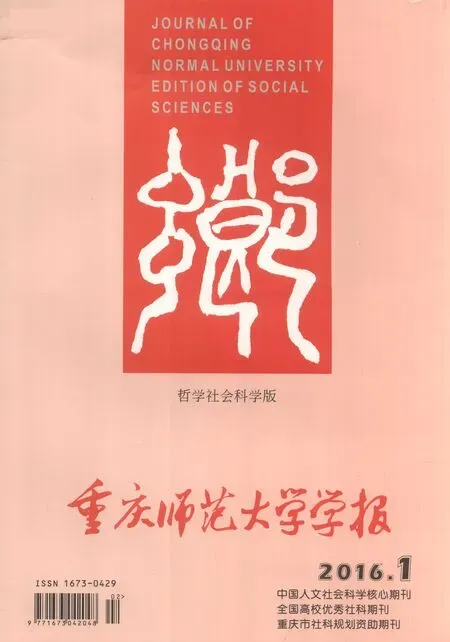读书、议政思潮与晋初政治
赵 昆 生 陈 晓 倩 谭 杰 妮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0047)
读书、议政思潮与晋初政治
赵 昆 生 陈 晓 倩 谭 杰 妮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0047)
自魏九品中正制实行以来,门阀世族凭借家世祖荫,世世代代入朝做官。在入仕从政、游玩享乐之余,门阀世族阶层也将读书论道、著书谈玄作为家学和特长发扬光大,出现了一个将谈论学术与评价政治相结合的思潮。魏晋更替之际,门阀世族又将此思潮引向表达自己政治态度和选边站队的方向。西晋建立后,经武帝大力提倡和引导,择善从良,百官大臣们建言献策,著书立说,为新王朝奉献自己的政治智慧和精神财富,出现了与西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媲美的太康之治。
读书;议政思潮;晋初政治;太康之治
自司马氏父子掌控曹魏政权以来,不断强化中央集权,政治统治趋于稳定。以九品中正制为主的官吏选拔制度有效地保护了门阀世族世代垄断政权、坐享高官厚禄的特权。门阀世族通过读经习文,撰文上疏,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为魏晋更替出谋献策,从而出现了具有这个时代特有的读经习文、议政献策思潮。这个出现在门阀世族阶层和官僚士大夫群体中的阶段性很强的社会思潮,影响着魏晋更替的进程和司马氏政权统治政治的表现方式,也表现出了这个时期门阀世族阶层的社会生活状态。
一
自魏文帝时期九品中正制确立为统治集团的官吏选拔制度以来,门阀世族阶层凭该制度世世代代占据高位。九品中正制运行到魏晋更替之际,已沦为保障门阀世族政治特权的工具。魏末吏部吏刘寔在《崇让论》中写道:“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举之。……观在官之人,政绩无闻,自非势家之子,率多因资次而进也。”[1]卷41《刘寔列传》晋朝初建时,议郎段灼上表称:“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1]卷39《王沈传》至此,晋统治集团内权力分布与构成设计已完成,门阀世族子弟在祖先权势的庇荫下,无须立功于沙场,也不必建树于治国安邦,就可以纵横官场。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西汉以来形成且在东汉末年战乱中经过战争淘汰仍然保存下来的军阀官僚集团势力,大肆扩张,羽毛已丰,成为统治阶级中上层势力的合法来源。“(孙)楚,骠骑将军资之孙,南阳太守宏之子。乡人王济,豪俊公子,为本州大中正。访问宏为乡里品状,济曰:‘此人非乡评所能名,吾自状之。’曰:‘天才英特,亮拔不群。’仕至冯翊太守。”[2]《言语》九品中正制又成为和平年代门阀世族阶层历世不衰、权位永固的支撑点。
因此,魏晋以来,门阀世族子弟悠闲自得,或饮酒服药。何晏称:“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2]《言语》阮籍、嵇康等“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2]《任诞》。“诸阮皆能饮酒,(阮)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2]《任诞》或游玩于山水之间,常常“诸名士共至洛水戏”[2]《言语》。宴饮游玩之间,读经、习文、议论时事遂成为一种弥漫于门阀世族阶层中的时尚,渐渐固定为一种家风和门风。如晋初重臣杜预,“祖畿,魏尚书仆射。父恕幽州刺史。预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1]卷34《杜预列传》这些家世背景为杜预的入仕执政提供了充足的知识和思想准备。做官的闲暇之余,“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1]卷34《杜预列传》专治《春秋》,成为家学,从事文化传承活动。裴秀,“祖茂,汉尚书令。父潜,魏尚书令。秀少好学,有风操,八岁能属文。”[1]卷35《裴秀列传》其也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和家风浸润,故仕途坦荡,官至尚书令等,同时还著书立说,“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1]卷35《裴秀列传》晋初建时的骠骑大将军录尚书事王沈,祖柔,汉匈奴中郎将。父机,魏东郡太守。王沈少时父亲去世,依从叔魏司空王昶生活。家族背景深厚,文化氛围浓重,使得王沈不仅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养成读书不倦的习惯,而且可以凭籍祖荫,长大后从容地进入政权的核心。
魏晋之际,君权易姓,但并不影响门阀世族阶层薪火相传,进入政权。晋武帝时的侍中、中书监荀勖,汉司空荀爽的曾孙,成年后,入仕担任曹爽掾,曹爽被诛后,“门生故吏无敢往者,勖独临赴,众乃从之。”[1]卷39《荀勖列传》因荀勖有治世之才,又无曹爽死党之嫌,改换门庭,迅速成为司马氏的红人。这些历经改朝换代的门阀世族阶层人物,如:冯紞,“少博谈经史,识悟机辩”;[1]卷39《冯紞列传》刘颂,“力能辨物理”;[1]卷46《刘颂列传》高光,“少习家业,明练刑理”,[1]卷41《高光列传》均出身名门,入仕有九品中正制的制度保障。他们可以凭自己对政治形势的正确判断和自己的喜好意愿,从容地选择入仕时间、依靠对象和从政路径。可以自信、大胆甚至狂妄的评论时事,褒贬人物,提出自己的政治理念。
门阀世族虽不愁仕途,但置身于统治集团的斗争之中,稍有不慎,不仅自己面临灭顶之灾,整个家族也要受到株连,“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1]卷49《阮籍列传》因此,在曹氏与司马氏两大政治势力中博弈的门阀世族人物总是要尽最大程度发挥自己的才能,既要保证自己的官阶名位,又要力争在政治斗争中拔得头筹,为整个家族谋得利益。 “世为名族”的刘颂,在曹魏政权中,“察孝廉,举秀才,皆不就。文帝辟为相府掾,奉使于蜀。”[1](卷46刘颂列传)晋建立后,出任河内太守,又专任淮南相。“在官严整,甚有政绩。……百姓歌其平惠。”[1](卷46刘颂列传)又连篇累牍地上疏武帝,发表自己关于“封建戚属”“分官任职”“宜复肉刑”等若干方面的建议。一方面治世有方,深得百姓爱戴和君主的赞许,另一方面不断地表达自己对司马氏政权的关心和忠诚,夯实自己在新政权中的基础。
读经习文是门阀世族的家学和家风。汉太尉皇甫嵩之孙皇甫谧,“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从小过继给叔父,叔田任氏见皇甫谧现状,痛心地教育他:“《孝经》云:三牲之养,犹为不孝。汝今年余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无以慰我。……修身笃学,自汝得之,于我何有。”皇甫谧始洗心革面,“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沉静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1]卷51《皇甫谧列传》后经多次“举孝廉”“相国辟”“下诏敦逼”皇甫谧入仕,皇甫谧“皆不就”。但其却关心统治走向,著书立说,阐述政治见解,有《礼乎》《真经》《玄守论》《事劝论》等著述面世。类似皇甫谧这样的门阀世族代表人物,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虽没有直接担任官职,效忠于当下政权,但仍以另一种方式参与西晋统治。他们身在政权之外,心在统治之中,以著书立说的方式影响着君主和百官的思想意识,教育家族子弟,为家族成员入仕从政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行为训练。他们这种著书、进言、立教的行为方式,构成了其时门阀世族阶层社会活动和政治参与的一道风景线。
随着时间推移,在这些物质生活优越、仕途得以保障的门阀世族的子孙后代中,渐渐游离出一个悠闲自在的群体,将读经习文当作修闲养生,限制在个人喜好的情趣范围内。“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1](卷35裴秀列传)老庄道家学说正好为文人士大夫们的放荡和怪异行为提供了某些抽象的玄理上的解释和说教,于是,研学《老子》《庄子》《周易》等成为门阀世族家学的重要内容和时尚。魏冀州刺史裴徽之子裴楷,“明悟有识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1](卷35裴楷列传)晋初重臣王浑之子王济,“力有逸才,……善《易》及《庄》《老》,文词俊茂。”[1](卷42王济列传)《老》《庄》《易》等著作文句表达晦涩,文字理解歧义,内容含蓄抽象,都成为门阀世族子弟卖弄虚玄、故作高深的东西,于是,“时重《庄》《老》而轻经史。”[1](卷50庾峻列传)不靠熟读儒家经典取得入仕资格,不以理政治世显示官吏的才能品德,而是谈玄议论。“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门阀世族人物,不论入仕或者暂时居家,皆积极参与谈玄论道。学术与政治,人生与社会,文学与自然,等等,都网罗在谈论之中。统治风云、政权得失是谈论的中心话题,而道家的玄理学说将话题引向抽象、深邃,从哲学的角度予以思考和解答。关于用人的标准──才、性问题,“钟会撰《四本论》”,“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2](以上皆引自《文学》)对才性同合异离的认知,实际上是魏晋以来各级中正官在考察士人、评定品状与吏部任免官员时如何确定一个共同标准的讨论。具体的行为上的量化标准没有办法认定,或者说不可能取得不同部门、不同群体的共同认知,因而,以官吏主选官员为代表,展开了候补官员选拔标准的大讨论,试图从高度抽象的理论高度,达到认识上的一致性。这些看起来是抽象的哲学问题,实际上为的是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
这个时期门阀世族子弟的处世原则、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突破了传统文人士大夫们所遵循的以儒家道德规范的约束,肆无忌惮,放荡纵欲。阮籍为首的名士正是这个时代离经叛道的代表。阮籍的父亲,阮瑀担任过魏的丞相掾,“知名于世”。阮籍成人后,“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1](卷19阮籍列传)优裕的家庭生活环境,使得读书习文不再是改变自己、入仕显达之迫,而是顺其情趣、满足个人喜好的行为方式之一。道家倡导的顺其自然、随性而安的理念成为阮籍的人生观,形成了以阮籍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特有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他们“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1](卷19阮籍列传)。世族高门人物不仅有入仕的制度保障,而且还有选择入仕时间、地点和官阶高低的自由。即使做官的方式也可以随意为之。“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1]卷19阮籍列传)以阮籍为代表,表现了一个时代中权势阶层的众生相。他们不遵守常规的社会秩序规定,也不受世俗的生活习俗、礼仪的羁绊,这是一个有着时代政治权利、学术文化诸方面巨大话语权的阶层。
荒诞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一定催生出怪异的人生理解和生命表达。阮籍侄儿阮咸,“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盆盛酒……时有群豕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1](卷19阮籍列传)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3](卷21嵇康传)“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1](卷49嵇康列传)著有《养生论》《太师箴》《声无哀乐论》等。精读《老子》《庄子》,“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2](《文学》)嵇康等在研读老、庄的过程中,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处世行为,更影响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和价值取向,在魏晋更替的大变化时代,他们以各种方式议政论道、谈古说今,出现了一个不小的思潮。
二
公元249年的高平陵事件,司马懿一举灭掉了以曹爽为核心的曹魏中央集团,实际掌控曹魏大权。“司马氏则当文帝、明帝国势方隆之日,猝遇幼主嗣位,得窃威权。其时中外臣工,尚皆魏帝所用之人。内有张缉、苏铄、乐敦、刘贤等,伺隙相图;外有王陵、毌丘俭、诸葛诞等,相继起兵,声讨司马氏。”[4](“魏晋禅代不同”条)高平陵事件后,人们开始发现,司马氏父子诛灭曹爽集团,并不只是与曹爽个人之间辅佐君主大权的争夺,而是权力世袭,开始了魏晋更替的渐变历程。百官大臣在认识司马氏父子专权真实面目的过程中,也确定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进而采取自认为最合理的行为方式。镇南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前将军文钦等上表魏帝,称:“故相国懿,匡辅魏室,历事忠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托之任。懿戮力尽节,以宁华夏。……齐王以懿有辅己大功,故遂使师承统懿业,委以大事。而师以盛年在职,无疾托病,坐拥强兵,无有臣礼。”列举司马氏十一项大罪,并宣誓自己的立场,说:“臣等先人皆随从太祖武皇帝征讨凶暴,获成大功。”对于曹魏政权,愿意“吞炭漆身,死而不恨也”。文钦在给另一位将领郭淮的信中说道:“太傅既亡,然其子师继承父业,肆其虐暴……包藏祸心,遂至篡弑。此可忍也。孰不可忍?”[3](以上皆引卷28毌丘俭传)《魏末传》记载:“贾充与(诸葛)诞相见,谈说时事。”大臣们偶遇,议政论道也是主要话题。司马氏的死党贾充问大将诸葛诞:“洛中诸贤,皆愿禅代,君所知也。君以为云何?”明确地告之,在都城洛阳,朝中权贵已表达了拥戴司马氏称帝的意愿。诸葛诞斥责贾充:“世受魏恩,如何负国,欲以魏室输人乎?非吾所忍闻。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3](以上皆引卷28诸葛诞传)即使经过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等父子三人苦心经营,朝中权臣中仍不乏从语言抨击到起兵反抗的大臣。
更多朝廷在位者选择站在司马氏父子一边,为其改朝换代建言献策。何曾建言司马昭:“公方以孝治下。”[1](卷33何曾列传)面对阮籍等门阀世族代表人物放荡不拘的生活方式和随心所欲的处世行为,效忠于司马氏的心腹大臣纷纷上书,要求以儒家伦理为衡量尺度,制止、严惩阮籍等荒诞行为。于是,司马昭“命荀勖、贾充、裴秀等分定礼仪律令,皆先咨郑冲,然后施行也”[2](《政事》),开始整治违背礼法的当世名人。“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在司马昭时担任选曹郎,“举(嵇)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3](卷21嵇康传)挑战司马氏的礼乐底线,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魏晋之际,清谈之风盛。“清谈起于魏正始中……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4](“六朝清谈之习”条)谈玄论道成为其时门阀世族子弟与官僚士大夫的一种时尚的群体集会。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2](《文学》)士大夫们通过清谈,宣扬自己的主张,在争论中完善自己的见解,家世门庭的社会影响更显突出。《文章叙录》载:“(何)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2](《文学》)司马氏当政时,“刺史王沈集诸参佐,盛论距吴之策。”[1](卷42唐彬列传)在不同的场所,官僚士大夫们在谈论中寻找政治观点、意愿的契合,成为政治知音,组建统治集团内的势力派别,互相提携,互相支持。所以,清谈表现了魏晋时期统治集团中的另一种政治活动形式。
在魏晋王朝更替过程中,对曹魏及其以前的王朝政治遗产的批判、否定和修正从来没有停止过。官僚士大夫们在鼓吹司马氏祖孙三代英明的同时,入木三分地剖析曹魏以来所实施的主要制度举措的各种弊端,以历史上的制度规定和现实中的消极影响为参照,批判否定,争先恐后地提出自以为最为合理的整改方案。其中,争议、否定最多的是九品中正制。助管官吏选拔的左尚书仆射刘毅认为:“魏立九品,权时之制,未见得人而有八损。” “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上夺天朝考绩之分,下长浮华朋党之士。”[1](卷45刘毅列传)在统治集团内形成了盘根错节的朋党关系,威胁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巩固。大臣李重上疏陈述九品之弊,认为该制已“为弊已甚”。[1](卷46李重列传)段灼上表称:“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1](卷48段灼列传)侍中、尚书令卫瓘“以魏立中正,是权时之制,非经通之道,宜复古乡举里选”,与藩王、太尉司马亮等人联合上疏武帝:“今除九品,则宜准古制。”[1](以上皆卷36卫瓘列传)刘寔著《崇让论》,王沈著《释时论》,深入鞭挞九品中正制的痼疾。在朝中大臣一片反对声中,“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1](卷36卫瓘列传)“帝竟不施行。”[1](卷45刘毅列传)晋武帝权衡利弊,发现九品中正制已经与整个集团内的权势阶层命运攸关。司马氏正是依赖门阀世族阶层一代接一代的支持完成不流血的魏晋更替,其巩固自己的统治,仍然离不开这个庞大的盘根错节的社会阶层支持。所以,司马炎即位后,充分认可该制度的政治作用和社会整合意义,继续沿用该官吏选拔方式。只是另辟其他举措抑制日益顽固坐大的门阀世族阶层在统治政权的作用和影响,重视藩王,让藩王全面进入统治集团,担任中央、地方和军队要职,形成了西晋建立后的藩王政治。[5]
魏晋更替中,最大的政治结构调整就是司马氏大肆分封藩王,藩王分封制迅速成为西晋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中权力存在的一部分。司马懿掌权以后,宗室势力迅速膨胀。司马懿兄弟八人,“俱知名,故时号为‘八达’焉”。[1](卷31安平献王孚列传)诛灭曹爽兄弟后,作为司马懿的核心依靠,家族成员全面进入政权。司马懿有九个儿子,除了司马师、司马昭先后继承王位外,其他七个儿子亦分封为藩王,在司马氏政权中独当一面。司马炎登基时,分封了二十七个同姓诸侯王。“封诸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1](卷14地理志)诸侯国与州郡并列。藩王掌控着中央、地方和军事要塞的主要权力,形成了晋初藩王垄断政权的统治态势,这引起了以门阀世族为代表的百官大臣高度不安,纷纷上书,表达自己的不满和修正意见。河内太守刘颂“在郡上疏曰:……封建戚属,咸出之籓,夫岂不怀,公理然也。”[1](卷46刘颂列传)认为武帝封建亲戚,建立诸侯国是非常必要和合理的,从辅佐大臣的角度思考,有利于统一中国和巩固新归属的汉蜀孙吴之地的统治。“吴越剽轻,庸蜀险绝” ,“宜得壮主以镇抚之,使内外各安其旧” 。这些地方最应该封藩建国,“今得长王以临其国……宜取同姓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吴蜀。”[1](卷46刘颂列传)让藩王们承担起保家护国的责任。同时,封藩于边地,可以有效地防范异姓将领割地谋反。
西晋建立后,藩王具体地担任朝中职官。齐王司马攸担任“骠骑将军,开府辟召,礼同三司” ,“时朝廷草创,而攸总统军事,抚宁内外,莫不景附焉” 。不久,转镇军大将军,加侍中。贾充死后,又代替贾充担任司空,侍中和太傅的官职仍保留。“及帝晚年,诸子并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内外,皆属意于攸。”[1](以上皆引卷38齐王攸列传)朝内外行政大权收归藩王,门阀世族的特权受到严重侵占,剥夺了门阀世族阶层进入权力中枢所担任的具体职位。百官大臣对日益严重的藩王专权作出强烈的反应。中书监荀勖、侍中冯紞等进言武帝,以齐王在中央任职影响太子顺利成长为由,鼓动武帝下诏,让藩王们回到自己的封国去,并由齐王司马攸带头。接着,大臣不断上书,阻止若干提高藩王影响力的措施。“齐王攸之就国也,下礼官议崇锡之物。”[1](卷50裴秀列传)博士庾旉、太叔广、刘暾等多人“上表谏曰”武帝,反对诸侯王仍兼有中央官职,“汉代诸侯王位尊权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讚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国,亦不复假台司虚名为隆宠也。”借古喻今,得出结论:“宰相不得久在外也。”[1](卷50庾旉列传)武帝虽然采纳了百官的建议,“咸宁初,遣诸王之国”,[1](卷38平原王干列传)但并未严格执行,加之灭吴战争即将开始,藩王又是大兵在握的主力,门阀世族头面人物将藩王赶回自己封地的设想最终落空。
新的朝代出现,需要新的社会、政治和人伦秩序。百官大臣们争先恐后为晋王朝设计理想的政治道德、社会规范和习俗风尚。尚书左仆射、侍中裴頠著《崇有论》,从抽象的理论高度否定那些位高权重,但“口谈浮虚、不遵礼法”之徒所崇尚的“贵无论”。认为“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 。世界不是虚幻的,一切成果都是人们努力获得的,所以,“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劳而后享” 。那些“有高名于世”的人物,应该“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心,行以敬让” 。忠、信、仁、俭等儒家倡导的人伦道德应该作为统治政治中的普遍价值取向。《崇有论》是西晋时期有代表性的一篇论著,从哲学的高度清算魏以来贵无论在人们思想中的盲目崇拜。从概念出发,抽象地分辨“有”和“无”的关系。又立足于现实社会,论证“有”──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礼乐秩序的意义所在,否定“口谈浮虚”的“无”,积极引导晋时官僚士大夫摈弃魏以来谈玄务虚的做派,“崇济先典,扶明大业,有益于时”。[1](卷35裴頠列传)将官僚士大夫、社会名流的文化热情、知识爱好等引导到儒家先典的讨论和运用中来。司马昭“及蜀平,兴复五等,命(荀)顗定礼仪。……共删改旧文,撰定晋礼”。[1](卷35裴楷列传)尚未禅代曹魏,先制定晋礼义规范,为晋帝登基做好制度和规范的准备。
司马氏政治军事集团在形成过程中,除了制定礼乐规定以外,政治道德的建设也势在必行。即要建设旨在维护统治集团内部团结、强化成员个人操守的行为准则,迫使成员们自觉地自我衡量和遵守,赋予这种准则共同的价值意义,保证坚持者一定会得到君主的认可和全体成员的尊敬,坚持者个人可以凭此美德在统治集团内飞黄腾达。司马昭时期的相国军事刘寔“以世多进趣,廉逊道阙,乃著《崇让论》以矫之”。刘寔列举了“魏代以来”的官场众生相:“能否混杂,优劣不分,士无素定之价。”正是由于没有区分候补官员才干的有效方法,一旦“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不管入仕者自己才情优劣,只看家族声望和权势,所以,自魏以来的入仕者,已经没有办法测试本人的真实水平。“观在官之人,政绩无闻,自非势家之子,率多因资次而进也。”刘寔针对司马氏政权所面临的政治现状,提出一个既是士人入仕前、入仕后都必须具备的崇高的行为操守,又是各级政权发现、任用、晋升官员的唯一判断标准──让。称:“古之圣王之化天下,所以贵让者,欲以出贤才,息争竟也。”“让”对于士人自己而言,既是个人才德的表现,又是入仕前的行为考察,“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让贤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让徒费简纸者,皆绝不通。”没有“贤推”的士人不能入仕。“让”是官吏选拔中的重要标准,而且也是必须具备的条件。进入官场后,“三司有缺,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1](卷41刘寔列传)“让”又成为官署考察具备晋升资格的主要条件。刘寔为进入仕途和驰骋官场设计出一个便于推广、易于操作的方式方法。对于士人而言,“让”既是入仕者必备的道德修养,又是可以检验的门票。对于在位的官员,“让”既是政治行为所坚持的操守,又是官场向上流动的积分。对于君主和各级官署、中正官而言,可以有效而简单地培养和发现士人的政治品格,进而决定他们在官场的去向。
其时晋武帝刚称帝,“是时风俗趣竞,礼让陵迟”。御史中丞、侍中、谏议大夫庾峻上疏,称:“彼其清劭足以抑贪污,退让足以息鄙事。”倡导将“清劭”与“退让”作为官场中的清洁剂,以此形成官员们自觉廉洁和主动退让贤者的道德风尚。针对当时政治生态中的贪污、浮华等浑浊习气,庾峻等催促武帝下诏,在没有办法废除九品中正制的官吏选拔制度的情况下,确定一个既要士人们能通过行为表现,又能保证主管部门便于识别、考察和量化比较的道德规范标准。
晋武帝“初即位,广纳直言,开不讳之路”,[1](卷47傅玄列传)激发起官僚士大夫议政进言的热望,其纷纷以著书立说、上书进表等方式抒发长年读书思考、日积月累所积攒下的参政冲动和满腹经纶。他们紧跟武帝深入政坛的步伐,面对新政权所遭遇到的种种问题,全面陈述自己所欲构建的理想统治模式。散骑常侍傅玄上疏,阐述治国要务:一是“用人得其要”;二是国家经济社会结构是“士农工商以经过制事,”“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此皆事业之要务也”;三是“为政之要,计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四是倡导儒学,“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武帝大加赞扬,称傅玄等上疏“可谓乃心欲佐益时事者也”。武帝要百官以傅玄等为榜样,“使四海知区区之朝无讳言之忌也”。[1](卷47傅玄列传)武帝时期,天下归一,人心所向,面对三国归晋后的统治格局,出现了由君主倡导、由皇权推动、涉及整个统治领域内的百家争鸣思潮。
三
晋初,君主多次“诏三公,卿尹、牧守各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希望百官大臣、社会名流“各悉乃心,以阐喻朕志,深陈王道之本,勿有所隐,朕虚心以览焉”。[1](卷52阮种列传)武帝雄心大志,建国伊始,设想革旧创新,出现一番新天地。这时的百官言论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性变化,即:由魏晋更替过程中的选边站队,主动地进言司马氏表达忠心,或者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公开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态度转变为晋帝下诏定调,指导着官僚士大夫朝着司马氏统治需要的方向,贡献自己的政治智慧和思想财富。武帝选择一些专门的场合,有针对性的有准备的听取大臣的意见。大臣们似乎也早有思想准备,一旦这种场合出现,就会系统而有逻辑性的奉献出自己的政治见解。
《晋书》中记载最有代表性的是晋武帝与阮种的对话。阮种是汉侍中胥卿八世孙,“弱冠有殊操,为嵇康所重”。晋初,由太保何曾举贤良而进入能与武帝对话的会议。武帝让与会者“深陈王道之本”。阮种道:“宜师踪往代,袭迹三五,矫世更俗,以从人望。”不要颠覆以往行之有效的统治方式,矫正民怨过大的习惯。武帝 “又问政刑不宣,礼乐不立”“又问戎蛮猾夏”“又问咎征作见”“又问经化之务”“又问将使武成七德,文济九功,何路而臻于兹?凡厥庶事,曷后曷先?”等等。阮种有条不紊,将自己的建国方略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供君主多方面选择,包括统治指导思想的确立、刑罚与礼乐制度的建立原则与方式;甚至很具体的对少数民族的治理措施。阮种的建言献策,深受武帝的重视,更启发武帝广听博议,“乃更延群士,庭以问之。诏曰:‘前者对策,各指答所问,未尽子大夫所欲言,故复延见,其具陈所怀。’”[1](卷52阮种列传)对大臣们敞开议政大门,欢迎百官大臣畅所欲言。晋帝的诏令,大大鼓舞着百官大臣参政议政、进言献策的满腔热情,在晋朝建立初期又一次出现了一个统治集团内谈政议事的小高潮。大臣们的“策奏,帝亲览焉”。[1](卷52阮种列传)使得晋帝决策与施政能够最大程度地吸取统治集团内的智慧才能,出现了史家所称赞的“太康之治”。
晋武帝统治的太康年间(281-290年),“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1](卷26食货志)东晋初年的史家干宝作《晋纪》,描述了太康时期的盛况:“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无穷人之谚。”[6](卷127《晋纪总论》)尽管古人的评价有太多的誉美之词,但一个不同于前朝的安宁、富裕的时期出现了。纵观历史上出现过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所谓“盛世”,都有一个致使其出现的重要因素,即:大臣们敢于直言现状、进谏献策。史家在总结汉文帝等统治时,评论文帝等对待大臣们的上奏,“此等狂悖无忌讳之语,敌以下所难堪,而二帝受之不加谴怒,且叹赏之,可谓盛德矣。”[4](卷2“上书无忌讳”条)总结唐太宗统治时说:“贞观中直谏者,首推魏征。……然其时直谏者不止魏征也。”[4](卷19“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征”条)大臣们能够并且敢于发表自己的言论,君主能够善待其言,择善而行,这样,不仅调动了统治集团中广泛的从政、善政积极性,而且最大程度地保证治国理政符合历史前进的规律。那么,一定会出现人治社会中的盛世──“太康之治”等等。
[1] [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 [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廿二史札记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 赵昆生.西晋藩王政治研究[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6] [清]严可均辑.全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责任编辑:刘 力]
Reading, thoughts trend of talking Politic and the Politic of the Early Jin Dynasty
Zhao Kunsheng Chen Xiaoqian Tan Jieni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The aristocrats will be an official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by his family power since the governor of Wei Dynasty carries out “Nine Rank System”. The class of the aristocrats also is reading books to talk about current affairs and write books to study Metaphysics, which is fostered and enhanced as family study and specialty. A trend which combines talking about academic with evaluating politic appears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istocrats who are inward and outward lead the thoughts trend to expressing his attitude of politic and choosing side. After Xi Jin Dynasty is built, the emperor of Wu strongly advocates and guides it. He also knows how to choose the good to start. The Bureaucratic Minister offer advice and suggestions, and they write books and set up theory. They devote their wisdom of politic and the spirit wealth to the new Dynasty. Golden age of Taikang emperor appears, and it can be to be on a par with ruling of Wen and Jing emperor and the benign administration of Zhenguan reign period.
reading; the thoughts of talking about politic; the politic of the early Jin Dynasty; golden age of Taikang
2015-09-21
赵昆生(1957-),男,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陈晓倩,女,广东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助教。 谭杰妮,女,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2014级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
K26
A
1673—0429(2016)01—0083—07
——兼论刘裕“族诛”说
—— 兼论葬仪之议中的刘贺记忆
——《世说新语》共词分析
——《陈情表》教学的两次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