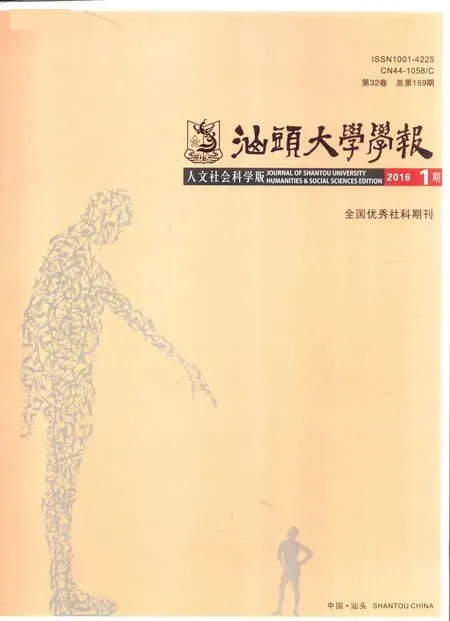论“霍桑探案”的现代性想象
周洁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 100024)
论“霍桑探案”的现代性想象
周洁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100024)
摘要:中国现代侦探小说有着很明显的本土意识,它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与变革中的民国司法和社会生态休戚与共,其消遣文学的表象背后承载了多重严肃的创作诉求。程小青笔下的私家侦探霍桑显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霍桑探案”普及科学理性认识论,将小说引向法治中国的现代性方向,直面社会现实,书写底层苦难,反思法治与道德的情理困境,寻求政治内容的民间表达,并在科学理性基础上,强调儒家传统的道德人格主义。小说中涉及的侦查技术与彼时司法水平相吻合,案件与制裁具有现实性和批判性,反映出民国通俗文人的司法理想和法律意识,以及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良好愿望。
关键词:侦探小说;霍桑探案;法治现代性;司法理想;情理困境
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滩风起云涌,既有政治上的改良和革命,则必有现实中的腥风和血雨;既有外交上的侵略和掠夺,则必有志士们的浴血和反抗;既有经济上的繁荣和物质上的奢靡,则必有贫富的悬殊和罪恶的泛滥;既有帮派的势力坐大,则必有政客的暗中勾结……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发展的黄金年代,正处于这种时局动荡、犯罪高发的背景之下,这无疑为创作者提供了不少现实素材。
当我们将目光聚焦在中国现代侦探小说上时,前所未有的“侦探”形象浮出地表。这个充满西方现代性色彩的角色,如何利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契机,让城市民众通过文本阅读与现实观察,对之加以反讽性的体验?有着众多拥趸的小说中的侦探,是如何被生产和被使用的?其想象性的建构,利用了哪些本土资源?而惯有的传统观念又在多大程度上遭到挑战,亦或隐而未现地持续发挥作用?……重新思考一个世纪前的文化现象,这些问题也许能从文学介入社会现象和历史真实,对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得出一些新的认识。
作为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集大成者,程小青及其笔下的“霍桑探案”系列小说在民国年间闻名遐迩,煌煌三十册畅销的《霍桑袖珍探案丛刊》和一系列由他撰写的侦探小说理论文章、由他主编的侦探小说杂志,为程小青奠定了“中国侦探小说宗匠”的称号[1]。本文将主要围绕程小青的作品,对上述问题进行梳理和考察。
一、侦探霍桑:名探、良吏、端士的完美结合
程小青的“霍桑”脱胎于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无论是从小说结构、人物设计,还是写作思路、破案技巧,都能发现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但若细加分析,霍桑并不完全是福尔摩斯的东方翻版,或者说,程小青的福尔摩斯中国化改写带有非常明显的本土意识,它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与变革中的民国司法和社会生态休戚与共。
开篇《江南燕》创作于1919年。这一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学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一种崭新的、“科学的人生观”正在被大力推崇。胡适在把科学观念应用于人文领域时,将中国传统内部的治学之道进行一番去粗存菁,把墨子、朱熹和清代朴学大师视为“科学家”,将宋学的格物致知和朴学的训诂考据解释为归纳与演绎并用的科学方法,进而得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治学宗旨。[2]
如果说胡适是在用西方近代科学方法梳理和树立中国人文学科方法论的话,那么程小青的创作可以说是用文学实践来把这一理念具象化。《江南燕》的开头几乎照搬了柯南道尔的《血字的研究》,详细描述霍桑的长相、性格和知识背景,甚至模仿福尔摩斯的出场方式,用细致的观察和缜密的分析,让他的伙伴十分惊讶和信服。类似华生给福尔摩斯开列知识清单一样,包朗也介绍了霍桑的学识广博,并强调他的兼收并蓄,“对于旧学,不分家派比较重义理而轻训诂,凭他具有的科学的头脑,往往取其精华,丢弃残滓”,“他始终觉得儒家思想的‘格物致知’和近代的科学方法十分相近,心中最佩服”,“同时他又欣赏墨子的‘兼爱主义’,长时期受到墨子的那一种仗义行侠思想的熏陶,养成他痛恨罪恶、痛恨为非作歹、见义勇为、扶助贫困、压制强权的品格”。这篇小说的开头两段,基本确定了后续系列作品中霍桑的整体性格和行事风格。
虽然深受西方科学理性和实用主义的影响,程小青依然无法完全摆脱中国文人治国的传统,他在全盘西化的浪潮中寻找中华经典的精髓,他赋予“助手包朗”作家身份,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不过分削弱文学/文人的力量。霍桑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更显示作者的人文理想:他极其聪明机警,但也十分平易近人;他锄强扶弱、爱憎分明,但性格上却有儒家的温和中庸,脾气也不像福尔摩斯那么怪异;他作息规律,没有坏习惯(不像福尔摩斯还有打吗啡的恶习);他虽然不近女色(也没有如福尔摩斯般持不婚主义),但却尊重妇女;他虽然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却秉持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穿中式服装,抽国产香烟,对西方的现代消费主义和物质崇拜嗤之以鼻;他在侦查过程中追求人权平等,主张实证主义,反对有罪推定,维护司法独立;他经常是众人陷于破案困境时的救命稻草,也是教育青年、指导警员的良师益友;他是一个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的现代侦查程序的执行人,又是一个背负民族使命感的现代法治文明的倡导者;他是一个接受过西方科学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同时又发扬着中国儒家传统中的仁义礼智信——他的形象简直堪称完美,他是程小青眼中理想的现代人模范。
刘半侬在中华书局1916年版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跋》中,以德性理解福尔摩斯,称其为“不爱名不爱钱”的“名探”、“良吏、”“端士”,这一说法放在福尔摩斯身上未必完全贴切,但放在霍桑身上却十分精准。对霍桑而言,“名探”表现为侦查过程中的科学性、准确性和高破案率;“良吏”表现为体恤为民,辅佐警方办案;而“端士”则表现为对道德感的高扬,将德治置于法治之上。对程小青而言,这种消遣的文学类型背后负载着许多严肃的创作诉求:在五四语境下,是对科学理性认识论的普及,对公平正义价值观的推广;在司法变革过程中,是对法治与德治的思考,对现代法制文明的探究;在市民社会层面,是对罪与罚、善与恶的辩证分析,对底层苦难的另类呈现;在都市文化角度,是对现代消费主义的批判和对传统价值观的打捞。
二、科学断案:现代侦查技术与民国司法同步发展
科学断案是现代司法区别于古代司法的首要特征。程小青曾将侦探小说称之为“化了妆的通俗科学教科书”[3],这一方面指的是侦探小说对于读者求知心理、理性分析和逻辑思维的培养和训练,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故事情节的包装,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读者介绍现代侦查技术的应用。在“霍桑系列”中,“技术”极少用于机关和道具的设置上,而被用于鉴定和检验;换句话说,是科技破解,而非破解科技,破案的关键往往在于推理和实证,故事中涉及的侦查技术也必须与现行司法发展水平相吻合,体现作者求真、严谨、务实的态度。
以指纹技术为例,它最先出现在青岛德国租界的警察部门,1918年,京师警察厅派员到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学习英式指纹技术,随后开始在全国推广;1924年,淞沪警察厅创设指纹室,但设备较为简陋,也未有科学的分类储藏方法;1929年,上海市公安局扩充指纹室,并设专员分管指纹的捺印、分析、储藏、记录、摄影和综理等工作;1934年,国民政府颁布《指纹事务办理规程》,以行政立法方式规定指纹的检验和鉴定。[4-6]在程小青的小说中,指纹科学在民国年间的发展情况得到如实反映。在1919年发表的《江南燕》中,霍桑批评包朗“中了欧美小说的毒”,只知以手印、足迹作为唯一证据,殊不知警察局的手指印存本只能对付有前科的惯窃积盗,“欧美侦探已遇到种种困难,更何况我们中国人?”他对指纹鉴定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持怀疑态度,而强调破案应根据事实,靠观察和分析解决问题。1933年出版《案中案》,程小青用小说来展示他所转变的观念。故事讲述一个著名女医师上吊身亡的案子,霍桑向来惯用的调查推理法并未奏效,先后锁定的几个嫌犯均被逐一推翻,最后由指印部呈交的关于凶刀刀柄和酒杯上的指纹分析报告,成为破案的关键和最有力证据,此时,上海市公安局已把指纹鉴定作为一项重要的痕迹检验技术。
类似的,小说中出现的验尸、解剖和血液鉴定,也是基于“司法部的法医实践被视为司法官员更普遍的调查和审判下的活动”[7]这一事实。1914年内务部颁行《解剖规则实行细则》,为现代法医检验技术的运用提供了法律规范;1932年,受司法行政部委托,获德国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林几在上海建立法医学研究所,积极培养法医学人才,创办《法医月刊》,同时受理全国各级法院送检的法医检验鉴定案件[8],这才使得侦探小说中的尸检或其他法医实践不再仰仗《洗冤录》之类的古代经典,由此有了现代科学明确的事实依据。
三、法治现代性:平等、独立、合法、正义的司法想象
现代司法的另一个要素是人权平等和司法独立,这也是法治现代性的核心价值之一。清末仿照大陆法系修订新的法律体系,改变礼法合一、重刑轻民等法律传统,开启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重要一步。[9]而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专职的司法行政机构、专职的审判机构,确立由受过系统法律知识训练的职业法官而非行政官员审理民刑案件的原则,则拉开了中国司法独立的序幕。诸如人权和法治、私权神圣、无罪推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标志着法制现代化的法律原则,在民国时期得以继续推进。
传统公案小说和现代侦探小说均以描写案件的发生、侦查和审判为主要内容,从这两种涉法类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司法改革的历史变迁。最为妇孺皆知的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大概要算包公故事了,作为一种民间社会的文学样式,它体现的是草根社会小民百姓的清官信仰和法律想象。包公既以明察秋毫的超凡能力和平冤摘奸的正义思想深受百姓崇拜和爱戴,同时也以其不畏权贵的刚毅正直和严酷威猛的威权执法而为人所敬畏。实际上,包公形象是一种“清官+酷吏”的神话化,其爱民如子和敬天保民的思想根植于封建王朝时代对皇权的维护和对君主的忠诚,这也就使得他种种威震天下的司法行为——譬如高堂之上的严刑审讯,或者具有皇权象征的金牌令剑和三刀御铡(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带有权力的独断性和专制的暴力性。
相比,在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中,私家侦探具有明显的独立性。他们并不依附于任何政权或团体;他们与警方合作执行任务,在调查过程中十分注重取证科学性和程序合法性,其目的不在于维护政权的统治,而是希望能以符合现代法治文明的方式使案件水落石出。虽然侦探小说多以案件的“侦查-告破”为主要内容,很少描写法院的“审理-判决”过程,但对专职从事侦查工作的警察局和不受行政权力干涉的官方侦探的描写,也反映出民国时期虽然有限、但已有所突破的司法独立。至于刑讯逼供或暴力执法,则断然不会出现在侦探小说中,这固然是民国文人的司法理想,实际上也体现了日益规范化的现代法律意识。
另一方面,在小说中屡破奇案的私家侦探往往以凡人形象出现,他们并非具有神秘的神性力量或者超凡的智力水平,偶尔也会犯犯错误、误入歧途,其破案秘诀不过是较普通人更细心、更理性、更谨慎、更博学,有着更强的逻辑分析能力。对传统的清官崇拜而言,这实际上是一种祛魅化书写,通过对现代理性人的塑造,将独断的公权力下放到民间,将“青天大老爷”拉下神坛。于是,侦探取代包公,成为拯救黎民百姓于冤抑欺侮的救星。正如民国文人范烟桥所说:“然而社会间机诈之事,层出不穷,侦探之需要甚亟。窃愿有侦探如福尔摩斯、聂克·卡脱华之产生,以救济哀哀无告之人也。”[11]
程小青的“霍桑系列”要比同期的侦探小说略进一步。私家侦探霍桑在以民本立场弘扬社会正义之余,还肩负着维护现代律法秩序的重任,作品反映出作者忧国忧民的现实关怀。借助这一独特的小说文类,他不仅可以通过对犯罪案件的直接描写触碰社会现实,同时也在思考革命反抗的罪与非罪,表达他对现行体制的批判或建议。
小说《断指党》讲述一个关于暗杀的犯罪故事,这样的选材在民国侦探作品中并不多见。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人而言,暗杀事件也许是清末民初社会氛围的重要记忆之一。面对清廷在政治上的黑暗腐败,暗杀曾被视为革命方式而付诸实践。辛亥革命以后,暗杀事件并未消绝,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指使手下暗杀革命党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共两党间的政党暴力杀戮,乃至抗战时期蓝衣社、锄奸行动队等团体针对日本人和投敌分子的各种暗杀活动,均不绝于耳,上海各大报纸也经常披露国内外暗杀事件,在舆论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毫无疑问,《断指党》的创作灵感来自清末民国的社会现实。不过,当时的暗杀活动多是为了促成革命起义、唤起武装斗争,推翻封建旧皇朝、建立资产阶级新政权,矛头指向统治阶级,但在程小青的文本里,他却对此进行了回避。他虽然也写暗杀事件,对象却非政府或执政党,而是“凭着权位和搜刮压榨的手段,弄得了巨大的造孽钱”的“贪吏、劣绅、奸商、土豪”,暗杀党认为国之积弱不振的原因在于“吏治不澄清”和“社会太麻木”,唯有通过以下犯上、釜底抽薪的“制裁”,才能“谋社会的根本改造”。程小青并非政治激进分子。作为一名底层知识分子,他目力所及的社会黑暗面是贫富悬殊、为富不仁、官商勾结、欺凌弱小,他笔下的暗杀团体“断指党”虽然同样带有侠客风范,却并非为了革命夺权或兴邦建党,而是希望劫富济贫,代黎民百姓除暴歼恶。他的地位和能力决定了他们的反抗方式——“没有力量推进上层的政治,只有从底层着手,使社会间孕育一种制裁的力”。因此,与其说“断指党”的反抗对象受制于平民群众的有限视野,不如说他们的伸张正义代表了大多数市民群众的朴实愿望,颇有些为民请命的意味。
但《断指党》并非一篇鼓吹暗杀的战斗檄文,其意也不在作一首充满浪漫情怀的革命英雄史诗。程小青借暗杀事件来写侦探故事,但实际上,其落脚点却是探讨正义的暴力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断指党”首领义正言辞地指斥社会民众对于贪官污吏的麻木不仁,助长了为非作歹的嚣张气焰,形成了骄奢淫逸的社会风气。他们抱着“牺牲的决心”、采取“暴烈的手段”以警世众人之举,颇有“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11]那种舍我其谁的大无畏气概,读来确实让人有些热血沸腾,不过作者很快就用他的理性和冷静将这种情绪降温。霍桑对他们“破坏了法律和社会的秩序”的质疑和指责,将小说引向了法治中国的现代性方向。面对一腔热血的革命青年,霍桑并未认可这种以暴制暴的非法行为,唯有当青年光明磊落地表示出勇于担当、自愿伏法的态度时,霍桑才流露出赞赏和敬佩的神情。
《断指党》虽然开出了侠客志士替天行道的药方,但程小青并不认为这是上乘之选,在此后的诸多小说中,他一直在探索其他可能的答案。对政府官员的态度,他表现出同时代文人少有的宽容,他笔下的官-民、公-私之间并非势不两立的状态,作品中也没有出现十恶不赦、草菅人命的流氓恶警。私家侦探霍桑一直扮演着官方警察的合作者和辅佐者角色,他和这些搭档们有着良好的关系,对他们的人品通常都表示认可,对其缺点,也仅是指正而甚少苛责。正如“断指党”着意在警诫社会败类、而非鼓吹民众造反一样,面对民国的司法现实,霍桑虽对官方有诸多不满,但仍希望借助体制外的反抗来推动体制内的改良。
四、文化协商:用东方伦理道德平衡西方现代理性
对于被视为旧派文人的大部分通俗作家来说,面对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治低潮和五四新文人的舆论打压,他们放弃前辈们的政治热情和革命意识,逐步从公共政治生活中退出,疏离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走轻松消闲路线,在商业文化主导下的现代传媒和大众娱乐活动中迅速占领了市民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彻底放弃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思考,当文学不再高扬直白的政治所指时,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内容的民间表达方式。他们以人伦道德的立场反思现代化过程中的民生问题,以充满温情的民间意识探讨严肃的社会命题:譬如科学理性的甚嚣尘上和误入歧途、譬如现代司法的公正严明和失却人道。
对于科学理性的质疑同样来自现代社会中的犯罪案件。侦探小说一方面标举着对科学原理和方法的趣味化普及,另一方面也为不受约束的科学应用惴惴不安。在《断指党》中,霍桑发现凶杀案的疑犯利用化学知识制造隐形墨水书写秘密信件,就已发出对科学犯法的担忧;在后来的《血手印》中,他再度陷入困惑:“科学在一方面确足以增进人类的文明和福利,同时也有人利用科学,当作残杀同类的工具,可是这岂是科学的罪呢?”他将此归结为现代社会日益弥漫的道德缺失,并认为五四以来泛滥而异化的个人主义埋葬了古代士大夫对家国的责任和担当意识。程小青强烈主张知识和德性的兼收并蓄,他为受过现代西方教育但中断了儒家传统文化血脉的青年人是否能够承担起救国兴国的重任忧心忡忡。他虽然只是处于底层的一介文人,却有着知识分子应该兼济天下、为社会谋福祉的远大抱负,这一点与处于精英立场的胡适不谋而合。1922年,胡适提出“好政府主义”,主张要由有知识有道德的知识分子精英承担政治责任,他也同样继承了儒家思想中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反对“独善的个人主义”[12]。虽然站在民主政治立场上的胡适所期待的好政府领导者是少数知识精英,而处于平民立场的程小青所寄托的复兴民族的国家栋梁是多多益善的青年才俊,但无疑他们都是站在科学主义的基础上,强调儒家传统的修齐治平道德人格主义。
这种“修齐治平”的图式反映了保留士大夫精神的知识分子对于“个人、家族、国家、天下”这一秩序体系的自我要求,他们所处的民间社会与国家体制之间有着共同的心理认同,这不仅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文人理想上,还表现在“小传统”的民间意识与“大传统”的政治制度之间呈现出一种同构的关系。民国侦探小说在追求西方现代理性和科学精神的同时,明显流露出通过东方伦理道德平衡善恶报应的创作意识。在“霍桑探案”中,这主要表现为破案之后对凶手的罪行量定上。程小青既要使其作品依循法理,又要使结局符合善恶皆有报的受众心理,还要在小说中弘扬正直勇敢、除恶惩奸的社会正能量。因此,在小说结尾处,经常能看到作者煞费苦心的设计和安排。
小说《白衣怪》和《案中案》都在思考这一问题:在一个主张公平法治的社会里,对于合理而不合法的行为、正义但不正当的报仇,应该如何处理和评价?换句话说:以公平著称的法律,能否保障大多数人伸张正义的权利?《白衣怪》写儿子为亡父复仇,《案中案》写老仆愤而手刃恶棍。在这两个小说中,于情,凶手惩恶除奸、替天行道,其举动堪称是大快人心的英雄行为;于理,他们谋取他人性命,已经触犯法律,理应受到制裁。情理冲突,如何解决?在一篇谈及创作心得的文章中,程小青强调,侦探小说“还须有一个正当而合乎人道的主旨,因为侦探的性质,就在保持法律的平衡”,“所以我们着笔时,也不能不把锄强辅弱的主义,做一个圭臬”[13]。基于这样的考虑,作者判处前者缓刑,既宣告其有罪,又免受刑罚;后者则是无罪释放,但为了保障法律的公正严明,作者唯有修改事实,让死者死于被“杀”之前,并对死者的自杀作出合理性说明,这也算是个两全其美的折中处理。对程小青而言,他既是现代法治文明的传播者,又是传统道德文明的坚守者,他有意设计这样的情理困境,用东西文化的协商去化解法治与道德的碰撞,使小说多了一层同类作品所缺少的思辨色彩。
五、人道主义:摩登上海的底层关怀
如果说福尔摩斯系列故事“是为大部分特权阶层写的”[14],那么,在中国的文本语境下,私家侦探却发生身份上的错位。他们以同情弱势群体、维护底层无产者、反抗权贵阶层为立场,自觉承担起向市民普及法治、科学、公平、平等等现代观念的职责。他们并非如城市漫游者一般,悠闲地观察都市生态,而是以一种介入式的干预,触碰法律边缘的社会问题。
面对现代都市消费文化,程小青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意识,他看到上海繁华背后的浮躁、虚无、享乐、堕落,看到隐藏在罪恶底下带有阶级性的人物命运悲剧,看到淳朴人性被侵蚀、传统道德被吞噬等现代性悖谬。李欧梵在文章中对程小青有过批评,认为他对这一“罪恶的渊源或颓废的所在地”缺乏深入探讨,又认为他把霍桑塑造成一个改良型的爱国分子、把侦探小说放置在民族国家的大叙述模式中,其实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做法,“因为五四作家群并没有把他视为新文学的一分子”[15]。笔者以为,这些并非确切的评价。霍桑的爱国主义和启蒙主义,恰恰反映了程小青区别于一般通俗作家的过人之处,而他对都会阴暗面的描写和揭露,也正反映了他对物质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
小说《舞女生涯》围绕当红舞星柯秋心被杀害一案展开,经过霍桑和警察的连夜追查和殊死搏斗,最终发现凶手竟是冒称表哥的王百喜,并在最后揭露柯秋心被诱奸、被拐骗、被迫卖艺卖身的悲惨遭遇。抛开小说扣人心弦的悬念和扑朔迷离的案情,这样的故事对于当时的市民大众而言,也许并不是太让人吃惊的新闻。小说中写到的匪徒绑架和抢劫头牌舞女的情节,就让人联想起若干年前轰动上海滩的“阎瑞生勒毙‘花国总理’案”[16]。当年高级妓院流行评选名妓,并以民国官职命名,书寓王莲英被评为“花国总理”,红极一时。沉迷赌博的流氓恶少阎瑞生因为负债累累,便将王莲英诱骗至荒郊野岭,劫走身上所有钱财并将其残忍杀害,弃尸而逃。而这远非个案。法国学者安克强在他研究上海妓女的著作中也曾指出,“偷窃和敲诈勒索是妓女这个职业必然面临的两个风险,不过,它们并非是仅有的风险,暴力会以更野蛮的形式出现。”[17]171他所说的“暴力”不仅来自盗贼和劫匪、嫖客和妓女之间,更残忍、更难逃、更常见的是来自老鸨的摧残和欺凌。
将舞女和妓女相提并论,虽然不是十分恰当,但也并无不可,不仅因为“她们中的很多人确实在从事卖淫”,而且“她们的出身实际上与妓女相同”[17]121,117。《舞女生涯》表面是写舞女被害案件的发生和侦破,其重点却是对从事这一行业的女性身世真相的披露,程小青有意要揭下上海滩上的舞星光彩照人的光环,书写她们不为人知的悲惨事实。柯秋心的绝命书声声泣血:“三年来,我已给他挣了不少卖命钱,但他还不肯放过我。我的堕落的生活和强支的病体,实在再不能忍受了。”如同老鸨之于妓女,被称作经纪人的王百喜在舞女业中扮演的角色叫监督人或大班,报纸曾屡次报道他们的恶劣行为,尤其是突出了他们将舞女推向卖淫的事实[17]121。对柯秋心来说,他是她的控制人,她是他的摇钱树,他会一直摇,直到最后一枚钱掉下来。
对于风尘女子的命运问题,程小青仍然怀着深深的同情和担忧。相比舞女的风姿绰约和收入颇丰,妓女尤其是下等的“野鸡”和“雉妓”,她们的生活要悲惨得多。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过惨绝人寰的遭遇,而噩梦多是从人口拐卖开始的。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真实的社会问题,政府的袖手旁观和法律的不作为,进一步加剧了事态的严重性。程小青创作《沾泥花》,就专门探讨妇女拐卖问题。小说首先暴露的是都会上海歌舞升平背后的阴暗面,即黑社会与娼妓业的相互勾结。当时上海的帮派直接控制着娼妓的来源,大部分妓女就是他们通过黑社会手段从农村拐卖、诈骗或抢夺来的[18],几乎所有的妓院都有黑社会的“后台”,以取得流氓集团的保护。小说中那位向霍桑求救的可怜女子是受了“拆白党”的骗,从上海被拐卖到长春去的,这在现实中也是实情,上海市档案馆现存的中国反拐骗救济会的档案材料中,就记载有妇女在上海被拐骗,然后被卖到奉天、天津、福州和烟台等地的案例。[19]198,470
在揭露人贩子的惨无人道之余,小说《沾泥花》也把妓女泛滥的问题摆在众人面前。旧上海曾因其娼业发达而被称为“东方花都”,从事卖淫的女子数量庞大得让人咋舌。1935年的调查数字显示,全市妓女数量竟高达10万人,有学者由此推算,彼时大约每13名妇女中就有1人在从事卖淫。[19]39-40上海的娼妓业如此发达,卖淫女如此众多,提供性服务的妇女形形色色,除了妓院妓女、私娼暗娼外,还包括职业舞女、按摩女郎、女招待、女向导、小商贩等等,这也算是大都会上海的“奇异景观”了。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程小青,当他从娼妓业中取材创作侦探小说时,他既不描写男子的狎妓冶游、寻花问柳,也不描写女子的卖肉生涯、陪客经历,而是将笔触直接对准娼妓业的上游——人口贩卖,以此为切入点,揭露行业乱象,代底层妇女发声,反映声色上海背后的黑暗现实,在呈现上海摩登的同时,也表现出作者颇为犀利、敏锐、深刻的思想意识。
晚清维新派知识精英试图通过新小说来构建一个具有崭新面貌的民族国家,五四进一步强化这种输入学理、再造文明的热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现代侦探小说也成为“科学话语共同体”中的一员,一方面传播新知、启迪民智,一方面也担负起道义上的使命感。作为现代中国最出色的侦探小说家,程小青的草根身份赋予他底层的视野,其笔下的城市书写有着真实的体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而作品中对科学理性的主张、对爱国情感的渲染,也与五四主题不谋而合。“霍桑探案”——与同时期的“侠盗鲁平奇案”、“李飞侦探案”、“蝶飞探案”等侦探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转型期的动荡社会里,通俗文人对中国未来走向的焦虑,以及期待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真诚愿望。
参考文献:
[1]范伯群.中国侦探小说宗匠——程小青[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
[2]汪晖.胡适的科学方法与现代人文学术[M]//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2部).北京:三联书店,2008:1226,1229.
[3]程小青.霍桑探案汇刊著者自序[M].上海: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印刷公司,1930.
[4]上海通社.指纹行政之史的考察[M]//上海研究资料.台北:中国出版社,1973.
[5]倪铁.中国传统侦查制度的现代转型——1906-1937年侦查制度现代化的初期进展[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08:126-127.
[6]张澄志.侦探学要旨[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2.
[7]Denial Asen.Dead Body and Forensic Science: Cultures of Expertise in China,1800-1949 [D].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2012:18.
[8]任慧华.中国侦查史(古近代部分)[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118.
[9]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3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542-563.
[10]烟桥.侦探小说琐话[J].侦探世界,1923(2).
[11]陈天华.警世钟·引子[M]//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514.
[12]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C]//欧阳哲生.胡适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71.
[13]小青.侦探小说作法的管见[J].侦探世界,1923(3).
[14]朱利安·西蒙斯、崔萍,等,译.《血腥的谋杀——西方侦探小说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11.
[15]李欧梵.福尔摩斯在中国[M]//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98,201.
[16]王亚陆.记阎瑞生勒毙“花国总理”案[M]//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1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95-96.
[17]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8]苏智良,陈丽菲.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226.
[19]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M].韩敏中,盛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李金龙)
作者简介:周洁(1985-),女,广东汕头人,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孔子学院事业部项目官员。
收稿日期:2015-09-06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16)01-004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