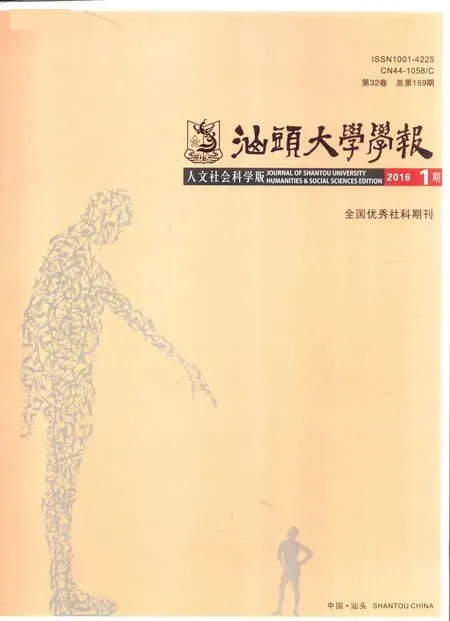内部自变异-动态系统理论研究的新视角
张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 广州 510420)
内部自变异-动态系统理论研究的新视角
张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广州510420)
摘要:动态系统理论(DST)关注的是第二语言学习者语言发展的过程。如何描述和研究这一多变量共同作用的变化过程一直是该理论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为此,动态系统理论将研究重点放在内部自变异的研究上。动态系统理论着重研究内部自变异过程的原因以及如何研究这一变异过程的方法。语言自变异发展过程对于语言教学有启示,当然动态系统理论在内部自变异这一研究问题上也存在不足,有待于更深入研究和完善。
关键词:动态系统理论;内部自变异;研究方法;语言教学启示
动态系统理论的语言发展观使这一理论研究语言发展过程的角度及方法较以往的语言研究方法有区别。动态系统理论认为语言学习是一个动态发展和使用的过程,在学习语言中使用语言,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学习语言,这是一个永远交织的、不断发展的过程[1]。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变量因素相互作用、通达联动、相互启动、相互竞争。动态系统理论对语言发展过程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视角,那么如何运用这一新理念来研究多因素参与互动的语言发展过程?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分析了关于动态系统理论研究核心——内部自变异现象研究的机理、研究方法,也指出了这一研究目前存在的不足和未来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
一、为什么研究内部自变异
(一)内部自变异新解
动态系统理论的绝妙之处就在于它将研究的核心放在研究语言发展过程中内部自变异(Intra-individual variability)上。这是因为这一理论旨在了解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变化,而语言发展系统中的个人变异最能体现这一核心理念,研究语言学习过程的个人变异就是研究多变量共同作用下语言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这些变量如同一个集合非常丰富,包括语言本体语境和非语言本体语境,如语言接触频率、语境、注意力、语言材料的凸显度、母语影响、语言学习的年龄、教学方法和手段、学能和个人差异等。因此传统研究中只研究某一个变量带来的语言能力的变化如同研究了冰山一角,并没有展示研究问题的全景。
动态系统理论着重研究内部自变异,也因为他们认为变异是语言发展变化的开端和推动力。高度复杂的变异过程意味着语言学习的质变,是语言学习者的必经之路。当学习者内部系统相对比较稳定的时候,系统的各种变化都比较少;而当学习者内部系统再组织、语言表征扩张的时候,无论是规律变化还是自由变异都非常多,内部自变异越频繁,吸态(attractor)变化的可能性越大,语言发展的可能性越大。van Dijk & van Geert[2]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学习者语言发展过程中的变异反映了相互矛盾的表征同时被激活,这有助于更完善、更高级表征的延续。所以在传统的语言发展过程的研究中,前后语言行为差异或语言行为不稳定的变化被视为测量误差,而在动态系统理论中这些则被认为是应该观察和记录的数据。
(二)动态系统理论研究变异的不同之处
动态系统理论之所以研究变异也因为这一理论对变异的看法有其独特性,他们将变异界定为内部自变异,语言变化过程是一个个性化、过程化、互动的过程。所以动态系统理论研究变异的视角和方法较以往的研究不同。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普遍语法学派并不关注语言发展过程中的变异。他们关注的是抽象出来的语言能力,而不是语言学习者到底如何使用语言的;他们使用的语料是用语法规则演绎出来的语句而非语言学习者真正使用的话语,因此他们对于语言使用过程中的变异视而不见。
在心理语言学领域,研究者们研究变异是将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变异视作静态的和阶段性的。他们认为变异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在语言学习的初期,学习者对于正确的或者错误的语言形式(变异)的使用是没有规律的;但随着语言能力的发展,语言学习者会逐渐选择使用正确的语言形式,变异随之消失。Rod Ellis[3]观察过一位11岁的葡萄牙语学习者学习英语语言否定式的发展过程,结果发现在第一个月,这位学习者使用了17次的“No”修饰动词表示否定(e.g.,No look my card),只用了一次don’t修饰动词表示否定(e.g.,Don’t look at my card.);但在第六个月,该学习者使用后者的频率显著增加。因此,Rod Ellis认为语言习得过程的变异在一定阶段就会消失。Gatbonton[4]在音系学的研究里也有了类似的发现。所以这派学者研究中介语的变异是为了了解语言学习者的变异发生在哪些发展阶段。这与动态系统理论的变异观是不同的:动态系统理论认为语言发展不是阶段性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有吸态(attractor state),有斥态(repeller state);有前进,有后退;语言发展过程也是个性化的,无法找到一个共性的发展过程。
在以Tarone为代表的社会语言学领域,研究者们把目光转向了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语言过程的变异。这些学者(e.g.,Adamson,Preston,Tarone etc.)自称为变异学派(variationist perspectives),他们指出语言变异过程是由于不同的对话者(母语对话者或者外语对话者)、不同的语境(正式语境或者非正式语境)或任务类型(笔头任务还是口语交际)等因素造成的[5]。他们将目光聚焦在变异形成的外部因素,这显然与动态系统理论的变异观点不尽相同,后者认为人类心智发展和语言发展的本质在于互动,因此变异产生的过程也是语言学习者与语言环境双向互动的过程。对于语言的变化过程只寻找外部原因,动态系统理论认为这显然是一维的、片面的。
二、如何研究内部变异
(一)内部自变异研究的基本思路
动态系统理论认为预测一个简单的、直接的、线性的因果关系不符合语言发展的规律。动态系统理论强调各种因素的互动,如人的认知能力、语言学习的环境因素和人的心态性格动机等因素都共同作用于语言学习的过程。而且这些因素的作用也是不停变化着,它们有时作用大,有时作用小。那么这些变化的因素在实验中该如何控制呢?
传统的研究方法是“通过分解并考察它的部分,可以最好地了解一个整体”[6],这是将每一个变量剥离开来,然后施以控制某个变量,从而观察这一变量的变化导致实验结果的变化以及对实验结果意义的预测。但是动态系统理论认为这种预测是主观的。因为他们认为凡是研究语言发展,都不能将某一因素单独隔离开来,都不能将人的因素和语境因素分离开来。语言学习的发展过程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语境资源和学习者本身相互作用、相互依赖,才能支持语言发展。动态系统理论不研究某一具体的因素,而是研究互动中产生的模式。这一学派认为他们的实验方法更像是形成性实验(formative experiment)的方法:研究者设定一个目标,然后找到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参与变化的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比如说教材,课堂内容的组织和实验过程的变化是如何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以达到一个教学目标。
此外,传统的实验研究使用的是平均值来研究受试的共性和差异,而这样做的前提就是认为每一个研究对象学习语言的路径大致相同,这就忽略了学习者内部和学习者之间杂乱的、每一天的变化,这些变化都有可能导致学习者语言学习过程的变化。Larsen-Freeman[7]也认为如果我们将这种可变性全部量化处理,变成了平均数,那么我们的实验就没有了带来涌现飞跃(developmental jump)的数据。
归根结底,动态系统理论的研究的是个性的语言发展过程,所以这类研究的实验往往是针对学习者个人的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ies),即跟踪某一个或者某几个个体语言发展变化的过程,从而总结出这些个体语言发展变化过程中相对概括性的特征。
(二)内部自变异研究的具体问题
具体来说,DST的主要研究问题是通过观察语言学习者语言发展过程的变异来看语言是如何发展的。例如语言学习者是什么时候怎样开始使用非限定性结构或者更长的名词短语的?影响语言发展的变量(比如词汇复杂度和句子复杂度)是同时发展的,还是相互竞争的?这些变量的发展是否是从易到难?这些变量是渐变的,还是起伏的?这些变量之间是否相互影响的?它们是怎样相互影响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得从考察相关的、可以操作的变量开始。但是动态系统理论强调多变量的自组织的发展过程,因此确定最相关的变量还是困难的。动态系统理论的做法是尽可能地将这些变量都纳入进行分析,再观察这些变量是如何起作用的。动态系统经常观察的变量是句子的复杂度和词汇的复杂度。句子长度是语言复杂度的有效指标:即句子越长(平均每句的单词数量),语言的复杂度越高。另一个指标就是句子类型:简单句、并列句和复杂句等,即语言学习者语言水平越高,使用的句式结构越复杂。
多元动态系统理论下的语言学习研究中,词汇的多样性可以用类型-词数率(TTR: type-token ratio)来测量,但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语言中的功能词(冠词、介词和副词)非常高频。这就有可能出现文章越长,类型-词数率越低的情形。所以在实际的操作中可以去除功能词,只按照实词(content words)进行计算。还有另一种作法就是简单的看词汇长度(word length)[8]。一般说来,使用者的英语语言水平越高,使用词汇的长度就越长,复杂度就越高。最后也有做法是建立词汇频率档案(Lexical FrequencyProfile)[9],但是该做法费时费力,而且要求所研究的语言有相关的词频语料库数据。
Verspoor,Bot,Lowie[1]用实证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如何进行多变量数据的量化和解读。该研究分析了一个母语为荷兰语的女中学生在六年中学的英语作文共计22篇,每一个样本均选用200个左右单词的作文,这些作文中的句子必须是完整的句子。通过实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受试如何变成一位更高级水平的英语学习者:比如名词短语越来越长,使用更多的非限定性从句。这里以词汇使用的复杂度为例,通过检索BNC数据库发现,受试在第一篇文章中使用的动词influence,force和control在数据库中使用频率为10000到30000次,而在第22篇文章中使用的动词elicit,induce和acquire在数据库中的使用频率仅为250-2000次。
描述语言学习发展过程的变化,动态系统理论还认为观察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应该更有意义。具体来说,这些不断发展的变量(growers)之间主要呈现以下关系:变量之间协调一致发展的支持关系,词汇的习得可能有助于句法的习得;变量之间的发展呈现轮流交替的发展状态的竞争关系,这意味着这些变量是相互竞争的关系。比如说有时候学习者在某一阶段使用的词汇难度增大,但是所使用的句子长度或复杂度却降低了;以及条件关系,即一个变量某一具体方面的发展是另一变量产生变化发展的前提条件或者是一种先兆。
Verspoor,Bot,Lowie[1]观察了一位母语为荷兰语的高级英语学习者学习英语的情况。他们记载了这位学习者进行英语学术写作时词汇发展和句法发展的情况。他们使用TTR(Type-token Rotio)测量词汇发展的多样性,通过句子长度测量来观察句法发展。结果发现这两者的发展是交替式、螺旋式上升的发展状态。在观察初期和末期,词汇发展和句法发展基本是相互支持、协调发展的;而在观察中期,这两者则是竞争的关系。但整体来说,这些荷兰的英语学习者学术写作语言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同时词汇的多样性和句子的长度也都在协调平衡的发展。
(三)内部自变异研究的操作方法
对于研究变异,传统的研究方法有语篇分析、话语分析和数据库语言分析以及一些质的研究方法或者是人群学研究方法。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通过观察眼球移动(Eye-moving)来扑捉受试者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随着时间和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来观察受试注意力的变化[10]。而van Dijk and Van Geert[2]使用Excel表格将这些语言发展过程的可变性清晰地展示出来,他们设计了新的记录数据方法使我们不仅可以观察到样本内部变量的变化过程和这一过程中各变量的互动,而且还可以推测这种变化的过程和这种互动关系是否具有显著意义。
最小和最大值表(min-max graph)可以用来观察数据变化的幅度。具体来说这个最小和最大值表是按照一个连贯的时间段来动态记录数值的最小值和最大值。这个连贯的时间段在动态系统理论里被称为移动窗口(moving window),每一个移动窗口的时间段和上一个窗口的时间段最大程度的重合,即只向下移动一个时间单位,每一个测量时间段可以用(t1…t5)来记录,所测量的最小、最大值时间表可以这样来表示:min(t1…t5),min(t2…t6),min(t3…t7),etc.,max(t1…t5),max (t2…t6),max(t3…t7)…。通过使用最小最大值表和移动窗口可以记载语言发展过程的变化,可以细致地反映语言发展过程中的变化细节[1]。
要进一步了解动态系统的语言发展过程,还应该分析发展过程中各变量的互动,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和去趋势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步最大值和退步最小值表(Progmax-Regmin graphs)是用以观察是否出现可能的发展飞跃。这种观察数值的方法就是观察随着时间窗口不断后移(1-5,1-6,1-7,1-8,1-9,etc.),找到语言发展过程中的进步最大值;然后根据时间窗口不断地前移(54-50,54-49,54-48,54-47,etc.)来找到语言发展过程中的退步最小值[2]。这一系列的实验可以清楚地展示语言发展过程中内部自变异现象,以及在这一内部自变异过程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内部自变异的启示
动态系统理论将内部自变异作为研究的重点,这在母语语言学习及二语习得的理论上和方法论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扩宽了研究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视野。
首先动态系统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是对传统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挑战,它旨在描述,而非解释和预测。在传统研究的领域,对于现象的解释总是基于对某一实验因素的控制和预测,而且这种预测是可以被可验证的假设所检验。但是动态系统理论的观点认为语言学习的发展过程不是线性的,是受到多方面、不稳定因素的共同作用,因此对某一因素采取控制不一定会带来语言学习效果的变化,或者某一学习效果的变化不一定是某一因素造成的。王初明[12]指出动态系统理论有助于改变语言学习研究中孤立地看待一两个变量、见树不见林、以偏概全的研究思维模式。
动态系统理论的研究方法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它用一套完整的研究方法体系为我们科学地展示了如何研究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变化。这一系列研究方法包括最大-最小值表、变量的相关性及其去趋势分析、进步最大值和最小值表和蒙特卡罗实验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蒙特卡罗模拟实验证明“个人语言学习变化”这一最个性化的研究的显著性意义,使实验结果更加具有概括性,更令人信服。
动态系统理论也具有指导语言学习及外语教学的意义。动态系统理论认为语言发展的过程非线性的、自组织过程,是多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看法也加深了我们对语言教学中纠错的认识:即语言错误的产生是自然的,也是学习者语言完善的必经过程。动态系统理论反对将所有的变异都归咎于外部的环境因素。他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维的,也就是说在语言学习的过程,很多的变异是由于学习者与环境互动、适应环境的结果。学习者是一个主动参与语言变化过程的主体,他也在不停地影响着周围的语境,这样的互动才会导致学习过程的变化。所以错误(各种变化)是语言发展的必经阶段,是学习者主动适应学习环境的表现[6-7],是学习语言的互动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此外,动态系统理论也为我们在教学中如何纠正学习者的错误提供了很重要的启示。语言学习过程中变量越多,产生变异的可能性越大,而变异是语言发展的推动力。Thelen and Smith[13]也认为只有当学习者接触到不同的语言形式,他们才能选择和适应新的语言形式。所以语言学习者接触的语言形式或者变量越多,语言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王初明教授的“学相伴,用相随”原则和“语言习得的有效路径”认为所学的语言结构能否用得出来、用得正确,还取决于此结构在学习过程中与什么语境变量相伴;相伴正确,使用就会正确,相伴错误,使用就会出错[12]。
因此,丰富的语境中多变量因素和大量地道正确的语言输入对于减少犯错的机会从而习得语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语言教师应该把花在纠错上的精力放在语言任务的设计上,放在学生犯错误之前。纠错应该是在语言的使用中、在语言产生大量变异的过程中纠错。我们应该为学习者设计那些促使他们产生大量变异的学习任务,学习者就有可能发展更加合乎本族语规则、更为系统化的语言。简单的操练不是好的学习任务,简单的纠错无济于事。只有那些提供了地道语言的、具有丰富语境的、能够促使各种因素在学习者语言心智,甚至包括肢体上产生通达联动学习任务才是好的学习任务,才能够促使学习者习得语言,自然没有产生错误的空间。van Geert[1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语言层面的各因素的充分互动和变化的过程使芬兰语的英语学习者产生了语言发展的飞跃,语言的错误率大大降低。
当然,动态系统理论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这一理论认为仅仅只是描述语言发展过程中的内部自变异并不是这一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也不是语言(外语)发展领域研究的最终目的[15]。动态系统理论的研究将内部变异视为研究重点,并且声称这一研究与前人相关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动态系统理论认为变异是语言发展过程在各种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学习者内部自组织的结果,但是如何使各种外部因素更好地作用于语言发展的过程,促进内部自变异的进程,这是值得我们继续探讨的。动态系统理论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也为这一研究的继续深入奠定了基础。
内部自变异是语言学习过程中多因素、多变量交互作用的结果,它是语言发展过程的必经之路,是语言发展的推动力。这为我们带来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从内部自变异角度来考察这些变量,我们也许能看到语言发展过程的真貌!
参考文献:
[1]Verspoor,M.,de Bot,K.& Lowie.W.A Dynamic Approach to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Methods and Techniques [M].Amsterdam: John Benjamins,2011.
[2]van Dijk,M.&van Geert,P.Focus on variability: Newtools to study intra-individual variability in developmental data [J].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2002,25: 340-375.
[3]Ellis,R.Sources ofvariability in interlanguage [J].Applied Linguistics,1985.6: 118-131.
[4]Gatbonton,E.Patterned phonetic variabilityin second language speech[J].A gradual diffusion model.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1978,34: 335-347.
[5]Tarone,E.Variation in Interlanguage[M].London: Edward Arnold,1988.
[6]Larsen-Freeman,D.& Cameron,L.Research methodology on language development froma complexsystems perspetive [J].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2008,92: 200-213.
[7]Larsen-Freeman,D.The emergence of complexity,fluency and accuracy in the oral and written production of five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J].Applied Linguistics,2006,27: 590-616.
[8]Laufer,B.& Nation,P.Vocabulary size and use: Lexical richness in L2 written production.[J].Applied Lingustics 1995,16: 307-322.
[9]Laufer,B.& Nation,P.A vocabulary-size test of controlled productive ability[J].Language Testing1999,16: 33-51.
[10]Paulson,E.Viewing eye movements during reading through the lens of chaos theory: How reading is like the weather [J].Reading Quarterly,2005,40: 338-358.
[11]Spoelman,M.& Verspoor,M.Dynamic patterns in development ofaccuracy and complexity: A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in theacquisition ofFinnish [J].Appled Lingustics,2010.
[12]王初明.外语教学三大情结与语言习得有效路径[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4):540-549.
[13]Thelen,E.&Smith,L.B.A dynamic systems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on and action [M].Cambiidge,MA: The MIT Press,1994.
[14]van Geert,P.A dynamic systerms model of cognitive growth: Competition and support under limited resource conditions.In Smith,L.B.& Thelen,E..A dynamic systems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Applications [Eds].Cambridge,MA: The MIT Press,1993: 265-332.
[15]Verspoor,M.,de Bot,K.&Lowie.W.Variabilityin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from a dynamic systems perspective [J].Modern Language Journal,2008,92: 214-231.
(责任编辑:李金龙)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一般项目“商务管理英语知识库构建及其在商务英语写作自动评分中的应用研究”(13BYY09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纠正性反馈与英语写作语言准确性的发展”(12XWW05)
作者简介:张砥(1977-),女,湖北襄阳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商务英语学院讲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07-07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16)01-006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