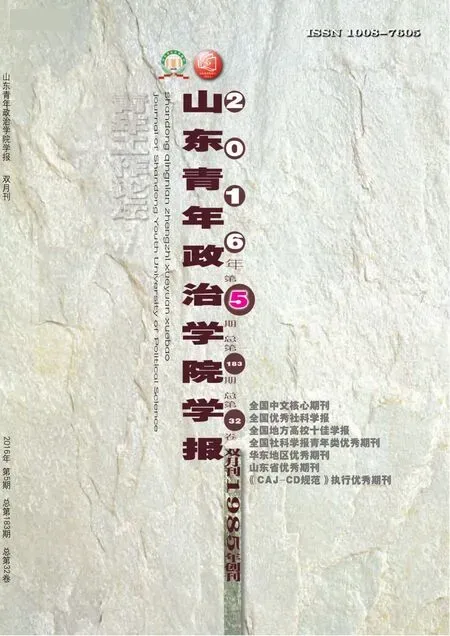论人类权利行为与义务行为
马立新
(山东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济南 250014)
论人类权利行为与义务行为
马立新
(山东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济南 250014)
所谓权利乃是社会主体在法律框架内享有的自由行使自我意志的一种行为权限或资格。在政治共同体中,所谓意志的自由不能超过法律覆盖的边界,且每一种意志自由的行使都必须与其他人的意志自由相协调。法权是否是一个国家或特定社会的最高权力就成为衡量和检验这个国家古典性或现代性的根本尺度。义务行为与权利行为一样都是出现在法律制度产生之后的人类社会中。如果一种意志行为,其中的理性力量战胜了各种非理性成分的力量,控制了意志的方向,基于这种心理机制的“分内”行为就是义务行为。义务行为并非出于本能或意愿,而是出于理性制导。在现代法权下,权利和义务的数量是对等的,有多少种权利就必然有同样数量的义务。权利行为是利己不害他的行为,义务行为是利他不害己的行为,两类行为的总和构成人类的全部正常的社会行为。
权利行为;义务行为;法哲学
“权利”与“义务”或许是当下全球传媒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但与传媒对两个词汇的高度敏感与众声喧哗形成对照的是,现实中很多人其实对其词义知之甚少。从学术的角度看,“权利”与“义务”是近现代法哲学的核心命题,前者更是现代法学家探索的重点。不幸的是,长期以来西方法哲学所主导的致思路径多是基于形而上学,往往热衷于概念的创建、推理与演绎,结果造成两者的概念与其所表征的人类实践生活相脱节。因此,对其正本清源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其现实意义。同时,作为一个中国法哲学研究者,面对动荡不安的各种世界文明冲突,也有责任就此发出独立的“中国声音”,提供具有建设性的“中国方案”。
一、权利行为
“权利”与“义务”,所涉及的其实是一个与“自由的限度”有关的哲学命题。为了能让读者更清楚地理解上述命题,笔者试图回到问题的原点——人类行为中去考察。以2014年为例,该年度发生的国际重大事件很多,其中值得格外关注的有三件:一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77飞机于2014年3月8日与地面失去联系,机上载有239名乘客,其中包括154名中国人;二是乌克兰事件;三是第86届奥斯卡奖出炉。因为马航飞机失联和乌克兰事件同时发生,今年的奥斯卡奖颁奖典礼显得不那么引人关注,但这也仅仅是“显得”而已,对于爱好电影、爱好娱乐的人们来说,每年的奥斯卡盛典永远都是他们的最爱。之于笔者,研究艺术是本人的职业,关注马航飞机因为飞机上有自己的同胞。而笔者更关注乌克兰事件,因为克里米亚以全体公决的方式脱离了乌克兰加入到俄罗斯的版图中。其中值得深思的是:克里米亚人的公投是完全的自由意志的体现吗?克里米亚人有这样的自由意志吗?如果有,是谁赋予了他们这种权利;如果没有,他们的公投结果又当如何看待?从接近97%的公投结果看,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克里米亚人的意志自由的绝对性;然而,如果进一步追问意志究竟能否绝对自由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立即陷入一个涉及自由逻辑的悖论中:如果自由就是不受任何外在意志或力量的约束,那么这样的自由在世界上根本不可能存在。人类的世界是如此,自然的世界也是如此。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无时不处在因果律所编制的网络链条上。因果律是宇宙中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本法则和根本逻辑。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立即就会意识到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自由或绝对的自由,这无疑普遍适用于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即所有客观事物都受制于因果法则而存在或消亡。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理解人类的意志自由。意志是否是人类独有的属性?至少叔本华是否认这一点的。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宇宙中一切事物都有意志而且都受到意志的主宰,因此他把意志定义为世界的本质。[1]从某种角度来理解,叔本华对世界本源的理解是有道理的。比如当我们把从自然界某个特定地方偶然发现的一块石头归咎于是这块石头的意志让其本身待在那个特定的地方的时候,因为除此之外,我们似乎找不到更好的理由来解释这块石头为什么会待在那里而不是任何别的地方。不过,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用因果律也依然是可以说明的。因为我们会发现,这块石头之所以待在那个特定的地方,是因为它的下面有支撑物,它的四周存在阻碍它运动的物体;如果这些阻止它运动的其他物体消失或有所变化,那么这块石头也会随着发生运动。面对这两种解释,相信一般的人更认同基于因果律的说法,因为对于意志说,无论是这块石头本身还是它周围的任何其他存在物都无法证明意志作用机制的存在,而因果律的机制则是完全可以在石头上获得证明的。比如,只要我们将这块石头下面的支撑物拿掉,它就必然发生运动形态的改变,直到遇到新的支撑物才能恢复原来的相对静止状态。意志本原说的最大缺陷可能就在于此。对于人类来说,作为意志主体,我们对自己的意志作用是完全能够感觉和体验到的。这一点迥异于自然客体。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即在人类可以验证自我意志的作用机制确存在的前提下,人类的意志是否自由呢?如果有人说,从意志是生命的函数来看,意志本身就是不自由的,它必须依赖于生命的存在,而生命并非是永恒的存在。这种说法无疑是对的。但即使是在生命存在的情况下,人类的意志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果真如此的话,读者可以试着想一想,人类将会是怎样的状态?笔者敢说,果真意志是自由的,那我们人类一天都生存不下去。既然意志是自由的,我们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做我愿意的一切事情,如此一来,人类基于维持自我生命的本能很快就会将宇宙中人类可以接触到的一切资源占尽。其实人类的自由远等不到将资源占尽这一刻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利益冲突,个体的自由最大只能行使到不妨碍他者的自由之处。因为自由一旦越界,他人的自由就会受到侵害或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要行使更大的自由,将导致人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爆发,因为没有人就愿意放弃自己的自由或被剥夺自己的自由;如果大家都各自约束自己的自由,大家相安无事,共同生存于一个利益共同体中。但无论哪种情况,人类的意志都将是不自由的。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一下克里米亚人的公投行为了。在乌克兰事件爆发前,这个国家的主权完整地行使到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整个乌克兰联邦共和国。国家主权的存在在现代意义上就意味着它的形成是这个国家全体公民的授权,即每一个公民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共同交付给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机构,一个国家的所谓主权就是这样形成的。从现代法理学上讲,主权是以宪法的形式被立法者确立起来的。宪法相当于一个国家全体公民共同制定的契约。在国家主权尚未被破坏的前提下,即宪法尚存续的情况下,任何个人或集团未经立法机构允许都无权通过任何方式改变主权的完整性。从这个法理意义上看,克里米亚人也许有权利为自己的未来做出决定,但这种决定在未得到国家全体公民允许的情况下是无效的。或者说,克里米亚人有举行公投的权利和自由,但前提是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不得侵犯其他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否则,他们的权利和自由的行使就是一种现代法理学上的违宪或违法行为。
当然,上述情况在某种极端特殊的情况下也许是可能的,这就是在自然的社会秩序下。所谓自然的社会秩序也就是在人类尚未建立国家、尚未进入政治共同体之前的像动物一样的社会存在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像动物一样在自然法则下生存,自然法则也就是所谓丛林法则,即弱肉强食、成王败寇法则。显然,依靠自然法则运行的社会依然是个有秩序的社会,依然存在自然伦理。比如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亲情、血亲通婚禁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信守诺言或约定等都是普遍存在于高等动物界的。自然伦理与其说是一种自然之道或自然天理,不如说是生命本能的必然要求,因为没有或者不遵守这些天经地义的自然之道,生命终将自我毁灭。但是,仅仅依靠这些自然之道,生命固然可以维持和繁衍,但生命的意义很难得以彰显。所谓生命的意义就是对生理生存的种种超越,所谓自由、平等、安全、尊严、幸福、爱情、权利、地位这些概念都超出了生命的生理意义,构成现代人的重大精神价值。只不过,人类的这段历史并不长久。而在人类进化的大部分时间里,生命基本上是处于跟动物一样的蒙昧状态,除了基于生命本能在生理意义上活着外,对上述各种价值的概念浑然不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谈论人类的自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试想,跟一个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自由的人探讨他的自由权利能有什么结果呢?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无自由可言。只有当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到政治状态之后,生命的超生理意义才有可能获得启蒙。因为人类一旦摆脱自然状态,进入政治共同体中,相伴而生的就是社会契约的共同制定。当然,这里的契约仅仅是原始意义上的契约,还不是现代意义上或基于法理权利和义务对等理念的契约。例如,此时的立法者和执法者可能不过是掌握着国家权力的人,因而他完全可以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而颁布各种法典,而不必经过全体国民的同意。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法典在政治社会中的存在本身就已经较之自然的社会状态进步巨大,在政治社会中人们在自然状态下那种不稳定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终于第一次获得了保障和确立。在自然状态下一个人的财产被强力剥夺后虽然从天理上是不允许的,但天理并不能作为随时有效的救援机制来对被剥夺者实施补偿,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剥夺者的财产很有可能被更强大的剥夺者来剥夺,以此来彰显天理的存在。这种以暴制暴、以恶制恶不过是丛林法则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处在个体能量末端的弱者只能接受被自然所淘汰的命运。显然,这样的社会状态是极不稳定的、极不安全的,因此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可能就是人类应对生命不稳定不安全状态的一种很有智慧的尝试。政治社会的优点是可以集中全体公民各自出让的一部分权利构成国家强大的权力,全体公民通过这种集合起来的超强权力来保障和捍卫自己的各种利益。因此,尽管为此每个人需要付出损失一部分个人权利包括自由权利的代价,但较之自然状态下的生存,人们在政治共同体中可以享有的权利还是大多了。从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政治共同体的诞生催生了人类权利意识的萌芽。人的财产权意识和生命权意识作为生命最重要最密切的两项安全保障机制很可能最早随着政治生活的开始而发生。对于人类个体来说,他进入政治社会的第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从此开始受到了国家的保护,即不经其本人允许或同意,任何人都不得动用、占有或支配他的财产;一旦被非法侵占,当事人立即会受到国家法律的惩罚。也就是说,此时,财产所有者即使体力弱小无法直接对抗侵略者,他也可以通过国家权力即诉诸法律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财产权。生命权也是如此。由此看来,“权利” 这一称谓只有当政治共同体建立之后即法律建立之后才真正被建构出实质性的意义来。
那么,由法律所建构的权利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性质呢?当我说我有权处置我的个人存款的时候,这意味着我可以自由支配我的个人存款,同时也意味着除我之外的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支配我的上述存款,这样说正确吗?不完全正确。严格的说,我的所谓财产权乃是法律赋予我的对我的正当收入的一种自由支配权;而对别人而言,法律均不允许其支配我的正当收入,后者也可以说除我之外的任何他人都有义务不干涉我的财产权的行使。
当我无端受到歹徒攻击而身体受到伤害的时候,我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歹徒因此受到刑事惩罚,这是因为我的人身权利遭到了侵犯,而人身权是法律赋予给每一个人的最基本的生命权利,它意味着未经我允许或同意,任何人都不得侵犯我的身体,也就是说只有我才有资格对我的身体进行任意支配。由此看来,所谓权利乃是社会主体在法律框架内享有的自由行使自我意志的一种权限或资格。至此,我们看到,在政治共同体中,所谓意志的自由不会超过法律覆盖的边界。
人类权利意识的萌芽滥觞于政治共同体的建构,然而权利意识由被动萌芽到真正觉醒则是一个漫长的从古典思维到现代概念转换的过程。检视人类政治史,民主政体虽然古已有之,但古典时期的法律框架无论是在民主政体中还是在专制社会基本上都是以惩罚和限制人类的自由为基础的,古典的民主政体与现代民主政体相比可谓有天壤之别,这种差别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古典法律与现代法律的差别。在古典法律下,即便有权利意识的萌芽,这种权利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也多是出于生命本能而针对物理实体(财产权)和生理实体(人身权)的维护意识。比如当个人财产或生命受到暴力侵犯的时候,出于生命本能必定会自卫抵抗,但因为清楚地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弱小,单纯依靠自身的力量不足以捍卫自身那些被侵犯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被迫求助于国家司法部门来讨回公道。因为个体知道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谁也没有能力跟国家权力相对抗。显然,这种维权意识是被动型的,只有当个人的利益受到暴力侵犯而自卫无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古典法系建构的基本诉求就是惩罚犯罪。在古典社会,无论是侵权者还是被侵权者都很难想象有自觉的“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只有到了启蒙运动的发生,人类的现代人权意识才获得了真正的觉醒。与古典权利思想不同,现代人权思想特别注重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生活等人的基本权利的确立和捍卫,并将这些基本人权视为天赋的、不可转让的。与此相联系,现代法系尤其重视对这些基本人权的捍卫和保障,也就是说现代法系本质上是对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生活等人类基本权利的强有力守护神,这从美国《独立宣言》[2]和法国大革命所制定的《人权宣言》[2]中都获得了最好的彰显。现代法系当然也包含着惩罚犯罪,但现代法系是将惩罚犯罪作为手段以实现捍卫自然人权的根本目的。自然人权也就是现代法系所称的天赋人权。这种现代启蒙思想从根本上动摇了古典社会根深蒂固的封建君权和王权等特权意识。自由和平等权利意识产生的逻辑起点必然是特权意识的废除。较之古典法系,现代法系无论在人类社会行为调整的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要大得多,可以说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现代人并没有因此感到自己的自由权利受到了更多的限制,恰恰相反,法律结构越是健全和完善,人们的权利就越有保障。这是从法律结构表象上着眼的。而从本质上看,现代人享有广泛的人权保障或者说现代人权意识的真正苏醒还在于特权的不复存在。只有取消了特权,人的平等和自由权利意识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来。特权的消亡也同时意味着法权的至高无上,而法权是由全体社会公民依照共同的契约精神赋予并建立起来的。在此种情况下,公民所唯一敬畏的是法权,也就是大家共同的社会游戏规则,而不是个别人的特权;也就是说只要一个公民不违法,他就是一个自由人,没有人可以任意侵犯他的法定的权利。因此,法权是否是一个国家或特定社会的最高权力就成为衡量和检验这个国家古典性或现代性、这个国家的人民为古典人或现代人的根本尺度。依据这一尺度,很容易发现某些现代国家虽然从历史时间上、政治形式上或经济体制上都现实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但从法理上看依然是个古典型的社会,朝鲜、叙利亚、前萨达姆政权时代的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国家都是典型的代表。
那么,在特权消除之后法权如何能让所有公民敬畏?尤其是在经过思想启蒙之后的现代国家,在这里人们的人权意识已经获得普遍觉醒,维权意识普遍强烈。这种人权意识的巨大变化是否会让人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无政府状态?至少从理论上讲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根据陈陈相因的意识惯例,人们对政府或国家的敬畏无非是因为它们掌握着强大的权力或特权,因而不可能跟他们处于平等的地位。在此情况下个人的自由即使有这种意识也无法获得保障,所谓自由也不过是政府或国家的自由——极少数人利用特权为所欲为的自由。而在现代社会,政府或国家的特权已经不复存在,其基本功能已经转换为对内保障和捍卫公民权利,对外捍卫国家主权;公民完全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自由行动,其中就必然包括对政府的监督、弹劾和罢免。不仅如此,这种状况也完全被台湾、泰国、乌克兰的动荡不安的当代现实政治乱局所证明。乌克兰事件本质上就是对亚努科维奇政权不满的一部分公民通过表面上的游行示威而实现实质上的权力更迭的一次重大反政府行动。每一个稍稍了解乌克兰局势的观察者都清楚,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下台与其说是被公民们罢免了权力,不如说是国外政治势力干预的牺牲品。通过这一事件,政权确实实现了更迭,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这一结果是乌克兰公民意志自由的一次彰显。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乌克兰人的这种意志自由表达是完全合法的吗?这里又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审视:一是参与游行示威的每一个公民是否是完全出于意志自由或自愿?二是公民在完全意志自由的情况下,他的自由权利是否是绝对的?显然,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答案都是否定的。根据前面的分析,任何人的意志都不可能是自由的,都是基于某种内在或外在的动机的激发。对于乌克兰人来说,参加游行示威这种行动本身只能说是一种意志行动而不能说是意志自由的行动,而如果一个人的意志行动不是自由的,就有可能受到了某种不可抗力量的约束或干预。外国势力对乌克兰人意志的影响在这一事件中是显而易见的。外国势力对乌克兰人意志的干预虽然谈不上强制或胁迫,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民意的欺骗、诱导甚至操纵。这是由信息不对称性传播原理完全可以解释的。因为我们如果单纯从乌克兰人的意志自由来解释根本是行不通的。没有这一事件,构成乌克兰主权一部分的克里米亚就不可能通过全民公决独立出去,而这一结果显然是参与游行示威的乌克兰人完全不愿意看到甚至完全反对的,也就是说这一结果与行使自由权利的乌克兰人的真正意志相冲突。当然,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同样是非常复杂的。但不管原因有多么复杂,乌克兰人的意志并不完全自由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再退一步说,即使乌克兰人的意志是完全自由的,那么他们难道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强迫他们行使同样的自由权利选出的总统如此不体面地下台甚至欲置其于死地吗?是谁赋予了一个公民占领政府办公所在地导致政府瘫痪国家机器失灵的危险境地的自由权利?难道他全然忘记了他当初出让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从而可以组成国家和政府的最终目的是更好地捍卫自身的权利了吗?因为如果没有忘记的话,他如此行使自由权利的结果所导致国家重大利益的重大损失这一事实本身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他自身的自由权利——在一个政府运转失效、社会动荡不安的国家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权保障。显然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意志行动——一方面想要表达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对自由权利的表达却让自己丧失了更多的自由。身处政治动荡之中的乌克兰人很可能早已丧失了对法权的敬畏和理性。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乌克兰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非常短暂,人民距离公民尚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在这个历史转变进程中,法性的启蒙、人权意识的觉醒需要付出某些定价、甚至是某些沉重的代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做惯了奴隶的人一旦成为了奴隶主很可能将会以一种更残忍的复仇方式对待过去的奴隶主,而不大可能因为自己过去的奴隶身份而对他自己的奴隶变得多一些同情和怜悯;直到有一天他的人权意识真正觉醒,此时,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意志只有当与别人的意志相协调一致”[4]时他的意志才算是真正自由的。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认为,当下台湾的政治生态乱象、泰国的政治生态乱象跟乌克兰人一样都是基于这个根本的原因;而欧美国家较少发生类似的政治乱局也不过是因为这些国家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启蒙思想的洗礼之后,人们的法权思想相对成熟、自我约束能力和理性精神健全。所谓自我约束本质上也是对法权的高度敬畏,具体从社会实践上表现出来就是行为的适度和妥协,其基本尺度就是法律规范。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指责、批评、监督和控告政府及其公务员,但不可以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随意阻挠政府正常行使行政权力。任何一个公民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从事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条件是他的意志必须与其他任何人的意志相协调。只有在这种意义上的权利才能被称为公民的权利、现代的权利和真正意义上的权利。也就是说,法理学上的权利是一种法律认定的公民对某种抽象的或具体的客体的所有关系,每个人的权利都与所有人的权利相协调。权利既然必须由法律所赋予和认定才有实质性的意义,那么任何权利都必然受到法律的限制和约束,一旦逾越法律的疆界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不允许超越自身的权利存在。法律的这种威严性正是通过其强制力彰显出来的,而强制力就是国家的执法能力。法律的这种强制被遵守的权力称为法权。由此可以推知,凡是执法能力薄弱的国家,法律的强制力也将无从体现,这个国家的法律也将形同虚设,在这样的国家里公民的权利也就无从保障,侵权行为将会大规模发生。政府被侵权将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国家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公民被侵权将会导致人人自危甚至革命爆发。需要强调的是,上述这些情况都是基于特权被取消的现代国家,因为一旦有特权存在,那么特权必然优先存在于政府手中,这样特权就可以利用自身的强大力量优先保障自己的权利,无政府状态也就无可能出现。至于人权的被普遍践踏也会因为法权的失效而使人们麻木不觉。也就是说此种情况人们无所谓权利与否,因为人们的权利意识尚未觉醒。古典国家的人们、处于奴隶地位的人们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在这里,人们对特权的敬畏远高于对法权的敬畏,因此,对于生活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听命于或臣服于特权乃是最普遍的意识和做法,又岂敢奢望享有游行示威、言论自由这样的现代权利呢?唯一能有的就是出于生存本能的反抗,但反抗的发生不到生存面临威胁之时绝无可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或暴力革命与其说是为自己争取权利,不如说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所以,这种情况跟我们所探讨的现代权利观有本质上的区别。在现代权利意义上,无论是无政府状态还是追求绝对的意志自由都不过是两种极端的权利观,是权利意识不成熟的典型表现。
二、义务行为
以上分析表明,权利的本质就是法律赋予公民的诸项自由,也就是自由行使的最高限度。很容易理解,在法律的限度内任何自由权利的行使无论是抽象的自由还是具象的自由权利都是主体真实意志或意愿的表达,而人的意志只有“做”和“不做”或者“行动”和“不行动”两种选项,无论选择哪一种,只要它是权利行为,主体的意志必然是真实的,这种意义上的意志表达即为自由意志行为。比如我按照自己真实的想法写一篇论文;如果我爱一个人我可以主动追求她;我有权利要求借我物品的人按时归还;当我不想被人打扰的时候我可以拒绝接受某人的电话,等等。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又都深切地感受到我们的很多行为并非是出于自愿或者意志自由,比如我们驾车遇到红灯必须停下;为某个单位雇佣,我们不得不干好本职工作;明知父母的一些话没有道理也不得不顺从;遇到单位组织的慈善募捐活动不得不违心地跟从众人参与……,诸如此类的行为占据了每个人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所有这些行为都不是出于个人意愿而是出于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能或对于利害价值的判断才不得不实施的,也就是说如果不这样做,当事人的利益就有可能受到损害;反过来说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为了获得对当事人利益攸关的某种好处,也就是边沁所谓的某种“功利”。具体说来,驾车闯红灯是明显的违法违章行为,而违法就意味着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受到法律制裁也就意味着当事人要受到某种物质损失或精神损失,即某种权利的丧失,而任何权利损失对于当时人来说都是一种痛苦。为避免遭受这种痛苦,当事人不得不遵守交通法规,虽然这样做对他未必有直接的好处。干好本职工作的动机则在于只有如此当事人才对得起雇主支付给自己的工资。听父母的话在很多情况下是遵从社会伦理惯例,而遵从伦理也就代表着子女的孝顺,因而能获得一个好名声;反之,则会被社会视为没有教养或者人品不好,也就是一个人的声誉会受到影响,这种影响当然会使得当事人内心痛苦不安。因此,当事人为避免这种痛苦宁愿顺从父母的话。违心地实施慈善行为也是为了避免个人声誉的更大损失。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四种情况都是有悖于当事主体的真实意愿或意志,但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些人类行为之间其实存在着性质上的重大差别。第一种情况即遵守交通秩序和第二种情况即做好本职工作跟后两种情况在行为背景和情节上是不一样的。交通法规是法律的基本规范,是全体公民的共同约定。做好本职工作是基于职业契约的要求,因为任何职业雇佣关系本质上都是契约关系,而契约关系不过是法律关系的一种简单形式,其本质都是主体真实意志的体现。两者的反面即是违法和违约,而违法和违约的结果都需要当事人付出直接而明确的痛苦代价。再来看顺从父母这种行为。在父母说话没有道理的情况下,子女顺从他们固然有获得好名声或避免获得恶名声的心理动机,但不这样做也不会对当事人构成直接的严重的利益损失,也因此行动的当事人不会承受像上面两种情况中的当事人所承受的巨大痛苦风险。同样的道理,我们从日常家庭生活中经常体验到类似的经历:即便是孩子犯了错误、做了错事、甚至犯了罪,作为父母依然对子女关心照顾,不弃不离。以我自己为例,假如我女儿吸毒,我明知道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我想我不会主动向警方报案。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推测这其中可能含有父母获得某种好名声的动机,但在我看来仅仅这一动机是无法充分说明类似于父母养育子女、子女孝顺父母这样的伦理行为的,因为这样的行为不仅仅存在于人类社会,也同样普遍存在于自然状态下的高等动物世界,虎毒不食子、群狼共同抵抗猛狮的进攻、动物配偶间的柔情蜜意尤其是雄性动物对配偶的拼死保护等都是我们熟知的事实,难道我们会因此设想动物界也存在着类似于人类这样的伦理道德文化体系吗?如果我们无法证实这一点,那么将人类间的这种行为定义为伦理性质也显得非常牵强,因为伦理道德作为一种典型的人类文化现象,毫无疑问是人类的创造物。对这种人类与动物界共有的自然的性质更合理的解释我认为是与生俱来的天性。所谓天性即自然之道或天理。自然之道犹如各种物理学、化学规律一样所揭示的乃是自然界的普遍的同时又是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事物只有如此运动才是正常的、合理的和客观的。事物不如此才显得反常和不合理。比如父母抛弃亲生子女,子女虐待亲生父母等都是有违人性的忤逆行为,这些行为通常都被人们视为违背伦理的行为,如果伦理在这里被理解为人性的自然之道的话我们认同;但如果伦理被理解为一种传统的社会构建秩序,这种观念显然无法圆满解释上述人类行为与动物行为的同质性。其实,人类间的这种自然之道彰显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绝不仅限于家庭关系内部。比如人饥饿了就要吃东西,天冷了就要穿厚衣服,性成熟了就知道追求异性,等等。这些行为跟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子女对父母的孝顺一样都是基于普遍的自然之道,而自然之道的本质就是因果法则或因果逻辑。这种行为显然不同于我们遵守交通规则或做好本职工作这样的行为,后者所遵从的是典型的法律逻辑或契约逻辑,而无论是法律还是契约都是人类创造的行为规范,是一种广义的文化或文明成果,也可称为一种社会制度或社会体制。至于违心实施慈善行动则更有可能出于避险动机,即避免在集体行动中被孤立或招致恶名的动机。这种行为已经与人类自然行为的自愿性和主动性拉远距离。至此,我们可以引出关于 “什么是义务”的问题了。
《现代汉语辞》对作为名词的“义务”给出的解释是:“公民或法人按法律规定应尽的责任。跟‘权利’相对。泛指道德的上应尽的责任。”[5]《现代汉语词典》对“义务”的解释跟《现代汉语辞海》基本相同[6],即“义务”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法律上应尽的责任;二是道德上应尽的责任。显然,义务跟责任关系极为密切。那么什么是“责任”呢?《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1分内应做的事:尽责任。2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因而应当承担的过失:追究责任。”[7]由此看来,义务与责任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法律或道德上应做的事;后者则是分内应做的事。问题是什么才是一个人“分内”应做的事呢?或者说除了法律和道德规定的事,人还有哪些事是“分内”应做的呢?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像吃饭穿衣和尊老爱幼这样的事既不属于法律范畴,也不属于道德范畴,似乎算得上“分内”应做的事。“分内”就是“本分以内”[8],而所谓“本分”就是“本身应尽的责任和义务”[9];如果这样推论是正确的,那么吃饭穿衣和尊老爱幼这类行为就成为人类的“责任”而不是“义务”。这样“责任”与“义务”的区别似乎就是前者是基于人性自然之道或因果逻辑的行为;而后者则是基于法律或契约关系的行为。但这种推论结果明显跟我们对于“责任”一词的习惯用法不一致。当我们使用“责任”的时候,比如说“做好本职工作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是想表达我们对于本职工作的自愿性、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如果我们说“吃饭穿衣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就显得很不妥当,虽然吃饭穿衣这些行为同样也具有自愿性、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那么,这样表达为什么让我们感觉别扭呢?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吃饭穿衣的自愿性和主动性是基于人类的生理本能,而做好本职工作这种行为则是基于人类的某种心理制导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尊老爱幼作为一种动物普遍的自然之道,同吃喝玩乐一样也是出于生理本能机制。由此,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将责任行为、义务行为和生理本能行为区别开来:责任行为乃是一种人类心理制导的分内行为,这种心理机制看来只有用叔本华的“责任感”[10]来解释才能说得通。“责任感”天然存在于人类的心理结构中,但在主体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显著的差异。叔本华认为,决定责任感个体差异的是人的“性格”[11],他认为,人的性格是一种稳定的来自于遗产的心理结构,不会受到学识、教育、年龄和身份的明显影响。[12]也就是说,天生具有强大责任感性格的人在人生的任何时候都会在具体的行动中自然而然地彰显出来;而天生缺乏这种基因结构的人虽可能通过后天的学习和经验积累从理性上懂得在工作上体现出责任感很重要,但在具体的行动中他总是很难做到;而如果偶然一二次做到了也是他基于利害关系的理性算计,而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这一观点可以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观察所验证,无需进一步证明。这样看来,责任行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正如一个人的性格从生到死都是很难改变的。
生理本能行为同样也是先天赋予的,但这类行为不同于责任行为,并没有性格方面的明显差异,而是普遍存在着所有人类甚至动物个体中。这些行为是维持人类和动物生存的最基本的最普遍的自然行为,因此具有客观性,遵循的是自然法则或自然之道,不受法律、道德或其他任何人类文化创造物的制约或干涉。按照这一观点,很多被传统定义为伦理道德范畴的人类行为应该被重新定义为本能行为。如尊老爱幼、夫妻之间的互相关心照顾、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共处、不损害别人……这些行为通常都是伦理学研究的范畴,并被认为具有道德价值。而在笔者看来,这些行为本身都是自然的,是本来就应该这样做的;进一步说是生存的必然要求,是合乎自然之理或合乎天理的行为;反之,不这样做才是不正常的、不合理的,有违人性本能的。人类发明创造的道德标准应该高于这个自然的尺度。如果一项行为能被冠以道德行为或德性行为,这项行为不仅仅应具有利他价值,而且还应建立在这个必要基础之上——行为主体跟行为受体(行为对象)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血缘关系、隶属关系或契约关系。像自愿救助跟当事人没有任何关系的失学儿童,为一个生命垂危的陌生人鲜血,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等这样的行为才具有真正的德性价值,像雷锋、陈光标、陈贤妹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被定义为道德高尚之人。反之,我孝敬我的父母能说我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吗?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分内之事;如果不这样做我甚至就失去了做人的基本资格;同样的,一个人捐献肾脏挽救自己父亲的生命也不能在道德上评价过高,但如果此人挽救的是一个陌生人的生命,他的这一行为则具有极高的德性价值。所有的正义行为都是基于上述关系之外的重大利他行为,具有最高的德性价值。不难看出,我们在此探讨和重新建构的这一新型德性观既不同于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也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伦理观。儒家思想是古典社会的产物。在古典社会,人们尚未建立起清晰的权利、义务、责任和本能概念,人权思想意识尚处在混沌状态。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理念,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基本行为规范(即所谓“三纲五常”)的儒家伦理思想看似包罗万象,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其基本设计架构充斥着太多的理想主义成分,它以否定和异化人性的自然属性为代价,以不切实际地人为拔高人性的普遍道德水平为手段来构建理想的社会伦理秩序,结果沦为一种“瞒和骗”[13]的文化,造就出“瞒和骗”的“国民性”。西方基于基督教义的伦理观从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中国儒家思想,而现代西方伦理思想又充斥着浓重的形而上学色彩,像康德的所谓“绝对道德律令”迄今缺乏实践上的证据。这些形形色色的古今中外伦理观长期占据着伦理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却因为与人类实践的脱节或背离而无法显现出人性哲学的启蒙与塑造功能。必须强调的是,道德理念虽可以重新建构,但建构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更好地衡量、甄别和评判人类的一部分实践行为的性质和价值,而不是在全社会强制推广普及这种道德体系。在笔者看来,道德科学或道德哲学的基础应建立在自然人性和社会人性演变规律的精确考察的基础之上,任何道德理念的创建首先应当是对人性哲学的重大发现,是一种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的证明和揭示。其次才是对这一理念的应用技术的谨慎探究。一种道德理念未被广泛证实之前就在全社会大规模强行推行不仅不可能获得预期的理想效果,反而会有可能招致人性的堕落和社会运行的风险。因为既然德性行为是一种利他行为,显然这种行为跟人类强大的利己主义本能相抵牾,人类要实施利他行动首先要克服这种强大的本能动机,很容易理解,在没有外力强迫的情况下,很少有人愿意做出这类利他行动;如果实施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迫不得已。反之,如果假借利他行为具有很高的德性价值而利用权力在全社会强制每个人效仿或实施这种行动,则这样的行动因为不是出于自愿而决不会长久;一旦强制力量消失,则人性立即恢复到其本来的状态。而强制别人做好事本身就是一种反人类、反人性、反人权的非义行为。也就是说,利他行动只能出于个人的自愿即意志自由,才会有实际的效果和德性价值,而出于各种功利动机的利他行动从本质上说不具备德性价值。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叔本华才将道德行为的基础建立在人类天然的“同情心”和“责任感”两座心理结构上,[14]并且同样认为德性只与人的性格有关系,不能通过强制或教化来获得或提升。[15]在此,我们看到德性行为跟责任行为有共同的心理基础,区别在于,责任行为是做分内之事;而德性行为则是做非分内之事。显然,德性行为的价值远高于责任行为的价值。
责任行为和道德行为具有共同的心理基础,那么这种共同的心理基础跟我们遵守交通规则这种行为的心理动机有什么不同呢?很明显后者是一种理性判断: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法律的规定,是必须要这样做的;或者说不这样做首先是要受到法律制裁,其次是人身安全面临巨大风险。而作为责任行为和道德行为基础的同情心或责任感则是一种人类心理结构中的非理性成分,正是这种成分主导了人类意志的方向。更进一步说,责任行为或道德行为主体在其心理结构中同样具有理性成分,只是此时这些理性成分的能量小于同情心或责任感的强度;这一特征恰好与我们遵守交通规则的心理机制相反,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的理性力量战胜了各种非理性成分的力量,控制了意志的方向。我们将基于这种心理机制的“分内”行为定义为“义务”行为。不过,这里的“分内”不再是一个含混的内涵,而具有明确的界限,它具体指向法律关系或具有法律性质的契约关系所划定的范围。也就是说,义务行为并非出于本能或意愿,而是出于理性制导。由此很容易推演出当一个人理性处于非正常状态的时候,他的行为不具有义务性质,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或受到相应的法律追究。除此之外,一切义务行为如不履行必然受到法律的追究,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同时,根据这一定义可以推知,在有法律之前即在政治共同体或国家产生之前,也同样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正如此时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权利一样。的确,仅凭我们的理性和凭借我们对于动物世界的观察就可以知道,在自然的存在状态下,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出于本能,都是遵循自然法则。
由此可见,义务行为跟权利行为一样都是出现在法律制度产生之后的人类社会状态中。又根据我们前面已经阐明的观点,在古典法律秩序下,鉴于特权的存在或者说法权的效力低于特权的效力,此时的义务还属于古典性质,与权利的地位完全不对等,或者说此时的义务本质上是对特权的臣服而不是对法律的尊重。鉴于特权是绝对的权利,因此,此时的义务也是绝对的义务。全体国民都是君主的臣民,都必须对君主效忠,这种义务就是绝对的,君主的权利也是绝对的,此时这种权利即可称为特权或权力。义务的现代概念滥觞于经过启蒙运动洗礼后的现代民主国家的产生。古典法权经过启蒙催化而觉醒生长出现代新质,从而跃升为最高权力,成为裁决一切权利公允性的契约性和公共性尺度。在现代法权规范下,义务只对法权负责,而法权是全体公民意志相互协调的结果,因此义务就具有了相对性,这种相对性就是对自身权利的制衡。在现代法权下,权利和义务的数量是对等的,有多少种权利就必然有同样数量的义务。一个人有权利从事任何性质的生产创造活动,他就有同样的义务不妨碍其他任何人从事同样性质的生产创造活动。这就是义务与权利的所谓相对性或对应性。然而,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义务和权利除了这种相对性外,还具有互补性:权利行为是利己不害他的行为,义务行为是利他不害己的行为,两类行为的总和构成人类的全部正常的社会行为。从这里也可以推断出,在义务行为与权利行为之间必然存在着部分交集,即还有部分行为是既利己又利他的,这部分行为既是人类的权利同时也是人类的义务。在法律框架内一切基于满足人类身心健康动机而进行的生产创造活动都具有这种性质,无需例证。这三种社会行为构成了人类社会实践的正常和普遍部分。
[1]【德】叔本华.作为世界和表象的意志[M].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211.
[2]【德】卡尔·贝克.独立宣言[M].彭刚译.北京:今日世界社,1956:1.
[3]王德禄.人权宣言[M]北京:中国图书刊行社,1989:1-2.
[4]【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M].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54.
[5]倪文杰.现代汉语辞海[Z].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4:1393.
[6][7][8][9]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370;1444;324;50.
[10][11][12][14][15]【德】叔本华.论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72;131;98;144;126.
[13]鲁迅.论睁了眼看[G//].鲁迅全集·坟.北京:人民出版社,1925:
(责任编辑:孙书平)
On the Human Right Acts and the Duty Acts
Ma li-xin
(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
There are two kinds of basic common human acts in philosophy of law: right acts and duty acts, all of which have been establish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so-called human social political community. The right acts are one of will-liberty that is limited and must be coordinated with any other social member according to the modern spirit of law. Whether the right of law is the supreme in all of social rights is a fundamental stardard which identifies one society as the classic or the modern. Differrent from human ethical acts and the instinct ones, the duty acts are intrigued by a stronger reasonal machanism more than a non-reason elements and together make up the right ones.
Right Acts;Duty Acts; Philosophy of Law
主持人语
马立新
2016-05-16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数字艺术伦理学研究”(13BA010)、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数字艺术德性研究”(13YJAZH063)阶段性成果
马立新(1966-),男,山东章丘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重大哲学前沿理论研究。
B104
A
1008-7605(2016)05-0001-09
特别策划·数字艺术法哲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种基于数字技术(以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型艺术形态——数字艺术(以网络游戏和网络文艺为代表)迅速崛起,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改变了原子艺术(即传统艺术)励精图治数千年所建构起来的相对稳定的生态格局。与原子艺术相比,数字艺术在生产、传播、消费和监管诸方面、诸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嬗变:一方面数字艺术呈现出无与伦比的多样化、自由化、民主化、奇观化,另一方面也呈现出日趋严重的致瘾化、低俗化、虚假化、盗版化。所有这些嬗变从本质上看都是人类艺术实践行为性质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数字艺术语境中,传统意义上通常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艺术教条——艺术无害论——所涉及的人类艺术行为的性质已经逾越了简单的伦理范畴,而上升为一个法理命题,必须用法哲学的视角进行关照方有可能为数字艺术的健康发展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作为数字艺术法哲学研究的奠基,本组文章尝试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逻辑出发,对上述前沿命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