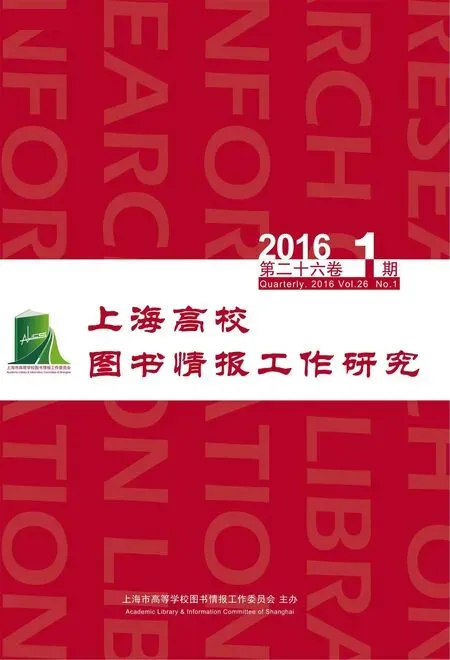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学徒思维”现象
吴志荣(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图书馆 上海201815)
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学徒思维”现象
吴志荣(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图书馆上海201815)
本文对“学徒思维”概念及其危害进行了分析,揭示近20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的“学徒思维”现象,对“知识发现”、“藏阅合一”、“学科馆员”等案例进行了剖析,并分析了产生“学徒思维”的原因。最后指出,我国图书馆学学术研究一定要摆脱“学徒思维”,才能取得自我主张。
学徒思维自我主张图书馆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学徒思维”现象越来越普遍,甚至习以为常,而强调引进的外部学术应该适用中国国情、适应学科本土化发展以及学科本身需要具有创造性的声音相当弱,使得笔者认为有必要揭示“学徒思维”现象,让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认识到这种思维方式的误区。
1 “学徒思维”的概念及其危害
1.1“学徒思维”和“学习者”的区别
本文所指“学徒思维”的概念是指“一直以外部学术为瞻,且不经思考和批判地全盘接受,从而使得自身永远处于学徒状态的思维方式”。
需要指出,“学徒思维”的概念和一般意义上的“学习者”相比,是有所不同的。
我国的现代科学体系来自于国外先进国家,清末的洋务运动以及而后的共和革命和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国外的先进学术大量输入我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各学科的发展。诞生于20世纪初的我国现代图书馆学,同样也是来自国外。先是取法日本,而后追随美国。早期的职业图书馆学家大都留学美国,如沈祖荣、杨昭悊、洪有丰、李小缘等。因此,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是必须的。历史证明,闭关锁国或闭门造车都是没有出路的。就是在现在或者将来,我们还是要具有国际视野,紧盯国外先进学术发展,学习国外先进学术,才有可能站在国际学术前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永远是“学习者”。
同时,当今时代,学科交叉现象严重,一个学科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也是无可厚非的。例如,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借鉴哲学、数学、社会学、教育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很有必要的。
然而,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成为能思的和能批判的,而不能成为全盘依赖、丧失反思能力的学习者,不然是绝对不利于自身学术的真正发展的。
以上所描述的“学徒思维”的概念中,所涉及的“一直”、“全盘”、“不经思考和批判”等含义,是“学徒思维”不同于“学习者”的关键。
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沉溺于“学徒思维”的研究者崇拜并依赖的外部学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外先进国家的图书馆学思想或做法;二是其他强势学科的研究成果。
任何来自英美图书馆界的思想或做法都被奉为经典;反之,如要开展任何研究,都要从国外先进国家的图书馆学研究成果中找到出典,不然就认为该研究偏离主流方向。同样,跟图书馆学有关的那些强势科学(如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等)出现了什么新的研究方向,立即会引起“学徒思维者”的兴趣,如能沾上边,就全盘引进。
最不能容忍的“学徒思维”,是实际对外部学术中的某些理论或方法并不完全掌握,却以偏概全,全盘吸收。
1.2“自我主张”对学科发展的意义
“自我主张”的概念有“独立思考”、“创新”等含义,是针对“学徒思维”的思维方式。“任何一种真正的学术都需要在其发展进程中经历过一个决定性转折,即摆脱它对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并取得其自我主张。”“它在广泛的对外学习中要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1]对中国的研究者来说,取得自我主张的总体标志,是在形式上,学术名词要真正根植于本民族的“活的语言”中,而内容要深入中国的社会现实本身之中。
我国的前辈学者在这方面具有十分强烈的意识。例如,1925年6月,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被推选为董事部部长的梁启超发表演讲,明确提出了要建设和发展“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命题;1926年创刊的《图书馆学季刊》的创刊词再次表明了中国图书馆学学者计划吸收西方图书馆学,结合中国传统的文献收藏整理传统和学术,“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的决心。沈祖荣、杜定友等学者也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沈祖荣对图书馆中国化问题有较为深刻的思考,认为“中国式的图书馆采用的技术方法应代表中国文化,合符中国人性”;杜定友也提出:“外国的图书馆学未必能适应中国的情况”。他们也为此付出了努力。刘国均和杜定友都创造性地提出了“要素说”,杜定友更是在1928年,早于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就提出了“图书馆的功用,就是代社会上一切人记忆一切的实际上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这样的论断。[2]
在20世纪,我国图书馆界出现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汉语主题词表》这样意义重大的成果,还出现了“情报检索语言”这样的分支学科。
这里的“要素说”、“公共脑子”、“收藏整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汉语主题词表”、“情报检索语言”等术语,就属于根植于本民族的“活的语言”。
这种对外部学术持能思和能批判的意识从而取得“自我主张”的努力,正是我们今天要继承的。
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学徒思维”弥漫在我国图书馆学各研究领域中,对外部学术进行本土化研究或者本土创新而取得“自我主张”的研究成果很为少见,大量的研究都亦步亦趋地跟随着外部学术盲目地进行着,使得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跳跃性很大,研究热点转换很快,从而缺乏研究的系统性和一贯性,其中很多研究内容则超出了图书馆学研究的范畴。前辈们提出的创建“中国图书馆学”的目标更是变得十分渺茫。
2 “学徒思维”的案例分析
以下列举一些对我国图书馆学影响巨大实质却属于“学徒思维”,无助于我国图书馆学学科发展的案例进行分析。
2.1关于“知识发现”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发起于计算机领域的“数据挖掘(DM)”及其相关概念“知识发现(KDD)”研究被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一些研究者纳入本学科研究范围。
“知识发现”是1989年在美国底特律召开的第11届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上提出的,是指“从数据中获取正确、新颖、有潜在应用价值和最终可理解的模式的非平凡的过程”。涉及到模型功能和基函数、搜索算法等研究,是计算机科学,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的研究。[3]
笔者将“知识发现”作为在“中国知网”中进行检索,获得4221条记录,绝大多数的论文均为计算机学科的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然后又将“知识发现”和“图书馆”作为
重新查找,共查到53条记录,这些由图书情报学专业人员所撰写的论文内容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介绍知识发现的概念(均抄自计算机学科领域);二是提出应该挖掘用户使用图书馆的数据来了解用户阅读倾向和阅读行为;三是少量提到知识发现要结合领域本体或文本结构。没有一篇论文是具体论述如何发现知识的。
图书馆所存储的文献中隐含着巨量的知识,图书馆与“知识”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与“知识”有关的研究会引起图书馆学界的关注,是能够理解的。然而,这类研究并不是图书馆学研究的范围。
“知识”是一个十分抽象而又复杂的概念,要把知识这个概念说清楚是极其困难的。我国哲学家金岳霖曾经出过一本专著——《知识论》,该书洋洋数十万言,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有思想深度的知识论体系,系统地论述了知识的来源、知识的形成以及知识的可靠性、衡量真假的标准等问题。人工智能领域是否能通过运算在数据库中发现“知识”也是很不确定的,而图书馆学的研究者研究知识发现就更不靠谱了。
正因为这样,大多图书馆学的研究者都避开使用“知识”一词,如用“信息检索”和“文献检索”而不用“知识检索”,用“信息组织”而不用“知识组织”,用“文献信息交流”或“信息交流”而不用“知识交流”(宓浩曾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知识交流”理论,但其他基础理论研究者一般都不用这个概念)等。20世纪80年代初,彭修义提出图书馆学应该研究“知识”,提出要建立一门“知识学”,得到当时一批急切要提高图书馆学理论层次的中青年图书馆学研究者的追捧,但后来也不了了之。
当前,一些数据库商宣传其推出的软件系统就有“知识发现”的功能,实际上只是检索到一批相关的文献而已,还远远没有达到快速发现相关知识的目的。
笔者认为,关于“知识发现”的研究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学徒思维”的案例。就如上所述,我国“学徒思维者”们崇拜并依赖的外部学术来自两个方面,而关于“知识发现”的所谓研究则既是来自国外发达国家的、又是强势学科的,那就更让“学徒思维者”们顶礼膜拜了。
此外,来自企业管理研究领域的“知识管理”和“知识转移”等的研究出现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也是这种思维定势造成的。
2.2关于“藏阅合一”的理念
20世纪90年代,关于国外高校图书馆普遍采用“藏阅合一”、“师生合一”、“书刊合一”、“语种合一”,即“四合一”的布局模式的理念传入我国,引起我国高校图书馆界的关注,其中“藏阅合一”、“大开间”、“全开架”的理念,更是被大多数图书馆人所全盘接受。可以说,当时在我国图书馆学界和业界,没有任何人质疑这种模式是否有问题,这也是“学徒思维”的典型表现。
而实际上,所谓西方高校图书馆都采用“藏阅合一”、“大开间”、“全开架”模式,以方便读者、从而提升图书借阅量的理念是我国图书馆界根据“学徒思维”杜撰的。(详见拙作“藏阅分离”模式或将回归?——关于数字时代图书馆布局的思考,载《大学图书馆学报》2009年第6期)[4]
这种杜撰出来的理念,让我国图书馆建设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资金,而且使得大量在21世纪建造的图书馆纸质馆藏的存储空间捉襟见肘,甚至已无处可放,并影响了符合当代图书馆进一步发展的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的空间的拓张。
该案例很好地说明了“学徒思维”的危害。
2.3关于“学科馆员”制度
为了提高服务水平,我国高校图书馆从20世纪90年代起引进了国外的“学科馆员”制度,试图更好地为学校的各学科建设服务。
然而,国外高校的教学方式不同于我国大陆地区的高校,也即国外高校的教学是离不开图书馆的,教师在开课前一定会把这门课程的参考文献目录交给图书馆,让图书馆准备好有关文献以供学生阅读;而大陆高校的教师就凭自己的讲义来授课,基本不会推荐学生阅读什么参考文献。在我国大陆地区,一个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可以从来没有利用过图书馆,而在国外肯定不行。
此外,国外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也是与教师或科研人员密切相关的,教师或科研人员是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同时,国外高校图书馆的人员素质与国内高校也有差距,国内高校图书馆中,既有某学科的学科背景,又有图书馆学学科背景的馆员为数很少。
熟悉专业库藏和专业文献获取渠道,同时又熟悉服务对象的专业情况,而服务对象又对专业文献有经常性需求,这三个因素是学科馆员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缺乏这些因素,生搬硬套西方的东西是行不通的。
因此,国外的学科馆员制度在国内变得水土不服。许多著名高校图书馆的所谓学科馆员为了嵌入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可谓是费劲脑汁,有的甚至为教师写开题报告,变相地成为教师的科研秘书,脱离了学科馆员的服务范畴。如果一个图书馆馆员的服务离开了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场地、设备,那么他的服务已经脱离了图书馆的服务范围。因此“对于‘学科馆员’这样的西方事物,仍然要客观地看待,科学地对待,博采众长还需面对现实,洋为中用还需以我为主。”[5]
可以说,“学徒思维”的案例很多,如云计算、关联数据、慕课、大数据……,所以必须揭示这种现象带来的危害,才能让我国图书馆学界对外部学术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
3 “学徒思维”产生的根源
3.1我国图书馆学的学科基础比较薄弱
这是“学徒思维”现象产生的主要根源之一。
我国的图书馆学诞生于20世纪初,学科内容基本来自于美国,1930年代曾经出现过一波学科发展的高潮,而后遭受战乱,学科发展基本停滞不前。1949年后,一方面研究力量薄弱,一方面又面临闭关锁国的形势,同时又受前苏联图书馆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科发展十分缓慢,而后在1966年至1976年期间又遭受了全面的挫折。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学科才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没有持续多久,在80年代末,随着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进入低谷,学科发展开始偏离轨道。不断涌现诸如图书馆发展战略研究、信息产业研究、有偿服务研究、图书馆精神研究、图书馆权利研究、图书馆信息公平研究等偏离图书馆学学科发展正确轨道的研究。
这种状况导致我国目前的图书馆学的学科基础比较薄弱。例如,至今对什么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还不统一,而这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3.2缺乏对学科的自信
图书馆学诞生之初就遭到很多质疑,认为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均为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是属于对“术”的研究,不能成为一门学科。而后虽然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在图书馆学理论上的贡献,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得以逐渐巩固,但由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而图书馆的社会地位不高,直接导致了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也不高。
这种状态让一些图书馆学研究者很不甘心,他们总是力图摆脱这种局面。因此,十分自然的,那些宏大的、形而上的、高科技性的、又似乎与图书馆学研究能扯上关系的观念或方法,常常受到那些研究者的青睐。
3.3不理解图书馆的基本功能和图书馆学存在的基础
作为“将人类记忆的东西移植于现在人们的意识之中的一个社会装置”的图书馆,是人类社会为了收集、整理、保存和提供记录人类知识的载体,也即文献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因此,图书馆的存在是有深刻的社会基础的。图书馆学研究就应该紧紧围绕图书馆的基本功能及其发展以及图书馆和社会的关系展开,这是图书馆学得以存在的基础,是图书馆学学科的核心内容。那些“学徒思维者”们对这些与图书馆建设与发展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并没有很深刻的理解(或没有兴趣理解)。因此,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否能符合我国图书馆发展的实际情况。
4 结语
尼采曾说:在很长的时间内,希腊人似乎要被外来的东西压倒了,他们的文化是一大堆外来形式和观念的混杂——包括闪族的、巴比伦的、吕底亚的、埃及的等等,而他们的宗教则仿佛是东方诸神的一场混战。但希腊文化并没有因此成为一种机械的混合物或一种“装饰性文化”,因为希腊人听从了德尔斐神庙“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坚定而诚实地反省了自己真正的需要,换言之,希腊人终于取得了其文化上的自我主张。[6]
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者应该认识到“学徒思维”的危害,要批判地接受外部学术,取得我国图书馆学的自我主张。科学研究是需要独立思考的,需要创新的,并不是那些运用“学徒思维”的思维方法所取得的“成果”所能取代的。
[1]吴晓明.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J].学术月刊,2012(7).
[2]范并思.20世纪西方与中国图书馆学——基于德尔菲法测评的理论史纲[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3]郭萌,王珏.数据挖掘与数据库知识发现综述[J].模式识别与人工职能,1998(3).
[4]吴志荣.“藏阅分离”模式或将回归?——关于数字时代图书馆布局的思考[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9(6).
[5]蔡迎春.学科馆员:期望与实践的背离[J].图书馆建设,2005(3).
[6](德)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吴志荣研究馆员,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图书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