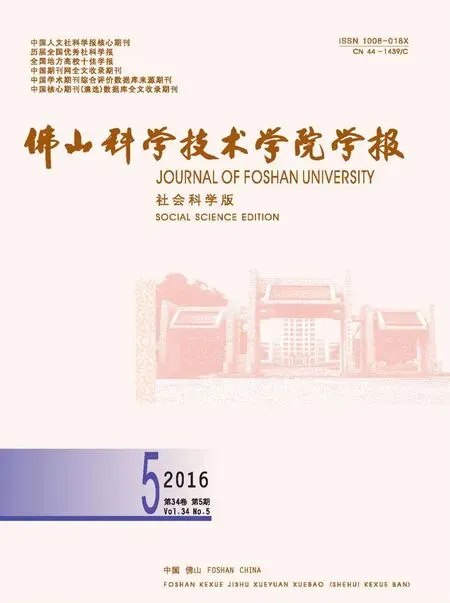管理哲学视野:荀子社会治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岳梁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215213)
管理哲学视野:荀子社会治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岳梁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215213)
思想的事情是今天中国的当务之急。生活在中国古代社会巨大变革时期的荀子是中国古代的思想者,他既要“继绝学”又要直面当时的社会现实,以世俗的人为“目的”提出了科学的社会治理思想:社会治理的核心是秩序——“正名”,这就是“礼”——“隆礼至法”;治理天下的行为标准,那就是“礼义制度”;确正名实议定等级,这就是“分辨”;治理是可以通过教育进行的,这就是“性善伪”——“人性”可塑与礼义教化;治理的最高境界,就是“圣王”的政治制度——“宜”;治理的最高目标,就是人民富裕、国家富强;实现民富国强的有效途径,一定是儒家的“以政裕民”、共同参与。
荀子;人性;礼义法度;职能管理
我们今天的人没有判断力,“跟着感觉走”就是时代最经典的浓缩。至少说我们的判断力是病态的,跟着堕落的世风亦步亦趋。今天的人对现实蒙着眼睛,反而在诋毁先贤时能力出众,这就是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因为他们无视现实,所以他们只好否定历史。西方的现代化是通过文艺复兴实施的,而文艺复兴就是透过古代文明的再发现与新认识才达成的。中国的现代化也理应如此,所以关键在于“理解与解释”及“理解与解释的角度”,我们必须尽心弘扬传统人间美德,久远的中国传统的农业时代的思想仍然可以为今天的现代化的中国的社会治理服务。荀子(前313—前238)的美德就值得大力弘扬,荀子的社会治理思想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高峰”,至今仍有巨大的生命力:“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我们的民族性与创造性。笔者认为,处于大变动时代的荀子是世界级的“管理大师”,既主张“与时俱进”又主张“法先王”,认为变为“天地之大道”,从而成为职能管理理论的最早提出者与集大成者。或许,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不很重视纯知识(为知识而知识)的探求,而是致力于社会秩序的建立与和谐,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才使荀子的世俗管理思想独居世界之最。但,放眼世界,非常遗憾,人们看到的,只是西方、只是西方职能管理理论的“提出者”泰罗,因为泰罗“明确”地提出了管理本身就是一种职能,而且泰罗的管理理论(管理哲学)据泰罗自己说,在各个领域都是适用的,即泰罗理论是一种社会治理思想。也就是说,当今的管理理论一般认为来源于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产物,是在上帝“死了”以后,即人是主体——理性人实现以后的产物,一般认为就是法约尔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与控制的管理理论,它以组织为基础,以效率为目标,以分工化、标准化、系统化等为特征。实际上,这种理论,至少在中国很多很多年以前就能“找到”:至少理性人的追求是这样的,荀子明确主张“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要求“祛魅”,这种“知天”与“不求知天”的划界(当然与近代西方“理性宰制的态度”有区别)比康德早的多。所以,在很早,中国就已经显现了职能管理,只是没有西方泰罗以来的精细化、标准化、具体程序化、行为(动作)化特征罢了。
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本土文化的定型期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自然,在笔者看来,此时的管理职能思想也就成熟地飞越长空,荀子就是这一管理职能思想的最重要的代表。荀子的管理思想令后人——赢者通吃而无所不能的人——惊奇与发呆,荀子超越了传统规则(一切规则)与时代理性,管理本身就是一种职能,这比西方早了两千多年。荀子的管理哲学思想或至高境界,用荀子本人的话,可以概括为:“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1]80
无论是从个体还是从国家来讲,《大学》开宗明义,不仅要求革旧更新,使人们达到最好的理想境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且明白地告知人们达到这种理想境界的步骤或程序(知所先后)——“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的行为路径。这里的“齐”就是“治理”的意思。无论是天子还是庶人,搞好自身的品德修养都是根本。当然,一般认为,只有到了宋明理学时,中国才真正地实现了理性化,即被称为“经验常识天然合理”与“人之常情天然合理”[2]137。
荀子生活的时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虽然影响较大,但仍然不是主流的意识形态,但荀子却主张共同参与治理社会。儒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那是到了汉武帝的时期,但也正是从此后“荀学”被逐渐淹没,荀子的管理思想自然也不会被彰显。
一、“曲得其宜”的管理境界
万事万物包括人,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但万物“有一”,这就是“道”;物能“显理”,而人能“知道”。管理就是“知道”与“用道”,人能使万物秩序和谐、与人合一,荀子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曲得其宜”,“宜”就是适宜、合理、契合、适度。管理的要义是设定确定而科学的目标,以目标行使管理。这就是说,管理必须有界限范围,“凡物皆有蔽”,荀子的界限范围就是“知有所止”。荀子列举学习而论之:“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已不足以浃万物之变,与愚者若一。学,老身长子而与愚者若一,犹不知错,夫是之谓妄人。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1]229。
荀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管理大师,而且具有科学思想,并凸显着辩证的思维方式,即在物与人中提升人的重要性,“人是目的”。荀子认为,人有“能知”的本性,物有“可知”之理。一方面主张理性,反对“神话”,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大天而思之,熟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熟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熟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熟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熟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熟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1]174;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的“局限性”或限制性,“学而后知”,即使“圣王也是如此”,因而必须按照“规律”办事:“人主不可以独也。卿相辅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将有卿相辅佐足任者然后可,其德音足以填抚百姓、其知虑足以应待万变然后可,夫是之谓国具。”[1]129总括来讲,就是“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1]8。荀子的最高管理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当时而动,物至而应”——“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1]81。既要满足人的欲求,又要节制人的欲求;既要尊重自然规律,又要“知天”、“用天”;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宜”。
在荀子的视野里,衡量事物的正确标准自然是“道”,合于道为宜,离开了道,任何的选择都可能带来灾难。具体地讲,在管理中,这个道那就是“权”或“衡”,即“衡不正,则重县于仰而人以为轻,轻县于俛而人以为重,此人所以惑于轻重也;权不正,则祸托于欲而人以为福,福托于恶而人以为祸,此矣人所以惑于祸福也。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1]244。当然,荀子所谓的道,就是“礼义法度”。也就是说,荀子所追求的管理境界是“宜”,而合乎“礼义法度”就是“宜”。
荀子主张“知行合一”,强调学与行的结合,强调积学、践履、改变对人之为人的重要意义,学可以成圣——“圣人者,人之所积耳致矣”,而不学则“为贼为愚为贫”。这里,荀子继承了孟子的思想。孟子认为,“人皆可成尧舜”。这说的是教化的作用,即人通过学习,可以成为尧舜。孟子还最早提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3]184。
知识的“圣”与政治的“王”的“圣王一体”是荀子治理理论的重要特色。荀子虽然主张“以圣王为师”——即“学”的必要,但强调的却是“法后王”,更重要的则是“从道不从君”,这完全不同于后来的“法尧舜”的儒家与“尊君卑臣”的法家主张。
职能管理,自然是以效率与结果为标准的,这就要求行为选择不是主观的,而且有一整套经过试验的标准与程序。实际上,荀子的思想也是这样的,“道”就是行为的客观标准,“心的行为选择不是”随意的:“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1]244。也就是说,“心”的选择不可靠(没有经过试验),而外在客观的“礼义”标准(经过试验的)才可靠。
二、性善伪——“治理”改造人
管理的主体是人,管理的客体主要的也是人,因而管理的前提就是对人性的假设,西方是人性恶的理性人假设,霍布斯的丛林论就是如此,每个人都趋利避害,都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且这是合理的;但当追求自己利益时有损害他人利益的可能,因而要“规范”,这就是法律,法律管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针对孟子的人性善,荀子提出了人性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成为性恶论的代表,或者说,荀子的思想特色是被“性恶论”所标识的。实际上,在荀子看来,“人性伪”,即人性是一个“伪命题”,即不存在人性问题,不存在一个先在的或先验的人性问题——善或恶,人就是人,就是存在着的人,就是生活着的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看清人,而且人是会变的,“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即“性善”是后天“伪”的——外在形塑的(当然这与人内在的“义”、“辨”、“具”等有关,但这些都是“潜能”,它与“实能”是不同的)。所以,荀子在《正名》篇中给性下了定义,“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这是说自然生命的本身就是性,人的动物学生命就是自然生命,即性无善恶——“生而有”、“天之就”、“无待而然”,性完全是中性的。换句话说就是,在荀子看来,人性无善恶,它既可以成善也可以成恶,成恶成善在于后天的“行为”即“伪”。所以,荀子所论证的是如何达成“善伪”的[4]72-74,即荀子对人性的论述是为其社会治理——“重建社会秩序”服务或立论的,因为荀子的目标指向是“圣王之治,礼义之化”。
许慎的《说文解字》说:“伪,诈也,从人为声”[5]166。那么,诈是什么含义呢?许慎说:“诈,欺也,从言其声”[5]56。对于性,在《礼论篇》中,荀子站在研究事物本质的角度是这样解释的:“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1]205这就是说性有三层含义:一则,性是事物本来就存在的,“生而有”;二是,性要显示或展示出来,这是后天即人的“事”,即“伪”是后天人为(伪有矫正的含义)的,但性是根本的,是后天“作为”的载体;三是,性又必须后天的作为,否则无以显现。圣人通过“性伪合”而成就“一”,即“性与伪”“合二为一”。荀子在《正名篇》中,站在对传统“刑、爵、文”传承的角度对“性”又有了进一步的解释:“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1]232而“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子明确指出,性是人生来就有的,而情则是性的本质,而欲望又是情的必然产物,所以人“必不免于有欲也”:“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不免也。”[1]242因而,不可能消灭(去)欲——欲不可去,即使尧舜也不能“去民之欲利”,而只有“道(礼)”才能引导欲——“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当然,只有到了宋明理学中国才“真正”实现了理性化,即“经验常识天然合理”与“人之常情天然合理”[2]137。王阳明把人所具有的向善道德心称为良知,这是把良知作为整个道德哲学的基础,这重开了儒家的意识形态——道德价值一元论。这否定了秦汉以来传统的精英主义,但真正的社会治理又必须否定精英主义的倾向。在笔者看来,荀子的思想就潜含着反精英主义的因子,即“性善伪”——每个人心中都有“良知”——“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质言之,荀子的“性恶论”是“人之性恶”,即恶是人性的一部分,而不是“人性本恶”。
中国农业化社会的整合应该是从孔子的儒家开始的,儒家重视与提倡孝道、纲常礼教与教育,所以到了荀子时儒家文化的社会整合意识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荀子既主张“法先王”,又主张“法后王”。意识形态的意义就是达到认同,从而整合社会,或者说用意识形态的认同所产生的组织力量来实现——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社会整合。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儒家的)就是“道德价值一元论”,即从个人内心的道德感出发推出孝道与家庭伦理、王道与仁政,从而把道德作为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孔子就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传命”。按照专家学者的研究,这本身就是“性善伪”的落地实践。
荀子一开始就是理性的,认为人有“知性”,不仅特别重视“心”的“自律性”,而且“物之理也”“用心”“可以知”。荀子强调“人为”即改造自然,在首篇《劝学篇》中,荀子就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1]5“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1]14荀子强调“性恶”、“解蔽”、“正名”——“名分使群”、“天人之分”;荀子的“类”具有明确的社会内容,其“人道”是“非先验的”现实的“社会规范”。
从常识理性来讲,无论是统治还是管制,无论是管理还是治理,其本质或最终追求无非就是人民的幸福、和平和有尊严的生活。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荀子对此是非常清楚的,所谓“治世”、“圣王”、“民意”即如此。
认识在于“解蔽”,而只有“虚壹而静”才能“解蔽”。荀子以人的社会存在为依据,首先承认“事物”的客观性,指出人的欲望的客观性与合理性:“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养五綦者有具,无其具则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1]110荀子主张“有具”而“长养”。但其客观性可能被“遮蔽”,所以荀子在《解蔽》中入手就告诫人们“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而现实中这些确实可能都是“蔽”:“数为蔽,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1]219按照现在解释学来讲,在荀子看来,“前理解”即“私”可以“遮蔽”人的认识,而不同的“物”的复杂性也都对人的认识起遮蔽作用。但荀子指出,“圣人”可以“解蔽”而达到客观认识,这就是“道”与“心”——“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
从根本上讲,人性假设直接关系到人的义与利。而义与利的争执由来已久,这又关乎到人的本质与理论主张,而历史上总是各执一偏。对于“义利”,从本体上讲,荀子的主张是——义利两有:“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1]286-287正基于此,荀子的管理主张是:见义,而不忽视利;见夏,而不排斥夷;见人,而不贬低禽。否则“动则必陷,为则必辱,是偏伤之患也”。这是要求,要“有具”“节”其欲,一切要“兼权”,换句话说,就是荀子对义利的看法没有“善恶”,要视情况而定,要“控制”——即“兼权”而避免“偏伤”。也就是说,对于义利要“计算”,而不能主观的武断“判断”。不仅如此,荀子还进一步认为,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之者”。
荀子反对阴阳、山川、怪异之事,而研究“人道”,“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君子之所道也。”[1]58认为不存在“遍能”或“全能”,更不存在“全知”,人有一长既是人才:“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谓也;君子之所谓知者,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谓也;君子之所谓辩者,非能遍辩人之所辩之谓也;君子之所谓察者,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有所正矣。”[1]58关键在于能够“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慎、墨不得进其谈,惠施、邓析不敢窜其察,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1]58-59所谓的圣人之道,无非就是依据仁义行事,明辨是非,言行一致,不失毫厘。总结来说,这样的人就是君子:安礼、乐利,谨慎而无斗怒。
荀子的管理思想与政治始终纠缠在一起,这自然就是“治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6]7,荀子也是这种观点:“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1]90分即礼,礼即秩序,即秩序井然,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在荀子看来,所谓治,就是秩序井然,即各司其职、各得其所。荀子不主张“兼技”与“兼官”,认为“有兼”必乱。这是否可以说,荀子是主张严格分工的呢!笔者一偏之见,认为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欲不可怕,关键在“理顺”。在荀子看来,人性无善恶,但人性有“情”、“欲”,情与欲是“与生俱来”的,“欲不可去”,而且“虽为天子,欲不可尽”。荀子认为,“欲”不可怕,关键在于“心之思虑”的正确引导,在于科学的“度量分界”;更进一步,圣人“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只是一般人又没有自我管理“分辨”的自觉与能力,所以“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1]247。
荀子的治理思想,在其各要素中,自然特别重视人才:君子——“人才”是管理的根本。荀子说:“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1]139在荀子看来,即使有“良法”,但如果没有人才,那也无济于事,也就是说,良法的实施在于“君子”;更进一步,只有“君子”才有良法——“礼义之本”,没有君子,就不可能有良法;再进一步,没有君子也就没有道,因为只有君子才能“知道”。一句话,人才是管理的根本与关键:“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揔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1]80
三、“礼”——根本的治理方法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管理的关键在行为“标准”的制定与坚决的执行。在荀子看来,人们的一切行为标准都应该来自于“礼”——管理就是“明礼定分”。换句话说,“礼”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合于礼的就对,就有效:“夫舍礼而言道,则空无所附,舍礼而复性,则茫无所从。盖礼者,身心之矩则,即性道之所寄焉”[7]76。“师法”则是行为的标准,因而在荀子看来,教育、引导与法规最重要:“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所以“人有师有法而知则速通,勇则速威,云能则速成,察则速尽,辩则速论。”[1]68
在荀子看来,春秋战国的问题既是道德缺失的问题,但更是制度的问题——制度混乱(没有制度)的问题,因而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荀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只是对君王的道德提醒,从而提出“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1]5;“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1]9。“礼者,理也”,“法者,法律制度也”,“分者,职责定位也”。管理就是要讲秩序有先后,这样才能有效率,这在荀子看来,就是“分辨”即“礼”——确定名实明确等级:“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8]17。
“性不能自善”,荀子的管理思想是追求“先王之道”,但这种“先王之道”不是泥古与信古,而是先王所制定的“礼义”,即“性善伪也”——我们要师法先王所制定的礼义(精神或精髓)。如果人性善,那就不需要“礼义”来矫正人们的行为。而礼义不是自然的,礼义是后天的产物。《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重视“周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礼即制度、秩序,而落实到现实中,那就是“文武之道”,即“宪章文武”。
荀子自认“师承孔子”而发展了孔子。荀子认为“礼”具有调节人的欲望层次的功能,“礼义者,治之始也”。在《礼论》篇中,荀子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1]194礼起源于人的欲望;礼者,养欲之器具也,礼就是功利计算或称知性计算;“礼者,养也”,即礼就是对“欲”的承认、引导、规范与控制;礼就是“度”——“边界”;礼就是“标准”——以“礼”衡量人的行为。荀子虽然认为人的“情欲”与生俱来不可灭,但也反对纵情纵欲,纵情纵欲就是“以己为物役矣”。荀子指出,人不能使情欲无限度地伸展,否则各种矛盾会随之产生。“能定能应”就是能把握住自己就能把握住外部规律,即用把握住内在来把握住(或适应与改造)外在,这就是人的这种特殊的存在。所以说,“能定能应”是对传统文化的典型概括——“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不慕往、不闵来”把握此在。在荀子看来,人之与动物不同,就在于人有感情、感觉,能辨别,于是产生“礼”。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就是有“度”:“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1]68荀子认为“礼义”很重要,但人(才)比“礼义”更重要。荀子非常强调人的重要性,认为:“有乱君,无乱国”,“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1]122法律规章是人制定的,也是人执行的,即“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官人守数,君子养原”[1]123,数就是规矩、礼数,原就是根本,而不是流。按照荀子的理解,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1]139
荀子重视“君子”的教化作用,认为通过教化可以矫正与改变人们的行为,从而达到所期望的目标要求:“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明白,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1]139。
四、“隆诚信”是治理的核心
以法治树信用,是今天中国治理的头等大事。治理需要诚信,没有诚信不可能达到真正的治理。诚信是中国治理的真正的大老虎,由于没有诚信,各种矛盾交织、成本居高不下,甚至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治理。这里政府诚信是关键,市场诚信是核心。比如说金融市场不诚信,上市是为了圈钱、理财是为了挖坑,那结果就是“劣币”驱逐、甚至代替“良币”,这必然造成诚实的企业没有办法经营,诚实的人、守规矩的人没有办法工作。没有信用会引起连锁反应,后果极其严重。这助长了市场忧虑与全社会的不安。西方谚语:上帝想让你灭亡,先让你疯狂。全民经商,全民买房,是企套利,全民套利,全民“空手套白狼”。嫌贫爱富,银行也由于“诚信”而喜欢“大企业”,政府也早说要大力扶持中小企业,但也由于“诚信”也是“雷声大雨点小”。结果,由于信息不对称——“不诚实”,中小企业要么死去、要么就不可能出生。低信用,走形式,爱造假,似乎今天很流行。实际上,战国时的荀子已经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啦!
战国时的时代特色是:邦无定交,强凌弱,众暴寡,背信弃义、奸诈谋巧;士无定主,朝秦暮楚,犯上杀君,窃国夺权者屡见不鲜。一句话,国家无常、规矩无常、人生无常,按照荀子的描述就是:“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欺惑愚众,矞宇嵬琐”[1]41。因而荀子特别提倡“信”,不仅认为“信”是无条件的,是人须臾不能离开的,而且认为“信”是社会每一个成员必须要履行的义务,是做人的根本,——“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实际上,“信”是先秦儒家治理国家的重要观点,几乎与礼等同:孔子把“信”确定为立政之本——民无信不立;孟子则提出,“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荀子则疾言,“口言善,身行恶,国之妖也”。
“信,诚也”,“诚,信也”,信从人从言,这是《说文解字》的解释。荀子对信的解释是:“信信,信也;疑疑,信也”,即相信可以相信的是信,怀疑可以怀疑的也是信。荀子指出,商贾有信,生意才能兴隆;百工有信,才能出好产品;农民有信,生产(农业)才能发展。尽管如此,但在荀子看来,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持,关键是做官的要“有信”,只有“上信”才能使“下信”,“上端诚则下愿悫矣”——“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1]168。针对“无诚”的战国局面,荀子明确指出:“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1]20。荀子相信,“信者强”“信立而霸”,“故自四五万而往者强胜,非众之力也,隆在信矣”[1]163,诚信是治国的必要条件,必须“修信治国”。
在战国时,个人为了实现自我,往往不择手段,如苏秦张仪之流,因而荀子认为作为个人的“信”非常重要,个人时时处处都要讲究信用:“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若是则可谓悫士矣”[1]22。不仅如此,讲信是不管个人境遇的:“宜于时通,利以处穷,礼信是也”[1]9。
荀子的“信”就是主张“礼义”治国,礼义“国之首务也”。“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国之命在礼”。荀子主张顺势而为,反对“是古而非今”,非常不赞同“仲尼之门”对齐桓公的贬损——“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认为,虽然齐桓公有相当多的“不足”,但齐桓公有“大节”:“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仇,遂立以为仲父,是天下之大决也;立以为仲父而贵戚莫之敢妒也,与之高、国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恶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贵贱长少秩秩焉莫不从桓公而贵敬之,是天下之大节也。”[1]50也正因为如此,齐桓公才“五伯之盛者也”。荀子是与时俱进的典范,荀子生于衰世,无论是论王道还是霸道,都是从现实事实出发的,“故君子时诎则诎,时伸则伸也。”荀子认为,治国必须用“礼义”来教化统一人心、思想与行为,“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揔也。”[1]152
五、社会治理:共同参与的分工与合作
荀子的时代已经大大不同于孔孟的时代,一般认为是农业社会逐渐趋向于工商社会,这样社会组织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而荀子一方面要求社会要建立大的分工与合作系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另一方面明确提出按照职能管理量才录用、据职奖罚:“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
管理之要在于组织,在于一种由组织而具体化之形式。从荀子文章所列篇目看,充分显示了荀子的管理智慧,作为国家或组织是一个相互联系与制约的整体,但各有不同的职能;作为个人,各在其位,各有其不同的职责与要求,按照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要求要准确定位;并明确了如何才能有效地实现其职能;更重要的是,荀子提出了各种职能的标准与其独特要求。如:什么是国富,如何才能国富?什么是强国,如何才能强国?什么是君道,国君是干什么的,国君有哪些职能(定位),国君如何才能有效地实现这些职能而又不越位?荀子的仁义理想可以概括为:“总方略,齐言行,知统类,一制度”。
荀子从“一”导出“专业”不可“二”——“类不可两也,故知者择一而壹焉”,否则必被“蔽”:“农精于田而不可以为田师,贾精于市而不可以为贾师,工精于器而不可以为器师,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1]225荀子是从“治理众人”而引发出这种管理理论的,这是因为管理的职能是非常复杂的、多样的、分层次的,不是人人都有判别“标准”的“能力的”。那么,怎么管理?谁能管理?按照荀子的解释,“专”是一个方面,对于一般的人讲,必须这样,但对于“圣王”——高级管理人才——志于道者——来说:“精于道者兼物物”,这正如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1]222,即“君子壹于道而以赞稽物。壹于道则正,以赞稽物则察,以正志行察论,则万物官矣。”[1]225荀子主张“官不能技”,即限制“官师”,这是标准的职能管理了。再进一步,就是求知学习也要有确定的目标,即要分工与划定界限范围,否则就是穷年累月也会无所获,荀子称此为“愚人”、“妄人”。
人有所长必有所短,关键在于“知有所止也”,这就是分工。荀子明确指出:“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谓也;君子之所谓知者,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谓也;君子之所谓辩者,非能遍辩人之所辩之谓也;君子之所谓察者,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有所正矣。相高下,视硗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通财货,相美恶,辩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1]58;而管理者(君子)的工作则是分工、协调与监督:“谪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言必当理,事必当务”[1]58-59。
职能管理的前提是社会分工,只有明确分工,才能各司其职,从而提高“效率”,在这方面荀子论述的非常清楚,如在《富国》中,就明确论述到:“掩地表亩,刺屮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偷,是将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熟,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馁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1]92在《王霸》篇中,荀子说:“‘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揔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1]112
简言之,按照荀子的职能管理,即能够“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1]90,那就会“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其结果必然就是“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1]95。
今也者,无论是管理还是治理,无论是统治还是服务,无论是自治还是协管,关键的是不要忘本,尤其不要否定传统的精华,荀子的管理思想能够为今天的中国人指点迷津。
[1]荀子.荀子[M].耿芸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3]孟子.孟子·万章下[M].梁海明,译注.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
[4]龙纯宇.荀子论集[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
[5]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79.
[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
[7]凌廷堪.校礼堂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
[8]大学·中庸[M].梁海明,译注.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梁念琼liangnq123@163.com)
Field of View of Management Philosophy:Contemporary Revelation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Theory of Xun Zi
YUE Lia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Suzhou University,Suzhou 215213,China)
Thought is a prior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ker in ancient China,Xun Zi not only needed to inherit existing theories,but also had to apply all his knowledge to the field of social governance.The core of social governance is Order,which is also Etiquette;The code of conduct of social governance is Testimonies;To resolve is to validate administrative ranking;He believed that governance could be achieved via education,and the highest level of governance,“Sheng Wang”is to keep everything in a comfortable order.To summarize,the ultimate goal of social governance is to bring wealth and prosperity to the country and people,and the most effective way is to involve everyone.
Xun Zi;Humanity;Etiquette&Testimonies;Functional Management
B222.6
A
1008-018X(2016)05-0007-08
2016-06-15
岳梁(1963-),男,河南三门峡人,苏州大学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发展哲学与管理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