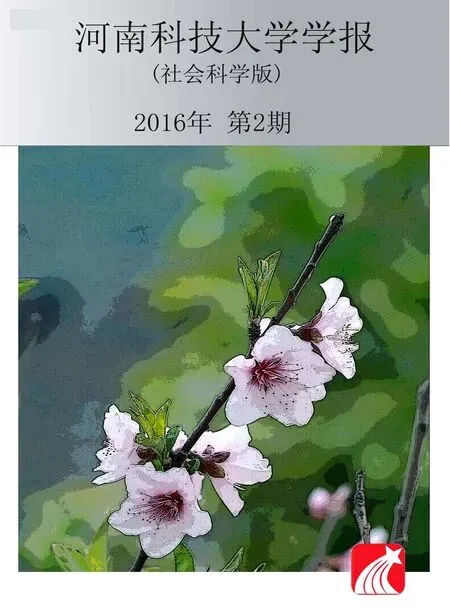从叶县县衙看明代等级生活与权力运作
李强楠
(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济南 250100)
【史海钩沉】
从叶县县衙看明代等级生活与权力运作
李强楠
(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济南 250100)
摘要:作为我国现存唯一的明代县衙,叶县县衙是明代县级政权衙门的实物标本。其空间布局、建筑细节体现着明代的等级精神;在各项制度较为成熟的明代,县衙成为基层权力运作的静态凝结,反映了明代县级权力的日常运作过程;其虚受堂和思补斋的设置以及楹联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对“贤人之治”的一致期盼与政治期许。
关键词:明代;叶县县衙;古代建筑
将建筑本身的结构、规模与社会的政治、礼制结合起来并相互论证,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等级意识也成为建筑的无形构架。在中国古代社会,无论是建筑的总体规划、布局形式,还是屋顶样式和装饰等都成为等级制度的现实体现。尽管中国古建筑的规制在数千年历史中或被僭越或被重新定义,但礼制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等级观念的基础,其实质一直被社会各阶层所恪守。“在儒家正统思想看来,礼就是要做到上下有别,也就是说,上栋下宇的建筑形象,本身就是礼的基本观念的写照。宫室之所以成为宫室就是因为它本身是合‘礼’的。”[1]中国古代的衙署建筑正是用建筑构筑的等级链条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对这个节点的研究和把握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建筑、古代等级制度和政治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以明代叶县县衙为例,对明代的等级生活和权力运作方式进行初步探讨。
一、等级链条上的衙署
叶县县衙是我国现存的唯一一座明代县衙,可作为明代县级政权衙门的实物标本,从中可以看出明代等级生活所具有的一些特征。
(一)叶县县衙所体现的等级精神
1.三轴并贯:等级秩序的静态铺展。叶县县衙位于河南平顶山叶县东大街,坐北朝南,占地16 848平方米,始建于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整座建筑由中轴和东、西两侧副线上的41个单位、153间房屋组成。叶县县衙的空间布局采用传统的中轴线布局,由中轴线及东、西两侧副线三部分建筑群组成。除位于中轴线上的大堂、二堂、三堂外, 县衙东侧副线上由南向北依次分布着监狱、厨院、知县宅等建筑;西侧副线上有古时衙署内工作人员办公及休息的西群房,有知县反省自身功过的虚受堂和思补斋及南北书房等建筑(见图1)。由于当时叶县行政级别较高,所以在衙属规格上县衙享受三间大门、五间厅堂的待遇。
就空间布局和县衙规格而言,等级秩序呈静态铺展。其中轴线和东西两侧副线体现了主从有序、主次分明的等级精神。三间大门、五间厅堂的间数和宽度暗示着衙署的规格和县官的级别。这种布局对于作为古代基层统治权力象征的县衙来说,绝非可有可无,它是国家权力和等级制度的渲染;虽不事雕琢,但已将主从有序、主次分明的等级精神从外观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2.中轴对称:等级秩序的一元凝聚。“礼的本质是‘序’,在建筑中的体现就是形成一元构图——中轴对称,突出重点,主次分明。”[2]在古代衙署的建筑群中,这样的排列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等级文化在建筑艺术中的反映。《中庸》有言:“中者,天下之正道。”[3]中正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之一,也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建筑文化。
就叶县县衙建筑的群体分布而言,建筑数量虽多,但因由“衙门—仪门—宅门”所组成的中轴统摄全局,看似繁多、杂乱的建筑群即变得井然有序、主次分明;就单体建筑而言,屋顶的瓦兽、檐下的斗拱、梁栋,皆以单体建筑的中轴左右对称,虽单一却异常规整有序。同时,建筑群的中轴线与大堂、二堂、三堂单体建筑的中轴线合二为一,将等级精神凝聚为一条线;主体建筑在中轴线东西两侧对称分布,进而凝结为一个点——衙署的几何中心——大堂。至此,权力的中心占据中轴,统摄全局。等级秩序从这一中心向四周弥散。

图1 叶县县衙平面图
3.屋顶台基:等级精神的一呼一应。“宋代民间著名建筑师俞皓率先将单体建筑分为三个主要部分来统筹,上分是屋顶,中分是屋身,下分是台基。”[4]古今的建筑营造皆沿用这种划分。“三分”本身即融合了中国的传统价值,与“天下三分”、“天、地、人”等观念遥相呼应。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的稳定使得这种建筑营造方式得以长期保存,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在屋顶与台基之间演变出等级规制,建筑遂被演化为现实社会等级生活的注脚。
屋顶和台基,成为古代等级精神在建筑中的表征。在“三分”中,变化最为显著的是屋顶,形式包括庑殿、歇山、悬山、硬山、卷棚、攒尖等。叶县县衙为单檐硬山式屋顶,虽建筑规格不高,但具有传统社会官衙的庄重和威严。作为县级衙署,其大门台基不高。这种设计本身也显示了县衙在等级链条上的位置。
4.建筑细节:等级精神的弥散强化。无论厅堂大门的间架结构还是屋脊的瓦兽、梁栋、檐桷绘饰,都体现着传统社会等级精神强大的弥散性和渗透性。《明史》记载:“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斗拱、檐桷青碧绘饰;门三间五架,绿油,兽面锡环。三品至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檐桷青碧绘饰;门二间三架,黑油,锡环。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梁栋饰以土黄;门一间三架,黑门,铁环。”[5]
叶县县衙的大堂、二堂、三堂均为五间七架,屋面兰瓦兽脊,梁栋、檐桷青碧绘饰;大门为面阔三间的硬山结构建筑。因叶县县衙的规格比一般县级衙署高,所以县衙的厅堂多于《明史》所载的“三间七架”,门也多于《明史》所载的“一间三架”。
(二)王权至上与伦常至尊
“建筑显著特征所以形成,有两因素:有属于实物结构技术上之取法及发展者,有缘于环境思想之趋向者。属于环境思想方面,至少有以下可注意者四:(1)不求原物长存之观念;(2)建筑活动受道德观念之制裁;(3)着重布置之规制;(4)建筑之术,师徒传授,不重书籍。”[6]3“制裁”中国古代建筑“道德观念”的主体正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价值观。作为古代社会等级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县衙文化的直接指向是王权至上和伦常至尊。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价值深刻地影响着衙署的布局和规制,也影响着衙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在中国传统社会,君主即为社会政治权力的核心,其他所有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开展皆以此作为中心指向。奉天承运,赋予了王权理所应当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7]不仅只是孔子心态的写照,更是古代社会众人心态的写照。王权的至上性和崇高性成为古代社会政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作为社会等级链条重要节点的衙署建筑上,王权的至上性则体现为对建筑等级秩序的严格遵从。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文化目光所及的任何权威都要遵循道德规范,儒家文化通过伦理道德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从政治到人生的最基本和最全面的规定性”[8]47。儒家文化语境中的道德规范即囊括了从政治到社会、文化一系列的规定。在这个无所不包的道德规范之下,等级社会得到了长久稳固的发展,伦理道德则是维系传统社会的血液。在此基础上,伦理道德和政治相互涵化、相互渗透。这种政治价值准则无形中的强大约束力,使得数量众多、地位较低的基层政权单位,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形式中得以长期存在和稳定发展。而这种政治价值准则也构成了传统社会建筑的灵魂。
二、衙署结构:静态化权力运作
“建筑之始,产生于实际需要,受制于自然物理,非着意创制形式,更无所谓派别。”[6]3作为中国古代官署衙门,其布局、规模、建筑特点等既受中国传统礼制的制约和政治文化价值的影响,也有衙门建筑功能上的要求。形式和功能之间存在的这种紧密关系,使我们可以从功能的角度反观现存衙署文物布局,进而了解中国古代衙署的日常权力运作。在政治权力运作系统较为成熟、稳定的传统社会,衙署结构已成为所属政权运作的静态化凝结。
(一)县衙结构体现的权力日常运作
叶县县衙主体建筑有大堂、二堂、三堂、狱房、厨院、知县宅、大仙祠、虚受堂、思补斋等。大堂主要发布政令,审理案件。大堂东侧为吏、户、礼科房,西侧为兵、刑、工科房。两侧还有东库房、承发房等机构。东库房具体负责财务收支,承发房则主管文件来往转送、档案保管等业务。二堂为审理案件遇到疑难问题时, 知县与幕僚、师爷进行磋商、研究对策的处所。二堂东侧为会文馆、西侧为会武馆,是县令接待上奉文武官员的场所。三堂又称“知县廨”, 是知县处理公务和临时休息的地方。两侧厢房为近身吏员及随从的办公场所。东侧副线上由南向北依次分布着监狱、厨院、知县宅等建筑,西侧副线上有古时衙署内工作人员办公及休息的西群房,有知县反省自身功过的虚受堂、思补斋及南北书房等建筑。
县衙建筑群中各单体建筑按功能和作用可以分为政权运作、文化生活、神庙祭祀三个系统。其中政权运作系统主要包括在中轴线上分布的大堂、二堂、三堂和附属建筑、监狱。文化生活系统包括西侧副线分布的西群房、南北书房、虚受堂、思补斋,东侧副线上分布的知县宅和后花园。神庙祭祀包括仪门两侧的土地祠、萧曹庙和大仙祠。
县衙权力的日常运作均在政权运作系统中展开,其与县衙的人员息息相关。“县衙中的人员分为官、吏、役三等,在数量上呈金字塔形。政务上的分工大体为:官主决策,吏理文书,役供差遣。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即正官、佐贰、首领,为朝廷命官,数量极少。知县总管一县之政务,佐贰、首领则分别分工负责劝农、水利、清军、巡缉等某一方面的事务;吏员为在吏部注册的公职人员,主要在六房、粮科、马科等各房科中办事,处理公文账册;衙役则司职站堂、看管、守卫、催科、抓捕等事,听候官吏差遣。”[9]县衙的人员设置与衙署的权力运作、建筑结构相互呼应。
作为基层政权,县衙涉及政权运作的事务主要包括日常政务和处理刑名之事。自下而上的政务先由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吏员向上禀告。“遇有大小事务,该吏先于长官处明白告禀,次于佐贰官处商确既定,然后当该吏典幕官书卷,才方自下而上以次佥押讫,正官下判日子,当面用使印信,随即施行。”[10]六科吏员应先禀告县令,然后再与佐贰官首领讨论,拟定解决办法,最后交由县令决断。上级或同级的文件来往,先经紧靠仪门的承发房分类,后交相应科房,再由科房吏员禀告县令,最后根据县令的决定处理。因此在日常政务的处理过程中,政务、政令在中轴线上往来穿梭。而此时主要涉及大堂的附属建筑——六科、三堂及附属建筑,权力的核心在三堂。
中国古代行政司法合一,处理刑名之事是县衙权力运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权力在地方的充分运用和巩固。“处理刑名县官受理百姓词讼称为‘放告’,受理词讼的日子称为‘放告日’,每隔三五日一次。放告之日,县官升堂后,出‘放告牌’,原告捧纸依次递进县衙。状纸递进后,由承发房吏接下挂号。县官接状后为慎重起见,往往并不立即审理,而是退堂后一一细览,第二天再与发落。不准状的退回,准状的再传原告、被告、证人三方细审。”[9]在处理刑名之事的过程中,明清主官审案主要包括立案、堂审和判处三个程序,权力主要在中轴线的二堂之前展开。此时权力的运作轨迹是由外而内,再由内而外,包含了社会信息的输入和县衙权力的输出。堂审和判处过程通常向民众开放,权力借此得以与社会联系。
作为县衙功能和古代礼制、等级制度相结合的产物,不论静态的建筑布局还是动态的权力运作,都将其核心集中在县衙建筑的中轴线和中轴线的主体建筑之上。这样的布局不仅有利于政务活动的开展,也是对坐北朝南、左尊右卑、左文右武、权力至上等观念的诠释。
(二)明代县级权力运作的特点
明代的各项政治制度已发展完备,并伴随着君主权力的巩固不断走向集权主义。这在衙署建筑布局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重重大门和高墙的设置,使得权力运作被紧紧局限在衙署之内。不论日常政务的处理还是刑名之事的处理,权力的运作轨迹始终都在衙署的中轴线上往返。即使对民众开放的审案过程,也是在三班衙役的“威武”声中开场,在县令的惊堂木下作结。开放的目的仍是为显示权力的崇高性、权威性和不可撼动性。高度的封闭性、内向性是明代县级权力运作的最主要特点。
诚然,高度的封闭性、内向性使得权力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下得以长久稳固的保存,这对正常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构建是必要的。但是当权力运作被紧紧局限在狭小的空间之内时,权力自身的强化、膨胀则成为必然。而世俗社会对自身利益的诉求也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增加,缺乏相应的社会疏导机制和安全阀,内外“压强”的不同势必最终会导致权力自身的不稳定,最终使权力本身被解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因此,不稳定性也与高度的封闭性、内向性一样,成为明代县级权力运作的主要特点之一。
三、 叶县县衙独特的政治文化意味
(一)与内乡县衙的比较
内乡县衙位于河南省内乡县城内东大街,元朝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开始兴建,其后历经多个朝代,曾被多次毁坏及重建,被海内外誉为“神州大地仅有的历史标本”,享有“龙头在北京、龙尾在内乡”之美誉。叶县县衙与内乡县衙是不同时期的建筑,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礼制和等级精神的辐射之下,二者在结构布局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例如坐北朝南、左文右武、前朝后寝的布局,中轴线上布置的仪门、大堂、二堂、三堂等主要建筑群,中轴线东西两侧的辅助建筑,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严格的地方官署规制和贯穿始终的等级精神。同时,叶县县衙仍有很多独特之处。
和一般的县衙不同,叶县县衙是一所五品县衙。叶县地域宽广, 由汉代的叶县、昆阳、红阳、舞阳4县和犨县合并为一县, 时称大县,每年上缴税赋 10 万石以上;同时由于叶县自古就是“南通云贵, 北达幽燕”的交通要道,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位置重要,故县令多由同知衔的五品官担任。因此,县衙规格也比一般的县高,县衙得以有三间大门、五间厅堂的布局。
在礼制严密的古代社会,这点特殊之处也在衙署的建筑之上体现出来,其中之一即叶县县衙的大堂由厅堂和卷棚两部分组成。它位于中轴线上的制高点,气势威严庄重。卷棚源于宫殿、庙宇中拜殿的建筑形式,用于官署衙门,是官员级别高在建筑形式上的反映。叶县县衙现存卷棚建于清同治年间,由当时知县欧阳霖主持增修[11]。而这样的卷棚,是我国现存县衙中唯一的一座。
除特殊的衙署规格、卷棚之外,叶县县衙最独特的是在西侧副线上分布的虚受堂和思补斋。思补斋即知县对自己的过错进行反省、思考、补过的地方。思补斋有楹联:“孔子乃至圣先师每日犹洁身三自省,吾侪本无名后学时刻领补过多反思。”虚受堂是知县受到上级表彰和嘉奖时,反思自己对于恩赐和荣誉是否受之有愧的场所。楹联为:“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这一斋一堂也是目前我国仅存的同类建筑, 不仅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也为叶县明代县衙增添了几分独特的韵味。
(二)独特之处的政治文化解读
“一般而言,政治文化是政治中的主观因素,指的是一个政治系统赖以生成和运作的文化背景与条件,包括政治价值、政治观念、政治信仰、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8]5作为政治系统所依赖的文化基础,政治文化的形成受到政治系统的影响,同时政治文化也影响着政治系统的运作。它既可以变革政治系统,也可以维护政治秩序的长久发展,同时也可以指导政治行为。叶县县衙就是在当时政治文化的作用下形成的。
三间大门、五间厅堂的布局和卷棚的设置是衙署被物化的等级符号,是礼制在建筑中的存在方式。《荀子》曰:“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12]“礼”成为贯穿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主线。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等级链条上的衙署,叶县县衙的此种特征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礼制文化、等级森严的体现。
作为目前我国现存同类建筑中仅存的中央规制之外的建筑,虚受堂和思补斋的存在为森严、肃穆的县衙增添了几许生机与韵味。尤其是虚受堂和思补斋门口的楹联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传统政治文化中“贤人之治”的政治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文人官员的理想路径,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官员对自身的德行极为关注,通过修身而成为有德之人是很多官员对自身的要求。由具有极高道德修养的领导者践行的“贤人之治”、“圣人以道治天下”则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致期盼与政治期许。虚受堂和思补斋的存在,即是这种政治期许的最好注脚。
四、结语
作为我国现存唯一的明代县衙,叶县县衙是明代县级政权衙门的实物标本,为今天研究明代的政治文化提供了实例支撑,明代政治生活的等级精神也在衙署之中得以充分体现。明代作为各项制度发展较为成熟的一个朝代,县衙是其基层权力运作动态过程的静态凝结。权力运作动态过程与衙署建筑静态凝结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既赋予了有形建筑以无形的建筑文化和政治文化,
也使得这些静态建筑在时隔百年之后,在等级精神逐渐褪去、建筑功能已经消逝的今天,依然可以以其特有的建筑群体组合型制、布局形式、尺度、装饰等为我们呈现其所承载的建筑文化、政治文化和权力的动态运作。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衙署古建筑探寻古代的等级生活与权力动态运作过程,印证我们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等级性、伦理性特征的认知。
参考文献:
[1]王鲁民.中国古典建筑文化探源[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115.
[2]孙杰.礼文化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体现[J].南方建筑,2003(3):3-4.
[3]朱熹.中庸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
[4]赵广超.不只中国木建筑[M].上海:三联书店,2006:76.
[5][清]张廷玉.明史[M].简体字本.北京:中华书局,2000:578.
[6]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7]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154.
[8]葛荃.中国政治文化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9]何朝晖.明代县衙规制与日常政务处理程序初探[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1):12-18.
[10]汪天锡.官箴集要[EB/OL].(2012-11-02)[2015-09-10].http://club.xilu.com/wave99/replyview-950484-25356.html.
[11]河南叶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叶县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355.
[12]张觉.荀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0.
Hierarchy and Power Operation of M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exian Yamun
LI Qiang-nan
(SchoolofPoliticsandPublicManagement,ShandongUniversity,Ji’nan250100,China)
Abstract:As the only existing yamun, Yexian Yamun is the specimen of county-level yamuns of Ming Dynasty. Its layout and architectural details reflect the hierarchy of Ming Dynasty. At that time with all kinds of perfect systems, Yamun becomes the static condensation of the grassroots power operation, which reflects daily process of the county power operation in Ming Dynasty. The settings and couplets of Xushoutang and Sibuzhai embody the consistent pursuit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expectations for the sage-ruling in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Key words:Ming Dynasty; Yexian Yamun; ancient architecture
文章编号:1672-3910(2016)02-0037-05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志码:A
作者简介:李强楠(1992— ),女,河南平顶山人,硕士生,主要从事行政文化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13
DOI:10.15926/j.cnki.hkdsk.2016.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