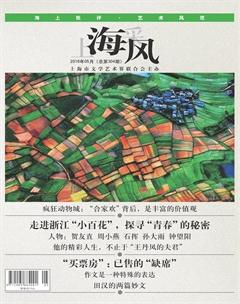陈敏之与顾准的子女们
罗银胜
顾准先生是当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和会计专家。顾准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经济理论研究、会计审计研究、政治哲学研究、中外历史研究等诸多领域,积极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先驱,他焚膏继晷,兀兀穷年,著述颇丰,富有创见。
陈敏之先生是顾准的胞弟,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从父姓,哥哥顾准从母姓。陈敏之先生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建委副秘书长、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陈敏之先生还是“文革”结束以后,立信的复校倡议人之一。
顾准在世时历尽坎坷,临终时身边只有弟弟陈敏之和经济所的同事陪伴。顾准先生一生充满了悲壮的色彩,落笔至此,令人扼腕叹息,潸然泪下!
出于可以理解的种种原因,顾准的儿女们最终没有出现在顾准的病榻前。对此,社会上许多人一直耿耿于怀,有的不理解,有的指责甚至谩骂顾准的儿女们,污言秽语,难以入耳。这样就使顾准的儿女们陷入百口难辩的境地,他们不仅痛悔史无前例的“文革”使他们家庭遭受灭顶之灾,痛失父母双亲;更是无时无刻不想念自己的敬爱的父亲顾准和母亲汪璧,他们甚至愿意背负“不孝逆子”的骂名而去换来世人的同情与理解。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我在上海立信会计学院院长办公室工作,与学校的校务委员和咨询委员多有联系。所以经常到陈敏之先生府上走动,汇报工作,讨教学问。同时,由于写作《顾准传》,我与陈敏之先生以及顾准的儿女们,有了近三十年的交往。我觉得,倒是他们的叔叔陈敏之先生,在晚辈面前体现了长者风范,不但对并不如烟的往事表达了“同情的理解”,还时常严于律己,原谅包容顾准的儿女们。而顾准的儿女们也表达了对叔叔的尊重和感激之情,深深地忏悔不堪的过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两代人之间从感情隔阂、相互埋怨到相互理解、包容,直至冰释前嫌。作为陈敏之先生等顾准家属的多年好友,我看到这样的情况,真的感到由衷的高兴。
陈敏之先生曾经说过:“回忆往事,对我来说是凄恻和痛苦的。1974年12月,当我捧着五哥的骨灰走上老山骨灰堂的陡坡时,我的心比我的脚步更沉重;五哥的孩子就在近旁,为什么他们视若不见,是什么东西横亘在他们中间,这些本来应该是他的子女做的事,为什么要我来做?我向五哥作了承诺,然而我仍然无法消除他们之间的隔阂。在五哥生前,一直到死也未能让他和他的孩子见一面,在那迷信盛行、把教条奉为圭臬的时代,要改变他们那时已经相当凝固的观念,又岂是我给他们写封信能够改变的。而我为了说动他们去见见已经垂死、苦苦思念着孩子的他们的父亲时,我的情绪又是那么激动,言词激烈,缺少理性的思考,缺少一个长者对孩子应有的通达的理解、抚慰。我为我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对他们的苛责、伤害了他们而感到疚愧。”言语之中,充满了理智、通达乃至反思。
顾准与汪璧1934年结婚。汪璧,本名方采秀,进入解放区后改从母姓,改名汪璧。汪璧是在立信会计夜校读书时和顾准相识的,他们原本是师生关系。1934年结婚时,顾准19岁,汪璧20岁。1937年前后的两三年中,顾准曾经有过两个男孩,都在不满两周岁时夭折了,患的是同样的脑膜炎症。
顾准的妻子和幼妹陈枫,于1941年冬来到解放区,一起进入华中局党校学习。顾准到淮海区不久,汪璧即离开华中局党校到淮海区工作。1942年11月扫荡前夕,她在淮海银行当会计,扫荡突围和转移过程中,由行署财经处张以鉴照料她。扫荡开始不久,汪璧在战乱中生下了长女顾淑林,此时她们母女俩都已集合在行署机关中。
由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生活不稳定,直到1942年,顾准夫妇才有了第一个孩子顾淑林,小名稖头(苏北方言玉米的土名)。顾淑林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60年代开始从事基础科学研究。1982年由于工作需要转向科学技术政策和创新研究。1992年至2000年任联合国大学新技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1946年,汪璧生下长子顾逸东(小名小米),6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为中科院院士、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空间技术协调中心主任。他的六叔陈敏之称他“在痛悔之余,以赎罪的心理,努力工作达到了忘命的程度,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顾准次子高梁(学名顾南九)1948年出生,文革时到内蒙古插队,文革结束后,成为吴敬琏的硕士研究生,曾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现任中信出版集团《经济导刊》总编辑。
1949年上海一解放,顾准就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上海市财政局局长、税务局局长,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顾准进入上海,添了一个女孩顾秀林(1950年生,小名五五)、一个男孩顾重之(1952年生,小名小弟)。
顾秀林像她的二哥一样,文革后考入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后进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后又远渡重洋,在美国夏威夷大学获得农业经济博士学位,现为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也是一位名声在外的反转基因斗士。
顾准最小的儿子顾重之素为顾准喜欢,顾准病重住院时,希望他能回来照顾,并且沟通感情和思想。当时顾重之在长春某林业部门工作,他在回信中表示他不会回来,而且是坚定的。这着实给顾准打击不小,他的本来已经垂危的病情从此急转直下。1979年陈敏之的母亲顾庆莲在沪病逝,顾重之在得知祖母去世后写信给他的叔叔:“随着奶奶的去世,有关这个家的许多往事都在脑子里翻腾,这都是过去的事情,再也不可挽回了。这个家已不复存在,但是这一切所留下的痛楚,将永远刻在心上,今生今世也永不能平复了。为了这一切,为父母,为兄妹,为自己,为亲友,为死去的,也为活着的,我应当奋斗,永远也不满足,永远怀着负疚和苛责自己的心情向上。逝去的已不能复生,然而我们奋斗之成果,或许能在他们灵前献上一小朵白花?”这可以看作顾重之的忏悔和誓言,而他确实也是这样做了。1979年高考,仅仅只有初中毕业学历的他,依靠自学获得了北京这一届高考的文科状元。后来,他成为一名注册会计师,现定居美国。
梦魇般的“文革”结束后,从炼狱走出的陈敏之和顾准的儿女们,获得了新生。这时,陈敏之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这就是把顾准的真实思想尽快地让他的孩子们了解,同时也向社会公开,借此把被历史严重扭曲了的顾准的形象恢复过来还其原来的面貌。
好在顾准的儿女们在大劫之后,有了“迟到的理解”。五六十年代,他们一直受到传统的正统教育,不仅要与沦为右派的父亲“划清界限”,自身也背负黑锅,遭到社会的冷眼和歧视。
1984年2月,顾淑林在读了父亲的遗稿后,满怀深情地写道:“1983年初到1984年初,我仔细阅读了这本通信录(系后来公开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手抄本)。流畅的行文,深邃的洞察力,中肯精辟的分析,使人折服。在这后面的是父亲对国家前途极度关切的责任感和探讨真理的热情、勇气,它是如此汹涌澎湃,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原有的父亲的形象,至此彻底地清晰高大起来。骨肉情感,对动乱年代和家庭变迁的痛苦回忆,成年以来对文中所及问题的思考,以及严酷的自我剖析,所有这一切,纠扰在一起,多少个夜晚不能成寐。1965年底,父亲第二次‘戴帽,我被告知父母亲决定暂时‘分手。‘这样可能对他(指父亲)的改造有好处。我们说好十年以后再见。母亲这样对我说。那一年我二十三岁。从这以后,我们和父亲没有再见过面,在这以前,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也十分有限。对我来说,从1961年底到1964年这一阶段算是接触最多了——每月一次的回家(我在念大学),其他的时间里,父亲要么在前方,要么在异地工作,要么在出差,要么在劳改。我们这些‘右派子女,从少年时代起就面对着许许多多的怀疑、冷眼和挫折,但忘我的学习工作劳动中,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谅解和友谊。我们的信仰可谓真诚,这里面原因很多,有学校社会的,有家庭亲友的,有个人的。我无法在这里展开来一一回顾。”不愧为顾准的儿女,此番话声情并茂,又不失理性。
噩梦终将过去,阴霾必将驱走!
在这场噩梦中,每个人都可能因为相互不理解,缺少沟通而受到一些误解、委屈。陈敏之从不讳言自己与顾准孩子之间存在某种隔阂,对此他感到心中不安,以致许多个夜晚午夜醒来以后不能成寐,他陷入深深的痛苦的沉思之中……他经常设法打破这一僵局,多次利用出差北京的机会,与顾准的孩子恳谈沟通,促膝交流。而顾准的孩子则常常表达了对老人最大的尊重,也不时流露深深的悔意与愧疚……
2002年,陈敏之趁自己身体状况尚可,决定将哥哥顾准的遗稿转交给他的孩子。陈敏之先生认为,“顾准临终前把他的遗稿托付给我,这是那个年代不得已采取的权宜措施。现在他的孩子们都已成长起来并且都已成熟,因此他的遗稿理应交给他的孩子。顾准去世以前和去世以后,由于我和他的孩子们分处京沪两地,彼此缺乏理解和沟通,难免滋生一些完全不必要的误解,这也是那个被完全扭曲的时代所造成的。可以说,所有一切误解都已消除、泯灭,还可以相信顾准的孩子不但能继承顾准的遗愿,而且可以比他们的前辈做得更好!”
2005年7月1日,著名经济学家顾准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在河南息县东岳举行。这一活动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与东岳镇人民政府专门举办的。陈敏之先生和顾准子女代表高梁先生都出席并致辞,作为顾准母校立信校友的我,也躬逢其盛,有幸参加。他们的讲话在怀念顾准的同时,特别强调顾准对身后的评价并不在乎。我们主要学习他的探索精神。他的思想并不代表真理,如果有不足,希望能得到不断的纠正与批判。
总结顾准的家庭悲剧,作为叔叔的陈敏之坦诚地说过:“当顾准的家庭悲剧已经成为历史,成为共和国历史中的惨痛的一页时,我想说,我必须说:一、顾准的家庭悲剧和类似顾准那样的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悲剧都是那个特定时代的错误,是历史性的悲剧,因而必须记住;二、在这个悲剧中受害的不仅是顾准一个人,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也都是受害者,对他们同样应给予理解、谅解和同情;三、我应当坦率地承认,我自己也曾经是一个思想奴隶。我相信,在共和国的土地上,没有成为思想奴隶的人是不多的。四、我同样也要坦率地承认,在顾准的家庭悲剧中,我的全部信息,都来自顾准,因此我的感觉、感情不可能不受到一定的局限。如果我因此而在无意中伤害了顾准的亲属,我真诚地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和谅解。”
2009年5月4日,陈敏之因病溘然长逝。高梁先生代表顾准家属,专程来到上海参加了追悼会。不久,陈敏之夫人林樱初提出,将留存在家的顾准生前藏书,全部送还给顾准的孩子。高梁先生打电话把这一消息告诉我,我特意准备了打包的工具和材料,帮他一起将他父亲的图书整理装箱,这样顾准藏书等资料完整地托运回京。陈敏之先生与顾准的儿女们终于有了完满的和解,顾准先生当含笑于九泉。
俱往矣!但愿顾准的家庭悲剧在共和国的土地再也不要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