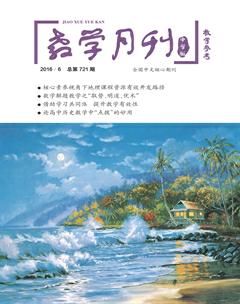对初中数学“负负得正”的教学探究
刘超 谢红英
摘 要:“负负得正”在数学上是一种规定,它具有超验性.基于有效现实情境和数学情景的整合使用,可以实现初中生对该法则的较高水平的认知.对教师来说,有必要知悉“负负得正”在数学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主要故事情节”,以便在教学中适时、适切地展示问题提出与问题解决的思维过程.
关键词:负负得正;情景模型;数学模型;整数环公理系统;数学认知
在有理数乘法教学中,“负负得正”的教学是一个难点.调研发现,学生对“负负得正”的认识大都停留在“这是数学上的一个规定”的层次,并没有理解其中的算理;教师对“负负得正”的理解主要是基于特定模型的解释、验证,并没有从数学的角度阐释“负负得正”.负数从提出到被认可经历了近两千年的时间,“负负得正”要一下子理解确实也困难.我们的教科书用近乎半页纸就把“负负得正”给“解决”了,总感觉有失妥当.基于此,我们需要反思,对于“负负得正”,教师应该知道什么?巩子坤教授指出:“从知识发生的角度看,负数的产生并不是演绎证明的结果.教学中适当地介绍相关材料,可以帮助学生认识有理数乘法法则的由来和合理性,前提是教师先要知悉这些知识.”[1]笔者认为,为了满足学生的好奇心抑或说为了遵循数学学习的认知规律,至少是教师层面,有必要知悉“负负得正”在数学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主要故事情节”,以备在课堂教学中遇到学生提问时,可以用略略数语给学生做出解释和说明,也不至于让学生云里雾里地一脸茫然.结合已有研究及个人反思,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究“负负得正”教学的有关问题.
一、为什么“负负得正”难理解?
“负负得正”之所以难以理解,是因为负数及其运算的相关知识具有超验性.巩子坤教授指出,负数超越了日常经验,而学生仍然习惯于用测量的结果来表征数字,不能运用推理的方法理解负数[2]91.从负数知识的发展史来看,数学家对负数的认知历经了两个一千年.一是,数学家花了一千年才得到负数概念;二是,又花了近一千年才承认负数的存在.这两千年的跨度预示了学生学习负数及其运算会存在巨大的困难.一代代数学家前赴后继的工作才让人们逐渐认可了负数.学生在课堂上学习负数、“负负得正”时也会经历类似的过程.在初中生的认知层面上,学生对“负负得正”认知的较高层次就是“为了保持数系扩充过程中相关运算律的一种合乎逻辑的规定”,遵守这一规定,运算就能够顺利进行.再者,负数最早出现于我国的《九章算术》,由于在解方程组的消元过程中遇到了“不够减”的情形,为了表示小数减大数的结果,所以引入了负数.由于我国古代数学家更多关注负数的实际应用,所以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对负数有着太多的误解(西方数学家对负数的认知是从关注负数存在的合理性起始的)[3].这一认识也使数学教师反思:在教学中尽可能地先从实用的角度(现实情境模型)引入超验性的数学知识也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尽可能地联系实际,给出有关“负负得正”的一些实例和有效问题情境,这些现实模型在一定程度上会帮助学生加深对“负负得正”的理解和认知.
二、“负负得正”该如何教?
田载今先生指出,“负负得正”这条法则不容易理解,编写教材时,编者们也为说明这条法则的道理想了很多,各版本初中数学教材都是借助实际问题为背景来说明[4].由此,结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认知特征,创设现实情境模型或数学模型来验证“负负得正”,帮助学生达到对有理数乘法法则的直观理解(能用语言表达或者用自制模型验证),而不仅仅局限于程序化的理解,就显得相当重要了.贾随军博士也指出,由于“负负得正”的超验性,基于有效现实情境的解释可以确保初中数学课程对数学严密性及推理的强调没有超出其应有的边界[5]79.实际上,国内外的数学教材大都是这么做的.调研发现,各版本教材中的验证“负负得正”成立的模型主要有两类:现实情境模型和数学模型.具体涉及归纳模型、分配律模型、相反数模型、两组具有相反意义的量的模型数轴模型、数轴模型以及分配率模型等.
彭启科老师指出,现有的“负负得正”理解模型均存在着各种不足与缺陷[6].如归纳模型,“两个因数变小了,而乘积却变大了”,这与学生的已有经验相矛盾.那么究竟什么样的验证模型才是好模型?为了进行比较分析,笔者调研了部分国外数学教科书中关于“负负得正”的验证模型的应用情况.分析发现,国内外教科书关于“负负得正”验证模型的使用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外教科书更加强调数学模型的使用.注重基于数学自身特征,基于数学的本质,用数学的思维、方法解决问题,现实生活情境只作为引入而已.相比之下,我国教科书应用了较多的现实生活情境,基于学生生活经验给出合理解释,帮助学生理解法则的合理性.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究其原因,首当其冲的则是东西方的不同数学传统.以我国为代表的东方数学自古以来就重视辩证思维,注重应用,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西方数学则重视数学抽象与形式逻辑,强调推理论证;再者,我国教科书对现实情境模型的较多应用也与课改理念遥相呼应,强调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关注学生对知识的认知过程.
二是与国内教科书相比,国外教科书侧重同时选用两种模型进行解释说明.如“新加坡版(原)(1982版)”“美国加州3版(2008版)”都选用“归纳模型”和“相反数模型”两种模型.“新加坡版(原)”先用“归纳模型”得到猜想,再用“相反数模型”进行验证;“美国加州3版”先用“相反数模型”得到猜想,再用归纳模型进行验证[7].由此,我们不禁要反思:第一,究竟什么样的“解释模型”或者“数学模型”是验证或解释“负负得正”的好模型?第二,借鉴国外教科书,数学模型和现实情境模型的整合使用是否有必要?若有必要,应如何选用、搭配?
三是我国和美国的各版本教科书在表述“负负得正”时只用文字语言,而新加坡版本(1982版、2007版)的教材则用数学符号语言(In general, where a and b represent positive integer). 实际上,《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中的相关论述——“经历运用数学符号和图形描述现实世界的过程,建立初步的数感和符号感,发展抽象思维”[8],就是要求让学生应用字母或代数式等数学的语言、符号表征抽象的数量关系及变化规律,逐步发展学生的符号感和抽象思维能力.从这一层面来看,新加坡的数学教科书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符号感和抽象能力.因此,建议教科书中对“负负得正”的论述应同时使用文字论述和代数符号表征.
三、几点反思
如上,我们结合国内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负负得正”的相关内容,关于“负负得正”的认知与教学,我们给出如下几点建议.
1.教学中不能为了“创设情境”而创设情境,如果选择的“负负得正”生活情境学生不易理解,那就应该考虑从数学本身出发,寻求直接的、更接近数学本质的方法解决问题.例如,两组具有相反意义的量的现实模型,虽然直观,但由于涉及其中的几个变量关系极为复杂,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更不可能从中归纳概括出有理数乘法法则.原人教实验版教材的“蜗牛爬行问题”背景就是由于涉及时间和方向的相反量,导致学生理解起来有不小的难度,所以修订版教材就以“观察数值变化规律”取代之.
2.根据顾泠沅先生的数学认知水平分层,学生对“负负得正”法则的认知有以下四个层次:只记住“负负得正”;通过模型的解释,学生能够接受“负负得正”;通过模型的解释,学生能够接受“负负得正”,并能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表征;学生理解算理,并能自主构建适当的模型进行表征和阐释.其中,后两个方面的认知为高水平认知.因此,在使用模型解释“负负得正”时,要结合初中生的认知水平和认知特征,选取或编制符合学生实际的模型.教师首先应考虑应用现实情境模型使学生对“负负得正”达到低水平的认知;在此基础上,应用“归纳模型”或其他数学模型,使学生实现对“负负得正”的高水平认知.但也应意识到,由于“负负得正”的超验性,培养学生的高水平认知也要适度,不能有过高的要求.教师应选择合适的内容素材进行适时、适度训练,一以贯之,方能有效.正如巩子坤教授指出的,有理数乘法运算的教学目标定位是“熟练地进行有理数乘法运算,对于一部分学生,能够结合例子或者模型来说明运算结果的合理性”[2]93.
3.解释、验证“负负得正”的现实情境模型和数学模型的使用如何取舍?张奠宙先生曾指出:“世界上还没有发现一个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负负得正的实际情境.”[9]贾随军博士通过对中学数学各版本教材的考察发现,从数学本身解释“负负得正”法则的比例大约占了6成.他指出,从数学本身入手是解释“负负得正”法则合理性的重要角度,因为数学本身是情境问题的重要来源[5]79.实际上,多数教师在呈现“负负得正”法则时,使用有关数学模型时会用到涉及负数的乘法交换律和结合律,与数学自身体系“规定运算法则在先,验证运算律是否成立在后”相矛盾.结合初中生实际,对该问题的处理可以“仁者见仁”.考虑到初中生的认知水平,我们认为应在遵循数学知识体系的同时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故选择数轴模型、归纳模型等是适切的.当数学的严密性与学生的可接受性产生矛盾时,就需要数学教师展示智慧,两者兼顾地化解矛盾.此外,应注重数学模型和现实情境模型的整合使用,使现实模型的“解释”作用与数学模型的“验证”作用相得益彰,在解释“负负得正”合理性的同时,促进学生对该法则的高认知水平的理解.
参考文献:
[1]巩子坤.“负负得正”教学的有效模型——兼论教科书的编写[J].教学月刊·中学版(教学参考),2010(1):6-11.
[2]巩子坤.课程目标:理解的视角[J].教育研究,2011(7).
[3]佟巍,汪晓勤.负数的历史与“负负得正”的引入[J].中学数学教学参考,2005(1/2):126-128.
[4]田载今.“负负得正”的乘法法则可以证明吗?[J].中学数学教学参考,2005(3):3-4.
[5]贾随军,等.20世纪以来中学数学教材中“负负得正”法则解释方式的研究[J].数学教育学报,2015,24(4).
[6]彭启科.“负负得正”理解模型的有效性分析[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28(10):78-82.
[7]谢红英,刘超.中外初中数学教材中“负负得正”内容的比较研究[J].中学数学,2013,(4):68-70.
[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
[9]龚烈炯.“负负得正”教学再思考[J].中学数学教学参考,2008(8):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