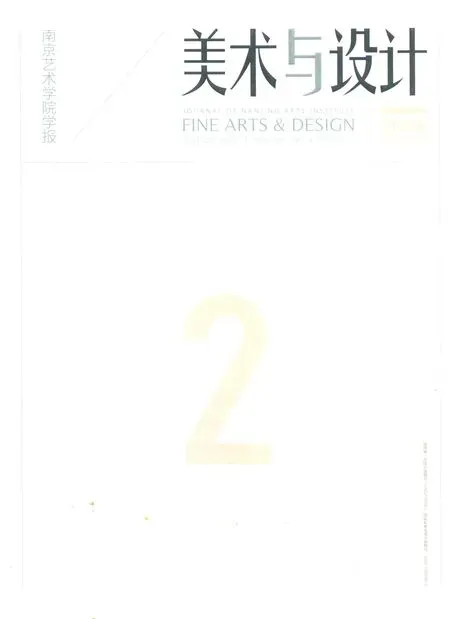中西交流与文化认同:1940年庞薰琹《工艺美术集》视觉文化研究
赵 帅(四川大学 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中西交流与文化认同:1940年庞薰琹《工艺美术集》视觉文化研究
赵帅(四川大学 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摘 要]1940年留法归国已近10年的庞薰琹在成都完成了《工艺美术集》这本设计图集,作为其风格转向且趋于成熟的阶段性作品,在战火硝烟和中国艺术路在何方的背景下,这份图集更显珍贵。以往,对这本图册的分析总是由民族性、大众化和文化身份的角度出发,本文藉由中西方交流的角度思考,在西方艺术思潮和设计思潮影响下的庞薰琹,如何处理和调谐中西方艺术,并在《工艺美术集》中体现,成为本文的着眼点。
[关键词]庞薰琹;《工艺美术集》;中西交流
1925年,远赴巴黎学习技艺的庞薰琹,于1930年回国任教,西方的艺术创作思想、技法,在回国之后的艺术作品中不断显现出来。尤其在1940年前后,随着庞薰琹社会活动的丰富和复杂,他的作品呈现出多元的态势。在对其社会活动进行梳理时,我们可以发现,1938年,他在昆明中央博物院任职,接触中国历代国宝文物,这年冬天到翌年春天,他深入“贵阳、安顺、龙里、贵定四个县,80多个山寨,调查研究苗族的民间艺术”[1],1940年,他又进入四川任教于四川省立成都高级工艺职业学校。这一时期,是他作品颇为丰盛的一个时期,他设计绘制了《中国图案集》四卷、《工艺美术集》一册,又创作了《贵州山民图》系列和白描《带舞》等等。《工艺美术集》是庞薰琹在1940年四川北川郫县吉祥寺尼姑庵,利用暑假时间完成的日用品设计的图集,1941年初夏,他又为《工艺美术集》设计了封面,并排列了目录顺序和完成序言。[2]从空间格局历时性上着眼,此书籍为《中国图案集》的再设计和延续,是庞薰琹艺术创作风格转型①苏利文评价庞薰琹:“抗战时期,他的艺术有两个重要转变,一是把精力转移到工艺美术,成为一个设计家。二是画风融会中西,回归东方传统……”,乔十光《探索,探索,再探索—记中国现代艺术的拓荒者庞薰琹》,《人民日报·美术世界》,1998.12.25。的重要作品之一;从共时性上看,在洋货充斥的市场上,将传统纹样应用在日用品中,这也是振兴国货生产的一种尝试。因此,此书成为作者选取、重点分析的原因所在。
目前围绕此书展开的研究,主要有金兰的“庞薰琹《工艺美术设计》色彩分析”,作者从色彩设计方法切入从而探寻此书中色彩的借鉴之处;周爱民“庞薰琹与中国图案艺术研究”,将此书看作庞薰琹对传统纹样的继承和应用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例证;黄晨“空间转换与视野转向:抗战时期,庞薰琹在西南地区的艺术构建”,将此书作为庞薰琹从绘画走向工艺美术的重要实物。总结前人研究,此书作为工艺美术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大多从民族化、大众化的角度对其进行概述式的分析。然而,深受现代艺术和现代设计影响之下的庞薰琹,在重新选取和设计传统艺术纹样时,对于有别于传统装饰纹样设计的西方现代设计方法选用,又有哪些借鉴和改变呢?本文试图从中西交流的角度来分析这本画集。
一、《工艺美术集》作品概述
《工艺美术集》是庞薰琹设计的一本作品图集,全书由30幅图组成,此图集由1940年7月开始绘制②根据庞薰琹回忆:“暑期中同学都走了……我坐在大殿里画成了一本《工艺美术集》”,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三联书店,2005,第195页;又根据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历,暑期时间为“7月10日至8月1日”,58-1-36-74,成都市档案馆。,于1941年8月③庞薰琹为《工艺美术集》作序,目前找到两篇文章,分别为“序”,1941年8月,载《庞薰琹》,庞濤策划,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6.10,第90-91页;“工艺美术集自序”,载《技与艺》,四川省立技艺专科学校校刊,1942年7月15日,第5-6页。完成,1942年,获得“由教育部学术审议会举办之第一届著作发明及美术奖励……两千五百元奖金”①“校闻·本校三教授荣获教部奖金”, 载《技与艺》,四川省立技艺专科学校校刊,1942年7月15日,第5-6页。。1946年春天,由朋友带到西方出版,未果②关于该图集被带到瑞士的时间,目前有三个版本,分别是1944年,原句为“我记得好像1944年有一个朋友向我建议带交瑞士去出版”庞薰琹,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三联书店,2005,第195页; 二为1945年,原句为“我记得好像1944年(记忆有误,应为1945)有一个朋友向我建议带交瑞士去出版”,“自述—撤至四川”,庞涛策划,载《庞薰琹》,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6.10,第78页;三为1946年春天,原句为“就在他离开成都的那年春天,他曾把一本他的现代工艺设计作品集托付给我们……他寄希望我们能使之在西方出版,然而我们没能实现他的愿望。”苏利文,“序三”,载《国家近代美术研究中心学术研究展—苏利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中国美术馆,2012,第22页。而由庞薰琹年表得知,庞薰琹于1946年2月离蓉抵渝,筹款回上海,载“庞薰琹年表”,庞涛策划,《庞薰琹》,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6.10,第308页,本处采用该书籍1946年被带交给友人这一提法。,1979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苏立文带回中国交还庞薰琹。1981年,《工艺美术集》更名为《工艺美术设计》,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81年出版,其中仅选择24幅刊印;1999年,更名为《庞薰琹—工艺美术设计》,加入部分《中国图案集》作品,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2006年,庞涛策划的《庞薰琹》中全部刊印该图集,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出版;2010年,由《读库》以笔记本的形式发布《工艺美术集》。
在这本书籍的序言中,庞薰琹简要梳理了中国工艺自上古伏羲时代至明之后中国工艺发展。佛教的传入,渐成中国醇和之风,至唐朝浑融消化,达到中国工艺美术之鼎盛时期。而这本集子,是在庞薰琹研究中国纹样史的闲暇时间,“采撷中国工艺图案固有之特性与精神,就现在之趣味与实用,试作此集,愿世人有以教正。”[3]这段话表明两层含义,其一是这本集子的图案装饰,是庞薰琹在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期间,摹写收集古代纹样的基础上完成的,在再创造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对于传统图案的心得;其二是将传统图案与现代日用品相联系,美与实用发生碰撞,这是庞薰琹在努力探寻传统与现代结合可能性的过程。
从作品出发,庞薰琹在设计这部分图稿的时候,运用了多种风格,就其自述来看,书中图案引用有产生于殷代的饕餮纹、书画同源的古体文字,周之风格,汉之双鱼纹样、龜之纹样,六朝纹样,唐之风格组成。选取纹样多为承上启下、维系演变具有无限生命力的代表,如双鱼纹,滥觞于汉,经唐宋元而至明清,演化为民间主要图案,种类之繁、变化之多蔚为大观,有“吉祥”之含义;也有在演变过程中逐渐衰微之图案,如龜纹,与龙、凤同为灵物,汉之后似少见于工艺图案,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之中,庞薰琹又将其重新应用。
图案色调维系这一时期的“灰色风格”③原文为:“他后来想到称此一时期的作品为他的‘灰色时期’”,迈克尔·苏立文,《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世纪出版集团,第175页。,采用同类色,在色相、明度、纯度上都比较接近,图案深沉、格调稳重。由于这一时期纹样少有颜色,尤其殷周时期纹样,以材料固有色为主,庞薰琹赋予传统纹样以新的色彩,在“图三,毛织,床前地毯”之中,引用殷代饕餮纹样,保留青铜固有色彩黛绿之外,穿插黛蓝、靛青和秋香色调谐;而在“图十七,沙发或窗帘布”之中,同样是饕餮纹样,但此时在色彩上黛绿面积缩小,出现了更为活跃的桃红、鹅黄,以黑色和精白穿插组成,更精彩的是出现了自由的构成和组合,以饕餮的眼睛做组合,纹样线条穿插,图幅大小更加自由和随机。在构图上,除了矩形组合之外,根据日常用品的实用性,还出现了圆形围合构图。以“图十五,印花纸伞”最为突出,纸伞图样选用西南地区特有植物,色彩丰富绚丽,构图饱和,四朵花形为主要图案穿插枝叶,晃动伞面图案应跟随一同转动,伞柄色彩为少数民族图样转换,钩饰细腻,把柄配以圆珠,凸显女性特质。同样是圆形构图和自然元素取材,“图十一,碟盘”则略有不同,漆盘设计色彩不宜过多,且用色深沉,如何选取蝴蝶以适合作者表达呢?庞薰琹在碟盘中采用漆黑色背景,上浮仓黑、绀青、黧、黎色彩蝶,因同为黑色系,作者仅以彩翅膀中的圆形彩斑组织画面,如果说蝴蝶的翅膀外围为线条围合圆盘,那么蝴蝶的蝶衣斑点则有规律的形成面在线中穿插,舞动的韵律更具生气。

图1 从左到右依次为:图三,毛织,床前地毯;图十七,沙发或窗帘布;图十五,印花纸伞;图十一,碟盘
二、西方艺术影响下的风格转换
庞薰琹的三十幅作品之中,全部取材于传统图案纹样,根据1953年庞薰琹著作《图案问题的研究》④庞薰琹,《图案问题的研究》,大东书局出版,1953年11月,本书精选200余幅作者在建国前陆续收集的历代纹样一同出版,因均由作者收集,为图册对照带来依据。对照分析,可从中找到12幅来源图样,可以看出作者绘制图册时的严谨和用心。这些纹样直接有来自于出土文物,在青铜器、画像砖、石棺、石刻等等纹样中描绘下来,“数年间积稿盈万”[4]。在图样的再设计过程中,作者对每一幅均作了不同程度的改动,这其中出现了一些西方图案构成的影子。
在“图二十,靠垫”中,纹样选择来源于汉代的鸟形和双鱼形相结合的形式,采取对称式进行方形组合。从构成上看,这一幅作品以几何线条的形式对于繁琐的鸟形轮廓和鱼的轮廓进行了简化处理,以弧线、直线、斜线和圆切割画面,在中轴线两旁的鸟身体被划分为几何十字形,而鸟周身被垂直线条划分,成为几何的抽象式体现;从色彩上看,这一幅作品在这一本图集之中,以黑色、精白、丹和鹅黄组织画面,对称的鸟和鱼的纹样填充对比色,以丹和黑色构成画面主要部分。黑色与精白、丹与鹅黄这种高明度的对比色使得作品愉快、活泼和鲜艳,层次丰富。而这样的分隔和处理,是受到了法国装饰艺术时期的设计影响,对称式和在鸟尾部的放射性线条处理,可以感受到尼亚拉加莫霍克电力公司大楼的雕塑《光之精神》的影子。在作品“图十七,布”作品之中,图形纹样来源于饕餮纹,以桃红、黛绿、鹅黄、黑色、精白组成,以点、线、面构成。图形采用二方连续的形式,以饕餮的眼睛轮廓作为画面的点;将饕餮的外轮廓曲线线条简化为几何线条,以直线和曲线形式穿插在画面之中,有规律的组织画面;以桃红色、黑色方格和黛绿、鹅黄色矩形做有机排列,规律延伸,以面作为图案基底。这样的排列,画面节奏感和韵律感逐次丰富,看似不规则的眼睛又保留了饕餮神秘和凶猛的个性,原始的激情蕴含其中。点在线上如康定斯基的图案般成为律动的音符,同时有组合在传统的二方连续规则之中,这种点、线、面的穿插和传统图案的尝试,颇具新意。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图十,方匣”对于周朝鱼纹样的形态保留,而以装饰画的形式处理背景,半露的月亮配合黑色与藏青的背景,漆盒深邃而古朴;“图三十,瓶”对于汉画像砖“射虎图”有机的复制和组合,营造出在浩瀚的草原与无尽的山脉间,多人射虎的紧张气氛,以黛色和牙色作为瓶颈和瓶身的主题色,附着上了深沉恢弘的美学意境。
这种中西尝试,是源于作者有意识的学习和应用。1925到1930年的巴黎,被现代艺术的影子深深的包围着,1925年,法国巴黎世界博览会盛行,装饰艺术运动开始发挥影响,立体主义、抽象艺术、超现实主义等等现代艺术流派影响着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而中华留法艺术协会于1929年在巴黎成立[5]……在法国游历学习的庞薰琹,对于西方艺术的接受和学习有了更深刻的体验。但是他如何走上对于传统艺术研究的道路之中?在《工艺美术集自序》之中,庞薰琹清楚的讲到在“决澜社”,因生计问题解散之后,庞薰琹开始思考艺术和社会之道,“盖以工艺与人生有密切之关系,或为沟通艺术与社会之捷径乎,”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庞薰琹开始从事工艺美术的研究。而在这篇文章之中,作者更深刻的分析到佛教艺术传入西域时为希腊式及波斯式,逐渐使其转变为中国醇和之国风;唐代中国与印度及印度以东往来交流,唐代装饰之风出现与西域、印度及其他之影响的新样式。而进入清代以后,工艺上数千年形成的民族性消失殆尽,这就是因为“仅吸收与同化其他民族之文化……以模仿西风为尚。”[4]在面对西方艺术的态度上,庞薰琹是主张“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利用西方的艺术与文化,充分的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发生对接和吸收,这是符合时代背景的。
1940年,中国处于民族危亡的时期,工艺美术家们一方面承受着敌人船坚炮利的袭击,在奔波流离、生活困顿的环境中艰难度日,“这几年来,油、盐、柴、米,蚕食了我的精神,鲸吞了我的时间。我需要工作,我也需要生活。我希望不再徘徊于技巧的小天地中。我深深希望能踏进思想的领域。”[6]另一方面,在中西艺术论争转向中国艺术之路路在何方的过程中,工艺美术家们的彷徨与孤寂也在侵蚀着他们的心。在这样的背景下,庞薰琹着手从传统艺术之中开始努力地吸取养料,从战前对西方艺术的矿如崇拜者,开始发生转变。其实,在《工艺美术集》之前,庞薰琹就已经开始着手为做这样的一本集册做准备了,1940年,画册的出现是一个长期积累的总结。庞薰琹1938年在中央博物院期间,零距离的接触到了中国历代国宝文物、考古专家以及古文化研究的学者经营,在跨学科的汲取之中,庞薰琹将在法国的现代设计理念、色彩、构图与传统纹样相结合,绘制出了《中国图案集》四卷。其中,第一卷讲述商、周纹样,第二卷殷周、战国纹样,第三卷汉代纹样,第四卷汉代与汉代之后纹样,这四卷书籍是《工艺美术集》的先声。在整理传统纹样的基础之上,对于纹样的穿插、组合、排列形式和色彩搭配,已经开始做着实践。图案的搭配中,甚至可以找到早年庞薰琹在上海摩登时代的影子。对于器物的选择和材料的应用已经可以看出端倪,赋予漆盘古老的元素,在饕餮纹样中暗含瓷器的身影,画像砖的人物着色和飞舞的服装缎饰,以及大胆的青铜纹样组合。所以,在这本图集中,中西方多种风格、艺术语言的尝试,也成为庞薰琹在探索自我艺术发展的一种路径。

图1 从左到右依次为:图二十,靠垫;图十,方匣;图三十,瓶
三、以“实用性”为出发点的设计图集
“审美”和“实用”,是设计史上的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而作为“现代设计”,产品的设计的“实用性”已成为共识。在庞薰琹的这本图集之中,传统纹样成为设计的重点,但是,产品本身的功能性设计,同样受到作者的关注与重视。本图集主要涉及器皿和布艺两大类型,在使用的陶器和瓷器物品之中,作者主要以简洁、大方的理念来进行产品的外观设计。以杯为例,“图二,壶”为例,壶身外轮廓为矩形,壶把和壶嘴设计均为有棱角的几何形体,以直线划分壶嘴、壶身和壶把,凸显其几何形体气质,装饰简单是功能主义设计的一种实践;而在“图七,长盘”之中,长盘两旁的矩形把手使得物品拿放更为简单,把手中部可转动的滚轴有着防烫伤的妙用,矩形的餐盘和颇有意境的画面处理,两者结合浑然天成;“图十三,匣”中,竹制材料和漆盒的混合使用,显示出作者在西南地区受到竹制材料影响之下的两种材料的配合和尝试,把手和锁的设计在同时期的设计中充满新意。而对于地毯的设计,庞薰琹除了区分出方形、圆形、椭圆形等多种形制外,一律采用深色调设计,这体现出作为地毯的耐脏和实用性;在“图十八,桌布”和“图十九,床单”中,作者将两者设计为一套产品,均由苍翠色围边,鸳鸯和花纹围绕在布艺中部。
从《工艺美术集》选材来看,构成装饰图案的主要器物为瓶、壶、方匣、盘、盆和碗等生活器皿组成,又有地毯、纸伞、桌布和床单等印染品融入。这样的选取,应该与庞薰琹希望将传统古物与现代器皿相融合有着一定的关系,选用陶器、瓷器的绘制,以毛织、印染、贴补技艺的加工,可以方便简单的应用到日常的生活之中。将“形式美”应用到生活之中的初衷,庞薰琹仅以“愿世人有以教正”[3]来概述。追溯更深层次的原因,首先,应该追随到康德关于美的超越性、普遍性观点,蔡元培在其影响下的“美育”思想,影响了庞薰琹对于审美的接受和应用。蔡元培曾说:“我们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刻、图画、文学里又找见他们遗失的情感。”庞薰琹希望以这样的形式,去影响工艺美术的发展,在洋货充斥的市面上实用品以“时髦”来压倒“国货”,在缺乏工业机器的背景下“提倡国货”的口号,更应注重民间工艺的美的问题。其次,庞薰琹有着深深的忧患意识,自身具有“精英性”。他曾分析道:“中国工艺原有的国外市场,已经逐渐为我们的敌人占去……(我们应)专司工艺的设计……采取各省固有特殊的工艺加以改良,使他能成为现代应用的器物。”[7]在《工艺美术集》之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设计不仅适合于国人的欣赏水平,并且同样会对海外市场的占据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特有的传统与文化在与实物的结合之中,保持了传统手工艺的制作技艺,在采用“传统图案”的基础上,也保留了特有的中国元素。而庞薰琹身后的这一群体,具有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和时代使命的原因,是其已经将自己置于时代的巅峰,“画家应该认识社会、认识世界,使自我站在时代之上。”
遗憾的是,这样一本集子在当时并没有被推广应用,这与战争背景下颠沛流离的生活环境有着莫大的联系。但也应注意到,这本集子的出现,作者的视野和角度是自上而下的观看方式,处于精英角度来观照和指导工艺美术的发展,这就导致了图样的出现,与人民生活环境相差距离太远。但是,作品在实践和转型的过程之中,艰难的摸索,更何况是在拮据的生活折磨之中酝酿完成的。1981年版的《工艺美术设计》,将每一件物品应应用于何处,选取何种材料,应注意何种问题等一并标注在了作品图幅下方,跨越40年的艺术设计作品,依旧新颖且不落俗套。归结起来,其一,应该是作者所坚守的回归传统,在深沉博大的传统文化之中和多元并包的少数民族艺术之中汲取更多的养料;其二,在面对外来先进的思想和技术时,始终以兼容并收的态度对其利用和改造;其三,作为知识分子的庞薰琹,对于内心家园的执著和坚守。也正因如此,当我们翻开那本战火硝烟下完成的图集时,内心依然能够保持平静和充满希望。

图1 从左到右依次为:图二,壶;图七,长盘;图十三,匣;图十八,桌布;图十九,床单

附录:

?
参考文献:
[1]庞涛策划.庞薰琹年表.庞薰琹[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6:307.
[2]庞涛.八十年前的一个梦.庞薰琹.工艺美术集[C].读库,2010:V.
[3]“序”,1941年8月,载《庞薰琹》,庞涛策划[G].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6.:90.
[4]庞薰琹.工艺美术集自序[J].技与艺.四川省立技艺专科学校校刊,1942(6).
[5]“敎育消息:國外消息:中華留法藝術協會成立”[J].福建教育周刊.1929(27):35-36.
[6]庞薰琹.自剖—为自己的展览会写的自我介绍[N].中央日报,1943年9月12日.
[7]薰琴.谈谈工艺[J].载工艺.四川省立成都高级工艺职业学校校刊,1941年2月12日:3.
(责任编辑:夏燕靖)
[中图分类号]J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16)02-0041-05
收稿日期:2015-12-26
作者简介:赵 帅(1989-),男,山西太原人,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设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