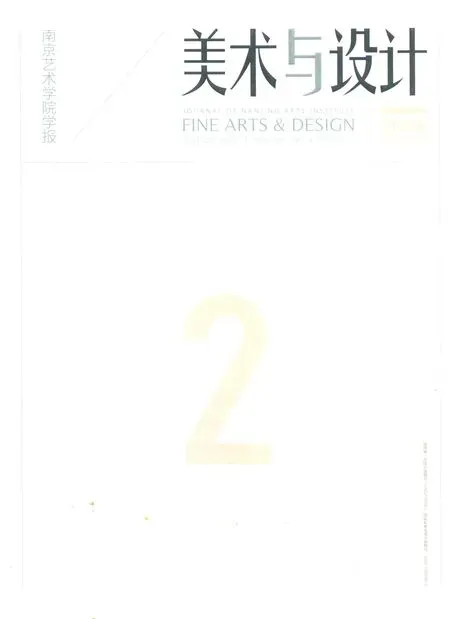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与乔伊斯流亡美学关系研究①
赫 云 李倍雷(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与乔伊斯流亡美学关系研究①
赫云 李倍雷(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摘 要]西方现代主义的产生,对一个爱尔兰作家的乔伊斯的影响巨大。西方现代艺术家都是具有“流亡”身份的艺术家,这一点使乔伊斯的“流亡”感到有了归属。这一归属使得乔伊斯主动接近和接受现代主义艺术的观念和创作主张,尤其把立体主义、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和方法运用在自己的作品中,使他的流亡美学具有现代审美性的特征。因而“流亡美学”不是孤立的,它是西方现代审美结构的一个部分。
[关键词]乔伊斯;流亡美学;现代主义
引 言
1904年初,乔伊斯的流亡美学还只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以及他醉心的文字世界里。从1904年10月踏上流亡之路起,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乔伊斯十年的漂泊不定的生活并没有把他塑造成一位流亡艺术家。他反而为生存每日奔波,被贫穷、困苦的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这一切。乔伊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离开了意大利,来到了他真正向往的先进的欧洲大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先锋人物纷纷聚集到中立区的苏黎世,苏黎世成了非常时期的艺术家的摇篮。他们反对、厌恶、恐惧战争,逃离了战争中的祖国,却依然为艺术而疯狂。“苏黎世是个充满刺激的地方。希腊人、波兰人、德国人、受到良心号召的反对分子、艺术家、投机分子以及间谍,各种身份的人都聚集在这个城市,常常光顾孔雀餐厅(Pfauen Cafe)——乔伊斯自己也常常在此喝酒,凑巧得以听人述说‘未来主义’、‘立体主义’以及‘达达主义’等奇怪的理论。”[1]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一次的苏黎世之行,以及后来的巴黎之行,乔伊斯没有资格自称是一名流亡艺术家,他的流亡美学也不过是纸上谈兵,也不可能取得后来被美国人大肆吹捧的文学成绩。现代意义上的流亡者是时间与空间的支配者。乔伊斯通过与现代艺术观念的接触,不但使流亡的空间得到扩展,而且也使时间得到更充分的延伸。从1915年6月30日到1919年10月16日,在短短的四年多的时间里,乔伊斯不但了解了各种“奇怪”的新理论,而且也在苏黎世这个小小的空间内,接触到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度的艺术家。乔伊斯流亡的时间在向着空间延伸,空间又被赋予了时间性。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以及后来的超现实主义为乔伊斯的流亡美学注入了新的血液,使它摆脱了传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作线性的发展、随着空间的移位作机械的运动的流亡模式,也使流亡美学的形式更自由、更开放。
一、接触现代主义艺术
乔伊斯在1915年6月底来到苏黎世。对于力图创新、颠覆旧传统的艺术家来说,苏黎世是最合适不过的地方了。到乔伊斯1919年离开苏黎世时,他从这座城市中受益不少,他的开放性、破坏性和求新欲望都得到了加强。乔伊斯真正的文学创作活动可以说是在来到苏黎世之后才开始的。乔伊斯在冷眼旁观苏黎世的各领风骚的现代主义的革命活动时,也小心翼翼、谨慎细致地吸收和借鉴了他们的革命果实。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乔伊斯的命运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标志着乔伊斯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那些聚集在苏黎世的艺术家们转眼之间又来到了巴黎。乔伊斯也非常幸运地从战时的艺术家摇篮苏黎世来到了流亡艺术家梦寐以求的、真正的精神家园——巴黎。巴黎对于艺术家,就像利菲河之于都柏林人。“如果你想享受生活,你必须去巴黎”(Dubliners, 84)。尼采也早就指出了巴黎对艺术家的重要性。“作为艺人,一个人在欧洲除了巴黎便无家可归。瓦格纳艺术的前提,那五种艺术官能的精致,对于细微差别(nuances)的把握,心里的病态,只有在巴黎才能找到。任何别处都不会有对于形式问题的狂热,对于舞台调度(mise en scène)的认真——巴黎人的认真是卓越的(par excellence)。”[2]现代主义者在巴黎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新活动,乔伊斯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现代艺术的乳汁,他渐渐地去除了自己身上的乡土味,取而代之的是扑面而来的现代气味。经过苏黎世和巴黎的浸染,乔伊斯的流亡美学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乔伊斯一向时时刻刻、别有用心地进行着自我塑造、自我标榜。他小心翼翼、有条不紊地吸收着他人的革命性的创新手段,把它们转化成自己的“独创物”。虽然乔伊斯拒绝加入某一现代流派的队伍,但人们总能从他所谓的自创的文学手法中发现别人的影子。德莱克•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就曾指出:“乔伊斯非常擅长伪装他的灵感来源。”[3]在1920年7月15日,乔伊斯写给他弟弟斯坦尼斯劳斯的信中,就透露出了他对当前先锋人物和先锋运动的细心观察。乔伊斯在苏黎世结识的画家朋友弗兰克•巴津(Frank Budgen,1882 -1971)也曾确认乔伊斯在自己作品中所使用的各种从现代主义借鉴过来的手法,只不过乔伊斯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某一流派的狭小视野里,而是非常巧妙地综合了各家各派的实验手法。“在《尤利西斯》中,存在所有经验的痕迹,包括立体主义、未来主义、同存主义[simultaneism],达达主义,以及其他。”[4]不论乔伊斯如何擅长伪装自己,经过了苏黎世和巴黎的洗礼之后,乔伊斯的流亡精神已经不再只是体现艺术家的孤独与忧郁、浪荡与漂泊,而是与欧洲大陆上风起云涌的现代艺术革命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自此,乔伊斯的流亡美学也由对内容的关注而转向了对形式的追求。乔伊斯曾借萨缪尔•贝克特之口,说出了“内容即形式,形式即内容”的主张。由此可见,乔伊斯对当时流行趋势的把握是准确的,也是用心的,因为形式已经成为二十世纪初欧洲艺术界最关注的对象。
苏黎世和巴黎才是乔伊斯实践流亡美学的真正所在地。它们赋予乔伊斯流亡美学以新的形式,使它在遭遇现代主义运动时免于被清除的命运。
乔伊斯如果没有把现代艺术观念注入自己的流亡美学中,那么,他所梦想成为的流亡艺术家最终只不过是一个落伍守旧、愚昧陈腐。也就是说,乔伊斯在苏黎世和巴黎的经历是他艺术创作的转折点。1915 至1919年的苏黎世,以及1920年后的巴黎,不但是艺术家的摇篮,同时也是现代艺术观念的诞生地。乔伊斯不是这些新主义的创造者和发起者,而只是个旁观者。这也正如理查德•艾尔曼在斯坦尼斯劳斯的《哥哥的保管人》一书的序言中所指出的:乔伊斯才能的一部分就是盗用和剽窃,他的天赋是使材料变形,而不是发明一种新材料。[5]乔伊斯缺乏原创性,也不具备原创的能力,如果他没有在欧洲大陆上接触到现代主义运动,仅凭他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背景以及他个人的能力是无法开创一个文学新局面的,更不可能使他的流亡生涯得到质的转变。吸收与借鉴现代主义的各种手法不但使乔伊斯的文学创作走向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而且也增添了他的流亡美学的新质,使之得以呈现现代美学的特征。这一流亡美学的新特征正是通过《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这两部作品得以呈现的。
二、乔伊斯与现代艺术的联系
西方立体主义的出现表明二十世纪的西方现代艺术家无法忍受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美学原则,他们终于通过颠覆传统的方式以求创新。那些现代艺术家多数都是流亡艺术家,对那些流亡艺术家来说,必须借助在宗主国掀起一场革命的机会,才能改变自己局外人的命运和地位,在高贵、权威的官方和学院之外才能为自己卑微、暧昧的身份找到合理的栖息之地。在巴黎——这个世界艺术中心,流亡艺术家们都来到这块“宝地”,以次创造一个艺术的新天地,这也正是流亡艺术家们的用意所在。
立体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是一名流亡者。他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西班牙,来到巴黎从是他的立体主义艺术的探索,由此他对传统艺术的颠覆性和破坏性也就不是一件新鲜事了。毕加索认为,一幅画只有不断地被毁坏,才能更接近本质,加工的过程也就是毁坏的过程。他甚至声称:“学院派在美感上的训练是一种欺骗。我们被骗了,但被骗得如此巧妙,连真实的一点点影子都找不回来。”“美术馆只是一堆谎言而已,而以艺术为其事业的人大多数是骗子”。[6]毕加索的第一幅立体主义的作品《亚威农少女》(1907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是立体主义诞生的标志。它是解读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真正起点,所以,忽略《亚威农少女》就难以了解西方现代艺术的全貌。潘罗斯(Roland Penrose,1900-1985)曾这样评论:“《亚威农少女》这幅画完成后的十年中,艺术界发生了一次空前未有的革命……立体派一出现,它的影响就开始传播到其他艺术领域里。……这种影响必然具有深远的性质,因为立体派对艺术作用的基本概念提出了挑战。”[7]这是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带有某种夸张式写照。
立体主义对欧洲绘画的透视学、色彩学、明暗光影学以及解剖学进行了极大的颠覆。首先颠覆了西方传统绘画的空间概念,以此来证明绘画的形式与结构可以独立存在,而不是要去迎合视觉的真实,它以菱形、三角形等几何图形来重新组织绘画原则和人类的意象。由此开启了对空间和形式探索的新途径。立体主义逻辑发展的结果是拼贴(collage)的发明。把互不相关的东西偶然组合起来,造成了物体自身性质的改变,也迫使观者不得不对现实的解释发生转变,拼贴变成了一种戏语或隐喻。碎片加拼贴是流亡者的全部生活内容在变得扑朔迷离、变幻无常之后,艺术家为了表现自己的真实感受和审美体验所采取的一个极端的创作手法。立体主义使现代主义艺术家在历史的废墟与碎片中,重新建立起一个拼凑的、粘贴的、叠加的世界。
1913年,被毕加索尊称为立体主义教皇的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 1880-1918),不但出版了《美学沉思录——立体派画家》,并且还最先把立体主义的绘画技法引入诗歌创作,将立体主义的作品登载在自己创立的文学刊物中。同时,另一位美国先锋派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 (Gertrude Stein,1874-1946)也在小说中借鉴立体主义的创作手法。这些先于乔伊斯把立体主义引入文学的创作活动,扩大了立体主义的影响和话语,到1922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出版时,立体主义在艺术界的影响已经是威震四方了,乔伊斯便想到了借用立体主义的手法和影响的威力,以至于首版的《尤利西斯》封面竟用了一幅立体主义的作品,这证明乔伊斯不但在模仿和借鉴立体主义,甚至不惜把自己的独创之作附上一层立体主义的色彩,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乔伊斯的画家朋友弗兰克•巴津,认为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借鉴了立体主义。我们不难看到,流亡——不但为乔伊斯提供了接触和了解立体主体艺术的机会,而立体主义艺术还为他的流亡美学增添了新内容和新形式。乔伊斯的流亡美学在现代主义的艺术观念的影响下所发生的质的转变可以从他的艺术作品中得以印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乔伊斯曾受过非洲艺术的影响,他只承认欧洲才是他的精神父亲。当1907年《亚威农少女》问世的时候,乔伊斯还怀揣着欧洲陈旧的、传统的写作手法抒写着他的都柏林。当乔伊斯离开了爱尔兰之后,他才在呼吸到了现代主义艺术的革命气息。因此,流亡成为他接收当时的前卫、先锋等现代艺术观念和手法的基本前提。乔伊斯受到立体主义关于时间和空间观念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他的《为芬尼根守灵》中。看到他颠覆了小说传统的时空观念:“乔伊斯以《为芬尼根守灵》这部面目全新的小说,成为在字母文字的严格线性得到确立后又将其取消的第一个西方作家。它融诗与文为一体,解放了词法、语法和传统的拼写规则。他巧妙地运用一词多义的词语,使这些含义同时出现在读者面前。这种‘全伙在此’的表现,与也是被观者同时领受的多视点立体派绘画正可谓异曲同工,与指出观测者在相对论速度下可同时看到空间中不同地方的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中的视觉结果也相一致。”[8]同样,在他《尤利西斯》也使用了非线性的、多视点的写作手段,打破了传统的时间结构,叙述不是在线性的时间上沿一个方向进行,情节由一元转向了多元。 《尤利西斯》中也受立体主义拼贴的影响。乔伊斯在这部小说中拆解了以往叙事结构,人物的行动和思维称为碎片,这就迫使受众将这些碎片的事件进行拼凑,从而阅读作品的。这些小碎片就以拼贴的方式被错置、叠加、混放在一起,就是立体主义的瓶贴形式。碎片的处理实际上是时空的再重组,毕加索力图使绘画的空间时间化,而乔伊斯则努力使小说的时间空间化。乔伊斯挪用立体主义的现代美学观念,不但使他有驾驭时空的新自由,也是他的流亡美学在新的时空碎片中获得了现代主义意义。如果没有乔伊斯的流亡,可能就没有《尤利西斯》;没有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很可能还是保守的。正是由于立体主义的现代美学,乔伊斯的流亡美学才真正走向了现代。
同时我们还看到乔伊斯接受了未来主义的观念。1922年出版的《尤利西斯》书中藏书就有马里内蒂的作品,证明了乔伊斯对未来主义的关注。未来主义奉行动力主义(dynamism)的原则,强调现代都市是机器加速度的动感世界,它渗透到了雕塑、音乐、电影、建筑、文学等多个领域,充满了激进的色彩。《未来主义技术宣言》声称:“所有模仿的形式将受到蔑视,所有创新受到赞扬;反对善和和谐;艺术批评是无用的;‘疯子’的称号应该是荣誉的奖章。”[9]未来主义者同时也充满暴力倾向:“在枪林弹雨中呼啸而过的一辆汽车要比《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更为美丽”;“我们要拆毁博物馆、图书馆,与伦理主义、女权主义及所有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懦弱行为进行斗争。”[10]在未来主义者摧毁、砸碎的破坏活动中诞生了一种新的现代主义的美学原则。机器的轰隆声、齿轮有节奏的旋转声不但是美的,而且是现代精神的最好体现。乔伊斯在1915年来到苏黎世,接触到未来主义的思想观念,他迅速地模仿并产生了有效的作用。如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把未来主义的前卫主张运用到了语言的处理中,使他的流亡美学显现了未来主义的现代精神。《尤利西斯》的第七章“埃俄罗斯”(“Aeolus”)就体现了未来主义对工业之美的崇拜心理。乔伊斯极力展现他对未来主义技巧的巧妙运用和轻松自如的驾驭能力,使“埃俄罗斯”中的都柏林,在未来主义艺术的笼罩下充满了声响和气味。“埃俄罗斯”是机器的世界,是对都市化、工业化和高速度的赞美。都柏林的城市交通系统是发达、进步、文明的现代精神的体现。纵横交错、川流不息的双层电车和单层电车四通八达,由城市中心呈放射状向不同方向驶去。都柏林就在调度员的咆哮声、铃铛的叮铃铃声、车体的咣当咣当声,以及擦皮鞋的吆喝声中脱去了麻痹、瘫痪的外衣,转而散发出现代的工业气味。都柏林的邮政业也是繁忙的,“成袋成袋的挂号以及贴了邮票的函件、明信片、邮简和邮包,都乒啷乒啷地被扔上了车”(Ulysses, 7.17-8)。都柏林的商业更是欣欣向荣,“从亲王货栈里推出酒桶,滚在地上发出钝重的响声,又哐当哐当码在啤酒厂的平台货车上……发出一片钝重的咕咚咕咚声”(Ulysses, 7.21-3)。从都柏林报业的一个个排版车间和印刷车间里传来的噪音犹如现代交响乐。《自由人报》的机器是有节奏的,“以四分之三拍开动着。咣当,咣当,咣当”(Ulysses,7.101)。机器支配着整个都柏林,它的权威性和扩张性无处不在。“机器。倘若被卷了进去,就会碾成齑粉。如今支配着整个世界。他这部机器也起劲地开动着。就像这些机器一样,控制不住了,一片混乱。一个劲儿地干着,沸腾着”(Ulysses, 7.80-3)。乔伊斯描写的这种车间里的喧闹和沸腾与波菊尼的《街道进屋》一样,都试图打破视觉与听觉之间的界限,以文字和画面来达到声响的效果。
《尤利西斯》中弥漫着的“浓烈的油脂气味(Heavy greasy smell)”(Ulysses, 7.223-24)和“温吞吞的鳔胶气味(Lukewarm glue)”(Ulysses, 7.224)是乔伊斯文学作品中第一次出现的工业味道。正是这种工业味道散发着未来主义的气息。这和未来主义者钟爱的烟筒和由此冒出的浓烟同出一辙。《街道进屋》中灰滚滚的浓烟与湛蓝的天空形成强烈的对比。正是这种对比象征着未来主义者心中工业发达、物资繁盛的未来景象。
乔伊斯以未来主义美学原则审视爱尔兰,使爱尔兰呈现一个完全不同的面貌,这一前所未有的面貌反过来又影响乔伊斯的美学观。乔伊斯以这新的美学观来经营他的流亡美学。超现实主义者对理性、道德和意识的排斥,对梦和游戏的热衷,与其说解决的是生命的基本问题,不如说解决的是流亡艺术家如何扬长避短进行创作的问题。因为流亡艺术家,就像吉普赛人一样,通常是与非理性、无道德联系在一起的,而正统的学院派的知识阶层才有权言说理性和道德。可以说,超现实主义运动在潜移默化中宣扬着一种流亡者的艺术,它为流亡艺术家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乔伊斯的流亡也由此获得了美学意义,也为乔伊斯的美学思想也增添了新的内容。
超现实主义认为,无意识和无所不能的梦境,以及未加导向的思维活动才是现实的绝对真实。只有通过梦境,才能通往客观实在。无意识和梦境打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因果关系和逻辑联系,而“同步性”的创作手法就成为超现实主义者获取绝对真实的有效手段。同步性(Synchronicity)是“由C. 荣格首次明晰的概念,指两个互不相关的因素的冲突,在理性理解中产生一种不和,激发出无意识行为。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经常运用这一原理。”[9]同步性使一切原本不可能的皆成为可能,这就迫使观者必须做出改变。“超现实主义的荒谬联系和因果混乱,必然会向观者的空间观念与时间观念提出挑战。”[8]超现实主义的时空观颠覆了理性与逻辑的统治地位,在表面上温文尔雅、井然有序的现实之外建立起了一个变形、扭曲的新现实。
《芬尼根的守灵》是从夜晚开始,是关于梦和无意识的故事。其中的人物同样也首先被符号化了。从乔伊斯的手稿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部书几乎是从画一幅超现实主义的绘画开始的。没有预先设定的明确目标,也没有明确的主题,似乎是在一种无意识的情况下的自动涂抹。这是超现实主义者所主张的自动写作的具体体现。该书中的人物也是在人与动物之间不断地变形。“蚂蚁与蝈蝈”就是肖恩和谢姆的变体,同时又与伊索寓言的《狐狸与葡萄》相重叠,这些都象征着人与动物的二元世界的对立与融合,进而达到一个更真实的世界。《芬尼根的守灵》中的人物也同样被符号化了。倒立的字母E代表HCE、三角形代表ALP、∧代表肖恩、ㄈ代表谢姆,而长方形则代表该书的标题等等。[11]这与米罗的《哈里昆的狂欢》一样,构筑的都是超现实主义的世界。《芬尼根的守灵》中的人物不单具有多重的、分裂的人格,而且本身就充满了怪诞和离奇。主人公HCE在多个角色之间不停转换。他一会儿是亚当、汉普蒂•邓普蒂、撒旦、政治家帕内尔,一会儿是马可王、理查三世、诺亚、爱尔兰传说英雄菲恩•迈克尔等等,变幻多端、反复无常。这就如同《哈里昆》中的那一只眼睛。说它是一只眼睛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小生物也可以,或者仅仅是一个无生命的物体,哪一种解释都成立。这就是超现实主义者最钟爱的“视觉双关”(Visual Punning)。从视觉艺术的“双关”,到语言艺术的“双关”,超现实主义者找到了一条通往超级现实的途径。也许没有谁比流亡者更具有这种“双关”性了。超现实主义把流亡艺术家的身份、语言、知识的这种双重性提高到了一个更本质的地位,丰富了乔伊斯流亡美学的现代意义。
迪克兰•科博德(Declan Kiberd,1951-)认为:“乔伊斯的手法完全是超现实主义的(Joyce’s tactic is perfectly surrealist)。”[12]超现实主义打破了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无意识、梦与真的界限,曾经绝对对立的事物,在新的时空体里,随时都可能相交,而那些低俗的、不堪入目的细节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艺术的殿堂。在黑夜取代白昼,梦境取代实境,幻象取代真象成为整个时代的风尚之时,流亡者也在此种新的美学观的作用下,开始了新的艺术实验。他们创立的美学原则更多的是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并没有解决生活中的基本问题。因为超现实主义的世界毕竟是主观的,所有问题只是在幻想和梦境中得到了解释。这就免不了使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带有孩子气,表现在作品中就是所谓的“神话”精神。这种故作的天真和稚气虽然是进入潜意识和自动主义的最原始的心理构成要素,虽然代表着一种不受理性控制的解放,但却极端地限制了超现实主义者的创作活动。乔伊斯在完成《芬尼根》之后表示,他已经无话可说了。这也预示着乔伊斯的流亡美学在吸收先锋艺术的新观念之后也将随之走入困境。
结 语
以上我们分析了现代艺术观念与乔伊斯流亡美学的关系,如下图表。

①《尤利西斯》中的一部分是乔伊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苏黎世创作的。而此时的苏黎世只不过是临时代替巴黎执行战时艺术之都任务的。战争一结束,这些避难的各国艺术家们又迅速地回到了巴黎。而且,乔伊斯是在巴黎制定《尤利西斯》的计划表的,并根据此表对之前的部分进行了反复修改。《尤利西斯》最后的完成和出版均是在巴黎。
通过图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那些现代艺术观念的倡导者几乎无不是背井离乡的流亡者。他们是巴黎社会中的局外人、边缘人。以未来主义为例:未来主义者的发起者本来是意大利人,但他们不得不在艺术的中心巴黎发表他们的宣言,而且又不得不以法语为工具。这表明现代主义运动其实与居住在宗主国里的流亡艺术家有着某种程度的必然联系,同时也表明乔伊斯的流亡美学与现代主义运动之间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基础。简言之,艺术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其实是每一个想要在异国他乡成就梦想的流亡艺术家所必经的一条路。这说明乔伊斯的流亡美学既有个体性,也有整体性。它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时代相联系的。从时间上来看,乔伊斯从《尤利西斯》开始,对立体主义等现代手法的吸收和借鉴也是清楚明了的。可以说,正是在此借鉴基础之上,乔伊斯的流亡美学才完成了向现代的转换。这已通过对乔伊斯最后两部作品的分析得到了证实。
参考文献:
[1][爱尔兰]艾德娜·欧伯莲. 永远的都柏林人——乔伊斯的流幻之旅[M].陈荣彬,译.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3:166.
[2][德]尼采. 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M].周国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340.
[3]Derek Attridg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ames Joyce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268.
[4]Frank Budgen. James Joyce and the Making of Ulysses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198.
[5]Stanislaus Joyce. My Brother’s Keeper: James Joyce’s Early Years [M]. New York and Toronto: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4: xv.
[6][西]毕加索. 现代艺术大师论艺术[M].常宁生,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0-52.
[7][英]罗兰特·潘罗斯. 毕加索:生平与创作[M].周国珍,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55-157.
[8][美]伦纳德·史莱因. 艺术与物理学[M].暴永宁,吴伯泽,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355. 260
[9][美]约翰·基西克. 理解艺术[M].水平,朱军,译.海南:海南出版社,2003:401,492. 492.
[10][法]P·勒·托雷尔—达维奥. 现代艺术家词典[M].刘常津,译.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06:308.
[11]结城英雄『ジョイスを読む:二十世纪最大の言葉の魔術師』[M].東京:集英社,2004:159.
[12] Declan Kiberd. Irish Classics [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477.
(责任编辑:吕少卿)
李倍雷(1960-),男,重庆人,东南大学艺术学院艺术理论系系主任,教授、博导,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从事艺术理论研究与艺术创作。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16)02-0093-05
收稿日期:2015-10-20
作者简介:赫 云(1971-),女,黑龙江人,东南大学艺术学院艺术理论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艺术学、比较文学。
项目基金:①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乔伊斯流亡美学研究”(11YJC752006)。